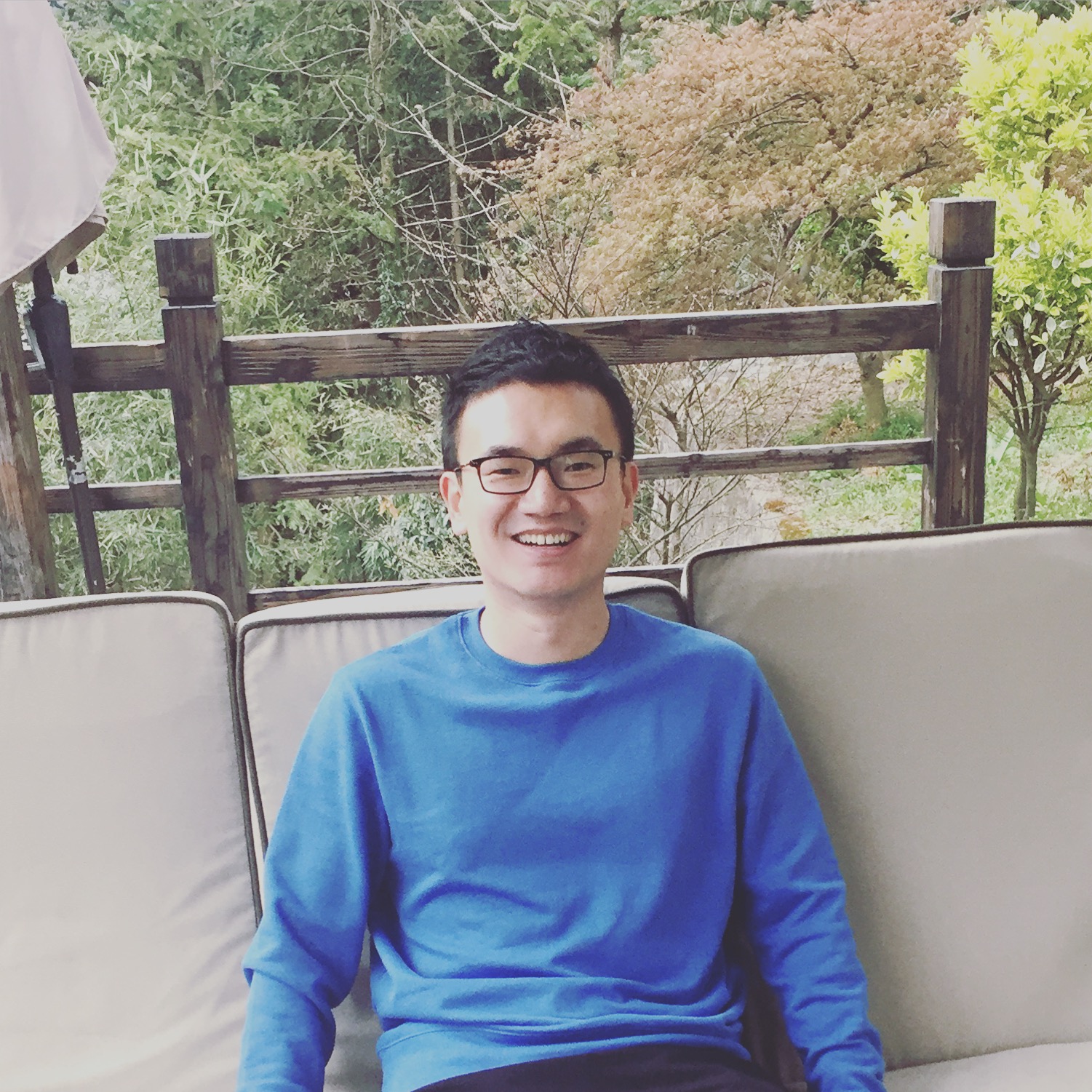广告公司一般说来是没有什么淡季和旺季的,一年忙到头,天天加班,干3年累得像别的行业干30年。肯吃苦,脑子活络的年轻人容易在这里完成职业生涯的起步,但到了职业生涯的中段,他们常常会离开这个行当,能熬下来,做到赵林这个职位的,少之又少。赵林记得自己刚入行的时候,全公司一百多个新人AE,分散在各业务条线,开始吵吵闹闹称兄道弟,渐渐又从窃窃私语到鸦雀无声。人来人又往,不过四五年光景,那些奇奇怪怪的年轻人多数在本行业已不知所终。公司里认识的朋友,能进入自己日常生活的是大浪淘沙。赵林时常因此有一种明确的沧海桑田感。
大型广告公司里的生态很有趣,一般来说,是业务部门先导,靠关系和服务打头阵;然后针对客户需求做文字、图片、视频,IT等各类定向开发,最喜欢谈创意和创新,却受制于需求无法彻底,一腔理想常常沦为糊壁头;优点是现金流好,利润率高,除了人一般没有什么别的硬成本,所以架构流程往往是虚的,人与人的关系才是真正理解这类公司的关键。加班多,同事相处时间就多;整合营销多,跨部门交流就多;喝酒唱歌多,趁乱交心摸大腿就更多。表面上一个部门的人,可能貌合神离,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却可能因为楼梯间同抽过一支烟成了好朋友;人事部的女总监可能爱上过IT部的架构师;客户部的AE可能睡过老板的司机,今天法务部Frank的老婆上公司抓小三;明天COO突然跟大胸前台闪婚……过去赵林常常因这些消息而愕然,认为业务都这么忙了,怎么这些人还有空搞这个?等到自己渐渐做到5年、8年,12年,15年……这些事有时也发生在他身上了,他才渐渐理解那些藏在西装、领带、衬裙、小礼服底下的,被压力和欲望折磨的,躁动的灵魂。如今,不论他们吵架骂人,情绪崩溃,或是搬着箱子突然滚蛋,他都能泰然处之。他大学学的是中文,辅修传播学课程,他笃信人心是万事之本。
WH公司每年会固定在第三季度搞一次时长一周的,半玩半培训的半年度年会,一般来说,是不许缺席的。为什么是第三季度呢?因为第一、四季度是比稿期,第二季度是新项目执行启动期,如果一定要选个可供喘息的季度,一般是第三季度。第三季度,就是广告狗们的玫瑰季。第一类公司,是最轻松的,他们的员工会在这段时间把年假用掉,结伴去海边拍朋友圈啦,到丽江和西藏失身啦,到伦敦去喂鸽子和大象啦,凡此种种;第二类公司,是比较纠结的,他们自诩福利好,可纯给员工放假去玩,老板又不舍得,因此就会搞出这种半玩半培训的怪胎;第三类公司最苦逼,他们的员工在第三季度得到的福利往往是:“居然能有几天可以按时下班。”“我完全没有见过6点钟的夕阳呢。”“这个时间从公司出来居然心里有点慌,公司是不是业务不好了。”“是啊,我下班居然不知道该去干吗。”(而且他们的员工看到这里会说,开玩笑,这个行业哪里有第一类和第二类公司)。WH公司则常年在第二类和第三类之间徘徊。
全公司员工喜迎半年会的当口,赵林却病倒了。他浑身酸痛,一直低烧,他在心里忐忑这是不是和脑袋里的东西有关,但又打定主意不想告诉陈微微。陈微微陪着他去医院检查,量体温,抽血,他一直挺紧张。后来拿着检查结果去找医生,他不想让陈微微进医生房间,但陈微微还是跟了过去。不过,那个中年男医生看看他们俩,只是冷冷地说了一句,年纪不小了,以后生活检点一些,夫妻生活适度为宜。赵林自己拿着单子看,体温不高,37度5,血液有几个指标超高,也不知道医生怎么看出来的。他没在意医生说的话,只是心里松了一口气,觉得不是肿瘤恶化就好。倒是陈微微红着脸说,听见没,你以后节制点。他点点头没说话。接下来他要吊盐水,陈微微打算一个人去半年会。尽管觉得自己很需要人陪,但是赵林觉得对着陈微微压力山大,只盼她快走。
陈微微走后第二天,他的烧就退了,身上也不疼了。这期间,陈微微和他没有任何联系。他回到自己松江的小房子里,打电话给何妮妮,何妮妮现在还在西餐馆混着,日常不忙,就答应来松江看他。他们碰面以后,赵林说不想在上海呆着。何妮妮说,你不是生病吗?不能好好休息一下吗?赵林说,那个房子里全是陈微微,这个房子里全是叶小枚,我觉得自己都没法呆下去。何妮妮叹口气,答应了。
何妮妮之前和日本男友去过一次莫干山裸心谷,说那里挺好,就建议赵林去那里,赵林答应下来。裸心谷离上海不算近,路也不好走,高速上是何妮妮开,进山以后,换了赵林。何妮妮一路挺开心,赵林则兴致不高。说实话裸心谷真挺美的,胜过他之前去过的周边任何一个景区,可他病后初愈又心神不宁,对景致提不起什么兴趣。不过入住后,他觉得客房宽敞,景观也好,就打定主意泡在这里,不再出去。
裸心谷房价挺高,一晚得2400,赵林和何妮妮只开了一间房,订了3天,赵林想全部自己出,何妮妮坚持分担了一半。两人睡下的第一晚,赵林梦见的还是跟陈微微马拉松。要知道在现实中他从来没有跑过这东西,他觉得单纯的跑步又无聊又傻。他也没有去过马拉松现场,只见过一些零星的报道图片。所以他的梦中只有一条漫长而昏暗的公路,根本不知道是哪里。只有他踉跄着跑,身边是黑压压的没有脸的人群,他胸前挂有一个数字很大的号码牌,他望向前方,能看到陈微微穿一身鲜艳的运动服,身姿矫健,体能充沛,在前一个阵营领跑,于是他开始觉得自己衰老,缺氧,双腿也不听使唤……可突然一晃神,他又发现自己是在出中学时的早操,原来边上黑压压的都是高中同学,而陈微微变成了督导晨跑的体育委员,那时,他们这些高中生,要在早上6点开始绕全城跑一圈,每天如此……但他怎么也追不上陈微微,他觉得自己心里难受。崩溃到快要跪倒的时候,他醒了,发现自己浑身是汗,被何妮妮从背后紧紧贴住,轻轻摇晃。何妮妮的双乳贴着他的背,她是热的,希望给冰冷的赵林一点温暖。
老板,我把你推醒的,你做噩梦了?
嗯。
你在床上一下一下地抽搐,把我吓死了。
对不起。
不要说对不起,你梦见了什么,想说吗?
不想。
嗯。
赵林有点闷,推开何妮妮,自己起来去洗手间。他没有开灯,回来后跟何妮妮说,你先睡吧,我去透口气。然后披着浴袍上了阳台。阳台外面对着一片绿色的山峦,除此之外再无他物,真有一种世外桃源之感,他望着这一大片绿,呼吸着新鲜空气,人渐渐地不再气闷。可他心里仍旧觉得没劲透了。觉得想死。阳台的木头桌子上摆着一个烟灰缸,烟灰缸边上有个糖果盒,里面是“宝路”薄荷糖,他拣了一个,含进嘴里,闭上眼,不断地深呼吸,希望能摆脱这种情绪。
大约又过了一会儿,何妮妮披着另一条浴巾也走了出来。她看看赵林,轻轻地说,进去吧,这样太凉了,你病刚好,复发了就麻烦了。赵林叹了口气,跟着她又进了房间。何妮妮说,你别总是唉声叹气了,叹得我也心情不好起来,这样有意思吗?有什么过不去的?赵林说,对不起,不是故意要叹的,那我注意一下。说完他躺了下来。何妮妮没有说话,过来一会儿,她靠过来抱着赵林,紧紧贴住他。贴了会儿,赵林身上渐渐暖和起来,于是他扭过来开始吻何妮妮,把手贴在何妮妮背上,觉得何妮妮热得简直有点烫手。吻了一会儿,何妮妮让他躺好,自己在上面,但赵林进去没多久就射了。他默默地说,对不起。何妮妮说,没事,我就是想安慰安慰你。赵林说,谢谢。何妮妮说,你可以轻松一点的。赵林说,好。
他们又睡了一会儿醒过来,躺在床上聊天。
妮妮,贾老师借你的钱还了吗?
没有。
那怎么办?
不知道,要不回来就算了。
你和男朋友怎么样?
还行吧。
不觉得外国人没法交流?
不会,他中文还行,不过我们通常用日语交流……为什么问这个。
没,觉得一直麻烦你陪我,不知道他会不会不开心。
他回日本了,我最近没事儿。
你喜欢他吗?
还行吧。
他回日本多久?
估计要一段时间。他回去说跟前女友谈分手。
什么情况?
嗯,一直没断干净吧。有一次我在他家,他早上接个电话,那女的打来的吧,就在哭什么的。他后来表示很不好意思,我心里有点乱,就起来走了。后来他就说,他还是回日本一趟,把事情处理处理干净。
你生气吗?
不生气。他和前女友得有十年了吧,我没法生气。
就跟你和贾老师差不多。
这种长期关系都很伤的。
是的……你干吗又蹭我。
前面那会儿太难受了,现在好些了,我回馈你一下。
啊,老板你不要回馈上瘾啊,要出事情的……
唔。
赵林跟何妮妮在床上赖到了下午,两个人都觉得饥肠辘辘,但又不想出门,就在房间里叫了些吃的。吃完之后,他们开着电脑看美剧,就这么把一天消耗殆尽。赵林觉得和妮妮的关系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轻松感,他们都很随意,也不怕得罪对方,没有话题和行为的禁忌,即使互相嘲讽,也不会生气。在裸心谷过了3天之后,他们回到上海。
何妮妮开车把他送到他家楼下,说,我就不上去了。赵林说,好。回到自己家,身边突然一个人也没有了,他又开始难受,最后他坐在电脑前面,开始给陈微微写邮件,说希望可以跟她分手。他坐在屏幕前面,想着过去跟陈微微之间的点点滴滴,邮件越来越长,不禁哭了起来,哭完以后,他把邮件发了出去。等到晚上的时候,陈微微给他回了邮件,只有一个字“好”。他再次回邮件给陈微微,说这两天他会去她的小房子把他的东西全部搬走。陈微微没有再回给他。他到厨房里拿出冰箱里冻着的日本酒,喝完一大瓶,沉沉睡去。
第二天,赵林叫了一个大众的货车,去陈微微家搬东西,在他的意识中,觉得自己和陈微微有很多共有的东西,然后收拾了半天,最后还是只有俩箱子和一个蛇皮袋。货车司机看着他那点东西,说,就这么点啊?他点点头,司机没再说话。回松江的路上,他给何妮妮打了个电话,说,我跟陈微微分手了,她也答应了。何妮妮说,啊?这么快?前不都见家长了吗?怎么又分手了?赵林说,这次是我提出的,就是从裸心谷回来以后,这次应该是分彻底了,我刚从她家把东西搬了出来。何妮妮说,她知道你的病吗?赵林说,不知道,不能告诉她的,按她的性格,告诉她她要看不起我的。况且现在分手了,就更不用说了。何妮妮说,不是因为我吧?赵林说,你不要自作多情。是我自己觉得应该跟她分手,跟你没关系。何妮妮在电话里笑,说,分了也好,上次你见她父母,我还在想,你居然还能有兴趣把结婚的那个套路再走一遍,也是蛮不容易的……赵林也在电话里假笑了几声,说,哈哈,想到不用再走那个套路,不禁心头一片轻松。何妮妮说,那你接下来什么打算啊?赵林说,什么打算?没什么打算,就这么过下去啊。何妮妮说,那就好。赵林想说点什么,但终于没说出来。
半年会结束后第一天,赵林也回公司上班了。一进公司的大门,他就习惯性地望向陈微微的位子,她在。过去在公司里遇到,陈微微会和赵林交换一下眼神,即使是冷漠的眼神,但今天,赵林走过去,看看她,她眉头紧皱,连头都没有抬。赵林心头一痛,深吸一口气,没有停顿地走了过去。明明是他提的分手,但他感觉像是自己被甩了。他想起去年这个时候,他们已经在准备去广州了,即将挖空心思地瞒着同事找机会上床;而今年,他们已经变成形同陌路的样子。但现实并没有给赵林太多时间伤感,假期之后的返工期总是非常的忙碌,很多搁置的事情要启动,要处理,而且压力很大。投身工作以后,赵林会暂时忘记自己情感上的这些问题,然而,晚上一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他还是会有点崩溃。松江离市区挺远,他又经常加班赶不上地铁,于是他花钱买了一辆小汽车。他原先在北京的车子给叶小枚了,但叶小枚不会开车,也不知道她怎么处理的。从WH公司开车到松江的小家大约要一个小时,在路上赵林听过电台,听过脱口秀,也放过一些流行音乐,但后来他固定在了郭德纲相声精选和古典音乐上。前一个东西像糖,能让他挡一挡心里的苦,后一个东西像水,能帮他稀释烦恼。现在,只有这俩东西能占住他的脑子,让他没空去难受。
从那个电话之后,赵林也没有再去找何妮妮,他希望自己能够靠自身的力量走出阴霾。他把时间都花在了工作上。周末,除去案头的部分,他也去市区走一走客户关系。女客户,他一般约她们在市区的五星酒店里下午茶,或者去西餐厅喝咖啡,顺便谈一谈业务,也了解第一线员工的服务情况,这倒还好,是他可以轻松应对的部分;问题是那些男客户们,他们在吃饭过后,往往热衷于去夜总会,过去赵林心里不是很愿意奉陪此类事宜,都是能避则避,或一概推给大老板去应酬,即使不得不去,也常常神游物外。但现在,他仿佛想通了,也彻底放开了,他开始主动陪着大老板出入这些场所,费心应酬,喝酒,耐心地跟小姐玩筛子,摸她们的乳房和大腿。大老板挺开心,喝醉了跟他说,对嘛,我就觉得你应该多出来玩玩,我晓得你是业务第一线出身,专业度高,但是你毕竟做管理也这么多年了,你现在在这个位子上嘛,人,就应该像水一样,你要融入你的角色……他没有说话,但从此大老板每次去应酬都会叫他了。
某种程度上说,夜总会里面的情形也常常让赵林觉得有趣。职场就是角色扮演游戏,每个角色都被分配了自己的任务,演久了,角色的特性就会带进自己生活的方方面面。来夜总会的,都是大老板和大客户,都是年龄在40岁往上的管理层。这些人在夜总会里都喜欢跟小姐说教。过去赵林常想,在夜总会里跟人有什么好聊的?除了美色,这些女人究竟有什么魅力呢?现在他发现,除了拼酒和唱歌,老板们多数都是拉着小姐的手,跟她们讲人生的道理。有些东西,跟他们在公司里跟普通员工说的,也并无差别,比如“要努力,我也是熬了很多苦日子才走到今天的“,“要感恩,这世上没什么事应该的,一定要记得老板对你的好”,“要舍得,你先舍才会有得,不放弃,你就不会得到”之类的东西。而这些陪酒的小姐,也并非全部都是敷衍,她们常常白日里有像样的职业,也应对得颇为巧妙,甚至超过WH公司的一些员工。其间有一个小姐,在和WH的大老板聊得久了以后,竟然某日到了公司报到上班,这让赵林颇为吃惊。这个叫Tracy的姑娘,尽管把妆容改淡了,衣着也调整了,但她还是太漂亮,一进来就引起了围观。Tracy,中文名字张梦露,她在WH的经历可以用“不虚此行”来形容,她泼辣,大胆,作风坚韧,虽然专业面近乎没有,却能靠着三寸不烂之舌指东打西,一开始,她被放在一个不重要的业务线,居然成功把一个烂稿子强卖给了A客户市场部,后来她侃晕了B客户的采购,多提升了15%的利润率;再后来,她居然和C客户大老板的女秘书成了闺蜜,然后成功切了一块颇具战略意义但她自己一毛钱也不懂的业务回来……她很快就因为表现出色荣升总监,而与之伴随的则是她把团队所有男同事都睡了一遍的传闻……赵林是内部唯一知道她底细的人,大老板专门做过叮嘱,他缄口不言,和Tracy敬而远之。
赵林也在办公室尽量避免与陈微微来往,但后来发现陈微微应对颇为自然。他觉得自己也是多心,于是二人的关系渐渐正常化。但有时望着这个被他看过全身所有细节的美好的姑娘,他心头还是会一阵酸楚。然而这种念头他也只是想想,他知道这是不适宜的。按陈微微的性格,根本不会介意与他的这些肉体关系如何深刻,或者于她而言也许根本就谈不上深刻。在这段爱情中——如果这是爱情的话,赵林更像一般意义上的女性,是他疑神疑鬼地查手机,纠结于爱和不爱,是他哭闹折腾,心里循环往复,而陈微微反倒处理得干脆利落,情绪思路都硬质清爽,行为合理得当,根本没有可以诟病的地方。简直像个成熟稳定的大叔。这种想法暗地里让他的自尊心受到了更大的挫折,原本他唯一的心理优势是“毕竟分手是我提的”,但陈微微在分手后的做派让他这种心理优势摇摇欲坠。他们的关系就像没有存在过一样,已经在虚空中消失得毫无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