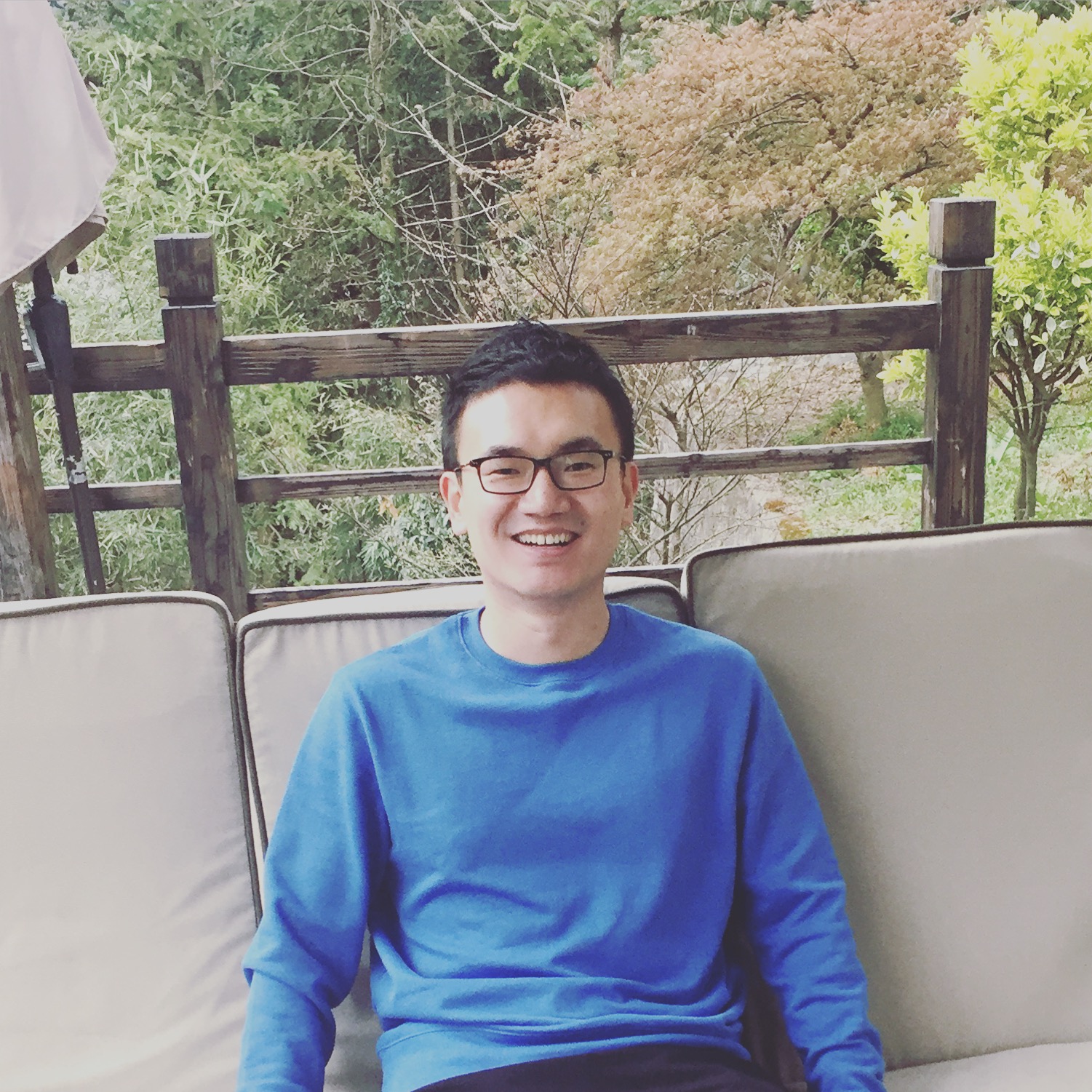赵林不跟毕可文(或者叫贾斯汀)联系很久了。也不想再提他的事。最早,赵林只是拿他的事当段子,和小姑娘吃饭时说说,希望引起小姑娘们对自己的兴趣。然而最终小姑娘们却都只想认识毕可文。这让赵林不是很高兴。
后来有天赵林和一个特别漂亮的姑娘聊天,说high了。姑娘走后,他突然萌发了把这些段子写下来的念头。赵林一直爱写点什么。过去写博客,写豆瓣,现在写微博,写朋友圈,虽然没有写出什么大名堂,但他自己挺得意。他靠着写点什么来装点自己并不美妙的生活。后来这个故事竟然发表了——就是前面的序章,发表在一个网络杂志上面。但反响很一般。除了不喜欢,甚至还有人谩骂他。读者们觉得这个故事没头没尾,三观不正,说他写着写着就开始瞎编。但其实这些都是事实。由于缺乏想象力,有些场景,连对话他都没改,自己读着都像原音重现。读者骂他,他又气又糊涂,大约不应该没有经过文学处理就发表?但文学处理到底应该是什么?是虚构或者掩饰?把A或B做的事情改改串串?就真是如此又有什么问题呢?需要为尊者讳吗?赵林从来没有把这些想清楚过。
杂志编辑七姐是赵林的伯乐,一直安慰他,说:“网友可能过于年轻了,你写得还不错,起码我喜欢。”
年轻不是挺好?赵林今年35岁了,常常想讨年轻小姑娘的喜欢而不得。他觉得自己大概已经过时,他很失望。不过这两年很多事都让他失望,他也习惯了。
他和七姐聊天,说我朋友里真有这么一人,还给她看了一眼毕可文的帅照。七姐劝他,你要么把这个人的故事多写一点出来?赵林嘴上答应着,但日子一天天过着,他也并没有当回事情。毕竟那个网络杂志的稿费也不高,赵林当时收入还不错,他并不着急。
赵林真正动心去认真写这些东西是在最近了。现在他已经没什么好干的了。他辞了工作。也没什么朋友。他好像开始意识到自己过去在生活中曾犯下无法弥补的错误,他觉得痛苦与悔恨每天都在吞噬他对生命的期望。那段时间他静下来在家里认真看了不少书,都是看过去的旧书。他买了不少世界名著,但真看完的没有几本。悔恨推动着他,他一个字一个字地看《情人》,《包法利夫人》,《百年孤独》,《青春》,《耻》,《战争与和平》……最后他觉得自己最喜欢的是辛格的《卢布林的魔术师》。因为他在主角雅夏的经历中找到了自己的影子,他想象着像雅夏那样自我囚禁,但现代社会已经没有近代波兰的那种犹太教生活体制,他也想过隐居,出家或者信教,但又都不得其门而入,他热衷了一段时间自我惩罚的手段,但都觉得逼格不够,也无法彻底获得安慰。中国社会留给他这种自我放逐者的选择很少,他觉得自己活着耗水耗电,徒添麻烦,最后想要么还是等死算了。
但就算有了这个想法以后,赵林也并没有豁然开朗。因为近年来,大约由于老了,智力减退,脑里常常一团糨糊无法思考。他想死,但也不想马上死,他能去哪儿?他到底应该怎么办?但他智力着实不高,想一会儿,便会忘记之前想的。再加上痛苦,他的脑中已无任何坚实之物,念头总是刚刚聚合又瞬间崩塌,像夜空中的黑鸟。最后只剩下一个笨办法:像小时候求证明题那样,他把想到的一些记述下来,写写,想想,凡事都把来处归置清楚,然后决定让这些落笔之物决定他何去何从。
赵林跟别人说毕可文的段子,都是说毕可文睡姑娘的事。他自己姑娘睡得少,但很爱说毕的八卦。这让他觉得自己很不好,但这却又是事实。自小打开窍起,赵林见了色情的东西就走不动路。他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正常。他也观察别人,但并不能确定别人是不是和他完全一样。但他不傻,知道自己不能把欲望挂在嘴上,也不要让别人,尤其是女生觉得自己猥琐。因此,很小的时候他就学会了自我矫饰。走上社会,人们都说他看起来很正气,像翩翩君子。赵林自己挺得意。但这话的另一个意思是,他有一张不令人产生欲望的,不怎么好看而且平庸的脸。
在赵林和毕可文这代青年的成长阶段,社会风气保守,女性的欲望是含蓄而内敛的,它不像男性欲望那么有攻击性,所以他们并不明白它如何运转。色情片中与文艺作品中对此的描述往往流于表面,也没有真正的指导意义。在赵林有性经历之初,也仍旧觉得不甚了解。究其原因,还是要归因于他过于平庸。
赵林对女性欲望的洞察力,要等他彻底成年,才渐渐养成。那时,他已经和叶小枚同居在一起,有了稳定的性生活。而在这之前,他常常要花费很多精力和金钱才能骗到一个比他小上三四岁的,更懵懂的女孩。她们对自己的欲望尚一无所知,彼此之间的互动往往就更糟得没边。
毕可文比他要幸运得多。他长得很秀气,骨骼不大,手脚修长,虽然不是很强壮,却有着匀称的比例。更重要的是,他的五官很精致,细长的单眼皮,有一点像日本影星浅野忠信,表情慵懒随意,挂着一丝略带讥嘲的微笑。他很白,脸上还有淡淡的雀斑,这没有给他减分,反而陡添几丝洋气。他有一看就是个聪明孩子的生动面貌。有些男生会觉得他欠揍,但多数时候他都讨女生喜欢。在刚进青春期的时候,毕可文就意识到了自己的优势。女生们把他评为班草,没谁看到他不脸红的。跟他传绯闻的姑娘,会变成校园明星。他早就可以睥睨同龄的姑娘了。才上初二,他已经能轻而易举地获取高二、高三学姐们的青睐。其实不止高年级的男生会到低年级“选拔”漂亮学妹。高年级的女生也会这么做,但不普遍,且前提是,这个男生真的非常特别。比如毕可文,他一年一个样子地成长着,而且没有长歪,在十七岁生日当天,当时的女朋友,一个高四复读班的女生把自己当做礼物送给了他。
毕可文和赵林这样的人,本不会成为朋友,毕竟他们在食物链中所处的位置差距太大。恋爱就像打猎,赵林在屡战屡败中已经懂得,要离毕可文这样的小白脸远一点,免得自己什么猎物也打不到。毕可文则要随意一些:他眼里根本就没有赵林这类人,他忙着处理粘在自己手上的猎物都来不及。
他们的认识是因为何妮妮。何妮妮是赵林的同事,他们在同一家广告公司上班,赵林是78年的,何妮妮是86年的,毕可文是82年的。赵林是何妮妮的领导。后来何妮妮把自己的闺蜜叶小枚介绍给了赵林做女朋友。然后很自然的,赵林也认识了毕可文,赵林按广告公司的风气叫毕可文Jusitin,或者贾老师,毕可文叫赵林“老赵”或者“赵总”。
一开始,两对男女还搞一些四人约会,后来因为兴趣点的关系,常常会变成俩男人一起聊天,俩女人一起逛街。赵林和毕可文喜欢去北京西路一个日料店。这日料店就在赵林公司附近。这日料店是上海很常见的一种,以一个日本姓氏做店名,叫“大仓”。大仓在市区只有两家分店。店主是个中年男子,很有腔调,瘦瘦高高的,常年穿T恤和牛仔裤,留莫西干短发。他早年在日本打拼,娶了日本老婆,35岁回上海,开了这家店。大仓的店面不油不腻,窗明几净,趴在上面不用忧虑袖管污染,卖的东西价格适中,制作考究,口味也优良。店主谭老板总是心情很好地在店里晃荡,补服务员的位,跟客人恰到好处地聊天,协助收银……他能记住每一个客人,能在客人下一次前来之时马上叫出对方的姓氏,并投以“您今天又来了”的熟人目光。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不论盛夏还是严冬,这家店卖的干姜水总是非常好喝。干姜水是进口罐装品牌里优选的,那种屈臣氏之类的货色早早就被剔除。再配以冻过的杯子,晶亮的食用冰块,有沁人心脾的效果。一口下去,让人觉得灵魂都要直立行走。
赵林和毕可文都喜欢喝这家的干姜水。一个冬天的午后,何妮妮和叶小枚去做脸了,赵林和毕可文则钻在大仓,享受着暖气,喝着冰干姜水,吃盐水毛豆,芥末章鱼和烤银杏。
那不是他们第一次聊天,但却是聊得比较深入的一次。一开始两人在说吃,然后才辐射到其他,他们互相分享新知,也建立了不少共识。类似午餐肉要下火锅煮才最好吃,可口可乐要易拉罐装的才能喝,色彩或者设计复杂的衣服最好不要买,新买来的东西要细细地把标签完整剥掉……诸如此类。以前赵林没啥自信,觉得自己一个男人关注这些挺娘,但和毕可文一交换意见,有一种找到同类之感,于是重新建立了自信。而毕可文觉得这个大哥,或者说“长者”还挺真诚挺健谈,同时他觉得跟赵林维持一个良好的关系会有利于何妮妮的工作,因为也颇为主动。
再后来,俩女人来电话,说脸做完了还想做个身体,于是两人接着聊。最后,就开始交换性史。首先是扳着指头比数量,赵林输得北都找不到。接着比离奇程度,赵林又是瞠目结舌。他三观尽碎,只好俯首称臣,把舞台让给毕可文,让他一个人唱独角戏。毕可文讲的故事里,令赵林印象最深的是“虹口道场狡兔少女”的故事。这个狡兔少女也是来自交谈中赵林的一句感叹,当时他脱口而出一句“这姑娘他妈的简直狡兔三窟嘛”。
那是毕可文刚毕业时的事情了。毕可文是南京人,毕业了打算留在上海。但他打定主意不想过那种天天坐班的生活。他想通过做自由摄影师来养活自己。他自降为本科生起薪要求,跑到影视公司做摄影助理,跟着摄影师当学徒。这个选择很有魄力。当时他去的那个影视公司在虹口,他就自己租了个小房子在虹口足球场边上。摄影助理这个活儿,出勤一次给300块每天,就是个现场服务员,开工的时候没日没夜,不开工的时候闲得蛋疼。
在闲得蛋疼的某日里,毕可文晃荡着,和其他三个大学同学一起去凯旋路育音堂看摇滚乐队演出。演出开始前,四个人穿着皮夹克,在凯旋路口的斑马线上模仿披头士,然后顺手拉一个路过的女孩儿帮他们拍照(后来赵林去他家,他还给赵林看了电脑里的这张老照片,上面只有四个城乡结合部F4,离披头士十万光年)。
演出开始后,他们发现台上那个换了网袜皮裙风情万种的女主唱就是拍照的姑娘。四个人乐了,思量一番,在演出间隙,壮着胆子一起去套近乎要电话号码,姑娘也挺大方直爽,大声就报出来了。四人存好号码都给姑娘发了消息,然后兴冲冲地分头回家了。毕可文应该是唯一一个没有马上联系姑娘的人。他没有在中国和中东都很常见的,青春期性交不充分综合征,他并不着急。这要换了赵林,肯定就是穷追猛打的节奏。
但当晚毕可文看完演出,在家楼下吃夜宵的时候,姑娘突然给他发了个消息:“你在吃夜宵啊?”毕可文吓了一跳,一回头,看见了背后不远处的主唱姑娘。姑娘正咧着嘴笑:“你也住这儿吗?”
这就是传说中的有缘千里来相会。姑娘说,来要联系方式的人多了,但要了联系方式过了一个小时在家门口碰见的,你是唯一一个,毕竟上海这么大。毕可文也懵了,这不睡简直对不起老天。于是两人心照不宣地饭吃了一半就回了。头一晚在毕可文家,后面一晚在姑娘家。开始也就是搞搞床上的花样,后来翻新了。
姑娘有天晚上一进门,没脱衣服,先拿出一把钥匙,说:“今天我姐不在家,我们去她家玩。”
毕可文没想到还有这福利,于是两人心急火燎地出了门。在凌晨的大连西路上一通走。
赵林插嘴问,这么急还走着去啊?毕可文说,打不到车,太晚了。
凌晨出来外面天有点冷,但所幸当时尚是初秋,也不至于太过分。昏黄的路灯下,黄叶落了一地,毕可文和姑娘紧紧依偎着走。毕可文感叹说,太美了,那个夜晚。姑娘也特别好看。他看看一脸羡慕的赵林,又说,虹口的晚上和白天就是不一样,有一种很神奇的光线和气氛,我给她拍了不少照片,可是后来都没有了。
姑娘的姐姐是个护士,那晚值夜班去了。姑娘说,我姐姐急着嫁人呢。毕可文说,是吧,那她去相亲吗?姑娘说,相亲能相到什么好的。毕可文不说话。姑娘说,要么我把你介绍给我姐姐吧,你和她结婚,当我姐夫好了。毕可文还是笑笑不说话。姑娘哼一声不理他。毕可文想想又说,那你把你姐姐照片给我看。姑娘说,一会儿她家里有。
最后两人拐进欧阳路一个小区,灯都没开,在姐姐家的沙发上,先挥洒了一记青春。然后姑娘光着腿起来,去写字台上拿姐姐照片,毕可文躺在沙发上,看姑娘细细的小腿,边看边抽烟。姑娘腿一踢说,禽兽,不要把烟灰弹在沙发上。
姐姐没有姑娘好看,也略有些丰满。姑娘看看毕可文的表情说,我姐姐皮肤好,胸很大。毕可文不说话。姑娘说,你不会真看上我姐姐了吧?毕可文笑,姑娘打他。两人转战到卧室。
下楼以后,路面上是凌晨出摊的黑暗料理。两人抽光了荷尔蒙,坐在冷风里,喝馄饨。但是好开心。真的好开心。毕可文说。当时觉得有点难过,但现在想想,还是开心的。
赵林问,我靠,这多开心啊,为什么难过?毕可文说,因为姐姐不好看啊,不然还能认识一下。赵林听得几乎暴走,但是忍住了。毕可文又说,后来又去过几次姐姐家,但是都没有第一次感觉好。赵林说,那还去过别的地方吗?快说快说,不要挤牙膏。
后来过了一段,姑娘又很开心地出现了,说:“我阿姨全家去东南亚了。”阿姨家也不远,在曲阳路一个小区的高层里。毕可文问,阿姨是姐姐的妈妈吗?姑娘说,是啊。阿姨家比姐姐家大,比姐姐家装修得豪华,而且是顶楼。
两人先在阳台的钢丝床上睡了一觉,醒过来,一起趴在栏杆上抽烟。
你们都抽什么烟啊?赵林插话。
骆驼。毕可文说。
姑娘问,贾斯汀,你会唱歌吗?毕可文说,不会。姑娘说,我给你唱一首歌吧?毕可文说,好。姑娘唱了一首《夜上海》。毕可文说,你不是唱摇滚的吗?姑娘说,这会儿不想唱那些。贾老师不说话。姑娘跑到里间拿出一把吉他,又唱了一首日文歌。毕可文说,我不会唱歌,我给你演一段话剧吧。姑娘笑。毕可文捏紧嗓子,在阳台上对着凌晨灰白的虚空,“黄昏,是我一天中视力最差的时候,一眼望去,满街都是美女……”毕可文演完,扭头看到姑娘。姑娘眼睛亮晶晶地看着他说,贾斯汀,你个坏蛋。
赵林从来没有看过毕可文演话剧,在他的坚持下,毕可文坐在日料店里,把文艺青年中已经烂大街的《恋爱的犀牛》的第一段演了一遍。赵林工作久了,疏于搞文化,听得头皮发麻,觉得毕可文真是太文艺,太会忽悠姑娘了,自己这个朋友,真是交对了。
(曾经《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作为一篇独立的短篇发表在one上,当时是2015年5月5日,再过两天就是这篇文章的一周年纪念日。因缘巧合,故事里的贾老师在今年五月又活了过来,虽然长篇和短篇可以完全独立来看,但是有兴趣同学还是可以去翻阅之前的文章。在App里手动搜索《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即可。)
《上海滩的贾斯汀·比伯》于每周二、四、六晚间在连载版面进行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