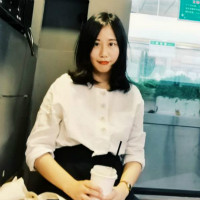人们都选择把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我只想躺下。
那一年的冬天,我决定出门远行。我背上双肩包,关掉手机,趁父母尚未睡醒,悄悄溜出了门。
是大年初三的早晨,大街上还残留着前一夜人们玩鞭炮的痕迹。楼下的早点铺子大门紧闭,卖重庆小面和安徽馄饨的老板们已经回到了自己的老家。我孤零零在街上走着,像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我的眼神扫向街角,平时蜷在那儿的流浪汉已经消失了,他去了哪儿呢?他是否改头换面,回到了他的家乡,正在和家人们一起过节?
来到公交站,我随意跳上了一辆车,车上除了我和司机外,一个人也没有。我看着那些已经不太熟悉的站名,想着要在哪一站下车。司机也很狐疑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问:“这么好的休息机会,不睡觉,大早晨是准备去干嘛呢?”
我找了一个靠窗的位置坐下,任由车子带着我朝前走,窗外的风景由熟悉变得陌生。我这才恍然惊觉自己已经离开这座城市很久了,久到无法辨认出它曾经的容颜,儿时玩耍的校舍已经被推平,改成了商场;童年频繁经过的街道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游乐场。
街上红彤彤的,到处都悬挂着过年的祝福标语与红色灯笼,一切都如此热情,像一位在大宅中恭候多时的老管家,然而我却不敢对他道一声“春节快乐”。在疲惫行进的那些年里,我也数度想过放弃在北京的生活,回到家乡。然而在饭局上,在觥筹交错间,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说:“衣锦还乡,衣锦才可以还乡啊。”
我下意识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穿的衣服,是旧衣,同事带我去北京动物园买来的,价格很便宜。我一向对穿着打扮不那么在意,也不认为过年就一定得穿新衣裳,这招致了母亲的愤怒,她对着我指指点点说:“你看看你,头发也不做下,穿的衣服也灰蒙蒙的,整个人看起来都没什么朝气。”
有许多事,我从未对母亲开口说过,每次打电话,必定是报喜不报忧。我没有讲过,有一年的春天,北京沙尘暴肆虐,我走在国贸的大街上,低头看着手机,寻找下一个要面试的公司的地址。那整整半个月,我四处求职,每晚回家后,围巾里都能倒出沙。洗澡时,面上可以搓出一些黄泥。
人们都选择把光鲜的一面展现给世人,而我只想躺下。大家都热热闹闹地四处拜年,互相聊着近况,我却想把所有的一切都给埋进肚子里,最好我不问别人,别人也不要过来问我。
但,亲戚们的“武器”是厉害的,不消一会儿就勾勒出了我的失败者形象——二十八岁,失业,没有结婚,也没有男友。不爱打扮自己,头发特别短,看起来跟个男的似的。亲戚好心介绍相亲对象,我却每次都能在聊天第一句时,就把话题聊死。
“你都快三十岁了,也该醒醒了。”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二,我听到人们频繁议论着我,好像我比电视里的小品要有意思多了。她们磕着瓜子,为我规划着未来,她们提出了不少建议,譬如让我赶紧回老家,譬如让我抓紧找对象,譬如建议三十岁之前赶紧生个孩子等等。她们的孩子也跟我不太一样,那些女孩儿留着长长的卷发,手上做了水晶指甲,她们看起来毫无烦恼。我们最多的沟通可能也就是一句——“在北京,生活很辛苦吧?”
我的脸上写满了我在北京奋斗过的痕迹,在冬天,北方的风真的像刀子一样割在脸上,像要把我的脸划开。可是,在北京,也有诸多无法与人分享的美好,譬如春天的玉渊潭,譬如夏天的北海公园,譬如无数的讲座与小型电影展。只是那些让我快乐的部分通常是家里亲戚从不在乎的部分。
无法证明自己是个成功者,这等于我的“远行”是毫无意义的。朦朦胧胧间,我又听到亲戚们议论,说谁谁家的孩子是交大毕业的,在很好的公司工作,毕业五年就在上海买了房,已经定居下来并结婚生子,正准备二胎。接着,她们又转头问我:“你呢,你要在北京买房吗?”
恐惧于亲戚们的拷问,我就这样开始了新一轮的“离家出走”之旅。我想,消失一阵是好的,起码这一天,我不会再受到那些人的骚扰。
2.
车不一会儿就驶离了市中心,我的前方出现了一片湖。车上没几个人,我打算就在这里下车。我想一个人在湖边坐坐,发会儿呆也好,反正周围也没有一个人认识我。
在岸边,一块突出的三角区域,不知道是谁放了一架钢琴,四周也没有人。偶有小孩过去,对着那架钢琴东摸摸、西瞧瞧,但真正的演奏家则一直没有出现。
我从双肩包里取出一本余华的书,打算看一会儿。
每年都是如此,我在春节放假之前做好了一个大型的阅读计划,比方说十天看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五天看完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等等,最后通通没有成行。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我无法把自己的房门紧闭,无法让自己置身事外。最终,书是书,我是我,过完春节后,书没翻两页,人还疲了。
总是听人说:“人要把自己还给自己。”我却始终不知道如何迈出这一步。现在,我关闭了手机,与那个喧嚣的世界短暂地失去了联系,这不失为一次机会,让我狠狠地叛逆一下。
年少时,我做过许多看似叛逆的举动,比如在学校明令禁止的情况下,把头发染成红色,比如喜欢穿一些有破洞和挂着链条的牛仔裤,比如在无人之地,大声播放摇滚乐。后来我才知道,我这些行为并不算什么,它其实只是青春期的小小发泄罢了,在父母和老师眼中,这样的孩子并不存在真正的杀伤力,他们害怕的是那些表面很乖,内心却充斥着各种抵抗情绪的孩子,就像我那个同桌,总是一声不吭翻墙逃学,等再次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衣服、裤子永远是破的,不知道去了哪里玩耍。
有一次,我十分好奇,问他逃课之后都去了哪儿,我以为他会回答——“去网吧打游戏。”结果他说,他哪儿也没去,只是在动物园里不停散步,给骆驼喂草,摸摸鸽子,向斑马问好。我又问他,为什么他的衣服,裤子会破,他说他是把自己的好衣服送给了别人,自己捡了些破衣服穿。
书看着看着,人就困了,我趴在自己的膝盖上,开始睡觉,朦朦胧胧间,我听到了钢琴曲的声音,我睁开眼,发现一个黄色的身影坐在钢琴前。这是什么曲子?是巴赫么?我有一点印象,但说不清楚。我站起来,朝湖边走去,越往前走,那人的背影越发清晰,我通过他的衣着辨认了出来,他是一名外卖骑手。
大年初三,有人没有休息,还在路上奔跑。意识到这一点,我忽然有些羞愧。那个骑手弹了一会儿就站起来,推着车子,继续走了,我还没来得及和他打个招呼,他就骑得很远了,那架钢琴又空置了下来。
有几年,我迫切渴望培养一项技艺,用以弥补我在学生时代的遗憾。小时候,父母送我去画画,画了没几年,我就没兴趣了。后来在各种文艺表演中,我看到那些会弹琴,会唱歌,会跳舞的同学,总要露出羡慕的表情。我也想过学习弹钢琴,但去了没几节课便半途而废了。有时,我将自己的种种不成功归结为生活给我的外部压力,比如工作太忙,或者别的理由,但有时我又觉得,如今混成这样,似乎是咎由自取。
短暂的安静后,湖边再次喧闹起来,人们朝着一个广场地带涌去,我这才发现那儿有个铺子在做开业宣传。我一向不喜欢过分热闹的场合,准备快速远离这个锣鼓喧天的区域,然而,一个黑色的身影吸引了我的注意——是魔术师和他的白鸽。我已经很久没见过在露天变魔术的人了,况且他戴着高帽,披着斗篷,看起来有一种古典式的夸张。我朝高处走去,想看清他到底要做什么,我期待在某个角落可以发现魔术师的秘密,他那些骗人的小伎俩或是简陋的道具之类。但,什么都没有,他变的竟是一种徒手的近景魔术。
就在我准备转身离开时,那只白鸽忽然扑棱着翅膀飞到了我身边,我这才注意到自己满身的面包屑,估计是离家不久后在路上吃面包时掉落的。魔术师很快发现了白鸽的失踪,有探照灯照到了我的身上,这灯亮度极大,把灰蒙蒙的天瞬间照得像金光闪耀的舞台。我猝不及防,恨不得找个地洞钻进去,这个刹那,我感觉自己像是《西游记》中无所遁形的妖怪,似乎马上就要扭曲着露出自己的真身。魔术师用喇叭喊话,告诉全场,我是被选中的幸运观众,让我到他的面前,他有一份礼物要送给我。
我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在众人的目光簇拥下走到了魔术师的身边,他给了我一个小小的杯子,让我对着里面吹气,然后许一个愿。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脸,这才发现他一点儿也不年轻了,双鬓是斑白的,眼角也有皱纹。我想说点什么,但终究没有说出口。他又悄声问我,你有什么愿望吗?我一时恍惚,随口答了句:“我想回到十八岁。”
我的确很想回到十八岁,但这根本不可能。
魔术师笑了笑,把酒杯拿回去,从里面变出了玫瑰和金币巧克力。他把这两样东西交给我,说这就是达成愿望的两把钥匙。我心想这根本就是扯淡,魔术不是魔法,既然做不到,就不要胡乱夸下海口。我再次看向台下,发现那些观众只是在起哄,他们似乎根本不在乎魔术师变出了什么,而我的愿望又是什么,他们只是图个热闹罢了。散场之后,谁也不认识谁,每个人都将回到自己的生活之中。我一瞬间意识到,那些我连名字都叫不清楚的亲戚们和这些观众没有区别,他们只是在某个特定的时间进入到某个特定的场合,然后坐在沙发上看戏,他们或许也只是信口开河,随便谈谈,根本没想过对我的生活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干涉。
表演结束,观众散场,湖边又恢复了平静,我不知道下一站要向何去处,我打算去火车站看一看,虽然根本不知道要去哪儿,但我或许可以买一张火车票,随便去一个地方,潦草打发这几日的生活。这仿佛是一种隐喻,如果我潦草地过完了这个春节,或许我就能轻而易举地打发我的余生。
走到火车站的时候,我发现这里的一切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当年,我第一次踏进这里时,刚满十八岁,因高考失利,我关闭了手机,漫无目的在城中漫游。考不上心仪的大学,又不愿受复读之苦(复读也有可能越考越差),我从此沦为了人们嘴里的笑话,仿佛这十几年的求学生涯如废纸一样只能扔进垃圾桶。
站在十字路口,我看到牌子上显示着南下广州的列车时间表,我开始思考是不是要去找个工厂打工。我又看了一眼北上的车,这意味着我可以去北京,或者我能混个什么电视剧的群演?打打杂?哪怕住在地下室也无所谓?那时的我实在是太年轻了,年轻到不知道自己要面对的是怎样的凶险。
我继续朝前走,走到了一面哈哈镜前,镜中的身影被拉长,我觉得滑稽,自顾自地笑了起来。透过镜子,我看到了自己的脸,其实还是和十八岁一样,没有太大的区别。
我低头,打开了手机,想看看失联的一天这世界上到底发生了什么。然而,我打开的那个瞬间,父亲的电话就打了过来,他用苍老的声音问我:“你在哪儿?”我没敢告诉他我在火车站,只说约了几个朋友出来玩,手机刚好没电了。父亲“嗯”了两声,问我要不要回家吃饭?我问:“有别的人在吗?”母亲忽然夺过父亲的手机说:“大年初三啊,不拜年的,谁来啊,你赶快回来吧。”
这一瞬间,我忽然意识到自己的所有担心都是自己幻想出来的,这一天压根不需要拜年,这一天也没人来我家拜年,没有人真的像窥视狂那样关心我的生活,只是我自己总是在无限放大自己的情绪。
“是不是回来吃饭?”父亲再次确认了一遍。
“嗯。”我很确定地回答。
挂断电话,我终于释然,我把包卸下,坐在广场的空地上,开始吃那枚金币巧克力。我从未吃过这么好吃的巧克力,仿佛所有的美梦藏于其中。我想起魔术师的那些话,钥匙或者愿望。这时一个女孩走过来,问我进站口在哪儿?我抬头一看,那正是二十一岁时的我,我想起王小波的那句话——“那一年,我二十一岁,在我一生的黄金时代,我有好多奢望。我想爱,想吃,还想在一瞬间变成天上半明半暗的云。后来我才知道,生活就是个缓慢受锤的过程。”
“进站口就在那边。”我朝前一指,女孩道了一声谢谢,兴奋跑了过去。我忽然忆起,这便是我第一次出门远行,第一次离开家乡时的样子。我没有拦住她,也没有告诉她我此后经历的一切,我只是静静地看着她跑向出发点,想顺手送她一朵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