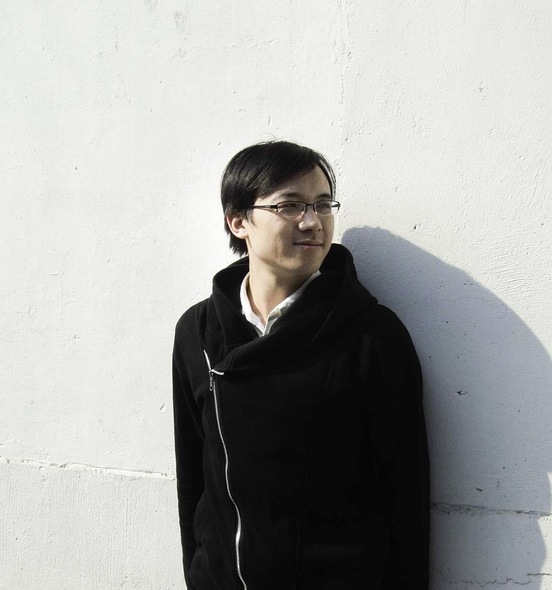作者回忆往昔,以白描的笔法记录亲人的故事。人在命运里浮沉,各有烦恼,也各有期待。
高考结束后,我决定趁暑假走出这个巴掌大的小县城,去上海找我哥。
我哥在上海宝山区的一家机械厂做技术主管,我去上海,自然希望他能带我在这个大城市好好玩玩,见见世面。
然而,我并没有如愿。
我哥每天忙得连饭都吃不上,双休都在厂房里处理各种技术故障,我只能在他的“住所”里窝着。“住所”不过是厂里行政办公室,用塑料板截出来的一个小间,里面一张床,一个电视柜。白天我哥去车间,透过薄薄的墙壁,我能听到办公室里人们的说话声和走动声,还有远远的机器轰鸣声。我不敢乱动,电视也不敢看,生怕发出声响影响了他们,只好躺在床上看书。
窗外炽热的阳光照进来,看门人的媳妇在水龙头下面不紧不慢地搓洗着衣服,时间极为缓慢地流逝。
早饭午饭都是我哥从食堂带回来的,我坐在床上吃,我哥穿着油迹斑斑的工作服,靠在门口抽烟。他问我:“是不是待烦咯?”我没吭声,默默地吃饭,停顿了半晌,他把我吃完的饭盒接过来:“晚上带你去找大姐。”
一
出了哥哥上班的工厂,还是厂区。
塑料厂,玩具厂,食品厂,木材厂;到晚上每个厂里都是不歇工,一条巷子走下来,耳朵边是各种机械运转的噪音。哥哥骑着车,带着我在厂区迷阵里穿梭,穿过铁道口时,我在一片破烂的临时建筑间隙,看到宽阔的马路和亮着灯的居民小区。那边才是上海。
在路上,哥哥告诉我,大姐一家原来在无锡开店,没有赚到钱,听说他在上海便找了过来。哥哥帮她一家在这附近找到住处,大姐夫天天去上海市郊运菜,大姐在菜市场租了一个菜摊卖菜。
“才来的时候,穷得要死,租房都租不起,还是借了钱给他们。”哥哥一边骑车一边说,“鬼晓得他们为么子混成这个样子。”
大姐一家住的地方,是一栋两层高的U字形楼,水泥墙面,没有刷灰,住了大概三十多家,花花绿绿的衣服挂满了走廊。天井处只有一口水井,围满了人,洗衣、洗头、洗澡,带着泡沫的脏水在水泥地面上四处流淌。光着身子的小男孩,一路呼啸地从二楼冲下来,后头就有家长拎着扫把追打过来,嘴里骂的话都是方言,我听不大懂。
但我一下子听到了大姐响亮的声音:“娘个X的,我说给他一块九一斤,他非要给我磨一块七。算完账,我一看,好咯,他偷了我一棵大白菜!我都冇看到!”
她正端着一桶脏衣服从门口往水龙头走去,很多年不见大姐,她本来矮壮的身体现在变得肥胖起来,穿着短袖的手臂肉都在下垂,也有了肚子,但走起路一如既往,还是虎虎有生气。
我哥推了我一下,我叫了一声:“大姐!”她扭头看过来,看见是我,连呀呀了几声,把洗衣桶搁下,速速跑过来,一连问了好多问题:“你么来了嘞?长这么高咯。还冇吃饭吧?”
我哥说:“冇吃,等你做饭咯。”
大姐胖胖的脸笑得漾起来:“没得问题,想吃么子?”
进大姐的租房时,先是一股刺鼻的恶臭扑杀过来,害得我差点儿窒息。我哥像是知道我的感受,说:“这栋楼后面是化工厂,味道有点儿大。待长就习惯咯。”大姐笑着说:“是咯,我都没得感觉了。起初来时,闻得要作呕。”
房间十分逼仄,十平米的样子,一盏灯泡悬在没有刷灰的水泥天花板上,释放出昏黄的灯光。一张饭桌,堆满了没有洗的碗筷,靠走廊的窗边灶台上,锅也没洗,盐袋、陈醋瓶、料酒瓶、筷子篓都混乱地放在一起。一张大床上,大姐的女儿婷婷和儿子欢欢正在打闹,被子都落到地上了。大姐责怪道:“两个孽畜嗳,你们要折磨死我,是啵?才洗的!你庆儿舅来,还不快叫!”婷婷和欢欢怯怯地叫了一声,就缩在被窝里悄悄玩。
三个大人站在房间里,显得分外挤,我又走了出去,大口大口呼吸。大姐打电话给大姐夫,让他买肉买鱼;菜是不用买了,反正今天没卖完的菜还有的是。
二
大姐做饭是把好手,我从小就知道。
她是我二父(叔)家的大女儿,在她之下,还有一个小她四岁的二姐、小她七岁的三姐、小她十岁的大弟、小她十二岁的细弟。二婶经常在地里和家里忙得昏天黑地,大姐就成了她的得力助手。
大姐一开火,油烟立马弥漫了整个小小的空间,我们站在天井都呛得不行。大姐夫回来就脱了上衣,打着赤膊,从租房外面的小卖部买来几瓶冰镇啤酒,大姐见到说:“我两个弟儿不喝酒的!”
大姐夫笑笑:“大热天,喝点儿酒解解凉嘛。”我哥也忙说:“没得事没得事。”
天井陆续有人搬出桌子和折叠椅吃晚饭,有人用浓重的河南腔普通话大声问:“绣红,你今天做什么好吃的呀?”大姐也用蹩脚的普通话回:“煎了个鱼,炖了排骨汤。”
有人把电视机搬出来,搁在水龙头边上的石台上看连续剧,婷婷和欢欢跟着一帮小孩都挤了过去。我说:“大姐,这儿真像是俺乡下。”大姐一头的汗,说:“是的咯,每天跟过年似的。”
我们也在天井吃,椅子不够,姐夫搬来了几个纸箱子摞在一起,翻倒过来坐上去,大姐蹲坐在小板凳上,婷婷和欢欢直接站着吃,仅有的两个塑料椅子让给了我哥和我。
大姐说我“瘦得跟猴儿似的”,不断地给我夹菜,又问我报了哪个学校、学什么专业。我说读文学专业,大姐点头笑着说:“几好的,你跟你三姐一样,从小到大都喜欢写东儿。”
大姐夫喝得满脸通红,也笑着说:“我其实小时候也会写作文的,老师还夸我嘞!”
大姐拿筷子敲他手:“不要X脸的,莫在我弟儿面前逞能。”
大姐夫不服气:“要不是后面屋里困难,我把书读下去,现在也是个大学生。”
大姐啧啧嘴,拿眼瞟他:“你就晓得说个没用的。今天你去拿菜,钱么少了十块嘞?”
大姐夫结巴了一下:“我么晓得,兴许是你数错咯。”
大姐又拿筷子敲他手一下:“你肯定又去买烟咯,我还不晓得你。”
大姐夫硬撑着说:“冇买!肯定是你搞错咯。”
大姐不理他,又给我夹菜。隐隐约约有风来,沉闷湿热的空气略微动弹了,化工厂的气味也随之压过来,我又一次感到恶心。
回去的路上,黑灰色厂房的上空,纤薄的云丝托着半圆的月亮。一个个小厂子门口漏出一片片白光或黄光。
大姐大我哥两岁,从我有记忆时起,他们成天都是在一起玩的。大姐那时候是个假小子,头发理得短短的,身子骨矮矮壮壮的。我哥看起来高大,其实性格很面,打起架来,人家控住他的肩头,他只能呀呀呀埋头哼着。于是,大姐就冲出来,对着那人屁股踹一脚,那人摔倒在地,她就补上几脚,吐口唾沫,拉上我哥就跑。
他们在我哥哥房间打扑克牌,大姐脑子没有我哥他们转得快,作为玩伴中唯一的女孩,我哥他们常串通好,让大姐输,大姐很久都没有发觉,输了也从来不耍赖,贴纸条就贴纸条,钻桌腿就钻桌腿。
大姐小时常常为了一些我们一点都不觉得好笑的事情笑起来,比如说我哥打了一个喷嚏,她都会笑,笑声力道十足地在房间里回荡。大家若跟着笑,她就笑得更凶,捂着嘴,笑得出眼泪了,笑得拍自己的腿,又去拍别人的腿。二婶为此特别恼火,每当大姐笑时,她总会跑过来骂道:“女伢儿要有个女伢儿的样儿了!么人像你这样坐没坐相,笑没笑相!”
读完小学,大姐就没有继续读书了。留在家里做些家务活,有时候去垸里专门做鞭炮的作坊插炮引,赚些零花钱。这些钱,她常常拿来买零食,等我哥他们放学,带给他们吃。晚上有月光时,他们沿着长江大堤走,一路吃我大姐买的瓜子,一路唱歌说话。大姐一大步一大步往前走,男孩子们在后面跟着。大姐说话最多,讲起大堤两边的防护林,说每年长江水涨起来,都有人在那里淹死,现在里面很多鬼。后头有人吓得要回去,大姐大笑不止,指着那个人说:“你看那个鬼,就在你后头!”那人一哆嗦,大姐又笑起来。
有时候他们躲在隔壁垸张大亮家的鱼塘边上,等人家去吃饭,便拿着网兜偷鱼,偷回来后在我家炖着吃。大姐炖鱼特别好吃,她指挥这个去拿豆腐,那个去拿酸菜,还有的人去菜园掐点儿葱。这边灶台鱼汤在咕噜咕噜冒着泡,那边男孩们搓着手围在一边,时不时冒出来问:“好了啵?饿得要造反咯!”大姐锅铲“当”的一声敲了一下锅沿儿:“催鸡屎啊!”
等鱼汤渐渐泛白,撒上切碎的葱花,便有人等不及拿起汤勺子尝上一口,也不怕烫。大姐并不跟他们抢,而是坐在边上,看他们吃,笑意满满地在边上说话:“莫吃到刺咯!”
三
白天醒过来,工厂的办公室又一次人声喧哗。我打开房门,办公室的人都吓一跳,全都盯着我看。我低着头,跑了出去。
阳光在铁皮屋顶上泛着金光,一只狗横穿整个空旷的厂区。我心里特别失落,我想要看到的并不是这样的上海。我往厂区外面走,一路走到大姐的住处,楼和天井都是空荡荡的,昨晚的热闹喧嚣像是一场梦。
在看门大爷的指引下,我找到了几百米外那个有几百个摊位的大型菜市场,大概是上班时间,来买菜的人并不是很多。想不找到大姐的摊位都很难,因为她敞亮的嗓门远远都能听见。
“菜很新鲜的!你看看噻,叶子上有虫洞,那是没打农药!”她不标准的普通话一直砸向对面买菜的中年男人。那男人迟疑地了一会儿,终于买了一把:“便宜一点咯。”大姐拿塑料袋子给他:“老板,我们挣个钱几不容易的!好好好,这三毛钱就算了,下回还来买哈。”
男人走后,我过去跟大姐打招呼,大姐亲热地说:“庆儿来咯,过来坐。”我进到摊子里面去,刚坐在椅子上,大姐就拿出西红柿给我:“今天你姐夫刚进的,我洗好咯。”我接过来,一口一口地吃,真的很甜。
她又对着卖鸡的地方喊:“婷婷!欢欢!你们莫乱摸鸡!有病菌!”外甥们说晓得晓得,又跑到卖鱼的地方去了。
我笑说:“幸好是两个,可以一块儿玩。”
大姐点头:“是咯,有个伴儿。我小时候,跟你哥也是这个样子嘞。那时候咱们大家还没分家,他刚生出来,是我带,我天天喂粥给他吃。你哥特爱哭,你妈管么样哄他都没得用,我一来他就笑咯。后来要分家咯,你爸妈要把东西搬到新盖的房子里去,我抱着你哥不肯让他们带走。我还记得我对我老娘说让她生一个跟你哥哥一样的伢儿,把他们都笑死咯。”
说着话,又零零星星有买菜的人来。我问大姐生意怎么样,她把账本翻了翻:“凑合咯,婷婷和欢欢一开学就要送回去。手头有点儿紧,都是你哥支援。”
下午,大姐夫也回到了菜铺。
他以前在我们老家是开米厂的。小时候每年麦子收割脱粒装好后,就会送到米厂,按照固定的比例,多少斤麦子换多少斤米。那时大姐在家里的任务就是每个月去米厂拉米回家,本来来回两个小时就够了,大姐却总是到天断黑才回家;过不了多久,大姐夫这边就来提亲,二父二婶也很中意他。他是个勤快人,我那时经常看见他帮着二父堆柴垛、挑粪和拉板车。我们一大家吃米也不用买了,大姐夫每个月都送最好的米过来。
定亲后的大姐变得矜持起来,换上了女孩子带花纹的薄衫,头发也留了起来,说话细声细气的。我哥他们一帮男孩子找她玩,她也不玩,躲在房子里对着镜子拔眉毛上的粗毛。以前她老跟二婶顶撞,现在也不冲了,叫做什么就做什么,连二姐她也不打了。
嫁过去后一个月,大姐就又跑了回来。
她跟婆婆处不来,婆婆说她不会收拾房间,嫌弃她这里那里都脏。她气不过,跟婆婆大吵了一架。大姐夫过来哄,大姐说,再跟婆婆一起住就要离婚。没办法,大姐夫把家搬到了米厂,大姐才跟着回去。
米厂在长江大堤脚下,红砖垒砌,机瓦屋顶,穿过碾米仓库,就到了他们的房间。我和我哥拜年时去过,电视机上、桌子上、窗台上,到处是灰尘,桌子上乱七八糟地放着各种杂物。大姐那时抱着刚出生的婷婷,原来紧皱的脸已经胖松起来,一笑眼睛眯成一条缝:“箱子里你姐夫买的红富士苹果,随便拿。”
椅子上还有脚印,我们不敢坐,说不上几句话,我就想走。大姐夫戴着口罩在碾米机那边干活,我走过去跟他打招呼,他笑着点头。
走的时候,大姐又在我的包里塞上几个大大的苹果。
后来,米厂破产了。大姐夫带着大姐,先去无锡的工厂打工,又去了义乌倒腾小商品批发,一点儿积蓄都赔光了后,又回到无锡打工。后来听说在上海种菜挺赚钱的,他们又去了上海郊区种菜园,还是没有赚到什么钱。
现在,他们靠着我哥的借款,维持这个小菜摊。
傍晚,买菜的人变得多了起来,菜市场的每个入口都一批批涌入人流。买菜的大多是附近打工的,少有上海本地人,南腔北调听得人脑袋发涨。大姐跟姐夫麻利地应付,婷婷和欢欢老实地蹲在那里剥豆子,我站在一边有点手足无措。
讨价还价中,大姐忽然大起了嗓门:“哎哎哎——你还没给钱!”只见一个年轻男人拎着一袋子菜,急急地跑开。我还没反应过来,大姐已经绕过菜摊追了出去:“别想跑!”大姐夫对我说了一句“你看着摊子”,也去追。
大姐虽胖,跑起来却很快很敏捷,一边喊一边灵活地躲开迎面的人群。大姐夫笨拙地在她后面绕来绕去。在菜市场门口,大姐一把揪住那个男人,劈头就是一巴掌,老家的方言就飚了出来:“你妈X的,跑鸡屎!”年轻男人刚要还手,大姐又是一脚踢到他的脚踝,对方一下子跌倒在地。
围观的人都哄笑起来,倒在地上的男人脸上挂不住,嘴上不饶地乱骂。大姐作势还要打,被赶过来的大姐夫拉住。男人爬起来给了钱,一瘸一拐骂骂咧咧地溜走了。大姐听见骂声,还要赶去打,大姐夫赶紧把她拉了回来。其他菜摊的老板说:“红姐,你厉害嚯!”大姐笑咯咯地回应:“老子打他找不到门!”
回到自己菜摊后,大姐夫小声地埋怨:“莫闯祸咯,你要是打了黑社会的人,么办?这边的情况很复杂的。”
大姐“嘁”的一声:“怕个么子。来一个打一个。你一个男人,还没得我敢打。”
大姐夫一时噎住,过不了多久,他又细声细气地说:“我去批菜,晓得点儿情况。上海郊区种地的,你看到了啵?各个地方的都有来租地种菜的,安徽帮的,湖北帮的,经常打架。你记得毛伢儿啵?他就打架时被打断了腿,现在还在医院躺着。这边也是,各个地方纠成一团,你得罪一个,就得罪一批人。何必惹这个麻烦?”
大姐不耐烦地挥手:“晓得晓得,啰里巴唆说这么多!我就是不喜欢别人欺负到我们头上来。像你这样怕这个怕那个,还要不要开张做生意咯?”
大姐夫低身把菜拿出来整齐地码在铺子上:“和气生财嘛。”
大姐哼了一声:“你是和气咯,生财了没得?”
大姐夫不吭声了,把西红柿一个个码好。
四
晚上收摊,婷婷和欢欢坐在大姐夫的三轮车后车厢,我和大姐在后面慢慢走。走过铁道路口,我看到远远的居民小区亮着灯,心中忽然起了一阵惆怅。
大姐问:“你还冇去市区玩过吧?”
我说没有。大姐一下生起气来:“你哥哥也是的,都来这么多天,也不晓得带你去一趟。”
我忙说:“他太忙咯。”
大姐摇摇头:“再忙也要带你玩一下的。不行,我明天带你去。反正我来上海这么长时间,也冇逛过。”
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就起身去大姐那里,走前我哥给了我五百块钱,嘱咐我不要花大姐的钱,我说好。
大姐夫负责在菜摊卖菜,大姐带着婷婷,我带着欢欢,一起穿过厂区,走到大马路上搭公交车。外甥们来上海后也没有出来玩过,大姐说他们一晚上兴奋得没睡着觉。
车子带着我们进入了宝山城区,沿路上的楼群逐渐变得干净起来。下了公交车,换乘地铁,大姐盯着蛛网一般的路线图,愣愣地发呆。我那时也没坐过地铁,看别人怎么操作的我也跟着怎么操作。
我买票的时候,大姐紧张地拉着婷婷和欢欢等在后面,喊道:“我这儿有钱!”
我说:“不消的,我钱够。”
我把买好的卡拿了过来,大姐问:“小孩也要钱啊?”
我说是啊,大姐啧啧嘴:“真是抢钱!”
刷卡过闸机时,大姐又一次不知所措,我教她刷,她刷了几次都没刷上,便气恼地骂:“搞这么麻烦,上个车这么折腾。”骂完又对婷婷和欢欢说:“你们钻过去。”
我忙阻止:“不行的,这边有人检查。”
好容易上了车,车厢里人极多,大姐抓住车厢中间的杆子,又让婷婷和欢欢也紧紧抓住。我说:“大姐,没得事的,我看着嘞。”
大姐咧嘴勉强笑笑,神情很紧张:“晓得晓得。”
一站又一站,大姐的神情始终没有放松。她的眼睛像是老鹰一样,扫视着整个车厢,看有没有人下车,好去占座位。
可惜没有。
婷婷和欢欢被大姐牢牢护在自己身边。到了中山公园站,有人下车时背包蹭了欢欢额头一下,欢欢疼得叫起来。大姐立马揪住那个要下车的人,锐声吼道:“你还想跑!”
那人回头去看,大姐兜头给了他一耳光:“看你晓得疼啵?”
那人被打蒙了,反应过来后,转身过来要还手:“你怎么回事啊?莫名其妙地打人!”
大姐头冲过去:“打的就是你!没看到我家小孩子啊?”
我忙去拉大姐,大姐的身子气得发抖。那人瞅了一眼欢欢,又说:“我又不是故意,你怎么说打人就打人啊。”
大姐伸手又要去打,被我拉住。我忙跟那人说:“你快下车吧。”
那人看大姐的气势,也有些害怕,嘟嘟囔囔几句下去了。
大姐细细看欢欢的额头,并没有什么擦伤,还是隔着玻璃窗骂那个人。地铁又一次开动了,周遭的人都沉默不语,既像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又像是在我们之外竖起了一堵厚厚的壁垒。
我们在人民广场站下车,一出站大姐就“嚯”的一声:“真是有钱得很,盖得几好看。”一路走到了南京西路步行街,大姐直啧嘴,“来上海一两年,都从来冇逛过,感觉跟这些人完全是生活在不同的世界。”
婷婷和欢欢要吃雪糕,我买给了他们吃,大姐要出钱,我不让她出,大姐笑道:“等你以后读完大学,找到好工作,带我们去纽约玩。”
我说:“要得要得,带你们去火星上玩都行!”
大姐笑得特别大声,周遭的行人都绕开我们走。大姐也觉得自己这样笑很奇怪,又收敛住了。
走到外滩,东方明珠屹立在江对岸,黄浦江浑浊的江水流淌,江风中带着水的腥气。我们趴在栏杆上,大姐说:“这江还没得俺屋那边的长江宽。水也很脏嘛!”
我告诉她黄浦江是长江的支流,她点点头:“这么说,沿着这条江走,我们都能回家咯。”
我点头说是,大姐沉默了一会儿说:“小时候,我跟你哥哥沿着江边走,我就问他这条江走到头是哪里,你哥说上海。现在真是走到长江头咯。”
我拿着哥哥的相机,提议在这里拍一张。大姐看看自己,胸口拍拍,裤脚拍拍,又拢了拢头发,弄好后把婷婷和欢欢拉到自己两侧。
拍完一张后,大姐问:“庆儿,我看起来显老啵?”
我回道:“哪里老咯,年轻得很!”
大姐微微笑了笑:“帮我拍好看点儿,你带回家给你二父二婶看。”
大姐又让我给婷婷和欢欢单独拍。我把两个小家伙抱起来放在栏杆上坐着,他们手拉着手,对着镜头笑。大姐站在我身边说:“这两个细鬼,以后长大像你哥和你就好咯,好好读书读出头。我跟你姐夫,一辈子就这个样子咯。”
江中的轮船发出了浑厚悠长的汽笛声,我们坐下来,大姐这时比在地铁上放松多了,风撩起她鬓角的几缕头发,她抬手抹了抹,眼角鱼尾纹的确是很明显了。在她身后,是外滩举世闻名的万国建筑群,她兴趣缺缺地瞭了一眼,打了个哈欠:“两个细鬼的,昨晚闹了一夜。”
我说:“你睡一会儿?孩子们我看着。”
她说好,头放在我的肩头上,过不了一会儿,就睡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