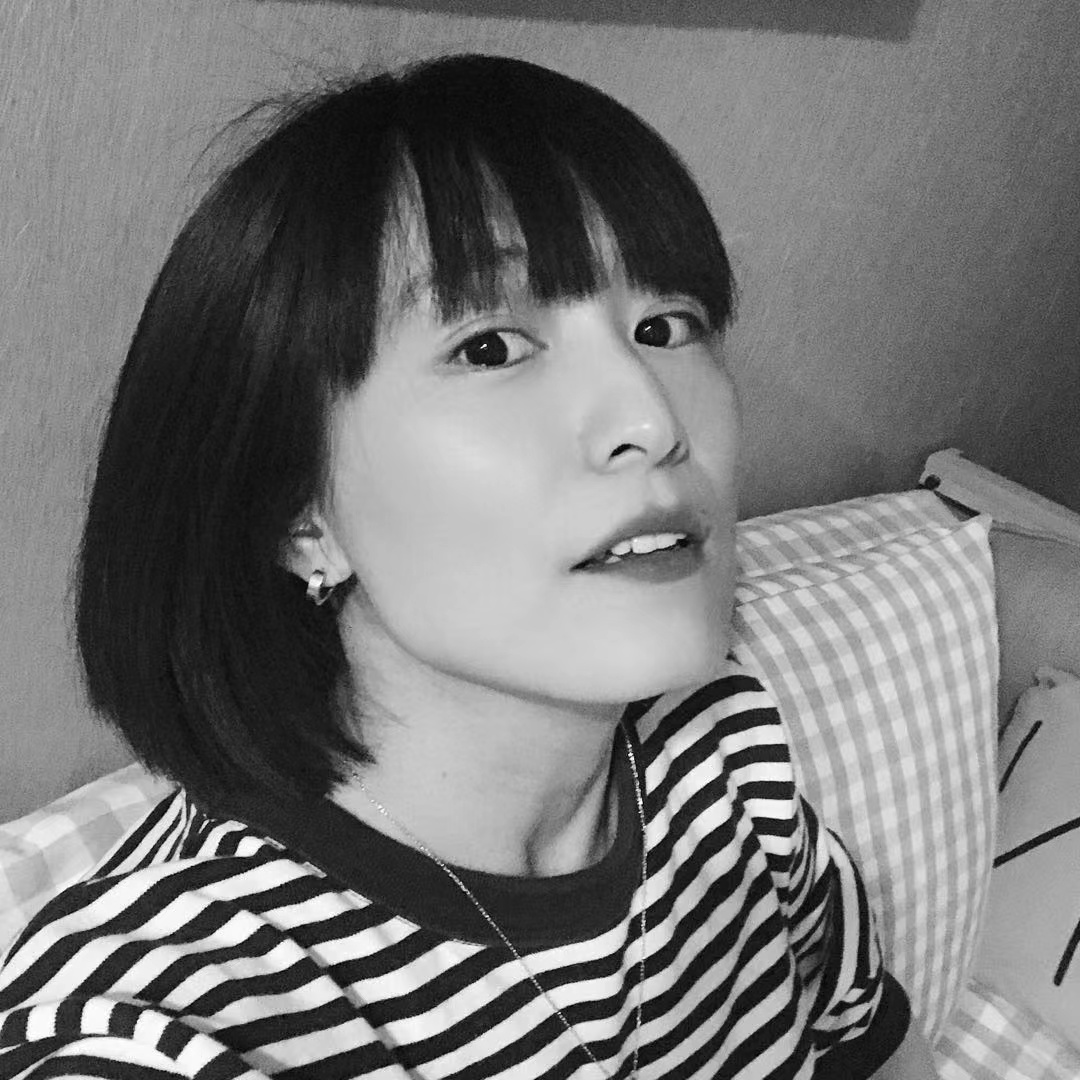原本是一场普通的酒局,我见到了一个存在于朦胧记忆中的女孩,并目睹三人觥筹交错间赤裸裸的交易。
这女孩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她从黄圃的玛莎拉蒂里钻出来,眉头紧皱,一双丹凤眼高高地吊着,很厉害的样子。黄圃——我最尊贵的客户,正从另一侧下车,单光宗跑过去给他开车门。
黄总晚上好,我和单光宗齐声喊道,同时九十度鞠躬。
换做往常,黄圃会对我们笑笑,或者拍拍肩膀,但今天他没空搭理我们,女孩正在瞪他,撅着嘴说不想进去。黄圃过去拉手,一下,两下,没能得逞。别这样嘛,宝宝,黄圃说。可我不知道还有别人,女孩说。黄圃把头贴过去,咕咕哝哝地小声哄她,我和单光宗都朝后退出一步。不用猜,还是那套:明天买包,后天滑雪,宝宝最乖,宝宝最美。单光宗冲我挤眼,小声道,宝宝十四,我拿手肘戳他一下,提醒他别乱说话。黄圃女友众多,每一位都叫宝宝,单光宗给她们加了编号,从宝宝一号到宝宝十四,只用了半年不到。我问单光宗,黄圃就不能换个称呼?单光宗斜我一眼,说,不懂了吧,这为了防止露馅。单光宗这个解释有理有据,很能令我信服,以黄圃换人的速度,记住每个女孩的名字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但这个女孩,我肯定在哪儿见过。
我来会所六个多月了,漂亮女孩见了不少,很长时间里我感到迷惑,她们好像都长得一样。单光宗说这是因为整容术太流行了,再加上网店里的爆款服装。前段时间她们喜欢穿半截上衣,把腰和肚脐眼儿全露出来,最近她们迷上了异常贴身的瑜伽裤,袜子必须拉到脚踝以上。“半山特产,新鲜大腿。”单光宗编了个顺口溜。这句话得罪了女服务员,她们联合起来开他的批斗大会。我眼疾腿快,装着打电话,就想往外跑。新来的大厅经理韩小雪上前拦我,说于洋你别躲,我一边绕到她身后,一边捂住手机,说嘘,别闹,辅导员催我交社会实践报告,韩小雪转过身来呸了一声,说滚吧,我连忙说好嘞,一路小跑进厕所,一直躲到批斗结束。事后,单光宗怪我太不仗义,我也觉得挺不好意思,为了赎罪,只好给他当了回跑腿的,去山脚下的711超市买烟和薯片。
会所名叫半山,地处半山腰上。山是城南的万佛山,香火很旺。山前面拜佛,山后边吃饭。拜佛的白天去,吃饭的晚上来,时间上碰不到一块儿;走的路也不同,拜佛的人沿山前的石阶爬上去,进庙烧香,吃饭的人从山后的公路开车上来,吃喝买醉。除此之外,山上也有几条野路,荒僻少人,不熟的人不敢擅走。山后除了会所还有酒店,五星级的,开在山顶上,名叫鼎间。客人喝多了,服务员就用摆渡车把人送上去住宿,回头上干勾于的办公室领一百块钱。干勾于是我们老板,跟鼎间的老板有业务合作,关系不错。
等黄圃的时候,单光宗又开始研究干勾于和韩小雪的关系问题,主要围绕着他俩干过没有。从三个月前韩小雪来到半山,他就开始研究这个问题,研究方法主要靠观察,外加一点儿想象力。心情好的时候,他说韩小雪不像那种人,心情差的时候,他说女人都她妈一样。今天单光宗的心情不好不坏,说话比较客观。单光宗说,于洋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什么?单光宗啧了一声,说,就大扫除的时候。上午十点,所有的服务员在大厅集合,点名、唱歌、做大扫除,干勾于从大厅经过,夸韩小雪玻璃擦得好。哦,我说,看着不像。单光宗吸了口气,又长长地吐出来,口里嗯了两声,说,从韩小雪的态度来看,确实不像。
我心不在焉,一边和他搭话,一边朝黄圃那边看。主要看那女孩。
她扎着高马尾辫,侧面头发上别一只珍珠发卡,修长的脖子,瘦薄的背,乳房是少女的轮廓,小小的起伏。落日余晖罩住她的侧脸,能看见上面细软的绒毛。我的大脑在翻腾,想从记忆里拽出那条线索,刚好合上她的轮廓,但没能成功。她的头总朝一侧扭着,看不见表情,手臂抱在胸前,像是还在气着,又像留有余地。秋风吹动她身上的绿纱裙,露出一截大腿,我替她感到寒冷。
给个面子吧,宝宝,黄圃伸手搂她。她推黄圃,一把比一把轻。最后她说,好吧,进去就进去,但不喝酒。黄圃嘿嘿地笑着,说怎么都行,只要你高兴。
单光宗去泊车,黄圃搂着她朝大厅走,我负责引路。
会所不大,共八个厅,风格各异,黄圃每个都熟,我和单光宗负责的罗马厅是他最常订的。罗马厅是个套间,有吧台和休息间。开餐前黄圃喜欢用吧台上的半自动咖啡机做卡布奇诺,他会打奶泡,拉花也会,我见过挺多次了。进了屋,我先把多余的餐具撤了,只留下三套,又走进吧台里,把储物柜里黄圃存着的碧潭飘雪拿出来洗了,放进骨瓷茶壶里。黄圃已经开始拉花,表情挺认真,袖子撸起来,露出手表,挺新的一块。我瞟一眼标志,劳力士。女孩站在黄圃身后,双手抱臂,一会抬头看灯,一会低头看地。咖啡做好了,黄圃端到她脸前,说,尝尝,她啜一口,淡淡地说了句还行。那一刻我忽然想起来了:是她,去年的政治理论大课,她就坐我后排。课是三个系合着上的,两学期,三十个课时,如果我没记错,她总共就来了一次。没错,就是她,高马尾,丹凤眼,眉头一皱,挺厉害的样子。不过现在她看起来不怎么厉害了,黄圃又搂又哄,终于把她逗笑。她笑起来奶声奶气,嘴里还咬手指头,我看着有点儿别扭。
单光宗泊完车回来没有进屋,只把门推开一条缝儿,朝我使个眼色。我回身朝黄圃鞠了一躬,说,黄总我先去了。黄圃今晚有贵客,交代我俩去门口迎候:姓孔,七点到,黑色奥迪,尾号三个九。下了楼,单光宗看看手机,说操,才六点半。我俩对个眼,一前一后地绕到侧门外的一棵老槐树后,单光宗掏出瘪了盒的软中华,是昨天晚上客人落下的,给几个服务员分了一圈,还剩下三根。一人叼上一根,点了火,怕风把烟吹到前面去,都朝地下吐。单光宗问,看见黄圃换表了吗?我说,看见了,劳力士。单光宗说,行啊,都认识劳力士了。我说,那当然,一个王冠嘛。单光宗问,知道什么型号吗?我说,不知道。单光宗开始斜着眼看我。从我刚来半山的时候起,他就爱斜着眼看我,我知道,他想用这种傻逼办法,让我显得像个土鳖。但我不和他一般见识。院子里开进一辆奔驰商务,七八个穿黑西装的人从里边儿下来,波斯厅的王光辉跑上去,满脸堆笑,把他们往厅里领。晚间秋风寒凉,直往人衣领子里灌,我俩缩着肩膀,接着说那块表。单光宗让我猜猜价格,我说懒得猜,你就直接说吧。单光宗又斜我一眼,朝树根处吐了口痰,说,六十万。操,他说,你说他们怎么能挣这么多钱?谁知道呢,我说着,抬眼看了看天。天光昏暗,天与山交界的地方,太阳已经落下,几片晚霞堆叠在一起,不那么红了,边缘处泛灰,像炉子里快要烧尽的火炭。可能是命好吧,我说。
我的命就一般。我没戴过手表,到高中才用上手机,还是城里的亲戚替下来的,除了接打电话,聊会儿微信都卡。别说是手表,上大学前我连穿件好衣服都难。考上大学那年,家里给了五百块钱,我拿着去县城买了身李宁,外加一双特步球鞋,都捡最便宜的买;大二那年我在超市当促销员,攒了一千块钱,上奥特莱斯买了两双耐克。没什么可炫耀的,我的大学舍友穿AJ和椰子,我跟他们聊不到一块儿。来半山后我认识了单光宗,知道了阿玛尼、古琦、路易威登……还有挺多,名字太拗口,我记不准。单光宗学历不高,但进社会早,见识比我多出不少。他在抖音上关注了几百个账号,有试驾汽车、品鉴名表,还有教你怎样正确地品尝勃艮第红酒。偶尔推送给我,说看看吧,这才是真正的生活。视频里,男人乘着豪华游艇,身边有成群的比基尼美女。我没什么感觉,那种生活离我太远,不像真的,再说谁知道是不是摆拍呢。但单光宗不同,他不但认为那才是真正的生活,还研究怎样才能过上那种生活。三年前他去参加练习生选秀,没能通过初选。为什么不再试了?我问他。不懂了吧,单光宗说,选秀需要成本,都是富二代,带资进组。六点五十九了,人陆陆续续又进去不少,但我们的贵客还不见踪影。
你说黄圃是干什么的?单光宗问我。
我哪知道,我说。
操,单光宗说,你一天天什么都不知道,还他妈大学生呢。
操,我说,大学生多了,谁规定大学生什么都得知道。
单光宗哼了一声,说也是,上大学屁用没有。
黄圃也没上过大学。这是他亲口说的,小时候学习不好,就送出去留学,留学也没用,钱还得回国来赚。黄圃对人随和,有时候也跟我们聊上两句,念过的小学,追过的女生,分手的前任嫁去了日本……赚钱的事儿从来不提,我们也不问。干勾于开会的时候专门说过,客人怎么说你就怎么听,别问,也别多嘴。我在黄圃的饭局上见过房地产高管、金融精英,也见过电视台记者、律师和医生,娱乐业的也有,拍电影的、搞直播的,如果有客人身份不明,表情傲慢,我们就猜他八成是个大官儿。女伴是永远不间断的。大部分时候一个,两三个的时候也有,长发,细腰,神情柔顺者居多。男人们说话,她们坐在一旁听着,不断地点头或者大笑,把气氛烘得闷热。看得出,有几个是真心喜欢黄圃,这表现在很愿意帮他挡酒,在他喝得烂醉的时候,默默蹲在地上,清理他的呕吐物。
有一次单光宗问我,为什么来这儿。我说想历练历练,提前接触接触社会。我没说实话。我来半山是因为这儿的工资最高,麦当劳一小时十二块五;上超市干促销员,一天一百二十元,站九个小时;来半山,每周干一个下午,两个全天,加上提成,月底能拿两千多块。四个月我能买一台苹果电脑,一年下来,省着点花,我就能攒下两万块钱,买一辆二手的310R。等到大学毕业,我就骑上宝马摩托,离开这里,找一份正经工作。这些话我没跟单光宗说过,怕他又拿眼斜我,说310R是最便宜的宝马摩托。可那至少是宝马。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单光宗,他的回答有点儿搞笑,说一开始单纯得很,只想傍个富婆,一年之后才发现傍富婆没那么容易,而且风险很大。于是他开始练习偷酒,偷客人的酒,也偷会所的。起先只敢偷一个酒底儿,自己尝尝,后来胆子大了,技法也练得纯熟,就半瓶半瓶地偷,拿假酒把客人的真酒换出去卖。来半山的第一天晚上,我亲眼看见他拿空瓶换走客人的茅台。客人还没走,他就把我拉进传菜间里,一手怼住门,一手将乳白色的瓷瓶倒举,控出小半杯酒来,让我尝。我当时害怕极了,怕客人发现了让我陪钱,也怕干勾于知道了,去学校告我的状。得了吧,单光宗说,谁认识你啊,再说他们都醉了。万一没醉呢,我说。你信我的,单光宗说,他们醉得分不清水和马尿,他们醉得连他妈跟谁干了都记不住了。
最近单光宗偷得越发大胆。上周有客人喝酒过量,进了医院,车放在会所没动,被他连夜开出去换了零件,赚了一万多块。钱跟大厅里管钥匙的李志飞分了,到现在也没被发现。这两天常听他念叨,人活在世,要轰轰烈烈。想到这儿,我心里咯噔一下。
七点一刻,贵客终于到了,黑色奥迪,尾号三个九。车门一开,下来个矮瘦的中年男人,四十多岁,穿着短风衣,戴一副眼镜,像我们学院的经济学教授。我和单光宗九十度鞠躬,说孔总晚上好。孔总很讲礼貌,点点头,说你们好。我说黄总特意交代了,车给您停去后院,安全方便。孔总又点点头,钥匙放进我手里,说谢谢你。
会所本来有两个泊车员,上星期刚辞职了一个,原因是嫌这里通勤不便。晚间忙不过来,单光宗就顶上,他在会所里干得时间最久,车也摸得多,手熟。趁干勾于不注意,单光宗也给我机会。我很有自知之明,太好的车不碰,怕出洋相,奥迪还行,我开过几回,心里不怵。
由于是新手,我的动作很慢,从前院出去,别人都是倒一把,调头,我就只能往前开,沿着门口的小喷泉绕上一圈,才能开出。车是老款,里边儿挺干净,有淡淡的木质香味儿。我挺喜欢这种感觉,开着车穿过院里修剪整齐的乔木,听着转向灯在车里咔嗒咔嗒地响,像钟表走字,一下又一下,现在的瞬间通向我的将来。现在,我开始幻想车里有一个女孩,洁白的皮肤,乌黑的马尾辫,我带她来这里用餐——半山之上,密林中间,幽静又繁华的三层别墅,她坐在副驾上朝外打量,脸颊泛红,眼睛闪亮。餐后,我们在山间散步,一路向上,住进山顶的——打住,我出来的时间好像有点儿久了。
我停好车,小跑着回到罗马厅——准确地说是罗马厅的传菜间,单独一个小门,不打扰宾客。单光宗正把白酒倒进描着竹叶的白瓷壶里,加上三只烫好的酒盅,一起放在专用的黑檀木托盘上。单光宗让我把酒端出去,自己去接窗口送进来的四道小菜。干起活来他总支使我,好像我是他的下属,什么都得听他招呼。他还骗我说我俩同岁。其实他故意报了虚岁,我偷看过他的身份证,二零零一年生人,比我小一岁,今年才二十二。我瞪他一眼,一手接了托盘,一手推另一扇门——连接主厅的那扇。门一开,一股甜腻的香味迎面扑来,我猜是那女孩身上的味道,香水喷得多,在一个地方待久了就有这味儿。
孔总坐在主位,右手边儿是黄圃,左手边儿是那女孩。两个男人把头凑得挺近,聊着什么区块链、融资之类的话。女孩把胳膊撑在桌上,右手举着手机,左手上上下下地划。单光宗也出来了,把四道小菜一样一样地往转盘上放。我端着酒在黄圃身后站定,等他把话说完了才问,黄总,倒酒吗?黄圃伸手敬了敬孔总那边。我开始服务,腰板挺直,步伐端正,行至孔总身侧,转身,一只手托着托盘,另一只手把杯子放下,又拿起酒壶,把那只三钱三的小酒盅稳稳地倒满。这套动作是来会所后专门培训的,主打一个信念:高贵的服务。刚开始我进不了状态,时不时就笑,现在好了,挺有信念。我给孔总倒完酒,又给黄圃依样来上一遍,接着转到那女孩的身后,看黄圃的眼色。我不想喝——听见她小声说了一句。黄圃依旧跟孔总谈区块链,没看她,也没有看我。我把酒盅放在她面前,见她没拦,就把壶嘴儿凑了上去。
这一点儿也不稀奇。依我的经验,黄圃带来的女孩都是海量,即使开始的时候,她们面露难色,说不能,不会,或者身体不适。上个月黄圃带来一个女孩,娃娃头,背带裤,说起话来有点儿吃字儿。黄圃说喝点儿吧,她摇着手说不喝不喝,语速太快,就成了波儿,波儿。黄圃说就一点儿,她说波儿波儿。黄圃说,先倒上 ,一会儿再说,她说,波儿波儿,真波儿。酒宴开始,黄圃说倒都倒了,就喝一杯。到第二杯,黄圃又说单数不吉利,好事成双。三杯酒下肚,她脸上泛起红雾,眉毛眼睛都弯下来,不再提“波儿波儿”的事儿了。上上个月,黄圃带来一个歌手,长脸,短寸,怎么逗都不笑。起先她说了好几次不,黄圃装听不见,后来她把杯口捂住,不让我倒酒,黄圃就站起身,说我给你倒。歌手冷笑一声,说少来这套。黄圃说哪一套?煎饼果子,闹太套。她忽然变得非常愤怒,双手拍在桌上,“啪”地一声,真把我吓了一跳。她起身朝外走,动作太快,椅子都被带翻,杯子也碎了一个。当时在场的所有宾客,连同我和单光宗,没有一个人说话。我们全都屏息静气,等着看一场好戏,比如她摔门而去,或者黄圃追上去,跟她拉扯,他们说不定会吵架,说几句精彩的国骂。但接下来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
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在睡前想起那个场面——是什么原因让那个暴怒的女孩在一瞬间变得温顺?我一遍遍思索,想用逻辑整理出故事的始末。太简单了,简单到只能撑起一半的轮廓,剩下的那半藏在空气中,没有形状也没有气味,像深井里的水波,游移不定,捞起来就碎。
现在我只能干瘪地复述事情的经过:她走到门口,手已经拉到把手,我甚至能想象出她接下来摔门而去的声响,黄圃就在这时喊出她的名字,邓佳佳。他的语气严厉,但不是呵斥,他的严厉中带有亲切和谆谆善诱的成分,像一个父亲在训斥出错的孩子。邓佳佳定住了,停在原地,在与他对视了几秒钟后,她回到桌上,长长地叹了口气。黄圃开了句玩笑,每个人都尽职尽责地贡献出最大程度的欢笑。事情就这样平稳地过去,好像从来就没激烈过似的。
她最终在他的软磨硬泡下喝了两大杯红酒,理由是为了艺术与世界和平。
单光宗说女人就吃这一套。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正拿着一根筷子从刺身拼盘里挑出一片北极贝。我问他这一套是哪一套?单光宗把北极贝放进嘴里嚼着,说,他给她使了眼色。我又问,那眼色到底是什么意思?单光宗用舌头舔了舔牙,说,我也不知道,但女人会看。
菜陆陆续续地上来几道,黄圃起身祝酒。黄圃每每开场喜欢使用成语,频率最高的是三生有幸和天长地久:三生有幸邀请到亲爱的孔总,三生有幸在这月明星稀的夜晚,三生有幸与诸位朋友聚首——黄圃还没说到天长地久,话就被孔总给截断了。孔总说黄圃你这是干嘛,自己人用不着这样。黄圃嘿嘿一笑,说大哥第一次赏光,该有的心意得到。孔总说心意领了,接下来咱们随意。孔总说这话时看了那女孩一眼。她一只手端杯,另一只手抱臂,身体倚着桌沿儿,来来回回地晃。黄圃说好,那我不客气了,大哥,小妹,咱们为相聚干杯。黄圃把胳膊伸出去,孔总也把胳膊伸出去,黄圃看那女孩,孔总也看那女孩。女孩见两个男人都看着她笑,紧抿着的嘴角也朝上翘了一翘。三只酒杯在半空中相碰,黄圃干了,孔总也干了,女孩抿了一口,听见黄圃说干掉干掉,只好一仰脖子,把剩下的全喝干净。我把每个人的酒盅再次斟满,黄圃紧接着端杯,连着三次,他们次次都干掉。我换下酒盏,又一次添酒,走到女孩身边时,听见她小声地叹气。但两个男人好像都没在意。
黄圃转动转盘,与孔总谦让着吃菜。孔总在美食上颇有见地,每吃一道菜,都会品评味道,进而讲出菜的用料和做法。黄圃频频称是,有时也跟上两句。他们从用料做法延伸到地域风味,又从地域风味转谈到人文风貌。女孩起先还听着,时不时地伸出手来,欣赏自己的美甲,后来索性刷起手机,一不小心搞出噪音,连忙把声音摁小。好几次我看见黄圃簇着眉看她,似乎想给她一个暗示,但女孩像是故意,始终不肯抬头看他。
“粉红佳人”端上来的时候,黄圃说,小妹,看看这个。
饭局开始后,黄圃不再叫她宝宝。也许是因为她表现得既骄傲又缺少礼貌,也许是因为黄圃发现即使如此,孔总还在坚持和她搭话。孔总问姑娘怎么称呼?女孩说王安琪。孔总说安琪,好名字。哪里人呢?女孩说寿村人。孔总说寿村我知道,好地方,福禄寿三村,同宗同源,出过举人,也出烈女。女孩笑一笑,接着刷手机。孔总过一会儿再问,安琪做什么职业?女孩说学生。孔总问哪个学校?女孩说就山脚下,财经学院。孔总说财经学院啊,我跟你们法学系的李教授是好朋友。女孩又不接话,眼睛始终盯在屏幕上,飞快地打字。
安琪把手机放下吧,黄圃说,一向欢快的语调往回收了两度,略带了点儿命令的意思。这可是专门给你点的,黄圃又说。
她这才慢悠悠地抬起头来,手机仍握在手里,说,我不喜欢甜品。
这不一样,黄圃说,不信你看。
单光宗把托盘放在她面前,雾气氤氤地在桌上散开。托盘是中空的,底部铺一层干冰,托盘上有个水晶冰碗,碗中央是个乳白色蛋糕,做成少女的形状,穿一条拖尾长裙。这道菜借鉴了魔术的灵感,最后的一步特意留给客人来完成。很简单,只需拉动少女腰部的粉红色蝴蝶结,蝴蝶结连着腰上的花边,花边里包着草莓酱和金粉,一拉一提,花边散开,鲜红的草莓酱从腰部淋下,白裙变红,闪着点点金色。每当这时,桌上总会响起一阵欢呼,女士们尖叫,鼓掌,拿手机拍照。活跃的气氛有助于增进感情,客人点“粉红佳人”,就是为了这个目的。
单光宗指着蝴蝶结的位置,让她拉一下试试,她一手托腮,一手握着手机,好像没听见似的。拉呀,黄圃说。她瞟了他一眼,说,真傻,我才不干。
我看见黄圃的脸色在一瞬间沉如黑铁。
孔总看看女孩,又看看黄圃,扶了扶眼镜站了起来。孔总说你们先吃着,我出去打个电话。
现在单光宗已经回到传菜间里去了,孔总也去了门外,饭厅里只剩下我们三个。我知道我该尽快离开,但鬼使神差地,却端起茶壶朝吧台走去。吧台所在的休息厅与饭厅通联,中间有屏风相隔,看不见人,但能听见声音。也许是距离够远,黄圃没有撵我。
我走进吧台里面,把壶里的茶叶倒出来,拧开水冲了冲茶壶,又用纸擦干,接着从储物柜里拿出黄圃存着的另一款茶叶,凤凰单枞。烧水、洗茶、冲泡——我慢吞吞地做着这些杂事,尽量长久地留在房间里,直到听见他们开始争吵。声音不大,但很激烈。她好像在质问着什么, 内容听不清楚,烧水壶在我面前嗡嗡作响。身后很快传来摔门的声响,紧接着,听见黄圃喊我,口气很冲。我小跑过去,看见怒气正在他脸上消散,再开口时他已经恢复了平常的语调。黄圃让我下楼找找,一边说一边用眼睛点了点墙角的衣架,上面挂着他和孔总的外套,还有一只粉红色女士皮包。黄圃说她走不远。
孔总进来了,面带微笑,从开始到现在,他一直是这个表情,像蒙娜丽莎一样。孔总往椅子里一坐,眼睛朝房间里扫过一遍,说,怎么,女朋友生气了?黄圃挠着头笑,说哪来的女朋友,妹妹,一个小妹妹。孔总端起我刚给他倒的凤凰单枞,闻了闻茶香,笑道,你小子,哪儿都有妹妹。
我出来后把门轻轻地带上,房间里忽然响起一阵笑声,不知道他俩说了什么秘密的笑话。旁边波斯厅的大门被人从里边儿推开了,那群穿黑西装的人都已经脱了外衣,变成粉的白的蓝的衬衫,他们正围成一圈,拍着手玩抓鸭子游戏。单光宗从传菜间的窗口探出头来,冲我挤挤眼,问,那小妞跑了?她好像是我同学,我说。单光宗啧了一声,说,怎么着,想英雄救美?
英雄救美,我没想过。我,二十三岁,身高一米七七,体重五十五公斤,除了一个还算年轻的身体和可怜的三千五百块存款,我一无所有。而她呢,仅那只粉红皮包的拎手上硕大的CD标牌就值好几万块。我该怎样救她,她又有什么是需要我救的呢?但也许我能借这个机会跟她制造一点儿交情,比如告诉她我们是大学同学。我知道,她不一定喜欢这样,说不定她会吓一跳,以后在学校里碰见立刻绕道。那次大课之后我没再看见过她,我猜她念的是西区的科系。我们学校有两个校区,东区就在这半山脚下,西区在市里,是原来老校,只留了三个科系,音乐、舞蹈、装潢设计。我忘了那次大课是哪几个科系在上,不过看她的形体,不是音乐就是舞蹈。当然,有万分之一的可能,她只是社会闲杂人等,来蹭了堂课,对外宣称自己是学生。如果是这样,我就更找不到理由加她的微信了。
我胡思乱想着走下楼梯,她果然没有走远,就站在大厅的中央,手臂仍是抱着,仰着头看那盏水晶灯。水晶灯很亮,吊在穹形的天花板上,垂着长长的流苏。大厅被照得明晃晃的,她的脸也白得明晃晃的。我放慢脚步,想着第一句话该说什么,她却扭过头来,先开了口。黄圃让你来找我的?她问。我点了点头。她的目光在我脸上停了一会儿,又回到灯上,说,你看它像不像一条裙子?什么?我说。你看它像不像一条裙子?她又说一遍。我也朝上看了一眼,灯太亮,晃得我眼前立刻出现一个白点儿。有点儿像吧,我揉着眼睛说,你不晃眼吗?她笑了,红嘴唇张得挺大。什么人能穿这条裙子呢,她说。那不得烫死,我说。她接着问我,黄圃是不是常带女孩来这儿?我过了一会儿才答,刚来不久,不太清楚。她的嘴角微微抽动一下,眼睛盯着我的眼睛,像要从里面抠出什么东西似的。回去吧,我转开脸说,大厅里挺冷的。
我跟着她前后脚进了房间,看见两个男人又把头凑得很近,像饭局一开始的时候,谈金融经济的样子。黄圃摊着两只手,表情像在诉苦。我听了几句,大约是说得罪了什么领导,导致项目批不下来。孔总只是微笑,并不发表意见,但他把身子侧过去许多,表示确实认真在听。
女孩进门后,孔总就听得没那么认真了,时不时地把眼睛移到她身上。现在她已经坐下了,两只手搓着肩膀,黄圃的苦还没诉完,孔总就开始跟她说起话来。孔总说回来了,外面挺冷吧?她笑着说是挺冷的,本想出去透一口气,结果冻个半死。“粉红佳人”有点儿塌了,她拿小勺舀着,大口大口地吃。明天霜降,得多穿衣服,孔总说。黄圃跟孔总碰了个杯,说,我这妹妹挺好,就是顽皮,闲不住。孔总说顽皮好,顽皮的女孩有趣。她拿眼皮撩了黄圃一下,挑着眉对孔总说,孔总您阅人无数,既然说我有趣,那我肯定有点儿潜力。别光停在潜力啊,黄圃说。她立刻从座位上站起,冲着孔总说,那是,有机会还请您多多指教,我单独敬您一个。现在她正抿着嘴笑,眼睛一眨一眨,做出可爱的模样,与之前相比,她简直换了个人。孔总说你先坐下,站着喝了不算,她眼珠朝上一转,说站着喝是我的敬意,坐下喝是您的情谊,我先表达敬意,咱再加深情谊。孔总大笑起来。从进房间起,我头一回看见他的牙齿,乌青的一排,泛着茶色,不知道是抽烟抽的还是天生这样。孔总对安琪竖起大拇指,说安琪我看出来了,你确实挺有潜力。她一仰头把酒干了,孔总也干了,黄圃说那我陪一个,说完他也干了, 三个人都笑了,气氛霎时轻松不少。他们就这样一杯杯地喝起酒来,彼此间敬来敬去,说俏皮话,每个人都红光满面。一瓶白酒很快下去大半,黄圃又加了两道菜,一个凉拌猪耳,一盘老醋花生。孔总抽着烟,朝半空吐一个烟圈,又圆又大。有一段时间她高兴得有些过分,两个男人说什么她都哈哈大笑。笑过一阵,她把身体坐直了些,用清脆的声音喊道,服务员,过来一下。我走到她身边,弯下腰问,女士有什么需要?拿听可乐,她说。她说话时眼睛完全没有看我,一只手摸着另一只手指上的玫瑰金尾戒。好的女士,我转过身去,感到自己的心开始坠落。
《偷手表的人》(下)将于明日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