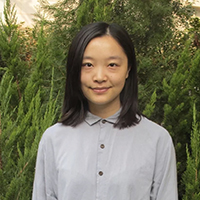细腻、扣住生活细节,捕捉感情的玄机。这是一段开始破碎的背德恋情,注定要承受重负,当人做出逾矩的选择,代价自然不可避免。
他是半夜两点打开门的。咔哒一声,锁开了。她在书房里有点慌张地问,谁?他走进来,看到她正在打游戏。连连看,不用动脑筋,最容易把自己放空。她从八点开始填美国签证的160表格,因为超时两次,到十二点才断断续续填完。虽然还有一大堆事情等着做,但她什么也不想,只想点鼠标左键,把三只猴子或三只猫的脑袋连起来,发出喵的一声然后消失。
他一进门,她就把游戏关了,不能像在自己家一样放松。他说你怎么还不睡觉。她笑嘻嘻问,你怎么来了?每次喝完酒,他总是回另一个家,有老婆和孩子住着的那个。他说我是来检查你有没有按时睡觉的。她笑着又关了电脑。
他去洗澡,她跑到厨房,把锅里剩余的粥转移到碗里,放进冰箱。上一次用保鲜膜的时候,不小心从中间撕开了,然后怎么都没法让两边平齐,撕出完整的一张。于是她只能把锅盖盖在碗上。他不在的时候厨房真脏,她想。
浴室传出水声。她敲敲门,进去刷牙。看见他站在玻璃后面,水溅在裸露的身体上。他说话了,用的是平时很少使用的句式,我有一个梦想。她一边刷牙一边笑,问他是什么。他说要建一个视听室,专门用来听音乐。原来晚上去朋友家喝酒,见到人家的视听室很不错,小孩子心理发作,也想要一个。她含着牙膏笑他,男人就是男人,弄一个视听室也要用“建”,好像是从地基开始,一点点把一个房子盖起来。他说是的,表情好看极了,喝完酒之后他才这么快乐。
然后她也洗澡,洗完一起去卧室。好多天没和他在一起了。他紧紧抱着她,嘴里有酒味。酒味好浓,她说。当然了,他回答。身上烫烫的。
那个朋友有个很有趣的叠名,离婚了,和女朋友一起住。吃饭时说起几年前看过的一部电影,几个人起了争执,朋友不帮女友反而帮他,女孩急了。当时就让我想到你,他说。
因为这几天例假,她好像总在发脾气。昨天下午不高兴,直接开门从车上跳下来。她没有接话,问还有什么人。
本来老婆也要去的,他说,后来有事不去,朋友的女友倒很高兴。
你是在暗示她看出了什么吗,她问。
对,女人都有直觉。
说着说着快睡着了,但是他的手一直不停。她感受了一会儿,转过身去抚摸他的。已经很硬了。
可惜,她说,今天不行。
你想吗,他问。
想,但是不可以。
他说那就好,我还以为你从来不想。
怎么会呢,她在黑暗里说。
入睡时已经快四点了。她感觉到他去客厅抽了一支烟。半夜醒来一次,上完厕所回来他在打呼。但很奇怪的,刚刚躺到床上,他就迅速把被子飞到她身上,盖得正正好好。然后用手臂揽过她,酒味浓重地在旁边呼吸。她想想好笑。他平时睡觉不喜欢被人碰到,看来是醉了,转身的时候手臂挥来挥去,肯定是醉了。
早上十点醒来。不知道为什么,她觉得这几天自己一直在皱眉,好像很疲惫的样子。也许是烫了头发。这两件事情没有直接联系,但是烫了头发多多少少会让人觉得疲惫。换句话说,会让人变老。她把他前几天扔在脸盆里的黑毛衣放进洗衣机,还有自己的袜子和内裤,然后去厨房洗碗。他刷完牙坐在沙发上,看样子还没有完全醒来。
地上真脏。过完年从家里回来她就注意到了,积灰的地方踩出一个个脚印。那几天老婆孩子旅行去了,他独自住在这里,在她回来之前把客厅的地板拖过一遍。但是男人做事,你知道的。她没有说什么,他有兴致打扫卫生她已经很高兴。这几天很忙,过年时中断的工作要重新拾起来,补写两份总结和展望,还在准备美国签证,所以对灰尘也就视而不见。
洗完碗是十一点。她问他今天的安排,他说要去工作。她把粥端出来,准备热一热然后继续弄资料。要进公司系统填表格,申请在工资证明上盖章,还要打电话预约面签时间,再看一看昨天提问的贴子有没有回复。这时他问她想不想出去吃饭。和他相处的机会让人很难拒绝,她犹豫了一下,还是说好。
她说想吃披萨。搬到他这里半年,她几乎没有吃过披萨和火锅。这种大份量的东西,一个人去店里点一桌会很奇怪。他想到有一家西餐馆披萨做得不错,但就在他家附近,会遇到很多熟人。
我带你去另一家,他说,那里有很正宗的意大利披萨,上次请朋友吃饭,喝酒花了两千块。
她听不太清后面在说什么。只觉得自己是生活在暗处的。前几天回大学听讲座,主讲人用嘲讽的口气调侃深圳二奶村,底下一片哄笑,连那些听不懂中文的外国留学生在交头接耳之后都笑眯眯心照不宣。她也笑,但不知道自己在笑什么。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她在心里说。然后很惊讶地发现,不知不觉之间,她已经把位置放到了大多数人的对面。她从来不觉得自己是那样的,事实上也有很多理由和借口,可是心不听那些。而更奇怪的是,她好像变得麻木了,这些话影响不了她。
然而还是有一滴眼泪掉下来。她在卧室换衣服的时候,把眼泪擦在毛衣蓝黄相间的横条纹上。他很敏感,经过旁边时特地仔细看了看她的眼睛。她装作没什么的样子,把毛衣套在身上。他不喜欢她哭,她知道的,况且也没有发生什么。
就去那家酒很贵的意大利餐厅。他开车,她絮絮说着什么。没来由地,坐在他身边时很容易想到,有一次她从机场回来,说想吃黑巧克力,他从背包里拿出五块,不同牌子不同味道,就是在这个角度这个姿势,从左边递过来给她。其中有一块到现在还没吃完,放在她和朋友合租的那间房子的冰箱里,而自从和他认识之后,她再也没有回去住过。她们很高兴,早上少了一个人抢厕所。但也问她,怎么不把你男朋友带过来看看。
餐厅里人不多。左边是小小的吧台,中间几排桌子,右边是开放式厨房,厨师把客人点的东西现场做出来。脱了羽绒服他们开始看菜单,她想吃玛格丽特披萨,炸奶酪,煎牛柳配薯条。他警告她说,煎牛柳是一道主菜,端上来很大一盘,她肯定吃不下。那就换成炸薯条和烤鸡翅,她说。这时左边来了一个爸爸,带着一个眼睛平平呈一条线,看上去像韩国人的小女孩。她看着她,想起前两天以为自己怀孕了,问他怎么办。
生下来,他说。
还好来了例假。事后她发短信问他怕不怕,他说当然怕。不过她还是很感激,他没有粗暴地说,去打掉。
她摸摸自己的领口。
有一个蝴蝶结。她突然意识到,刚才在卧室把眼泪擦在衣服上的时候,不小心把毛衣穿反了。蝴蝶结应该在后面才对。同事经过她座位的时候经常开玩笑,悄悄一拉把蝴蝶结拆开,惹她生气再嘿嘿笑着帮她绑好。她一下子觉得很窘迫,起身就去厕所。他在后面追问,你点什么,到底吃烤鸡翅还是煎牛柳。
随便,她扔下一句。
看见自己从镜子里一晃而过。不敢细看,散落在胸前的头发好像把领口遮住了。她走进隔间,飞快地把衣服脱下来,转一圈再穿好。摘下帽子理了理头发,静电,一根根都吸在脸颊上,赶也赶不开。
上完厕所出去。洗手时还是没有在镜子里注视自己,只感到一团模糊的影子,黑色的,面目不清。
回到座位上,她觉得有什么不对劲了。屋子好像比之前暗一点,阳光收起来,灯还来不及打开。右边桌上喝汤的男孩现在斜躺在一张空座位上玩手机。他已经点好菜,在对面喝水,因为开车暂时不能碰酒精。是发现了还是没有?从眼神看不出来。她挪了挪椅子,把嘴唇贴近杯口。这两天他脾气不错,她心里知道,容忍她耍耍小性子,来看她的时候还买了盐和橙汁。但因为这件事情,也许还有疲惫,她开始心不在焉。邻桌的女孩一点也不好看,但她一直看她,看她用颜色鲜艳的塑料叉子舀蔬菜吃。他以为她喜欢,说他的孩子也有一套,但是现在长大了已经不用。她继续看着,看见女孩的爸爸把白色T恤的领子竖起来,像农民企业家。嘲讽的是,餐厅墙上的电视里正在播一部叫《乡村名流》的电视剧。
一直到吃完她都不想说什么。他点了炸奶酪,煎牛柳,以及烤鸡翅。在煎牛柳端上来的时候,她看到的确是满满一盘。我已经告诉过你了,他说。她开始觉得肚子疼,什么都吃不下。她知道自己这样很讨人厌,就像塞林格在《弗兰妮与祖伊》里写那女孩怎么百般不爽地在男朋友对面吃一顿饭。她很烦这本小说,没想到今天自己就变成了她。
但是他还是很包容,说吃不下可以打包。然后除了沙拉,他们把所有的东西都打了包。煎牛柳一口没动,披萨还剩下两块,咬剩的半根奶酪也被她扔进烤鸡翅的盘子里。他去阳台上抽烟,她坐在座位上,慢慢把羽绒服穿回身上。
结账的时候他拿过背包,翻皮夹找信用卡。她想起他会在包里放一本笔记本,和她从前用了三年的日记本同样的牌子,只不过大几圈。几年前他有记笔记的习惯,写一些简短的句子,没什么修饰,但因为用词准确,她觉得算得上好。这几年因为感情的问题,日子过得有些混乱,渐渐写得少了。但是他说过,还是会继续写。前两天天气不错,她刚刚过完年回来,对他有些疏离,坐得远远的听他读十一月写下的一些话。是秋天的最后几天,他坐在看得到阳光和落叶的房间里,写外面的叶子铺得像一张地毯。她忍不住大笑,说最受不了这样的陈词滥调。落叶像一张地毯,没有美感的句子。
但是现在她忘了这些,只记得他从来不让她看这本子。她可以理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隐私。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她忽然很想在他的笔记本上画一根针。就是一根细长细长,银色的,底端极其尖利,顶端有一条细缝的缝衣针。她让他把本子拿出来,他一边刷卡,一边随手放在她面前。她没有翻开,只是抚摸封面,问他能不能在最后一页画一张画。他说不行,就要把本子收回去。她又重复一遍,他没有理她。
他们下楼取车。一路上她像中了邪,一直在念叨要画画。他问为什么,她说有两个理由,一是就像狗要在自己的地盘上撒一泡尿,她也要在他每一本本子的后面画一样有自己气息的东西。二是她已经想好要画什么。她没有看出来他有点动怒了,或者说,那个控制着她的邪念,这时候还没有打算让她察觉。上车以后她继续抱怨,他说别一个要求接一个要求,再说我就烦你了。她问什么叫一个要求接一个要求。他说我急着去上班,看你想吃饭就带你过来,知道你吃不下还是点了所有的菜,现在又要在我的本子上画画。这时她故伎重演,说你再这样我就跳车了。他没有反应。她问你要不要我走?他不回答。于是她跳了下去。
他开车走了。她跨过车行道和人行道之间的绿化带,抱膝坐在街沿上。看看周围,不知道是哪里。给他发短信:我不认识回家的路,今天就在这里坐到天亮。
他回电话吼她,问她想干什么。她说不知道。他说要工作,让她自己回家。她也吼回去,那是我的家吗?他非常生气地过来接她,把她送到楼下,让她自己上去。她不同意。然后他们上楼吵架。她把所有东西拿出来说要搬回去住,他说好,开始帮她整理箱子。她用笔记本电脑的电源砸他。他说我不想再过和从前一样的日子,请你放我去工作。她说我没有不让你工作。他说我不可能让你在我的本子上画画,这是我的笔记本,你要尊重我。
她知道他说得都对。但是她不愿承认。
他还说,非常冷静而残酷地,就像警告她煎牛柳有满满一盘,她一定吃不了一样,说我这是要告诉你,不是你提出的每一个要求都能被满足。你是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你想找人和你玩赌气的游戏,我不适合。
她有点懵,像一个被遗弃的孩子,垂着手站在时空的通道里。然后缓缓地说,我提什么要求了,吃东西算要求吗?那些真正的要求,比如和你一起去旅行,比如结束你的婚姻,所有我提出的真正的要求从来没有被满足。
快到四点他才走,生气她占用他的时间,说了很多狠话。她坐在沙发上,不知道作何反应。八点多,她给他发短信,说想听听他的声音。在那个老婆孩子待着的地方,他从来不接电话。她想起今天临走前他的手机响了,他接起来叫了老婆的小名。她以为自己麻木了,这种事情不会刺痛她,但是她深深记得那个脱口而出的字。
他老婆买的台灯放在他们的客厅里。多少次,她想用剪刀把那层白纸戳破。
他在短信里重申,她已经是成年人了,自己的情绪必须自己调节。她再发,他就问,你想在今夜把一切毁掉吗?
屋子里空荡荡的,她手足无措,拿出自己的日记本,在上面写:爱如何在自私与局限的前提下仍然保持纯净?接着又反省自己:认真工作,高高兴兴生活,真心地,不问明天也不计后果地谈恋爱。不要妄自菲薄。感受他的爱。
然后她把这些都划掉。躺倒在沙发上,看着夜色照进窗户,外面有树没有人。亲爱的,她喃喃自语,我从来没有想过要把一切毁掉,也不知道自己到底要干什么。也许只是生理期,一点点激素的变化让我变成了一个不可理喻的人。另外,你知道吗,宇宙的玄机有时候仅仅在一件毛衣的蝴蝶结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