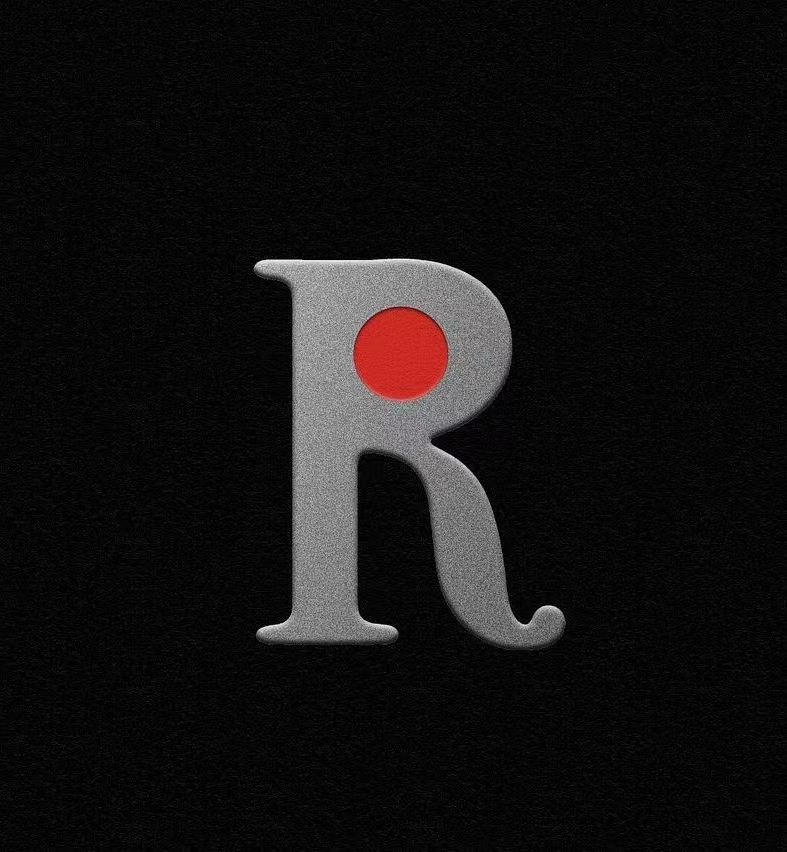结婚是在抵抗习惯,离婚是在抵抗世俗,在两者之间的状态,是在抵抗……文中的三个男人在推杯换盏中,表面镇定,可心里却都背负着关于女人的秘密。
一、平铺直叙
一大早,他开上车,拉着妻子,去往二仙山。二仙山距他们的居所一百五十公里,开车要一个半小时。那天天气不太好,起初有一点雾,后来雾散了,下起了小雨。雾和雨没能让高速关闭,这让他意外,也有些失望。上高速之前,他们在路边一家早餐店吃了饭,他吃了一根油条一碗豆腐脑,她喝了一杯豆浆。自从她的体重突破三位数后,就开始节食。吃饭期间,他问她落没落东西,现在回去取还来得及。她说没有。吃完,雨停了,他们回到车上,他把团在手里的餐巾纸扔出车窗,被妻子白了一眼,不过,他没发现。他嘬着牙花,发动车子,直奔高速。过了收费站,妻子翻包,突然说:防晒霜没带。他踩下油门,车速提到一百二:问你落东西没,你说没有,现在怎么办?妻子说:掉头回去呀。他说:高速啊,怎么掉头?继续提速,到了一百三。
此后的半个小时里,俩人都不再说话,他不停嘬牙花,她听着广播,一直换频道。路上车辆稀少,有一辆摩托车超过了他们,蓝色头盔划过一道亮光,刺他的眼,他骂了一句什么,她没听清。又过了十分钟,他们看到超过他们的摩托车和一辆货车停在应急车道,两名司机正在和交警交涉。摩托车司机摘了头盔,是个秃子,头颅依旧闪光。半小时后,妻子说想小便,他把车开进不远处的服务区,妻子上厕所,他下车,靠着后备箱抽烟。烟抽了一半,妻子还没出来,一辆摩托车停在他的旁边。骑手摘下头盔,挂在车把上,从裤兜里摸摸索索,掏出一支烟,继续摸索,最后看向他,说:大哥,借个火儿。他递过打火机,看到对方的光头上趴着一道疤。
两人攀谈起来。光头问他去哪里,他说二仙山。光头说:我也去二仙山,听说二仙山上有座庙,庙里没有和尚,就两个看门的,是公职人员,供着两尊菩萨,特别灵验。他问他是否要许愿。光头回答说是,去了二仙山不许愿,等于白跑一趟。他又问光头是否信佛,光头说:那不信,愿是替老婆许的,非逼着我来。说着话,他的妻子走出厕所,一边走一边擦着裙子。到近前,他发现她的裙子湿了一片。妻子咒骂着:什么破厕所,水龙头是坏的,能当喷泉了。光头掐了烟,对他笑笑,骑上摩托,走了。他觉得这个笑内容复杂。他们也上了车,往二仙山开去。一路上,妻子骂水龙头,骂保洁,骂服务区,他不搭话,仍在嘬牙花,并偷偷把音响音量调大。
下了高速,先过一座石桥,叫二仙桥,过了桥,到了二仙山山脚,把车停在停车位,停车位外面竖块牌子,写着“停车收费,一小时十元”。下了车,妻子又开始骂景区乱收费。之前他只在电视上见过二仙山,电视画面色彩浓艳,二仙山看起来像是一块甜度过高的抹茶蛋糕,见到实物,那不过是一个光秃秃的小山包,有一些石头,还有一些树。更多的是人,人点缀着山,使山花花绿绿起来。两人往山上走,他走在前面,她跟在后面,相距四五级台阶。刚下过雨,石头台阶湿漉漉反光,她脚下打滑,身子一趔趄,叫了出来,他回头看了一眼,继续爬山。到半山腰,路两边出现卖香和纪念品的摊点,妻子买香,他看纪念品,多是佛像手串之类的饰品。他拿了一串手串,放在手心摩挲,问摊主价格,摊主说一百八十八,他撇了撇嘴,将手串放回原位。妻子买好三支香,双手捧着走到他身边,他问多少钱,她说五十八一支。
再走半个小时,到山顶,出现一座红砖绿瓦的庙宇,重新修葺过,看不出年代。门上挂着一块匾,用红漆大字写着“二仙庙”。门口一左一右站着两人,身穿保安服,每人面前摆了一个纸箱,上面用记号笔写着“功德箱”。门前排着两溜儿长队,每个进门的香客主动往功德箱里投钱。他仔细观察了一会,有人投五十,有人投一百。妻子递给他一张一百的纸币,他接过来,问有没有五十的。妻子说求佛要虔诚,不能在乎钱。他又开始嘬牙花。
跟随人流走进,院内青砖铺地,对面有一殿,大门敞开,里面光线昏暗,隐约能看到香炉和两尊佛像。香客依次而入。他们前面是一对老年人,手挽着手,看样子十分亲昵,他们后面是个中年男子,面色阴郁,一脸络腮胡子,缩着脖子,好像要把头缩进胸腔。轮到他和妻子,他跟在妻子身后,进入大殿,殿内香气缭绕,妻子双手将香插入香炉,跪在香炉前的蒲团上,嘴里念念有词,不知祷告什么。他看到两尊佛像,均两米来高,一个虎头人身,一个牛头人身,背对而立,却又回首看向对方,皆目露凶光,想必就是二仙。拜完,出了大殿,又下起雨来,两人没带伞,见香客都往大殿一侧跑,便紧随其后。殿侧有一月亮门,进了月亮门,是一座三层高的现代建筑,上了大理石台阶,众人都在台阶上避雨,旁边有一旋转门。他往门内看去,正对门口是一吧台,吧台后面墙上挂着几只圆钟,将“二仙宾馆”四个烫金大字围在中间。他笑起来,说:是酒店。妻子看看天,说:要不住下吧。他想了想,说好。订了一间双床房。房间在三楼,阳面,靠中间。
宾馆有餐厅,在负一层,自助餐,有凉有热,有荤有素。吃饭时,他又看到之前的光头,光头也看到他,端着餐盘过来,坐在他身边,她的对面。光头说:幸会啊,又见面了。他点点头,笑笑。她没表示,用筷子对一株青菜不依不饶地进行裁决。光头吃了一口红烧肉,说:菜还行。她撇撇嘴,把青菜夹到桌子上:整根的,这咋吃?光头说:可能是粤菜师傅,广东人都这么吃青菜。光头吃饭快,转眼放下碗筷说:饱了,我先上去了,我住308,没事找我玩去。起身走了。吃完饭,他们回房间,他在门口看了一眼,对门就是308,门把手上挂着请勿打扰的牌子。
他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转了几个频道,都要收费。妻子去了趟卫生间,嘟囔马桶上有污垢,出来,撩起铺在床上的被子,大叫了一声,有虫子。他走过去,发现床上趴着一只黑色甲虫,妻子说是蟑螂,他觉得不像。这是北方,我还从没见过蟑螂。他这样安慰妻子。妻子并不认可,要他给前台打电话换房。他抽了一张纸巾,捏起虫子,扔到窗外,说:早上问过,就这一间了。妻子拉着脸,各个角落查看了一遍,再没见到虫子,才躺到床上去,扒拉起手机。他看向窗外,灰暗中升腾着白色的水雾,看不到雨水,只能听见雨落在地面和屋顶噼噼啪啪的声响。他关了窗,声音小了很多,拉上窗帘,房间内暗了下来,只有妻子手机屏幕散发出来的一方光亮,在黑暗中闪闪烁烁。他躺到自己床上,很快睡着了。
他在梦里掉进深渊。背后有人推,他没看见是谁,想看已经晚了。他的身子在黑色的雾中穿行,自由落体,什么都看不到,耳畔有风,通过耳孔,灌入他的脑袋,在里面鼓荡,头很痛。一直下坠,没有终点,他希望早点落地,粉身碎骨也好,万劫不复也罢,来个痛快,一了百了,总比身处无限扩张的恐惧中来得好。头被敲击,“笃笃笃”,把他的脑袋当成木鱼,还有和尚诵经的声音:
南 无 阿 弥 多 婆 夜 哆 他 伽 多 夜 哆 地 夜 他 阿 弥 唎 都 婆 毗 哆 地 夜 他 阿 弥 唎 都 婆 毗 阿 弥 唎 哆 悉 耽 婆 毗
他勉强睁开眼,发现和尚是他的妻子。他惊醒,出了一头汗。妻子在敲他的床头:你听听,外面吵什么呢?耳朵里残存着木鱼的回响,他撑起身子,听到走廊里有人在争吵。一男一女,男人声音熟悉,是光头。因为价格没谈拢,她要三百,他只给两百,最后女人骂了句“穷逼”,踩着高跟鞋,“哒哒哒”走了。他走到窗户前,拉开窗帘,雨停了,天还阴着,一个穿红外套包臀裙的女人走出宾馆,像是灰色的表皮上突然渗出的一滴血,异常夺目。妻子问,什么人?他说不知道。妻子说,是不是那种交易?他还说不知道。一会,敲门声响起,他问是谁,对方说:大哥,吃晚饭去了。光头的声音。
吃完饭,光头提议斗地主,他看了看妻子,妻子说:你们玩,我要休息。光头说:不够手儿,我再找个人。光头让他先回房间等,自己去买扑克,酒店旁边就有家超市。回房间路上,妻子嘱咐他别玩钱,他让妻子放心,申明,哪怕手机斗地主都充不起欢乐豆。
除扑克外,光头还买了一箱啤酒,罐装的燕京,冰过了,包装上挂着水珠。放下东西,光头又退出去,敲响隔壁门,一会儿,领着络腮胡走进来。
干玩没意思,光头打开三罐啤酒,说:咱边玩边喝。斗地主的赌注不是钱,输的一方要喝酒,很快他就喝了三罐啤酒,头有些晕了,想睡,但光头兴致还很高,说好不容易出来一趟,还不玩痛快了。捋着话头,光头又说到自己的妻子,一个疯婆子,见面就干仗。他又手指头上的疤说:看这儿,我老婆干的,从那儿起,我就不留头发了,提醒她,也提醒我自己。他说:我家倒不干仗,一天话都说不了两句。一直沉默的络腮胡突然说:不是想不开,千万别结婚。
玩到十一点一刻,妻子打来电话,说自己要睡了,让他在外过夜,免得敲门吵醒她。他退出牌局,匆匆回房间。妻子正在洗漱,脸上泡沫飞扬。妻子洗完脸,问他有没有拿自己的钱包,他说没有,她说她的钱包不见了。他让她再找找,她有点不耐烦,说都找遍了。于是,他叫来服务员。服务员查看了门锁,完好无损,又叫来经理,经理坚称宾馆的安保措施非常完善,不会进贼,让她再仔细找找。她很生气,指责经理态度恶劣。经理道歉,但就钱包丢失一事,仍在推责,并声称可以查看监控录像。
他们一起看监控录像,录像显示,从早到晚,除了夫妻二人外,没有第三个人进入房间。妻子又怀疑小偷是从窗户进入的,院子里的监控并不能照到三楼。经理马上否认小偷从窗户进入的可能性,说每扇窗都安装了铁丝网。他回想了一下,确认了这一点。他们再次返回房间,检查了铁丝网,没有弯曲或者撬动痕迹。经理再次请求妻子在房间里仔细找找。妻子发火了,指着经理的鼻子大骂。他不作声,开始翻被子,整理行李。他在枕头底下发现了那个巧克力色的钱包,他没有声张,悄悄将钱包藏进口袋,直到妻子说要报警,他不得不用咳嗽暗示妻子。但妻子的情绪完全被怒火控制,已经丧失理智。她报了警。
送走警察,妻子的愤怒变本加厉,坚信是他偷拿了钱包,他无从解释,佯装睡觉。一会,伴随着妻子的唠叨,真睡着了。半夜醒来,他发现自己躺在家里的床上,妻子就睡在旁边,他悄悄下床,从厨房出来菜刀,对着妻子猛砍。第二天一早,他睁开眼,妻子还在睡着,走廊里传来行李箱拖动的声音。原来是做梦,他顿感轻松,又有些遗憾。
二、叙述诡计
从三清梁步行下山,再走出两公里,到五里铺;五里铺搭一辆牛车(或者拖拉机),到四方镇;从四方镇坐公交,到县城;买一张去省城的车票,坐车大约两个半小时,到省城;打车去火车站(买票要查身份证,还好在这三十年的逃亡生涯里,他积攒了足够多的伪装经验,早就办理了十几张假证,这次他用的是一张海南岛居民的身份证,他在海南岛生活了几年,熟练掌握了当地人的口音),再乘十二个小时的绿皮火车,到了九龙市(离他的家乡近在咫尺);马不停蹄转公交,直奔二仙山。每年这个时候他都要经过一番长途跋涉,冒着被捕的风险来到二仙山,目的只是为亡妻祷告。
他的妻子死于二仙山上的二仙宾馆。是他杀了她。那是一个雨后的清晨,妻子还在熟睡,他从一个噩梦中惊醒,鬼使神差地抄起枕头,盖到了妻子脸上。之后,他在妻子身边坐了半个小时,消化完紧张情绪,他扔下妻子,独自离开宾馆。起初,他感觉轻松,直到走下山,整个身躯被埋在山的阴影里,他开始打战,胸膛里像掖了一块冰,浑身发冷。而后,恐惧袭击了他,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是个杀人犯。他跑起来,妻子紧跟在身后,如影随形,他只好加快脚步,以期摆脱妻子的鬼魂。他身上出了很多汗,却越来越冷。于是,他往南方跑。他渴望阳光,却不得不躲藏在阴暗之中。
他很后悔,这是显而易见的,无须掩饰。他想,每个杀人犯都会对自己犯下的罪行后悔,不管他们口头是否承认。这不是怯懦。绝对不是。
事情怎么会发展到这一步呢?他记得他和妻子刚结婚那会儿,还是很恩爱的,一心想对对方好,他发誓会一直包容她,她也立志要爱他一辈子。其实,结婚之前他就知道她爱唠叨的毛病,但是呢,当时他完全不觉得这是缺点,甚至认为这是性格开朗的表现,正好和他的内向形成互补。她的强势也恰恰能够制服他的懒惰,让他成为一个积极奋进的人。事实上,他们的婚姻也经历了层层阻挠,后来他想,如果他能在哪怕其中一个困难面前屈服,都不会是现在这种局面,偏偏,他全部克服了它们,亲手拉开了一场悲剧的序幕。
他们的相识颇具戏剧性,他的哥们娶了她的闺蜜,婚礼上,他是伴郎,她是伴娘。他和另外几个兄弟,每人手持一桶喷雪,对着新娘狂喷不止,另外两名伴娘远远躲开,只有她冲出来,护在新娘身前,手持笤帚疙瘩,对他们进行驱赶。这群荷尔蒙分泌过剩的年轻人把这视作挑衅,他们迅速转移了攻击目标,一边起哄一边冲她喷白色泡沫,不一会,她头上就像裹了一层蜘蛛网。气愤之下,她轮圆了手中的笤帚疙瘩,突然一撒手,笤帚疙瘩标枪一样射出去,正中他的额头。这是他霉运的开始,但在当时,他以为幸福来敲门了呢。他挂了彩,血顺着眼皮流下来,流到嘴里,是甜的。
他们离开婚礼现场,到距离最近的一处诊所进行包扎。她骑摩托车带着他。是一辆黑色的雅马哈250,新郎送新娘的彩礼,车头灯上还贴着大红的囍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他都认为雅马哈250是世界上最帅的交通工具。
摩托车庞大,她的身材娇小,上身努力前倾才勉强够到车把,这样她的屁股就难免接触到他的裆部。几次摩擦过后,他可耻地硬了。还好,她似乎没察觉。后来他想,那个笤帚疙瘩可能不是普通的笤帚疙瘩,是被施过“打我一下就会爱上她”魔法的笤帚疙瘩。他完全被她女强人的风范征服了。他们陷入热恋,爱情这东西,是自带滤镜的,会让对方显得完美无瑕。这是他婚后反思得出的结论。婚姻,就像一场战争,有时候关乎胜负,有时候关乎生死。
前几年,他到二仙山,听一名香客讲起二仙庙的来历。一个虎仙,一个牛仙。开始,虎一心要吃掉牛,在旷日持久的追逐和奔逃中,它们逐渐爱上了对方。牛爱虎威猛矫健的身姿,虎爱牛光洁油亮的皮毛。终于,有一天,它们心有灵犀般一同停下脚步,牛走到虎面前,说:我不跑了,你吃掉我吧,被你吃掉大概是件很幸福的事情。虎说:我现在舍不得吃你了,吃掉你我会很伤心。于是,它们相恋了。当然了,它们的结合遭到了虎族和牛族的一致反对,牛的父母晓之以情动之以理,告诫它老虎很危险,奈何牛已经被爱情蒙蔽,对父母的规劝不屑一顾。而虎那边呢,在它将自己的恋情公之于同族之后,遭到了上百只老虎的嘲讽,甚至有虎说:你晚上磨牙的时候会不会把你老婆吃掉?它当即发了火,驱散了看热闹的虎群。它们就这样顶着巨大压力走到了一起。
可想而知,婚后,它们的矛盾很快爆发。首先,饮食就无法调和,牛看到虎撕咬动物尸体,血在嘴边滴淋,会觉得恐惧和恶心,而虎也数次对牛寡淡的饮食习惯表示出鄙夷。其次,牛越来越受不了虎身上的腥臭味,敦促他注意个人卫生,可虎只当没听见,虎呢,偶尔也会嘲笑牛的洁癖。更为重要的是,它们的性格反差实在太大:虎外向,爱交际,朋友遍天下,时常有些狐朋狗友(真的狐和狗)来家里拜访,喝得酩酊大醉方才离去;牛内向,宅,没什么朋友,也不喜欢虎交朋友。争吵在所难免,吵着吵着,就要动手,虎亮出獠牙,牛架起犄角,都恨不得杀死对方。交锋过后,两人都受伤了,随之陷入冷战,都暗自发誓,谁先说话谁是孙子。它们分居了,各占据一座山头,屁股对着对方。三五年过去了,虎突然想起自己还有个老婆,就从山头走下来,走上另一座山头。它没看到牛,只发现一座牛的石像,屁股对着它,头勾过来,悄悄向后窥探。它有点伤心,坐在石像旁边,大哭起来,眼泪哭干了,它把自己也哭成了一座石像。
他觉得,这个故事中不中洋不洋,毫无逻辑可言,大概是开发商为了吸引游客制造的噱头,听过就故意忘了。这次在去往二龙山的长途汽车上,他又听前排乘客向邻座兜售这个故事。讲话的是个男人,听众是个女人。说话的间隙,男人还剥开一个橘子,分了一半给女人。他本想睡觉,却被吵得睡不着,他诅咒他们相爱,继而结婚。
上了山,在庙门前排队,在他前面是一对男女,应该是夫妻,他一眼看出他们貌合神离。祷告完,下起了雨,他住进二仙宾馆。晚上,有人敲门,他警觉,确认没有危险才打开房门,是个光头,叫他斗地主,他想推辞,又怕光头起疑,就答应下来。同玩的还有白天见到的那个男人,没见到他妻子。一边玩一边喝酒,他留着心,每罐啤酒只喝一多半儿,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同时,少说话。听光头说起自己妻子,他插了一句,不是想不开,千万别结婚。另外两人相视一笑,似乎深有同感,一起喝了个酒。
后半夜,他正睡着,警察来了,他一下子紧张起来,还好只是那对夫妻闹出的乌龙事件,他的担心一直持续到警察离去,缩在床上,心里说,他一定想杀了她。又想,谁没想过呢?不过有人行动了,有人没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