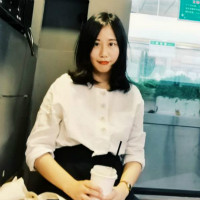我在逼仄的小巷中饲养我的童年,唯一的快乐都来自于那个“神秘人”的降临。
这些年,我总是会做一些有关“穿越”的美梦,我的要求不高,并不想穿到遥远的古代,建功立业,我只是想返回九十年代,回到我的童年,敲开我家那扇破旧的大门,然后对父母说,买房子吧,去深圳创业吧。
每当我将这个想法透露给父亲,并表示出对其职业生涯的不屑时,他总是会用一种复杂的目光望着我说,一切都不是你想象的那样。
“还记得豪杰吗?”
父亲的话如一支箭,将我迅速带回了访冬巷。那时我家住在一个菜场旁边,每天早晨都会被鱼腥味扰醒。那是一栋筒子楼,三家人共用厨房与卫生间,我在逼仄的小巷中饲养我的童年,唯一的快乐都来自那个“神秘人”的降临—一旦他出现在巷口,我就明白,我又能吃上糖了。
“神秘人”叫豪杰,说他神秘,乃是因为他的装束——他身形瘦小,看起来跟猴儿似的,总是戴着一顶宽檐的黑色礼帽,这让我想起美国西部片里那些腰间别着手枪的牛仔。和那些言语没有遮拦,什么都乐意讲的人不同,豪杰显得寡言、沉默。听母亲讲,豪杰和父亲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门对门的邻居,念同一个小学,同一个中学。在父亲结婚之前,他们俩的关系好得像是连体婴儿。
“他是做什么的呢?”
每当我问起豪杰的职业,父亲总是显得犹豫,一会儿抽烟,一会儿去开电视机,好像就是不想把话说清楚。那时我在念小学,对职业一事看得极重,总会幻想自己未来有一份体面的工作,并因此获得不菲的薪水。
那年夏季即将结束时,父亲出差回来,给我带了一个巨大的礼盒,我从外面完全窥探不到里面的世界。我问,这是什么?父亲笑笑说,你自己拆。我拿着裁纸刀,剪刀,左右开弓,费了好大劲才把礼盒给弄开。打开一看,里面是一个魔术套装,还附带一本厚厚的说明书。母亲撇嘴说,买这玩意干啥,浪费钱。父亲说,没事的,别人送的。
我这才知道,父亲这趟出差是去了广西,恰好在那遇到了豪杰,这个礼物是豪杰叔叔送给我的。
“所以他的职业是魔术师吗?”我天真地问。
“你说是就是吧。”父亲出差归来,十分疲惫,似乎没有心情跟我说太多话,他只是嘱托,让我好好保管这盒魔术套装,因为这东西贵得很。
那之后,我沉迷于魔术世界中,一会儿幻想从抽屉中变出兔子,一会儿尝试在扑克牌中参透有关命运的天机。我看着图纸上复杂的文字与步骤,总是会陷入一种幻觉之中——既然这些都是骗人的把戏,那么魔术师的工作岂不就是蒙骗大众?
后来的数月,城市变成了马戏团,里面上演着各种各样的狮子钻火圈或猴子踩自行车。过去那些或风光,或脸上洋溢幸福感的人瞬间变成了被奴役的动物,在我经过他们身边时,只感受到时代的残忍与绝情。
冬天时,父亲下岗了,接着是母亲,然后是舅舅和舅妈。外婆看着家里失业的青壮年劳动力,整天唉声叹气。父亲指着街边的电动三轮车说,实在不行,就想办法弄辆车吧,跑跑“麻木”,也能活下来。母亲没什么主意,打算到商业街问问有没有人需要服装售货员之类的。
那一阵,人们不再光临我的家,牌局和酒局似乎还有,但也只隐藏在那些幽暗的角落中,大街上无所事事的人越来越多,大人们个个愁云惨淡。我意识到有一些东西正在暗中发生变化,但说不出来那是什么。
唯一生意好的地方是巷子口的夜市,那儿充斥着不如意的酒鬼和试图安抚自己情绪的饿鬼。
春天来临时,城中出现了两桩令人胆寒的大案,一个案子是有人在公交车上安装了炸弹,车行驶到长江大桥上时,燃起熊熊大火,一整个车上的人都被炸飞,残肢断臂悬挂在大桥两边的树上。第二个案子是一群从北方来的劫匪,抢劫了商场的金店,并持枪打伤了一名警察,那颗子弹洞穿了警察的太阳穴。
仿佛是电影里的情节陡然被泼到了大街上,一整个三月,我惶恐不安,不敢坐公交车上学,生怕它爆炸。放学后,我也不敢再到处乱晃,担心又有哪个持枪的歹徒对着街上的行人一顿乱射。
我的情绪降到了冰点,整天怀疑有灾祸降临,而就在春天快要结束时,“消失”数月的豪杰再次出现,这一次,他换了一身崭新的皮夹克,头上依旧戴着宽檐礼帽。刚一落座,他就从包里掏出了各种各样的新奇玩意儿,里头有一些进口的糖,还有一些我叫不出名字的洋货,不过,最吸引人眼球的还是一个黑色的“大哥大”。他把“大哥大”放到桌上,对着我父亲说:“送给你的。”
我父亲自然不敢接受这贵重的礼物,母亲也吓了一跳。我那时天不怕,地不怕,对什么都感兴趣,上去就把“大哥大”拿起来,放到了自己的怀中。母亲见状,对我劈头就是一个巴掌,我疼得不行,将东西还了回去。
那一顿下午饭,大家都表现得很沉默,我平时就贪玩,还挑食,所以也没上桌吃饭。母亲说,既然你不爱吃饭,就滚一边玩儿去吧。我抱着皮球离开了家门,但实际上,我还是站在门口,小心翼翼地听着里头的动静。
大人们说的话,我总是听不懂,我也搞不清楚他们具体有什么烦恼。我那时觉得,没工作也不是坏事,起码父母多了很多时间陪我。殊不知,没有工作对大人而言是很恐怖的事,等于天塌了下来。
趴在门口,听着屋内的话,夜渐渐漫了下来。虽然他们的声音不大,但我也很听到一些话语,听来听去,我大概明白了他们在说什么。似乎是豪杰叔叔在做一个大买卖,缺一个司机,我父亲驾驶技术不错,所以他希望可以让我父亲跟着他一起做事。我心想,这是好事啊,总比在外头骑电动三轮强,可母亲说着说着,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哭了起来。
筒子楼隔音不佳,母亲的哭声很快引起了邻居们的注意,隔壁的陆爹爹见状,一把将我抱到旁边说:“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人啊,你要当心啊。”我知道陆爹爹指的人是谁,但豪杰叔叔并未在我面前做过什么坏事,相反,他很喜欢给我买各种各样我爱吃的点心、糖果。
母亲的哭声止住后不久,豪杰走了出来,他看见门口的我,摸着我的头说:“饿不饿,我带你去夜市吃东西。”
“好!”
就这样,我跟着豪杰来到了夜市,这里的东西泛着诱人的香气,看起来可比我妈做的那些寡淡的饭菜强。我指着一锅卤物说:“我想吃卤蛋。”
豪杰听到我的要求,很快响应,帮我买了两个卤蛋,但他突然把东西藏了起来,不给我看。
“我来跟你玩个魔术吧?”
“什么魔术?”我仰着脸问。
“我会把鸡蛋变成小鸡。”
“扯,怎么可能?”
在昏暗的路灯下,魔法悄然发生,那两颗卤蛋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只嫩黄色的小鸡。我被这一幕吓坏了,误以为是蛋孵化成型,吓得哇哇大哭。豪杰把那小鸡收了起来,不知从哪儿又把卤蛋变了出来,交到了我手里。
“魔术好玩吧?”他问我。
我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喜欢魔术带来的刺激感,但不喜欢那种被蒙在鼓里的感觉。
没过多久,街市两边的小摊小贩越聚越多,气氛一瞬间变得格外热闹,眺望远处,可以看到一个小百货公司。逢年过节,我们都在那儿买年货和糖果。豪杰突然指着那个百货商店说:“看到了吗?过一阵,它就会炸掉的,嘭,都是火。”
我不明白他的意思,就楞楞地看着,想象他又在说什么变魔术的事情。
那天夜里,豪杰留到接近凌晨,才离开我的家。临走时,他赠给了我一把玩具假枪,说是在深圳买的,本想送给他外甥,但外甥已经有很多玩具了,所以就多了出来,留给我。
联想到城里的劫案,我并不敢接受那把枪,豪杰把它塞到我的怀里说:“拿着,别怕,人得学会保护自己。”
后来的一个月里,豪杰隔三差五就跑到我家来,他会带我去台球厅玩。那时娱乐场所都是连着的,左边是台球室,右边就是录像厅,再然后是游戏室及舞厅。我自小就喜欢看电影,能在录像厅一坐就是大半天。豪杰问我,喜欢看什么?我说,《纵横四海》,他问,为什么喜欢看这个?我答,因为周润发帅啊。
我不怎么会玩台球,只能看大人们“比试”,豪杰的话不多,但几乎把把都能把人压制下去。有时,人们怀疑他在作弊,他只是笑笑说,这玩意儿还用得着作弊吗?
除了台球,豪杰还会陪我去游戏厅打拳皇,我没什么章法,总是一顿乱按,豪杰却颇有条理,手法不重,但总能发出大招。输了的我,总是垮着一张脸,如乌云压顶,豪杰总是拍着我的肩膀说,这玩意儿没什么秘诀,熟能生巧。
在我父母为了生活奔波的那段时间里,豪杰俨然成为了我的“教父”,他带着我走街串巷,吃喝玩乐。虽然母亲很不喜欢我和豪杰待在一起,但父亲总是说,算了,没关系的。夜里,我隔着一面轻薄的窗帘,听见父母在议论豪杰。母亲讲,每天跟这种人在一起,孩子会学坏的。父亲叹了一口气说,放心,豪杰这个人害谁都不可能害到他头上。
初中第二年,我们全家搬离了访冬巷,我也被迫换了一个学校念书。由于是转校生,人又生得瘦小,很快被“不良少年”选中,成为了他们欺负的对象。在学校里遇到的事,我不敢往家里说,父母工作辛苦,我没理由再让他们有多余的烦恼。
我再一次过上了担惊受怕的生活,并祈祷初三毕业快点来临,这样我就能逃脱这个恐怖的学校。
一天下午,我独自走在回家路上,走到窄巷中时,几个人冲了出来,问我要钱。我打开钱包说,没钱,前几天不是给过你们了吗?那些人不依不饶,作势要揍我。这时,我看见豪杰出现在了巷子口,他摘掉黑色礼帽,露出脸上的刀疤。那些人见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瞬间转换了攻击对象,我用手指蒙住眼,不敢看,但好奇心还是让我透过缝隙窥到了一切——豪杰没有动手,他只是吹着口哨,拿着几只玩具似的小飞镖。他将飞镖扔向那些不怀好意者,那些人一边走,豪杰一边扔,最终,这些人被豪杰的气势吓退,一哄而散。
“没事吧?”豪杰走过来,摸了摸我的脑袋。
“人得学会保护自己。”
我佩服豪杰的气势,但自己又生性胆小,完全做不到他那种云淡风轻。那天,豪杰“护送”我回到家附近的巷子口,并告知我,他有很长一段时间不会再来了。我问,你要去哪儿?他笑了笑,拍着胸脯说,大买卖,你们小孩不懂。
那之后,日子过得不咸不淡,我每天都在思考,豪杰嘴里所谓的大买卖究竟是什么?父母对此事只字不提,他们只是警告我,用功读书就行了,其余闲事不要多管。偶尔,我会企图弄清豪杰的身世,但每当我问起周围有可能认识他的人时,大人们总是摇摇头,让我不要再问了,知道了没有好处。
这样的日子不知道过了多久,在某一年,雨水泛滥的季节,我在家里做作业,听到外头有人敲门,砸门的声音很重,一拳一拳的,像是个机器人。我离开书桌,打算去开门,母亲迅速将我拦住,蒙住我的眼说:“别去。”我问:“出了什么事情吗?”母亲拼命摇头,就是不说话。
父亲走到窗边,打开了录音机,里面流淌出厚重的歌声,这歌声和砸门声混在一起,显得格外不和谐。母亲指着床说,你先去睡觉吧。我摇摇头说,睡不着。母亲说,听话,快去。
“是豪杰叔叔吗?”我问。
“不是的,你别瞎打听了。”母亲严厉地望着我。
那个夜晚,我把自己蒙在被窝里,其实心里头全是事,我好奇那个砸门的人是谁?父母为何又如此恐惧?难道是家里欠了外债,有人来追债么?似乎也不是,毕竟那个人也只是一直敲门,并未喊打喊杀。
不知过了多久,雨停了,敲门声也止了。我从被窝里钻出来,说自己要上厕所,然后跑到阳台上去看那个敲门者究竟是谁。夜太浓了,将一切涂成黑色,我什么也没看清,只是感觉那个人的脚步很重,很重,似乎不舍离去似的。
后来,这件事成为了我家里的一个禁忌,一个十足的谜团,每当我想问些什么,父母总是瞪着我说:“大人的事情,小孩子少管。”
然而,我不可能始终是一个小孩,我会发育,会成长,我始终会变成一个大人。而父母会长出白发,会衰老,他们会渐渐失去对一些事的话语权。
在进入社会之后,我逐步意识到了父母谋生的不易,同时也开始想,会否贫穷就是一种会遗传的玩意儿。有人继承了万贯家财,有人继承了贫穷,而我们大多数人都是后者。
刚去北京的时候,我雄心万丈,误以为自己可以进入大公司,凭借着自己的努力,做到管理层,赚到百万年薪,但事实相当打脸,我混到三十多岁,不仅没有升成主管,更没存下几个钱,我和父母当年一样的“失败”,一样地“一贫如洗”。
更可怖的事情是,因为年纪太大了,外加行情不好,我遇到了公司裁员,并且成为被裁的第一批员工。
我灰溜溜地滚回了老家,滚回了那个窄小的阳台上。父亲望着远处的夕阳,剥花生米吃。他没有责怪我什么,只是让我坐着,他去给我泡一壶茶。在这个过程里,我忽而想起,数年前,父亲来北京探望我,我和他坐在窗明几净的咖啡馆里,我雄心万丈地给他描绘未来,表示自己不会“重蹈覆辙”,不会再像他们当年那样了。父亲那时只是笑笑,说咖啡不好喝,并未说其他的话。而现在,我忽然意识到了自己当年的狂妄,原来在时代面前,没有几个人可以勇立潮头的。
在阳台上,我和父亲说了很多闲话,不知怎么的,我鼓起勇气,再度提到了那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那天来找你的人到底是不是豪杰叔叔啊?”
父亲点了点头,笑着说,当时来找他的人确实是豪杰。豪杰家里有七个兄弟姐妹,从小就穷,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更是吃不饱饭。后来豪杰的父亲很早就病死了,家里就更穷了,豪杰很早就出来混社会了,什么苦都吃过了。
“后来呢?”我问。
“后来?后来啊,他发现吃苦没用。路上的小摊小贩,还有各种工地上的工人,哪个不苦,但是呢,他们能发大财吗?”
我点了点头,想着父亲还要继续说什么。这时父亲忽然不说话了,他转过身,去一个五屉柜旁,翻出了一张泛黄的旧报纸。很显然,是年代产物了,那报纸旧得吓人。我打开一看,发现上面显眼处,记载了一个抢劫犯被逮捕的全过程,那个犯人的名字我并不认识。
“这是?”
“是豪杰啊。”
灰暗的照片上,男人并没有戴帽子,他的头,有半边像是生了秃斑,十分丑陋。我又看了好几眼,试图辨认出豪杰的影子,可是什么也看不出来。
“别看了,快进来吃饭,都几点钟了。”母亲在客厅抱怨着,我和父亲异口同声地答:“好,知道了。”
吃过饭,我帮母亲洗碗。在哗哗的水流声中,母亲告诉我,当年,豪杰确实是干了很多笔“大买卖”,赚了不少钱,但做的都是一些违法乱纪和铤而走险的事。他对谁都不信任,唯独信赖我的父亲,所以想让我父亲给他做司机,这样,他跑路的时候,会安心一些。
父亲不是没有动过心,毕竟这钱来得简单又快,但他最终还是关上了那扇门。
“上了那条路,就无法回头了。”父亲按下了电视遥控器,继续看他的抗日神剧。他说人一辈子,可能就是这样,想发大财,就要铤而走险。做普通人呢,可能就会比较穷。
我坐在沙发上,呆呆地望着电视机,想说些感慨的话,但又觉得命运如此诡谲,绝非我三言两语可以总结。我从塑料袋中取出了一只苹果,又拿起水果刀,缓缓地削了起来。
“别急,慢慢来。”
父亲说话的瞬间,我手中的水果皮应声而落。我始终还是没能力削出一个完整不断的苹果皮,但这似乎也并不妨碍什么。
“嗯,挺甜的。”父亲接过我手中的苹果,边咬边说:“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