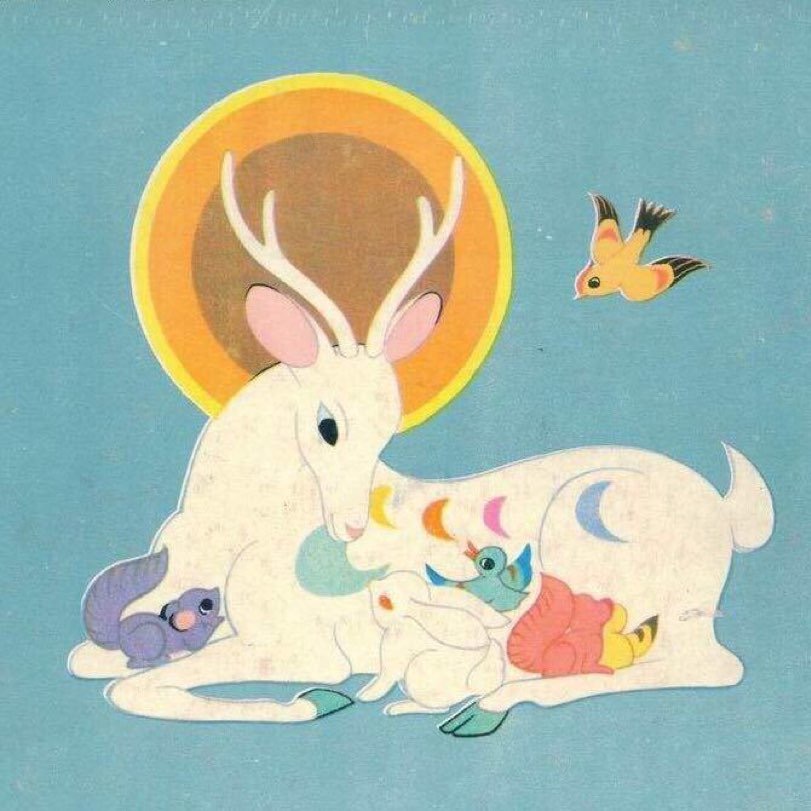留在这里,需要一腔无边的孤勇。
1
这里还没有高铁站——说“火车站”会更确切一些,因为不管是高铁动车,还是绿皮火车,这里都坐不到。好多年过去了,这里仍然只有一座汽车站。最频繁的车是去市里和省会,最远的车可以去首都。
汽车站的辐射能力有限,旅人从三百公里以外的非大型城市过来,多数需要中转,甚至不止一次。到站后,小车司机们纷纷上前招揽生意,问他们去哪个镇乃至哪个村。包车的费用逐年攀升,但还价往往能还个两到四成。
我的租客在黄昏时分抵达。雨后的天空像一张湿润的胭脂色笺纸,车站上方盘旋的鸽群是无意间甩上去的一溜儿墨点。大巴车下客一如往常般聒噪混乱。所有人都争先恐后地挤在行李舱那里,嗷嗷待哺的一窝乳猪似的。有个大个子弯下腰钻进去,起身起得急,脑袋结结实实地撞到了舱门,不禁骂骂咧咧地走远了。听口音是徐州或鲁南一带。
租客是个大学刚毕业的小伙子。他等人都走完了才去取他的行李。发现他除了背上的登山包还有两个行李箱和一个大编织袋时,我上前搭了把手。
他说,耽误你时间了。我说谈不上,最近淡季,门市没什么人。
后备箱本身就有些杂物,他比较大的那个行李箱是三十二寸,放不下,只能让他坐副驾驶,再把行李箱放置在后排。他掏出面巾纸,用矿泉水淋湿后简单地清洁了一下行李箱的表面和滚轮。我说没事,车本身就要洗了。
2
我的居所在县城东北。此处汇集了城区最古老的一条商业街,最大的寺庙,当年最兴旺的工厂和最红火的百货商厦。明明是花木繁茂的五月天,但它显得比深秋还萧条。晚上九点钟以后,行走在扩建并铺了柏油的空旷马路上,两侧店门紧锁的商铺和梧桐树叶间渗下来的荧荧的路灯光,会让人怀疑它的真实性。它看起来太像一个录影棚,一处造景。
租客对它的历史一无所知,没有理由为这片区域的没落而遗憾。他只问我,附近哪里适合跑步。我告诉他,从门前的巷子穿过去,在生长着一株高大合欢的岔路口向北,沿着坡上去就可以看到淮河入江水道。河边是跑步的好去处。
作为一个刚刚考过来的异乡人,跑步在那时是他下班后唯一的活动。逢上我没有在店里吃饭的傍晚,我们也会一起在院子里吃点东西。无花果树和栀子被晚风吹来一阵阵的草木香,水果特价的广播遥远地循环着。
他和大学最要好的同学也是这样喝了一顿酒之后,就各奔东西。同学去了深圳一家五百强,他则是参加了一次公务员和两次事业编考试。另外两个岗位没进面试,他只能来这里,一个他以前从没来过,甚至从没听过的地方。我说,我们建县很晚,历史上像拔河一样扯来扯去地归属周边的几个大县,建国后又过了十年才有了名姓。看上去不够现代化,但和一些古县比起来,它年轻得多。
他解释说这跟一个县的年纪无关,只是和它离得太远。长三角地区,除了上海苏杭等大城市,他熟悉的地名也就只有金华和义乌这两个物流最常见的起点。好比包邮区的人也很难叫得出他们那里的南澳、饶平、博罗、鹤山……
3
租客工作的地点在乡镇。每天七点起床,八点钟搭同事的顺风车,历经半小时车程到达单位。中午去职工食堂用餐,午间回办公室小憩,下班后再跟同事们一起回来。一起拼车的有四个人,大家轮流付油资。
至于为什么不住在镇上,他的说法是不想长期看不到高楼。高楼不需要太多,也不需要太高,有一点点就可以。镇上没有高楼。他们的办公楼共计五层,是镇上最高的建筑,像台显微镜一样检验着那片土地的全部细节。
他刚来,没有按部就班到他考上的那个岗位就职,而是被统筹安排,分派到办公室。办公室不是广义上的办公室,在体制内,它是一个专有名词,类似于秘书处,打理领导的日常事务,负责消息的上传下达,是重要的枢纽科室。来这里工作,能更快地了解业务的范畴,单位的运转模式,以及同事们的个性。
报到当日正好赶上乡镇启动新一轮秸秆禁烧工作,他服从调度,加入专项工作组,接手的第一项任务是将在编在岗的人员和九个村的八十七个联组结对。他原本以为这就是做一张Excel表格的事,但现实大大出乎他的预料。这一天,前前后后大概有十几个同事过来找他。以“前些天脚崴了”“老家就是某个村的”“孩子还不满周岁”等形形色色的说辞请他重新调整,就近分配。
基层机关办公室的布局不像企业的格子间,一般是一个办公室三张桌子。按照级别高低工龄长短,资格最老的坐在最里面。他刚来,自然坐在头一个,紧靠着门边。
一个剪着干练短发的中年女同事来串门子,朝最里面的桌子努努嘴。
“这泡怂死到哪块去了。我来看看他是眼睛瞎掉了还是手害得流脓了,得罪人的事叫新来的细伢子做,简直是把苦把人家吃!”
他后排的同事笑了笑,说客商来了,人被书记叫过去作陪。
“好事他跑得比谁都快。”
他几乎听不懂这里的方言,但隐隐约约能通过声调和咬字判别出一句话释放出的是什么样的情绪。他配合他们的对话,无奈地笑了笑。此后的一周内,他的五官频频捏造出这种笑容,不是为谈话内容,而是为方言本身。他在问路、购物、采集村民信息……各种语境中,都会出现迟滞的几秒。假使不这样,那可能是对方在听到他带有岭南口音的普通话的一瞬,眉眼间就率先浮现出一种“这是个外地人”的轻微警觉。
和年轻人对话,这种隔膜的效应会减弱。他们主动和他说普通话。但他们本地年轻人之间交流也还是用方言,那样的气氛是说普通话怎么也达不到的。就像吃一顿饭,光吃饭也能吃饱,而喝一点酒就可以吃得更畅快更交心。
4
梅雨季节来得比往年早。
东南季风让太平洋的暖湿气流细化为连月不开的绵绵阴雨,大理石地面上漉漉的脚印,盥洗室四壁间淋漓的雾珠,和橱子里流连不去的霉味。
我本以为租客要花一段时间来适应长江中下游地区这恼人的初夏,可他很快就网购了一个带有烘干功能的布衣柜,训练有素地组装好了那些长短不一的管子。他把内衣袜子衬衫分门别类地装了进去,热情地邀请我来参观。
“和广东的回南天差不多。”
他生于潮汕,初中时举家迁徙至佛山,后又转到广州念高中,直到大学毕业都没有真正意义上离开过广东。大四他考过一次研究生,没能上岸。毕业之际,他面临几种选择——继续考研,投简历等Offer,回佛山到父亲和叔父一起经营的洁具厂里做事,还有就是考公。
父亲征求他自己的意见,他说想考研或考公。父亲说,男孩子还是早点进入社会得好,何况学的本来就是技能型专业,想深造以后念在职研究生也不是不行。
他能看得出,对他这个独子,父亲不忍心讲出真相——他早已认识到他没有打拼的个性和受苦的能力。一个缺乏决断的内向的男人去做一份按图索骥的工作更为恰当。
他留恋校园生活,不想完全放弃考研,试图同时筹备两种考试。但书目纷繁,内容浩瀚,双管齐下的难度很大。最后他决定专注考公,防止一心二用以致一事无成。学校通知他们在六月三十日之前搬离宿舍,他原先将东西打包好,打算拖回佛山,临时又改变了计划。
他租下一间房,留在广州备考。西关的老式民宅里,他的卧室连着一个狭窄的小阳台。门敞开,不远处的市井喧嚣像是时间的一部分,榕树下邻居们的交谈更是清晰可闻。他一点也不感到吵闹,反而很心安。有种婴儿在羊水里泳动的奇异的感觉。
“现在想想,在广州逗留,是因为心里很清楚,留是留不下来的,哪天一走,回也就很难再回得来。”广州的那个岗位一共有三百四十多人竞争,他落第几乎顺理成章。还有一个岗位相对可惜,只差一点点就能进面。至于最终考取的这个事业编,一方面招聘三人,一方面仅限应届毕业生,大大提高了命中率。
面试成绩值得官方就公平性和严肃性宣扬很久——面试的十人中,本县两人,本省的其他地市三人,除了他以外的四个外省人分别来自齐齐哈尔、池州、贵港和宁德,而最终晋级的都是外省人。另外两人相对幸运地分去了离城区更近的乡镇,但池州的那个丝毫不介意这些细微的差异。她的目标是以最快的速度考回她待了四年的合肥。
5
把乡镇当成跳板的考生不在少数。没有上级的明文规定,组织和人社部门也不能过多地行政干预,例如在招考时限制户籍和服务期。更何况许多本地考生参加工作后也会继续备考,寄望进入市直省直单位。他们案头露出一角的公基行测参考书是最有力的证明。
乡镇留住人很难。不止是在编的人员,凡稍有些体力和技艺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待在家里的皆为老弱妇孺。就连农民也不愿意再守着田野。流转过的土地承包给大户后,耕种和收割全是大规模集体作业。
县城文化馆的人来乡镇开研讨会,他负责会务,也旁听了一会儿。会议的主题是如何保护发源于此地的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一种风格独特的秧歌。前不久,这个项目的国家级非遗传承人去世了,他们为后继无人感到焦虑。会上,大家纷纷献计献策。轮到一位老者发言时,他请大家不要怪他泼冷水。“年轻人插秧吗,年轻人愿意种田吗。不要说年轻人了,在座的上岁数的,你们还插秧吗,还愿意种田吗。现在全都是机器了啊。真要像当年那样唱秧歌,恐怕要请科学家发明一种机器人,叫机器人配合栽秧机在田里唱。有些东西的消亡是自然规律,不是你和我可以力挽狂澜的。但好在我们如今记录的手段很高明,可以录音,可以录像。若干年以后的年轻人如果看到了,像我们今天看到化石一样兴奋、好奇和向往,那就是它的幸运。”
消亡的不仅仅是如此这般的民间文化,还有乡镇乃至县城本身。我告诉租客,县里对外宣称有四十万人口,其实常住连二十万都不到了。未来的某一天,也许会兴起上世纪末撤乡建镇那样的浪潮,把人口不足的县合并。这个县历经几千年才有了得来不易的属于自己的名字,也许又将改姓他人。
6
返粤过了一个春节再回来,租客平静的生活起了微澜。一方面,县里的网信办听说他是计算机专业,想通过宣传部借调他帮助工作。另一方面,他参加上一年度红十字会志愿服务活动认识的一位青年女教师正式向他表白。
在我看来,这两件事都是好事。他反倒是考虑了很久。
他不喜欢自己的专业。如果喜欢,他会像那些被戏称为“程序猿”的同学们一样去上海,去深圳,甘于英年早秃,用代码为自己在996的内卷职场上垒筑铜墙铁壁,抵御互联网行业残忍的风刀霜剑。被别人发现他的技能也未曾令他萌生慧眼识珠之类的感激——进入体制后,他逐渐转型,慢慢成为一个文科生,统计、填表、写材料。回归本职后,不出意外,他将成为领导眼中最爱的万金油、多面手、复合型人才。这种口头的美誉置入“老人动动嘴,新手跑断腿”的环境里势必打开能者多劳的局面,而且时间一长,人人都会觉得理所应当。
至于那个女教师,他的第一反应不是自己对她有无好感,而是未来,她能不能跟他走,或他能不能为她留下。
粗略地估算一下,大抵近十年内,县城体制内适婚男女的比例严重失衡。教卫两大系统的情况更为突出。有个亲戚在医院做护士。她择偶的标准非常简洁明了,仅仅要对方有一份正式工作。可就算是这样,也让她待字闺中整整六年才成功出嫁。她的情况不是个例。
在县城,所谓的正式工作仅限于“铁饭碗”,也就是公务员、事业单位和国企。拥有这个身份的人往往也希望另一半在性质上与自己“比翼齐飞”。科长与医生,教师与银行主任……都是体制夫妻常见的搭配。只是这些年,在编的男青年不仅锐减,成家也早。他们像香椿,一旦冒出芯芽就被眼尖的食客掐走。主动示爱的女教师恐怕正是感受到了这种危机,才早早先行一步。
两桩我眼中的好事到底都被租客婉拒了。工作上,他对比了借调后的收入,发现不光是隐形的福利待遇差了一大截,明面的交补和下乡津贴也将成为历史。情感上,身为独生子女的教师不会和他去往三千里外的城市,他也不敢轻易下狠心久居异乡将自己一生流放。他有一位以人才引进的方式招录过来的女同事,与跟她一批招引的某个同乡惺惺相惜,相处一年后就地成婚,安家置业。没有人脉,没有资源,在人情网比都市更细密的县城里,一切都从零开始。有了孩子后,日子过得愈发紧锣密鼓。尽管双方家庭轮流派出代表援助,更多的时间还得靠这对年轻夫妇自力更生。她和租客闲聊时自嘲,说就算毕业后不回老家留在西安天天揣着肉夹馍挤二号线,也不会像今天这样马不停蹄上气不接下气。
留在这里,需要一腔无边的孤勇。
7
有一个近些年更名为森林公园的林场位于租客工作的乡镇。每逢盛夏,县里会按惯例举办地方性节日,带动旅游消费,促进招商引资。这个时候,包括租客在内的镇上的职工们都要去森林公园值班,给景区提供政府层面的必要帮助。
租客很喜欢林场。林场种植的树木是清一色的水杉,一棵棵英挺如兵,列队般整齐排布。
“很神奇的,当时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不是一大片树林,是一大批人。”
他的值班场所是个类似于报刊亭的小铁皮屋。有时候太闷,他也会出来走走。在离杉林有段距离的一个池塘边,他发现了一截树桩,看样子也是水杉。树桩很粗,截面乍见已模糊,细细察看,年轮密集而丰富。他待了一会儿,准备折返。这时来了个略有些年纪的农民,戴着草帽,提着红色的塑料桶和鱼竿,径自走到池塘边,坐在那一段树桩上开始做垂钓前的准备工作。
租客旁观了片刻——农民技法娴熟,很快就钓上来三四条。鱼的个头不大,但很鲜活。租客问都是些什么鱼。农民说是小草鱼,昂刺之类的。说完抬起头来看了他一眼,反问他是哪里人。租客很罕见地俏皮地用学来的方言回答他:“我就是这块人啊。”
二人都笑了。
租客又问他,这棵树是不是被他所伐,好充当钓鱼时的坐具。农民摇了摇头。他说是有一年夏天,大风刮倒的。“要是它长在那边的林子里,反而不会倒。真是‘物似主人形’呢。”
这句谚语是说一个人用的东西或是养的宠物花卉,时日长了,面貌气质自然而然就会近似于主人。一开始租客并不懂,但农民娓娓道来,像展开画轴般从头细说了案例,予以佐证。
他说几十年前,有个南京来的女人不合群,不和贫下中农打成一片。不管是上工下田,还是吃饭洗澡,她都独来独往。没什么人会说她的好话。她刚来的那年,公社号召大家植树造林,她插的那个生产队带头响应,她就跟着大伙儿一起来到这里种树。人们常见她干完了活,一个人去池塘畔坐着,身边是一棵刚栽下去不久的和她一样瘦弱的小树。等到树长得有她一人半那么高的时候,她和一个修无线电的工人结婚了。婚后,她还是隔三差五就来池边树下坐着,直至县剧团下来招人。她由于会唱一点京戏,被剧团选中,从此去了县城。
乡里的人再见到她是她跟着剧团来农村巡演。这里的观众更爱听扬剧淮剧黄梅戏。京戏和她这个人一样,并不受待见。大概又过了三五年,一次演出中,她唱《苏三起解》唱得好好的,突然倒地不起,送医后没抢救过来,诊断结果是脑溢血。
她丈夫按照她的遗愿把骨灰送回南京。没有人质疑这个做法,认识她的人都知道,她最大的心愿就是回南京。她的丈夫在给乡里乡亲修无线电时透露了更多不为人知的细节。比如她曾经乱用血压药,想制造症状,请组织准许她回南京;比如她在池塘边种下一棵树是因为南京她家附近也有个差不多的池塘,池塘边也有棵树;比如她一直和南京一个名为嘉骏的男子互通书信,从信中内容看来,二人相交非浅。
结婚对别人来说,是互相的成全,对她来说,是自我的放弃。
租客听懂了,这是一个下放到这里的知青的悲剧。
哪一位去往南京转,
与我那三郎把信传。
言说苏三把命断,
来生变犬马我当报还。
这段唱词为她的悲剧画上了句号。
租客远眺杉林。那里碧波翻滚,白鹭翩飞。五十年前,上山下乡,知青们汇集于此,种树成林。三十年前,追逐着改革开放的浪潮,林场改制,逐步向市场经济靠拢。二十年前,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成为普遍现象,夏季举办的地方性节日里,号称天然氧吧的森林成了纳凉避暑的最好去处……这些往事如春江东去,浩浩汤汤,后人记不分明。只有那个种下树,后来倒在舞台上的女子在他心里烙下印迹。五十年后,他作为又一代知识青年,来到最基层,站在了她曾经站过的地方。
8
我的房子算是祖产,历经三代到我手里已经很旧了。拆迁办的人来量过不止一次,每次都不了了之。这里早就不是县城热门的区域,政府卖给开发商很难有什么大价钱。住户稠密,赔偿金也不是小数字。
拆迁无望,邻居们租的租,卖的卖,还有的推倒重建或重新装潢。我原也有这样的打算,看到他们的房子焕新后反而比之前难看,翻新计划也就搁置了。再说院子里还有我视若珍宝的枇杷石榴绣球,“人挪活,树挪死”,大兴土木必然影响花草的生长。
因缘际遇,租客恰巧就是看中了这个房子的老相和植物,说很像他在广州的住所。“很多花,阳台不封,顶上还有露台,露台上也种花……广东的屋子都是这样的。在这能找到这种房子太难得了。”
他所言甚是。政府拆掉了老街,好像用压路机就可以碾平县城的皱纹。接着又凭空建了一座毫无来由新砖新瓦的古城,好像网红妄图注射一针玻尿酸就能复制出奥黛丽赫本的风采。许是梦想出现络绎的游客一边品尝随处都能买到的特色小吃,一边顺手带件小商品批发市场统一供应的纪念品的盛景,古城像丽江古城、凤凰古城和全国大同小异的古城那样设计了商业街,提前挂好了银铺、绣庄、茶楼、酒肆等莫名其妙的老字号店招,但不见几家商户入驻。
空荡荡的古城就像是袖珍版的县城。看不见什么年轻人,只有卖不掉或卖掉了也没人住的房子。看不见实力,只有和实力不相等的野心。——这一点,入江水道北岸的电视塔最能说明问题。不知道哪一任父母官是突发奇思,还是看到黄浦江和珠江都穿城而过两岸生辉心存艳羡,就把县电视台驱赶到了荒无人烟的对岸,造了一座侏儒版的“东方明珠”或“小蛮腰”,而忽略了那不及上海广州百分之一的人口。难题交给了电视台自己,一早一晚的通勤班车根本无法让记者准时准点在主城区完成采访。于是行政和业务分家,记者仍留在老办公楼随时待命。光景一长,管理者也发现新窝很难焐热,一众倦鸟不等令下就纷纷归巢。斥巨资修建的新办公楼里除了比楼更新的一流设备,仅剩下保安和他养的几条流浪狗。
纳河入城的蓝图不知哪年哪代才能成真,但我分明记得,城中有一条河在二十多年前被填为平地,铺成干道。河网纵横的水乡城景自此黯然失色。明明出土过新石器时代的文物,县城却总以得名太迟而自认晚辈。又要反复瓦解与重构,又要寻找积淀,一直在文化上没头没脑地乱撞,想奋力终结那种精神无据而灵魂无根的状态。
比起县城种种画虎不成反类犬的借鉴,我效仿南国人家种三角梅失败的经历还算不得贻笑大方。“冬天又潮又冷,零上比北方的零下还冷,人挺过来都费劲,何况花呢。广东到处都是三角梅,真是好。不过我很久都没去了,还是以前带团的那会儿。有个广州的地接,和我玩得很好,总叫我再去。”
“以后去不用找他了,直接找我。”
……
租客在这里上了四年班,跑了四年步,拼了四年车。第五年,他辞去工作,像毕业后的那年一样,潜心备考。我问他考哪里,他说是佛山一个区的公务员。下班后,搭乘广佛线再转乘一号线,用三十五分钟就能去到热闹的北京路步行街,吃到他最喜欢的那家肠粉。
最后的那一年,他没有固定收入,靠给一家广告公司零星地剪辑一点视频维持生活,还要挤出一笔钱来交社保。这些他都没有告诉父母。
我觉得他完全可以边上班边复习。他却害怕归期遥遥无期,坚持要逼自己一把。
我有个朋友说过,有的事不作兴说万一,好像说了,这个万一就中了。对它要满心满意地祝福,只许好,不许坏,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我谨记此言,对万一只字未提。租客倒看得很开,主动给出了折戟沉沙的假设。倘若是那样的话,他也还是要回广东去,去珠海。他的一个同学利用这几年迅速成长,刚从外企里跳出来成立自己的工作室,邀请他过去帮忙。
我问他,如果这里是广东的一个小县城,他会不会留下来。
他想了想说,也不会。缓慢、寂静、狭长的生活不是不好,只是有时会眩晕。一早醒来拉开窗帘,茫然得像在大海中央——这不仅仅是从小地方到大都市奋斗的年轻人才会有的心境。平原上的人去高原会缺氧,高原上的人到平原会醉氧。恐怕是相同的道理。
在凋零的镇上,他也曾见到过人头攒动的景象,但仅限于每月的初三和十七。古历这两天赶集,本地人称之为“逢街”。从油盐酱醋到鞋帽衣裤,从食品到五金,从老人机到小家电,一整条街像火锅那样辛辣地沸腾着。据他观察,卖得最好的东西永远附属于电瓶车。这种县城和镇村的主力交通工具,夏天需要遮阳篷,冬天需要挡风被。后来出于交通安全和文明创建的要求,不光禁止驾乘者私自在电瓶车上安装遮阳篷,还敦促他们规范佩戴头盔。这么一来,那种一线城市屡见不鲜的顶部带两根竹蜻蜓会迎着风旋转的头盔就成了逢街群众中最走俏的单品。他们经手的土种鸡土种蛋小磨麻油浅水藕经过一道道安检,一个个转运中心去往都市。都市的趣味和时尚也逐级淘汰到他们手中。
逢街过后,小皮卡和大货车就开走了,开往下一个镇。它逢街的日子是初四和十八。清了场的道路只剩下菜帮子、吊牌、撕开的用于封口的胶带……和复杂的气息。整条街如梦初醒。像火锅食毕,再美的食材也是残羹冷炙,唯有领口的怪味催着人尽快离席。
他深感奇特的是逢街的流动大军里竟有牙医跟着四处走穴,现场给村民洗牙、拔牙、补蛀牙、装假牙。患者多是上年纪的老人,他们坐在尘土飞扬的路旁,面对着人来人往,打开光怪陆离的口腔。城里人瞻前顾后需要狠下决心的事,在这里就像端个凳子出来晒晒太阳那样随便。
他听到有人问一个排队的老奶奶怎么不让儿子媳妇领着上县城牙科看看。回说他们太忙,她也怕去,看到街上开得飞快的车,心里慌,听到车喇叭也害怕。
握着日子的手掌,各有各的纹路。他们或者也不想每个月只依靠这两天来把一整个月安排明白,就像他本心上也不见得多爱一整个月下来也未必有两天闲暇的城市,只是大家都习惯了,习惯那样活着。但他回家的次数并不多。起初是经济原因,没有太多积蓄,而来回一趟机票费用高昂。两年后,众所周知的公共卫生问题不仅使得出行异常困难,也让公职人员最大化地投身到防疫工作中去。他记得,第四年,他被安排到省道卡口检查过往车辆。三班倒,夜班从晚上九点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他以为夜里的车不会太多,再怎么也可以稍微盹一下。事实却是和白天一样,一刻不休。
夜间以大货车居多。隔着护目镜和朦胧的夜光,他拦下车,仰起头,让货车司机们出示行程码和核酸报告。有的司机穿越了大半个中国,行程需要上划才能浏览完毕。久而久之,他感到,不管那车斗里拖的是建材、食品、废旧、化肥、家具,还是一笼一笼的鸡鸭鹅猪羊,那些司机都长着同一张脸,脸上都写满了同样的生计与年月,双亲和妻小都在一脚刹车一脚油门里陪伴着他们驰向同样的曙色。
有次凌晨三点多,他的防护服已湿透,正要去处理,远远地又射来了车灯。驶到近处,他看清了,车牌是罕见的“粤”字打头。
显然这一路上,各地的政策和手段都相似,司机降下车窗,娴熟地打开页面供他查验。他看过无误,说道:“甘夜仲赶路,去边啊?”夜行疲倦,司机本来没有意识到,说“扬州”,随后眼睛立马像天提前亮了似的:“你系广东人?”
又有车来了,多耽搁一分钟都可能堵车。
他向司机挥挥手:“夜晚揸车小心。祝你生意兴隆,168一路发。”
9
租约到期前一周,一个年轻的男孩过来看房子。租客出去了,我领着男孩简单地看了一下房间。里面有几个整装待发的纸箱。我告诉他我住楼上,一般不在家吃,厨房基本给房客一个人用。他说他应该也不怎么在家吃,乡镇有食堂。
又是一个刚考过来的年轻人。——租客回来后,我如是对他讲。
他买了几样卤菜,其中的素鸡是我们这里的名产。我们依然在院子里坐下,暮色依然优柔地在窗棂与玻璃间逡巡。“过去,知青有老三届,有新五届,有后五届。现在看看,我们应该叫又五届。五届五届又五届,陆陆续续地,总会有人来,总会有人离开。”
我们吃一筷菜,喝一口酒,没再说什么,却好像把话说尽了。吃完了饭,他还会去河边跑步。我对那里再熟悉不过了。虽然现在也不丰富,但从前县城旅游的资源更贫瘠。河边,还有从河边向河心延伸的一大片生长着柳树的草滩几乎是小时候老师带我们春游的唯一去处。每年汛期,上游开闸,陡然抬高的水位就会将它淹没。远远地,只能看到柳树最高的那一截树梢在水面上沉浮摇曳。但它们一直没死,好像也永远不会死,来年春天照旧是孩子的游乐场。甚至我们一点一点地看着它从野生滩涂蜕变至今,被冠名为湿地公园,像一个学着做闺秀的野丫头。
白天,人们在河边钓鱼,放风筝。晚上遛狗,散步,谈恋爱。租客跑步时撞到过在树丛里接吻的情侣,也曾在筑堤的石头上看到骂人的话。他说那字刻得很深很用力,好像很恨地在说:“某某某,你个二胡卵子。”
我不禁大笑。他一定是亲耳听过有人这样骂人。我说你知道吗,江淮官话里,这的确是骂人的话,指的是“瞎搞”“捣蛋”。可是偏偏有很多人用它来称呼南京青奥会的吉祥物砳砳。调侃的背后隐藏着一种深沉的感情,那就是你丑,你滑稽,你比不上从前那些吉祥物甜美娇憨,只因你是我的,是我们的,就再怎么嫌弃你,都不能不喜欢你。那么,“某某某,你个二胡卵子”下面没写出来的那一句,不一定不是“你怎么还没来找我”。
他恍然大悟,但他看到河那一岸孤伶伶的广播塔,心情绝不会像我这样复杂。每当它亮起,变色,变到通体纯红,在我眼里就是一个直直插入大地的感叹号。
从高高的河堤上望过去,有感叹号孑然地映衬着,县城的天就变得更加开阔。晚照沉甸甸的,明净而浑厚,像酝酿了很久的心事。天的下面是暗黢黢的楼影。一如他说得那样,“高楼不需要太多,也不需要太高,有一点点就可以。”那些不算太多也不算太高的楼影浓缩了他回还的梦,帮助他与曾经的自己更快地重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