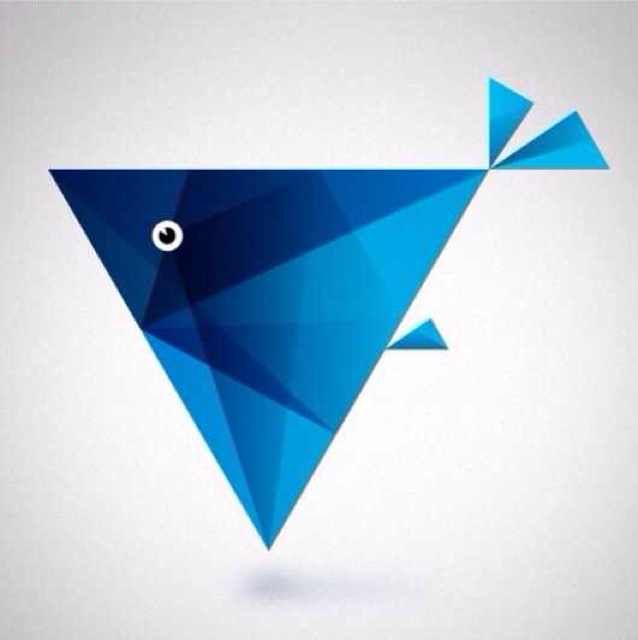约定的事情平平无奇,偶然相遇才弥足珍贵。
一、巨型草叶
我是在一个早晨挥舞着一把小镰刀走进那片草地的。草非常高,每棵都直直刺向天空中的云朵,远看像肩扛刺刀行进的队伍。一朵奇形怪状的云已被刺破,被高处的风胡乱吹向更远的地方。我的头顶上一下子变得空空荡荡,仰头时毫不费力,再低头才发现自己已远离村庄。
我的目光被一片巨草挡住,草丛里隐约传来动物走路的唰唰声,让人怀疑远处也有一对耳朵在听。我停下脚步,抽出镰刀,准备开始割草,我要为我日渐瘦弱的白羊准备越冬的粮食。它正藏在另一片草地上,等待通红的落日沉向大地边缘。
我是被一只白色翅膀的鸟引到这里的。我本来只想在村子边上随便割些草,冬天还有好久才能到来,我有足够的时间散漫生活。那只鸟故意在院中的梧桐树上叫了一声,然后扑棱着翅膀飘向了这里。我觉得它在叫我,我的周围没有别人,它只可能在叫我。于是,我拎着小镰刀,背着柳条筐一路颠簸到了这里,意外发现了这片巨草。
起初,我还以为自己遇到了一片玉米林,心里还在好奇是谁将玉米种到了一片荒野之中。走近以后我才对自己的孤陋寡闻感到羞赧,那是一片我没有见过的巨草,每棵草都顶着一颗巨大的水珠,水珠在初升的太阳下泛着彩色的光。微风吹过,那些水珠开始轻微地晃动,我总担心它们会掉下,心也跟着不住晃动。它们大概是许多天前落下的雨。那个夜晚,我知道野外正在下着一场大雨,我只听到雨滴下落的簌簌声,它们没有落地的声音,原来全被草叶稳稳接住。
巨草接住水珠的一瞬间肯定会深深弯一下腰,再直起,一下一下点着头。别的水珠不会再落到这棵草上。地上的草与天上的水珠数目相同,一棵草只接住天上的一个水珠。多余的水珠被风带到另一个村庄,那已经与我无关,那里会有另一个孩子发现它们。
现在,整片草地都是我的,没一个人来和我争抢,这让我很意外。我砍了三棵草,筐已经满了,三颗巨大的水珠坠落在地上,砸出三个蛋坑。土地肥沃松软,轻踩一脚就会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巨草下面有许多动物的爪痕,我能想象它们在夜晚小心穿行的画面。
整个白天我都在巨草下方乘凉。我怕别人发现我的反常,开始慢慢等待黄昏,黄昏到来我便有了天然的屏障。我低着头走在一群同样低着头往村子赶的人中,我知道每个人都小心地隐藏着一个秘密。我们互不交谈,谁都不想先泄露自己的秘密。
黄昏时,我在巨大的蝉鸣声中走进村庄。太阳已经落山,炊烟一股股向天上蹿去,星星隐藏其间。我将巨草倒进羊圈,把小镰刀挂在院墙的泥缝里。我突然发现,镰刀已经锈迹斑斑,许多年时光突然消失。镰刀尺寸太小,今后再没人使用它。
二、目光飞行
夜深人静的时候,总有风到来。它们在野外集合时我就觉察到了,它们会专程来吹响院子中的梧桐叶。多少年来,那些毫无规律的声响一直在梦里惊扰着我,使我觉得自己并未远离这个院子。我的肉体已睡熟,只剩下目光慢慢推开屋门。一只白羊站在柔软的月光里,悠然地咀嚼着巨大草叶。它的身体也变得巨大,像一头白色的牛。我开始担心它会叫,那叫声肯定会惊醒一村庄做梦的人。
月亮周围的云向东移动,院子里交替明暗,空中像有一盏晃动的灯笼。羊的影子也跟着胡乱晃动。羊脚下仅剩的一片巨大草叶被风一吹,慢慢飘了起来,木筏子一样随着水波晃荡。目光飘到草叶上,它便晃晃悠悠,飘向广阔的银河。村庄慢慢变小,我看到了它的整体轮廓,许多房子杂乱的石头一般排列在河流沿岸。河流?这是一幅充满矛盾的画面——我从未见过村庄的河流,我只听父亲描述过那条早已干涸的河流。
远处,一颗火流星坠在一座高山下的树林里,我仿佛能控制那团燃烧在空中的火焰。我本以为树林里会燃起大火,但却没有,火流星钻进树林后销声匿迹,整片树林纹丝不动。火流星在空中留下的亮色轨迹从尾部慢慢消失,那是逐渐融化的玉树琼枝。
那座山眼熟,是多年后我外出读书时遇到的一座山,我刚走出村庄便迫不及待地去看一座山。眼瞅着太阳即将落到山的另一边,同伴开始担心一种只在夜晚飞出的讨人厌的虫子。山脚下的水流里游着一些花背鱼苗,我蹲下来看了许久。同伴催促我继续向前,我们终于在黄昏时爬上了那座山。
晚霞异常绚丽,铺满天空,同伴脸上漫着一层变幻的光。一段破烂不堪的野长城,像我家多年的院墙,随时有可能倒掉。景色是美丽的,是在村庄无法看到的,我便决定稍作流连。同伴突然离我而去,不知所踪,她和那座高山一同消失了。我记不清她的名字,她的形象也慢慢变成流沙,我象征性地喊了几声,其实内心知道,我的声音根本跑不出目光所及之地。
我感到自己即将迷路,便站在山上四处张望。我的村庄重新出现在月光下。多么安静的一个村庄啊,整个村庄沉在一个巨大的梦底。梦像一条河流,在云层以下地面以上的空间内流淌,最下层是老人的梦,最上层是孩子的梦,风没有梦,风本身就是梦。
我看到了自家的玉米地,看到父亲从村庄里站起,变成一个巨人。他掀开一片云,没有发现我,只得去掀另一片云。整个天空的云被翻遍,一场大雨降落在村庄的野外,被一片巨草轻轻接住。一只萤火虫引领着我的目光开始降落,一个村庄开始迎接我。我看到了挂在院墙泥缝里的生锈的小镰刀和墙角破烂的柳条筐。为了避免暴露,我的目光先落到院中的梧桐树上,看暗中无人才慢慢飞回屋子。载着目光飞来的那片巨草叶子,缓缓落进了羊圈,被白羊轻声咀嚼。
年轻时的父母在熟睡,他们旁边是另一个小小的我。整个院子显得那么嘈杂啊,蛐蛐抚着瑶琴,蝉鸣铺满夜空,老鼠肆无忌惮地拜着圆盘样的月亮。
三、同样的梦
我的到来必有特殊含义,我可以看到多年前的自己。我需要阳光的普照,需要露水的浇灌,需要饱腹的食物,需要一个落脚之处。屋子里的粮仓贮存着多年的余粮,母亲掌管着粮仓的钥匙。村外多年不变的庄稼又一次丰收了,父亲再一次费力地将庄稼收割、晾晒、贮存,生活再一次进入一个漫长的循环。
午后,一个稚嫩的声音在背后叫我的名字,邀请我玩一个多年前的游戏。一个孩子他慢慢走出屋门,我便看到了多年前的自己。我坐在梧桐树夸张的树荫下,向他讲起自己做的梦,讲到一半的时候,他站起来,讲了梦的另外一半。我张大嘴巴,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原来我们做着一样的梦。
那个孩子讲完以后,直直地走进院墙,随后墙里响起了他的脚步声。我觉得那堵墙是一卷帘幕,帘幕后应该是一个车水马龙的城市,那个孩子肯定走进了一条灯火阑珊的街道。他的消失和出现一样神秘,让人无法捉摸,他能在任何地方消失,也会随时出现。约定的事情平平无奇,偶然相遇才弥足珍贵。
我开始长久地关注院中的墙,它慢慢升高,变成漫天遍野的暮色。我看不到边界,便在一个夜晚长吁短叹。我永远追不上他,心境杂乱无章。屋檐下飞舞的雨丝,随风升起又降落的枯黄树叶,一个漂浮多年的轻声呼喊,真的不会留意一串远去的脚步声吗?我真的在这个村庄长久地生活过吗?
眼前的一切使人产生了怀疑,那些拼凑的画面变得毫无意义。我又感到内心在缓慢地坍塌,那极其细小的声音只有我一人可以听到。我坐在院中的葡萄架下,远远望去,天空中未散的炊烟,保持着一个多年前夏日黄昏时的怪异形状,那是一座缓慢飘舞的空中楼阁。柴草燃烧后产生的呛鼻味道在院子中散漫,使人顿感困意来袭。落在墙角矮草上的蝴蝶,突然向墙外飞去。星星已经隐隐出现,缓慢到来的黑夜让我放缓轻浮的脚步。
坐在巷子里的老生又在黄昏时端出饭碗,虚情假意地招呼着我。那是美味佳肴,整条巷子飘着面条的香气。我饥饿起来,但我知道老生早已将碗吃空。我在黑夜叹气,那个孩子总在黎明回来,在我的窗外练习拳脚功夫。他重重踩着地面,哐哐的声响让人感到节奏之美。我跟他穿过黎明时空空的街道,走向村庄南面巨大的麦场。他转眼又消失了,将我自己留在最高的麦秸垛上,等待那个拎着拐杖远远呵斥我的驼背老生。我会一直等到晚上,月亮升起时老生才会来到麦场,向我讲述一个有偿故事。
四、破土而出
佝偻着身子的老生像一只刚出土的金蝉。他头裹一方布巾,身着宽大的粗布衫,手中的拐杖出奇地重。白天他不爱露面,只爱踩着月光出门。下午的风从西面刮来,在麦场铺满青草和泥土的味道。远处树林的剪影直直顶着低垂的星空,无数蝉鸣向天空汇聚,看不到的流云使星星不断眨眼。
老生缓缓坐上早被我擦拭干净的石碾磙,咳嗽一声,麦场便在层层的蝉鸣里晕出一片宁静。前一夜,他的故事只讲了一点,留下了一个大大的悬念,我伸长脖子,饥饿的雏鸟一样张嘴待哺。
又是那个金蝉子九世轮回的故事,老生总能找到金蝉子与耳边蝉鸣声之间的联系,我早已知道他的伎俩。他开一家药材铺,家中藏有许多线装书籍,蝉蜕是他妙手回春的灵药。
故事结束时,我向老生交上几个蝉蜕作为听资。老生捋着胡须,频频点头,临走前使劲一跺地面:“你听到大地之下的咯吱声了吗?那是无数金蝉在拱向地面。”
大地确实在晃动,地下隐藏多年的金蝉,似乎有无穷的力量。我向树林走去,晃着手电筒,往树干上乱照。许多说话声在树林更远处隐约亮起,一句话亮一下,树林里便有了许多球状闪电。我走了他们走过的一条路,所有的树木他们都照过了。我决定停下,等待那群人离去,我不能让我的竹笼再一次空空如也。
黑夜笼罩的大地之上,那些杂乱的脚步声终于潮水一样层层退去,说话声慢慢飘远,球状光亮团团熄灭。村外成了我一个人的,我变得开心又感到孤独。我害怕他们中间也会有一个人躲在角落里,便开始边走边咳嗽,故意暴露自己的行踪。
我终于在一棵不起眼的杨树上,发现一个浑身沾满泥土的金蝉。它本来不急不慢,被我灯光笼罩的一瞬间,开始拼命向上爬。我用木棍敲击着树干,在它面前制造一场地震,在它即将逃出我的控制范围时,又将它挑落下来。草丛无法将它藏起,我打开竹笼,将张牙舞爪的它引入笼中,随即关上监狱的大门。
夜里破土而出的生命躲过了那群村里的人,却没躲过我。它开始在笼内左冲右突,发现无路可走后又静静地抓着笼壁养神。它在地下隐藏了多年,积攒的力量没有用武之地,便开始假装睡着。我拎着竹笼继续在村外游荡,走了许久,却再无收获。
五、金蝉脱壳
夜已深了,村庄开始沉睡。我拎着竹笼,走进专门为我留的一条巷子。每走一步便有一声狗吠,巷子里有了一架声音的木梯。狗不认识我的脚步声,遥远地方传来的脚步声太轻浮。我悄悄摸进院子,将竹笼放在窗台上,用手电筒一照,发现它半个身子已从壳中钻出,折叠的翅膀在逐渐伸展。它身体稚嫩,还无法飞起,需要一个长夜让翅膀变硬。
我也睡去吧。推开屋门,我整个人开始恍惚,屋子像要倾斜,我扎煞着双手保持平衡,却依然站不稳,向着一侧倾倒下去,躺在成片的星光下。呜呜隆隆的声音在脑子里旋转,闪闪发光的草开始满天乱飞,那是短暂的混乱。进入睡梦后所有的影像全都消失,只剩一种声音绵绵不断地摇摆。那是变幻不定的蝉鸣,时而高亢,时而低沉,像许多更加细小的声音汇聚而成的一阵风。风无法捉摸,从窗台摔到地上,从地上滚到院子中央,不断颤抖。
天光照亮院子,院中正乱作一团。竹笼滚到了院子中央,被几只母鸡包围。母鸡轮番啄着竹笼,每啄一次,笼里便传出一声蝉鸣。我挥舞着木棍将鸡群轰开,将竹笼挂在木棍的顶端,觉得自己挑着一盏守夜的灯笼。我开始炫耀,昂首挺胸走过巷子和街道。没人看我一眼,仅半天工夫我便觉得索然无味。蝉在我的面前一声不叫,好似一个哑巴,我决定将它放走。我打开笼盖,高高举着,它爬到笼口,稍作迟疑,振翅飞出,绕树三匝,飞进梧桐树冠。
夜里的清露将成为它无忧的饮食,茂密的梧桐树叶会为它遮挡月光的打扰,那是绝佳的藏身之处。居高的金蝉开始奋力叫嚷,声音从树冠源源不断流出,顺风飘过下个村庄。所有的蝉鸣都来自那棵梧桐,蝉鸣无休无止,将天空层层顶高。
秋风又起了,我一连几天没听到院中的蝉鸣,于是在一个午后爬上了梧桐。我的目光曾经在此短暂停留,我看到的景色多年未变。我以高出村庄的视角再看村庄时,便发现村庄的每棵树上都镇守着一只蝉。我一拱头,蹭得树叶哗哗坠落,一只秋蝉吱啦着,从我的头顶离去。越来越多的秋蝉从村庄的树上离去,它们汇聚到一起,扑棱着翅膀,向村庄外面飞去,转眼钻进田野上腾起的雾气中。
年轻的母亲在院子里看不到我,便有些着急,她慌乱地走出了家门,沿街叫喊我的名字。我默不作声,隐在梧桐树顶的风里。整个村庄越来越安静,我有点害怕,便抱着梧桐树干滑到地上,静静站在院子中。母亲抱着一堆柴禾走回院子,一眨眼的工夫,她已是满头白发。她看不到我,一个透明的人一样从我的身体里径直穿过。天在那一个瞬间黑了下来,我看到一轮巨大的月亮和触手可及的星空,星星像一颗颗巨大的水珠,摇摇欲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