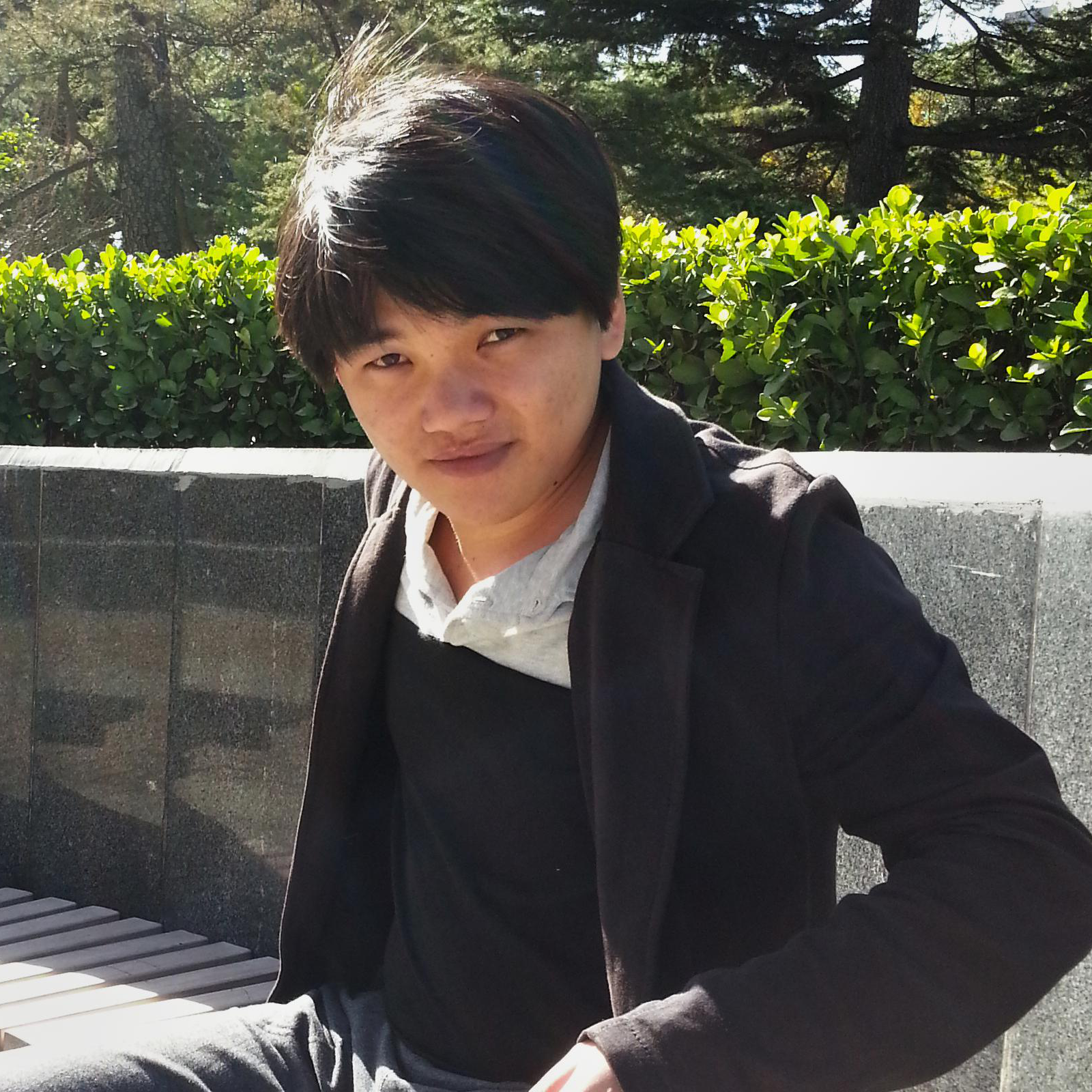人活着不易,每天都要花费超过十二小时努力工作才能赚到柴米油盐。
进入旋转门要快,把自己当成精准的齿轮,否则会被这栋大厦卡在门外。在我前面,已有四男四女迅速钻进了这扇旋转门,只有我仍站在外面,找不到合适的时机进去。我想起刚来这座城市的时候,不会坐电梯,不管是直梯还是扶梯。我花了三个月学会坐电梯,花了更多时间不会在这座城市迷路。
当我在地铁里闭上眼睛都不会坐过站时,一睁眼我已在这座城市待了快十年。
我坐地铁抵达这栋大厦。周末的地铁里没什么人,可我却不习惯坐下来,而是仍靠在车厢的韧带处,每次地铁转弯时,都会感受到隧道在跟地铁掰手腕。从地铁出来后,贴满车厢的整形广告继续载着别人往前驶去。这栋大厦和太阳都在我的头顶,可我走到旋转门前仍花了半小时。在这十年间,我进过各式各样的门,其中以弹簧门和折叠门居多,唯独没有进过旋转门。我不知道旋转门里等待我的是什么,每次搬新家的弹簧门里都是经久不散的甲醛味,每次换工作的折叠门里都是上下班点卯的考勤机。我抬头仰望这座大厦,网上说它是这座城市最高的建筑,里面有个重达千吨的阻尼器,抵挡每年如约而至的台风。
我来此地不是面试,更不是上班。大厦里有上千家公司,但没有一家我有资格入职。我以往上班的地方没那么气派,有的在居民区,有的在半地下室,有的甚至还是共享办公室。我在这个夏天刚过去的立秋坐地铁来到这里,纯粹是想找一个高处结束生命。
我听说最好的自杀方式不是上吊,不是服毒,而是瞬间从高空坠落。人活着不易,每天都要花费超过十二小时努力工作才能赚到柴米油盐;死去亦不易,尸体需要三四个月才能完全腐化。一般的上吊服毒会让死亡成为一场盛大的围观,只有跳楼才能把脸摔碎,不惧他人指点。这场蓄谋已久的自杀我也要尽量维持体面,即使我现在已无尊严可言。
我前面已空无一人,身后也没有人,我终于没有借口再赖在门外不进去。我看到这扇旋转门像开启的扇贝,丝毫没有闭合的迹象。我在等待秋风关上旋转门,可是那股能吹落银杏叶的风却迟迟未至。我深吸一口最浓的秋意,然后浑身上下秋凉如水般进入旋转门。
大堂保安让我登记。我走到迎宾台,把一个将死之人的名字一笔一划地留在登记簿上。我抬头看到墙上贴满了导视牌,可我却在上面找不到属于我的牌位。我要去的地方是楼顶,但我却在登记簿上留下了一个公司名。这家公司位于这座百层大厦的三十楼,我今年也正处于百岁生命中的而立之年。
我如今不会再摁错电梯,我知道箭头向上就是上行,箭头向下就是下行。我此刻要上去,要上到最高处,从我的出生一直来到生命的尽头,或许我会在三十楼,也就是现在的年纪里停下来,走出电梯看看这层楼里有什么。我在电梯上行到三十楼的过程中,浮光掠影地回顾了自己短暂的人生。遗憾的是,我记不住任何一年。
电梯在三十层停下来了。死亡不比上班,迟到一分钟就会被扣工资。死亡可以慢一点,即便我早已决定在今天结束生命。距今天过去还有五六个小时,我还有时间从电梯里走出来,当成上班族游荡在这层空间。外面无人候梯,我不必跟人打招呼,也无需回应别人的招呼。我以为这层空间会有奇观,可是它跟我曾进入过的其他空间没有任何不同。巨大的玻璃切割出了不同的公司,每家公司门外都有一台考勤机。指纹留在上面,就等于种下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树叶。可是他们却在里面做着千篇一律的工作。
电梯边有个公共区域,有人喝咖啡偷闲。我闻到浓烈的咖啡味,一种闻着香喝着苦的滋味。我从每家公司门外走过,玻璃阻挡了我的视线,我看不到里面那些伏案工作的背影。格子间的玻璃模糊不清,但窗玻璃却一目了然,也许窗外的天空没有隐私可言。我走到长廊尽头,站在一扇巨大的落地窗前,看到下面纵横交错的道路就如人体内的毛细血管,每辆车都是一粒细胞,负责维持这座城市的活力。天空的弧边被建筑群掩盖了,好像被剪刀裁剪成了方块。只有站在高处,才能看到天际线和大地就如眼睑,永远没有睡醒。
我站在三十层的高空寻找自己的住所,它位于这座城市的东边,我在现实世界里找不到它的方位,却能在心里转乘四趟地铁后准确找到夹在两栋楼之间的那间公寓。这间公寓没有办法做饭,浴室跟床只隔着一扇透明玻璃。除了晚上迫不得已的睡觉,平时我都会去咖啡馆打发时间。如今我置身宽敞的落地窗前,不再感到身心压抑。公寓的窄窗还有一扇纱窗,看向对面楼层的窗户,就像看到落到捕蝇纸里的苍蝇。此外,还不隔音,走到这座城市的街头,几乎听不到人声,因为无人说话,每个行色匆匆的路人都戴着耳机,但这间公寓却充斥着世上所有噪音。每晚临睡前,隔壁的啜泣和对面的喊声都会同时涌到我耳边。有时还会有电钻装修的声音。我每次都在震动的墙壁上寻找洞穴,可是那个电钻只把喧嚣传过来,钻头却没有丝毫越界。
我在玻璃门即将合上的关头,迅速往里瞥了一眼。
我看到一个打扮入时的前台在玩手机。手机屏幕照亮了她的妆容,她的长睫毛犹如水中藻荇交横。我的脚步声惊扰到了她,她飞快地把手机揣回包里,可是来不及拔的耳机线却像无处可逃的虾须,弯曲地垂到地面。她抬头见是一个陌生人,以为是来面试的,正准备拿出纸笔让对方登记,可我却径直走过去了。我走后,似乎还能听见她受惊的呼吸。
我在等电梯,准备继续往上。等待电梯的时间有些漫长,我坐在一个尚有余温的凳子上,前面有瓶没喝完的矿泉水。瓶身被人揉皱了,水看起来还是满瓶。蓝色的瓶盖没有拧紧,我怕它掉下来水流一地,悄悄覆盖上自己的掌心拧紧。
电梯到了,有人从里面出来。我把这瓶矿泉水及时拿到地上,此时我面前的要是一杯卡布奇诺该有多好,这样我就能被当成这座大厦的一员,而不是一个心怀忐忑的外来者。判断一个人是不是属于某栋楼,最好的办法是看他手里拿的什么饮料,要是咖啡,那就是公司职员,如果是矿泉水,那就是面试者或者其他什么人。原因很简单,因为没有一家公司会给面试者喝咖啡,给的都是这种瓶身不用力就能揉皱的矿泉水。
我这次不知道该在第几层停下来。三十岁往后的岁月我还没有度过,只在书上看过别人的中晚年生活。我怕变老,又期待变老。就像怕过生日,又期待过生日。三十岁是一百岁的百分之三十,在纸上一百个空格中看起来无限接近五十个涂满的格子,但在电梯密密麻麻的按钮上,又无限远离最终的目的地。数字能抵达精确,同样会给事物制造混乱。
我随便摁了一个数字,到达这个数字需要一点时间,我转身去看贴满电梯间的广告。
电梯停在了四十楼。这个年纪的人大都已成家立业,梦想让位给了无穷的琐事,有的家庭和睦,但仍会在下班后待在停车场里抽根烟,借助缭绕的烟雾怀念当初。有的夫妻不和,因为有共同的孩子勉强维系,随着孩子最终长大,才会把自己当成废弃的年画,从家里强行撕出来。我如今尚无子嗣,即便也曾有过机会儿女成双。我怕将来会步大部分人的后尘,因此坚决不给自己制造麻烦。可是没有儿女,也未必能过上想象中的生活,另一半迟早会年老色衰,自己也将精力不济,再浓烈的感情都会趋于平淡,届时假如没有爱情结晶在彼此之间充当润滑剂,往后的日子必将一片荒凉。
这些年,这两种思想一直在我脑海角力,后来我索性不再理会,我在等待自己上年纪,只要到了一定的岁数,生儿育女的希望就会彻底化为乌有。可是,岁月是一种你留意就会延误,不留意又会提前到来的航班。我在等待变老的日子里,始终不忘观察自己的身体,没想到白发不增反减,皱纹也被每天的一日三餐熨平,而且还感到前所未有地清醒。我知道这不是回光返照,这就是我当下年龄的真实写照。
思绪过多让我失去了工作。我给自己放了两个月的假,我用两个月的时间熟悉了这座城市。不过这种熟悉就像考试前的临时抱佛脚,过后便忘,两个月后这座城市还是让我感到陌生。每次走在街头,我都要借助手机才能弄清方向。城市虽大,但我真正熟悉的始终只有那间公寓和那家离秽咖啡馆。我当时走进这家咖啡馆便是被这个名字吸引,但我几乎一进去就后悔了,因为里面的陈设和别的咖啡馆如出一辙。世界上虽然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但却有两座乃至数座完全相同的咖啡馆。我闻着咖啡香味,想象这些咖啡豆的籍贯,究竟源于大洋彼岸的南美洲,还是来自盛产咖啡本初之味的非洲大地。当然,不管这些咖啡豆来自哪里,都要用浸泡或滤泡的方式助人提神。也许咖啡进入体内除垢离秽方能达到提神功效,或许这就是这家咖啡馆叫“离秽”的原因。我在里面喝了两杯冰美式,当晚失眠了,躺在床上仍能听到电钻响。
我此刻走出电梯,来到四十楼,好似提前来到了十年后。这层的每间办公室都尽显奢华,几乎看不见玻璃制品,哪怕门都是用的金丝楠木,里面的鎏金装潢让我以为跌进了太阳旋涡。三十楼办公室的玻璃门喜欢关上让人猜想,四十楼的楠木门却公然大敞,好像关住了里面的穿金戴银,就会让这些豪奢明珠蒙尘。我几乎一眼就能看到里面镶金的画框,上面的蒙娜丽莎比巴黎卢浮宫里的整整胖了五倍。两排酒柜像蜂巢一样摆放,瓶身独特的红酒像走秀台上惊鸿一瞥的玉腿。所有的一切,都符合这个年纪的审美,哪怕只有一克金,也能像摊煎饼一样摊得到处都是,不愁别人看不到。
待业两个月后,生计迫使我去找新工作。离秽咖啡馆的店员看我的神色也有了异样,因为我用别人喝完没来得及收的杯子冲速溶咖啡。我在网上找到一家游乐场的工作,游乐场分为现实与虚拟两部分。现实部分有跷跷板、旋转木马和摩天轮;虚拟部分是一个不起眼的奇妙屋,戴上VR眼镜,可以体验不敢在现实世界体验的跷跷板、旋转木马和摩天轮。我在奇妙屋里工作,工作内容很简单,每天闭园后负责检查那些VR眼镜有没有缺失,很适合我这种胆小之人。没人的时候我也不敢戴上VR眼镜,我怕里面的跷跷板像只象鼻把我甩到天上去,我怕摩天轮像失序的齿轮让我坠下来,我怕旋转木马停不下来。奇妙屋里的体验虽然虚假,但感受却无比真实。胆小如鼠的我不仅惧怕真老虎,也惧怕纸老虎。每次听到游客在奇妙屋里大喊大叫,我都会溜出去偷偷抽一根烟。我不敢当他们的面抽烟,他们都是一些带小孩的大人,他们可以当着孩子的面吞云吐雾,我不行。奇妙屋里除了VR眼镜,还有一些能触手可及的小玩意,有飞天的桌子,遁地的牙刷,隐身的电灯,瞬移的纸巾。因此奇妙便成了捣乱,因为桌子只有在地上才会放稳一颗伏桌偷懒的脑袋,牙刷只有握在手里才能清洁牙齿,电灯隐身跟漆黑一片没有区别,纸巾瞬移也就无法让蹲麻的屁股及时站起来。我不喜欢这间奇妙屋,它的作用只是强行给现实制造一点乐趣,就像在黄连上抹上一点蜂蜜,不仅无法让黄连甜蜜,甚至还会更苦。
我没有在四十楼多加停留,我身上的半旧衣服配不上它的崭新。没有人使用电梯,电梯仍停留在这层。我进入电梯,看到相同的广告。看来我的人生不管有多少岔路,最终都会回到原点。我不知道下一步该在哪层停留,我想象不到四十岁以后的人生,也不知道哪个时间节点对我有重大意义,我年轻的身体还没到盖棺定论的时候。
电梯继续上行,我没有再摁按钮,我的迟疑不决最终会让我突然来到一百层,就如我从四十岁那年睡了整整一个甲子,一觉醒来已至百年。随着楼层数在持续变幻,留给我的时间不多了,可我仍然没有下定决心参观自己的哪一年。我做不了任何决定,我更喜欢别人帮我做决定,让自己的命运掌握在别人手里。我的人生就像凫水涉岸,虽然岸就在面前,但我却不愿费力游过去,我更愿意让大雨为我推波助澜,哪怕触礁或者溺水也在所不惜。
电梯最后在五十楼停下来了。这些年来,我见多了这个岁数的人。他们暮气沉沉,身上散发出难闻的老年味,但又尚有精力用香水掩盖这股味道。留了一头年轻人才会留的发型,两边剃光,中间留长,不为时髦,只为白发总是从两鬓冒出,因此剃掉两鬓,就等于仍是一头乌发的小伙子。不过其他部位却难掩他们的苍老,比如登不了山、走不了路的老寒腿,又比如驼背,好像驮着一块无形的巨石,只为慢点来到终点,还比如摇动的牙齿,俨然回到了吃流食的婴儿时期。我在远离市区的奇妙屋里见到许多带孙子游园的五旬老人,不过在如今这个晚婚晚育的年代,他们很有可能是带着看上去跟自己差辈的儿子出来游园。每次遇到年龄悬殊的一老一少,我都不敢溜出去抽烟,我怕老少之中任何一个发生意外,或者双双发生不幸。我会格外留意他们,并尽量不让他们进来,我怕他们误把虚拟当成现实,体验完后发现世间的险峰不过如此,从而胆大包天亲身去涉险。只有游乐场里的现实部分才能让他们知难而退。游乐场属于一个正当年的大人和一个无忧无虑的孩童,唯独不属于一个迟暮的老人,哪怕另一个孩童也在无忧无虑的年纪。
我最终决定去参观五十楼,虽然我害怕面对自己的五十岁。五十岁是人生的中点,无疑是一个最尴尬的年龄,往后看是过去一半的最好年华,往前看是不可控的剩下一半。前五十年纠结于各种人事,以至于从没有为自己活一天,后五十年等待自己的是层出不穷的疾病,不知道命运的轨道将会在哪里戛然而止。我不安地开始了参观五十楼,在电梯门打开的一刹那,我就想回到电梯里,可我没有回去,也没有用手捂住眼睛,我甚至还瞪大了眼睛。我看清了五十楼的设施,里面没有咖啡和红酒,而是无数的茶叶,每个等待退休的人都握着一个保温杯,里面泡烂的茶叶就像护城河里蔓延的绿藻。所有人的穿着都一个样,上身穿蓝色夹克,里面的白衬衣还能看到洗皱的领口;下身是黑裤子,皮鞋擦得锃亮。手机字号很大,但仍要把戴着老花镜的脑袋无限趋前。
酽茶虽香,却分外苦涩,是一种跟咖啡不一样的苦。咖啡苦是年轻人必须要吃的苦,将来才有可能享受到功成名就的甜。而茶苦却是那种浓到极致归于平淡的苦,是那种看透人生的自我抚慰。他们大都谢顶,头皮却跟脸上皱纹丛生的皮肤不同,透亮发光。三三两两地凑在一起交头接耳,看上去就像串了一串佛珠。我路过长廊,把每家门窗敞开的公司内部景观都尽收眼底。书法作品挂满了白墙,就像保洁员误把扫帚上的脏水泼到了上面,有些还在滴墨。深红色的办公桌揭示着夕阳西下的晚景,我闻到桌上没盖的茶杯尚有余味。他们大都握着保温杯坐在门口聊天,有些还在抽烟。这些我没见过牌子的烟在他们的嘴中越吸越短,地上的灰烬被进进出出的双脚踩踏。
卫生间在长廊尽头,我进去小便,隔壁有个如厕难的男人。我进去时他扶墙小便,我出来后他仍在扶墙小便。我在他身边只听到几声尿不尽。我洗手拧开水龙头,看到镜子里的自己有一头半月不剪又长长的乌发,眼睛被头发挡住了,撩起来的时候能看到两颗疑惑的瞳孔。那个男人还在小便,我刚把水龙头打开,他就以为自己成功了,低头一看,发现小便池里彩色的樟脑球仍在渴盼甘霖。我关了水龙头,独自出去,并在门外停了一会儿,我没听到声音,不怕他出来跟我撞个满怀。我沿着长廊往回走,想起我五十岁的人生也有可能小便难,决定那时每天尽量少喝水。
我在等电梯。电梯还在下行中,最终落地需要五十年的时间,最终上来又要五十年的时间,前后加起来就是漫长的一个世纪。那个男人出来了,他经过长廊时没有跟任何一个喝茶抽烟的人打招呼。那些喝茶抽烟的人看到他神色有异,也没有跟他打招呼。他来到了我面前,我又出现在了他身边。
“上还是下?”他问。
“上。”我说。
“我是下。”他说。
“干嘛去?”我问。
“上厕所。”他说。
隔壁的电梯坏了。我把这个从五十楼下到一楼,又从一楼上到五十楼的电梯让给他。他摁亮了三十楼的电梯,也许在三十岁的时候,他碰到的问题中还没有上厕所难。
我又在等电梯。我今天大部分的时间都在等电梯,在等一个带我走向未知的电梯。我决定去死的这天仍然摆脱不了无尽的等待。我等过一分钟后成功变绿却因为堵车仍无法通行的红绿灯;我等过前一天再三交代第二天对方仍然迟到两个小时的约会;我等过延迟半年之久才发放的薪水。这辈子我都在等待,连死亡也是如此。
电梯终于到了。五十楼往上是一个手可摘星辰的高空,我感觉自己出现了耳鸣,好像天空把日月星辰同时往我耳中猛灌。我的大脑嗡嗡作响,犹如有数不清的蜜蜂在我脑中筑巢。我忍受着蜜蜂振翅般的耳鸣,坐着电梯继续往上,感受到双脚似乎悬空在玻璃栈道,而脚下是深不见底的深渊。整个电梯也在摇晃,就像一颗抛到高空的铅球准备改变运行轨道,从另一个方向掉落下来。我被迫扶住电梯轿厢,不让可能出现的电梯故障危及我的生命。我虽然决定今天去死,但也要死于自己的精心谋划,假如中途出现意外,说明我的人生彻底失败了,竟连自己的死亡都无法做主。
电梯在五十层往上的高空爬行难,我像坐在穿行在城市四面八方每站必停的地铁。电梯往高处走,地铁往低处钻。高空有飞鸟舒云,飞鸟翅膀上带来了远方的草籽,舒云里蕴含着给大地消暑的雨水。然而,高空没有大地可供草籽生根发芽,大厦楼顶寸草不生,没有植物能高居百层而枝繁叶茂;大地也不需要靠雨水降温,因为季节的更替早已让这座城市做好了越冬准备。但是在地铁往低处钻的隧道,却有呼啸而来的风为上班族摇旗呐喊,即便漆黑一片的隧道也能在强劲的风中感受到灵魂的战栗。地铁就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电钻,带领人们钻入地心深处,那里有高温地核,形状跟距地球1.5亿千米的太阳宛如双生。
我胡乱摁了一个数字,然后及时停下的电梯回馈给了我一个花甲之年的风和日丽。我来到了六十层,这个我年轻时以为活不到的年龄。我信步走出电梯,耳鸣没有了,在我脑中振翅的蜜蜂误入到真正的百花丛中去了,日月星辰也好端端地列张其上,仍在发出可照旷野的萤萤之光。不过我的脚踩在六十层的红毯上依然感到不踏实,我还没有来到窗前俯瞰风景,但我心里却比任何时候都清楚,我的双脚离地面足有170米。假如没有塔顶依托,世界上没有能超过这个高度的摩天轮。天空之眼并非天的眼睛,而是人类观察天空的放大镜,是寻求高与低瞬间转换的刺激物。
我走在六十层的长廊上,不像走在四十楼和五十楼的时候那样如履平地。我像一个真正的六旬老人,走出了步履蹒跚的老态。我在这里没有闻到任何饮料的味道,只看到寡淡的凉白开滋润着每一个有气无力的喉结。这些都是一些被返聘发挥余热的退休老人。
人生终将会趋于完全的平淡,只有白开水的温度还能证明曾有过的绚烂。不过白开水的归途只有用两个瓶子互相倒灌放凉,现在服用药物也无法用滚烫的白开水,仍要等白开水完全晾凉后才能不伤到喉咙和脾胃。用一百度的高温烧沸的水无法让嘴巴有滋味,也无法让身体享受到酸甜苦辣。年逾六旬的枯唇假如本身没有味道,或者散发着年迈特有的苦涩,白开水入喉只能像田田的荷叶上滚落的露珠,不会留下一点痕迹。我不爱喝凉白开,哪怕在水里放糖或者撒盐,也好过喝白水。纯净的白水并不适合想入非非的青春期,也不适合生龙活虎的壮年,唯一适合我现在看到的这些垂暮老者。
长廊尽头没有落地窗,也没有厕所,只有一扇无法推开的仿古窄窗,上面錾刻着花鸟虫鱼。
我不明白这扇窗户安在六十层高空的意义。
我站在窗前,身后是那帮迟暮老人。他们精力有限,尽量不说话,有的在原木桌上写写画画,面前没有电脑,他们只相信自己的大脑。有的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世界风云变幻浓缩在这张小小的报纸上,让他们还能对地球上的疥癣之患做到心中有数,不过在我决定赴死的这天,这个疥癣之患似乎有癌变的危险。世界濒临破碎,人类却用战争为地球寻医问药。
我透过这扇仿古窗,看到远处的群山笼罩在薄雾中,每一棵树都在极力向阳,可是雾气却像一条蘸湿的毛巾,敷冷了太阳。我没有听见鸟啼声,这个高度可以隔绝一切声音,连地面上此起彼伏的喇叭声也被消音了,我只能看到那些车辆堵在立交桥上和红绿灯前。拥堵的车辆像一只首尾不能相顾的蜈蚣,是这座城市除了那些密集的建筑物之外最显著的标志。高矮不同的楼房都有许多窗户,或许它们狭窄的面积需要靠窗户拓宽。天空没有边际,任何建筑物都可以跟它租用空间,而不必担心天空耗尽。有些寿终正寝的建筑物像一棵大树那样倒下来,我看到一股伞状的灰尘从地面轰然升空,到我面前时已被无垠的天空稀释。我用目光追随每一朵疑似尘埃的云朵,可我终究无法辨认出来。
我眺望地面,看到拥挤的建筑群中出现了一个缺口。这个城市从来没有缺口,它会在每一寸空间里塞满房屋,即便是公园,也只是像奶油蛋糕上迫不得已的樱桃点缀。连接城与城的更多是飞机,而非汽车,天上的飞机云跟城市里的道路一样多。飞机云很快由浓转淡,又由淡变浓,空旷的天空不愁没有飞机,也不愁没有航道,即便每一个航道都会像黑板上被迅速擦去的粉笔字。
我的身后传来老人的呢喃,我转身看到他们不是因为疾病在呻吟,也不是因为儿女不孝在唾骂,而是在轻声朗读报纸。他们还没看完今天的报纸,明天的报纸又将新鲜出炉。他们已然跟不上新闻出现的脚步了。他们的身体在退化,而世界又在日新月异,报纸无法解决他们与时代的错位感,只好沉浸在往事中。他们并非从小一起长大,有的是本地人,有的是年轻时靠打拼留下来的外乡人,本来没有多少共同话题,不过曾一起经历过的火红时代,让他们产生了说不完的话题。
怀旧是时间节点上的七寸,任何人都可能被打中七寸,从而产生厚古薄今的偏见。我看到沉浸在往事中的他们脸上荡漾出了幸福的笑容,是一种谈到过去心领神会的默契。假如真要以过去衡量幸福与否的标准的话,我想只有原始人才是古往今来最幸福的一批人,毕竟在此之前,人类还只是树上的猴子。
按理说,我应该认同他们的观点,否则就无法解释我为什么在今天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不知该从何说起,我从不否认前人的幸福指数比我们高。如今我之所以产生轻生之念,并非不幸福,如果幸福只是吃饱穿暖的话。而是我的心出现了问题,它就像一个沙漏,我已无法留住日常的荣耀与屈辱。是的,当一个人对任何事都不会感到光荣或者屈辱的话,那他就离死不远了。这种感觉由来已久,在我被不停辞退时,我的心就像在梅雨季节悄悄破裂的墙壁,等到我被游乐场扫地出门时,这股裂缝已经变成皲裂的田地,而女友的不辞而别,则最终让我破裂的心彻底化为了齑粉。我被游乐场辞退是因为在那间奇妙屋里有我没有都一样,女友离开的原因虽然她没有明言,不过我却能通过那间转身难的公寓看出端倪。
这些事情都发生在昨天,而今天是我三十岁的生日。昨天我对今天怀揣着无限憧憬,本来打算今天带女友到这家大厦的顶楼餐厅庆祝自己的三十岁生日,没想到游乐场的负责人临近下班的时候跟我说,我被辞退了。我回到公寓后,等到了午夜三十岁生日到来,可是却第一次没有等到准时下班的女友。第二天,也就是今天,我独自来到了这座大厦,不是为了庆祝生日,而是为了结束生命。网上说,这座大厦的顶楼餐厅很适合庆生,想必也适合吃最后一顿晚餐。
我的余生已在四十楼、五十楼和六十楼经历过了,我了无遗憾地离开六十楼,离开这些边看过期报纸边共话过去的老人。电梯载我来到第一百层的顶楼餐厅,我还没能感受到耳鸣和头晕就在打开的电梯门里看到了这家餐厅。
每张饭桌上都包了一张纯白的桌布,桌上的烛光有的刚刚点燃,有的已经燃尽了。此刻正是吃烛光晚餐的时候,看来今天有很多人跟我同一天生日。这些与我同日生日的人有小孩,有学生,有年轻人,还有老人。他们来自不同的地方,操着不同的口音,却因为同一天生日共同来到了这里。
“先生,有预定吗?”
“没有。”
“先生几位?”
“两位。”
女侍者把我领到一个靠窗的位置,告诉我说这是刚刚退订的一桌,问我现在点餐还是等另一半到了再点餐。我说我的另一半到了,现在点餐。女侍者看了看电梯口,又看了看我身边,问我是不是还在路上。我指了指对面的凳子,说已经坐下来了。
“先生,你真爱开玩笑。”
“我没在开玩笑,我跟自己一起吃饭,就不算两个人吗?”
“对不起,先生。”
“没关系,这个窗户可以打开吗?”
“先生,不可以。”
“那如何欣赏夜景?”
“先生,我们这里有专门的观光摩天轮,可以坐在里面饱览城市夜景。”
我匆匆吃完晚餐,来不及擦嘴,随女侍者来到餐馆旁的摩天轮。
摩天轮有一圈透明的座舱,可以三百六十度全方位地看到霓虹闪烁的夜景。刚下来的那批客人没有一个呕吐,看来这个摩天轮不会让人不适。可我依然不敢坐上去,女侍者看到我的身体在发抖,告诉我摩天轮很安全,这么多年连一颗钉子都没有松动过,每天都会有专人定期检查。
我看着摩天轮最顶上的座舱和最下面的座舱,看似一条距离最短的直线,但它们却永远不会相交,而且摩天轮转动后,它们还会随时变化位置,却仍无法相衔。我只坐过一次摩天轮,还是跟女友,那时我们刚在一起。有一天她说,我们去坐摩天轮吧。
我说,我怕。
她说,坐过摩天轮我们的爱情才能圆满。
我这次是第二次坐摩天轮。我决定把自己当成脱靶的子弹,坠落到无尽的黑处,填补生命中的缺口,给自己的人生画下一个圆满的句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