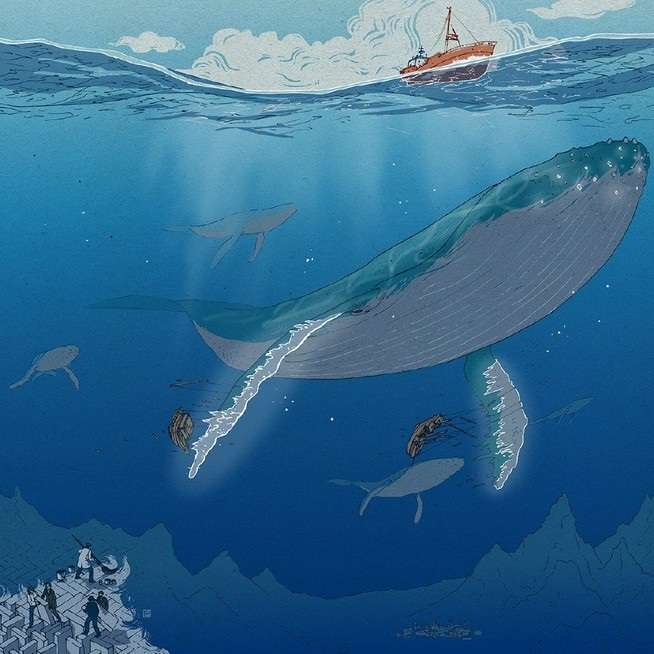所谓边缘人物,就是游走在市中心而不被在乎的人。
1
苏北的小镇白石街不知何时兴建,主干道是青色的石板路,年代久远,石板如羊脂般光滑,被压出了细密的裂痕。两侧白墙黛瓦,凌河而建,墙上石灰斑驳。街南侧是运河,女人们在岸边洗衣服拉家常,男人们把大米扛上货船,又从货船上扛下一袋袋劣质的服装,河面上麻鸭扑棱着翅膀嬉戏。街中间支流穿过,架起一座石拱桥,桥洞成了孩子捉迷藏的好去处。
孙海峰穿着凉鞋吧嗒吧嗒走在石板路上,往日清脆的足音竟让他心神烦乱,几个老女人在他身后窃窃私语,等他回过头,她们又转过脸,大声谈论最近的菜价。
一年前的春天,孙海峰的妻子万芳芳在白石街消失了,说消失不准确,是跟老孟跑了。“假如生活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心急!忧郁的日子里须要镇静。”孙海峰自从在儿子语文课本里读到普希金的这几句诗,就时常宽慰自己,可他镇静不了,他不知道生活为什么要欺骗一个老实巴交的男人。孙海峰原来的生活不坏,记忆里除了白墙黛瓦小桥流水,还有一座香气四溢的油坊。他的“孙记油坊”传自他父亲,在镇上开了几十年,香气也飘了几十年。油坊辉煌的那些年,庄稼人推着一车车金光闪闪的黄豆来到他的油坊,他们带回一壶壶豆油,一块块豆饼。老孟是榨油的老主顾,他家里人口多,七八口人挤在村上的三间小瓦房,没人愿意给孟家说媒,老孟打了半辈子光棍。
老孟后来进了城,一年后回来召集了十几个民工,说到城里盖大楼挣大钱,再回来已经是包工头,整天开着奥迪车在白石街闲逛,跟着他的民工都低头哈腰给他递烟,称呼他“孟总”。
万芳芳走得毫无征兆,前一天还跑到外乡看淮剧,第二天就悄无声息走了,给孙海峰回了一条短信,就换了号码。短信说:我对不起你和儿子,我想追求我的幸福。话说的很直接,很诚恳,没像镇上有个女人骗他男人说去城里当保姆,结果当到了别人床上。过两天儿子问妈呢,孙海峰说去船上给人烧饭了,一年半载回不来。儿子还小,能瞒一天是一天,告诉他徒增烦恼。
街上几个女人第一时间跑来替孙海峰打抱不平,一个女人说去年就有人在县城看到万芳芳和老孟手拉手逛街,另一个女人说昨天傍晚看到老孟在街上散步,没开他的奥迪车,贼眉鼠眼,像特务一样。几个女人见孙海峰没回应,把旁边的瘦高男人推到前面,说,你来总结。瘦高男人是20世纪90年代高考落榜生,考了四次没考上,脑袋就不太正常了,喜欢拿粉笔在石板路上写字,又爱凑热闹,别人说完他就总结一下。瘦高男人挠挠头说,兄弟如手足,女人如衣服。女人们哄笑,指着瘦高男人说,你说女人如衣服,你一件衣服都没有呢。
孙海峰不想在白石街呆下去了,一方面是天天听到议论万芳芳的流言蜚语,另一方面得为生计考虑。镇上开起了大大小小的超市,卖包装精美的色拉油,连白发瘪嘴的老人们都知道“鲁花”“金龙鱼”,没人再来榨油了。要说他一个人,靠开油坊攒的老本事能糊口,可妻子跑了儿子还在。小家伙不算聪明,一次三好学生没拿到,跟孙海峰说了几次想补习数学和英语。镇上有补习班,师资有限,价格不菲。孙海峰咬咬牙,补,儿子语文作文不好,干脆一起补。这镇上没有赚钱的好门路,他试过到货船上扛沙袋,工资说得过去,腰吃不消。到医院查过是腰间盘突出,还有骨刺,得开刀,住院休养。他走出医院,把病历和缴费单统统撕掉扔进垃圾桶。
阳光给石板路和白墙铺上了一层金沙,街上传来饭菜的香味,三三两两的人们结伴往东边走去,那是他熟悉的学校方向。“相信吧,快乐的日子将会来临!心儿永远向往着未来。”他又想起了普希金的诗,想起去年夏天,老孟的老光棍弟弟结了婚,在街上碰到他给他散喜烟。那时万芳芳还没跟老孟私奔,她倚在门口,笑眯眯地看着意气风发的老孟弟弟,专注地听他和丈夫讲话。老孟弟弟说,别人都以为我结婚是靠我哥哥,他一分钱都没给过我,他是个只顾享受的人。爸妈对哥哥说现在有钱赶紧把婚结了,哥哥说急什么,有钱还怕没女人?万芳芳插话说,那你哪来的钱结婚?老孟弟弟左右看看,像公布一个秘密,小声说,我在南京送外卖。孙海峰说,跑腿的?老孟弟弟笑着说,别小看跑腿的,月薪过万,比镇长挣得还多。万芳芳把头发拢到耳后,叹气说,难怪镇上的人都往城里跑。
2
孙海峰到南京干上送外卖的活,发现并不像老孟弟弟说得那么容易,活是多,骑手也多,加上平台抽成,除去每月伙食费加水电房租,也就剩个四五千。儿子补三门功课,就是个讨债鬼,隔上个把月就打电话过来,爸,老师催交学费了。
得开源节流。加班不必说,没人逼你,多劳多得。节流首先得降低房租,他看中一个朝北的单间,里面一张木质上下床,原先是房东两个儿子的卧室。中介说房租九百一个月,孙海峰有自己的小算盘,如果能找到人合租就能平摊一半房租。还真在这一片骑手群里找着一个,叫李立,二十出头的四川小伙子,个子不高,留着平头,皮肤黝黑。孙海峰问他为什么愿意合租,李立说缺钱,很缺钱,孙海峰问他每天单子的量才知道比自己还玩命。李立说在老家谈了女朋友,要十五万彩礼。孙海峰咂咂嘴,他老家乡下也是这样,老孟弟弟花了七八万彩礼。孙海峰说,来到南京后,反倒没听说过城里人在彩礼上狮子大开口的。李立说,哥,不是这么个账,南京人结婚就是一分钱彩礼不要,你得有一套婚房吧,多少钱你算算。孙海峰点点头,不要芝麻要西瓜,是这么个道理。李立说女朋友还有一个追求者,算是当地的富二代,丈母娘整天对女儿煽风点火,要她务实点。女朋友很坚贞,说非李立不嫁。丈母娘急了,发了最后通牒,告诉李立两年之内拿不出十五万彩礼,女儿就嫁给富二代。
孙海峰外卖送多了,也遇到不少奇葩事,下了单,提些奇奇怪怪的要求。比如有一次,一个男人点了盒德芙巧克力,打赏了五块钱,备注说他和妻子吵架,请骑手开门对他妻子说:老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孙海峰不想接单,可他是“专送”,没法拒绝,要是不能满足顾客要求打了差评或者投诉那是得不偿失,一个差评五十,一个投诉五百,顾客就是上帝,什么委屈自己兜着吧。孙海峰把巧克力送到男人妻子手上,低着头,别别扭扭地说,老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也许是他的苏北口音太重,穿着白色睡衣的年轻女人束了束腰带,问他说什么,他抬起头,年轻女人的眉眼竟然和万芳芳有几分神似。他握紧拳头,重复一遍,老婆,我错了,请你原谅我。
下铺的李立经常和女朋友视频聊天,他瞥过那女孩,在美颜效果下和网上的女主播们很像,一口火辣辣的四川话,和李立老公老婆叫着。李立视频聊天时,孙海峰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心不在焉地划拉手机,眼前出现了扑闪的画面,就像投影一样,有万芳芳,李立女朋友,也有点外卖的漂亮女人们。眼睛胀,身体也胀,他只好侧过身子,拉过脚底的床单盖到腰上。
李立说嫂子怎么从来不来,孙海峰顿了顿,说,死了。李立就不问了。两人熟识后,李立也就口无遮拦,有一次问孙海峰生理问题怎么解决,孙海峰摇摇头,害羞地笑,干柴也得碰上烈火啊。李立说,地铁站边上有一家如意发廊,里面都是二十来岁小姑娘,脸蛋漂亮,胸还大。孙海峰心痒痒的,送外卖时特地绕到李立说的如意发廊转了一圈,一个黄头发的姑娘推开磨砂玻璃门,松了松衣领,直勾勾地盯着他,说,进来玩会呗。孙海峰被姑娘稀里糊涂地拉进门,带进昏暗的房间,他想起万芳芳倚在门口微笑,老孟仔细擦洗他的奥迪车。一阵急促的手机铃声响了起来,是他的“讨债鬼”,他一阵哆嗦,挂了手机,飞似地冲出了发廊。
有一天夜里下班,孙海峰刚准备灭灯睡觉,李立回来了,身后跟着一个妖娆的女人,穿着低领紧身裙,露出小半个乳房。孙海峰一眼看出不是李立的女朋友,李立笑笑,说,孙哥,这是露露,要来我这看看。孙海峰赶紧穿衣下床,说,那你们聊。孙海峰出了房门,下了楼,破旧的出租房墙体上画上了大大的“拆”字,墙边靠着几辆共享单车,都上了私锁。街面冷冷清清,湿漉漉的,像洒水车刚浇过水,白天禁行的卡车活跃起来,轰轰隆隆,鱼贯而行,偶尔驶过一辆改装过的轿车或者摩托,炸鞭似地呼啸而过。秋夜的月色朦胧,暗光淹没在烟雾里,灰蒙蒙的烟雾夹杂着丝丝缕缕的烧烤味,在岑寂的城市里游荡。孙海峰不想去评价李立的道德,他想知道这女人是自愿的还是有偿的,如果是自愿的,她看上李立什么,如果是有偿的,李立舍得动他的彩礼钱吗?孙海峰想起白石街上的瘦高男人,他现在和他一样,也是一件衣服都没有。“我操人家那心干吗?”孙海峰对自己说。
孙海峰抽完两支烟,露露下楼了,对他说,大哥,我们什么也没干,我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她点上一支烟,扭动腰肢,走上街面,拦了辆出租车,撅着屁股钻了进去。
上了楼进了屋,李立穿着大裤衩躺在床上,抽着烟,脖子和胸口残留着汗渍,眼神有些躲闪。李立坐起来让了一支烟,孙海峰没接,说在下面刚抽过。李立笑着说,什么也没干成。孙海峰不搭话,冲澡的时候拿毛巾往墙上噼里啪啦地抽。
3
露露又来过两次,孙海峰想好了,这两天重新找个住处,跟李立分开,李立需要隐私,他也需要。
孙海峰这隐私没跟李立说。半个月前的黄昏,冬至刚过,天上冷飕飕地飘着细雨,孙海峰正在等红灯,马路对面一个骑手车胎爆了,骑手下了车,摘下头盔,是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茫然地站在车前。孙海峰骑过去,检查了车胎,内胎坏了,骑不了了。女人穿着雨披,雨水顺着帽子和露在外面的头发流下来,她皱着眉头,抿着嘴,好像要哭出来。他明白女人的无助,时间就是金钱,这句话用在骑手身上很合适,不按时送达就会打差评,投诉。女人打了几个电话,好像都没得到帮助,蹲下身抽泣,不停抹脸上的雨水和泪水。他问了女人的单子,和自己的目的地南辕北辙,要帮她送他就完成不了任务。女人看着他为难的样子,说你走吧。他按灭手机,说,我跟你顺路,我来帮你送。女人的单子结了,他没完成任务,被打了两个差评,今天一天算白跑。
钱被扣了只能再节流,他和李立有个约定,每个月犒劳一顿,到烧烤摊大排档消费太吃力,无非是买点菜在家烧火锅。他们俩第一次到超市买火锅食材,在冰柜里挑了又挑,李立拿起一包羊肉卷,说,这行吗?孙海峰说,你看着办吧。李立把羊肉卷放进购物车,孙海峰也拿起一包牛肉卷,说,买这?李立说,你说了算。两人在超市里磨磨蹭蹭,都不愿意往收银台走,最后李立说,哥,你儿子补课得花不少钱吧?孙海峰会意一笑,可不,你那彩礼还没准备好吧?李立把羊肉卷和牛肉卷放到货架上,说,这玩意不划算,我们一人不吃个五六包也吃不饱。孙海峰说,就是,还不如买贡丸。他们买了贡丸,买了白菜冬瓜土豆海带,回来自己调底料——辣椒酱加盐和味精。孙海峰说,蘸料怎么办?李立说,腐乳加酱油,切几瓣蒜,加一把花生碎,我读技校时都这么调。白酒可以放开喝,他们不约而同看中了超市塑料桶装的劣质白酒,三升才二三十块。孙海峰这一扣钱火锅也舍不得吃了,挨不过面子,对李立说这两天拉肚子,下个月再吃。啃起硬邦邦的荞麦面包。
过了一个星期,车胎爆掉的女人打电话来,问孙海峰住在哪,想给他送点吃的。孙海峰不是一个人住,不好领人上楼,就站在楼下“拆”字旁边和她见了面。女人给他送了一袋茶叶蛋,说现煮的,让他吃几个。他囫囵吞枣一连吃了三个,噎得直翻白眼。闲聊几句,得知女人叫赵春花,安徽当涂人,丈夫出车祸死了,她带着女儿来南京送外卖。孙海峰说,你把女儿带来,她上学怎么办?还是在这边上的学?赵春花说,不在我身边不放心。
接下来几天,李立和女朋友打情骂俏时,孙海峰也背过身子跟赵春花不咸不淡聊上几句,赵春花说得多,孙海峰说得少,都是张家长李家短。至于赵春花丈夫生前怎么样,孙海峰妻子什么情况,他们避而不谈。这种话题即使有机会谈,也不是现在谈,他们不是小年轻谈恋爱,有一说一,到这岁数应该厚重如山,沉默是金。
孙海峰找着个新住处,赵春花介绍的,跟她同一个小区,朝北小单间。孙海峰觉得还是一个人住惬意,虽说多承担了一半钱,但不用合伙吃喝,可以省下这笔不必要的开支。听说孙海峰要走,李立说,因为露露?孙海峰说,不是。李立又说,因为我跟女朋友聊天妨碍你?孙海峰说,想哪去了,过一阵子儿子放寒假要来,没地方住。李立说,那行,后会有期吧。孙海峰嘴角蠕动了一下,本来想问他彩礼钱还差多少,想想还是别问了。
孙海峰跟赵春花住到一个小区,一来二去见面机会就多了,但只限于在楼下,他从没见过她带女儿下楼,她说女儿在屋里玩呢,不爱出门。孙海峰第一次登赵春花的门是帮她修门,她和女儿住的也是朝北的单间,房间里收拾得干干净净,衣橱上贴着卡通图案,油漆斑驳的桌上铺着报纸,有一盏台灯,床上铺着褪色的白床单,有几处破了洞,绣着红牡丹的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放在床的里面,枕头铺着老式的枕套,绣着鸳鸯。床下是笨重的红色行李箱,盆盆罐罐,以及拖鞋。赵春花的女儿坐在桌前画小鱼,十来岁的样子,胖乎乎的,额头上长着星星点点的痤疮。赵春花说这是她女儿婷婷,对婷婷说叫叔叔。婷婷站了起来,歪着脑袋,翻着白眼,咧着嘴,瓮声瓮气叫了声“叔叔”。孙海峰心里一颤,婷婷是……难怪赵春花不放心她。赵春花把手插进婷婷的长发梳理起来,叹息说,胎里带出来的,在特殊学校念了两年,受人欺负,想想还是带在身边吧。
孙海峰回去心情很失落,有个女人是有了衣服,多出个女儿又像系上了一条围巾,加上他儿子,两条围巾勒得紧紧的,哪里喘得了气?
4
孙海峰再碰到李立是到奶茶店接单,按道理说他们不在一个片区,不容易碰面,李立说他干“众包”了。孙海峰说,还住原来那?李立说,嗯。孙海峰说,挺好?李立说,挺好,你也挺好?孙海峰说,挺好。忍不住问了一句,你和露露怎样了?李立啐了一口说,早分了,她就是个公共汽车。孙海峰笑笑,取到了奶茶,说,那再见?李立点点头,向他挥挥手。
孙海峰骑上车,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想起露露,勾人的眼神,高耸的乳房,细细的小腰,笔直的白腿。他嘴里生出咸味,身体又不安分了。李立说她是公共汽车,公共汽车只要花钱,谁都能上,孙海峰冒出这个想法时吓了一跳。
天气预报说夜里下雪,孙海峰提前喝了碗姜汤,十一点多果然飘起了鹅毛大雪。骑手群里怨声载道,都嚷着回去睡觉。骑手最讨厌雪天,冷是其次,看不清路,地又湿滑。
孙海峰不愿回去,儿子说补课成绩有了提高,想寒假接着补。孙海峰接到一单,水煮肉片,两公里远。虽说只有两公里,雪天骑车欲速则不达,摔了跤洒了菜反蚀一把米。孙海峰调整好头盔,缓慢前行,路上白茫茫的,车灯在空气里劈出一段光柱,雪花如沙粒在光柱里跳动。目的地到了,是一处静谧的高档小区,有高层,有别墅,橘黄色的路灯挂着水珠,光秃秃的梧桐树落上了积雪。顾客住在十二楼,孙海峰来到电梯前,从包里取出外卖时,傻了眼,盛水煮肉片的塑料袋破了。他只好把滚烫的包装盒捧在手里,水煮肉片的红油溢了出来,流到了他的手背和手指上,粘稠的汁液灼烧着冰冷的皮肤。他来到十二楼,按响门铃,一个散着长发的年轻女人开了门,伸手要来接外卖。孙海峰没看她的脸,注意力全在水煮肉片上,他说,烫,袋子破了,我给你放到桌上。女人打量着孙海峰,说,你是和李立合租那大哥?孙海峰抬起头,是露露。先把外卖放到桌上吧,他说。红肿的手背和手指隐隐发痒。露露拉开门,孙海峰进了门,暖气扑面而来。房子是精装修,欧式风格,真皮沙发,立式空调,大电视,都是高档货。房里有点凌乱,沙发上扔着一件白胸罩,茶几上落了瓜子壳,烟灰缸里积满了烟头。
露露说,还接单不?孙海峰说,不接了,雪太大了。露露取了几张湿巾纸擦了擦他手上烫伤的患处,又找出一管红色包装的药膏,挤出一条,涂在上面,不一会患处就消肿止痒了。露露拿纸杯给他倒了杯水,趁他喝水收起了沙发上的胸罩,倒掉了瓜子壳和烟头。
露露收拾好房间,说,辛苦你了,手还疼不?孙海峰心里一热,眼泪差点滚下来,妻子跑了后还是第一次有女人关心他,和赵春花聊天都是聊别人,把自己置身之外。孙海峰不知道怎么回答,指着水煮肉片,慌乱地说,菜凉了,快点吃吧。露露说,天冷了,一起吃点吧,冰箱里有鸡蛋,我来煎荷包蛋,还有一包花生米,再热一壶黄酒。孙海峰不想承情,可到嗓子眼的话说不出来口,脚也像生了根,任凭露露煎荷包蛋,热黄酒。露露看着邋遢,热黄酒倒是讲究,切上姜丝,放上话梅,文火煮烫,一丝不苟,一打听是浙江绍兴人。露露说,我不会做饭,只会煎荷包蛋。孙海峰在喝完水的纸杯里颤颤巍巍倒了一小杯黄酒,呷了一口,心里的雪化开了。露露和李立一样爱说话,她说她爸爸死得早,妈妈嫁给了渔夫,继父是个色鬼,抓过她屁股,她高中没读完就逃了出来。孙海峰没敢问她做什么工作,到底是李立口中的公共汽车,还是她对他说的“不是你想的那种人”?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孙海峰两杯酒下肚,说起他妻子的事。露露说,那你没想着去找她吗?孙海峰叹了口气说,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她去吧。黄酒的后劲上来,他话也热了,问她和李立什么关系。她说,什么关系也没有,你知道他多狡猾吗?他把女朋友的微信号备注成“表妹”。
窗外的雪越来越大,隐约听到了树枝压断的脆响,时起彼伏的车辆警报声。露露说,雪太大,你车骑不了了,现在打车也打不到,就在沙发上睡一晚吧,暖气很足,盖个毛毯就够了。
孙海峰泪腺一松,两行浊泪顺着脸颊流进了脖子,他一个劲地摇头。他是这么想的,一个寒冷的夜晚,一件暖和的衣服摆在赤身裸体的男人面前,男人无论如何都会穿上的。
孙海峰钻进漫天的大雪,推着车在雪地里嘎吱嘎吱踽踽前行。黑夜在弥散,城市像善于伪装的动物,充满诱惑和欺骗。
赵春花的微信还是加不上,电话依然是关机。她给孙海峰洗了三个月的衣服,跟他说联系到了上海脑科医院的专家,说婷婷这种情况可以治疗。孙海峰把鼓鼓囊囊的信封塞到赵春花手上,说,这是我全部的家当,赶紧带婷婷去看吧。赵春花临走前一天晚上,哄睡了婷婷,邀孙海峰来到出租房。她画了眉毛,涂了眼影,抹了口红,拉着孙海峰的手说,今晚出租房没人,我们到浴室里吧,本来想约你去隔壁如家的,怕婷婷醒了找不到人。孙海峰不知所措,赵春花拉过他的手从上衣下摆伸进去,捂在小巧的胸部上,孙海峰的手往下滑,摸到了她小腹上蛇皮一样冰冷的疤痕,猛地缩回了手,说,我该回去了。
5
孙海峰没再见过李立,微信聊过几次,李立说老家女朋友嫁给富二代了,露露也找到了男朋友。孙海峰想安慰他,约他出来吃饭,李立说不用了,他想去长江大桥吹吹风。孙海峰说,我陪你去。李立发了个哭脸,说两个大男人有什么好去的,他只想一个人待会。孙海峰担心李立会寻短见,从长江大桥上跳下去,结果是杞人忧天,李立每天都会更新朋友圈,转载各式各样的致富经。
赵春花的朋友圈已经几个月没更新,孙海峰趁着月假,决定在出租屋一醉方休,他在超市买了羊肉卷,牛肉卷,毛肚,买了海底捞的底料和蘸料,在烟酒店拎了一瓶“海之蓝”。他喝得醉眼蒙眬,听见有人敲门,他开了门,一个面目模糊的人站在门口,拖着一只笨重的红色行李箱。孙海峰眯起眼睛打量来人,那人的面孔像服装店的塑料模特一样洁白光滑。
赵春花?
别看了,我走了很远的路,什么也不想说。
你是万芳芳?
我是谁不重要,你要是想听,我后面会慢慢说给你听。
你来做什么?
我想留下来,如果你让我走,我也不会低声下气地求你,我马上就走。
孙海峰茫然了,说,我也不知道,我现在醉得厉害,你陪我走一走醒醒酒吧。
孙海峰踉踉跄跄地走在前面,拖着行李箱的女人走在后面。马路上的汽车水泄不通,排成一条歪歪扭扭的长龙,不停地按着喇叭,送外卖的骑手们在车流的缝隙里闪转腾挪。对面人行道上一个老男人坐在轮椅上,怀里抱着一条黑色泰迪犬,由老女人推着。一对年轻的夫妻弓起胳膊,小女孩架在他们胳膊上,蜷着双腿,作飞行状。天空暗淡下来,呈现出夜晚的趋势,孙海峰跌跌撞撞,抱住一棵梧桐树剧烈地呕吐,他摸出手机,举到眼前。
半醒半醉间,孙海峰看见,夜空依旧,但月光更亮了。他还看见,他手机里也有一个月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