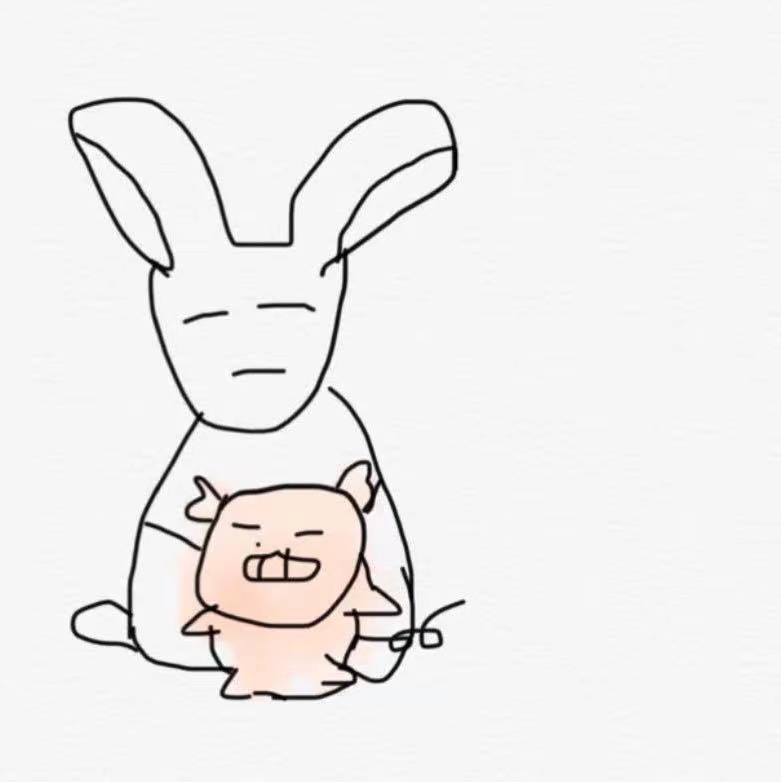确诊老年痴呆后,孙红的祖父开始走盲道。
第一次是在冬至那天晚饭,祖父正吃着饺子,突然把碗筷一摔,站起来就穿衣服、穿那双已经被他踩过半个世纪的解放鞋,一家人阻拦,祖父硬冲不出,竟靠在门边开始抹眼泪,全家人悲从中来。祖父48年参军,参与过建国以来大大小小各种战争,自打孙红父母记事以来,从未见他流过一滴眼泪。正僵持着,孙红站出来,说爷爷可能就是想走走,我陪他去走走,没事的。
出了楼门,祖父冲到街上找盲道,十二月的哈尔滨雪下得很厚,祖父盯着地面扫了三圈,转头问孙红:
“盲道呢?”
孙红用脚把盲道上的雪扫出来,露出竖向排列的黄色条纹凸砖,祖父终于心满意足,解放鞋一甩,踏上盲道,孙红在旁边跟着,每当祖父再次问盲道的时候,他就伸脚把盲道清出来,回家后,孙红的左腿和裤腿结出一层薄透的霜,皮肉冻得发紫。
这天后,祖父一发不可收拾。他每天都走盲道。有时正在午睡,他一个挺身就从床上翻起来开始穿衣服,有时他浇花浇到一半就提着水壶走到街上,因这情况,孙红住到祖父家,每次听到大门一摔,他就追出去。
祖父走起盲道来轴得惊人,他会站在一辆占用盲道的汽车前等4、5个小时,任凭雪落满半身,一动不动,直到车主过来挪走,他会因为不规范的盲道来回折返,仿佛再走一遍错乱的砖就能排序整齐。孙红猜测:这是爷爷正在和病魔抗争的途径,爷爷当了一辈子军人,绝对不会对任何敌人妥协。
但事实上,祖父并未取得什么优势,春天后,他彻底失智,忘记吃饭,忘记所有人的名字,忘记自己的家在哪里,唯一记得的只剩走盲道。夏天到来时祖父去世,在其生命的最后阶段,仍不忘让孙红推着自己去医院的盲道上行驶,孙红缓慢推着,祖父佝偻身体,已经睡着,他的毛衣皱缩堆砌出几百条沟坎,和主人一般苍老,孙红望向前方,看见笔直的盲道一直延伸到住院楼拐角,成为一堵躺在瘦弱老头面前的黄色高壁。突然,祖父醒来,轻声说道:
“起风了。”
孙红没感觉到风,他弯下身,为祖父盖好毯子,发现祖父又睡着了。
葬礼结束后,孙红父亲接祖母去南方,卖掉老屋,留孙红一人收拾祖父遗物。祖父房间整洁,保持干净在30年前他尚在军队时成为了肌肉记忆,在活力与智力一起如同沙尘一般从他的躯体里流散后,习惯成了尊严的最终防线,孙红把墙上的相框一个个取下,把祖父书柜里的书一本本塞进纸箱,抽屉里有一排勋章,孙红装进自己随身背的双肩包里,推回抽屉时,一个牛皮本子掉出来,他翻看两页,里面记载了50年前祖父在朝鲜打仗的事,再翻两页,他发现不对劲的地方,这是新本子,字迹也不陈旧,他想了一会反应过来——这是祖父在彻底失智前重新写出来的。
孙红带着这本日记回到青岛,读完后,因没有勇气保留,在深夜去海边焚烧掉书稿,灰烬被风吹进海里。在卖掉老屋,拿到佛罗里达州来的第一封信件后,他凭借阅读记忆按照自己的文法与用词习惯重新写出祖父的故事:
******
12月12日,我背着一部电台行军,周围是极深的草甸。电台中心位置已被流弹打中,寻找频道时只有风沙声,我不知是否与损伤有关。我隶属于陆军第120师第7团,目标汉城,我独自一人,渡过鸭绿江后因一场雾战从大部队遗失。
这里很冷,风大,与家不同。我靠着指南针和一本地图往汇合点前行,途中几次看见韩军的汽车车灯划破黑夜,都侥幸逃脱,在离汇合点仅剩3公里时与美军小队遭遇,被榴弹炸飞,醒来后双眼不能视。
如今已过数月,我双眼复明,才得以记下至今为止所遭遇的事。
遭遇战后,我重伤倒地,往燃烧声相反方向爬了很久。朝鲜半岛的土地与家里的味道不同,总有铁锈的臭味,灌木很多,在初冬时节不比刺刀容易对付,我背部有大伤口,有些粘稠的血顺着脖颈流到脸上。爬了可能有一整晚,我在一个边缘停下,翻下去,肉体在土坡上和碎石一起轮转,我想起出发前我把浆洗的军装挂在院子里晾晒的画面。我做好了觉悟。
再次苏醒,触感柔软,我感到浑身疲劳都已离去,自检身体,发现胸前缠了三层绷带,背后伤口有清凉感,也许是草药。我撑着地板慢慢起身,弯着腰摸了一圈,墙壁是不规则的石质,完整,有弧度,地上有一团干草,这是我沉睡的地方,干草边有一个一人宽的窄缝。我心里有了数,这是一个山洞。我钻进缝里一路往外探,七八步走出去。我听到水流声,听到夏天阳光晒到石头上特有的锋芒声,我听到草叶晃动声,听到敲打声,我还听到有人向我快步走来,我蹲下,把身体转向那个人的方向。很快,声音到我面前,停住,那个人也蹲下,把一个球形物体放进我手心,他把我的手推向我的嘴边,我闻到香味,咬下,是桃子。
他说了很多句话,我听不懂,他递给我一柄长物,我接住,是我的三八式步枪,枪托上有三道划痕。我愕然。他把一个单字说了三遍,发音像是“金”,我想这是他的名字,我也讲出我的名字。
因为语言不同,我和金只能靠在对方手掌心画画来交流,时日一长,竟创造出一种特殊的字符,互相有了默契。金告诉我我们在一座巨大的、奇异的、充满活力的山洞里面,金带我去摸了一些无比宏伟的树,我不认识品种,其中最粗大的一株我得绕着走4、5分钟才能回到原点,这里还有一个果园,繁茂丰硕,我在里面摸到了桃树、杏树、柿子树等多个原本不会在同季节成熟的果树,这让我百思不得其解。水果成为我和金生活中的主要食物来源。
一周时间,我在心中建立出这个山洞的微缩模型。一条河流切割中心,北边是果园、高草丛、河流分支延伸而出的一方水池,南边是丘陵,广袤的森林,我和金的山洞就在丘陵边缘。这时我的眼睛已能隐约感觉到光暗分别,我意识到天亮天黑在这座山洞中也是存在的,金告诉我山洞很高,但最高处顶壁不可置信地薄,如同虫翼,日出时阳光穿透照进来,夜深后,若是天气好,甚至能看见模糊星迹。这里只是更朦胧些的外界内心。
金说他比我早来三个月,最初一个月里遍寻不到出口,心灰意冷,但时间流逝,还是振作起来生活。外界正打仗,炮火连天,这里却安静如秋夜,金甚至不再焦虑。他用匕首雕刻木头,长跑,他给过我一些小摆件,老鼠、麻雀,不算精巧,但也没走形,后来金雕刻的作品越来越宏伟,他用森林里腐朽的足有几百斤重的枯木雕刻出1:1的动物。我在森林中散步时遇到过鳄鱼,老虎,犀牛,还有一整个狒狒群,数量在三周时间内不断增加,最终停留在9只这个数字。
山洞里没有动物。我们没从河流中钓上过鱼,森林里潮湿翠郁,但从没有过一声虫鸣。金每天早晨晨跑,他说这是他保持创作活力的秘诀,我有天跟在他身后一起慢跑,跑至森林时,突然听到了一声鸟叫,循声找去,最终摸到树桩上的一团鸟窝,里面有两只大鸟三只小鸟,木制,像是金中期的作品,比早期要精细,但比后期更写实。我离开鸟窝木雕,继续慢跑,鸟鸣再次在身后出现,我被一截倒木绊倒,摔在灌木里,鸟鸣消失。我摔伤膝盖,有一块皮肤被尖锐碎石划破。金用草药帮我厚敷,用他所剩不多的绷带帮我包扎好,我在他手臂上画出我早上奔跑时发生的事,金回答我说这在他每次奔跑时都会发生。我表示这很奇妙,金很开心,他说他不是教徒,但这里像天堂。
三天后,我膝盖伤愈,清晨再次跟随金奔跑,除了动物鸣叫外还听到植物生长所发出的声音,像是雨滴落在吉普车顶棚,但更有秩序。跑到丘陵地带时,我再次摔倒,整个人从坡顶滚到坡底。
金的绷带用完了,他帮我上好药,叮嘱我先躺着休息,等草药干透他会来给我换药。我受的大部分是皮外伤,只是左肋骨暗暗发痛,这让我的睡眠变得零散且混乱。某天白天,我醒来,走出我休息的山洞,突然看见模糊的橘黄色影子浮在半空中,面前是被光晕压弯的高草丛,一个背影正弯腰,身体摇晃着,下一瞬,我失而复还的视力再次离我而去。我跟着声音走去,走到金的旁边,我拍他的背,问他在做什么,他牵着我的手,弯下腰,把它放在地面上,我摸到圆滑的鹅卵石,密密麻麻镶在泥土里。金的左手提着一桶还在滴水的鹅卵石,这是他刚从河里捞上来的,金的右手拎着一块大石头,这是他把鹅卵石凿进土地中的工具。金运用他的智慧帮我做出一条道路,为了我跑步时不再摔倒。我们为它取名为盲道。
我其实有很多次想象过金的模样。他很年轻,可能与我同龄,身材健壮,像年轻豹子一般充满活力与热情,眼睛会很圆,会很有神,经常笑,不会因为身处囚笼而失去灵芒。
盲道铺好后,我每天和金一同奔跑,早晨一次,傍晚一次。我们从山洞出发,穿过森林,这里的盲道歪七扭八、高低不平,出森林后我们跑过河流,进入高草丛,盲道笔直平整,高草丛后是果园,盲道画出一个接一个的圆弧,然后我们回到丘陵,盲道变成山道,跟毛笔字一样写意,盘旋而上。开始三天我总是跑得很慢,磕磕绊绊,金牵起我的手帮我一起熟悉,几天后我健步如飞,甚至比拥有视力时跑得更快,我想古代打仗时蒙马眼应该就是这个道理,什么都看不见的时候就什么都不害怕,跑到极速时,精神牵引肉体飞起来。
我在盲道上奔跑时,世界开始改变。首先是声音,金的木雕活过来的声音,森林里,老虎奔跑时压断草叶,老鹰扑打翅膀,猿抓住一截树干,然后把自己像秋千一样摔向另一枝。声音之后是气味,我闻到更加具体且分散的味道,我在果园里闻到果子从种子开始生长的味道,一颗苹果,吊在那里,核最先诞生,万千血肉都为其而来,它是整体的产物,树木,人类,石头也是同理,我在丘陵顶闻到风的味道,刚纺出来的纱巾,刚印刷好的纸张,这就是风的味道,是它的过去,也是它的未来,我在坡顶坐了一下午,终得以领悟:风是四维的产物,时间于它没有意义。
最后改变的是时间,我开始在奔跑中穿越时空。路途时,我借山洞中的声音找回自己曾经所听到的声音,借山洞中的气味找回曾经所闻过的气味,让它们在我黑暗的疾驰中降临,其中我最喜欢的场景是当兵前一年的过年,父亲从山上砍回木柴,在一个空旷的小房间里干燥,最后塞进炕下,等待点燃,祖母剪了很多窗花,大年夜那晚我会用糨糊把它们粘在结满冰霜的玻璃窗上,我们杀了一头年猪,足有300斤重,母亲用它炖了两大锅杀猪菜,东北的冬天会很冷,我和两个弟弟穿好棉袄、棉裤、手闷子、貂毛帽子,像三只矮胖的红薯,我们走上冻结的冰面放烟花。
我闻到森林里的雾气,比风的气味更加饱满,我放慢步伐,慢跑到盲道边最粗壮的那棵松树旁,我把手搭上松树,我摸到树心中水流正从根部往上奔腾。
我点燃引信,烟火飞上漆黑的夜空,片刻后在空中炸裂,紧接着,其他村民点燃的其他烟火也都在这一瞬间迸发开来,夜空比春天要更绚烂。
我奔跑结束,余韵即散,我摸到树心中喷薄向上的水流渐渐式微,即将在最顶端消逝,我又跑起来,水流变得强劲,顶端爆发,然后散到几千根枝条上,我伸出手在盲道上疾驰,不断触到一棵又一棵树,整个森林的松树都在毫不停歇地放着烟花。
很长一段时间,我沉迷于这种把戏。再后来,我开始走向更远的过去,甚至挖掘出早已遗忘的儿时记忆,我终于醒悟,幻想来自我对故乡的渴望。这一天傍晚,我在丘陵上坐着,金在日落时分回来,他看见我,用一种蹩脚的口音呼喊我的名字,我站起来,抓住他的手臂问他知不知道我们在这里有多久了?
金说有半年时间,他觉得有过200次日出日落,只会更多,不会更少。
我说战争已经结束了。我们该回家了。
金说还没结束。
金把我带到河边,他把我的手放进冰凉湍急的河流里,我的手变成一条无助的鱼,不知归途亦不明去处,在河水里不上不下的位置漂浮着。金说等等,我等了等,一枚弹壳撞进我的手里,我捡起来,抚摸,我确定这是一枚7.62口径子弹的弹壳,甚至是属于我方军队的,我能摸到刻印出的编号。我把手又伸进去,很快,几十枚,几百枚,最终有几千枚弹壳从我的手边游过,如同洄游的鲑鱼群。我拿出手,在金的手臂上提问这些每天都会有吗?
金回答,战争还没结束。
我不再奔跑了。我排斥看到可能永远也不能回去的老家。偶尔我从盲道走到高草丛,然后走出盲道,随意躺倒在草窝里,等待太阳给予的光芒渐熄,再通过盲道走回山洞里。有一次我在草丛里被一柄插在地上的匕首绊倒,我拔出来,发现是一把军用刺刀,我用军刺把它做标记处的土包掘开,发现了一套军装,一把汤姆逊冲锋枪,四盘弹夹,还有两枚已经生锈的手榴弹。我带着军刺回去,问金这里的出口在哪里?他最开始是从哪里发现的我?
金说战争还没结束。
停止奔跑后,我的眼睛开始复明,我开始看到一些朦胧的影子,到处都在摇曳、晕染,粘在一起,模糊到看不清颜色,只剩形状。曾经村子里有一位画水墨画的老头,我去他家买对联时看到他家挂满画稿,与一般的水墨画不同,色彩纷呈,正是我此刻眼前所见。我跟在金后面,努力分辨眼前所有事物的边界,我发现金也不再奔跑与雕刻,他最常干的事是躺在丘陵上望着薄如蝉翼的天盖发呆,原本我同情他,我知道他的家被海分割在世界的另一端,直到有一天我在他身旁躺下,他抓住我的手臂说,如果地球一共只有这个山洞这么大就好了。
一些失眠深夜,我从山洞出来,发现金也坐在洞口,向下俯瞰,我邀请他,我们一起在盲道上散步。我告诉金我走在这样的道路上能回到过去,金说他的感觉与我不同,更像是去向未来。他抓起我的手,伸长,在手肘处画下一个点,一根线连向左边,一根连向右边。我问他未来是什么样子,他说很模糊,他有了几个孩子,买下一座农场,田地里都种满玉米,后院里有一座十几米高的土坡,他在坡顶种了一株苹果树。我说这是盲道的魔力,安全感。金说他偶尔也会闭上眼睛在盲道上跑,我问那是什么感觉,他回答风,到处都是风,推着自己的,被自己的肉体划破空气创造出来的,以及更多的不知从何而来的,包裹自己的。
我说:“风带我们穿越时间,它是现在之外的力量。”
金听不懂我的话,我抓住他的手臂,在他手上重复了一遍。
在视力逐渐恢复的过程中,金的模样和我想象中有了些出入,他不年轻,可能已近中年,脸上皱纹明显,他十分健壮,总穿着一件棉布背心,肩背上的肌肉如山脉一般峻峭,他有一头金发,卷曲,他有一把配枪总挂在腰间,M1911。
在我完全复明的前一天,我带进来的电台响了。接上讯号,我再次和组织联系上,组织说会派人搜寻我的位置,同时要求我想尽办法与大部队会合。
那天晚上,我再次踏上盲道,闭上眼睛奔跑。我不断回忆在部队受过的训练,在战场上涌出过的愤怒,我曾经的班长死于轰炸,尸体不完整,我中过弹,子弹一旦碰到皮肤,就会更加贪婪嗜血地往身体更深处钻,我很害怕,我想念我爱的人,我知道肉体的痛苦终会结束,但悲伤的余波不容易轻易散去。我在盲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睁开眼,却始终没有回到曾经身处战争之中的过去,没有愤怒,只有迷茫。我停下来,坐在盲道上。战争没有结束。我用我和金发明出的字符在盲道边的沙地上写下这行字。这行之后我又写下几百条,天亮时,我去高草丛挖出金的冲锋枪和手榴弹。
金是敌人,我从第一次见面就在怀疑这件事,他说的不是朝鲜语,更加冗长,音调转换急促,他汗毛很重,有体味,有美军的装备。他囚禁了我,他在等待信号把我带回他的组织。他是敌军,是我必须要消灭的敌人。
我的三八式步枪只剩两发子弹,太久没开,我不确定它还能否击发。我把高草丛埋着的冲锋枪和手榴弹擦拭干净,藏进森林,刺刀用布条绑在小腿上。清晨,我请求金带着我一起慢跑,我们一起到达我事先藏好装备的地方,我停下,用呼喊声叫住金,然后我睁开眼睛,金走过来,我抓住他的手告诉他我的眼睛已经完全好了,然后我走到树后,端起我的三八式步枪,瞄准了金的脑袋。我想开枪,但脑子里转来转去的都是这几个月和金生活的场景,金看着我,没有表情,没有动作。我突然闻到风的味道,我听到风在我第一次从盲道上奔跑时被创造出来,穿越200天的时空,在这一秒都向我涌来。我低下头,发现自己正站在盲道上,我看见了金蹲在地上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地敲出盲道,看见我们一同奔跑,鸟兽为伴,我看见金第一次雕出一只栩栩如生的乌鸦,对着阳光举起来,笑得如同孩童,我看见我放下了枪,我们共同找到了出口然后离开了这个山洞,我看到我的国家,城市建设成我从未想过的漂亮摸样,每条道路上都有笔直的盲道,我看见金在我的枪口下,在空中,画出一段字符,他说他原谅我。我向后退一步,画面全部消失,只剩下金在眼前为我画出的字符以及洞穴中电台讯号传来的电流声。我扣动扳机,子弹没有卡壳,旋转着从金的胸前穿进去,用环绕自身的气流撕毁了他的心脏,最后从他的身后穿出来,这一刻,我的眼睛完全复明,终于看清楚了金的眼睛,他的眼睛锐利,瞳仁很小,在眼白间紧紧缩成一个点,让人不寒而栗。
金捂着胸口,浓稠的血浆从指缝间滴下,这时是早上,阳光透过一层大地透镜,又被森林里高大乔木的枝叶打散,缓慢地洒遍金的身体,他倒下,倒在几株蘑菇旁边,眯着的眼睛终于睁开,但瞳孔扩散,算不上有神。我搜金的身体,拿走了他的身份铭牌和他的配枪,弹夹里没装子弹,之后我花了三天,终于在森林里的一个土坡上找到一个被落石掩盖的入口。走出山洞后,我用电台联系上了队伍,成功汇合,战争没有结束。1951年7月,我跟随我所在的连队回到国内。
******
这本重新写成的日记被孙红收进放祖父遗物的抽屉里,和那些奖章、老照片以及国外来信摆在一起。当年过年,孙红和父亲喝掉三斤白酒,父亲红着脸讲述祖父小时候因为他偷了同桌一块橡皮而打了他一顿,孙红拿出这封信,父亲看完,沉默,孙红紧接着拿出佛罗里达来的那封信件,抖落出里面的照片递给父亲。他说原来不是愧疚,是怀念。
信是在卖掉老屋时发现的,祖父去世半年后,哈尔滨的老屋终于找到卖家,孙红独自回去交接。他看见楼梯间墙壁上的信箱里被塞得接近满溢,打开,里面多是吊唁信——祖父的故友以及曾经待过的部队机关,其中,有一封从佛罗里达州寄来的平信,撕开,里面只有一张照片,一张7人全家福,全是典型的白种人外貌,照片中心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者,眼睛很圆,眼神和煦。他们身后有一间谷仓,两扇门敞开,能看见其中堆积的玉米,远处是一座小山坡,坡顶有株果树,但太过模糊,难以辨认。孙红翻到照片后面,看见上面画了一行奇异的符号,像是游戏里或是影视剧里会出现的那种特效咒语。
卖掉房子后,他拜托新主人如果再收到国外的信件,就转寄快递到他在青岛的住址,如果方便,可以复印一份,分开寄过来,以防丢失。每一封孙红付100元的报酬以示感谢。
他在青岛的四年间,佛罗里达州的信又来了4封,皆在夏天,每封都只有一张照片和照片后的奇幻字符。第五年后,信再没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