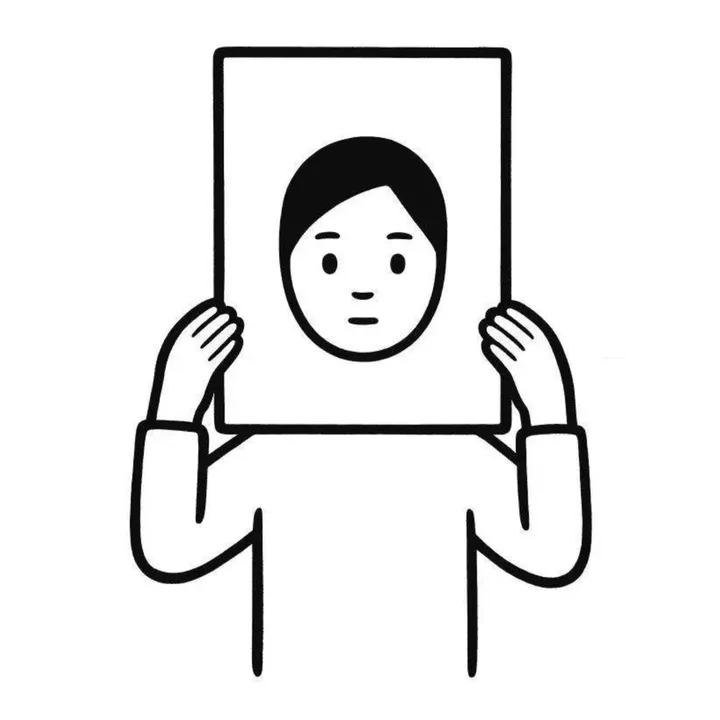母亲死后,我连续梦到同一个女人的背影,她有着长及腰的头发,整片发丝像瀑布一般,还会发出簌簌的声音。我反复在梦里操纵她转身,企图弥补着某种缺憾。
母亲没有这样的身形,年轻时也没有,她曾经很胖,有一圈下坠的肚子,我很怕她转身的时候,我看到的却是她平静的面庞。
醒来时陷入落寞,明知道什么正在逝去,又毫无办法,这似乎是一个信号,某种还未割断的缘分正在延续,只不过是换了个地方罢了。我不曾看到女人的正脸,也没有见母亲最后一面,呼吸机还在运作的时候,她温凉的手指已经瘦弱如削尖的铅笔,摸上去硌在心里,眼睛闭着,嘴巴在面罩之下蠕动,像是在呼唤谁,又像是在被谁呼唤而应答,人临死之前的几天里可以看到什么,或者听到什么,游魂在逼仄的病房里站立,有别人的关系,有母亲的关系,他们兴许认识我,在和母亲谈论关于我的事情,母亲逐渐焦躁,他们一定在争论关于我的未来,我能否扛得住失去一次至亲所带来的情感崩溃,我握紧母亲的手,她紧张的面孔重新从容,眼睛睁开,因为刺眼的阳光而在眼角流下一滴滚烫的泪。
我点点头,确信她看到了什么我看不到的,机器发出细微的嘀嘀声,是生命的倒计时,明示厄运降至,神与佛祖均不在场。夜里三点,我醒来,母亲喃喃自语,耳朵贴在面罩上听,反复在说,知道了,知道了。拿开面罩,母亲呼吸急促,血氧报警。凌晨四点,我从卫生间回来,母亲偷偷变成一条直线,抢救一个小时。凌晨五点,母亲的手冰凉,像路边搁置的石头,呼吸机停止,医生宣布时间,母亲又变成了一个点。人真可笑,无非是点、线、面,我们就是面,一个个不同的横截面,我现在横在你这个面上。
胡倩动弹不得,手肘被我压住,头歪向一侧,脸颊左眉角的那颗痣没有随着时间长大,她说,你现在真的压疼我了。我挪开身子,不再大面积发表关于母亲的看法。月光从窗帘缝隙透进来,
胡倩扯了扯被子把脖子以下盖严,生怕被月亮看个精光。你对死亡还真有见解,她说。我点点头仰面躺着,天花板有月光的影子,正如水波般流淌。我只是有点想我妈了,我说,她其实是个好人,你也是个好人,我没想到你还能来找我,我们有多久没见了。胡倩说,我不是个好人,你也别把我当好人,我知道病房里什么样,有时候轮不到你发表那么多看法,情感也没地释放,人死了就是死了,太平间和殡仪馆还要安排,晚一步,连个地方也没有,你一点也没变,总是事后高谈阔论,我挺讨厌假惺惺的,但是没办法,我还是想到了你,我们确实很久没见了,天亮之后,我还是要走的,你明白吗?我看着月光出神,她的声音好像也没变,尖锐刺耳,有时候不中听。我说,1997年6月28,泰森像吃饺子一样把霍利菲尔德的耳朵咬了一口,当时你在吃我妈做的饺子,包完后,我说我不够吃,她重新剁肉,又包了一些,你当时吃的就是她给你包的,韭菜馅的,我们找了个电视机,我忘了在哪了,晚自习结束也没赶回去,饭盒丢了,校门关了,我带你去了一个地方,教你打拳,那里很空旷,地砖上有草冒出来,谁也找不到我们,你把拳头握起来,像软馒头一样锤在我身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感兴趣,我们都很兴奋,兴奋于逃课,夜不归宿,在空旷而长草的荒芜之上空挥拳头,振振有词,你说的是将命运锤在身后,我说的是你尽管打,打在我的心上。胡倩好像没有听到,侧过身去,拽了一把被子,把背留给我,她的背格外瘦削,受尽中年的折磨。我们不再交谈,卧室的气氛逐渐凝固,时间随着月光的倾斜流逝,这像一个梦,我贴近她的身体,伸手去抓,握住她的胸。
五天前,胡倩找到我,我刚处理完母亲的事情,将她安葬在桃花山公墓,公墓在当地的一座山上,山本不叫桃花,名字很俗,被种满桃花后改造成景观基地,可以旅游可以祭祀。母亲喜欢桃花,也喜欢吃桃,没有别的选择,这里有大力度的折扣。近来我的梦里带有桃花,女人是在桃树下的背影,我相信母亲已经安心,正在某棵树下啃桃子。胡倩和我约在咖啡厅见面,她脸上没有发福的迹象,肌肤紧实,不知道是不是化妆的缘故,倒也不是长相年轻,有一种猛然从青春被拉扯变形的意味,也许我身上也有,只不过方向不同罢了。白色丝质衬衫,黑色垂感长裤,一身知性的打扮,唯有眼袋有些发黑,像是熬了几个通宵,或是为什么而疲倦。我们随便谈着什么,她像是不记得当年那些事,我没提,也没什么好提的,无非是个见面而已,我告诉她我离婚了,生活挺顺的,母亲前几天也走掉了,无牵无挂了。她听出我的自嘲,轻蔑地笑,但又真切地表达了同情,大概都是形式主义。我喝了一杯拿铁,觉得挺无聊的,刻意不去回忆二十年前的事。我说,其实没有那么可怜,比较自由,若为自由故,什么都可抛。她喝下自己的咖啡,隔着小圆桌看我。有时候由不得我们,她说,带我去看看你母亲吧。
那天晚上的月亮像个钩子,天上没有星,一切都被若隐若现的云遮掩着,胡倩把软拳头打在我的胸口时确实用力了,我摔倒在地。她被我吓到,蹲下看我,我顺势拉倒她,我们仰卧在石砖地上,草从校服缝隙里钻出来,往天上长,遮挡着我们的羞涩。她说,你骗我。我说,我妈包的饺子就是有劲。她笑着看天。几颗星从云边游出来,我说,你看,流星。她说,哪里?我说,我已经许好愿望了,我不能告诉你,你今后前途一片光明。她说,傻瓜,你这不是告诉我了吗,那你呢,将来光明吗?我说,将来我要开一个拳击馆,参加比赛,我要做像泰森一样的男人。她笑着说,咬别人耳朵吗?我说,咬你耳朵。我抱住她,假装去啃咬她,她的耳垂很凉,纹路像宇宙的星辰,我把它含在嘴里,她没敢动,我也没敢动,时间在我嘴里静止。她推开我,站起身,我们往学校走,又远离学校,走上大路,又远离大路,路灯挨个熄灭,我牵起她的手,点亮心里的灯。将命运锤在身后,胡倩说。我点点头。身后没什么值得怀念的,往前看才是我们学会的,我们还年轻,如果老师问起来,你就说我胁迫你的,我说。
显然她没有同意,我们翻半夜的墙回去,墙也许是太高,也许是墙对面的一块石头,我不知道,胡倩的腿像树枝般折断,响声很脆,不合时宜的石头将美好的夜晚打破,我不再相信流星,流星也是石头,石头是恶的。
我把她抱到校医室,值班大夫看不了骨折,老师在医院给她固定好石板后见到了我妈,随后是她爸,我曾经幻想过无数次见家长的画面,但是没有预料到老师是见证人,一个秃顶的中年男人,站在我和胡倩之间,把我和她之间仅存的污点全部抖了出来,他是这么说的,一个整天就知道打拳的臭小子和一个把学习好彻底浪费的傻妮子。你摔不得,你摔不得,她爸焦急地说。那是另一个中年男人,瘦弱、胆怯,他看着我的时候,仿佛犯错误的是他自己,我无地自容。胡倩说自愿跟我出去的,阿姨的饺子很好吃。我妈则指责她勾引了我,就像我爸被别人勾引去了一样的勾引,那个年代,如此沉重的词汇,加在一个断腿的女孩身上,这个世界的重量都因我而被她承载了。
急诊室的天花板在往下坠,所有人的额头上都有汗,我站在其中,看着医生用小锤最后敲击石板,调整着角度,胡倩半卧在蓝色塑料布铺盖的病床上,咬着嘴唇,牙齿像要陷进肉里,我妈和谁吵了起来,声音逐渐嘈杂,胡倩看着我说了什么,又好像没说,我们之间被什么东西阻隔着,我知道一切要完了,像是经历了一场盛大而没有结果的拳击比赛。
车子在桃花山脚拐上去,空气湿润,一片桃花树从云雾里生出来,每两棵树之间各藏着一块碑,母亲在靠近山顶的位置,那里风景好一些,看得远,母亲生前喜欢往远了看,但是有些事情也是没有料到,人不是全能的,她没能等到父亲的一句道歉,也许我还可以等,但生活又有什么可道歉的呢。
我转头看胡倩,她把手从副驾驶窗户伸出去,张开手指,用指腹接风,之后是头,头发向后飘荡,眼睛闭着,感受墓地的桃香。你像是来旅游的,我说。她把头别回来,说,我就回来几天,就当是旅游吧。
我继续把车子往前开,沿盘旋的道路向上,在一处杂草略多的空地停下来,母亲就在前面还没太完工的C区,有工人正在敲敲打打,把墓园的边沿用大理石块砌起来,把桃树围进去,使其像个园子。连墓地都有期房,可以提前预定,我说,当我妈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我跑过来把位置提前定好了,虽然我跟她商量过,也跟她描述了这里的风景,山顶、桃树、时常碰见云雾、俯瞰小城,但这种感觉很奇怪,有点对不起她,一种人为加速死亡的错觉。胡倩下车,我们脚踩在湿软的泥地上,雨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下的,不大,空气里有清新感,没有诡异的气氛,人死并不诡异,周遭还有种烂尾楼的假象。她说,命运是定好的,不是我们说了算的,提前预定只能说明你走在了前面,总比走在后面强。我不喜欢她说教,但是遥远的陌生感驱逐了我的反驳,我带着她往前走,经过工人后在母亲的墓碑处停下,我俯身拔掉桃树下生的杂草,胡倩看着碑前的照片。阿姨胖了,她说。我没有回话,就当来旅游的吧。
拂去碑沿上的露水,站在这里往下看,视线勉强穿透阴霾,看到滨海县的全景,楼宇不高,十几年没有变化,像个从没有长大的孩子,但是我们都在变老,老是什么概念呢,阻断死亡的墙一个个倾塌,母亲躲在我身后的小盒子里,已经失去了力量,安静而又祥和,等我老了,谁为我来拭去碑沿上的露水,又站在哪儿才合适。C区还有地方吗?胡倩问我。有很多,我挑了这里,那边远一点的也可以,我伸手往前指了指接着说,就是视野没有这里好,其实没什么差别,看风景的从不会是死人,都是我们的借口罢了。你现在还打拳吗?她又问我。我拍拍肚子,说,我已经像发面馒头了,拳馆开不起来,爱好坚持不下来的,我现在在工地干,不干重活,就四处看看,偶尔和人打架的时候觉得自己年轻。她笑了,说,现在打架不可取了,到处都是摄像头。我说,你说得对,我上次打架赔了好几万,总是我在赔钱,说明我赢了,成人的社会赢了是要输钱的,我也可以躺在地上挨打,但总是哪里说不过去。胡倩说,你骨子里不服输。我说,要是以前也有摄像头,我就可以知道是哪块石头把你的腿搞断的了。她说,你还记得。我说,记得。胡倩挨着母亲坐在石台上,我点上一支烟,天空开始滴雨,某种晴阴交替,胡倩和我要了一支。她说,你不准备问我什么吗?我说,有什么好问的,你不是单身就是结婚了,我们这个年纪是按着时间线规律地走着的,不偏不倚地正中所有可能性的下怀,结局不会出人意料的,你会回去,北京还是南京,我不记得了,我还是喜欢滨海这个地方,那里远点的方向是一片不起眼的海,就一个尾巴搭在县城的一角,但是可以感觉凉爽,和完全被控制的规律感。
胡倩站起来,把烟含在嘴里,用力吸,咳了两声,身体像个虾米似的弯曲,说,你也许说得对,我没有做过什么不规律的事,我们翻墙的那个夜里,我跳得用力了一些。我说,墙实在太高了,石头太硬了。她继续说,我爸带我回去的时候告诉我,我必须小心,我和别人不一样,路上他就哭了,我第一次看他哭,那时候他还是个中年人,眼泪不太容易见到,后来不一样了,他几乎每天都哭,说他无法陪我走到最后,他怎么可能陪我走到最后呢。雨线如丝,她扯着我的衣襟,挽住我的胳膊,我们躲在桃树下,云雾在山根散去,又在山腰汇集,小城若隐若现,我能听到她的心脏,在我的臂弯处,以二十几年前的频率跳动。你会常来这里吗?她说,墓园的C区,这个山头,也会成为你规律的一部分吗?
夜深的时候,我们醒了,月亮已经逃走,玻璃上是成片的黑,我们起先都没说话,我可以看到她的眼睛,睁得很大,漆黑的瞳孔比夜更深一些,再往里看,不知道藏着什么,只是黑。她盯着我,我像是她的家人,她像是我的一部分,前妻走后我没有这样抱过任何人,母亲几乎成了全部,晚期,工地也去的少了,我忘记了被人抱住和抱住人的感觉,有些恍惚。我说,我又梦到女人的背影,她头发很长,谁也不像,站在我妈病床的一旁,我们看着点滴往下落,等待生命的仪器停下来,病房的电视机里泰森张开嘴,他准备撕咬耳朵,欢呼声从四处惊起,我妈目不转睛地看着,时间回到1997,我们无能为力。
胡倩黑色的眼睛在低声说,我也和你一样,梦到过一些人,一个人,都是我爸,他从不同的高处跌落下来,树顶、楼房、悬崖,总是摔得很疼,他最怕跌落了,我也不能跌落,但是我感觉我一直在跌落,坠在了你的怀里。我搂紧她说,没事,你就往这坠吧,你早该往这坠了,现在还不晚。胡倩说,晚了,我们别说这些话了,你还能教我打拳吗?我说,现在吗?
我们从床上爬起来,我的卧室不大,于是移步到客厅,挪走沙发,拉开窗帘,月亮藏在云后面,星是零碎的,玻璃透着夏日夜晚的凉气,季节是相同的。我撤下步子,摆成弓字形,两手握拳,看着胡倩,她随便搭了件我的T恤,宽大的衣服把她衬得更加瘦小,像只将要被丢弃的木偶。
不用担心,今晚我们不用翻墙,把你的手握成拳头,大拇指压住食指,看我,我说,两只脚一前一后,哪个在前都行,左手放在脸颊旁边,记住,你随时都可能会挨打。胡倩嘴角上扬,眉角的痣跟着笑起来,说,我知道,我们都没少挨打。现在出拳,把你的右手往我脸上挥,尽量一条直线,可以用到腰腹,感受身体向前倾,把力量全部推出去,我说。你比之前专业多了,她说。那时候我们还是孩子,我说。胡倩把拳头推到我的身上,绵软无力,接着又是一拳,我把胸膛露给她,她连续挥击,力量越来越弱,我们没有开灯,我看到她的眼角挂着泪珠。我说,你还不如当年有劲了,那时候你还能击倒我呢。她继续用蹩脚的姿态攻击我,我迎上前去,双臂把她环进怀里,她不停地扭动,抽搐。我抱紧她,说,好了,停下吧,我们现在谁也打不动谁了。月亮仍旧是一个钩子,我们躺在客厅的地板上透过落地窗往外看。胡倩说,流星,你看到了吗?我说,我当时是骗你的,石头只会硌断你的身子。胡倩说,不是石头,我身子容易断,跟什么都没关系。如果有人找你学拳,你会教吗?我说,我现在不教了,我在工地上班,我已经四十多岁了。胡倩把头靠着我的胸膛,伸出手指,指着夜空的某一个角落说,刚才那颗流星挺大的,就和当年你看到的那颗一样,于是我许了个愿望,希望你能答应。我说,你别走了,家里有两个房间,不习惯你就睡我妈那屋,或者我睡我妈那屋,我们凑在一起试试,把之前的遗憾补上。
工地变得很忙,滨海县开始有了大项目,人们终于记起了这个小城,开始用力把它往更高处拽。梦里的女人回头了,有时候是母亲,有时候是胡倩,她们都笑得认真,母亲从病床上坐起来,看窗外的鸟,像是喜鹊,双腿站立在窗台外,正在唱歌,它飞过后母亲就不见了,有时候觉得母亲是鸟,或者像鸟一样的状态存在着,胡倩没有再走,住在我的房间里,她把物件收拾得规整,把我曾经获奖的拳击奖杯摆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每天都会挥击空拳,变得健康而强壮,每年都变得年轻,永远停留在17岁。梦里的她们两个交织在一起,都不太真实,后来我不再做梦,也意识到,缘分只是我的一个慰藉罢了,母亲死了就是死了,胡倩也在1997年的夏天就已经离开了,她早就通过了我,我回忆的事情大多是我自己的想象罢了。母亲一辈子恨女人,女人仿佛可以抢走一切,一切都可以被女人抢走,最后的呓语里不知道是否在和父亲对话,等一个合理而温馨的道歉。桃花山的桃花凋敝了,母亲睡着了,滨海县被笼在一片阴郁里悄然生长,胡倩好像没有来过,流星也只是普通的石头罢了。
胡胜全找到我的时候,我正在工地干活,楼有27层高,竖直插在土里,楼外有坚固的脚手架,我在17层被他找到。滨海县没有这么高的建筑,这算是第一座,我喜欢经常上来,站在高处往远处看,能忘掉的都忘掉了,人就那么渺小,脚下一滑,什么都没了,没什么好提的。他十几岁的样子,寸头,十分干练,不像他妈,估计是遗传了另一半,和我并排站着,透过脚手架往外看,城市下沉,圆弧形的对面是隆起的桃花山,漫山遍野的桃花在这里只是比碎屑还小的渣渣。你是叫王川,对吗?我没有搭理他。他继续说,你和我打一架。我把安全帽摘下来递给他说,这里不安全,打架没意思的。他张开脚步,两只手一前一后,握起拳头,盯着我看,他说,我妈让我来找你,和你打一架。我已经不打拳了,你妈在哪呢,楼下等着你吗,你们是来旅游的吗?他说,我妈就在那儿,他伸手指着远处的桃花山,我突然明白了什么。我说,是C区的墓园吗。他点点头。我看到天空有流星划过,在雾霭的阴霾里,我知道我在骗自己。
我没有和他打架,他眼里好像含着恨,我不知道他在恨些什么,胡倩没有提过她有一个儿子,她几乎什么都没提,我的梦又被勾了出来,胡倩变得清晰,但又不得不模糊。我带他回去,把母亲的房间收拾出来给他住,他不知道怎么称呼我,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也不知道胡倩跟他说过什么。胡胜全晚上会做噩梦,我从卧室出来,听到他在翻身、呻吟,嘟囔些什么,他的恐惧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胡倩把什么留给了他,他又带着什么在慢慢长大。我累了,回屋睡去。第二天醒来,他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说,你会教我打拳的,对吗?我妈说你是她见过的最厉害的人。我知道她一定在瞎编,我没有反驳,和一个死人反驳有什么意义呢,现在胡倩也只是一个符号,安静而又祥和地呆在C区。我说,是,1997年6月泰森的那场比赛,我和你妈一起看的,她也想学,我教了她,她很轻易地就击倒了我。胡胜全说,那你也教我吧。我说,你吃东西了吗,冰箱里有牛奶,我煎两个鸡蛋,你把牛奶拿出来放到微波炉里热一下,如果还想吃,我们就出去吃。
胡胜全倒是听话,他打开冰箱,取出袋装牛奶,我告诉他倒进杯子里再放进微波炉,他照做,把微波炉设定两分钟,接着我让他递给我两个鸡蛋,他重新打开冰箱,取出鸡蛋,然后盯着微波炉。他愣在厨房,眼神不安定地发散,好像并没有在看微波炉,屏显倒计时归零,微波炉发出“叮”的一声,胡胜全倒退了两步,差点倒在我的身上。我拍着他的肩膀,他回过神来看我,眼里都是惊恐。胡胜全的父亲从车里飞出去的时候,他被胡倩抱在后排座椅,胡倩多处骨头都坏掉了,那一年胡胜全十五岁,胡倩骨质天生疏松,钙化不足,那是一次几乎致命的打击,胡胜全的父亲被挂在一棵桃树上,当场死亡,胡倩知道自己的时间不会太久,在看到儿子和学校的混子击打在一起的时候想起了我,也许我就是她的稻草,这里的她已经不是一个人了,涵义实在太多,我不知道她当时在想什么,她在滨海的那几天什么都没提,她完全可以直接告诉我,她有一个儿子,要把这个儿子托付给我,自己被卡在自己的骨头里,我怎么会拒绝,高傲的姿态是她的尊严吧,我不知道,桃花山的桃花此时开得正旺,C区已经全部建完,你的母亲在哪个碑里,那里又是否可以看到整个滨海和正在竖起的摩天大楼。
你和我妈到底是什么关系,胡胜全问我。我说我们是同学,她也是我的第一个学生,后来我开了一个拳馆,你的母亲是最厉害的,她打赢了所有的人之后就走了,但是你知道,她的身体会轻易骨折,但是不要怀疑。胡胜全说,我妈最后已经不能说话了,她躺在病床上看着我,她曾经跟我说过你,说你教过她拳头,尽管这并没有让她变得更好,我是说更健康,如果她不在了,她让我来找你,我不知道找你能干什么,你根本不像她说的那么厉害,你们很久没见了,但她相信你,她最后握着我的手,还有什么话要跟我说,但是她已经不能说了,我没那么不坚强,我根本不会哭,我的父亲,我的母亲,我根本不会哭。我说,好了,不用再说了。我们来打一架,现在。
把沙发挪到墙边,客厅的空间对两个男人来说还是有点小了,我扎好马步,握起拳头,把腹部尽可能地收紧,尽管还是一团糟。胡胜全站在我的面前,聚精会神,把腿有模有样地叉开,抖着双手随后团紧,拳头似石头一般。
我瞬间有一种假象,他像极了当年的我,站在空旷荒芜的广场上,也像极了当年的她,准备把拳头挥击到我的心里。胡胜全坚定,愤恨,希望母亲可以看到他站在这里的样子,又害怕,胆怯,不足够强大的战胜一切经历的恶,也许他长大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父亲会从汽车内甩出挂在一棵桃树上死去,母亲的骨头生来脆弱不堪,滨海县永远不会像北京南京一样有着铺天盖地的高楼大厦,这里只需要站在一座山上就可以看到整个全貌,1997年6月的电视机还拥有不入眼的屁股和碍事的天线,时间覆盖了一切又催生了一切,高楼在悄然耸立,变化是细微的,人的离开也是,缘分在缓慢散尽。我的母亲已经越来越平静,想必牙齿早就腐化,啃不动几颗桃子,碑底下的盒子外也会有爬虫留蛀,试图咬破外壳,好奇于内部的一把灰烬。我眨了眨眼睛,看到胡倩此刻正坐在墙边的沙发上,我的母亲在厨房里包着水饺,水正烧开,她把第一锅韭菜水饺从盖帘上推进沸水,拿勺子搅匀,她知道胡倩来了,多弄了一些肉馅,电视机无端被打开了,画面模糊而拙劣,泰森很黑,脸上没有皱纹,他空击拳头,霍利菲尔德站在他的对面,他不会想到泰森会用牙齿把他的耳朵咬出血。我们都在安静地等待着,母亲不在乎父亲会不会回来,也不再发出呜咽,她专心把馅子点落在面皮,捏起对角,扭出好看的花。胡倩猛地站起来,惊呼,泰森咬住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泰森咬住了霍利菲尔德的耳朵!那一刻,我们都浑身一紧,像是咬住了自己的命运,什么被提了起来。
我深吸一口气,看着胡胜全,我说,我打赢你,从此,我就是你的父亲。他眉头紧蹙,把拳头挥击而来,眼角划过的还有一颗晶莹的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