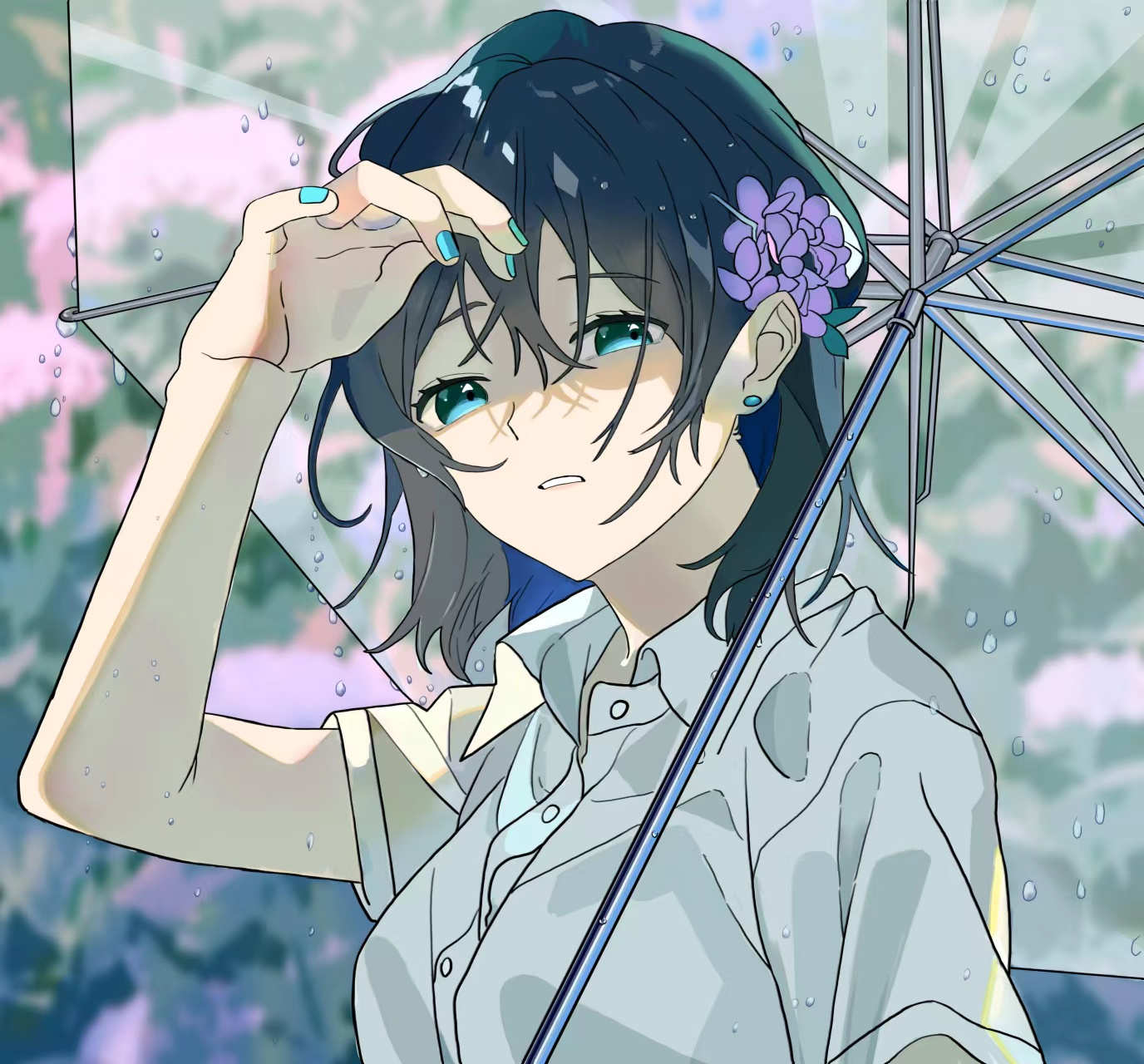“哎,你们有屎吗?有的话,全加到我外卖里去!”
我很小声地说,不想被太多人听见。电话另头的人咳嗽了声,还夹杂着喷溅声,似乎正在喝水。他有些没缓过来,说,你说什么?我再补充说,人屎、狗屎,不管谁的,只要加进去,我给你们双倍的钱。他听明白了,抛下一句,你疯了。我说,我没疯,现在的我比任何时候都要理智得很,你可以弄不?他说,弄不了,你自己去弄吧,神经病。说完,那人便撂了电话。我看了一眼我的投诉,还有好几轮和骑手的通话记录。我捏紧了拳头,走过被人群充斥的街道。算上今天这次,我已经被偷了足足四次外卖。
这四次外卖偷窃,全发生在今年下半学期,二月到四月。其中很大一部分责任,应该由学校承担。他们说,学生不该熬夜,所以十点便熄了灯;学生不该沉迷游戏,所以强制取消了电竞社。这次,他们说,学生不该非健康饮食,所以禁了外卖,校园里再也见不到骑着电瓶的黄色身影,并且让一幢只有三层楼的食堂无时无刻不人满为患,水泄不通。你很难想象,排了二十分钟的队,最后等来一碗干寡的裸土豆丝炒饭是什么感受。但办法总比困难多,自从外卖被禁入校园后,学校的北门成了绝大多数外卖骑手的群聚地。十二点,黄泱泱的头盔在门前仰望,呼喊,并在伸缩门上方完成一次又一次交接传递。然而我更想说的是,越多人存在的地方,就越有小偷的出现,况且北门压根没安装摄像头。
我怀疑这是校方存心如此,目的是想给点外卖的学生一次深刻教训。当头一回价值二十五的牛肉炒饭不翼而飞时,又气又急的我奔去北门的警卫室,找保安一问究竟。那天充斥着冬天最后的干冷,寒风没放过一处裸露在外的皮肤,吹袭着直到发红。我打开警卫室的门,有个小年轻正面对取暖器,一侧坐在椅子上,双腿翘在另一侧的椅子头,惬意地刷着短视频。我说,哥(我也不知道怎么称呼),我外卖被偷了。他第一反应不是回头看我,而是连忙把手机锁屏,脚像弹簧一样缩进自己椅子底下,端正地站起来,拉椅子到我这面,再坐下,说,怎么了?我又说了一遍,我外卖被偷了。
他听清楚了,随便拿起桌上的一支笔,说,什么时候?在哪?我说,就刚刚,十二点。位置在你外面,骑手把它放在玻璃上了。我指着他面前的窗户,经常有些骑手图快或者偷懒,顺手把东西丢在窗户的边沿。骑手给我拍了张照片,就放在那。十二点发的,现在十五,一刻钟之内,东西不见了。他装模作样地在纸上画了几笔,说,好的,我们会处理。我说,我外卖就放在你面前。他说,什么?我把照片给他看,窗户后面还能看见他的头。我说,你有注意到吗?他说,我没有工夫注意你的东西。我说,那调监控吧。他理直气壮地哼唧一声,说,没有。我说为什么没有。他说,学校就是管你们这种学生,不喜欢去食堂,浪费钱,点些垃圾,我见你们见得多了。我说,你怎么说话的。你见我们见得多了,难道就可以对小偷视而不见吗?他又在纸上涂了好几笔,朝我摆摆手,说不想和你吵,回去吧。有消息通知你。
我生气了,这人存心在耍我。我连姓名,电话还没给他,他拿什么通知我,刷视频的手机,还是不顶用的破纸。我说,你现在必须给我解决。他也烦了,嘴巴嘶的一声,眼睛瞥过来,说,找茬是不是,信不信叫人过来,小心我打你辅导员电话。我说,我信,只要能把外卖找来,你把校长叫来我都信。谈话崩裂了,他果真吆喝来门口的帮手,两个身着黑布料,标准保安制式服装,青面差了獠牙的人向我逼来。冷风吹得我哆哆嗦嗦,而那两个却岿然不动。他妈的,三四件大衣裹在他们身上,我呢,还趿拉一双拖鞋,脚趾冻得麻木。
左边一个说,学生,别在这闹事。我说,我外卖被偷了。右边一个插嘴说,没办法,谁叫你点呢。我说,就没人管管吗。左边的摊着手,说,上头叫我们别让送外卖的进来,要是帮你去查,不就和他们对着干嘛?我说,那现在怎么办。他们面面相觑,最后,右边的扔下一句话,说:下次不要点了,丢了你后果自负。他们的意思表达很清楚,管不到现在。我吃了这个亏,打碎也得咽下去。北门边有几棵树,冷风刮得一阵接过一阵,枝头好不容易钻出的绿叶被打在地上。我的外卖就这么不了了之。
第一次发生偷窃之后的半个月里,我在食堂吃的又回归到了清汤寡水的菜式,像以素斋度生的僧人。可它其实卖的不止这些,有鸡排,红烧肉,五光十色地铺在每个摊位,一眼望去应接不暇。前提是我能在下课铃后的五分钟以内,跑过隔壁教室体院的人,再抢先一开始上午就没课的人。不然,我只能望着乌黑一片的人头,然后以手扶膺坐长叹,叹至轮到自己的时候,打饭的阿姨笑眯眯地瞧着我,说嘿,又是你,是不是还要土豆丝加番茄鸡蛋?来,八块。我接过红黄相间的餐盘,吃到一半,倒了。我忍不了了。
日复一日的味道麻木了味蕾,口腔像含着一块石头。我打开美团,点了份爆辣炒面,只希望活动一下迟钝已久的味觉神经就足矣。我挑个没人的位置坐下,食堂人来人往,旁边有好几对情侣还对着喂饭,你一下我一下,沾上口水的筷子在彼此之间的口腔游荡,甜蜜洋洋。没坐下五分钟,我被他们“推搡着”站起来,脸像被人扇过一般滚烫,哪里都像敌对我。要是我也有个人陪着吃饭,何必点个外卖孤独地解决一餐?我走出食堂,天气逃不过冬天的尾巴,空气干凉,硬硬的。
天空阴沉得像关了灯,食堂外面散着迷蒙的光,我背道而行,离光越来越远,经过稀稀朗朗的人群,没过一会儿,眼前出现立着几棵树,和一块禁止通行牌子的北门。骑手打电话过来,说,我到了。我说,你到哪儿了。他说,北门。我说我在啊。他说具体在哪?我说,我就在正门口,我给你拍拍手,听得见吗?啪!啪!啪!他等了几秒,像守着我声音出现,然后茫然地说,没听到啊。门外面,一辆货车呼啸而过。你看到货车了吗?我问。这什么也没有,他答。一下子,我明白了,他根本不在北门。我们一直在错位的世界里隔空交流。你送错位置了,那不是北门,我无奈地说。他也意识到了什么,一口气说了三个等等,我看看。他看到什么了呢?我觉得他看到了一扇小门,铁制的,黑漆涂抹表面,门板还有些镂空的花纹。他一定把外卖钩在了花纹的一撮小弯上。那是南门,和北门截然相反的方向,他错得不能再错。我问,你找到了吗。他在那头沉默许久,只听得见嘈杂的呼麦声,像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地有阵风卷过。渐渐地,风平息下来,他开口了,说找不到了,要不赔吧。
他的确赔了,二十五,十五是炒面钱,多的是封口费。他说自己已经被投诉了三次,如果加上这次,不仅一个月白干,还要卷铺盖走人。我说,别担心,我不会投诉你。他舒了口气,边说谢谢边挂电话。接着,我在投诉理由的一栏写下:连哪个门都分不清楚的家伙,趁早换个工作,别再当骑手祸害别人。于是到毕业之前,我再也没见过这个人跑北门送谁的外卖。有时我会后悔一阵,心想自己做的是不是过了,但忏悔很快被打消下去,其实这和做了爱再戴套一样为时已晚。而那个晚上,我的愤怒胜过了理智,仅此而已。
发生了第二次以后,为了解决屡禁不绝的外卖偷窃,我找了大汪,他我舍友,不怎么去上课,经常在宿舍闲的没事打游戏,中等个,胖身材,睡床上堆的。我扒拉他床边,招呼说,有个活儿给你。他躺着在,翻个身挠几下屁股,懒洋洋地说,干吗?我跟他说了一个计划,擒贼计划,直白浅显。计划内容是:我负责出钱,买外卖,做饵放在伸缩门上,守株待兔,要真有贼心不死的小偷偷东西,大汪就会替我出力,压过去,两个人合并把他逮住。我想得出来的不能再多。他又挠了会儿,说听起来挺简单,没啥问题。
我选大汪没太多理由,一是想找个能镇得住场子的,二是有闲工夫帮我个忙。其他人要么考研要么谈恋爱,没空搭手。他同意了,工资三顿午餐,挑的食堂顶楼,最贵也最好吃的牛排汉堡。我记得很清楚,计划实施的那天星期三,天气依旧一成不变,云朵阴郁得像被泼上几瓶墨水,气温低至沙漠夜晚的寒凉,太阳射下的光线混乱而不规则,我和大汪北门边上的亭子上,仅隔十步之遥便能望见伸缩门。
我点了份肠粉,一小盒装,因为这种大小提带便携,不容易引人注目。假设我是个小偷,首先看上的肯定是它。我们提前五分钟占好位置,定位显示骑手即将送到。大汪捏着手,说,真能抓住他吗?我点点头,笃定地说,能。骑手打电话来,我叫他挂在门上。靠近警卫室边一点,一块白色的小东西耷拉着,像面飘不起来的旗帜。他还给我拍了照片,确定了位置。没错,是它。我们等着面前的空地出现人影,并越来越多。我不敢晃神,视线牢牢盯在塑料袋上面,生怕一眨眼就无影无踪。高矮胖瘦的学生接二连三地出现消失:他们走过来盯着手机,而后接过外卖,再盯手机回去。每个木讷的举动让我感觉,这些人丝毫不担心自己东西会被别人夺走。而一旁,保安仅仅象征性地喊了几句:不要再搞了你们。既单薄又无力的声音投进那些骑手的呼喊声之中,就像被人群碾过的蚂蚁。
他们的无所作为使我愈发不能松懈,时间凝滞下来,被拆成两秒、一秒,一秒内我同时看见四个人有提的动作,三个人回头,一个人往宿舍跑,但没有人动那盒肠粉。所有人的一举一动慢放似地呈现面前,如果说人的潜能会在某刻爆发,那便是此刻。可盯了许久,直到人烟散尽,肠粉依旧完好无损地挂在原地。也许该死的小偷凭直觉嗅到了危险,也许压根没来。总之最后,随着大汪肚子里一声剧烈的咕噜响,擒贼行动以空手而归结束。
我无奈地取下肠粉,大汪倒也不客气,撕开袋子剥起盖,捅双筷子直接开吃。回宿舍的路要不了五分钟,进到楼里,他把盒子一甩,手背擦擦嘴,吃完了。大汪打声饱嗝,说下次还干。他翘着屁股满意地走在我前头,我却看见了一坨耗尽余粮的肥肉。要是小偷迟迟不现真身,大汪说不定真能就着我这块良田坐吃山空。我闭上眼睛,揉了几圈太阳穴,心想接下来计划必须要一步到位,马到成功。
所以我开始每天去北门观察,以小偷的角度思考问题。首先,环境必须适合,人多才有机会下手,这是毋庸置疑的,但一开始,我并没有算进去时间。实际上,双休的北门人是最少的,因为很多学生趁着休息出学校逛街,或者回家,甚至大部分人星期五就溜走了。排除这些,剩下的有星期一至星期四。而星期一,保安不同以往,像打了鸡血一般站在门口值岗,我观察了好几个星期才知道答案,某个校督导每周一中午会路过北门,去后边的公园绿道晃个三圈,呼吸新鲜空气。保安哪怕不想真做也得装装样子,告诉周围人自己在尽职尽责。除非小偷的脑子缺了根筋,否则绝不会在这时候顶风作案。那么只剩二、三、四三天,在经过几番斟酌下,我把日子敲定在距离上次计划过后五周的星期四,因为那天,北门的美食街,有超过一半的饭馆为了庆祝美食街成立三周年,推出大大小小的折扣促销活动。到时不光街上人山人海,外卖订单也会跟着接连不断。
我把整个计划给大汪从头到尾讲了三遍,他也连着吃了三个汉堡,红色的酱汁围满整张肥厚的嘴唇,像涂上一层饱满的唇釉。他嘴巴不断咔嚓咔嚓,发出生菜的咀嚼声,说,你就点一份外卖?我说,怎么了?大汪晃了晃手指说,一份太少了,贼很容易不上钩。我顺着说,依你之见?他灌了几口可乐,缓会儿说,广撒网,多敛鱼。这才是道理。我明白了。所以在二周年庆典当天,我照顾了五家店的生意,花去将近一百。
大汪说,抓贼和我打的游戏一个性质,之前观察的地方太接近北门了,是人是傻子都可以看见我们两个坐亭子鬼鬼祟祟。如果要成功,先不能打草惊蛇才是道理。他吃饱喝足,晃悠身子,从食堂出来带我去亭子边上,弯着眉头瞧我,说,你觉得除了这里,还有哪儿能完整且清楚地看到门口?我观察了一遍,四周空旷无余,看是看得见北门,但同样哪里都可以被小偷发现。我摇头说不知道,他抬起胖乎乎的手臂,指着边上一幢建筑,说,六号宿舍楼,最靠近门口。我们爬到大概三楼四楼,照样还能看到这儿的情况。到时候有小偷出现,一个人在这录屏,另一个下去抓他/她,人证物证俱全。
接着,他领我到了楼里面,在三楼楼梯间的窗户边,我俯视北门,保安室、校园外的车流、零散的树木,一览无余。我惊讶地问大汪,你怎么知道的?他腆着肚子,不在意地说,观察地形,先占高台,CSGO必学的意识。他那语气仿佛不像一个普通大学生,而是隐居山林的一心研究兵法的道人。后来,我才知道,大汪游戏里的段位是老鹰,距离最顶尖的只隔了两个段位。
大汪平常待在电脑前,待的时间比起学习、吃饭、休息多得多。寝室的哥几个聊天的时候,也不见他参与。大汪戴着耳机,不说话,急促地敲击键盘,仿佛把我们当不存在。不过有时他会洗澡,做些个人卫生,至少没变成穴居山洞的野人,散发野兽的腥气。但现在,我对他的印象有了很大改观,不再是一个顶幅眼镜,板着臭脸,一天到晚打游戏的死胖子。一瞬间,“谋士”“堪大用”的词汇闪过脑海。
我提了五个塑料袋,按先前计划好的位置,一个一个放上去。我瞄准了时间,上午十点。街对面,热闹的音乐像礼炮一串一串对准我们喷来,彩球绑着红布条高高飘扬,风吹得它的身姿扭曲滑稽,灰沉的楼房竖起别扭的标牌:速来!这里的店主使出了浑身解数吸引学生。我有一种强烈的预感,在热闹得不真实的街面上,小偷即将出现。
很快,学生越聚越多,到处都是叽叽喳喳的声音,我钻进宿舍楼,站在大汪旁边。准备好了吗?他问。嗯,我肯定地说。他移过头,视线牢牢钩在底下。我左右观望,大气不敢出一声,生怕突然的动静打乱节奏。人群时而像团聚的蜂群,时而又散开像落雁。影影绰绰的人影们接近白色塑料袋,摩擦,贴合,但却完好无损。从左边第三个栅栏,到右边门口,小年轻值岗的地方。五份外卖像水里高高吊起的饵,目光变成了浮标。紧接着,水面起了荡漾。靠近门口左边一个位置的栅栏,我点的牛肉面,经过两个有说有笑的情侣后,不翼而飞了!我大喊,大汪,有鱼上钩。他手机调出照相模式,并拉最大,我们两个凑在镜头看了一眼,果然不见了。他说,你现在下去,我在上面找。
我二话不说跑到楼底,但摩肩接踵的人群将我团团围住。我根本看不清谁手上提的外卖,早知道先在塑料袋上做好标记。他妈的,这让我怎么抓?正当泄气之时,大汪给我打来电话。有个穿白衣服的家伙,正带东西往北门右边跑,体育馆方向,他说。我越过好几个人,踩在侧边的绿化带,一路追向前。到了右边小路,我没看见谁穿白衣服。我没看见他,他人呢?我着急了,问大汪。眼睛眺望栅栏,杆子上面空空如也。有说有笑的人堆中,我狼狈摇头的模样,像一只滑稽的无头苍蝇。
电话那头,我只听见大汪的呼吸声,模糊不清的声音搭扣那家伙的踪迹,一会儿清晰一会儿模糊。你看见了吗?我说。再等等,等等。他似乎屏气凝神,突然,他又大喊,我看见他了!哪里?我说。他转到六号宿舍楼下了!快去,你离他不远,我看得见你,大汪的语气难掩激动。我连忙掉头,冲进人堆,不管有什么擦碰,我铁了心地要抓住他。突然,白色的身影闯入眼帘,是不是他,我说。没错,大汪说。我直接走上前,将他按在地上,周围传来一阵惊呼,纷纷避开,留下一个短小的空间。
他一边用力挣扎一边说,你是谁?快把我松开。我说,当小偷是吧,杂种玩意。他说,你血口喷人,当什么小偷啊我?我的膝盖抵住这人的背,他身上仿佛背负一块巨石,动弹不得,周围很快围满了凑热闹的学生。我说,我外卖呢?他说,什么外卖,我不清楚。我照着头给他一拳,别他妈装傻。他开始大叫,打人啦,有人打人啦,救救我。几个看起来像练体育的学生,来回打量着我,似乎随时出手拦下。小偷不断撒泼,叫着快来人啊!他们真的相信了,一个把住我的手臂,一个擒住肩膀,严肃地说,别动。我说,你们看清楚了,他是小偷,偷我外卖的。擒我肩膀的人眉头一挑,说,你说他偷你外卖,那东西呢?我被扯过去,小偷艰难地爬起来,扭着肩膀,并张开双手,装作无辜地说,你们看,我什么也没有。这人既没有带书包,也没有宽厚的大衣,藏匿赃物对他来说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看你还能找出什么借口,他说,故意尖锐的声调犹如小丑。而那些体育生也不听我解释,顶着一副铁面无私的做派押着我往警卫室走。我心想黑白居然被这家伙硬生生颠倒过来,气不过还想踹两脚,他往后蹦跶几步,边蹦还边说,这家伙不服。
人群外面,有人猛地大喊,快让开。我听出来声音是大汪。他挤进来,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我有证据。他举起播放视频的手机,像举着一把火炬。视频里,一个和他一模一样的白色背影,右手拿着塑料袋,鬼鬼祟祟地挪动步伐,并投进涌动的人潮里。
那几个看完后,哑口无言,并松开我,挪到小偷面前,紧握的拳头准备砸在他身上。我巴不得这些人狠狠揍他一顿,给个十足的教训。但小年轻面目威严,换掉之前慵懒的模样,从人群里探头,说你们闹什么呢,还要打架?都给我进警卫室去!我们被四五个保安带进室内,小年轻一进门便垂下脸色,指着我说,你又想惹什么幺蛾子?我说,我抓了小偷,你们不管偷外卖的,只能我来管。他一把跨坐在椅子上,翘起二郎腿,说,你是学生,还是警察?抓这抓那的,真闲啊你!大汪说,你可以看看视频,我们没说谎。他撇了撇嘴,不理我们,问那几个体育生,你们干嘛来的,和他们一伙儿?他们摇头摇得跟拨浪鼓似的,说刚看见他们在街上打,自己劝架来着,一点儿关系没有。小年轻瞪大眼睛,看着我说,你还敢在街上打?我说,我得要抓住他,不然跑了怎么办?他回头叫体育生离开,已经没你们的事了。然后问站在角落的小偷,他是高个子,身子有种病态的瘦,脸颊两侧隆起颧骨,可一到振振有词的时候,他的颓态荡然无存,鼓起腮帮子争辩,“我没有”“他们诬陷我的”“我不知道”,让我感觉单薄的皮囊马上就会被他撑爆。我说,你到底在抵赖什么,视频里面已经很清楚了。他说,视频里你怎么确定他就是我,今天穿白衣服那么多,那里面只有一个背影,甚至连正脸都看不见,而且,你找到外卖了吗?
小年轻拿过大汪手机,反复拉了几遍,说人太多太乱了,分不清楚哪个跟哪个。我说,那现在怎么办,就这么算了?大汪说,他估计把外卖藏起来了。小年轻横了我们一眼,说,你们真当自己名侦探呢。我说,没人来照顾过这种破事,我费劲心思抓贼,当侦探也是好侦探。他说,省省心吧,没人在乎的。然后,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打纸,潦草写了几笔,并同样朝小偷摆手。我大吃一惊,惊讶的情绪顺着喉管下去没把我差点噎死。
我拦住小偷,说你不许走。小年轻撕下纸,递给了他,对我说,这地方你说了算还是我说了算。我气得鼻孔吐出的气息变得滚烫至极,我想到了一开始丢掉外卖的无奈,南门的骑手,与大汪交易的三个汉堡,还有蹲点,设饵的经费,前前后后所做的努力,现在全被他轻蔑的话语轻而易举地击碎了。我仿佛成了一具被扎了无数破洞的稻草人,冲动止不住地冒出来。我心里再也没有顾忌,按住小年轻的头,把他摔在桌子上,红色的血印没过纯白的纸张,休学通知单的印章,也同样盖在那个位置。
准备回家的那天,只有大汪一个人来送我。他说,你要是忍住没打那个人,其实也不会沦到现在这样。我说,我没办法。他叹了口气,是啊,忍住了也许就不是你了。那个年轻警卫挨打了之后,就被周围人送到附近医院,而且换到其他位置工作。小偷还是被放了出来,因为他一口咬定自己,什么都不知道。我和大汪因为基于错误的判断而冒失采取行动,他也拿了留校察看和通报批评的处分。至于我么,只能一年以后重新再来,父母在老师面前求了大情,好说歹说没把我勒令退学。我到底做了什么呢?思来想去,其实最后什么也没完成。大汪说,我们相处了这么长时间,你要走了,让我请你吃点好的,为你践践行吧。我没拒绝。他弄了份豪华烤鱼,没刺的江团。我们站在北门,警卫室空无一人,他们去开检讨会,我并不清楚内容,但没人看管的感觉挺好。风飘过脸庞,生些暖意。骑手把外卖挂在栅栏上,我过去拿,结果有几个人在我前面抢了过去,顶头的是那个小偷。
他说,听说你要走了。
我说,你很开心吗?
不至于开心,他说,我什么感觉都没有。
我说,那你干什么呢?
他说,待在学校是一件很无聊的事情,无论学习,考试,还是和人交流,我需要一些刺激。
我说,这些话你可以找其他人讲。
他说,我喜欢跟你说真话,因为你要走了,你把我说的传出去都没关系,没人会相信一个休学的坏学生。
我说,你这是什么,犯罪分子的内心独白吗?
他浅笑了一下,你说是那就算是吧。
我说,无所谓了已经。
他说,那我继续讲了。
我站在边上,听他开口。偷窃这种事情,它不像骗,或者抢,也许对受害人来说,就是一次不大不小的消失。不会有傻子为了补齐一点点残缺,就把自己整个身体投进去。他们会说算了,没事的,大不了下次注意,要么重头再来。我偷的外卖,自己一次也没吃过,全分给他们。我就是想看看,有多少人会费心思找回去。一个人没有,有的可能会发在朋友圈发顿牢骚,但真的一个人也没有。我对偷外卖逐渐失去了兴趣,直到看到你做的这些。我很好奇,你图什么呢?就像现在,我可以堂而皇之地夺走你的东西,你也可以打我一顿,不过那样的话,好不容易争来的休学就不可能再是休学了,所以你只能光看着,然后什么都做不了。而且越到后面,你的东西越会被一点点偷走,你也陷入寻找,放弃,重新补齐的循环里,不管多久都是一样,这也许听着很玄乎,但我说的就是必须面对的现实,他摆出无奈的样子撅了撅嘴。
我喉咙似乎卡着一根刺,说不出任何话。
他把那份鱼,放进了另一个人的书包里面,说,你自己拦住了我,却把真正该抓的放跑了,不觉得很搞笑吗?那人就在你身后。我想到了当时按住肩膀不松手的体育生,背后背着一模一样的书包,也许拉链那一角还有块卡住的塑料带子,但谁都没发现,我也好大汪也好。那些人围过来甚至不是出于见义勇为,而是害怕同伙暴露,不得不采取的必要行动。他从包里掏出那份已经馊得像潲水的外卖,放在地上。他打趣地说,现在这叫,物归原主,可我丝毫笑不出来。
他拍了几下肩头,对我说,再见了。
他们走了。大汪看着我,眼神复杂,说他们拿了就拿了,别放进心里。我说,现在没事了。他说,陪你去外面吃一餐吧。我晃晃手说,用不着你破费了。然后,我想到了他们挑衅的眼神,假惺惺的言语,以及幸灾乐祸的表情。我说,这件事不能这么算了。大汪说,可你没办法再弄下去。我说,那最后也要恶心他们。我打了电话,问了一圈外面的店,他们没有屎。我说,这件事靠你完成了,大汪。我走了之后,他们肯定愈发肆无忌惮,但不会有人想,外卖的食物里会动手脚。现在,这是我唯一的报复。大汪点了点头。
一个月之后,他打来电话,说叫我把餐订好。东西弄到手了。我和他还在北门碰面。再次见到时,大汪明显比以前精神许多。他在微信上联系到一个专门整粪便的,兔子的望月砂,麻雀的白丁香,猪的氮磷钾,大汪这次买的,来自大象。
我说,大象里面有啥,他说,他也不清楚,只知道那店家夸,用过的都说好。他提了一个袋子,豁开小口,我伸鼻头过去闻了闻,说不出来的一股草腥味,好像一口气把一整把野芹塞进嘴里。我说,味道那么冲,不会被闻出来吧?他说,弄些味儿大的东西就发现不了,而且就弄一点进去。我想了一下,在麻辣烫那一家下了单,并且塞了特辣。大汪说,一直想问你,为什么执着于装这东西进去,换泻药,芥末不行吗?
我说,道理很简单,因为没人吃过屎。他们顶多会觉得味道小怪,并且心安理得地品尝。你有没有吃过蝉蛹?大汪摇头,说没有。我接着说,我第一次吃并不知道那玩意儿是什么,但是很脆,很爽快,只不过有人提醒我,说这东西是蝉蛹,我才把所有和恶心关联的东西代入进去。如果那个人没有提醒,说不定可以把那碟黄不溜秋的小东西吃完。我想让他们一直记得这回事——有件绝无仅有的东西曾经进入自己的胃袋。
麻辣烫很快送过来,我小心打开包装的结,并启开盖子,将一小坨黄色的东西掺杂进去。那东西晕开在金灿灿的汤汁里,很快沉没了。我重新把它打包装好,并撕掉袋子的标单,一份无名之主的外卖成型了。我点了十份,让大汪摆在学校的每个角落。我相信有的会发霉,有的腐烂,有的被当作垃圾扫走,但肯定有一个,会被哪个贼性大发的人发现。我不相信会这么巧撞到他们的人,然而尝试很多次后,总有一位会中奖。那个人问过我,图的是什么?可答案从来不是拼个你死我活,谁胜谁败,而是那句他把偷窃比喻现实的托词。我厌恶这种说法,即便做一个现实腿上的水蛭,把它盗取的东西再全部吸回去,我也在所不辞。
我和大汪干了两个月,两个月过后,时间到了。我用提前买的QQ小号,往学校的公告墙匿名发了一则消息:如果近期以来,您在校园里捡到一份外卖,请不要捡起,更不要打开食用,该食品里面掺杂大象粪便,若不慎误食,请立刻就医。然后,当天晚上,听大汪告诉我说,辅导员在群里抱怨,学校里有好几十号人请假跑到医院里,有些情况严重的还从医院叫来救护车。我听到这里,内心有种被填满的感觉,但又有种失去堵在嗓子眼里,想说很多话却说不出来。临末了,我只回了大汪一句,谢谢你了。
在那个公告的末尾,我添了一句谁都看不懂的话:我真的要为失去的东西做些什么,即便粉身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