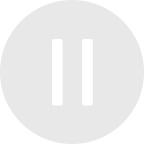1
房子新装潢晾了一个月,才打电话请朋友吃饭,20平的小户型,咬咬牙掏空存款才买下来。
李舒送了一盆吊兰,摆在电脑桌顶凌空的架子上,长长的枝条垂落下来,好似我们上次在苏州园林看见的那盆。
朋友们都说:“Vanessa的房子虽然小,但是装潢却考究得可以当模板”。实则上我是一个庸俗又世故的人,绝对想不出来其他别致的设计。只因为从看房到选材料,陪我的人都是李舒,唯独乔迁时他不在。他飞去米兰,参观一个建筑展览,时差颠倒也早已成为他生活的一部分。
李舒是个设计师,而我更愿意将其称之为艺术家,他是为数不多令我深觉不应该有任何波澜挫折,只该被生活善待的人。
我和他认识在一个共同朋友江米的diy厨房,头次见人将天妇罗搭成塔形,海鲜酱油按之字形淋下去,最后还要摆上萝卜花。他包揽了整餐饭的摆盘,美其名曰是爱好。
我哑然,以为江米请到了米其林三星大厨,可她将我拉到一旁:“是个设计师,有时候觉得你们俩还挺像的,就想介绍你们认识。”
挺像的,又有什么像的?
他连发梢都一丝不苟,白衬衫的袖子细致地挽到手肘,而我全身每个细胞都叫嚣着懒散和毫无规矩。李舒将生活过成了只能束之高阁、唯恐一不留神就会摔碎的艺术品。而生活对我来说,不过一日三餐、一成不变,活着而已。
其实也并非毫无默契。
我说自己世俗,他说自己烟火气。熟络到第一次见面就不必客气,又譬如他讲的笑话我永远都能接住下一句。
江米悄悄拉住我:“他年轻有为,你们又有共同语言,要不要试试?”
我最擅长抱怨,实在是因为工作颠三倒四,日常倒班的黑眼圈如影随形,就算敷上再多面霜和晚安粉也遮掩不掉我的粗糙和苍老。而李舒这样的人,想要的也不过是佳人温婉在侧。
2
后来加上微信,李舒邀请我去他的工作室。设计图稿摞在一起,最上面一张是个小户型装修设计图,他倒也不避讳,直接问我的意见。工作室有着恰如其人的精致,墙角一盆茂盛的绿萝,可以看得出他忙里偷闲的生活。
他带我去了一家茶餐厅,没有网红火烈鸟,也没有适合拍照的灯光,倒是机械元素很像蒸汽时代风格。店主和李舒大约很熟悉,不一会,他便笑着问:“还是那几样吗?”
李舒喜欢喝铁观音,盛在和店铺风格全然不同的杯子里。“要不是他,我还真没见过把自己的杯子寄存在店里的顾客。”店里的装饰有不少是李舒自己设计的,譬如轮盘拼成的凯旋门,当做店主同意他寄放杯子的谢礼。
他没有讲究到令人生厌,却精致得叫我叹为观止。
“其实也算缘分,我在网上请工作室设计店铺,设计师刚好就是李舒。”店主端来我的双皮奶之后,指着铁锈红的桌布,“因为有些细节让他不满意,我们差点在电话里吵起来。”
我觉得有趣,便盘问细节。李舒半是无奈地反驳:“哪里是我斤斤计较。”
从未见过李舒这样近似完美主义的人,他搭配的桌布餐具也要与设计相得益彰。他始终不肯承认自己趋近完美,但更愿意将其归咎于生活的精致。
我甚至不敢带他参观租的单间,因为小小的空间里塞满杂物,从而无法喘息。我曾把生活隔断在那个杂乱无章的单间,得过且过,而工作像周而复始生生不息的轮回,整日苦苦挣扎,已然占据大半精力。
认识久了,他更叫我觉得我自己的生活有多粗糙。
譬如在通宵加班之后,蓬头垢面收到一张清晨霞光万丈的照片,或者收到一盆他自己移栽的绿萝。
我学着拾掇自己,化个淡妆,换上5cm高跟鞋。他出差去利物浦后,我收到他寄来的快递,里面是一条小黑裙,下摆很有设计感,我认出李舒的字迹,他比较擅用钢笔。“第一次设计衣服,总觉得很衬你。”
江米问我如何能放弃原本杂乱无章的生活习惯,“李舒对你的改造很明显嘛。”
李舒的工作清闲吗?也不。遇到苛责的甲方,总会通宵修改设计图稿,又或是接到加急设计单。他给我推荐了很多小物件,三分钟急救面膜、去红血丝眼药水等等。
“你怎么能做到每天不慌不乱?”我难免好奇,终于捉住机会问他。
他好似玩味,歪头凝视着我:“有机会再告诉你,我会挑一个好时机。”
3
如今我终于下定决心掏空积蓄买下这小公寓,转职到较为清闲的部门。从前总是将钱财看得很重,将每日繁琐的生活当做累赘。突然清闲下来之后,才觉得美满无处不在。
而在此之间,李舒和我来了一场短暂的苏州之旅,园林深处评弹声里,他给我斟了一碗茶:“如果你每天都过得很有仪式感,就不会觉得慌慌张张,不知所措。”
一生这样长,总会遇到一个人教会你如何爱上生活。若有人问及,你看重的是那个人还是生活。我必要认真的回答:“是因他而学着爱上生活。”
生活总是需要一点仪式感,而后慢慢温习,将之变作习惯,融于骨肉,方知真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