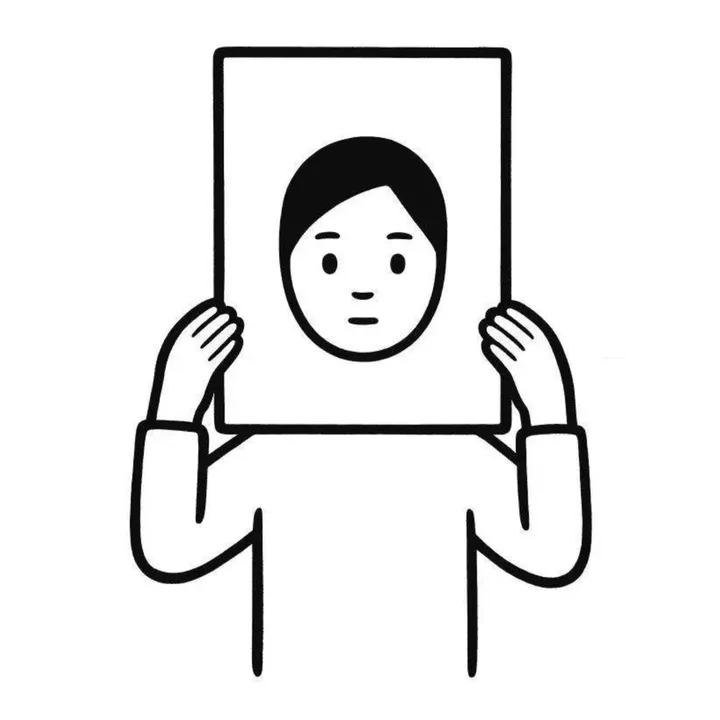一位中年父亲在看似完满的家庭生活与职场规训下,内心渐生疏离与空洞。深夜湖边独自抽烟,是他唯一确认自我存在的私人时刻。一位冬夜野泳的神秘女人闯入他的视线。
1
他出门时,妻还在睡,儿子也是。近来总觉得一张床睡不下了,儿子在肉眼可见地长大,他不得不让位,往床的边角去,侧头看,妻儿离自己都远,鼾声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尤其在黑夜里,他模糊觉得自己在瀑布的下游,哗啦啦的呼噜是无休止的流水,冲刷他老旧冰凉的身体。而儿子越来越像一个汉堡,那种庞大的,挤压的,随时外溢流出汁水的肉球。这不代表他不爱。他爱他们,重复的每一日里都是。
动作轻柔,他向来谨慎小心,不愿吵醒和打扰,但自己又生出烟瘾,每每这个时刻便换上外衣,塞进一把钥匙,轻声把门闭上,去走廊按电梯。电梯像一直在等他,白色指示灯始终是17层,似乎在肯定他的出走,算出走吗?他已经把烟叼在嘴唇上,等下了楼便按动打火机。也没什么不同的,十几分钟而已,他可以拿出这十几分钟仅仅用来面对自己,此刻无人指摘,无须与他人对话,不用考虑应变,哪怕打火机一次没有燃起,还可以按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无比轻松。他深深吸一口气,随着电梯失重的瞬间又缓缓吐出,把自己想象成太空任务执行者,正在等待出舱。轰隆隆,电梯停稳,他迈出去,往楼门口走。蹭,蹭。火机把烟点燃,脚步声叩亮声控灯。四下无人,但已有寒风钻进大厅,他裹紧外套的领口,咳出的烟雾盖在了脸上。
2
儿子家长会他去的,上周五晚上,女老师看着很年轻,穿着高领毛衣,头发齐肩。具体说了什么,他没记,同桌男家长在桌洞里打手机麻将,他靠在小小的座椅上瞄了几眼,六筒八万三条四饼。他比儿子瘦,他质疑儿子坐这里能否舒坦,前后伸不开腿,左右张不开身,尽管儿子才八岁,既然他来了,总该质疑点什么,而不只是一味地听。他突然和女老师对视,听到她讲语文考试里的看图写话,他在想,不知道这么年轻的女性有没有一个儿子,在他的理解里,年轻是不该有孩子的,那会蓦然增大自我的年龄,尤其对女性。妻怀孕时他还记得,身体开始变形,每天惴惴不安,吃饭会吐,走路像老年人,妊娠斑往脸上爬。有时候会自责,生命的代价太大,他也是始作俑者。女老师肯定没有孩子,她漂亮极了,客观,优雅,平等地陈述事实,不给予同情,按照名单把班上的同学们都评价了一遍。没什么特别的。他歪头看桌洞里的手机屏幕,男家长正在自摸,难以抑制自己的兴奋,上下踮动脚后跟。前面的女家长头发过长,时不时甩动,发梢掠过桌面,他闻到一股呛人的香水味,幻想持有一把剪刀,食指和拇指穿过孔洞,从下往上,一刀刀下去,一段段掉落。
3
马路对面有一山野公园,当初与妻买房也是看中环境,空气好,天然氧吧,还属于学区,但晚上也格外冷,温度同比降低有三四度。公园中心有片野湖,这个季节属于初冬,还不至于上冻。他习惯在湖边转,把烟头扔进湖里,看着星火漂在水面上,慢慢熄灭然后融进黑暗。月光浓的时候,湖面闪着银光,像仍处在白日里似的,有种时光的错置感,仿佛自己抢跑了,赶着要去追什么。这个时段里,他不刻意去想,就是走路,走路,走到手头的烟抽完了才琢磨往回去。不管多久回去,她们还在睡,呼噜声还在,一切并未改变,一切从未发生。儿子应该自己单独睡了,两室一厅的其中一室堆满了杂物,收拾出来给儿子,摆上一张单人床和一张书桌,这样也能分辨到底是谁在打呼噜。也许妻不会同意,他总感觉妻与儿子的感情越来越特殊,谁也离不开谁,谁也不放谁走。她们越是如此,他便越觉得远,不过生理上难道不就是这样吗,孩子在母亲体内十个月,她们一体,共用一切,跳动一切,不离不弃,而他自己,才像个外人。
远处湖面裂了个口子。他停下脚步看。波纹层层叠叠推涌过来,圈中心有个影子,在水面进进出出,上上下下。他继续看。想到落水,想到挣扎。他不确定那是个人影,可能是狗,是猫,是某种动物,距离较远,今夜月亮藏在了云后,使得水面死气沉沉,原本是一片黑的凝滞,这会儿好像整个湖在搅动,在震颤。他眯起眼,看清了,是人在游泳,在朝他划动手臂。
4
儿子生产前,妻肚子大得离谱,他将耳朵贴在肚脐上,除了能听到微弱的心跳,还能感到被小手或小脚推动。皮肤下的动作有些恐怖,妻说,这是我们的儿子。那时已经找朋友看过性别。妻说,他很有劲儿。她沉浸在期待的幸福里,他陪她置办婴儿床,床上的风铃,选奶粉的品牌,冲奶器,尿不湿。他的期待并没有什么不一样,想象过儿子的样貌,他加上她的,怎么也生不怪,端端正正,就小孩子模样。实际生了也是,儿子皱巴巴的脸慢慢舒展,一阵儿像他,一阵儿又像妻。微小的翻版,两人生命体的集合与重塑。婴儿床没有派上用场,妻一直搂着,小婴儿躲在胳肢窝里像蚌里的珍珠。有天夜里,原本他们都睡着了,儿子突然醒了,身子开始挪晃,挤着双眼睁开,发出低沉的悲鸣。他看着仍在熟睡的妻,并没有叫醒她,而是起身轻巧地把儿子掏在怀里。他抱着身为婴孩的儿子在客厅围着沙发转圈,就像如今围着湖一样。儿子抽噎着,喉咙吐出的气是奶甜的,他轻轻拍着他的身子,如海盗船般起伏摇摆。这是他的儿子,这切实的接触和渐大的哭声让他恍惚,有种儿子是突然出现的错觉,他需要再认真一点对待,拿出这辈子从来没有过的认真。这是爱,是责任,是基因,是人类共同的命运。
他并不知道尿不湿里已经坠满了排泄物,依旧想着白天里学会的儿歌,一遍遍念,一遍遍唱,试图用娃娃国和娃娃兵消解哭声。
5
不需要营救,也没有危险,上岸后才看清是个女人,穿着竞速泳衣,湖水从身上泄下来。女人摘下泳帽,湿发散在肩膀。他把烟头扔在原地,用鞋底碾灭。女人往他身后走,去长凳拿起浴巾擦拭身子。他看了眼手机,凌晨一点过五分,身后公园长凳上有几件衣物和一个长方形的包。他哈了口气,能看到白雾,又不自觉地缩紧身体。他冷,看到女人后便更冷了,女人毫不避讳,低头把头发捋顺,浴巾沿着脖子往下一块块抹干,在大小腿上打圈。过后才把长风衣裹在身上,浴巾塞入包里,双脚踩进靴子,正要走时,好像才注意到他。其实早就注意到他,但是女人不慌不忙,也不怕,反而让他觉得奇怪。大半夜里一个人往湖里钻,这湖不适合游泳,晚上看不出来,白天能见水里的藻类纠缠在一起,稍不注意就会勾住双脚,怎么用力都蹬不开。他听说过那起溺水,一个老头阴天傍晚扎了猛子下去,没再上来,等天气晴朗时才被人发现一直悬于水中,像在琥珀里的虫。
他看着女人拎起包往马路边走,那里停着一辆黑色越野车。她上了车,车灯亮起,车窗玻璃落下来,女人看了他一眼。他确定女人看了他一眼,然后车子才沿街开走了。
6
他与妻说起来,妻问他怎么知道的,他才想到她根本不知道他半夜出去抽烟的事儿。他解释说听邻居讲的,大半夜回小区看到有个女人在湖里洗澡,搞不好是鬼。妻是坚定唯物主义,在高校教马哲,完全不信这一套。她说,喝多了吧。他说,没喝酒。妻听得莫名其妙,他也答得莫名其妙。儿子放学回来,他们要陪他写作业,还要陪他玩耍,他总觉得儿子身体长得比脑袋快,总觉得他不成比例,尤其是当他单独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儿子单纯的目光总让他有一种无限的担忧,怕他永远停留在这个时刻,无限索取他和妻所拥有的一切。儿子说,爸爸,陪我玩。他看着他粗壮的小臂,手里拿着奥特曼动画片里丑陋的怪兽,他们将在沙发和床上上演一场大战,儿子会把怪兽扔得老高,再远远丢出去,口中振振有词,宇宙,拯救,光线,泰罗,雷欧,阿斯特拉。玩到后面,他只是听着,手里捏着不知道名字的奥特曼人偶,陪着儿子在客厅走来走去。等儿子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后,他才放下人偶回到卧室,又听到妻在和朋友打电话,她有一个北京的闺蜜,正在经历一场严肃的情感危机,妻劝她说早该要一个孩子了,那是解药,身体的和情感的。他退出卧室,却又不知该往何处去,热烈,吵闹,家像蒸锅,到处都是开水,是滚烫,是一个接一个看似坚实的气泡。
7
他上了女人的越野车,双方都不诧异。开始他坐后座,像个打出租车的人。女人让他坐副驾驶来,他乖乖听话,坐下后立即系上安全带,头也没歪。他不敢看她,她还是刚游完泳,上身披了件棉衣,敞着怀,下身套进一条睡裤里。车里暖风开了一阵儿了,他觉得热。女人身上还湿漉漉的,有一种湖的味道,白天他刻意去看了,水里有鱼和蛙,还有塑料瓶子和断掉的线。车子沿着马路往远处开,他们都没话。女人调整着内视镜,照着把头发捋到耳后。深夜的街道上没有车和人,路灯安静地发光,他们像在滑行,听不到一点引擎声,车速不快,女人让他帮忙从后座拿条干毛巾,他递给她。她双手离开方向盘,又一次用毛巾揉搓头发,然后擦了擦锁骨把毛巾搭在脖子上。他看着前面的路,又想到熟睡的妻儿,这是相反的方向,她们还在打呼噜,仍旧未知,像每一天的每夜一样。
湖里不好游,去年夏天有个老头溺死了,南北都竖了牌子,禁止野泳,他说,说话时还是看着前面的马路。十字路口到了,他们在等红绿灯,还是没有行人和车,灯绿后,女人打了左转向灯,车子绕到山野公园的西侧马路,径直向前开去。
8
下午他处理了几份文件,觉得头疼,跟没睡好有很大关系,领导说到处都是错字,他重新拿回来修改。他干的就是这活,文字雕琢细致,有时候比机器更像机器,从未出过差错,AI都比不过他。可最近觉得疲倦,对待文字有奇特的观感,黑色的字像密密麻麻的小飞虫,它们乱窜,鼠标这条鞭子控不住它们。他反复倒水,反复喝水,多次去卫生间,排尿,洗手,洗脸。他想起女人在车上说的话,大多数中年男人,都如死了一般。他反驳了,当下就觉得生气,好像女人在指责他,大多数,这个极大的限定词他没听到,只觉得他在被概括,被定义,他说他生活顺遂,虽然挣得不多,但幸福稳定,妻儿从不失眠,每个夜里总能酣睡,呼噜声就是活着的证据,就是活好的证据,他在其中是至关重要的一环,是呼噜声的发动机,是船桨,是机翼。
可生活哪里出了岔子,他掬了口自来水,猛地喝下去,冰凉甘甜。妻说,自来水不能喝,除非装净化器,那里面有细菌,有游虫,有看不见的肚子疼。儿子望着水柱发呆,一碰不碰。他跟他说,只要不喝,洗脸洗手都可以的。儿子还是不动,他过于听话,过于愚蠢。他的幸福就是如此,过于听话,过于稳定,过于一种永不超限的过于。他咕咚咚喝水,把嘴伸到水龙头下,仿佛自己变成了水龙头,尽可能把胃灌成湖。
9
女人还在游泳。他坐在长凳上帮她整理衣物,今夜她带了一条长长的毛毯,厚实的羽绒服,换新的黑色内衣。内衣他不怎么敢碰,草草将它们叠好,便开始抽烟。温度降了不少,湖面有些冰碴,再过一阵儿,整个北方将有大幅度降温,到那时整个湖都会冻得死死的,去年就是这样,钓鱼的人往湖面钻洞,整个下午都凿不开。他看着女人往远处游,像一条不知疲倦的黑色大鱼,月光浇在她的身上,每洒一下,都好似刺她肌肤,她便潜入水中,忽再一跃而上。他静静看着,银河如七彩乱石沿天际铺开,他不应该能看到银河的,这里仍旧光污染严重,天上一片暗红,但他确实看到了,像掉进一个梦里,梦里没有多余的奢望,只有看,只有等待。
女人抱着身子从水里走出来,他拿着毛毯迎上去。你游不了几天了,下周降温,湖面又得上冻,他补充说,不过你可以白天来,中午。女人照例擦着身子。我是说,中午阳光充足,即使降温,水面也许可以敲开,我可以试试,他说。等女人擦完身子,他拎起包,他们往越野车走。上了车,女人坐在副驾,开始用干毛巾擦头发,他发动引擎,踩下油门。这款车他没开过,家里是一辆轿车,开了将近十年,座椅越来越凹陷,每次看路都要挺直身子。这个不用,他在路口同样左拐,车子开始绕山。
10
他和妻是介绍的,算是门当户对,上了年龄才知道自己上了年龄,镜子面前一照,沟沟壑壑不知道什么时候生的。结婚时也是,不管怎么化妆,他们都跟漂亮不挂钩。记得化妆师把粉使劲扑,他说他是男的,不太在乎这个,但心里也在嘀咕,二十和三十差了多少,大学时他在校舞台上参加演讲比赛,女孩给他正衣领,眼神都是爱慕。后来更是,说垮就垮了,头发也变得稀少,儿子调侃道,我的秃头爸爸和英语课本上一样。粉扑到嘴里,他喊停化妆师,妻笑着过来安慰,他看到她眼角的细纹,像刀刻的。所有的掩饰都是虚伪的,他们不再年轻,他拒绝化妆,用湿巾擦了把脸上了台,聚光灯灼热地杀过来,他热泪盈眶,什么都看不清楚,妻说爱,他说爱。他好像没有选择,又不想装作自怨自艾,他接受,是心甘情愿接受,所有人都是这么过来的,正如女人所说,大多数都是这么过来的。掌声响起来时,妻把他拥在怀里,誓言被捂热,开始发酵,他的儿子也注定要在那一刻生长,子弹随着酒席结束射出,所有都只能是一条直线,没有弯曲的可能,再也没有。
人们退场时也埋下诅咒,幸福的定义是只在幸福之内定义,因此得到的没有例外。那天夜里他们忙到凌晨三点,收拾酒品,家中杂物,梳理款项,最后躺在床上连做爱的心情也没有了,他睡了一个冗长的梦,梦到自己的葬礼同样热闹,同样繁琐,同样程序,妻在梦里问他,这一生活得快不快乐,他想表达,却被逻辑限制,死掉的人无法说话。
11
绕山野公园三圈,大概花费三十五分钟,后来他油门踩得浅,时间拖到四十到五十分钟。担心女人游泳感冒,他从家里出门时会带上儿子的保温杯,杯身画着疯狂动物城的狐狸尼克。女人第一次看到,他就说了,我儿子不用了,家里只有这一个保温杯,我和妻都不用的,冬泳不保暖会感冒。女人说他贴心。他说没什么,只是强调杯子反复洗过。女人不嫌弃,上车后总会喝一杯暖暖身子。他没问过她为什么深夜要在湖里野泳。女人也不说。两人不是绑定关系,但好像心知肚明,彼此的需要有时候会越界,每当这时,男人就选择下车,把钥匙交还给女人,独自走路回去。第一次上车时,像开门进一家咖啡店一样简单,他们把车窗落下来抽烟,谁也不打扰谁,车子转了一圈,停下时他想起溺水案。他是想劝她别游了,水草不长眼睛,但又怕她别游了,一旦习惯了就退不回去了。
他也担心过,妻会起夜,发现他不在家会问,以前他临时去单位加班,也是夜里走的,妻会要求语音,视频,她说她怕,她一个人。那是以前了,很久以前了。
12
爸爸认识了一个人,夜里在这湖里游泳,每次天黑透了就来,左右几个回合,也不怕冷,他跟儿子说。儿子看着湖面,嘴里吃着糖葫芦,使劲咬其中的一个山楂圆球蛋儿,说,爸爸,我不想吃这种的,我要吃扁的,我妈都是买扁的。他说好。他拉着儿子的手去公园门口又买了一串扁糖葫芦,儿子吃着往湖边跑,他在后面跟着。他说,爸爸白天没见过她,也不知道她是干什么的,住在哪里,每天夜里她都来,不是一点就是两点,你和妈都睡了,偏偏最冷的时候,可她不怕冷,车里就换好了泳衣,披着外套就往水里走,开始我也怕,以为真的是什么冤鬼,可鬼有那么漂亮吗,脱下外套,她还在打抖,是个活生生的人,却偏偏要往最冷处去,你说水里有什么?儿子回头看看他,说,鱼。他朝着儿子手指的方向看,一条白色的鲤鱼猛然回头,扭着尾鳍。他继续说,像某种生活习惯,像跑步,像打牌,像抽烟,像你吃糖葫芦和玩奥特曼,总要找件事做,是这样吗?儿子说,爸爸,你尝尝扁的,扁的可甜。他接过糖葫芦,舌头贴在糖衣上,牙齿咬碎山楂,他感到了甜,腻,有什么融化在嘴里。他把糖葫芦递给儿子,说,你吃吧。
儿子跑到湖边,他还没来得及说小心,就听到儿子喊,爸爸,结冰了,湖结冰了。
13
女人站在湖心,依旧穿着黑色泳衣。今夜无月,远处看,她格外高,像个迷路的巨人。说了不信,全冻住了,你快回来吧,他喊。又在心里嘀咕,再不回来,把你冻成冰雕。女人原地跺脚,湖面纹丝不动,她又蹲下来看冰,找来湖面上的石头,试图敲打。他没办法,同样往湖心走。下了湖滩,就能感到刺骨的冰凉,巨大的冰面升腾着寒气,他连打了几个喷嚏。脚底下比岸上还坚实,他估测有三四厘米,手伸不出来,手指僵硬,从指尖开始疼。
险些滑倒,他把衣服裹在女人身上,拽她往岸上走。他们走得很慢,过了许久,却感觉仍在原地。他终于问了,为什么要在半夜里游泳,冬天太冷了。女人停下,打着寒战,问他,你要管我了吗?他没别的意思,手机显示零下八度,出门时就在犹豫,他也怕冷,都知道湖面已经像水泥,为何还要往里走。他说,白天,中午,湖南面有个裂口,钓鱼的人凿的,你可以去那里洗澡。女人又问,你觉得我在洗澡吗?他说,其实,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女人裹紧身子,呼了几口气。他看到她脸上冻得煞白,想把棉帽给她。女人说,你又是在干什么。他仔细想了想这句话。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他已经把抽烟换成了陪女人野泳,女人他不认识,不熟,也没有了解的必要,天暗下来,所有的事物都缠上了黑茧,有自由在里面产卵,他变得失控,大胆。
14
妻只是问他,都在我们睡后吗?他模糊回答,嗯,透透气。妻又问,每天吗?他说,不会,有时候睡不着,心情不好。妻再问,心情不好了吗?
对话太陌生了。他看她的眼睛,里面混混沌沌,他拿来和女人对比,其实没法对比的,女人的眼睛他也没盯着看过,好像他眼中从来只有自己。妻说,你其实可以跟我说说。她用了其实两个字,好像他有什么已经隐瞒很久了,他该如何坦白,那天他跟儿子说过了,一个野泳的人而已,从这头到那头,他只是看。他从小不会游泳,没人教,长大了去过一次泳池,和妻和儿子,她们穿着游泳圈在水面上浮着,他在玩手机,儿子调皮,偷偷上岸,绕到他身后,推他下去。入水时他觉得自己死了,恐惧让他立刻凝固,一点挣扎也没有,他怕水,怕突如其来的推,拖,拽,赶。
他说,没有,烟瘾上来了而已。妻说,那以后要不要在家里抽烟?他说,不好,我尽量戒。妻说,不是那个意思。他说,接孩子的时候我看到很多爸爸抽烟,一手拎着孩子一手吸烟。妻说,我们不是在说这个。他说,爸爸不应该吸烟。妻说,你有没有在听。他说,我知道你在说什么。妻说,我没有要管你。他说,因为我们年龄大了吗,这些数字都像梯子,要么你,越爬越高,要么我,越爬越远。妻说,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最后说,我知道。
15
越野车没有在十字路口左拐,山野公园下起雪,湖面上都是白霜。他抽完第一支烟,车子就来了,女人没下车,招呼他上来,也没有穿泳衣,但依旧是一身黑,高领毛衣,头发盘在脑后,把自己捂得严严实实。他还是像第一次一样坐了副驾驶。他说,下雪了,真冷。挡风玻璃的雨刮器每隔十几秒便左右摇摆一次。路口等红绿灯时,他发现车子占错了道,但没问。他将车窗开了一个小缝,这样烟可以透出去,但有雪会飘进来。他指了指窗户,说,没事吧?女人说,你会游泳吗?他说,不会,没试过。女人说,你想试试吗?他说,湖面还得冻一阵儿,年后可能才化。女人说,你想试试吗?他说,可能冬天的缘故,水草也少,没见你被缠住手脚,夏天那个老头挺惨。女人说,你想试试吗?她连续问了三遍。绿灯亮了,车子继续向前行驶,那片区域他不怎么去,工作和学校都在身后,直到油门轰响,车子猛然加速,他手指夹紧香烟。轮胎与地面摩擦像哭,他想到儿子尿床,儿子被人欺负,儿子掉入湖中。他说,如果我儿子溺水,我会试试的。女人拐动方向盘,转了个急弯,车子掉头回来。女人说,我喜欢野泳,尤其在夜里,身子冻得发抖,入水后就不会了,浑身都是暖的,像有人抱着。女人继续说,一旦喜欢就放不下了,可有些事,没有一旦。他没听,脑子里在想妻,如果妻也掉进湖里,他也会跳下去,他又想到,其实不用,妻会游泳。
16
雪如预测的一样,连续下了一周,妻和儿子都停课了,他在单位待了两天,也被撵回来,随着大雪,都停摆了。马路上的雪越来越厚,半夜不再肃静,铲雪机在那时候工作,把路面推个来回,可一夜以后雪又盖上一层,只得来夜再推。他们都不出门,湖也没再去过,在他的想象里,湖水从上到下都冻得结实,哪怕是鱼,都早死透了。烟戒不了,半夜下楼走出几米,被风雪推着回来,也抽不上几口。三个人都在屋里,儿子抱着平板趴在床上,妻把抽油烟机开到最大,他弯腰收拾一地的玩具。喧闹间,他把儿子叫来,问,这是什么时候买的?儿子看着他手里拿起的一个巴掌大的人偶玩具,蓝色的,两条胳膊一前一后,趴着,背上有一个发条,一个游泳的人。儿子说,洗澡玩的啊,早忘了。他不记得他买过。儿子抢过来,用力拧发条,说,这样玩。玩具小人的胳膊前后打圈,头也会跟着摆动。他接到手里,在掌心看,等小人泄力后陷入静止,一动不动。妻在厨房喊,干吗呢,准备吃饭。儿子咚咚跑过去,说,爸爸在收拾玩具。他把玩具小人塞进裤子口袋,大声说,来了。
17
妻没有空,寒假前的家长会还是他去的,座位依旧狭窄,女老师说了说成绩,儿子的成绩在他们的辅导下名列前茅,得到了表扬。点到儿子的名字时,他还站了起来,感谢了老师,又强调大部分是妻的功劳。随后女老师谈到安全,假期不让去江河湖海玩耍,更不能游泳。同桌的男家长嚼着口香糖说,哪有大冬天游泳的。他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对他说的,但他回道,有人喜欢冬泳,看的人冷,游的人不冷。同桌的男家长没有理他。
雪早就化了,太阳晒了一周,看不出一点雪的痕迹。家长会结束后,他没有立即回家,而是去了山野公园。尽管中午,公园还是很冷,没什么人来,踩上湖滩,冰面仍旧结实,可以支撑他往里走。于是他就走,到了湖心,拿出刚才从后备厢掏出的锤子,用尖的那头,照着冰面使劲,冰碴溅他一脸。比想象得容易,没一会儿,湖面被锤子凿出个洞,他继续用力剜,大冰块开始晃,水纹在底下缓缓流动。最终,他破出一小片湖,然后拿出家长会期间一直在口袋里把玩的小人。他把小人拧满发条,捏紧两只胳膊,投入湖中。小人摆动双臂,前后撩起水波,在小湖转圈。他把手抄进兜里,哈着气。正午的阳光刺眼,他抬头看,眼底被映得血红。再低头时,小人浮在水面,慢慢浸水,缓缓下沉。他捞起它,又一次拧紧发条,扔进水中。这一次,他学着小人的模样,隔空摆臂,想象着出水,入水,再出水。冷。他只有冷。玩具小人沉入湖底。
18
野泳是有瘾的,我还会找片湖,不上冻的湖,女人说。他看了看手机,说,整个北方都在上冻。女人说,那我就去南方。他说,给你这个,不知道南方用不用得到。女人接过保温杯。他想了想说,欢迎回来。女人问,回来又怎么样?他说,你不在时我也会去湖边抽烟,有时候觉得自己就是那片湖,夏天布满落叶,冬天晶莹剔透,但不管怎么变,都是水,里面有万物,就成一个世界。女人说,所以是我打扰了你。他说,你在湖里我认识你,除此之外,我什么都不知道。女人说,你以为你是湖,可你连湖水都没碰过。
车子重新停到山野公园门口。他从车上下来,女人也下来,两人倚着车身抽烟。女人说,说说那个老头。他清了清嗓子,说,一个夏天傍晚,老人拎着一个藏蓝色的包,把衣物脱在长凳上,从湖滩滑进水里,看上去像失足,但其实他游了好多年,他游到湖心便潜入水里,然后一直没有出来。周围没有人,天上很快下起了小雨,老人挣扎着,但出不了水,双脚被缠得死死的,是水草,从水底看,雨滴像在写字,他的呼喊都变成了字,字写得再多,没有人看到就没有人知晓,等第二天雨停了,他才被人发现。女人说,老人早就做好了准备,他傍晚一个人来到湖边,下水时一丝不挂,就好像出生那天,水什么时候都是暖的,老人游到湖心,把一只脚伸到水底,那不是水草,是所有经历过的日子在拽着他,他没有反抗,他尽力配合,把那想象成母亲的手。
他们笑了。女人重新上了越野车,她打开车窗看着他。他想起第一次的对视,依旧陌生,依旧好奇。女人说,谁也不知道真相,除非你跳进水里。他伸手往兜里摸烟,烟没了。他说,我抽完了,该回去了。女人说,那就这样。他说,好,再见。越野车闭了车窗,他看着车子从缓慢到疾驰,消失在马路尽头。
往回走时,他感觉脖子突然凉凉的,抬头看,天上飘起冰晶。他掏出手机,据天气预报显示,接下来的一周,冰冻,极寒,将持续下雪,那时他还不知道一切即将停摆,女人永远不会再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