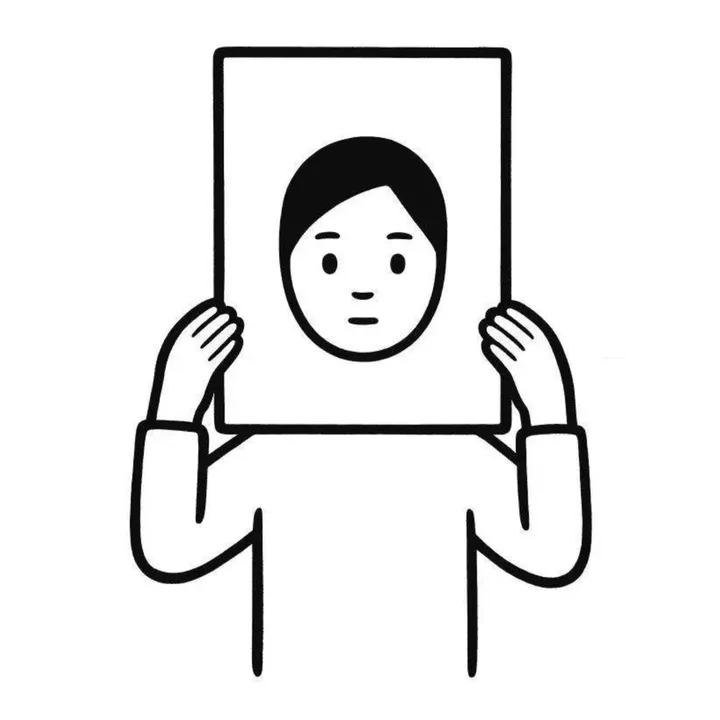这是一篇以九十年代单位分房为背景的怀旧文,通过一个孩子的视角,细腻勾勒出大院里的人情冷暖与时代变迁。“裂缝”既是楼体质量的缺陷,是雨水侵袭的通道,也悄然成为了人与人之间相互理解、相互依靠的缝隙。
九四年建成,单位分房,按资历评分排高低,根据排名再选楼层。每套一样,老三室,一层两户,七十五平方米。职位极高的似乎家里人多,三室不够住,因此要夺对门一间,便住上四室。对门是小王小李,面积削掉十几平,住两室,勉强登得上资格排行榜,幸福感大于一切,不会挑三拣四。
阳光在楼间夹缝里相当充足,晒得院墙暖烘烘的,搬家那天格外兴奋,两个地排车满满当当,家电家具陈旧,轮子每转一圈,都有浮尘抖落在马路上。我背着书包跟在地排车后面,几乎小跑,背包不觉得沉,里面是课本和四驱车。我爸满头大汗,还在抱怨前一天被我妈卖掉的书,整整两个麻袋。我妈同样拉着另一架地排车,不言语,在她心里,书是最无用的东西,能当废品卖已经不错了。我爸的反抗无用,沉默和暗藏的不满总像输液的点滴一样灌进他的血肉里。他们怎么走到一起的,一直是个谜,我时常思考生活的形状,没有答案,只能得出的结论是,我大概就是这奇形怪状的谜底。
整栋建筑三个单元,坐北朝南,南北通透,南面是岱庙,北面是泰山,楼下有个大院,长满荒草,暂时无人打理。人们都忙着入住,前期装修的建筑垃圾还撇在大院一角,风一来,灰尘洋洋洒洒,在院子里打转。我爸资格够老,可以住标准三室,听人建议选了五楼,视野好,南北都没遮挡物,虽然十几年后南北均盖起高楼。当时还是令人满意,家里人口多,加上我姐我爷,五个人也住不开,我妈问四室的条件,被我爸驳回,幸福感可以自己建立,不用再麻烦领导。因此每人分得的空间极小,那时候并不觉得不妥,没有独立房间,小孩就像皮球,可以弹来弹去,和爸妈睡一张床,和爷爷睡一张床,也都不觉得拥挤,相反每到饭点,五个人簇拥在客厅一张圆桌上,幸福感是爆棚的,小孩的眼里没有别的,饭碗是满的,筷子碰盘子,叮叮当当的,每个人嘴角都像有饭粒,是粘在嘴巴上的小喇叭,说话声音都洪亮,随便都有回应。电视机是大背头的,厚重的脑袋里装着千奇百怪的事,新闻联播后永远是天气预报,预报员拿着小杆子,指着会动的电子荧屏,我们屏气凝神,似乎在和未来交融,但关心天气总大于关心自己的命运。
客厅很小,大部分空间都分给了卧室,尽管这样卧室也不大。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我爸找人在客厅整面墙上按了张镜子,推门进家会看到自己推门进家,整个空间被纵深拉长,十五的客厅变成三十,空间折叠的技术很奏效,灯光一亮,感觉家里富丽堂皇。所有人都很满意,我姐穿着裙子在镜子前跳舞,我妈化妆,我爸抽烟,烟雾都是双层升降,我爷对着镜子戴帽子,整理自己的八角帽檐。镜子外面一家人,镜子里面一家人,有时候会产生错觉,在学校上课时会琢磨家里的我在干什么,他会不会偷偷穿过那面镜子在家里捣乱,偷我的玩具,穿我的衣服。还有另外的爸爸妈妈,生活像被切割开,也是第一次感受到被切割,被复制,独一无二并不是真的独一无二,群像才是真相,五个人变十个,十个变二十个,一层两户变两层四户,两层四户变四层八户,再变整栋楼,塞满了所有时光荏苒的无所事事。
六楼没人选,我家楼上一直空着,我上去过好几次,两扇对户门闭着,都是两层,那个年代是这样,一层绿色的镂空防盗门,一层木门,镂空防盗门铁栏扭曲成花朵状,故意设计,还有一张纱网防蚊。我尝试过几次,两扇门都打不开,但随着时间推移,铁门渐渐掉色,锁也变得陈旧不堪,纱网发硬变脆,手指头就可以戳破,然后从锁孔上方的纱网漏洞穿手进去反开,第一层防盗门就破了。接下来是第二层木门,木门只有一个锁孔,我想过很多办法,用自家钥匙能插进去,但拧不动,用铁丝能插进去,可以转动,但没有作用。也忘了为什么要进攻这两道门,其实房间格局和我家是一样的,没什么可看的,但自从打开第一层防盗门后,每天放学我都会上来蹲在门口待上半个小时,研究破门的诀窍,仿佛里面有什么宝物,做梦也会想到一箱箱的财宝,一扇机器猫的任意门,几个奇奇怪怪的动物都在里面藏着。从鬼鬼祟祟到大大方方,再到拯救者和英雄,我从楼下搬来各种工具,螺丝刀、锤子、镊子、坐在凳子上开锁。终于有一天,我爸劝我下来,说楼上要来人了。
六楼外墙有一条裂缝,在阳台的上方,验收不合格,下雨天会严重漏雨,雨水从阳台积蓄,漫过两指的门台,涌向整个房间。原来选六楼的职工勃然大怒,闹了局里好半天,最终调整到二中宿舍,六楼因此闲置。我爸说是不是最近修好了,又可以住人了。修没修我是知道的,那扇门就从没开过,怀着好奇我也在等,不知道什么人会住进来。前一天晚饭,饭桌上掀起了讨论,我爷说这不是坑人家,我爸说房子闲了半年多了,也是房子,我妈说每次下暴雨咱家也漏,还不是因为楼上地面满了水,住了人,人家会管。我就把楼上想成了一片泳池,每逢下雨时,楼上开始灌水,我的每次翻身都像搅动那满满的池水,扑通通的气泡往梦里钻。
周日的下午,楼上门开了,我站在楼梯上看。一个魁梧的男人驮着一台绿色的冰箱进了门,门口探头出来一个男孩,瞟了我一眼又缩了回去。我好奇地往上走,哐当一声,冰箱落地,男人迈出门,看了眼防盗门的破洞纱网,又急匆匆下楼,期间还看了我一眼。我继续往上,看到男孩正在客厅里用一张破布擦冰箱。我在门口停下,看了看完全没有装修的房间,水泥的地面和四面的白墙,墙根那层皮都被水浸泡过,像张着嘴的膏药。里面没什么财宝和动物,房间简单明亮,空气中飘浮着刚被男孩擦起的灰尘,我咳嗽几声,往里走,想去阳台看看那道裂缝。男孩依旧在擦冰箱,好像我不存在,我兀自在屋里走动,还没到阳台,便被从厨房出来的女人喊住。你是楼下的民民吧。我点点头。她招呼男孩和我打招呼,男孩这才停下动作,说自己叫刘畅。
他和我一样大,在一个学校上学,那个魁梧的男人是局里的水电工,也是他爸,他妈和我妈是同事,都在局里的招待所当服务员。按理说水电工是分不到房子的,听说他家以前就住在招待所院子里的平房,也是辗转了多个地方才到了这儿,不管怎么样,这套裂缝的房子算是有人住了。裂缝我也去看过,我和刘畅站在阳台上,围墙很高,到我们的脖子,得踩着凳子才能探头往外看。裂缝就在左面的斜上方,露着变形的钢筋,因为一直没有修缮,也没法做封闭的阳台。一下雨就潲水,不过他爸有的是办法,在阳台上做了一层导水渠,右侧钻了一个小孔,这样一来,雨进来就流走了,起码不会进屋。阳台上堆满了各种植物,平时也不用浇,等着下雨,一下子喂个饱。刘畅说很喜欢这个房子,每次都会爬六层楼梯,他喜欢上楼梯,但我不喜欢,如果我爸再选,我会让他选一楼。
自从他来了,我好像变得有事可干了。一放学我们就在大院的高草堆里集合,那里有一块大石头,很像西游记里的晒经石,作业铺在上面可以让阳光检查。他学习不好,经常抄我作业,我不在意,一直觉得作业是一种很无聊的存在,但也会自作大人般地批评他的学习态度。刘畅的存在好像是一种对我自己的弥补,朋友之间的不对等曾一度令我感觉自豪,也并不是一种恶意的对待,而是心里一种侥存的幸福感,我的房子没有裂缝,我的爸爸是在办公室里,他用钢笔写字,而那个貌似魁梧的男人在漏水漏电的场景里用胶布和电线劳作。因此,我和刘畅之间的距离曾一度模糊地让我认为我们注定是不一样的,从头到脚的不一样,趾高气扬的不一样。我为我当时的态度致歉。事实证明,没有什么不一样,同一栋楼的楼上楼下还是同一栋楼。来年的夏天,我家阳台也出现了巨大的裂缝,钢筋像一根弹簧般翘出,整个阳台封闭的玻璃被挤碎,我妈忙着搬挪阳台的杂物,又因我爸在阳台藏的一捆捆书而大发脾气。下雨,雨水发疯似地涌进来,渗透墙面,随着火花,家里断电。我妈去找刘畅他爸。男人和刘畅一起到我家来,刘畅拿着手电给他爸打着光。男人先用一张巨大的塑料布挡住破掉的窗户,遮住雨水,在墙面找着电路,他说我家的电路走得太乱,就算没有雨,也会随时短路,交缠太多,线皮太细,长时间的高温会烧透表皮。刘畅的手电照到哪里,男人就在那里戴着橡胶手套拿着电笔和电线忙活,像钩针,像一门艺术。没一会儿就来电了,男人把原先的电路抽出来,告诫了注意事项,又看到阳台的积水,让刘畅一起来帮忙。我们舀着水,把盆递给我妈和他爸,他们便从厕所和厨房再倾倒掉。刘畅这时候说,不用客气。我愣着看他。他稚嫩的脸庞上满是骄傲,他继续说,我将来也会和我爸一样。我又看看我爸。他穿着拖鞋站在客厅里,抱起胳膊看着忙活的我们。他不会干活,不会做饭,家里的大大小小的事都是我妈在做,好像他除了上班就什么也不会干了。我点点头,才说,谢谢你们啊。刘畅又说了一遍,不用客气。男人在我身边高大得像一棵树,他拎起刘畅的胳膊,拍拍他的裤子。我妈谢了他,问他多少钱。男人不要,他说都是局里的活,楼上楼下,有事随时叫。
从那时起,其他邻居也经常找他,他成了大院里的明星人物,水电和一些简单的家电维修,全都会,也很乐意上门帮忙。有次我和刘畅聊天,我跟他说,其实你们家之前一直没人住,就是因为那间房子不及格。刘畅笑着说,那你们家房子也不及格了。随之钢筋问题被反映到了局里,没几天就派人来检查,启用了吊机,重新补了墙缝,压进钢筋,做了加固和外墙防水。刘畅还跟我说,我爸说了,要感谢漏水,要不这个房子我们住不上,轮不到我们。漏水的事儿解决了,他家也一直没有做阳台封窗,地面也还是水泥的,拖把拖过去一层层水洇,和学校教室里一样。刘畅的衣服大多是他妈自己用缝纫机做的,我在他家玩的时候见过,他妈踩着缝纫机,哒哒哒的机器针头一下下砸压,两只手缓缓移动布料,整齐的缝线和收口。甚至我的衣服破了,我妈都会上来假装唠嗑,让她帮个忙。
接着,大院的荒草被锄得干净,我和刘畅猜测要建楼了,不到年底,一栋比我们高的楼建成了,第二批分到房子的职工又住了进来,往北看,泰山全遮住了,只能看到对面窗户里晾晒的衣服。刘畅家也是,他问我为什么对面要盖七层,我们是六层。我回答不上来。后来才知道,楼压楼,就像邻居家的门框高低,也是一种比,一种气势的倾斜,领导要高于领导,不能止于领导。
很多年后,大部分人都搬走了,房子开始买卖,学区房的价格极高,租也有利益。大院变得拥挤,人和人都陌生。刘畅对面那户也有了人家,每天早上六点就开始往楼下咚咚咚跑,急着上学。刘畅没有成为他爸那样的水电工,而是卖起了手机,他妈也在他大学毕业前因为肺癌去世了。头一周还在我家坐着唠嗑,说起孩子毕业后工作的打算,毫无预兆地住进了医院,已经晚期了。那天发丧,我也上了楼,一进门,刘畅跪下就磕头,满眼通红。他已经变得像他爸那般魁梧,比我高一头,却在此刻无比羸弱、瘦小、无助,我扶他起来,他仍旧跪着,我当时还并不理解失去亲人的痛苦,但在那一瞬间的场景里产生了难以言喻的愧疚,我寒暄几句,匆匆下了楼。我妈仍旧在屋里悲叹命运的不公,生命的长跑仅仅一瞬,我却又听到缝纫机的哒哒哒声,听到刘畅说,我妈正在给我做新衣服。
后来,我在朋友圈里看到刘畅发的寻人启事。模糊的监控照片上是一个无所事事的老人,配文,家父出门走丢,头脑不清楚,患有轻度痴呆症,有见到的请联系。我发去信息询问,晚上对方回复已经找到了。我放下手机,发现窗外已经开始下雨。我妈来了电话,跟我说阳台又开始漏雨了,你爸退休了什么也不管,也不知道找谁。我安慰她几句,想到那些零碎的年代里,魁梧的男人和掌着手电的男孩,正在那个脱色的建筑里用尽最大的努力堵漏着不住涌泄的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