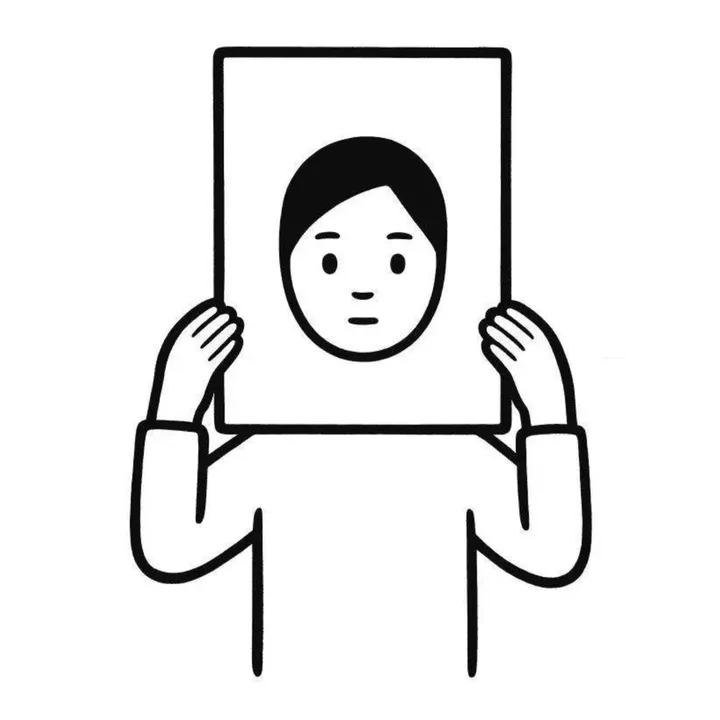画室,小孩,模特和枪。
摸枪是在周日的下午,阳光从窗帘罅隙射进来,正好打在枪体,金属反光令孙立民眼底刺痛,眯起眼成条窄缝。陈楠站在沙发上,拉紧窗帘,闭住这偷进的光。人太多,陈楠说。孙立民懂。手枪正在孙立民左手掌心撂着,冰冷且沉赘,窗外是街面的嘈杂,一楼沿街的客厅窗户正对胡同口,孙立民听到交谈,行走,自行车轮滚动,甚至汽车碾撞飞来的碎石敲打外窗。枪比他的手大,枪筒三分之一悬空搁着,孙立民有点撑不住,但不敢动,又盯着枪身铆足劲看,侧身有棱线,细微的凹槽,往下是扳机,能插进手指的空洞是控制子弹的关键。孙立民也懂,他喜欢玩气枪,他买过一把,黑色沙鹰,打塑料BB弹,子弹什么颜色都有,他最喜欢黄色,习惯用废弃小药瓶装满,塞进上衣口袋,打完一梭子,拧开瓶盖倒在手心里,一颗颗上弹。
陈楠重新坐在沙发上,盘起腿,把枪掏回去。他说,就给你看一眼。孙立民还是有点不信,他问,你从哪买的,和真的一样。陈楠对着枪柄哈了口气,撩起校服半袖下摆擦了擦,指着擦拭过的拨动机关说,这个是保险,知道什么是保险吗?孙立民上手,陈楠把枪搂进怀里,说,这个不能乱动,我爸说过,这个很危险。孙立民又问,是保险还是危险?陈楠也解释不了,说,我爸是警察你知道吧。孙立民咽下口水,往窗外看了一眼,窗帘虽然厚实,室内也有打散的微光,他当然看不到外面,但能感到外面全是人,涌来涌去。孙立民说,真枪?陈楠说,真。
孙立民跳下沙发,从客厅地板的书包里往外拿东西,里面都是一些初中暑假作业,他们约定好的一起学习,到目前为止都还没写一个字。他找出画本,牛皮纸的封面,打开空的一页,翻折到背后,又拿出一支铅笔。孙立民走回沙发,说,我不碰,我画一张行吧。陈楠把枪丢在沙发上,坐垫被压出个凹进去的边沿。孙立民把这个也画了进去,没一会儿,画本上就多出来一支铅笔素描的枪,还有一圈弯曲的涟漪,像砸进什么东西里。孙立民应该是信了,他极其认真,扳机和保险都仔细察看,尽可能一比一去画,他也想知道梭子什么样,但梭子不能拿,陈楠不让。有什么好画的,真没劲,陈楠说着坐在地板上,倚着沙发,并没有打断孙立民。半小时以后,窗帘早被拉开,作业铺在地上,陈楠整个人趴着,用钢笔戳着作业本,仿佛忘了还有把枪扔在沙发上。
画画是孙立民兴趣班学的,他倒是不排斥,每个假期都去,时间安排在上午,上五休二,也许是他妈不太想管他,把他扔到画室里就走,中午吃大锅饭,吃完饭老师把他送到公交站,自己坐公交回去,到青年路下车,不过马路,不出二百米到家。他一般不回家,公交继续往前坐,终点站在大河水库,下来还需要过个马路,胡同口第一扇窗户就是陈楠家了。俩人在陈楠家写作业,写成什么样也没人看,没人管,自由,散漫。孙立民他妈知道这么回事,不愿意多问,只要她下班前孙立民能回到家就行。这一点孙立民也从不马虎,他妈是招待所服务员,白夜两班倒,白天要上到下午六点,他看着太阳将将落山,就开始收拾东西,都往书包里塞,画本最后往夹层里小心翼翼地装。他也不知道画画是不是自己的爱好,但时间久了性格越发平稳,画也确实越画越好,画什么像什么,也都是素描那一套,一支铅笔,反复勾勒一条线,上上下下,左左右右,也很像是胡乱打发时间。但只有孙立民自己知道,比起画画,他喜欢的其实是涂黑的墨,线条暗涌,从白底缓慢生出的在场感,跟画画水平没什么关系。
画本上的枪没有梭子,孙立民在那里打了个叉号,他不知道真枪的子弹是不是也是圆的,电视上见过,都是尖头的,但是他也怀疑过电视上用的那些就是真的吗。他把画本收进书包,说,我画好了。陈楠像是没听见。孙立民又看了眼窗外,马路边有商贩出了摊,摆上了一排水果。孙立民重新把枪拿在手里,试着去找枪托的按钮,看看梭子会不会弹出来,他想看看子弹。枪冰冷,搞得他双手冰凉,孙立民把枪放下,搓了搓手,又重新拿起,找不到按钮,梭子牢牢锁在枪身。他又照着枪口往里看,黑洞洞一片,他闻了闻,看看能不能嗅出点火药味。什么也没有。于是他把食指塞进扳机孔洞,试着按压。按不动,他拨动保险栓,上下摆时还有微弱的响动,之后继续扣动扳机。还是按不动。陈楠的爸爸是警察没错,但枪是假的,他猜得没错,陈楠在吹牛。孙立民收好了书包,说,我得回去了。陈楠停下铅笔,站起来说,你不玩了吗?孙立民说,没意思。陈楠这才想起手枪,回沙发捡它,说,得了,你不是想看嘛,给你摸摸,你多玩会呗。孙立民推开木门,又打开防盗网,径直走了出去。陈楠追了出来,说,你看出来了。孙立民把书包往肩膀上拽了拽,继续往前走。陈楠又说,我爸真有,真的。孙立民倒也不在意,十几岁的小孩怎么可能把玩真枪,他一开始就不信,也没当真。
气枪在卧室抽屉里,BB弹还剩不到半个药瓶,孙立民回家后把枪拿出来。塑料质感太差了,经过先前对比,他叹了口气,虽然知道都是假的,但假的层次感不同,接近真也是一种真。他把BB弹倒在书桌上。滚动的子弹被他的小臂上前框住。按钮清脆,取出梭子,一粒粒挤进。拉栓上膛。孙立民拉开窗户,对准夕阳,猛射一发。子弹肉眼可见七八米后急速下坠,后软糯消失。他掉头回来,瞄准床上的枕头继续发射,砰砰几下,觉得没什么意思,完全没有威力,索性把枪放回抽屉。他抽出画本,一页页翻,前面是他画的动物和景,后面还有胡丽。
胡丽是画室的大学生,半个老师,负责杂务。孙立民叫她丽姐,但又觉得自己和她差不多大。虽然个头差不多,但孩子还是孩子,孙立民身上的稚气胡丽也是知道的,就他自己不知道,坐在马扎上一出神,就忘了时间和年龄。孙立民画本上的这张胡丽就是在画室画的。胡丽客串模特,扎着高马尾,坐在中间的靠背椅上,穿着一件绿色的裙子,抱起两个胳膊。姿势倒是随便,没有那么固定的讲究。胡丽来的时候孙立民已经学了大半年,所以画起来也有模有样,他勾勒胡丽的面庞时觉得她格外好看,耳朵从发丝里露出个尖,特别像精灵。胡丽的刘海长,莫名会扎到眼睛,她说等一会儿,从口袋里拿出发卡,把刘海别到耳后,一对耳朵就全露了出来,耳郭像个新生的蘑菇。一瞬间。孙立民觉得自己有点怪,手里的铅笔开始抖,他快速地涂黑掉胡丽的脸,又用橡皮一个劲儿搓。事后胡丽问他,怎么就你画的我最奇怪,我的脸呢,你这个小屁孩。孙立民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用手捂住画本。胡丽揉揉他的头,又轻轻推了一下。孙立民小声说,太多人盯着你,我画不出来。
画室其实就是出租屋。在虎山路小区最里边,六楼,顶层。两室一厅的房子,客厅腾空,挨着落地窗放着一张写生的桌子,上面摆着几个苹果和梨,还有几个石膏体静物。沿墙立着七八个画架和马扎。卧室一个放杂物当仓库,另一个放着两张上下铺,可供学生临时休息。来画画的学生年龄不一,大部分是高中生,最小的就孙立民。老师留着大胡子,教育机关出来的,不收小学生,但和孙立民已故的爸爸也算半个同事。碍于面子,勉强收了孙立民,给他个凳子和架子,随便画,也不收钱。胡丽来了以后也觉得好奇,就问这个事儿,大胡子没把话说得那么直接,还是孙立民自己说的。
那天上午结课后,胡丽搬着凳子坐在孙立民旁边。他吓了一跳,赶紧合住画本。胡丽说,你怎么老捂你的画。孙立民说,别看,我画得又不好。胡丽说,你到底多大?孙立民说,初一,我妈非把我送来,一到假期就来。胡丽问,你爸呢?孙立民说,没爸。胡丽嗯了一声,把画本一把抢过来,开始翻看,小声说,咱俩差不多,我没妈。孙立民心里咯噔一下,既凉又暖,舌根生了一汪痰水。胡丽又说,这有什么,无非这样呗,哦,也不对,你还小,不好接受。说完又揉揉孙立民的头。他是平头,头发根根直立,扎得胡丽手疼。孙立民说,我不小了,我和你一样高了。胡丽哈哈笑,说,你画得还挺好的,就是我没有脸。她翻了几页,说,这是什么?孙立民站起来,看了一眼,说,枪,手枪,真的。胡丽斜睨了一眼孙立民,说,真枪?孙立民点点头,说,我同学他爸是警察,我去他家看的,真的。胡丽用指腹摩挲着画纸,说,这有个叉。孙立民说,画走样了。胡丽说,没,挺好,从来没见过真的,这枪能开吗?孙立民心想,他其实也没见过真的,但话赶话,不知道怎么圆了。他心里想着BB弹从枪筒里射出去,扳机按动回弹。孙立民说,有保险,打开就能。胡丽把画本还给他。孙立民赶紧岔开话题,他说,你妈怎么没的?胡丽捂嘴笑,把头发捋到耳后,说,我妈没死,跑了,跟别的男的跑了。孙立民嗯了一声。胡丽说,那我算不算骗你?
孙立民脑子一下乱了,他重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人。她整理着自己的马尾,取下发圈,甩了甩头发,重新扎高,耳朵像在头发间跳动。胡丽挑着眉毛看着孙立民。他从没有和任何一个真正的女人有过这样的交流,连他妈也没有,他也不懂欺骗和被欺骗的关系,他自以为的成熟一下子被成年人攻破了,他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谈话,他还是更喜欢和陈楠交流,但胡丽身上有种奇怪的橘子味,正缓缓散发奔向他。他想起爸爸的车祸,也是一货车的橘子,从高架桥上滚落,沿着路面像铺开了整面橘色的地毯。爸爸在迎面的轿车里,驾驶座的车门已经严重变形。橘色的消防员拿着扳手和切割工具摩擦出火花,吱吱啦啦。孙立民和妈妈赶到现场时,爸爸还能说话。孙立民捡起地上的一个橘子,又想起家里客厅盘子里摆的橘子,他比对着它们,大小,色泽,纹路。妈妈哭得凶,爸爸还能安慰,他说,只是腿,腿被卡住了。孙立民把手里的橘子塞进上衣口袋,回家后可以继续垒高橘子盘。路面倾斜得厉害,仍有橘子从侧翻的货车篷布往外滚溢,看上去像瀑布。孙立民拉妈妈的衣袖,扯,拽,把下摆一角团在手心。他说,妈,好多橘子。躲不开的汽车,将它们碾轧出汁液,飞溅在路面上。吱吱啦啦,吱吱啦啦。气味是刺鼻的,孙立民回忆起来了,不是只有橘子,还有汽油,还有摩擦的铁屑,汗,爸爸随后长久的沉默,和妈妈的眼泪。
喂,你不用默哀,我妈没死,我也不记恨她,选择题而已,胡丽说,你做过选择题吧?孙立民抬起头看她。胡丽接着说,我不懂画画,但在这能赚钱,一个月给我三千,模特另算,一个小时六十,哎呀,说了你也不懂,虽然你不交钱,但学得算快。孙立民点点头,收起自己的画本,把画架腿踢拢。胡丽说,但老师嘱咐了,你是最小的,让我照顾你,算你欠我的。孙立民说,怎么个欠法?胡丽又揉揉他的头说,我还没想好,留着以后再说吧。孙立民说,我又不需要照顾。
实际上,胡丽照顾了画室所有人。厨房有完整的炊具,胡丽来之前都是大胡子老师点外卖,饭费当然是学费里的,也许是因为嫌赚得少,才雇的胡丽。十一点半左右,厨房就开始有动静了,胡丽好像乐于下厨,菜刀咔咔劈在案板上,但几乎是盖浇饭,这样对于她来说也省事。孙立民一般不觉得难吃,一吃完,胡丽就送他去车站,像是老师嘱咐的,也像是他妈妈嘱咐的。因为没有学费,他只上半天,孙立民自己也可以理解,毕竟还有作业要写。这回,画室所有学生都没吃几口,孙立民勉强把盖浇饭都吃了,土豆丝好像没熟。胡丽不说话,拿起手机自掏腰包给大家重新点了份外卖,默默收起了所有的饭盒。她走到孙立民身边时问他,你怎么都吃了。孙立民擦了擦袖口,说,挺好吃的。胡丽说,嗯。她拿过孙立民手里的空饭盒,一并收进垃圾桶里,接着对画室里其他学生说,我给大家点了米线,一会儿就到。孙立民好像看出了点什么,问她,你怎么了?胡丽侧头看向孙立民,说,我?
孙立民知道这种感觉。他的妈妈之前也有过这样,回家后瘫坐在沙发上,身子挺直,但没错,是瘫在沙发上,整个人的精神像被捆住,提拽着躯体,不得随意倒下。孙立民会倒杯水,端过去,问一句,你怎么了?但他也清楚,到底是怎么回事。爸爸的意外,对于他来说,也是一场精神的捆缚,他也许更加冷静,从哪个电视节目里听来的句子,失去意味着成长,冷漠才是成熟。但他不会冷漠,学不来,懵懂的成长和焦灼的热情在不停地烘烤着他的佯装。他坐到妈妈身旁,准备接受指责,只要接受就可以了,其他什么都不要说。
此刻,他觉得胡丽也是同样的状态,他补了一句,丽姐,我哪里做错了吗?胡丽像是没听见,往里屋走。孙立民起身帮她倒垃圾,又帮她收拾好厨房的灶具,等外卖到了,拎进屋,分给其他人。都安排好后,孙立民第一次看见胡丽抽烟,她躲进杂物室,细烟叼在嘴唇,打火机点燃,火苗明透了又暗下去,她随便拣了一支画笔,在墙壁上空涂着。孙立民走进去,什么也没说。胡丽说,也有你的一份,快去吃,吃完送你去车站。孙立民说,丽姐,我带你去个好地方。胡丽把烟掐了,又打开窗户,说,去哪儿?
陈楠开玩笑,孙立民推搡他。陈楠说,你不会是喜欢上这个姐姐了吧,漂亮吗?被这么一说,孙立民浑身都刺痒起来,他矢口否认,对于喜欢是什么,他压根分不清楚,青春期刚来,嗓音也是上个月起的变化,总像口中含着块方块。陈楠也好奇,大河水库就在他家附近,也没理由不去。大河水库全名叫什么,孙立民也不知道,整个河道极其宽,中间鼓着大肚子,两端收窄,不知通向何处。河岸有半人高的水草,常有垂钓的人藏在其中。孙立民来陈楠家时路过,总能看到人们红色的水桶里装满的鱼,个头不小,还在扑腾。他对钓鱼没有兴趣,但邀约发出时,也想不到更好的去处,他实在没去过几个地方。这次他把气枪塞进书包,又带了两个药瓶的子弹,射射水草或者鱼,还带了画本,写生画水波光,总之他能想到的有趣的事都准备着了。
和胡丽一起来的还有一个男的,戴着黑色的全盔,摘了头盔有一头卷发,立马蓬松开,比胡丽高一头半。摩托车引擎还没熄,嘟嘟嘟地发声,后座横置着长条包,里面放着钓竿。从哪下?男人说。孙立民站在坝石边指着下河沿的土路。胡丽说,车就放这吧,前面我看也过不去了。陈楠跑过来要摸头盔。男人递给他,说,戴上试试。陈楠把头盔套在自己头上,嘟嘟囔囔说话。男人说,还真小孩子。胡丽拿胳膊肘捣他,跟孙立民和陈楠说,这是我男朋友,杨凯。孙立民立马回,凯哥。杨凯灭了引擎,背上鱼竿包,拉起胡丽的手往土路走。又回头冲陈楠说,头盔给我拿好了。陈楠取下头盔,端详,说,真酷。孙立民跟在后头,看着胡丽的手被杨凯攥在手心里,他觉得杨凯在莫名地使劲。
下午没有太阳,河面无风,近来天气都差,空气潮热。孙立民领口已被汗水浸湿,他找来一块大石头,搬在河边当凳子。胡丽不坐,她站在一旁问孙立民,有什么可玩的?孙立民看着陈楠已经当了杨凯的狗腿子,在不远处抠一湾泥巴。孙立民说,钓鱼?也可以干别的,我看很多人都来这里玩。钓线已经挂上了钓钩,杨凯利索地甩进河里。他们没带桶,陈楠在挖坑,杨凯教的,钓上来的鱼可以暂存。孙立民说,我还带了画本,枪。胡丽说,我不会画画。孙立民从书包里掏出气枪,把小药瓶一块递给她。胡丽接过来,说,假的。孙立民说,可以发射,你试试。胡丽按孙立民说的,把子弹倒在手心,一颗颗按进梭子,然后拉栓,瞄准天上的某个点。砰的一声。子弹飞出去。胡丽又瞄准水面,水草,水下的石头。接着举起来,瞄准远处的杨凯。砰。子弹射出去,不到半路又落下来。孙立民说,你男朋友?胡丽说,听说我要来大河,非要跟着来钓鱼,你也带了朋友。孙立民说,我同学陈楠,他爸是警察。胡丽说,所以枪是他爸的,我说那把真枪。孙立民把枪拿过来,也冲着远处的芦苇开了几枪,说,嗯,警察才能有真枪。胡丽又问,警察还能干什么?孙立民被问愣了,说,抓坏人。胡丽大笑起来,说,他们什么也做不了。说完,胡丽朝杨凯他们走去。孙立民才注意到,胡丽今天穿了一条牛仔短裤,短到大腿半截,白皙的双腿下是一双黄色靴子。她的腿纤细,像两根筷子,他又想到他妈,自从爸爸走后,他妈开始变胖,腿也越来越粗,脂肪仿佛是抵抗变故的有力武器。孙立民知道男女朋友是什么意思,他觉得自己也可以,他没有摩托车,但有把枪。他拉栓,学着胡丽的样子瞄准杨凯,眼神顺着瞄孔扫过去。杨凯搂住胡丽的腰,杨凯抓住胡丽的胳膊,杨凯在她的唇上啃了一口,杨凯指了指背后的河,杨凯往这走,杨凯越来越近。
枪被杨凯一把捉走。瞄啥呢瞄,杨凯说,这啥玩意?孙立民后退两步,险些跌倒,脚踩进泥巴里,他拔出脚,鞋面已经浸了泥。杨凯拿着气枪朝着地面打了几下,子弹软绵绵地弹到一边。杨凯说,幼稚。孙立民说,给我。杨凯把枪丢给孙立民,接着去翻孙立民的背包。孙立民扭身,但拗不过这个大人。杨凯有一米八,体重也有一百八十斤,实打实的壮。他拎起孙立民的书包,从里面掏出画本,蹲在那块大石头上。孙立民握紧手枪,不说话。杨凯翻着。远处胡丽的笑声传过来,陈楠滑倒在河堤上,后背湿了水。胡丽把他扶起来。陈楠转着身看自己的后背,像追自己尾巴的猫。孙立民后悔带他来了,他拉低了我方的年龄。杨凯从口袋里掏烟,磕出一根,递给孙立民。孙立民不碰这个,也不会。杨凯甩甩手,给自己点上,说,你这画的胡丽?孙立民凑过去。杨凯把画本还给他,继续说,你喜欢她?孙立民不吱声。杨凯又说,我让给你,你能行吗?说完从石头上跳下来,颌着下巴看孙立民。杨凯把烟灰弹远,有一部分落在孙立民的鼻尖上。孙立民抖了抖头。杨凯说,卖的,这个你懂不懂?就是交易,不分年龄,不分贫贱,给钱就行,你有钱吗?孙立民摇摇头。杨凯吸了口烟,说,真是小屁孩,你还想知道什么?孙立民不信,他知道杨凯说的那种人是什么,但胡丽绝对不是。杨凯继续说,大学生?假的,技校没毕业,学的厨师,那时候就开始接夜场,我不是他男朋友,算皮条客,皮条客这个你懂吧,哎,给你解释起来真烦。杨凯搂住孙立民的脖子,指着胡丽和陈楠。他们在弄鱼竿,胡丽把鱼线扔进水里,陈楠已经不为湿衣服哭了,重新打起精神,帮胡丽拽紧鱼竿。水洼里有两条鱼,一大一小,杨凯刚钓上来的。杨凯说,鱼,我们在钓鱼,你就是鱼。孙立民说,什么?杨凯说,我知道胡丽最近和你走得近,她说认识了一个小孩,我们不接小孩,很麻烦,你知道很麻烦就行,她不是什么好人,说的话不要信,我也不是什么好人,但我不喜欢骗小孩,你听明白了吗?
胡丽扭头看他们俩,朝这喊,你们快来,抓不住了!杨凯吐掉嘴里的烟,拍了拍孙立民的肩膀,跑了回去。孙立民没动,陈楠也回头喊他。杨凯抢过钓竿,猛地往后退,双手骤提,河面被鱼线割开一条口子。他喊,这鱼挺他妈大。孙立民把手枪收进书包,看到地上的烟头还没灭,他蹲下,拾起烟头吸了一口,呛鼻,咳嗽了两下,重又将烟头扔进水里。他看着远处的阴云淡了下去,像失了墨,天色将晚,雨好像也要来了。孙立民又闻到空气中一股橘子的味道,他仔细分辨,河面浮来一个蓝色的塑料筐,里面堆着一层腐烂的橘子。他看了看河边的三人,他们仍在跟一条鱼较劲,孙立民想把这些画下来,他坐在石头上,摊开画本,雨正是这时候一滴滴掉下来,在画本的空白页,一团团洇开。孙立民用手去抹,画纸反而湿得更快,他戳出个洞,这个洞露出了画本,陷进他的手心。
孙立民好几天没去画室,他妈问他怎么回事,他只是说不想学了,他妈并没有深究他内心的想法,反正不要钱,但又担心没人看他,也是反复劝说。他没心情听,于是把自己关在屋里。对于成年人的那些事,他捉摸不透,也不好理解。他反复鼓捣那把气枪,画本也被他涂黑了,只有胡丽他没舍得,用橡皮把脸擦干净,凭着记忆重新画了上去。拉皮条是什么,卖的又是什么,他在胡丽的头上画了尖尖的耳朵,又画了一对犄角,嘴唇两端往上提,绿色的裙摆他擦掉一半,露出大腿,改细。他把胡丽的鞋子脱掉,五根脚趾依次勾勒出来,并拢。裙子的一侧肩带滑落,胸只露了一半,他涂了黑点,那是乳头,他咽下口水。胡丽的胳膊没在胸前了,它们自然下垂,又别到腰后。胡丽站起来,凳子被他擦掉,她转身,臀部,他在幻想裙下的弧度。两只手交叉,在后腰处打结,胡丽转了一圈,在笑,肩带继续滑落,她露出另一半胸,他没涂黑点,他需要告诉自己这是假的。胡丽在走,一对犄角顶出了画纸,这是他想象的魔鬼的样子,还有无数双手,在四周向她伸触。她又变得楚楚可怜,蜷缩回凳子上,像身体的什么部位在疼,犄角在变小,完全被头发遮住。胡丽在哭,他受不了。他想起胡丽抽烟,杨凯抽烟,他想学,他觉得自己很小,身体一边皱缩,一边无限膨胀,他压不住那东西。孙立民把画纸迅速团成球,从窗口扔了出去。他倒出所有的BB弹,它们在桌子上散落一片,黄色的子弹像袖珍的橘子,开始不停地滚落。孙立民跑到床上,蒙进被子里,他呻吟着说,妈妈,又说,爸爸。
孙立民一上午没看胡丽,他只盯着自己的画板,画笔在手里捏着,却什么也画不出来。窗外有雨,课上到半道下起来的,大胡子说去调车,就没回来。胡丽又充当模特,坐在中间,穿一件白色防风衣,宽松的短裤,好像风吹得有点冷,她打了几个喷嚏。几个高中生没停笔,画纸上画着胡丽,都不太一样。孙立民起身去关窗户,雨确实不小,打进屋,溅了他一脸水。他重新回到凳子上发呆。胡丽叫他。他抬头看看。胡丽说,你怎么不画。孙立民不说话。胡丽没再问。孙立民是被他妈拽来的,他在家里她不放心,觉得他会憋出病来,钥匙也不给了,回家敲邻居门,邻居给开,按时按点。孙立民他妈后来和他好好谈过一次,但方式也过于幼稚,他开始讨厌这种交流,对方总把自己当孩子,限制,控制,管制,而她惯用的句子就是,我已经失去你父亲了,不能再没有你。孙立民懂,一切也按她说的来,老老实实当一个孩子。但他坐在画室里,却开始觉醒,或者叫逆反,坐不住,屁股底下的凳子挪来挪去。他想知道真相,但又不敢面对。
雨下得越来越大,楼下的道路开始积水,课程不得不中止,中午开饭前就要撤走。学生都陆续出门,大胡子来电话了,也直接回了家,并嘱咐胡丽把孙立民送到家。胡丽应下来,走到孙立民旁边,他依旧坐在凳子上。胡丽看到他的画布是空的,问,你最近去哪耍去了?孙立民站起来,说,不太喜欢画画了。胡丽重新把孙立民的画架支好,把他摁在马扎上,自己走回中间的椅子,坐下。她说,现在,就我和你,你重新画。孙立民望着落地窗,雨像炮弹一样打在窗户上,临近中午,天空滚着黑云,整个画室越发昏暗,孙立民已经看不清胡丽,只有一个大致的轮廓。孙立民去开灯。胡丽把他叫住,说,别开,你画。她把发圈拽下来,头发立刻披散到肩,接着她脱掉防风衣。孙立民照做,他拿出铅笔,和大拇指交叉成十字,开始定位,他找着光影的关系,距离,胡丽实体的边棱。孙立民觉得这才是画画,他又忘却了自己的年龄,轰隆的雷声劈进屋内,胡丽都被吓得一抖,他涂抹在画纸的笔依旧稳定。孙立民皱起眉,盯着胡丽看,又低下头画上几笔。胡丽坐在中间,她说,我抽支烟。孙立民没理她。胡丽点上烟。火光把嘴唇照亮了,孙立民才看清她嘴角的痣,在左侧上方,像一枚图钉,他点在画纸上。他又看到胡丽尖尖的耳朵从升腾的烟雾里钻出来。孙立民再次抬头,胡丽一手捏住烟,一手脱下衣服。她说,你别停,我们做场交易。孙立民继续画,这个场景他在画纸上想象过,现在胡丽就在他面前的椅子上,背对着窗户,窗外的雨越来越大,天气愈发暗沉的,他能看到的胡丽也是,朝向他的慢慢只有黑色胡丽的身影。但孙立民能清楚地知道,胡丽已经完全褪去了上衣,接着是短裤,她把它踢到一旁,内裤也脱下来,那里有一团深于胡丽本身的黑,现在她一丝不挂地坐在椅子上。椅子有点凉,她弹起身,又重新坐下。胡丽说,你画。孙立民耳朵里是雨的滂沱,画笔摩擦画纸的声音变得微弱,他生怕用力把胡丽戳破。他见过女人的裸体,他的妈妈洗澡时他偷看过,臃肿的身材没有任何吸引力,事后他还会陷入一种对自我的责难。这次不同,是胡丽主动的,孙立民继续画,他的身体也起了反应,这才感觉血管里的液体是活动的,在疯狂流淌和蹦跳。胡丽站起来,说,你喜欢我。孙立民停下笔,说,我不知道。胡丽光着脚去开灯。吸顶灯亮起来,孙立民捂住眼,不敢看。胡丽走上去,拉开孙立民的手,说,见过吗?孙立民想往后退,他觉得那不是雨的轰隆声,是自己的心跳,它像无数条鱼,开始扑腾。胡丽拉着他,不让他逃走。他看到胡丽的耳朵变得暗红,像凝固的血。拉扯没一会儿,孙立民突然抱住胡丽。胡丽一惊,扶住了墙。孙立民说,丽姐,丽姐,丽姐,我喜欢你。胡丽笑起来,说,你继续叫。孙立民的双手紧紧搂住她的腰,身体贴近她的胸,胡丽身上确实有橘子味,他觉得那可能是某种香水,她的肌肤温润,有股可见的气流钻往他的鼻孔。孙立民低下头,看到她葡萄般的乳头,接着闭上了眼。他的手开始上下抚摸,他仔细感受,胡丽的背上有一道道疤痕,他没敢再摸,大口喘着气。孙立民说,丽姐。胡丽把手探下去,停在他的下身,说,你还是个孩子。孙立民说,我知道。胡丽又把手抬起来,去摸孙立民的头发,说,那些,你信吗?孙立民说,我不信,杨凯不是个好人。胡丽轻轻推开孙立民,对他说,好了,你帮我做件事。孙立民问,什么?胡丽在他额头上吻了一下,说,我想要那把真枪。
孙立民不确定陈楠他爸有没有真枪,他再次向陈楠求证。陈楠说上次给他玩的枪确实是假的,是赃物,就是他爸没收来的仿真枪,有人拿着在银行吓唬人。真的他也摸过,和这把差不了多少。枪在佩袋里,有一圈系绳,可以挂在腰上。陈楠玩的时候没有梭子,摸上两把还给他爸,他爸才把枪组装好,放回腰间。陈楠答应给他那把假枪。孙立民不要,他说,你把它偷出来。陈楠说,你到底要干吗?孙立民说,你真怂。陈楠说,你要干吗?孙立民能猜到胡丽拿枪干什么,但他没问,只是答应了胡丽的一切要求,他要想办法弄到枪。枪大概是用来杀人,枪口的设计就是为了瞄准,当然不是BB弹瞄准枕头,水草,石头一类的东西。
陈楠说,我知道你要做什么,但你要还我,让丽姐看两眼就可以了,这个得提前说好。孙立民说,你怎么知道?陈楠说,那天钓鱼,她问我枪是不是我的,说很好奇,我给她说了,真枪没几个人能摸到。她觉得我很牛逼,丽姐想让我拿出来玩,但她不是我好朋友,虽然长得挺漂亮的,我知道你喜欢她,但她比你大好多。孙立民打断他,说,我是你好朋友。陈楠说,必须的,我爸爱喝酒,喝多了只会睡觉,这个时候我妈就把自己关在屋里,我爸睡客厅的沙发,衣服也不脱,鞋子也是,什么也不管,呼噜打得比雷都响,他也该长长教训。枪我没法藏,周六,要么周天,你来挖,我把枪偷出来,埋在我家楼外面,那棵槐树底下,你来的路上应该看到过。孙立民说,你真行。陈楠接着说,我把那把假枪放进去,我爸除非出任务,要么不会发现,枪不是随时都用得到,就像个威慑。孙立民说,什么射?陈楠说,你追不上她,你和我一样,还是个小孩。孙立民想和陈楠说说杨凯那些话,但忍住了,他的面前又浮现出胡丽的身影,胡丽凑过来,轻声在他耳边说着,你听好了,我想要那支真枪。孙立民说,第二天我会埋回去,你再挖出来。陈楠说,挺羡慕你,你妈也不管你,我那天回去挨了顿打,我第一次顶撞,我说我走路跌河里了,撒谎也挺有意思的。孙立民听着。陈楠最后说,我们都是未成年,我查过,什么都追究不了。
枪挖出来时已经接近午夜,陈楠用超市塑料袋把它包好的,埋得不深,袋子一角露在土的表面。孙立民抖落上面的土,把枪塞进书包里,顿时觉得书包沉了很多。他妈上夜班,他没有钥匙,用拖鞋挤住门缝,好半夜能回家。枪不能拿手里太久,他也怕。胡丽已经在大河水库等着,这个时间他坐不了公交,只能用跑。他拉紧书包背带,沿着一颗颗路灯洒下的椭圆形的光圈往前,往远。书包越来越沉,他大口喘着气,天边的月亮早就升起来,弯得厉害,也像一把手枪。孙立民跑上桥,跑下桥,又跑过另一个桥洞。
胡丽还是穿着那件绿色的裙子,裹着一件黑色的外套,站在河坝上。她看到孙立民跑了过来,开始沿着小路往河边走。孙立民喊她,她像听不见,继续往下走。他追上去,说不出话,不知道自己到底跑了多久。胡丽的鞋面湿了水,她才停下,对孙立民说,枪带来了吗?孙立民喘了一大口气,从书包里掏出塑料袋,拿出那把手枪,递给胡丽,枪太沉,他像递出一块砖。胡丽接过来,右手游走了一遍枪身,握在手心。孙立民缓过神,说,我看过了,有子弹,尖头的。胡丽侧身往外瞄。两人站在水边,路灯的光沿只能够到胡丽的一半身子,拿枪的另一半隐在黑暗里,与静止的河面交融。胡丽问,怎么开枪?孙立民说,保险,扣一下。胡丽说,你知道我要做什么吗?孙立民说,知道,杀人。胡丽说,你不怕吗?孙立民说,你身上的疤是打的吗,凯哥说的是真的吧。我也恨很多人,那个货车司机,他喝酒了,把车开得像一只螃蟹,我爸躲不掉,被撞在石墩上。还有我妈,她像丢了魂,又变得很凶,什么都怪我,也不想看见我,我才十三岁,我有多大能耐。人死了就死了,复仇也很爽快,我喜欢玩枪,但之前打的都是软弹。我可以帮你,你不要做那种事,丽姐。胡丽笑起来,说,帮我做什么?孙立民说,我未成年,什么都可以。胡丽说,好。
她向孙立民走了几步,把自己的双脚从水里拔出来,又脱下外套,扔在石头上。孙立民不知道她要做什么,但已经下定决心帮胡丽。杀了杨凯,或者其他成年人,很多成年人,都可以,只要是欺负过胡丽的,他都可以依次扣动扳机,把梭子里的子弹打光。他不在乎。他闻到橘子的味道,但他知道那味道绝不是当下的,是属于那场车祸的,他自己也该在那场车祸里同时死掉,包括他的母亲,所有人,他们是在死亡的背后滋生着的蛆虫,永远被控制住,被啃噬着。接下来所要做的一切,只是死亡的另一种自动延续罢了。胡丽说,我要和他们算账,每一个人,在我生命里肆意流淌过去的每一个人,在我身体里存在过的每一个人,你听得懂吧?孙立民点点头。胡丽已经站在了光里,她把手枪递还回来,对孙立民说,你拿着。孙立民接住,说,你告诉我是谁。胡丽说,你把枪举起来。孙立民照做。
他两手举着,不知道要瞄准哪儿。夜里的风有些凉,孙立民打了个寒战,刚才跑出的汗正在从皮肤挥发。胡丽的裙摆被轻巧地撩动,尾端轻击着她的脚踝。孙立民看到天上的月亮,圆得像一颗BB弹。他挖出枪时就看过梭子,里面向下排列着整齐的尖头子弹,他小心翼翼地推出一颗,藏在口袋里。现在手枪里还有七发子弹,他仔细数过。他可以走近七个人,按胡丽的指示,向他们扣动扳机,如果打得准,每人只需要一发。还好他平时经常练习气枪,他想,真和假没那么容易区分,他一样可以驾驭,生和死也是,根本不是一线之隔,连那个界线也没有。他瞄准远处的河面,眯起眼。河对岸的路灯开始忽闪,手枪瞄准。有货车从对面的道路横向驶过,手枪跟着车的轨迹缓慢滑动。胡丽走进了手枪的视野,再次站进水里。她面向孙立民,站稳在枪线上,抱起胳膊。风让她也同样打着寒战。孙立民正要放下枪,胡丽冲他喊,别动。他被吓到了,双手愣在半空,大口呼吸着,说,丽姐?胡丽说,瞄准我,开枪。孙立民浑身开始发抖。胡丽继续说,杀了我。孙立民依旧站着不动,他感觉自己在慢慢凝固。胡丽继续说,你不会懂的,任何人都没错,是我。我自己才是那个终点。可我没有勇气做这件事,我选中你,你是我生命里最后一个人,小屁孩。
子弹从枪口涌出去。声音轰鸣,短促,直贯夜空。孙立民的手掌被剧烈地震动,疼痛感好似把骨头打碎。手枪被他下意识猛地扔出去,在水面泛起一片波纹,随即沉入河底。孙立民扭过头。胡丽惊恐的尖叫声这才被他听到。她蹲在地上,手捂着耳朵,孙立民看到她的手在流血,红色的液体透过指缝渗出来,像一条裸露的红色静脉。子弹打伤了胡丽的耳朵,胡丽嘴里嘟囔着,孙立民听不清,也不知道该说什么。他走上前,也蹲下来,看着胡丽嘶哑地吼叫。孙立民又站起身,他想到那把水中的枪,他还要还回去,重新埋在土里。他往河里走,小腿渐渐被浸没,他越走越深。那盏忽闪的灯灭了,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河面的水也静止着,孙立民被吸纳进黑色里,仅靠着头顶劈下的月光继续往水深处走。他俯下身,在摸,手指,手掌,胳膊,插进河水,他摸到水草,石头,还有一条巨大的鱼。孙立民滑倒,跌进半身高的水里。他不会游泳。水面的波纹开始变成浪,他在拍打。他应该害怕,但没有,他很平静,拍打只会让他沉得更快,仿佛他自己选择这样。他嘴里又开始喊,妈妈,爸爸。但声音极小,只有他自己能听到。那股橘子味又来了。孙立民喝了口水,没有吐出来,他咽下去,又咽下去。他摸到了那把枪。他抓紧了那支枪。
孙立民被一把提起来,从水里冒出了头。他湿漉漉的身子被拖拽到岸,软趴在石头上。他听到粗重的喘气,水从他嘴里往外漾。月光像是这才弥漫开来,四周被披上了一层光,映出原本的模样,孙立民看到胡丽站在自己身旁,右耳郭上面豁了一块。胡丽说,你个死孩子,不犹豫的啊。孙立民咳出口里的水,坐在石头上,说,走火了,我第一次杀人。胡丽转而被逗笑了,她揉了揉孙立民的头,又把自己的裙子撩起来当成毛巾,擦着孙立民湿漉漉的头发。孙立民埋进胡丽的肚子,他再次感觉到胡丽温润的肌肤,小腹的呼吸起伏,像河面的波。他说,丽姐,你疼吗?胡丽说,疼死了。
来的方向先是起了响声,高频轮转,胡丽停下擦拭,孙立民也站起来。红蓝色的车顶灯从路尽头缓缓靠近。胡丽说,冲我们来的。孙立民说,枪。他把枪用上衣擦干,又说,怎么办?胡丽说,我现在不想死了,我怕疼,我的耳朵在流血。孙立民一只手握紧那把真枪,看着远处的警车越发靠近。他对胡丽说,你走吧,我还是个小孩,什么也不会发生。胡丽说,我不走,你还是个小孩。他们又笑起来,孙立民凑近了看胡丽的耳朵,像被什么咬掉了一小口,缺了个尖。
胡丽拉起孙立民的手。风弱了,警笛声越来越大,警车停在河坝上,下来三个人,手电筒射出光,依次打到岸边,河面,孙立民和胡丽的身上。孙立民拽紧胡丽的手,他手心出了汗。光柱停下,胡丽眯起眼。孙立民听到皮靴踢踏着,踩在土路上,他跟胡丽说,丽姐,我想到个事儿。胡丽说,什么?三个人开始冲他们喊,别动。孙立民说,陈楠,估计又要挨打了。胡丽又笑了。孙立民扭头看她,手电筒的光太强,他看到胡丽的脸变得亮白,笑容逐渐模糊成一片。接着,他的眼底也被射进强烈的一束白光,孙立民感觉熟悉,仿佛回到了在陈楠家摸枪的那个下午,这光跟当时反射进眼里的,是同一束。一切早已命中注定,徐徐展开。突然,孙立民什么也看不见了,他被钳住,他倒地,他没松手,手掌心里是另一只手,他轻声说,丽姐,丽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