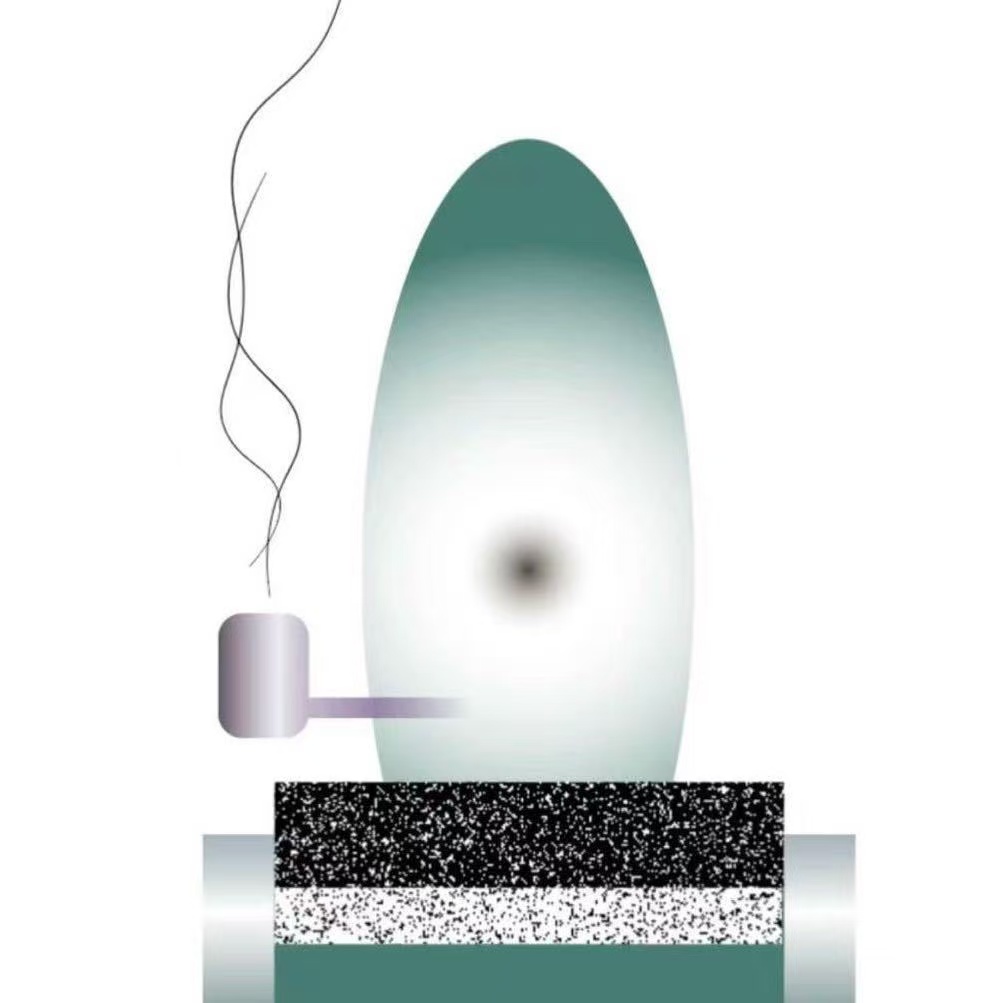对于学美术的学子而言,考试是一道窄门,故事跟随一位老师的视角,探索门内门外的世界是否真有区别。
冯一加来请假的时候,我正埋头给学生改稿。她说,从下午开始就不大舒服了,脑袋发晕,现在晃一晃就疼。我很爽快就批了假,让她回寝室休息。谁料她说着说着就哭了,我只好停下手里的活儿安慰几句。她前脚刚走,老何就摇头,说现在的孩子太娇气,生个病也哭。我没接话,低头才发现原本要用浅灰色做渐变的地方涂成了深灰。
“冯一加的假不敢不批啊。”慧姐说。
冯一加的画板上只用美纹胶带裱了一张四开纸,下午色彩课的水桶和调色盘都还没清洗。显然,她没为我的课做半点儿准备。我想她大概是不想上央美设计课。我还记得她上次的作业——一个“时间”相关的题目,她画了破碎的钟表和镜子。我对她说了句“有点俗套”,她没吭声。但我把她隔壁女孩的作业贴在了墙上。这样想来,或许她不想上央美设计课是因为讨厌我。
我被安排在清华设计班——名义上是清华方向,但保险起见,这些孩子也会准备央美的校考。在十二月以后,因为临近央美的考试,我每周要跑三次宋庄,大多数时候不讲课,只在教室里挤着那张长桌改画。到了晚上,班主任老何和教清华色彩的慧姐会坐在角落管纪律。没事干的时候,老何喜欢嚼槟榔,慧姐在她的小米手机上写同人小说——这是知情的学生告诉我的。他们不怎么和我聊天,因为我还在美院读大四,他们仍把我当学生。也因为我还在美院念书的关系,学生更乐意和我聊天,尤其那些志向考央清的孩子。我只比他们年长三四年,他们却把我当作比其他任课老师更值得信赖的大人。有时候我会从这群十七八岁的孩子嘴里听到一些超乎年龄的沉重故事——关于家庭矛盾,或是希望渺茫的前程——我口头给予于事无补的安慰。事到如今,如果我还天真地认为参加艺考的孩子全都是为了理想,未免太不成熟。我知道他们争着让我帮忙改稿只是为了偷懒聊天,我不会拆穿。比起紧锣密鼓地训练,我认为他们更需要休息。
学生们穿着印着画室Logo的黑色长羽绒服在楼下的超市进出,衣物的下摆无一例外都沾着五颜六色的水粉颜料,结账的队伍快要排到门口。我熟悉那个画面。四年前集训的时候我胖了许多,那时候食物是唯一的慰藉。当初在画室,老师请来五年前考上清美的学姐来做分享。学姐说,不要担心变胖,集训的时候大家都胖,肥胖是随时可以减的,但考试就只有那么一次。
在北京跑计程车的师傅大多住在燕郊,所以夜里从宋庄回燕郊的车并不难找。我很快在软件上打到一辆黑色比亚迪,车子正从两百米外的岔路掉头往画室的方向驶来。当我站在路边等车的时候,慧姐叫住了我。
“许老师,我想麻烦你个事。”
“什么事?”
“刚刚我接到女寝那边宿管的电话,说冯一加这孩子烧得厉害。”
“不好意思啊,我的车快来了。”我快速觎了眼手机界面,“还有两分钟就到了。”
“哎,我也不想麻烦你……不过,你方便捎她去一趟医院么?”
我知道慧姐今晚要去见她男友的父母——这也是学生和我透露的情报。虽不情愿,但我还是答应了。
“辛苦你了。”慧姐语毕,望着我欲言又止。
“怎么了?”
“明天是中传(中国传媒大学)的初试。”
我很快意会了。
“冯一加肯定是去不了了。”她叹息着说。
我摇下车窗,和司机在白桦树下等了一会儿。看到冯一加的时候,我朝她喊了一声,招手。她被宿管扶上车。路灯下,我看见她的脸颊比在教室里的时候要红得多。我没问她“还好吗”之类的废话。我们全程无言。
司机说,最近又是一波流感,好多人中招。我说是啊。司机问我,她是你学生啊?我说对。他说这一带全是画画的。我点头。他说前阵子宋庄美术馆有个画展,真是太冷清了,除了学生没人去看。我敷衍了一句是吗。沉默半晌他又问我,你们这些画画的,出来之后都干什么呢?他从后视镜瞥我一眼,补充道,除了做老师。我说,也有干设计的。他说设计好啊,赚钱。我笑笑,不置可否。
我带冯一加去了通州一所离画室最近的医院。她很虚弱,我让她在椅子上坐下,帮她挂号,排队,陪她抽血,做检查。医生说是甲流,给她开了药。我把袋子里的药一个个给她说明,告诉她哪些药得每天吃,吃几次,一次吃多少。她木然地盯着我手里的药盒,点头。她看起来很沮丧,我猜测大概是因为明天中传的初试她没法参加。
我想安慰但拿不出理由。我不了解冯一加。
在画室,他们管冯一加叫“加哥”。学生之间有那样的传统——无论男女,只要画功过人的一律称“哥”。在“加哥”之外还有“琦哥”和“雨哥”,或许还有更多,但更多的我暂未形成印象。简言之,冯一加是班里名列前茅,备受瞩目的学生,也是有点麻烦的那类。她是复读生,去年被父母送来画室的时候还几乎零基础,却只用半年时间就冲刺到了山东省美术联考的高分——名副其实的黑马学员。但她去年没参加高考,原因不明。
我只是一名代课老师,无需对学生的情况太上心,甚至没必要把班里的学生都认全。但我记得冯一加。不是因为她画得好,也不是因为班里的学生总是提到“加哥”,而是因为班里只有她可以未经批假就不来上课。由于先入为主地断定了这学生和我有过节,加上我原来就不喜欢特权学生,因此对冯一加抱持了更深的成见。主课的史老师却似乎对她很看重。每回碰见我,史老师都会问问冯一加,还有冯一加隔壁的女孩——于欣琦的情况。于欣琦是央美附中的,基本功扎实,设计素养也相当不错,当然最重要的是——她情绪稳定。我对于欣琦很是赞赏,对冯一加则用委婉的方式表达了我对她学习态度的质疑。但史老师对冯一加的宽容超乎我的想象。
史老师说:“如果发觉她累了或是情绪不对,就由她去吧。”
我想不通什么叫做“由她去吧”。史老师究竟是想让我放任她的情绪不管,还是顺应她的情绪多加照顾。对他人的痛苦熟视无睹这种事我实在做不出来,于是在送冯一加回去的路上,离画室还只剩不到五百米的时候,我忖量了一下措辞。我告诉她,当年我孤注一掷,除了在北京的学校哪里也没报。更准确地说,我当年只考了北电,央美和清美。
“都过了吗?”她问。
“只过了央美。”
“可那是央美。”她咕哝道,“我没你那么厉害。”
“你比我厉害。当年在画室,我是最不被看好的那个。”我并不完全走心地说,“所以,你都会过的。最终选择权在你。”
冯一加疲惫地抬眼看我,说了句谢谢。
我目送她走进画室的大门。那是一对足足有四米高的铁门,围墙很高。铁门正徐徐将那个羸弱的背影关进方方正正的,已然漆黑一片的寂静里。中庭的银杏树一片黄叶也不剩了。北京已经进入深冬。
接到这份代课的工作时我正急需一笔钱。为了毕业设计和之后的工作,我得买一台新电脑。中等偏上的配置一套下来也得要一到两万。但这是笔不可省略的开销。之后的工作——我比同龄人要更早地开始思考这些。因为年初顺利地和小我一级的学妹谈上了恋爱,在学期初我就和她一起搬到了离学校不远的小区外住。我们分摊房租水电,自己打扫和做饭。在学校课程之外,我从老师那儿接一些散活儿,也做助教,还没毕业就有一些收入,这让我有了一种可以脱离父母,独立生活的底气。
显然,出国留学于我的情况而言是不现实的,最理想的毕业前景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找一份美工类的工作。或许,更理想的是在一家游戏或影视公司呆一段时间,就回家乡开一家蛋糕店。“美术不是刚需,但人总得过生日啊”——我玩笑般的语气这么和女友说,只有自己知道这是某种切实的考量。我们都是辽宁人,都不喜欢北京,受不了南方城市的潮热,也看不惯上海的势利。等凑到了钱就回东北——这算是我们的共识。
八月,我第一次去给学生上课的时候,那时我还有点教学理想。尽管只是临时教师,我还是备过一两次课,想在应试技巧之外讲点别的,回答一些诸如“设计是什么”,“为何世界需要设计”之类的宏大命题。但教学科长说,这太深了,像是给美院学生听的课,而不是这群高中生。我困惑地回话,他们不就是未来的美院学生么?
“虽然很遗憾,但在他们考入美院之前,尤其对于只剩下三个月时间备考的学生而言,讲这些内容的效果,不如多背几张稿。”
是的,背稿。我也是那么过来的。
所以我的工作很简单——解读考题,分析考卷,提供参考,协助改稿,监督背稿。在前期,有大量的时间,我在教他们如何在拼趣或是各种灵感平台上找漂亮的图片,然后怎么把它聪明地“抄”到自己的“库”里。我偶尔感觉自己在做着完全违背美育初衷的事,但在接触了更多学生之后,我逐渐掌握了非常现实的情况:那些更需要通过读设计专业来找工作的孩子,往往因为家庭的经济状况而无法支付昂贵的设计课程费。而那些家庭条件足够支撑读纯艺术专业的孩子,却往往受成长环境影响,因为有着更加敏锐的设计触角而选择学设计。
对于只能给他们提供参考答案而无法带来更多,我深表遗憾。
星期天的下午有一门随堂测试。冯一加在考试开始的五分钟之后才进课室,带着几声咳嗽。她笑脸回应身边“加哥”“加哥”的问好,视线越过一排排的人头开始浏览屏幕上的模拟题。考题是教学科长布置的,和人工智能与未来生活相关。这对于他们来说应该不难。这类型的题目——在上次课的时候我就讲过了,所有这种和未来技术相关的题都可以套用一个构图,甚至连细节都可以不变,只需要改改文字说明。
冯一加一直在和空白的纸张战斗,打了好几个草稿最终又擦掉。这时她隔壁的于欣琦已经把构图画好了,正在用铅笔写标题的宋体字。我回忆起自我接手这个班的设计课以来,她就不太上课。或者说,过去我也缺乏对她的关注,所以我不确定她手头上是不是已经有一个或两个考试时可以套用的稿子。我不知道这时候走上前去给予帮助对于其他学生而言是否存在不公,但她是个还在生病的学生。
“病好些了吗?”
冯一加嗯了一声。
“你有已经过关的稿子吗?”
“上次那个被你否掉了。”她说。
“那是你唯一的稿子吗?”
“是。”
我在心里数落了一番自己的马虎。我想当然地以为他们手上都已经至少有一张成熟的,可应对考试的万能稿子了,没曾想忽略掉的是史老师最为关心的冯一加。我把冯一加领到走廊上。阳台风很大,我没带外衣出来。但我无暇顾及此。
“没有稿子,你得和老师说啊。”
“我不打算考央美了。”冯一加说。
“不考了?”我差点儿要气晕过去。
“我觉得,自己应该像许老师说的,就主攻那些有把握的。”
“啥意思?”
“孤注一掷有时候胜率更大。”
“不是。你可别曲解我的意思啊。”我说,“我也没让你放弃央美啊。我是在肯定你的实力。”
“我在这方面没有天赋。我看不懂央美的考题,也不会套稿。我只擅长画那些放在桌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
我知道,我知道她是这样的孩子,缺乏想象力,没经受足够的素养上的培育,因此审美还略有欠缺。其实最为致命的是——她缺少一点儿灵通——也许是有的,只是还未开窍。可画室里大多数是没天赋但有恒心的孩子,她比那些孩子还强一些,至少有天赋也有恒心,因此不能放弃希望。
“你必须得考。”我说,“不会套稿子,我教你怎么套。没有稿子,我给你。”
冯一加的视线退至我身后,不说话了。我回头见是史老师。
“史老师。”我找到救星,“冯一加说她不想考央美了。”
“为啥?”
“她没信心。”
“山东省联考状元对自己没信心?”史老师说。
“我靠,你是联考状元啊?”我惊呼。
“冯一加,你要没信心,谁敢有信心。”史老师又说。
“校考和联考又不一样。”冯一加嘟囔。
“这样,我今晚给你一张稿子,你就背这一张。”我说着翻起手机相册,找到一张四年前我没能用上的稿子。
“群里这个头像是你对吧,你通过一下好友。”
“通过了。”
“发你了。”我说,“你今晚先试着套,不会套再来问我。”
“赶紧谢谢许老师。”史老师说。
冯一加别扭地向我道谢,转身进了教室。
“她文化课咋样?”我靠在栏杆上问史老师。
他用手比了个六。
“六百?那上北京的学校绰绰有余了。”
“她只想上清华。”他说,“说是小时候在清华园门前的一棵树下坐过,有感情。”
“啊?”我没绕过弯来。
“神神叨叨的。”史老师说。
“我当时也放过狠话。”我打了个喷嚏,接着说:“我说我只考央美本院。城院在燕郊,连北京都不是,我才不去。结果现在在燕郊上学,否则没学上。”
“是啊。还好我让你报了城院。”
冯一加几乎是原封不动地誊抄了我发给她的那张稿子。当然,很有可能这是她的一种反抗手段。尽管如此我也懒得和她计较。毕竟我要做的只是把课好好上完,确保她会去考试。那晚我连夜帮她改了稿子,翌日告诉她,考试的时候若是押中了题,直接用就好。
平安夜,画室给每位学生发了苹果。晚自习的时候慧姐顺势布置了写生苹果的三个不同角度。有学生举手表示这是不地道的,因为画了这苹果,就不能吃了——大家都知道画室里流传着那种传说:吃了静物就考不上大学。慧姐不为所动。据说现在她写的同人小说是长篇,当下已经到了收尾阶段。
我清点了一次作业,确认收齐。此时看见冯一加提着水桶从教室前门进来。她的颜料盒是班里最干净的,因为她每画完一次就会整理一次,将脏了的颜料毫不心疼地全部挑出,替换成新的。她座位的后面整整齐齐地码着一盒盒未开封的马利和温莎牛顿的颜料。总有学生向她借白颜料,她也总是很大方。
“这次作业画得不错。”我经过她的时候对她说。
“不愧是加哥。”于欣琦说。
“不愧是加哥。”其他学生也跟着起哄。
在那之后,我和冯一加的关系有所缓和。我想那不是错觉,因为她开始和我说话了——不只是聊关于考试的事。
课前休息时我们聊天。她告诉我,她和于欣琦是画室里最好的朋友。后来她又告诉我,她其实不那么喜欢于欣琦,因为她怀疑于欣琦抄她的色彩。她告诉我,她其实对班里从内蒙来的那个戴眼镜的男孩子有好感。又告诉我,她对班里那个北京的短发女生也有说不清的喜欢。她说,她好像总是通过这样的方式提起来教室画画的兴致,其实她也没有真的喜欢上谁。她和我说,她不喜欢让老何帮忙改她的素描,因为她讨厌槟榔的味道。但她又同情老何,因为她前几天看见老何和他的女友在摩托上吵架,最后她抛下他,自己打车走了。后来老何一直很低落,可能是分手了。她还和我说,她知道史老师给她悄悄开了许多后门。她也知道,那是因为史老师担心她做傻事。
什么傻事?我问。
弃考。她说。
*
放假前的最后一堂课,工作室的老师没和我们聊毕业设计的事,只是挨个问我们:
“你的理想是什么?”
我实在很难理解他为何要在理想已经近乎破灭的,疲于找工作、考研或保研的四年级问我们这个问题。但在场的同学还是装模作样地各抒己见。有人刻意讲得很落地和务实,也有人发自内心地表达了对社会的奉献精神。我是刻意表现得务实的那一类。
中间有一名女生说:“想要早点退休回家养鱼,想过平静的生活。”
这句话惹来一阵哄笑。
在这个阶段谈野心仿佛成了一种羞耻。但至于是否还存在野心和理想这件事,我也已经变得模棱两可。老师没对任何人的理想发表评价,只是问我们知不知道实现这些的基础是什么?他没等我们思考就自答:
“钱。得有钱。”
他说,犹太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他们最明白赚钱的道理。《塔木德》这本书啊,你们有空得看看,实在太精妙,太智慧了。这个社会就是这么运作的——没钱谈理想是空谈,这是现实。工作和理想得区分得开,越早了解到这一点越好。
那一刻我理解了他的提问不是为了聆听什么,只是为他后续的观点作铺垫。是的,他的话相当正确,也正是这两年的我在奔波于作业、奖项、兼职和费力不讨好的创新创业大赛中意识到的。可为什么我听得如此不是滋味——以至于反感、厌恶、想要呕吐。或许是因为听到这种话的场合居然是在本该是象牙塔的校园里,或许是因为在一个象征最高水平的学府里,我们居然不聊学术,而只是大谈特谈金钱。
我开着电脑,在他一连串无聊的长篇大论的背景音中检阅邮箱。果不其然,投出去的工作简历没有得到任何的回应。我感到疲惫,合上电脑。
学校的课程一周只剩下一节,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待在画室。女友为了回去给姥爷庆生,早就请好假订了回辽宁的机票。而我因为代课的关系,春节前都无法回家。不过在画室,我可以和学生聊天,聊游戏,动漫,美剧——这些都是令人愉悦的。但我很快发现,冯一加已经两天没来画室了。我问老何,老何说她病了,回去休息几天。我想她身体底子是不太好。要知道,健康也是一种天赋。在艺考面前,这种天赋也极其重要。
回寝室吗?我问。
回家。老何说。
冯一加没来教室,这对我来说已逐渐变得寻常。可我还不能习惯她不在画室也不在寝室。回家——我还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她这几次的设计作业,进步特别大。”我对老何说。
“她有悟性的。”他点点头说。
“她什么时候回的家?”我实在按捺不住好奇。
“前天吧。”
“回山东?”
“对。”
“还会回来吧?”
老何不解地看我。
“当然会回来。难不成不考了?”
“也对。”我笑着说。
事实证明,我对于冯一加回家这件事确实是小题大作。她第二天就回来了。像平常一样,她第一个来教室,把所有的铅笔削尖。中午和于欣琦一起去吃饭,午休偶尔留下整理颜料盒,傍晚披着没吹干的头发来上设计课。
没什么不对,没什么不好——可正因为这样,我愈发感到不安。我消解这种不安的方式是夸赞她——说她又进步了,完全理解了。说她发挥稳定,画面干净。
下课后,她问我要不要去超市。没等我回答,她就说,许老师,你得去。因为我要请你喝咖啡。我说我晚上不喝咖啡。她笑着说,那就奶茶。
夜里下雪了。这是今年北京的第一场雪。不仅下雪了,还下得很大。学生在庭院里纷纷张开双手想要接住轻飘飘的雪。我捧着从保温箱里取出的盒装热奶茶,她手里拿着罐装的热拿铁。我们坐在庭院里闲聊。
冯一加说,她觉得欣琦是会上央美的,雨哥能去清美——对于这两点她非常清楚。
那么你呢?我问她。
她说她哪里也不会去,她累了。
我当她在开玩笑。
“大家都很累。”我说,“考试累,上学累,上班更累。活着就很累。”
“怎么也得过了这一关才是啊。”她伸了个懒腰,咖啡险些洒出。
“如果我总是在高考面前认输,就好像地缚灵一样,无法逃脱重复自杀的诅咒。这样很难看,你说是吧?”
“没那么可怕。”我说,“我的意思是你当然不会。”
“不会什么?”她问。
“不会认输。”
她笑了,说,是啊,她不会轻易放弃去清华美院的梦想的。在她小时候经过清华园门前那棵树的时候就有那样的直觉,她感觉到一种召唤,所以她觉得进入那个校园里念书,是迟早的事。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想到史老师说的,如果发觉她累了或是情绪不对,就由她去吧。于是我对她说,你该休息一下的,这两天的课你都可以不来——如果你累了的话。
她向我点头,和我道晚安,我目送她回寝室。
回到燕郊,我躺在床上如何也无法入眠,于是披上女友给我买的及膝长羽绒服到小区楼下散步。公寓门口新开张了一家酒馆,门头挂了一盏红灯笼,上面用书法体写了“江湖边”三个字。我走进去,点了一杯桃花酿和一小碟拍黄瓜。
等待的时间,我无意听见老板和隔壁桌顾客的对话。
是那位女顾客先开的话头。她自称是一名编剧,说想和老板聊聊天。老板说,好。编剧好,现在这个时代正需要好编剧。女顾客想必是对号入座了对方口中的“好编剧”,因此而喜笑颜开。在酒上来以后,他们谈话的内容还是时不时传入我的耳朵。我因此得知老板在广州打了三年工,去云南开过店,但很快倒闭了,又去宁波,做一些商品小生意,攒了点钱才来了燕郊。他有个女儿,八岁,被他送去了武当山学武。
哇。女编剧说。很有勇气啊。
老板说,我自己的基因还不清楚吗?显而易见,我女儿不是学霸,没有艺术天赋,写作文也一塌糊涂还不爱看书,就好动。学武她至少开心啊。
那么以后怎么办呢?我居然开始为一个陌生的孩子担忧起这样的问题。就像担心我的未来,担心冯一加的未来——那么以后呢?找到工作以后呢?考上大学以后呢?
离开酒馆的时候,门前的雪已经有脚踝那么厚了。
我去画室的频率比之前更勤了。一方面是我害怕无所事事,另一方面——自那天在雪夜里的谈话,我从冯一加积极的腔调中品味出了某种无可救药的消极。我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不知道此时她究竟是在寝室休息还是回了家。我想我应该要因为冯一加听进了我的话而感到高兴,可这一回,她已经三天没来教室了。我为她的情况心神不宁,直到史老师在走廊里找到我。
冯一加不会来上课了。他说。
“真不考央美啦?”
“她不考了。”他说。
“这是什么意思?”我追问。
“休学一年。”史老师从口袋里摸出烟。
我愕然。
“那今年的高考呢?她也不参加了吗?”
他耸肩。
我心中顿时升起无名怒火。
“她可是今年的联考状元!人不能次次考状元。”我有些激动地说:“这不是太可惜,太遗憾了吗?”
“我带了二十年艺考了,情况就是这样。”他抽了口烟,朝灰色的天空呼出白雾,“考题是不确定的,规章制度是不确定的,但,学生——才是最不确定的。你知道吗?经过这二十年的观察,我只相信一件事——未来,这里不会再有好的设计师了。”
当然不是。
我想反驳他悲观的看法,但此刻就连反驳的理由都变得不确定了。换作是过去的我,我会有十足的信心,拍拍胸脯告诉他,我就是那个好设计师,只是需要一点儿时间。我们不赶时间。可如今大家都这么着急,都这样赶时间,没有谁再愿意等待了。
手机伴随着清亮的消息提示音兀自亮起。那是一封新邮件,一家游戏公司实习面试的邀请。我打开那封邮件——简历经过多次辗转,最终发来邀请的不是我申请的岗位,也不是我意向的工作地点。即便如此,我还是接受了被安排在一月三号的线上面试邀约。
已经是新的一年了。
现在看来,这大概是唯一确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