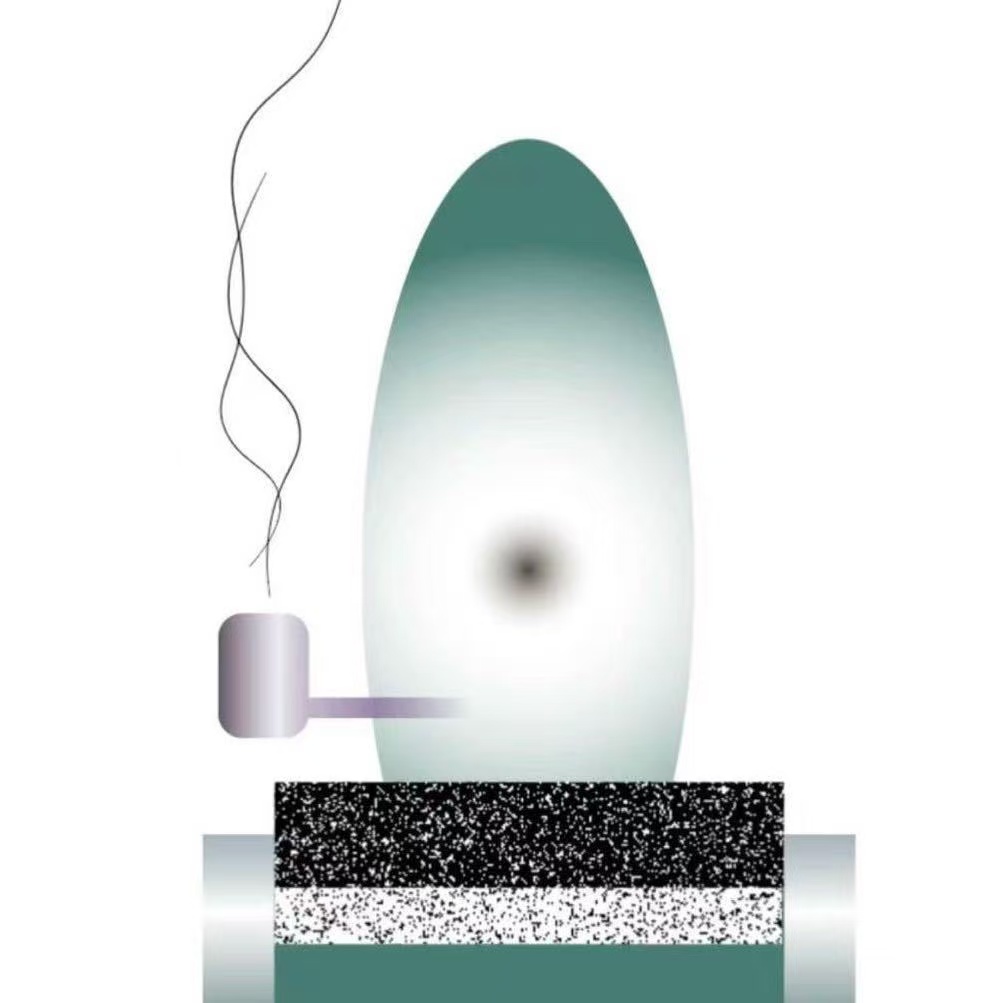人会因为什么缘故结婚?人在异国,祎雯因为偶遇孟圆而开始思考这个问题,有的选择并非为了获得标准答案。
祎雯坐在大叻火车站站台旁的椅子上解决早饭——夹着松花肉肠的越南法棍面包和一杯冰咖啡。再过十分钟,她就要背上她的老伙计在这趟前往灵福寺的火车上演奏了。
三个月前,她也是这列观光火车乘客中的一员。她把当时在火车上驻演的萨克斯手认成了中国人,起因是这位萨克斯手和一名中国旅客说了几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后来才知道,他是土生土长的越南人,只不过在学校里学中文。他叫做Minh。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在空气中比划了一个“明”字。Minh在河内上大学,在大叻做暑假工。“这种工作不是像童话里的一样吗。你们还缺人吗?”祎雯说。Minh哼笑一声,“等你在这儿工作几天就知道了,没有童话,只是一份工作。而且没有人会在这里一直做下去的。”
祎雯大概也不会想到,一周后她真的成了火车上的提琴手。得到这份工作的时候,她在大叻还没住处,只好在青旅过渡五天。那五天她的下铺每天都是不同的人——几内亚的老大哥,印尼妹妹,日本男高中生,从美国来的油管博主……她关注了那个只有小几千粉丝的博主的账号,他发的视频基本上都和旅行相关,但是剪辑制作都并不十分专业,内容也谈不上有趣。不过在她退宿的时候,这位年轻的博主送了她一本有七公分厚的越南旅行指南。她想说在小红书上其实就能找到更详尽又时髦的攻略了,但她不想扫兴,所以满面笑容的同时很珍重地收下了。在大叻,祎雯买了台二手自行车,学着她见过的一名旅者的样子,把那本厚厚的旅行图册用绳子拴在自行车后座上,发觉这才是这本书的正确用法。现在她去上班的路上都像是去旅游了。
在Minh回河内上学之前,他们经常在火车站聊天,聊天的内容通常是中文,音乐,还有火车上的八卦。在一次收工的傍晚,Minh问祎雯杜拉斯在中国是不是很多粉丝。“为什么这么说?”祎雯问。
Minh捋了捋胸前并不存在的两条麻花辫,“很多中国女孩子的打扮就和杜拉斯那部电影里的一样。”
祎雯笑起来,“我懂你说的。”
他们每天在火车上演奏的曲目几乎是不容更改的,但在曲目不变的基础上可以自由发挥。这种有限度的即兴空间就像车上的乘客一样,日复一日——韩国的大爷大妈,日本男高中生,退休的欧洲人和度蜜月的情侣,可在此类基本固定的人群的基础上,又有着不同的组合——住安娜曼达拉别墅度假村的和住青年旅舍的总是散发出截然不同的气息。
这是她在越南旅居的第三个月。在越南呆了九十多天,仍然一句越南语都不会说,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Minh的中文实在说得太好了。平时在别的场合,她也更习惯用不大地道的英语和同样英语水平一般的越南人沟通。不得不说,Minh回河内的那天她是有点想哭的,一想到这段时间的快乐大部分源自于Minh,她就开始为之后枯燥的工作时光哀悼了。不过Minh告诉她,他加入了河内一个爵士乐团,钱不多,但可以搞创作。那个乐团经常去外地演奏,最近的一场就在大叻。他眨了眨左眼,“到时候你会来看的吧?”“当然。”祎雯说。
Minh所在乐团的表演正是在今天,周五晚上九点,在大叻市中心一家爵士酒吧。怀抱着见面的期待,祎雯很有动力地在十点二十五分上了火车,开始给提琴调音。从车厢敞开的窗户中,可以看见远山顶部的黑云和澄澈天空形成了一道分界线,而那道如刀疤一样的分界正在朝这个方向挪移。雨很快就要到他们身边来了。哦,讨厌的雨季。祎雯在心里暗骂。她还特意为今天晚上的约会穿了新买的羊皮浅口单鞋呢。
如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在列车启动之后,她按曲目单上的顺序演奏《秋叶》《卡萨布兰卡》《加州梦》《斯卡布罗集市》《柠檬树》——拉奏的间隙,她留意到一个靠窗的女孩,女孩戴着窄椭圆状的黑色墨镜,正专注地聆听音乐。即便看不见她的眼睛,祎雯也能确定——那个女孩相当,相当地专注。女孩专注于音乐多过于窗外的风景,她沉浸在一段时间当中。这样一位听众的存在让祎雯比过去的任何一天都拉奏得更加投入。她想到Minh曾经对她说:“没有一个真正搞音乐的愿意一辈子在火车上驻演的。”所以他要去那个“可以搞创作”的地方。不过到底什么是创作呢?祎雯想,她现在难道不是在创作吗?为那个墨镜女孩。她因为感受到她的悲伤而弹奏悲伤,这不是一种创作吗?她没有要成为音乐家的那种渴望,能够拉琴已经是她为自己争取到的最大的自由。她本科在北京读金融。后来违背父母意愿,在悉尼一所综合大学学了音乐——那个她心心念念、却与原专业毫不相关的方向。祎雯自知天分不高,悟性也不足,可毕竟是真心喜欢。托父亲的一些关系,回国也能在国家大剧院乐团演奏,常年不见天日地在地下室排练,每天要补充维D和鱼油。今年才终于舍弃一切,来到越南。
火车靠站的时候黑云也降临了这一片天,雨在任何一分钟都可能降下来。祎雯收拾琴包的时候,墨镜女孩走过来和她搭话:
“你拉得真好。”
“谢谢。”
“《卡萨布兰卡》,我很喜欢这首歌。”
祎雯回以礼节性的微笑,“你怎么知道我是中国人?”
“在越南的中国人不难认的。尤其你是北方人吧。”
“北京人。”
女孩抿起嘴角,“我姐姐在北京工作,但我只去过一次北京。前年冬天,下了一场很大的雪,那次我是和我妈妈一起去的,去了颐和园。”
“颐和园啊,我家住得离那儿不远。”
“那里的雪景真漂亮,就是太冷了。”
“是啊。很冷。”
“我妈妈昨天去世了。”
祎雯很震惊,却只能回复她:“我很抱歉……”
“对不起,我不想让气氛太沉重的,但我实在是没别的人可以说这些。不过你的音乐给了我一点安慰,真的。”
“你可以和我说的,我有时间。”
“你待会儿还要继续在这车上拉琴吗?”
“已经结束了。今天只有这一个班次,没有回程。所以我有一整天的时间。”祎雯轻快地说。
墨镜女孩想了想,“灵福寺你肯定已经去过了吧?”
“没有哦。”祎雯说。
“那要一起走走吗?”
祎雯背着琴,在路上和女孩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女孩名字叫孟圆,是惠州人。她说,其实昨天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她大哭了一场,实在是难以接受,尽管她心里知道总有那么一天会到来。但到了今天,她有一种解脱感。过去她觉得到广州工作都是一种远行,现在她觉得惠州没什么值得牵挂的了。
“我从今以后再也不是谁的女儿了。”孟圆说。
她父亲很早就离开了,母亲一人带大她和姐姐,姐姐远嫁到了北方。她除了姐姐工作的城市北京,没到过更北的地方。可她就要到英国去了。
“去读书么?”
“去结婚。”
“结婚?”
“是的。我未婚夫是英国人,他想带我回他的国家生活。”
祎雯点头。 “那也挺不错的。”
“他只是老了一些,但对我很好。”
“他多大年纪?”
“快七十岁了。”
“你呢?”
“明年三十。”
祎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他身体不好,前妻去世很多年了,他只是想找个护工而已。可在英国,尤其在伦敦,护工是很贵的。外人怎么看,我不在意。我有朋友说我很蠢,说人家找的老白男可都是有钱人,他只是个垂垂老矣的穷白男。可至少——他来惠州见我的时候是很真诚的。我不懂英文,他也不懂中文,可我听懂一句话,他说我漂亮。他不是用那种色眯眯的方式说的,他觉得我似曾相识,又说我像是他的女儿。他用翻译器告诉我,他认为遇见我是很幸运的。你知道,这些说辞其实对我没有用处。一个男人要把一个女人拐走,所有好话都可以脱口而出。我虽然没谈过几个恋爱,可这点觉悟还是有的。总的来说,他不是那种危险的男人。他是个好人,只是老了。”
“你们认识多久了呢?”
“一个月。”
“一个月!”
孟圆没理会祎雯的吃惊。
“我们在软件上认识的。一个T开头的软件。我英语不好,是一个懂英文的朋友给我俩说的媒。他是个有轻度阿尔茨海默症的老人。”
祎雯蹙眉:“且不评价你那位朋友。可是,和一个几乎不了解的人结婚,还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这不是很冒险吗?”
“和谁结婚不冒险呢?”孟圆说。
祎雯不语。
“这种病恶化得很快。说不定不久后就会忘记我名字。”孟圆浅浅笑了一下,“我们会结婚,但很快——对于他来说,我就只是个陪护的女人,或者是一个陌生人,就像他对我而言那样——一个陌生人。”
“问题是,他没有钱。没有钱,在哪里都不好过。”
“也不是完全没有。他手上有一笔存款,两万六英镑。不多。但那笔钱在他离开之前都是不会动的。他没有子女,因此承诺这笔钱最后会给我。当然,我也不会为了图那些钱要他早逝的,毕竟那真的没有多少。”
是啊,所以你图什么呢——祎雯欲言又止。
片刻的沉默。
“至少,你该知道他是做什么的吧?”祎雯问。
“他是个写小说的。”她说,“小说家——在英国,这样的人是不是非常多呢?至少在中国,在惠州,或者在广州,我身边没有那样的人。我上的是职业专科学校,读的经济管理,现在也只是在不同的行业里打杂。做过一段时间电商,直播卖货那种,可是我口条很一般。”
“或许你的天赋在其他方面。”
“是啊,其他方面,可能吧。你知道吗?我偶尔会觉得并不是每个人都会那样幸运地认识到自身的天赋。就像——你的天赋,明显是艺术方面的。而我的姐姐,她是个高中物理老师,但我认为她的天赋很可能其实是在别的地方,像是潜水之类的。因为我记得小时候她能在泳池里憋气三分半钟。可这种天赋好像没什么可发挥的余地对吧?”
祎雯轻笑起来,“那可不是。关键时候能救命呢。”
“可我不会为了这个祈祷来一场大洪水的。”孟圆说。
祎雯伸手,轻轻掸掉她手臂上的一只隐翅虫。
“谢谢。话说回来——我不懂英语,甚至连中文的小说也没看过几部。但是我未婚夫的小说,我想我会把它们慢慢看完的。”
“哇……这很浪漫。”
“浪漫吗?”孟圆摇头,“我不觉得浪漫,我只是觉得可惜。他说他写了一辈子小说,可他之后恐怕是再也写不了了。你说他会忘记吗?他笔下的那些故事。”
“他的那些小说出版了吗?”祎雯问。
孟圆摇头,又停顿了会儿,“不清楚,我没有问。可如果他是个成功的小说家,应当不至于找我这样的女人结婚吧。”
“你这样的女人怎么了呢?你是个勇敢的女人。”祎雯说。
在通往灵福寺的巷道,一排高低有致的一户建前,孟圆终于摘下墨镜。她注视着祎雯,眼角绽出今天第一个发自内心的笑容。
“真奇怪,这句话在此刻对我来说很鼓舞。你是第一个说我勇敢而不是愚蠢的人。”
祎雯并不是一个对寺庙感兴趣的人。她对宗教无感,也无求于神明。在北京的时候,祎雯去过一次雍和宫,只是为了陪朋友给一条手绳开光,为了扭转工作上的霉运。朋友说雍和宫很灵。去完那一周,她的工作果然迎来了转机。但祎雯不好说那是不是手绳的作用。总之,她一直在往返灵福寺的火车上演奏,却一次也没有去过灵福寺。不过,灵福寺的彩陶马赛克贴片倒是让她觉得新鲜。尤其是看到西天取经的塑像和满墙的汉字经文。比起在大叻,她觉得自己更像在云南,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在用菊花花蕾制成的巨型观世音菩萨像面前,孟圆很虔诚闭起眼睛,做着祈祷的动作。
“你信佛吗?”祎雯问。
“我妈妈信佛。”在句末,孟圆吐出一丝透明的叹息。
在七层宝塔的大钟前,孟圆写下了三个愿望。三个愿望都和她的未婚夫有关。大多都是关于健康,快乐,平安这类朴素且毫无想象力的主题。祎雯问她怎么不为她自己祈祷。孟圆说,我为他祈祷就是为我自己祈祷。虽然我还不完全了解他,可我很快是他的妻子了。
“如果他的寿命足够长,我可能会有一半的生命围着他转……”见祎雯脸上显出可怖的神情,孟圆打着圆场说:“欸,别倒吸凉气,我没有在讲鬼故事,而且这不可怕。我觉得这是浪漫的一种,你觉得呢?”
“浪漫吗?”祎雯耸耸肩,“这听起来更像诅咒吧。”
在孟圆敲钟祈福的时候,祎雯也写下了两个愿望:
希望慢慢慢慢慢慢地变富,
希望所有的蟑螂能从世界上消失。
祎雯敲了六遍钟。其中有三遍在为别的旅客当摄影模特。
下雨了。
雨水有所保留地从厚重的云里落下,在灵福寺的范围内还算温柔;可一离开寺庙,那雨的性情就变了。要去哪里呢?她们没有问彼此这个问题,只是并肩疾走,没有谁在领谁的路。直到摩托车的尾气都在雨中变得黏稠,孟圆才用手挡着前额,问祎雯:“我们要去哪里呢?”
“去找一家咖啡厅,好吗?”祎雯征求意见道。
“好。”
她们穿过一条卖杂货和廉价衣物的街道,在朦胧的狗吠中拐进一条上行的山路。那是一个很陡的坡,在雨后,土路变得很滑,而那坡路又相当的长。祎雯突然怀疑这时候去山上那家咖啡馆是不是一个对的决定。祎雯回头看向孟圆,孟圆非常认真地盯着脚下的路,脸上没有露出丝毫难色,像接受她身上的任何命运一样,坦然接受了祎雯不靠谱的在雨中上山的提议。
山上有一间佛学校,建筑楼前立着越南国旗和几面宗教旗帜,楼体上的字已经很苍老了。一只乌鸦从深色的柚木中窜出,甩下一声短促的鸣叫。
“真不好意思。”祎雯说,“我不知道这个路这么难走——不过,快到了。”
实在是失策,那家咖啡馆除了风景之外什么也没有。饮品是最基础的老几样,没有吃的。此时已经是下午一点,照这个雨势,她们要在这里待到傍晚了。
山上只有她们两个人,老板娘做完咖啡就靠在躺椅上刷Tiktok了。短视频的音乐渗进黏腻的空气中,电扇摇着头,老式收音机里断断续续地漏出越南电台的歌声。一首听起来像法式乡间民谣的越南语歌牵住了祎雯的思绪。
“之前总是我在说。”孟圆在电台换曲的时候开口,“现在我有点好奇——你为什么会来越南呢?”
“这里便宜。”祎雯的笑容中透着一丝不确定,“而且……安全?”
当然,这都不是她来越南的真正原因。至于真正的原因——那更像是一种迟到的青春期式的叛逆。她并不是一个计划周全的人,她不认为自己会在这片土地上长久待下去。但她也不认为自己会回去。她不知道自己会不会结婚,至于生小孩——那更不敢想象。她今年二十七岁,已经不年轻了——在国内常有人告诉她,她不年轻了。可在这里没人说这样的话,没人知道她是谁。她唯一的朋友,Minh,不会指责她做的任何选择,不会评判明智与否。没人要对她负责,她也无需对谁负责。但她迟早要回去面对她该面对的一切,她知道。她的人生就像那趟往返于灵福寺的火车一样,从来在出发和抵达之间徘徊,且她自愿滞留在那样一个维度当中。偶尔她会产生那种感觉——并不是她选择了越南,而是越南选中了她。
“不瞒你说,你是我认识的第一个音乐家。”
“我不是音乐家。顶多算个乐手。”
“写小说的就是小说家,画画的就是画家,玩音乐的就是音乐家。这有什么不对呢?”
“要是我像你的未婚夫写小说那样和音乐打一辈子交道,那么我才够胆称自己为音乐家。”
“你会的。”孟圆说。“你已经在这么做了。”
“你真是对所有人都充满信心啊。”
“是啊。包括我自己。”
“这一点让人羡慕。”
祎雯呷了一口拿铁,食指在杯耳内沿那处未打磨平整的凸点上来回摩挲。她想,如果说自己是为了逃避责任而选择一种虚无的生活,那么孟圆——她则像是为了逃离虚无,去主动拥抱责任。无论是作为护工、妻子,还是在更久之后——一个丧偶的女人,她都将为“责任”这一件事本身,去选择去爱一个人。
这究竟是一种清醒,还是一种失心疯呢?
“晚上我朋友在市中心的酒吧有一场演奏,你要不要也来听呢?晚上九点。”
“什么样的音乐呢?”
“爵士。你喜欢听爵士吗?”
“我不太懂,但我喜欢音乐。”
她的小羊皮浅口鞋在雨中泡坏了,这是那天最糟的事。但这种坏心情在她见到Minh之后就消失了。Minh无视她雨后的狼狈,给了她一个拥抱。祎雯向Minh介绍了孟圆,也和孟圆介绍了Minh。Minh和孟圆握了握手。在表演开始前,祎雯没有多少时间可以和Minh寒暄。不过她能从Minh的状态中感觉到他过得不错,一个有才华的年轻越南男人,对音乐尚有梦想和野心的大学生,那是多么美妙的一个阶段。祎雯说不清自己内心的澎湃有多少来自于Minh或是Minh身上那些她向往的特质。
在开场前,舞台上唯有器乐在场,背后的墙面上投影着城市夜景。顶部的红色灯光向下融进薄雾当中。不断有人推开沉甸甸的门进来,安静地落座。祎雯问孟圆喝不喝酒。孟圆说,你喝什么我就喝什么。祎雯问,你酒量还行吗?孟圆点头。祎雯说,那就是相当好。
她点了两杯马提尼,在表演开始前她一口也没有喝。吹小号的似乎是越南有名的乐手,唯有介绍他的时候主持人花了一定的篇幅。到Minh的时候,只是一句带过。但祎雯给了他全场最热烈的掌声。
孟圆俯身问:“主持人说了什么?”
“不知道,但我听到我朋友的名字了。”
那晚,乐团演奏的是改编版的《在宁静的湖泊》,一首二十世纪的沙龙音乐。Minh后来告诉祎雯,萨克斯的那段独奏他写了快一个月,乐团本来打算取消他的独奏部分,是他坚持争取下来的。后来他又说,你知道这首曲子原来最出彩的其实是提琴的音色吧,所以我总是想象你在我旁边演奏这个曲子的样子。这句话很隐晦,可祎雯听出来了,她没做回应。其实在得知这是Minh选的曲目那一刻,她就已经明白了。她曾对他讲过这是她最喜欢的一首曲子。她那晚多想站在他身边拉奏啊。
叫她意外的是,那晚被那首曲子打动的人不只是她一个。孟圆在这首改编曲中潸然泪下,她说,演奏得真好,尤其是你朋友吹的那个金属管乐。祎雯说那是萨克斯。萨克斯,她说,它的声音让我想到了英国的伯吉斯公园。我没去过英国,我只是听说过这个地方,我未婚夫告诉我的。他住在那里,午后常常在那里散步,写点东西。我不知道那是个什么样的地方,他说那不是一个很有名的公园,不过是一个社区公园,但经常有人在那儿露营,钓鱼或是野餐。
祎雯默不作声地倾听。
“祎雯,实话说,我不知道爱情是什么。可我在想,我是不是正在爱上他?”
祎雯摇头。她不知道。她当下对一切问题都没有把握。尤其在一杯马提尼之后,她已经有些晕乎乎的了。
孟圆第二天就要回国,她母亲的葬礼在下周举行。在散场的时候,孟圆告诉祎雯,她没能见到母亲最后一面,但她不为此难过。她庆幸母亲在她脑海中的形象很好地保持着她最有生命力的样子。母亲查出癌症是在去年秋天,医生说已经到了晚期,很难捱过冬天,但母亲把生命延长到了今年夏天。大家都说这是个奇迹。
那确实是个奇迹。祎雯说。
孟圆说,那不是奇迹。母亲总是担忧她的婚事,没看到她出嫁,她是不会安心离开的。现在母亲终于解开心头的郁结,因此可以瞑目了。
祎雯把手放在孟圆的背部,下巴贴在孟圆的肩膀上。她们在三针松下默默地拥抱。
祝你幸福。祎雯说。
我会的。你也是。孟圆说。
周一的早上,如往常的任何一天一样,在列车启动之后,祎雯按曲目单上的顺序演奏《秋叶》《卡萨布兰卡》《加州梦》《斯卡布罗集市》《柠檬树》——那是她已经非常熟悉的旋律。她闭上眼睛,左手指尖在琴弦上来回跳跃,火车正沿着铁轨在颠簸中倒退。在乘客用手掌鼓出的节拍声中,她可以很好地辨认出沉默的方位。那个沉默来自孟圆曾坐过的窗边的位置,来自她身侧,Minh曾经伫立着吹奏萨克斯的那块空地。此时,从这两处同时投来一种目光,来自上周五,来自上个月。她的脑海在音乐中展开了那种模棱两可的想象,关于孟圆和她的未婚夫,他们在伯吉斯公园散步,用并不相通的语言交谈。为了读懂丈夫的小说,她开始学习英语。她爱上他的丈夫了吗?或许,即便是那个时候孟圆的心里还依旧留存这种疑问,抑或者答案已经不再重要——她毋庸置疑会幸福。祎雯忽然有了那样的信心。
奏罢最后一个音符,火车在灵福寺靠站。一滴共鸣的眼泪迟钝地从祎雯的颧骨淌下。她想,她其实不曾真的懂得音乐,就像她不曾理解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