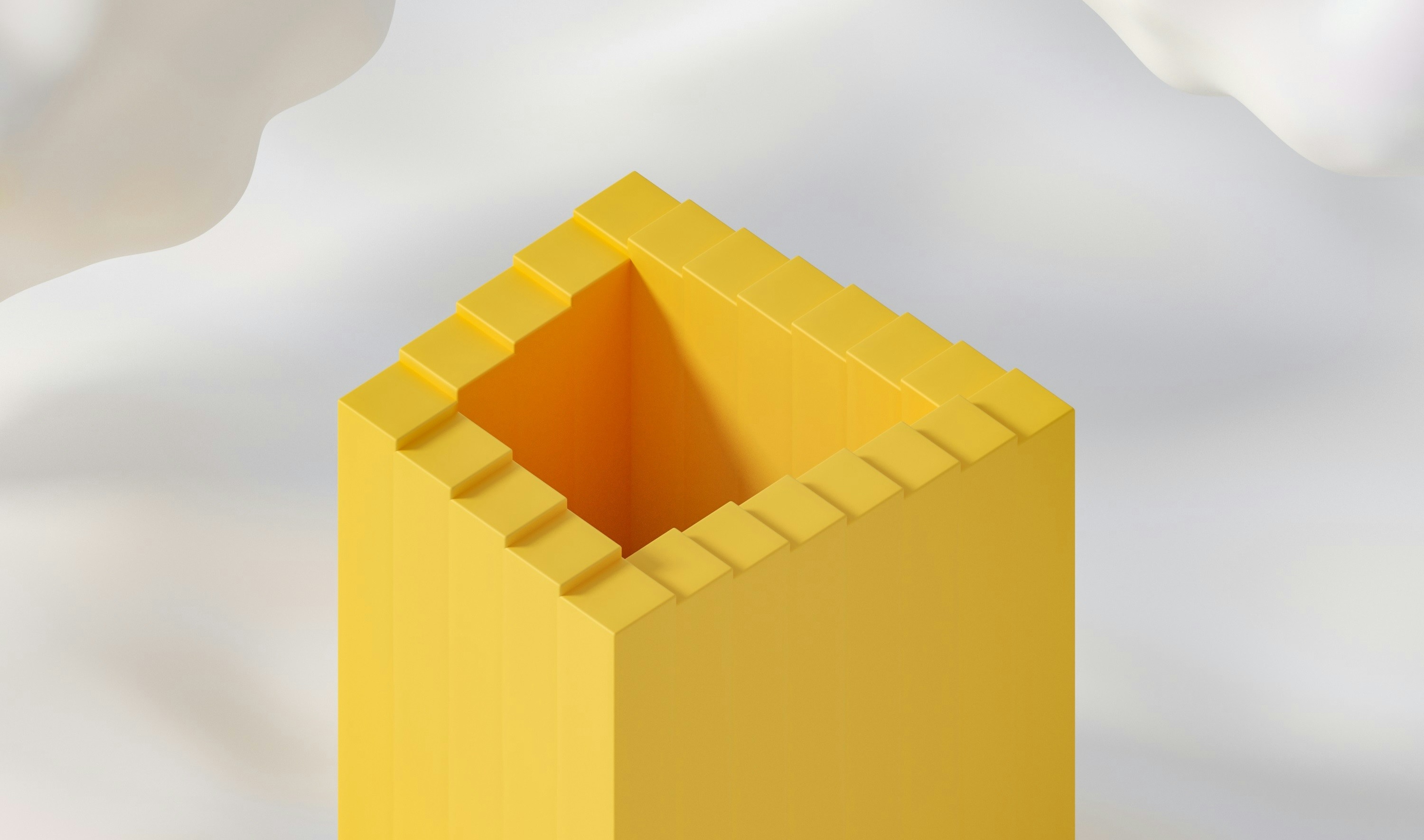
家人并非自己的选择,因此也最是劳心劳力。
2024年12月20日,周五
我把我妈送去了精神病院,医生和我说,她的疾病是因为压力导致的。我问:“不遗传吧?”
她没说话。
我说:“我不喜欢你的眼神。”
她让我去缴费。
医生肯定觉得我是一个奇怪的人,但她收了钱,应该知道钱难赚,屎难吃。而且,她会越来越鄙视我,因为我妈就是那样一个人。
晚上,我告诉老公医生要我辅助我妈治疗,说要找到压力的来源才能从根上解决问题。
“那就找啊。”他说。
她能有什么压力?她这辈子都在不停地告诉所有人她很可怜,现在我就是她讨取同情的受害者。
“但你妈确实病了,那就确实有压力呀。”丈夫说,“我们要解决问题,好好想想吧。”
好好想想吧。
1
如果要追溯到最开始,发现我妈不对劲,是因为我拿到了她的体检报告——腰肌劳损,多见于长期久坐或是干重体力活。
她已经六十岁了,也许吧,反正是过了退休的年纪,每天除了吃喝遛弯,没什么要做的。我给她请了保姆,没过半天就被她辞退了,钱原封不动地打回了我的账户上。
好在劳损情况不严重,她又再三保证会正常用药,事情才不了了之。
直到几个月后,我发现她走路的姿势越来越迟钝才开始怀疑,趁她大号的时候去检查了她的床头柜。
“一天两片,三号拿的,十五减三乘二……”我把剩下的贴片倒出来数,见数量没错,还没来得及松口气,就看见柜子上的照片。
她把自己和我爸从照片里裁了出来,平均剪成了四份。相框左上角贴着她的上半身,左下角是她的下半身,右上角贴着我爸的上半身,右下角是下半身。至于最中间,是我穿着婚纱,捧着花在对镜头微笑。
惊悚和回忆同时扑面而来。我看着我爸的脸,心想自己多久没有见过他了?
2
在我小的时候,最爱爸;懂了点事之后,又觉得他是个可恨的男人;等到他离开我们,又慢慢发觉出他其实是个倒霉蛋。
他的工资没妈高,不会做饭,不会洗衣服,很会看电视,以及在妈拖地时把脚抬起来。不过这件事他不太擅长,因为他抬不了多久就会开始抱怨。
我小时候坚定地认为,家里的一切矛盾,都是妈在没事找事。每次她把自己关在房间里哭的时候,爸都会躲进我的房间,他说:“你妈老把自己搞得很累,其实根本没必要。她一旦觉得自己受苦了,我们就都不能高兴,要陪她受罪。你长大以后可不能这样。”
我似懂非懂。
至于他们分开,也是因为妈的哭泣。
那天是妈生日,爸拉着我们去游乐园,他说:“今天的任务就是陪你妈,能不能完成?”
“保证完成!”我挺胸敬礼。
那天有一个很棒的上午,很棒的中午,以及很糟糕的晚上。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他们吵架了,我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只顾着害怕今天的快乐会戛然而止。
爸离开了一会,等他再回来,手里拿着三张摩天轮的票。
我从来没坐过摩天轮,它转一圈要二十块钱。妈让把票退了,爸问:“为什么要退?你不想坐吗?刚才不是还想坐的吗?”
妈露出不知所措的表情,在我的欢呼声中,被爸牵着往检票处走。但她依旧不高兴,因为吵架的根源没有解决。
前面排着很长的队,站一会,她说:“退票吧。”
“为什么,你不想坐吗?”
“太冷了,还要排好久。”
爸摸摸她的手,说:“你去检票亭接点热水,带着女儿去,我一个人排就好了。”
她不动,又排了一会,表情越来越闷闷的。等前面的队伍越缩越短,她越来越频繁地叹气。
“把票退了吧。”妈不知道第多少次这么说。
“为什么呀?”
“我害怕,太高了,我不想坐,真不想坐。”
爸终于弄懂了她心里的想法,整个人都轻松了很多,把她搂进怀里,说:“我怎么不知道你恐高?咱家还没坐过摩天轮呢,他们说这个不吓人的。”
“我害怕,真害怕,算了吧,算了。”妈不停重复,神情从郁郁寡欢变成焦虑,并时不时地深呼吸。
“那我把票退了?”爸问。
“你想坐是不是?”妈问。
“我想坐,你不想坐,那就算了呗。”
她又不说话了。这时,正好排到我们,检票员抽走爸手里的票,帮我们做了决定。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准确说是坐进摩天轮的那一刻,妈就恢复成了吵架前的样子,她的头一直面向窗户,对着城市星星点点的灯光、马路上穿行不息的小汽车赞叹。
“好玩吗?”爸很得意地问。
“好玩……”她说,“真好玩,真的挺好玩的。”
我看向窗外,在玻璃窗的反射中,恰巧瞥见了妈的脸,她的表情和语气全然不符——没有一点笑意,眉眼带着忧郁。我有了一种很强烈的感觉,她并没有在看窗外的景色,只是在望着自己的倒影出神。
我以为那是我的错觉,因为回去的路上,爸一直在回味摩天轮,他自己讲两句,就要问问妈,妈的回应也是处处都好,更使他兴致盎然。
然而,那并不是我的错觉,因为晚上,他们就爆发了争吵。说是争吵也不准确,他们从头到尾都没有提高过一次声音。
妈说:“我只是不明白,为什么我总要去做我不想做的事。”
“你不想坐你就应该说。”
“我说了很多次了,很多次,你不知道吗……”
“我看你也不恐高。”
“对,我从来就不恐高,我一点也不恐高。”
在她定定的注视下,爸终于露出诧异的表情,我想,这反应是妈期待的。她又说:“我在上面也不开心。”
“一点也不?”
“一点也不。”妈坚定地说,“我对它一点也不感兴趣。”
“那你就应该说!”
“那种场合我怎么说?钱都花了,人都上去了,我说不出这种话,你在强逼着我表演开心,在强逼着我不扫兴,在我生日的时候,让我忍着难过……”
“那你现在为什么要说?”爸打断她。
“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为什么总是我来照顾你们的感受!”
“谁让你照顾了?你总是在干这种事。”
后来,在凌晨两点,爸收拾东西离开了家。我站在卧室门边,看着妈捂着脸哭泣。我不知道该说什么,逃避着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3
之后很多年,我只见过几次爸。他们没有离婚,只是各自生活着,直到因为我结婚重聚,表达了祝福。
“我那个时候可怜他。”我对丈夫说,“你说,他当年要是选了一个对的人,后半辈子就该有一个家庭。”
“那就没有你了。”丈夫问,“所以你妈为什么要把照片裁成那样?”
“我怀疑……她精神可能出了问题。”我感到羞耻,“这不是正常人会干的事。”
“不至于吧,要不再观察观察?”
我沉默片刻,突然想起固定在我妈各个柜子顶端的监控器。它们是妈买回来的,但我一次也没有连接过。
两年前,妈在洗澡的时候滑倒,因为手机在外面,耽误了很久才得到救治。自此,我就总感觉焦虑,怕会发生更严重的事情。于是,我每天下班之后都会骑半个小时的车,去看一眼妈,免得她出了什么问题却不说。
冬天越来越冷的时候,妈突然神神秘秘地拉着我,指着高柜顶给我看——
“监控器?你买这个干什么?”
“这不是不想你来回跑吗。”妈局促又期待地等着我的反应,把我带去厨房、卧室、甚至厕所——数个突兀的黑色圆球扎根在房间里。
我不知道该做什么反应。
如果是我,绝不能接受自己被如此全方位,无死角地监视。从挖鼻屎,到给别人打电话,我说了什么,做了什么,即使没被实时看见,也能随时被调取出来。
“这样我干什么你都知道。”妈说。
“把它拆了。”
“拆了做什么?好不容易装上的。”妈嗔怪道。
如果是我,我更不能接受被自己的孩子如此管教,我觉得耻辱,窒息。
“把它拆了!”
妈被吓了一跳,但她还是执着地把监控序号和软件链接发送给我。
“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你自己可伟大了?”我冷冰冰地说,“别人到我们家,看见到处都是摄像头,都会觉得你在包容我发疯,你真了不起啊。”
“你怎么会这么想?”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我不会看的。”
“我钱都花了……”她不知道该怎么办。
我拿起外套拉开门,只丢下一句:“那关我什么事?”
走下两层后,我停下脚步,迟迟没有听见她的关门声。
我缓缓蹲下来,坐在台阶上悄无声息地喘息,就像她一样——她一定也坐在地板上,和我发出同样痛苦的喘息。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不想跟着她一起伤害她自己,也不想打击她的好意、否定她付出的时间和精力。我们总陷在这样压抑的怪圈里。
4
“你妈可能真的不在意。”丈夫说。
“怎么可能呢?”我很笃定地说,“她不可能不在意。我真信了她,我就完了,只要逢年过节,她都能把这事拿出来说。”
“我觉得,你在为没发生的事情生气。”
“因为我知道它一定会发生!”
我不想和丈夫辩论,拿出手机下载软件,把那一排序列号输入进去。妈并不知道监控器已经连通,她正绕着客厅迟缓地行走。
已经晚上九点了,电视没有开,房间里显得昏暗冷清。她的每一步,似乎都在我为人子女的良心上捶打。
大概走了有二十多分钟,她把衣服脱下来,拿去厕所清洗——完全没有用洗衣机的意思,拿出盆坐在小板凳上开始手洗。
我起先不觉得有问题,直到她一件短袖洗了足有半个小时,先是左边袖子、右边袖子,再是左衣摆,接着是右衣摆,然后又去搓左边袖子、右边袖子……
“你妈像动物园刻板行为的熊。”丈夫说。
我没理他,把声音拉高,听到妈的嘴里念念有词:“二十,二十,到二十就停,好吗?”
是要洗二十遍吗?
但过了一会,她又开始说:“三十,三十……”
“你知道她腰肌劳损是怎么来的了吧?”丈夫问。
是的,可是,为什么会这样?
终于,在我即将忍无可忍,要打电话过去暴露自己的时候,她停了下来,把衣服晾好,回到卧室。
她却并没有睡觉,而是开始摆放屋子里的各种东西——桌面的四个角都放上抽纸;从柜子里拿出拖鞋,四个一组排列在床的四角;两个枕头分别从枕套里拆出来,枕套摆在头和脚,枕头摆在左右手。
她直挺挺地躺在床的正中央,像是祭坛上的祭品。
她的模样因为这些动作让我感到陌生,然而她并不认为自己的举动骇人,脸上挂着某种苦涩的微笑。
5
我无数次见过这种微笑,也无比痛恨这样的微笑。因为它的出现从伴随着一些特定的话语:我没关系;你别管我;你过得幸福,我就幸福。
就像爸说的那样,我逐渐清晰地意识到这是谎言。
在我工作第一年的假期,我给自己定了去泰国的机票,妈得知之后百般阻挠,发给我抢劫杀人、器官买卖的推送不计其数。
最后,在我的坚持中,她问:“你非要去是吗?”
“对,我想去。”
“那我跟你一起去。”
“你去干嘛?”
“我不去怎么办?异国他乡的,你要害怕的。”
“我不害怕。”
“等到时候你就害怕了。”
我那个时候更像是在赌气,同意她跟着我一起去,但没有为她改变任何行程。
那场旅行,从头到尾她都没有任何抱怨,但我能感觉到她也没有任何兴趣。不管什么景点,我走她就走,我停她就停。
逛大皇宫的时候,她和导游一起坐在出口的台阶上;到了玉佛寺,她又和一群逛累了的旅客坐在亭子下,坐了有一个多小时。好像她来的目的就是看我玩过一圈,等我把她带去下一个地方。
到吃饭的时候,我挑了各种口味的海鲜,她却只顾着吃最便宜的糯米饭。我一不留神,她就吃完了一整碗,然后又去夹第二便宜,又很占肚子的煎饺。
“吃虾。”我说。
“吃着呢,吃了好多了。”她撒谎。
我忍着没回应。到走的时候,她看着桌上的剩菜问:“要打包吧?我去付钱?”
“打什么包?不要了。我付过钱了。”
“还剩这么多呢。”
“我说不要了!”
从饭店出来,妈像个犯了错的小孩跟在后面。我想和她道歉,却不知道该怎样开口。
最后几天,情况更糟,一次在海边她突然问我:“你是不是不高兴呀?”
我反问她:“你看不出来吗?”
“跟妈妈说说呀。”
“好,”我深吸一口气,“我不需要你给我省钱,我也不需要你陪我到处跑。你想做什么就去做,不想做什么就说出来,这很难吗?我真的好累,不管我做什么,你永远一副受委屈的样子。”
“我没有……”
“对,因为你靠自虐来满足自己,我们都是压迫者,你永远在妥协,妥协会让你觉得自己伟大,伟大会给你带来快感。”我越说越难以控制情绪,用手指着妈的胸膛,“你心里永远在唱道德大戏,你踩在我、爸、所有人身上搭你的戏台。”
之后,我甩下她快步走开,停下回头的时候,已经距离很远了。夜色中,妈低着头默默沿着海岸线向前,椰林下一群穿着亮色泳衣的少女,正冲着路过的白人男性飞吻。
她和周围的自由的热带风情格格不入,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碎花汗衫,无措地避让那些奔向大海的旅客。
6
“我很后悔,你知道吗?”我对丈夫说。
泰国之行的最后一天,我去看成人秀,妈不愿意去单独留在酒店。等回来的时候,她正在吃泡面。
我不知道该怎样形容那个时候的感受,尤其是她冲我微笑,问我开不开心的时刻。尤其是我打开门,看见她坐在一盏小台灯下的时刻。
酒店房门还没有关上,走廊里的灯光在各种金色装饰物上来回反射,营造出一种富丽堂皇的氛围。而屋内,我妈面前摆着一桶泡面。
我反手带上门,把走廊的光隔绝在外,一时间感觉自己正步入黑洞。
“你知道我妈那天晚上说什么吗?”
“什么?”
“她说,她想告诉我,这几天是她这辈子过得最开心的日子。”
丈夫陷入长久地沉默,把我搂进怀里。
“我干得那么糟,她却说这是她最开心的日子。好笑吗?她才是真正的语言艺术家。她要是骂我,我绝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内疚。她就用那么轻飘飘一句话,把我撵碎了。”
7
后来,我搬去和妈住了一段时间,丈夫对此表示理解。但很快我就意识到,我对她的精神疾病完全无能为力。
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举行那样的四角仪式,也不明白她把家里所有的瓷碗都收进柜子,非用不锈钢方饭盒吃饭。我只能在她做重复行为的时候打断,在她进厕所超过十五分钟后推门闯入,把盆里的衣服通通丢进洗衣机。
但这是在浪费时间,就像是面对冰箱里腐烂的食物,我在不断擦拭污水,却没有解决发臭的根源。
一个月后,当妈又一次把我晾好的衣服取下,拿去手洗,我没有暴怒,只是很疲惫地靠在门框上,怀抱着双臂看她。
她知道我在背后,却没有回头。
“为什么非要这样?”
十分钟后,她说:“不然我害怕。”
这答案我听过无数遍,我看着她的背影,也许又过了十分钟吧,我问:“你害怕什么呢?”
搓洗声,不停歇的搓洗声,泡沫破裂,水面搅动的声音,厕所的四面墙似乎在向无穷远的退去,我和她站在无边无际的平台上,成为平台上的两个小点。
“我要被公司开除了。”我说。
她停下来,很慌张地看向我。
“你这样我没法上班。”我说。
那天,我被妈从家里赶了出来,她不肯再让我进门。再往后,同样退休的姨妈开始照顾妈的生活起居。
我每天都打电话问姨妈情况,到年关将近的日子,她要回老家了,我在餐馆把红包交给她,她才犹犹豫豫地说:“你平时要多关心关心你妈啊。”
“我做得还不够吗?”
“你妈这个人轴,但是这个世界上,她最爱的人就是你了。”
“她跟你说什么了?”
“你别急呀,没什么。其实说到底,你妈这个心病还是因为你。”
见我不明白,姨妈接着说:“你妈现在只要一停下来,眼睛就控制不住到处乱看,脑袋里就不停地冒出来念头。”
“什么念头?”我问。
“就比如说吧,我现在是她,我看见桌子上这一罐牙签,脑袋里就有个声音说,把它们都倒出来,一根一根摆在桌子的四个角上。”
“为什么?”
“为什么?”姨妈叹了口气,“因为她觉得不这么做,你身上就会发生不好的事。我跟她说这是迷信,她说她知道,但是万一呢?摆了就能安心,不摆,那个念头就会越来越强烈——万一呢,万一出事了呢,摆一下就好了,别让自己后悔。”
我如坠冰窟,感觉背后发麻,丧失了所有的语言能力,甚至有些想要呕吐。我不知道自己怎么了,思维好像僵在了这一刻,拼尽全力地放空大脑。但我眼前始终有个手机屏幕,妈刻板的行为,困兽一样的举动,都缩在那个屏幕之后。
我还是不可避免听到了心底的声音:“她的痛苦来自于我。”
“不,不,不,这不是我的错,这和我没关系!”我在心里大声辩驳。可是为什么,不管是从任何角度、任何道理上我都没做错事,我却无法停止自责。
8
这几天,理智让我回避解决问题,但情感却告诉我:你没有办法入睡,不是吗?
凌晨,我从床上爬起来。丈夫被我惊醒,问:“怎么了?”
我一言不发,他看见我拿那串红色钥匙,又问:“你去那边,你妈睡了吧?出什么事了?”我推开他,把他那句“我陪你”抛在身后。
我在夜晚的风里,越走越觉得情绪翻涌,如果出门前是一分愤怒,拍门的时候就有十分。
妈显然受到了惊吓,她头发乱糟糟的,声音也很嘶哑,轻声问:“怎么了。”
“没怎么,我来说你的精神病。”
我们坐在沙发上,窗外偶尔有汽车驶过的声音。她已经完全醒来,却垂着头不开口。
我说:“我已经预约了,明天我们去精神病院。”
“你要把我送进精神病院?”
“对。”我骗她,“一个小时三百块,我老公说你真能花钱。”
“我不去。”
“那我就直接打电话让医院来接人,让左邻右舍都看见。”
妈终于抬起了她的头——那是一种怎样费解和痛苦的眼神,它精准地攥住了我躲藏在愤怒后的心脏。
在她的注视下,我强撑着说:“我已经受不了了,你在不停地,不停地给我制造麻烦。”
“我没有要你管我。”
“我不管你?所有人都看着,你因为我在这里自虐,你要我怎么报答你?你给我条明路吧,妈。”
“我不用你报答,我就是为了让我自己安心,你姨妈问我,我都解释的。我反正退休也没事情做,做点什么不是做呢?人家老太太看电视,我摆摆东西,有什么呢?你别有压力,我没关系的……”
她又这样说。
“你没关系?好,现在我是你。我今天从早上忙到晚上,没有干任何有意义的事情。我耗尽了精力,腰疼得要死,但是没关系,我就是一根蜡烛,哪怕燃尽了,只要能照亮女儿一片脚指甲就够了。我知道我的各种仪式可能没用,但是没关系,我已经六十多岁了,我已经不值钱了,我不重要。”
我陡然转变语气,狠狠地盯着她:“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你,我付出了我的所有,你怎么能如此不知感恩?没关系,我能忍耐,我能接受,只要你好我就好了。”
“问题是,我不好。如果没有你,如果你不这样为我好,”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会觉得好很多!”
“我没有为你,你不要把我做的事情当作是为你。”妈依然在逃避。
我觉得可笑,说:“那就请你不要再借着我的名头。”
“你真厉害啊。”妈望着我。
我想她可能会拒绝我,甚至责骂我,训斥我,万万没能想到她会说出这样一句话。无力感如潮水一般将我淹没。
我掏出手机给她看了一张照片,是抽屉里的安眠药。我用今天晚上最平静笃定的语气说:“我已经变得很坏了,你不用再做那些了,我打算去死。我死了,就不会再有坏事发生了。”
妈陡然抓住我的胳膊,她干瘦的手指几乎要钳进我的腕骨。看到她惊慌失措的表情,我感到一丝畅快,等待她说些什么让这份畅快加倍。
她却什么也没有说,在几秒钟的安静之后,我看见她的两颊在以又快又轻的速度震动。她确实被我吓到了,急需要什么东西来安抚情绪。
我等待她开口,却迟迟没有,我们像两个忘词的尴尬演员。突然,我脑袋里闪过一丝灵光,似乎看见她用舌尖飞快地在上颚画着正方形。
是的,我该想到的。她把仪式藏进了身体内部,越焦虑越无法停止。忙碌的唇舌让她无法开口,只能用眼神表现出祈求。
她该说一些真正有用的话。我等待着一个母亲对女儿的挽留,却只得到她仍旧沉浸在她觉得有意义的事情中。
这太可笑了。
“这是我们的最后一面,希望你不会对你现在的行为感到后悔。”
妈依旧牢牢的抓住我,但她的力气远小于处于壮年时期的女儿。我把她的手从胳膊上撸下来,于此同时,我感觉自己湿润的眼眶逐渐变得干涸。
“妈,谢谢你爱我。”我说。
9
这就是妈决定去医院治病前,发生的所有事。
医生说治疗强迫症是漫长痛苦的过程,患者只要对抗自己的行为,就必须面对时时刻刻的焦虑和恐惧。妈比入院之前瘦得更多,眼神里总带着惊惧,我从没见过她那个样子,她比之前更像一个疯女人。
“我让她变得更糟。”不知道第多少次崩溃地从医院走出来,我对丈夫说,“我现在开始觉得,也许她不需要治病。”
“什么?”
“只要保证她身体不出问题,精神不正常有什么呢?那个时候她至少有获得感,不痛苦。所以,会不会是我太傲慢了?我做的事情真的是对的吗?”
“你妈说她不想治了?没有吧。”
她确实没有,她温顺得惊人。然而,妈对一切安排的顺从,和她难以掩饰的痛苦搭配在一起,营造出一种巨大的可怜氛围。
我无法面对她看我脸色行事的模样——她是我妈,为什么我们会把自己过成这个样子?
“我小时候总感觉,不管我做什么,都会让她难过,这感觉真的是糟透了。”我说,“现在反过来了,她应该也觉得自己做什么,都不能让我高兴。”
丈夫说我想太多,所以才会有这么大的压力。
我没有回话,他不懂,我只是突然间不再怨恨妈了。
妈是个好人,她过于好,所以好到很坏。可悲的是我继承了她这让人痛心的缺点,因此,我们成了一对被困死在爱和善意中的母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