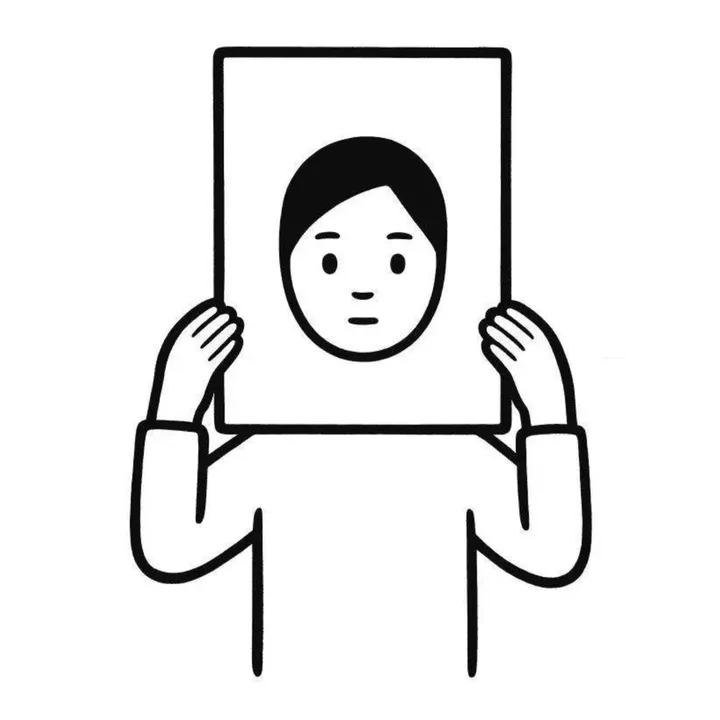上午十点,天气格外阴冷,雾霾很重,通常清晨就会散去,今天仿佛是为了特意遮盖那栋废旧建筑。大酒店建于我小时候,大概七八岁,从小区后面一街外的路口拔地而起,等我注意到它时,它已经封顶,窗户上开始撕胶,只记得几件礼炮从窗外腾飞而起,爆开几展条幅,被升空的气球挂着。悬了那么几天,把后面的山遮得严实。九十年代,经济下滑好像是必然的,大面积的下岗也走进了我家。我妈开始着急,在家洗碗总是打碎,不是手抖,有时候是故意的,破裂的声音响不响好像代表了自己内心不敢言说的不满大不大。尽管说大环境如此,到底有多大,归结起来,还是回到个人身上。我爸看上去不受影响,国外没有下岗一说,只有失业,他还是按月打钱,汇款单的钱数也不变,偶尔在逢年过节时增加一位数字。我那一阵儿念书,总是出神,想象自己念完书,进了棉纺厂,干不了几天同样面临下岗,幼稚的自己并没有意识到时代的变化不像刻舟求剑,我家附近的棉纺厂不是下岗的问题,是彻底消失在历史的长河里。
酒店废弃三五年了,即将在我三十六岁时彻底被爆破。回来,见证它屹立不倒和灰飞烟灭。我妈还是靠我爸年年寄来的钱过活,我以前也是,真的怀疑他已经死了,就是立了个遗嘱,找了个代理人,或者跟银行签了个协议,机械性地按月往我妈账户上打钱,再往深了想,可能他也没打钱,都是我妈骗我的,再想,自己会崩溃。还有一个小时,酒店每一层的四角和中间几根立柱的炸药会分毫不差地同时爆炸,项目会保证三十层的建筑在半分钟之内变成零星的砖瓦,像一次性瀑布般完全倾泻。
我站在窗口,把牙刷捅进嘴里,看雾霾中隐隐约约的大酒店。窗玻璃和窗框都已经撤掉,为了尽可能降低损失,能拆的都拆了,只剩个骨架,像个庞大死亡已久被风化成骷髅但依旧直立坚挺的巨兽。二零零年我站在同样位置刷牙,侧头看到从楼顶挂下布满的条幅,看不清字,只觉得它像一个黄袍加身的英雄,也像铩羽而归的落士。扬起的披风是血和窟窿。那年,据说有虫会啃食一切电脑,一千年的节点总有大事发生,人们相信宿命,相信不公,相信自己的渺小和不起眼终会被诸神彻底看到而折腾丧命。那年我十二岁,喜欢上一个女孩,我许诺要带她开房,就在大酒店的顶层,可以俯瞰岱庙,再远至整座山下之城。女孩说,没有身份证开不了房间。那我就等,成人后却觉得不上那么高也行,酒店的房间里其实都不是来看风景的。几辆挖掘机开始撤离,好像把地面的杂物都清空了,有种特别的仪式感。不知道还有多少其他人在看,我又洗了把脸扭头看我妈。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织毛衣,大红色,说是我的本命年,还要在衣服的领口绣出一条龙,愿好运能绕脖一周。我说,妈,过来看大酒店爆破。我妈好像没听见,仍在钩针。我擦干脸上的水渍,心里默默倒计时。我妈说,有什么可看的,荒了好几年了,早就该倒了。话语刚落,一声巨响接着冲击过来,漫天飞尘如一朵地生云,膨胀,渐近,扑涌。我关上窗户,尽可能阻挡凶猛翻滚的土尘,也在尽力隔绝遥远的记忆。我走向客厅,对我妈说,我试试这毛衣,真喜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