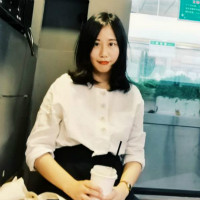人都有想藏起来的秘密,可当秘密是一个人呢?遥远的童年,访冬巷的孩子们都知道,某栋楼十八层的阁楼躲着可怕的怪人,多年后真相大白,主人公回忆起多年前和怪人的交集,只能对一桩悲剧唏嘘无奈。
1.
收到郝凡的消息时,我正和男友缩在出租屋的客厅里看恐怖片。房间内没有开灯,画面阴暗渗人,一个女学生手持摄影机闯入无人的荒野中……我吓得直冒冷汗,而手机上闪烁的光直接让我惊呼出了声。
时间是夜晚十一点十一分,郝凡问我要不要趁假期去他的店里玩。我回,郝老板,你又捣鼓什么新玩意呢?郝凡答,他开了一个密室推理的店,是实景版的,最近生意不怎么样,所以想着找一群朋友去玩玩,测评一下,他可以根据反馈,调整一下游戏剧情和玩的模式。
九十年代,我和父母生活在一条名为访冬巷的窄巷内,那一带全是筒子楼,住的多是工厂子弟。由于筒子楼几乎家家户户相连,所以串门显得极为便利。也就是在那时,我结识了许多的小伙伴,郝凡就是其中之一。
和我们这些常年都在上班的社畜不同,郝凡从大学毕业的第一秒起就下定决心,绝不给人打工。他揣着知名院校的学历,一头扎进了创业的热潮之中。这些年,他在夜市摆过地摊,开过连锁的米粉店,也做过所谓的传媒公司。赚没有赚到钱我不清楚,只觉得他像一个永不知疲倦的发电机,似乎没有任何的失败可以将他击倒。
年纪变大之后,我越来越不喜欢“刺激”的东西。十几岁喜爱的过山车、蹦极等等,在二十五岁后都成了我避之不及的东西。我对探险一类的活动也毫无兴趣,生怕墙壁里突然闯出来的僵尸或地上的“假蛇”会吓得我魂飞魄散。
“那你倒是挺给我面子的。”
当我站在郝凡的实景密室前时,他笑着调侃道:“怎么样?有没有觉得特别地熟悉。”
我站在那一片居民楼的废墟前,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儿时的记忆借由虚假的建筑复苏。我一瞬间有些恍惚,感到自己像被注射了缩小药剂的工藤新一。我不再是那个一米六二的二十七岁成年女性,我变矮了,变小了,我穿上了儿时的白色护士鞋,还有藏蓝色百褶裙……
游戏的提示折页写着,在踏入这里的那刻,每个人都被魔法缩小了,人们再度回到了童年的河流之中。在这里,你和你的小伙伴将重新携手,勘探废旧楼栋的秘密,同时,找出线索,解救那个住在阁楼里的“怪人”。要注意的是,他是最终帮你们逃出生天的帮手,还是最终将你们全部杀掉的幕后黑手,完全取决于你们的行动和态度。
我越看越觉得莫名其妙,遂将剧情提示扔给一同前来的老友方俊。小时候,我们住在同一栋筒子楼里。印象中,当别的小孩在楼下玩捉迷藏、四个大字等游戏时,郝凡总是被“锁”在家中写作业。我记得他家里有一个扎实的铁栅门。有时候,经过那个门前,看到郝凡扑在书桌上的身影,总会让我联想起监狱的囚犯。
踏进幽暗的楼栋,地上湿漉漉的,墙壁上有废旧的报纸,地上偶尔会出现一些血痕。有一些假的小蜘蛛缀在玻璃窗的旁边。整个气氛确实烘托到位了。有一阵,我迷恋看推理小说,里面有一种案件类型是孤岛生存,即将几个人关到一座无法与外界联通的小岛上,然后,随着夜幕的降临,岛上的人会离奇死亡。此地虽非孤岛,但大门已经锁起,如果找不到线索,就无法在限制的时间内逃出去。
我们走了一会儿,上到了二楼,那儿有一个狭长的通道,空气里有消毒药水的味道。在长廊的尽头,一个绿漆的老旧长椅上,一个男人坐在那儿,脑袋上架着一个白色的棉布枕头。“啊……”我忍不住喊了出来,那枕头人便朝我们扑了过来。我吓得到处乱跑,跑了一会儿,那个枕头人忽然不见了,我这才放下心来,扶着楼梯扶手喘气。
虽然明知道一切都是演员假扮的,但身临其境依旧觉得恐怖。我抬头,看向报纸,那儿写着一九九八年的新闻,洪水,还有枪击案,在报纸的下方,有一个纸牌大小的版块记录了那一年的一个小新闻——由于暴雨连绵不休,冲垮了精神病院的大门,一些患者跑到了大街上,对着市民露出夸张的大笑。
2.
玩了约三个小时后,我们终于拿到最终线索,取得了钥匙。
这是一把能打开两扇门的钥匙。一扇门关着一个精神不稳定的病人,一扇门则位于我们通向出口天台的必经之路上。
游戏提示:钥匙只能用一次,你们只能选择打开一个地方的门。
“莫名其妙,管那个人干嘛,我们又不认识他,当然是选择开天台的门啊。”
“不是的。”我拦住朋友说:“这个人既然被安排在这里,肯定是有用的,万一咱们到了天台,又说需要那个人的帮忙怎么办?”
“晕,没什么好犹豫的,又不是真的。”方俊摸摸自己的肚子说:“我饿了,我只想赶紧结束然后让郝老板请我吃火锅。”
在游戏的最后关头,我们变成了一盘散沙,我觉得争执并无必要,打开哪扇门都不会决定我们在现实世界的生死。
“游戏倒计时十分钟。”喇叭里忽然响起郝凡的声音,我转身,指着那个阁楼说:“要不我们还是去那看看吧。”
众人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快速地朝那个小屋跑去。跑到屋子门口时,我听到里面传来一个男人的低吼声。我想象里面藏着一个丧尸,或者怪物。会不会我一进去就被咬了脖子,然后这故事就变成了《生化危机》?我一边暗中咒骂着这个游戏的烂,一边想着尽快让一切结束。
“别管了,还是去天台吧。”我们内部已经产生了分歧。
在我正准备将钥匙旋入锁孔时,黑暗中,那个枕头人扑了过来,夺过我们的钥匙,跑到天台边,打开了天台的门。周围瞬间响起了警报,游戏结束了,我们的探险失败了。
我不明所以,正准备冲着一切的始作俑者——郝凡发火,谁知那个枕头人摘下了头套,原来这个NPC就是郝凡假扮的。
“郝老板,大半夜的耍我们,不对啊。”
“赖我,我请你们吃火锅去。”
还没有将一切理清,我就被带到了热闹的夜市中,一瞬间,灯红酒绿,和方才那个幽暗封闭的老旧筒子楼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众人沉醉在食物溢出的香气中,我却感觉自己还困在楼栋的阴寒之气里。郝凡走过来,像儿时那样,拍了拍我的肩膀,问:“怎么了?”我摇摇头说,没什么,只是玩游戏太累了。
火锅很快端了上来,人们开始夹菜,大快朵颐,我没什么胃口,只是一直在喝汽水。郝凡坐在我的旁边,他问我是不是有什么不舒服,我于是将心里的想法和盘托出说:“我感觉游戏好像不是这么玩的。”
“那你觉得应该怎么改进呢?”
“你这个不像是什么探险破案类游戏,更像是在拍电影,而且还是那种别人看不懂的文艺片。你的故事也没有剧情,只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很渗人。”
郝凡放下了筷子,很严肃地看着我说:“你还记得那个住在十八栋顶楼的人吗?”
从有记忆起,我就知道,在十八栋的顶楼,住着一个怪物,那个怪物专吃小孩。父母叮嘱我,千万不要靠近那个地方。可大人们越是这样强调,我们这群小孩越是对那个地方产生好奇。
九十年代末,我们尚不知道什么是互联网,有空的时候,我们会呼朋引伴,到楼下梧桐树边的空地上玩游戏。我们玩得最多的是躲猫和四个大字,但这两项玩乏了后,我们会选择去玩点更“高级”的,比如“阁楼探险”。我们一般是五六个人,按照年龄顺序,排成一个队列,年纪最大的孩子会手持“武器”(通常是一根木棍),走在最前面,然后其他的小鬼头就跟在后面。我胆子小,年龄也偏小,一般是夹在中间的那个。
去十八栋的路上,我们每个人都昂首挺胸,颇有自信的样子,但越靠近顶楼的阁楼,我们的步伐就越慢,头上渗出的汗也越多。好几次,我听到楼上传来如野兽咆哮般的异响,我便嚷嚷着,别走了吧。每到这时,站在队伍第一排的人都会朝我做个鬼脸然后调侃:“胆子这么小,下次别来了。”
尽管大家都表现出很勇敢的样子,但只要那间阁楼房里发出怪声,所有人都会四散而逃,有一次,一个小孩还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弄得头破血流。这样的探险,一共进行了六次。前五次都失败了,但在第六次的时候,我们终于看到了那个“怪人”的真容——他穿着蓝白条纹相间的睡衣,嘴唇发白,眼睛下有浓重的黑眼圈。他趿着拖鞋,脚踝处套着厚实的锁链。
他让我想起古装剧里那些被封印的大魔头,我想,以我们的力量必然无法与之抗衡。在看到他真容的那刻,所有人都愣住了,紧接着,很快,我们开始疯狂朝下跑,生怕这个人身上会抖落污秽之物,给我们每个人带来霉运。
在那次探险之中,郝凡也在场。跑到一楼空地的时候,他弯着腰,喘着气,然后看着我说:“你觉得吓人吗?”我拼命点头,告诉他,再也不想到十八栋来了。
杯中的汽水喝完了,郝凡又给我倒了一杯。他举着装有啤酒的杯子,对着我说:“我们碰一个?”我点了点头,听到玻璃杯相撞发出的清脆声音。
夜风并未驱赶燥热,我感觉浑身都是粘稠的汗液。月色朦胧,我想起来,似乎距离那个团圆的节日已经不久了。
郝凡一口气干完了杯中的酒,望着我说:“其实我心里有个秘密,这么多年来,一直没有告诉过别人。但今天,我想说出来了。”
3.
在遥远的异域,一对父母为了完成自己的艺术实验——将小儿子卡图兰培养成一名优秀的作家,于是将大儿子迈克尔关在屋子里,用各种办法折磨他,并利用迈克尔发出的哀嚎来刺激卡图兰的创作欲望。
这是英国剧作家马丁麦克多纳《枕头人》的核心剧情。
在访冬巷的相距不远的两栋筒子楼里,同父同母的一对兄弟被父母分开抚养,哥哥因智力障碍被视为怪人,弟弟因学习成绩极佳被视为天才。弟弟不知道哥哥的存在,一直以为自己是父母唯一的孩子,直到某一年的夏天,他看见哥哥的尸体泡在池塘边的臭水沟中……
这是郝凡告诉我的故事。
两个故事皆让人不寒而栗,我感觉精神恍惚,不知道该如何应对。
“也就是因为我哥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做好学生很没有意义。我很标准,像是那种严格筛选下来的鸡蛋,什么无菌啊,什么可生食之类的。但实际上呢,我没有一天是开心的,快乐的。”
我忽然意识到,这样可以解释,为何郝凡在大学毕业之后没有成为一个上班族,或许他在那时就受到了不小的精神刺激,已经不愿意再“假装正常”。
“我就是要让我爸妈不舒服,让他们明白,培养出一个好学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你这个想法太幼稚了,如果你硬要跟他们作对,说不定断送的是你自己的前程。”
“是,你说得对。如果按照世俗意义上的成功标准,我肯定是个废物。但如果按照我父母的想法来,我可能早就没了。我想,在他们眼中,我哥就是一个残次品吧。他们虽然让他活着,但并没有给他爱和尊严。我有的时候甚至会很内疚,觉得自己是多出来的一个人。是因为父母觉得哥哥没有任何希望了,于是把我生了出来。”
在我的印象之中,郝凡的父母自下岗后一直过得辛苦,他们长期在外忙碌,有时甚至一个人要打两份工。母亲常对我说,你看,别人没有家长管,都那么听话,你呢?
有很长一段时间,郝凡是我们整个楼栋里其他小孩的压力来源,他就是传说中的“别人家的孩子”。
“你有找你爸妈聊过你的想法吗?”我问。
“聊?怎么聊?我爸前年去世了,我妈今年老年痴呆了。”
4.
城市总在不断地翻新建设中,曾经热闹的地方如今沦为一片废墟,曾经是臭水沟的地方经过了治理竟变成了一座充斥着鸟语花香的口袋公园。
我坐在公园的木质长椅上,远远看到一个男人推着一个坐轮椅的老人朝我这边走了过来。男人摘下帽子,露出一张胡须未刮,略显沧桑的脸。
男人是郝凡,我曾经的邻居,老人是他的母亲。
“黄阿姨,不认识我了吗?”我站起来,朝他们母子二人走去。
“认识,认识,你是不是明年就上小学了?”
郝凡笑了笑,低声对我说:“看,她只记得小时候的事情。每天都喊我是她同事。有的时候,她醒过来了,晓得我是她儿子,但根本记不清我到底几岁。”
郝凡坐了下来,从荷包里取出一张黑白颜色照片,照片中,她的母亲留着两条麻花辫,面容青涩。郝凡说,那一年,黄阿姨二十四岁。紧接着,郝凡又掏出一个墨绿色封皮的小日记本,他把本子交给我,我打开一看,第一页是普希金的一首诗,第二页是一副手绘的花卉图,第三页则是日记,日记的主人用十分工整的笔迹写着自己怀孕了,我又朝后翻了翻,到中间页的时候,我发现笔迹变成了红墨水的版本,日记的主人说自己不小心染上了感冒,很严重,在家里吃了点西药,把病情压下去了,希望对孩子没有影响。
“这是?”我不忍再朝下看,把日记本还给了郝凡,窥伺他人隐私的感觉并不好受。
“我妈在生我哥之前吃了一些感冒药,我哥生下来的时候看起来很健康,但后来发现脑子好像有些问题。我爸妈很后悔,但已经没有任何救治的办法了。而且我哥有时候会发疯,发起疯来会到处打人……”
“所以你爸妈就把你哥锁了起来?”
郝凡点了点头,告诉我,本来,他父母和他哥是住在一起的,但等郝凡出生之后,他父母担心他哥的情况会影响到弟弟的生活,于是在另一栋,租了一个狭小的阁楼,把他哥安排到那里去了。
“很多年我都走不出来,觉得特别痛苦。我变得很叛逆,我父母越讨厌我做什么,我就越要去做什么。有一天,我一个人在路上闲逛,经过一家剧院,当时天气很热,我想着,要不进去随便看场话剧,也凉快一下。然后我就看到了《枕头人》。看完这部剧后,我一个人在位置上哭得稀里糊涂,特别滑稽,旁边有个女孩给我递了一包餐巾纸。然后我们就认识了。”
“你在剧院遇到了你现在的老婆?”我惊道:“还挺浪漫的。”
“故事的开始是浪漫的,但中间总是会有很多挫折。我们结婚的第三年,准备要个孩子。结果体检的时候发现两个人都有地中海贫血基因。我们当时很担心孩子会变成重型地贫儿……但问题是,我老婆已经怀上了。”
“我记得你的孩子很健康啊,我还去喝过满月酒。”我说。
“是的,万幸,他很健康,好像冥冥之中有谁在保佑他一样。这几年,做了父母,我感到我逐渐开始有点理解他们当年的决定。我想,如果我遇到了一样的事情,我可能已经完全没法生活下去了。当年,他们那么难,还是把我抚养长大了……”
就在我们两个人想继续聊下去时,黄阿姨伸出干枯的手,抓住郝凡的胳膊说:“快,快推我回去,我要给伟伟送饭了。”
“伟伟是谁?”
“伟伟是我哥的小名……”郝凡站起来说:“我妈现在记忆比较混乱,他不太记得我身上的一些事情,但对我哥的事情居然记得很清楚。我有时候想,在我小的时候,她跟我爸要守着我哥的秘密,多痛苦啊。”
雨淅淅沥沥地下了起来,郝凡打开雨伞,撑在他母亲的头顶。我站了起来,同他告别。他又跟我道歉说,那个密室游戏是一个恶作剧,让我不要放在心上。
冥冥之中,我感到郝凡似乎是想通过那个游戏去寻找什么答案,而现在,答案浸泡在湖水之中,或许早已经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消失了。
在数十年前的雨夜,由于房门没有关紧,郝凡的哥哥从自己的小房间里跑了出来,他第一次体会到了自由的感觉,然而没过多久,他就因为意外落入了水中。这件事使黄阿姨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而我没有告诉郝凡的事情是,在那个看似美好其实阴云密布的年代,他的哥哥曾经救过我一次。我记得那天我正独自走在放学的路上,路中央突然杀出来一个奇怪的男人,男人朝我露出诡异的笑容,我吓得不知所措。就在这时,郝凡的哥哥,那个我们曾经误以为的“大魔头”,不知道从哪儿抱着一个枕头出现,和那个恶人扭打在了一起。我吓得匆匆逃走,再也不敢去回想这件事情。如今,一切尘埃落定,我突然想对他道一声“谢谢”。
雨越来越大,下得天地一片模糊,我撑开雨伞,独自在湖边漫步。我抬起头,看到对岸站着一个男人,男人的头上顶着一只云朵一样的白色枕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