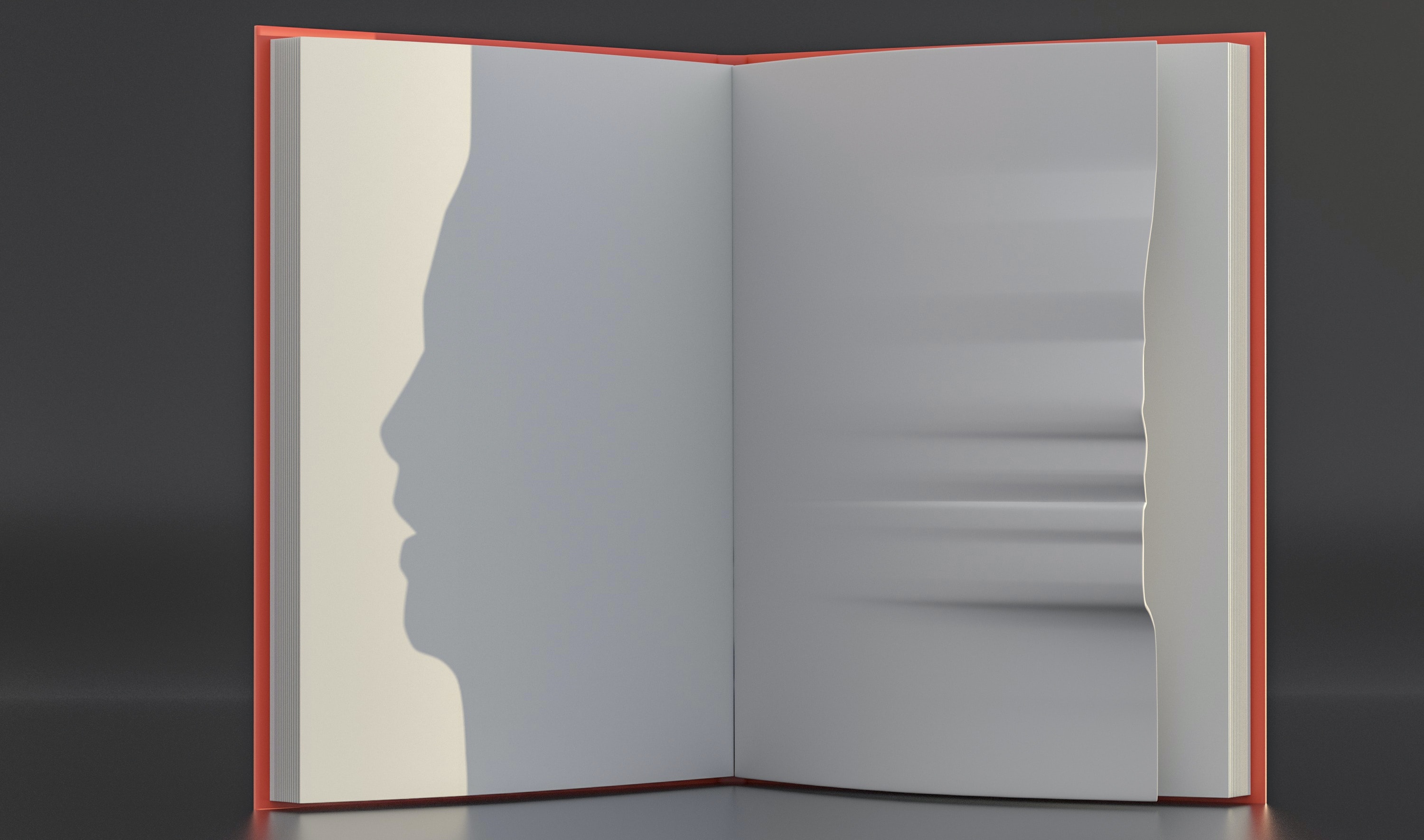
「后台谈话」是由「ONE一个」发起的作家访谈类专栏。我们相信,不管文学场如何人声鼎沸,「后台」始终是那些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艰难求索的作家,和他们的心灵内史。
谈话者
陈崇正,广东潮州人,北京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著有长篇小说《美人城手记》《悬浮术》,小说集《黑镜分身术》《半步村叙事》,诗集《时光积木》等。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陈老师您好。祝贺你的两本新书《美人城手记》《悬浮术》的出版,我找到了几个关键词,想从这里开始对陈老师进行访问:社会问题;人性;想象力;历史文化。这四个关键词,我想都是和你作品有关的,其中您对哪个关键词更感兴趣?为什么?
陈崇正:小饭老师好,很开心有这么一次对谈的机会。您所提到的这四个关键词,都是大问题。我想谈谈想象力。中国小说的源头是传奇志怪,街头巷议,神鬼之事,构建的是天上人间多层世界——猴子是在石头里蹦出来的,历劫的人物含玉而生,督战三军的军师通晓占卜,乱世英雄来自天上的星辰。完全忠诚于现实的小说创作在中国时间很短,而想象力作为中国小说的硬通货从未缺席。当然,并不是说充满想象力的小说就没有现实根据,多少研究者还希望还原大观园中的药方和菜谱;而是说,现实的元素在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那里仅仅想象力宫殿的砖瓦,是挂住新编故事的衣钩,是说书人手中的折扇。中国这个诗歌国度,自古就不缺乏浪漫精神,我们在凝视日新月异的现实世界时,也一定不要忘记有一条属于想象力的河流至今滔滔不绝。没有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只能沦为实在主义,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
小饭:有人说《悬浮术》的故事情节复杂且曲折离奇,充满了惊险刺激的场面。那在这整个创作过程中,哪个部分对你来说最困难?哪个部分又让你自己最为满意?我指的是人物或者情节上。
陈崇正:《悬浮术》最初是打算作为系列中短篇创作的。其中最难的部分,应该是为这么斑驳的一次写作,提供一个自洽的精神命题,最后我用一个关于“悬浮”的哲学讨论完成了对九个篇章的统一,这个应该是难度最大的挑战。我最满意的是我在融合科幻元素的同时,叙事的质地从来没有离开过现实。也就是说,整个创作过程中,我一直在思考现实,将诸多现实问题融汇在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里加以讨论。当然,诸多问题并没有答案,答案从来都在风中飘,小说家的职责也不是提供答案,而是提供一个看见现实的角度,然后,在南方以南,试图用文学为这样一个复杂多变的AI时代命名。
小饭:我确实对《悬浮术》很感兴趣。我得说这个小说的写作风格很独特,想象力和人物设定像网络小说,叙述又很成熟,是经过训练的老手之作。我的问题是,在驾驭这一类超现实的题材,带有科幻风格的作品的时候,你是如何平衡自己的——是否会避免堕入俗套,又希望在一个审美体系中做出创新?
陈崇正:这个问题涉及小说和故事的关系。我努力在虚实之间构建一个好看的故事。对我而言,小说还是离不开故事,或者说,应该在小说中提供一个别人乐意阅读的故事。小说和故事不应该对立起来,相反,应该充分利用故事的可能性拓展小说所能承载的地域空间。
小饭:我想提到你的另一部作品《美人城手记》,您自己说《悬浮术》可以视为《美人城手记》的外传,两者共享了同一个世界观——我知道这里的“世界观”并非一种观念,而是一个“宇宙”。那如果我们需要谈论一个观念的话,在这两部作品中,你想表达一种或哪几种,是什么样的观念?
陈崇正:正如老婆饼里没有老婆,美人城里也没有美人,只有对科技发展的忧思。作为《美人城手记》的小说原型,潮州美人城原来是一处废墟,后来被铲平建了楼房,但在我的记忆中,这个地方永远是个神秘的乐园,我多年以前就不断谋划着如何在纸上对美人城进行重建。所以《美人城手记》这部小说就是在这样真与幻的交错中展开,已经与机器融合的后人类开始不断一遍遍讲述故事。《美人城手记》确实与《悬浮术》在世界观和人物设置有共通的地方,因为这两本书的写作时间其实非常重叠,我一边陆续写着《悬浮术》,一边继续修改着美人城的故事。所以,共享了世界观,并不是一个观念,而应该理解为一种创作理念,也就是我这十多年来一直在坚持的文学地理学——如何通过统建一个写作的根据地,让虚与实的人物都能在同一个时空中得到共享。这样的共享并不是等比例的统一,它并不严密,而只是作为一个镜像而存在。这样的镜像共享,往往会给读者阅读带来意外之喜,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创作者的运行内存,我需要不断回到美人城世界中,复习已经完成的作品中的复杂人物关系。但我觉得这样的映照还是值得的,它让我的写作不再是孤立的,而是充满了先手与后手的机锋和联动。这样写作的好处还有,我是一个有城堡的人,走在街上可以昂首挺胸。
小饭:那有没有读者说过陈老师的作品,尤其是《悬浮术》和一些短篇作品,经常包含着香艳的部分?在写作的时候你会避免香艳的描写,还是会尽可能写好那个必要的部分?
陈崇正:文学作品中包含必要的描写也是正常现象,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渲染某种情色氛围。相反,我不断在追问自己,是否可以删除掉这部分的描写,以求让我的作品获得更多的阅读人群。但往往是,如果去掉这部分的描写,那么故事的逻辑或落点就不太成立,它是故事有效的组成部分。因为这个问题,我的小说无法推荐给朋友的小孩,新书失去走进中小学校园的可能,亏大了。现在大人都不看书的,书如果不能卖给小孩,要失去一半以上的图书市场。
小饭:如果我理解得不错,孩子们确实对科幻,奇幻这些题材上更感兴趣。那陈老师您认为在科幻这个框架下写作,相比传统的写作,更容易的是什么?更难的是什么?
陈崇正:夹带科幻元素的写作对我来说只是一种探索。或者说,我从来没有将我的写作当成是科幻小说创作,而只是借助了科幻元素的一类创作而已。只是出版图书之后,为了让更多读者来买书,所以将这样的小说宣传成科幻小说。我估计真正喜欢科幻的读者读了我的书,是会失望的。我理解这样的心情,阅读期待的落空,只是希望他们不要骂得太狠就好,这个事情只能厚着脸皮干下去。写书人为了卖书,也只能如此。我在这样的探索的同时,也保留了其他几个生产线的创作,包括完全贴紧现实的写作,也包括面对历史的重新挖掘。科幻是非常好的写作工具,它的难度在于要提供一个自洽的科幻设定,这个太难了,对一个文科生来说,只能完全靠想象的触觉。我对自己说,瞎写吧,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们现在奉为真理的诸多科学定理,可能多年以后就变得幼稚可笑。就像我们现在看《海底两万里》,其实和孙大圣去东海龙宫,也没有太大的区别。
小饭:坦率地说,在《悬浮术》和《美人城》的阅读过程中,我确实想到了《三体》。你怎么评价这部似乎已经被经典化了的科幻著作?如果有朝一日,你要致敬这部作品,你会怎么做?
陈崇正:《三体》相当棒,刘慈欣的厉害之处在于,他能无中生有对自己设定的故事世界给出一个底层运行的逻辑定理,这个太了不起了。所有的故事都围绕在同一个名为“黑暗森林法则”的逻辑底下进行,这样一个耳目一新的设定为小说提供了稳重的基石,所以《三体》再写一百万字也是好看的。
小饭:的确是这样。我听过王尔德有一句名言:“不要虚掷你的黄金时代,不要去倾听枯燥乏味的东西,不要设法挽留无望的失败,不要把你的生命献给无知、平庸和低俗。”——我是前几天恰好看到的,但我感觉这句话跟你的创作似乎有某种关联,我无法清晰表达出来,所以把这个问题抛给陈老师。
陈崇正:我这几天也在常常反思自己,常常自我怀疑的性格是否会在我的写作中留下不可克服的美学漏洞;不过,这样的反思本身已经是陷入死循环的悖论。我塑造的人物总是过于犹豫,不敢果敢;又比如我写不出令人骄傲而昂扬的情节,而这些在处理宏大情景时必然带来不足。故此我准备在后面的写作中发展一个孤胆英雄的创作人格,以便让我的人物更硬气一些。
小饭:有反思的作者都是更好的作者。我认为是这样。同时我还关注一个作家生长的起点。“有许多闪耀和光辉的思想仅仅是从一般的文化修养上产生出来的,就如同幼芽总是长在普通的绿枝上一样。”每一位作家的创作对我来说都是一个脑图,我的问题是,你的创作,或者说所谓的根基,是从哪里长出来的?
陈崇正:写作的根基无疑是复杂的。这个问题可能不会有标准答案,我看到不同评论家也对我有不同的分析。但我想,或许是一种内在的真诚,比如是承认我是乡下人,我是土气的,是卑怯的,是自我怀疑,是无法确定,但由此衍生出来的另一端竟然是,我对自己能做好写作这件事似乎有谜之自信。总觉得别的做不好,写作应该还行,真是太膨胀啦。
小饭:接着前面一个问题,那你的创作有没有受到其他作家的影响?尤其是国内前辈作家的影响?你是如何借鉴他们的写作风格的?会介意说出自己的“师承”吗?
陈崇正:当然有的,苏童余华等先锋作家都是我的老师。我也不止一次提到王小波,他教会我可能性的叙事艺术。当然远远不止这些,比如卡夫卡、卡尔维诺、萨拉马戈、帕慕克……可以列一串长长的名单。作家注定是杂食动物,必然是在不断寻找自己的坐标。
小饭:“想要逃避这个世界,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想要和世界结合,也没有比艺术更可靠的途径。”——你认可这句话吗?
陈崇正:这个可能有点夸大艺术了,这样的观点对于艺术家可能成立,但对于普通人,其实活着就好了。我更重视一个人的生活质地和生存本能,可能如何生活比艺术本身更重要。活着,更好地活着,努力工作赚钱,去享受生命中的每一个阶段,可能我们能收获更多。生活本身是大于艺术的。人还是活得庸俗一点容易幸福,贪财好色,大裤衩人字拖,这样完成一生,也许比蝇营狗苟扑向伟大事业更为划算。特别是一个人没有发现自己有什么过人之处,那么尽早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普通人,大概能避开百分之八十的痛苦。
小饭:友谊、勇气、信仰和自由,我想这些都是重要的东西,其中哪个对你来说最为重要?
陈崇正:都重要吧,太难做选择了。自由其实是一种能力,没能力哪里来的自由,生活是如此,艺术创造也是如此。对许多人来说是巨大难题的东西,在艺术大师那里,他会说,本来就应该这样,都可以,你花那么多时间干啥?
小饭:嗯,非常同意陈老师的这个说法。你的小说是否有改编成电影或者电视剧的计划?这方面的进展是否顺利?
陈崇正:这个事还是需要机缘和运气,目前看来运气还不太够,希望我的作品影视改编都能找到好人家。
小饭:确实,每个时代的写作者各有各的运气。作为这个时代的写作者,你希望你的小说对读者有什么启示?提供什么样的帮助?或者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或许这不是一系列好问题,但我也很想尝试问问。
陈崇正:写作就是不断给不存在的事物命名的过程,希望读者会喜欢这些土里土气的故事吧。不过,我常常怀疑自己是没有读者的,如果能拥有五百个有效读者,已经是莫大的运气。
小饭:陈老师,你未来的——三年内,或者更长,十年内——你的写作计划是什么?有什么新的作品即将推出吗?
陈崇正:带着科幻元素的写作应该很快到一段落,我会转向更为现实主义的写作,有一些列书写南方以南历史和生活的写作计划。我四十岁了,我们八零后都不年轻,不知道你对时间的感觉如何,我最近常常有岁月惊心之感。时光飞逝,而我写作的拼图远远没有完成。
小饭: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会停止科幻元素的写作?您在访谈的一开始说过,“没有想象力的现实主义只能沦为实在主义,不会有长久的生命力。”刚刚前面你又提到过“科幻是非常好的写作工具”,既然如此,为何要丢弃这个工具?难道现实主义写作对你来说更有生命力更值得持久努力吗?
陈崇正:并不是丢弃,只是阶段性的轮换。锄头是个好工具,但如果要砍柴还是得用回斧子,并不矛盾。贴近现实的写作是另一种挑战,比如我近些年写了几个非洲故事,但其实我并没有到过非洲,只是我持续在关注去非洲淘金的中国人,他们的生命遭际也是中国故事的一部分。而且我相信,书写一个发生在我经验之外的现实故事,其中对想象力的挑战并不比我写一个夏商周故事更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