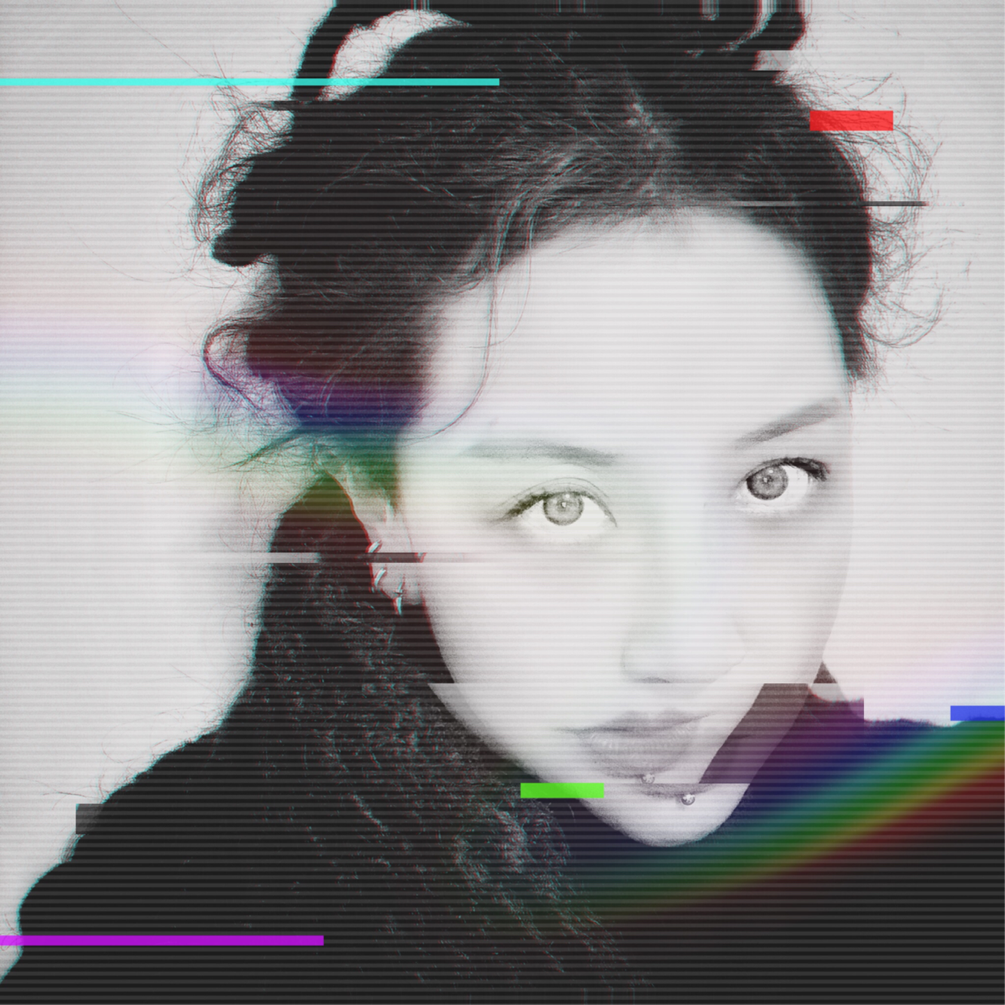1995年,身为初中生的“我”第一次接触迪厅。2014年,“我”成为了上海派对的组织者,距踩踏事件一步之遥。2020年,当派对成为禁忌……这是一位饮酒者的派对故事,人生何以至此?不敢追问,也无话可说。
1
2020年打从一开始就显露出某种不寻常的气氛,4月下旬依然很冷,假如忘了穿外衣出门,走在街上会被一阵突然而至的寒风吹个透心凉。整个月里我只外出过两次,遗憾的是两次都没穿外衣,也许我只是对生活的真实面貌缺乏想象,总以为一切已经开始回暖。上海前所未有地冷清,街上大部分店铺都关着门,路过永嘉庭,看到沿街那两家店连桌椅都已经全部搬空。从前这儿是城中时髦场所,来客从早到晚络绎不绝。那些衣香鬓影的人都哪儿去了?
几个月前,一种肺部传染病在全世界多个国家同时暴发,瘟疫目前尚未结束,所造成的影响仍将在未来持续。每天从各种渠道传来消息——不论从事何种行业,都正在、或者已经遭受严重打击。这种时候人会产生奇怪的心情,好像一切并不真实,反而更像书里看到过的景象。在网络上搜索与经济现状相关的内容,随随便便就能找到几十本标题中含有“大萧条”的书,其中有一些非常著名,例如穆瑞•罗斯巴德写的《美国大萧条》。我们将要面临的状况会更好或更糟?不用参照历史也能知道,经济衰退恐怕已成定局,这是当下首先要面临的问题。
朋友G约我吃午饭,地点是我选的,一家位于建国西路的法餐厅,那儿同时也供应东南亚菜和一些奇怪的食物,价格昂贵、味道一般,唯一优点是环境好。大大的院子中间,看起来有些年头的喷水池不紧不慢喷着水,青石砌成的池壁布满青苔,池里养着金鱼和乌龟。订座时,接电话的人会告诉你:“景观位先来先得,不能预订。”眼下生意应该没从前那么好,所以我跟G说不用着急。但我知道他肯定会提前到,他是对守时有强迫症的人。一次我们约在衡山合集附近吃饭,那天刮大风,我以为他可能不想出门或要迟到一会儿,于是发微信问了一声。结果他回复说:“已经到地铁站了。”接着又发来一句:“我飞也要飞过来。”
天气不错,久违的蓝天白云和艳阳高照,路上为数不多的行人都戴着口罩。走进饭馆时,看到G已经占据了水池边位置最好的桌子,他面前摆着一杯生啤但没怎么喝,心情似乎不太好。果然,我刚坐下点完菜,他就连珠炮似地开始大讲特讲。内容不外乎这几样:年景不好,生意受影响;度假计划被疫情耽误;谁和谁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最近又道听途说知道了哪些重大消息……说得天花乱坠、精彩纷呈。我一向知道G话多,不过他颇有见识,口才很好,人又风趣,听他抱怨并不使人心烦。我们基本上无话不谈,只是我相对说得少些。
那顿饭吃了近三个小时,吃完甜品又喝了两杯啤酒,我看G没有要散的意思,便提议去滨江道走走。他高兴地表示同意,这时我才知道他从来没去过黄浦江西岸。这种情况并不鲜见,城市里的日常风景对本地土著没多少吸引力,就像去青岛时,一个当地朋友告诉我,他们从小到大很少特意去海边。如果一样事物打从出生就已经包含在生活的内容里,那么你肯定不会觉得它有什么稀奇。只有对旅客而言一切才大有不同,旅客是专程出来玩的,肯定希望能多看些东西。
饭馆距离滨江道大约4公里,我们健步如飞,半路觉得渴,又进便利店买冰棍吃。最后带着半打冰透的啤酒继续走,还顺便捎上了两瓶健力宝。在一个路口等红灯时,我们在树荫下的马路牙子一屁股坐下,喝着健力宝,就像来自上世纪90年代的两名外地旅客。G出了不少汗,情绪明显高涨起来,兴奋地说:“这也太Old school了!”健力宝还是记忆中的味道,仿佛瞬间回到了二十年前的某个夏日午后。从前我也喜欢跟朋友们坐在马路边谈天说地,再加上已经连续好几个月没在外面行走,这久违的松弛终于令心情愉快起来。
滨江道游人多如过江之鲫——拖家带口搭起帐篷野餐的,带着宠物跑步的,躺在颜色鲜艳的野餐垫上搔首弄姿拍照的,玩滑板和直排轮的,放风筝的,跳街舞的……男女老少应有尽有,一派享受生活的热闹景象。我们在一处能观赏江景的草地随便坐下,一边看着黄浦江上颜色丰富、形状各异的货船慢慢经过,一边喝起了啤酒。除了氛围嘈杂些,整体感受还不错,凉风迎面吹过,阳光照在我们身上,蒸发汗水的同时稍稍驱散了心头的阴影。如果未来还能回想起这一天,我会说这是个清爽宜人的美好下午,啤酒味道甘甜。
G问:“你还记得我们怎么认识的吗?那天晚上外滩可是死了不少人。”
“当然记得,那天大家都忙坏了,没说上几句话,想不到我们后来会成为好朋友。”
“那么大、那么好玩的派对后来再也没有了”,G有些遗憾,“美术馆前厅整面墙全部用来做VICE的字幕投影,酷得不得了,当时那句口号怎么讲的来着?”
“……世界在下沉,我们在狂欢?”
“对对,就是这个,”他喝了口酒,“根本没想到不久后世界真的下沉了。”
“也已经没人还有心情狂欢。”
“唉……”。
时间在耳畔嗖嗖飞过,我们相对无言,只能举起手中的啤酒。
“干杯,朋友。趁我们还有自由。”
2
2014年,我从北京来到上海,在一家非营利性艺术机构工作。这类机构国外很常见,国内数量还不多,因为做展览和维持日常运营非常花钱,但又很难创造营收,背后需要强大的资金扶持。我们的展览门票低廉,不涉及艺术品买卖,每年还做大量公益活动,包括文化、艺术、诗歌讲座,各种现代舞工作坊和手工艺工作坊,以及各类艺术教育课程。我所在的商务部是唯一有KPI考核的部门,日常工作主要琢磨怎么搞钱。既然单位有不错的场地,工作内容也有一定自由度,那就多做些活动吧——由此,我开始策划派对。
打着艺术的名目招揽合作方,既有场地租金收益进账,又能吸引大量参加活动的人,可谓一举两得。假如给我一张酒牌和一个带厕所的空房间,单靠卖酒就能大赚特赚——我对此深信不疑。在世界上大部分地方,只要有一个空间,里面提供酒和不错的音乐,年轻人总会趋之若鹜。大城市尤其如此,所以派对向来是上海夜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你问人们为什么参加派对,通常会获得多种答案。在我看来,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打发一些时间,乃至还能结交新的朋友,拓展各方面见闻,或者仅仅为了打扮漂亮出门去玩……这些都是参加派对的核心诉求。
派对与其他娱乐活动最大的不同,是与所有时髦事物在主题上的相关性。无论一场派对是先锋的、个性的、时尚的、酷的……参加者将据此分辨到场的大部分是不是有共同爱好的人。简而言之,这类人群多半具有一定程度的艺术素养和审美需求,喜欢多样化生活方式,追求个人形象的夺目,并愿意为此花费时间和金钱。无论派对组织者希望传播什么样的信息,也无论主题关乎文化、艺术、音乐或其他,到头来,无非提供一些日常生活之外的体验,而这些体验或许正是许许多多年轻人选择留在大城市的原因。
我与G的相识得追溯到我来上海第一年办的大型跨年活动,他是朋友介绍的赞助商之一。那场派对构成丰富,主体内容是知名电子音乐人的多媒体艺术秀。我们在1000平米空间里搭建了立体环绕全息投影舞台,单是营造氛围的透明乔其纱就用了三百多米。此外,很少会在室内演出中使用的高达5.5米巨型LED墙也是一大亮点,以及12台高级投影装置,还有供人拍照的多处LED灯管装置。单是搭建就花了一个多星期,期间技术和沟通上难题频发,各方人员焦头烂额,我觉得只要能活着把活动做完就已经是最大的胜利。
这样的演出配置不太容易在Live house实现,要么场地不够大,要么层高达不到要求,要么没有那么多预算进行前期投入。假如放在音乐节,露天环境的氛围必然要差一些。但这并不是全部,我还邀请了某国际青年文化媒体在朝鲜和美国拍摄的三部从未在国内公开过的纪录片在二楼a空间循环放映,其中一部纪录片内容是NBA球星罗德曼访问朝鲜(金正恩是NBA球迷,当年他亲自邀请了这次访问)。此外,楼上b空间是一家游戏公司赞助的射击游戏实景体验,当时他们正准备推出一款多人在线枪战游戏,请了十名高挑靓丽的Show girl,她们将于整个派对期间身着紧身战斗服装手持玩具冲锋枪在场内与观众互动。
我写的策划案足有四十多页,整个机构动用了所有资源和人力,只为了把这场派对做牛逼。主要出于票房压力——电子音乐人的演出费和租借的设备费,以及搭建费、物料费等等均是庞大支出,因此100块的票价我认为不贵。彼时国内艺术机构还从来没有做这类活动的先例,大家非常担心,就怕到时候没人来。为了促进售票,我又想了各种法子,包括找到某德国精酿啤酒品牌谈合作,对方答应提供20桶生啤赞助——这能确保门票包含1杯啤酒,但又不用花预算去采购。最后是托各方关系弄到的一大堆品牌赞助,酒店房间、艺术衍生品、红酒、化妆品、小礼物等等不一而足,派对开始后每小时抽奖一次。
“过个欢乐的新年吧!我们的跨年派对最牛逼!”——宣传口号简单直接:有酒,有音乐,有朋友,有时髦、先锋的文化艺术……更重要的,有一个属于你的空间。跨年的夜晚,你肯定不想独自待在家,这样的日子怎么能一个人度过呢?应该约上朋友们出来玩,大家痛痛快快喝一场!
我像葛朗台似的带着账本和一大堆文件——各种合同、采购物料清单、活动申报单、执行进度表、发票……每天从睁眼就开始算账,最怕听到同事说哪个地方钱又不够,或者突然要买什么清单上没列出来的物品,以及供应商开不了正规发票……做活动那一个月大家每天加班到凌晨,好在人力不用花钱,我们的保安和保洁都是现成的——预算就批了那些,我得确保每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尽管如此精打细算,最后依然超支了,活动报批时公安部门要求增加外聘安保,包括额外租赁进门的安检设备等等,这又是一大笔计划外的费用。好在同事们非常能干、配合,大家想尽办法解决所有问题,圆满完成了任务。
2014年12月31日,整个上海洋溢在新年狂欢的氛围中,人们倾巢出动。外滩将举办规模宏大的灯光秀,全城还有各种大大小小的演出和活动。我们的派对做爆了——单是门口安检设备统计的入场人数就有三千多,这还不包括从后门进入的媒体、艺术家、各路朋友和关系单位的人。至今我都不知道那天夜里一共来了多少人,派对开始一小时后,我就陷入了恐惧——人太多了,那座二千多平米的建筑里从来没有同时容纳过那么多人。
我顾不上享受音乐和美酒,在极度疲劳中,不得不打起全部精神应对各种突发状况。对讲机响个不停,一会儿门口的保安说已经排队到淮海路,要求开始放人进入;一会儿里面的保安又说必须暂停放人,因为空间都挤满了……我们恪守安全原则,宁可得罪排队的人也不往里面多放,所以很多买了票看演出的人其实没有看到前半场。他们不知道演出是准时开始的——我们得在午夜12点前结束全部活动,所以11点半必须清场。单位所在的艺术园区平时晚上10点就关大门,这已经算是放宽约束,对我们网开一面。
当天夜里,外滩发生了踩踏事件。事发时我们并不知情。派对结束后,我跟同事们留下来喝了一夜酒,大家沉浸在劳累中,也为活动大获成功而高兴。我非常疲倦,同时又觉得满意——我证明了我的能力,这对未来开展工作将大有帮助。可是尽管已经痛痛快快地敞开喝,最后却毫无醉意,高度的精神紧张让人仿佛脱离了现实,后来过了很久都无法松弛。元旦清晨回家时,我在出租车里听到了新闻广播,很快又看到工作群里的各种消息,这时无边的恐惧才真正袭来。我不敢去想万一我们的活动出了纰漏应该怎么办,从当时现场的状况来看,发生任何问题都有可能。
要到很久以后我才明白,我人生的派对恐怕在那个夜晚彻底结束了——同时结束的还有灾难发生之前上海那无拘无束享受生活的氛围。所有欢乐、刺激、新奇、热爱冒险的心情,以及曾经对派对的热爱和派对给我带来的快乐,都已经彻底宣告结束。后来我还策划、举办和参与过许许多多活动,但无论在任何派对上,我再也没能享受其中。这就如同你跨过一扇门,从此便进入了另一个世界,门两端的生活在某个时刻之前无法彼此想像。这种在生活过程中获得的经验你肯定在一些书里读到过,但实际的滋味只会让人无话可说。
决定离开北京搬到上海时,我模糊地意识到往后将脱离从前的工作和生活圈子,迎接新的生活。可是新生活里是否会有新面貌,是否还能创造新的内容,我却无法确定,只感到一种长久的失落萦绕在周身。在首都机场等待飞往上海的航班时,我茫然地在记事本里写下心情,过去的一切就此画下句点。
“文艺终归是无用的,但并非像有人说的由于‘没有社会生产力’,而是需要花极大代价来维持一种无关目的、结局也不明的情怀。这代价可能是一生庸碌无为浪费的光阴,又或许是令你无法入睡并间或袭来、只能靠酒精麻痹的阵痛。最后你发现一切正在或始终要成为幌子,或迟或早,或者已经来临而你却并不自知。”
3
2020年1月,我跟几个朋友约好了去幸福路上一间地下音乐Club跳舞,那是他们最后一天营业,过后将从原址搬走,未来是否会重开则不得而知。当晚演出的其中一组音乐人从北京来,那曾是我非常喜欢的电子乐组合,上次看他们演出还是2012跨年夜在北京XP俱乐部。
去之前,我们在朋友家迅速喝光了一整瓶Tanqueray金酒,到那儿的时候大家已经有点儿晕乎乎的。人非常多,目测有超过500人挤在那个不大的空间里,氛围粗野,气味难闻,随处可见正在喝酒或已经喝醉的人。唯一的卫生间里到处是呕吐物,脏得无法落脚,当我在二楼一张小桌旁好不容易找到位置坐下时,躺在旁边的人“哇”地大吐了起来。
这家Club向来以脏乱著称,难以想象有一年我居然还在那儿过了生日,除了一个北京来的姐们儿和一个上海朋友,身边都是些不熟或根本不认识的人。朋友又约来了另外的人,后半夜开始下雨,大家莫名其妙地吹蜡烛切蛋糕,群魔乱舞,畅饮福佳白,喝到天亮才走。此后关于这地方荒诞、怪异、混乱的印象再也没刷新过,直到它的结束象征着我迎来了某种生活方式的彻底终结。
最后那个夜晚的感受同样很糟,意外事件频发——看演出时我又一次跟身旁故意冲撞别人的外国人吵了起来,一位同行的朋友喝大后蹲在街边不停呕吐,回家后发现我不知在哪儿弄丢了围巾。次日我们忍着宿醉的头痛在群聊里互发丑态照片——这可以算每次派对之后的余兴环节。看着一张张欢闹、闪亮、大笑、茫然、呆滞或疯狂的脸,那位呕吐的女士发表了精辟评价:“去时光鲜亮丽,走时残花败柳。”
现在我还能想起当时那种无疑是忍受的心情。朋友们劝我:“反正是最后一次,以后这地方就没了。”我懂他们的意思——好也罢坏也罢,过了这一夜一切都将不复存在,还有什么好生气的?但我不知道是不是为了告别才去,也说不清那儿究竟有什么值得怀念。那地方既不是上海最好的俱乐部,音乐也谈不上多么出色,环境一塌糊涂,混迹其中的人更是一言难尽。总体说来,我认为那是各方面都谈不上有水准的地方,可我又的确在那儿消磨了许多时光。
在门口的路灯下拍照时,我捂住了脸。回家后,我一夜没睡好,心中涌动着一股负面情绪,甚至让我开始怨恨以往热衷的夜生活。为什么要在那样的场所花费那么多时间和金钱?也许只是因为生活单调、兴趣匮乏,就像歌里唱的——我无处可去,特别是夜里。于是内心孤独,落入了寻欢作乐的陷阱。说到在上海的生活,除了工作,我基本上总是无事可做。或者很久以前就是这样,从小到大,除了混夜店或到处跟朋友喝酒,我没有谈得上生活的个人生活。
不知道为什么,我总会认识许多跟我差不多的人。那些夜晚在一起玩耍的人白天从无交集,其中很大一部分我甚至不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多大年纪、来自哪里。大家说着差不多的普通话,抽着差不多的烟,听着差不多的音乐,打发着差不多的时间。他们无论男女均衣着光鲜,大概率从事广告、公关、艺术、设计、市场营销等行业。上海多的就是这类时髦青年,以致在几乎所有派对上你总能看见一些眼熟的面孔。从前你们或许在永福路的烟杂店擦身而过,也曾经在襄阳北路24小时馄饨店坐在隔壁桌,巨鹿路、富民路、长乐路、东湖路……还有前几年被整理掉的永康路,到处都是这些人的身影。
2015年我住在永嘉路时,旁边的永康路还是浦西梧桐区最热闹的酒吧街。每天从下午开始路上就聚满了喝酒欢闹的人群,天黑后景象就更加可观。我曾经在那儿无数次遇到我的英语老师Benjamin——手里举着一大杯啤酒,远远地跟我打招呼。他来自英国,有两条漂亮的花臂和一口正宗伦敦腔。在课堂以外的地方跟他说话总会给我造成错觉,好像有部在上海拍摄的电影正在放映,而我也是其中一个角色。
有些人追求的永远只是形式而非内容,过去我无疑就是形式主义者中的一员。我选择住那个街区正是因为喜欢这种氛围——下班后可以直接跟朋友约在家附近的酒吧见,尽管那条街上的调酒水平很少达到令人满意的标准,但鲜亮地坐在马路边的高脚凳上,面前摆着一杯美观的酒,跟衣冠楚楚的朋友一同接受过往行人的注视,在自由的氛围中畅饮……这一切无疑可以填补那些不足。
在漫长的生活中,我一边努力试图过上严肃的精神生活,一边又无法遏制自己身上轻浮和虚荣的一面。这两种追求虽然谈不上完全对立,但其中难免存在许多矛盾之处。一个拥有严肃精神生活的人,将很难或每每无法真正融入享乐氛围,因为后者并不需要思考,而思考却是前者感受生活的基石。于是我总显得郁郁寡欢、若有所思,多喝了几杯又会被突如其来的情绪攫住,于是无法自控地剥掉文明人的外衣,经常张牙舞爪与人争吵或干脆滚倒在马路边。
每个喝到天明次日又假装正常去上班的时刻,我都搞不清我到底在干什么,这种日子一点儿也不轻松。为了寻求解脱,我先是离开了职场,又开始逐步远离从前浮躁的生活方式。大约从五年前开始,夜间我不再外出胡混,除了跟外地远道而来的朋友见面,我很少再踏足夜店和酒吧。但每年有那么几次,依然会经不住朋友的邀约去参加一些派对。什么日本音乐人的夏日跳舞派对啦,澳洲冷门DJ的迷幻之夜啦,说唱歌手的潮爆演出啦……我们会根据主题选购服装,并在微信群里讨论彼此的妆容,每个人都用心打扮,所有准备只为了进门那一刻闪亮登场——我喜欢这种派对精神,无论这是不是虚荣的另一种表现形式。
当我回顾从前的日子,发现绝大部分内容都与喝酒有关——不是喝酒,就是在什么地方跟谁一起玩。对于生活,我所有的热情大概就体现在这一点上。除此以外,发生的大部分事情转眼即忘,与喝酒有关的内容反倒记得很牢。那些时间、地点和人物仿佛地图上的坐标,沉迷漂流、目的地不明的人只能以此标记自身存在过的痕迹。我不得不承认这样的生活方式对我而言可能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为什么一个人能如此永不厌倦地饮酒作乐呢?
最终,派对向我揭示了答案。所谓“派对精神”,在我看来是一种奋不顾身的享乐精神,包括兴致勃勃的参与感、奇思妙想的装扮灵感、对奇遇的期待和追求刺激的冒险欲望……每场派对都如同变装舞会,人们可以尽情释放对审美和享乐的激情。派对还让我见识了生活——永远有更好看、更年轻、更有钱、玩得更彻底的人,在争奇斗艳的场合从来没有最出色的唯一,所能看到的只是各式各样的人群和五彩缤纷的颜色。
长此以往,认识外部世界的同时,人也将逐步建立自我认识,渐渐你明白了自己的底线在哪里,又有哪些是你不可能做到的事情。这些经验只能在社会生活中获得,尽管工作和生活也会带来这样的教育,但比起这些,我觉得派对还不错,至少偶尔会很快活。可是本质上的问题从来没有得到解决,精神危机和内心空虚不可能在寻欢作乐的过程中完全消弭。也许人们从来都夸大了文化的作用,又或者我一直对形而上的东西怀有过高期待。
到头来,人们参加派对只是为了打发一会儿时间:跟朋友玩玩,随便喝上几杯,见面时亲密拥抱,散场就各自回家。这是一种共识,没人会伤感——某种程度上,都市里的派对永远不会结束,因为永远会有下一场。而无论派对多么精彩,意外结识的人如何有趣,过后你们将很难或几乎不会进入彼此的生活。
派对是一种只在特殊时间与场合才会发生的事件,其中每个因素都是偶然,并非任何人的生活常态。没人会思考背后的意义,所以曲终人散的时刻迟早会来,尽管那种潇洒的派头看起来非常符合每个玩世不恭者内心的需求——在城市无边的夜色里,当你投身于更广袤的、群体性的空虚之中,个体空虚仿佛便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
4
2022年冬天,我与G在大理的一间酒吧意外重逢。当天晚上有个派对,两位爵士音乐人即兴演奏后,有DJ放音乐跳舞,主题大概是“重返未来”之类。来的人大部分常住大理,也有一些消息灵通的游客,没有人针对主题刻意装扮,这是另一种散漫自在的氛围,与上海完全不同。随着人越来越多,气氛很快热烈起来,我坐在吧台边喝酒,当G推门进来时,我们同时看到了对方。他很快露出熟悉的笑容,抬手跟我打了个招呼,穿过人群径直走过来坐下。
G如同往常那样打扮得体——短款翻毛领皮外套,里面是件浅色T恤,胡子刮得干干净净,头发也梳得很妥帖,凑近能闻见香水味。有时我想,他大概就是那种天塌下来也要保持发型不乱的人。自从上次在黄浦江西岸晒完太阳后,我们便再没机会见面,不知不觉竟已过去两年。这几年上海发生了许多事,认识的人一个接一个离开,听说他在泰国待了很长时间,而我也彻底结束了从前的生活,目前正在旅行中。
“你在喝什么?”G看了我的酒一眼,兴致不高地翻着酒单。
“猎杀幸存者。”
“有意思。听起来很够味,我也来个一样的。”
酒吧老板是我老友,数月前匆忙离开上海后,我辗转来到大理,在她家楼上的空房间住下。她一看便知G是又一个离开上海后流离失所的人,这几年她的酒吧安抚了一波又一波这样的人。她问:“你俩约好了来的?”我答没有。她露出好看的笑容,“下一轮喝江湖儿女吧,我请客。”G捧场地鼓起掌来。
几杯酒下肚,我们脸上微微泛红,情绪已经调动完毕,开始叽里呱啦地大聊酒单上那些名称奇特的调酒,又频频点酒,大有不醉不归的架势。关于这两年在上海的生活和离开后的近况,我们没有多谈,要消化那些遭遇恐怕还需要时间,反正眼下情况一目了然——旧世界分崩离析,尽管我们驾驶小船逃离,但过去的生活几近崩塌,未来不过是在继续在各自内心的汪洋上漂流。
爵士音乐人已经表演完毕,人群中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这场即兴演奏水准很高,再次证明大理是个藏龙卧虎之地。DJ开始播放转场音乐,随着熟悉的前奏响起,地下丝绒乐队那首《All Tomorrow's Parties》不知不觉将我的思绪带回从前,唤起了许多往昔回忆。
And What costume shall the poor girl wear
那个可怜的女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去参加所有明天的派对
A hand-me-down dress from who knows where
只有一件不知道哪儿来的旧外套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去参加所有明天的派对
And where will she go and what shall she be
她该到哪儿去 她又该做些什么
When midnight comes around
当午夜来临之际
She'll turn once more to Sunday's clown
她将再一次变回星期日的小丑
And cry behind the door
躲在门后哭泣
And what costume shall the poor girl wear
这个可怜的女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去参加所有明天的派对
Why silks and linens of yesterday's gowns
为什么不穿昨日的丝绸与亚麻长袍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去参加所有明天的派对
And what will she do with Thursday's rags
她该拿星期四的破衣服怎么办
When Monday comes around
当星期一来临时
She'll turn once more to Sunday's clown
她将再一次成为星期日的小丑
And cry behind the door
躲在门背后哭泣
And what costume shall the poor girl wear
这个可怜的女孩要穿什么样的衣服
To all tomorrow's parties
去参加所有明天的派对
For Thursday's child is Sunday's clown
星期四的孩子就是星期日的小丑
For whom none will go mourning
没有人会为她感到哀伤
A blackened shroud, a hand-me-down gown
一块黑色的裹尸布,一件别人穿剩下的袍子
Of rags and silks, a costume
用丝绸和破布拼成,一件戏装
It's fine for one who sits and cries
它正好适合那个坐在那儿哭泣的人
For all tomorrow's parties
为了所有明天的派对
…… ……
1995年,认识的哥哥在故乡小城开了当地头一间迪厅,位于工人文化宫旁边的老干部活动中心四楼。当一个夏天的夜晚被朋友叫到那家“迪迪Disco”时,我已经在旱冰场接受了最初的欧美舞曲启蒙——香蕉女郎、荷东迪士高、水叮当……在旱冰场上班的一名二十来岁男青年每天都放这些歌。当时我并不知道“迪迪Disco”将在此后的人生中起到什么作用,而这个夜晚堪称一次重大转折。
我有些懵懂又心怀期待地向楼上走去,越靠近四楼音乐声越响,几乎到了震耳欲聋的程度。每一次鼓点的节奏都吻合着心跳节拍,站在“迪迪Disco”门口时,我不得不用手扶着楼梯——就连栏杆都在传递那种激烈的震颤。整栋大楼仿佛在震动,周遭的世界嗡嗡作响。那个瞬间我头一次感受到某种从未有过的激情,未知的生活打开了一扇门,里面有什么在召唤我。心跳得越来越快,我浑身冒汗、头脑发热,迫不及待要投身到音乐和夜晚的世界中……多年后回想起来,这应该就是我青春期的开始。
许多年轻人正在舞池中热舞,我目不转睛盯着看。他们是怎么做到在众目睽睽之下如此尽情肆意地舞动?我也想像他们一样。过了不知道多久,突然音乐开始变化,节奏明显慢了下来,旋律听起来更优美。有人喊了一声:“恰恰时间到!”更多的人从四面八方涌出来,迅速在舞池里找到位置并面对面排成好几行。接着,我听到了那首伴随我一生的歌——前奏部分一阵急刹车声,一男一女说了两句话,很快音乐响起,人们随之欢乐地跳起了恰恰。他们像排练过似的按照节奏挪动脚步并左右晃动身体,脸上洋溢着喜悦和陶醉的神情。
这首歌叫《Cha Cha Cha》,原曲出自Finzy Kontini于1987年发行的专辑《Place to Place》,当天晚上播放的是经过重新编曲的荷东迪士高版本。自从那个夜晚听到这首歌后,很多次我再去“迪迪Disco”都是为了能再听一遍,怎么也不厌倦。那种排舞并不复杂,我当晚就学会并跳了起来,很快我跳得越来越好,并在舞池里见到了过去在电子游戏室和旱冰场里遇到的一些人——不论在什么地方,喜欢这种生活方式的多半都是类似的人。
“迪迪Disco”的门票多少钱我已经忘了,印象中我从没自己花钱买过票。我跟同年级的几个朋友总是逃掉晚自习,想尽各种办法轮流装病从学校溜出去,以便能在10点之前到达老干部活动中心。跳完恰恰我们就走,很少留下来多逗留,当时毕竟还是初中生,再怎么叛逆、没规矩,也得有个限度。这种生活当然隐藏着危险——你根本不知道在夜场里会碰见什么人,可周遭的氛围又的确显得天真、单纯而快乐,年轻人们只是聚在一起跳舞和享受音乐,那些喜悦而快活的面孔丝毫不会使人联想到任何阴暗、猥琐和低级的画面。
在“迪迪Disco”度过的时光谈不上参加什么派对,但那种脱离日常的体验或许就是派对的启蒙和夜生活的开端——我从此爱上了迪斯科音乐,并最终成为复古风格的终生追随者。所以人生有时神秘莫测,不是吗?许多看似不相关的事背后却有着隐秘的联系。成年之后,我辗转一个又一个城市,开始一场又一场派对,认识了更多的人,又与更多人告别,直到懵懂无知的少年步入中年……我猜我还是想纪念,在已经度过的前半生,总归有许多事值得纪念。
G问:“你在想什么?”
我举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回忆了一会儿往事。”
“这杯江湖儿女真的好喝,从来没尝过的味道,”他又叫了两杯酒,“跟你一起玩,总有奇奇怪怪的惊喜。”
“可不是吗,人生可以没意义,但一定不能没意思啊……”
随着转场音乐结束,DJ开始播放舞曲,酒吧里人声鼎沸,渐渐听不清聊天的声音。越来越多的人脱掉外套进入舞池,他们肆意喝酒、纵情跳舞,每个人都显得如此丰富和立体。这个平凡的冬夜瞬间变得生动起来,那些在闪烁灯光下时隐时现的脸庞不止好看,甚至还精彩极了——每个转瞬即逝的片刻仿佛都能发展新的故事,就像一场又一场永不结束的电影。
酒意迅速上涌,我有些头晕目眩。G依然很清醒,认识这么多年,喝过一场又一场大酒,我从来没见他醉过。这真是件奇怪的事情,我想,我们这些在派对上相识的、奇怪的陌生人,可以随时坐在一起痛饮,分别后又从不想念。不可否认,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种关系,就像世上万千的派对永远对所有人敞开大门,只要你愿意,随时可以自由来去。
“我曾经想过自杀,”G突然没头没脑地说,“这个念头今年春节后开始频繁出现,结果正考虑着死法,我家小区突然就被封起来。”当时大家都以为局面是暂时的,谁知事态很快急转直下,直到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秩序被彻底摧毁。4月15日,G在家里目睹对面楼栋的一位住户跳楼身亡。
“报警后,一直没有人来处理现场,物业只能撑了把户外阳伞在楼下遮挡一下,结果顾头不顾脚,他的一双光脚就那样一直露在外面,直到天黑得看不清。”这件事给G带来很大刺激,“好像已经有人帮我把没做的事情做完,在家里哭了几天,觉得就这样死了也没什么意思……不过就那样随便摆在地上,潦草的样子。”于是他喝光存酒,决定“再活一阵子好了”。
我不知道能说什么,沉默地拿起酒杯跟他碰了一下。看着周围喧闹欢笑的人群,我们好像成了两个内心破损的人,如同下错车站的旅客,面面相觑,茫然地停留在陌生的地方。刚才仅仅听到我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G已经用手掩饰着脸流下泪来。他曾是那样意气风发的一个人……我们的人生何以至此?我不敢再追问,也已经无话可说。
醉眼迷离中,周遭一切变得摇摇欲坠,过往张扬、纵情的一张张面孔已经成为远去的暗影——原来大家沉迷的不过是用积木搭成的房子,轻轻一碰就塌成断壁残垣。喝完最后一杯酒,我们走到门外告别。大风从身边呼啸而过,将地上的纸片和尘土吹向远处。G照旧潇洒地挥挥手,头也不回转身离开。我们没有约下次见面的时间,反正人生海海,像我们这样的人,终究会在哪里的派对再重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