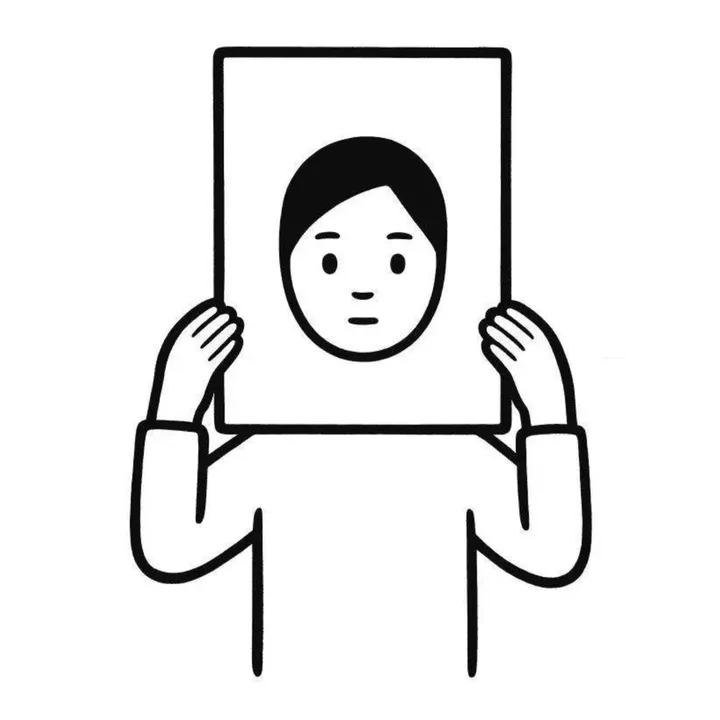艺术令人走火入魔,还好你没有什么建树。
1
胡丽丽左手拿着巴掌大的笔记本,右手握住一支圆珠笔抵着下巴等我说。她背靠宾馆的窗台,铝合金凹槽滑轨里还有落进的雨水,越积越多,更远处,黑夜被细密的雨丝切割、阻断,潮气悄无声息笼罩大地,又一个雨季潜入南方大陆。我说,去年十一月,我们到那儿,土地是龟裂的,车轮扬起的尘溅到眼睛里,颗粒大得很,幸好我近视,戴着眼镜,陈教授就倒霉了,一路拿护腕巾擦眼,后来索性把魔术头巾往上拉,把脸都盖住。胡丽丽边写边说,没有脸的陈建德。我拿起床头柜的一盒烟丢向她,说,说什么呢?你们搞新闻的不是讲究严谨吗?烟盒弹在她隆起的胸前,顺着绿色的裙子滑落地板,胡丽丽拾起来往回丢,说,搞娱乐新闻行不行?
我接住烟盒,抽出一根,点上。胡丽丽说,你继续,别管我就行。她回头打开了窗户,雨气扑进来,窗帘随风轻微摇晃,像个耳朵,象的耳朵。
去年初,我们从养鸡场回来,本是拍母鸡下蛋和鸡蛋破壳,幼小的肉体啄破蛋壳的那个瞬间,柔嫩、易碎,琥珀般纯净的画面被收进陈教授的佳能R5微距镜头。我正准备收起架好的设备,他却拐进了屠宰区,出来后,说上一组拍摄可以结题了。我也没多想,我们拍了很多诞生时刻,哺乳类,蛋生的,卵生的,还去海洋馆蹲过一个月,为了拍一只小海豚的出生。回来后,陈教授草草提交了结题报告,办了场小型展会。事后,一直在寻找新的母题,我也有几个提议,例如拍拍人像,小孩,老人什么的,但都被否了,其实他早就有数了。
正式开始拍摄死亡时刻是秋天,青蛙吐出的舌头,弹射在一只苍蝇身上。一条蛇,吞下一只石头缝里的老鼠。猎狗撕咬一只野兔。我们不设局,刻意让动物吃掉动物有些不人道,但有时候看一只活蹦乱跳的野兔突然被野狗咬住脖子,内心还是会咯噔一声。陈教授不会,手都不会抖,稳定器都不用,手掌托好,快门按下,画面就卡住了,这是他说的,卡住了,不上不下的,野狗介于吃与不吃之间,兔子也是,介于死与不死之间,一切只是一个平衡,我们捕捉了平衡点罢了。他疯狂沉迷于类似的捕杀时刻,我作为助手,很难提什么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去秦岭拍野狼,拍熊,走了三天,在树丛里藏着,对焦,捕捉到一头熊,还没等它进食,发现我们后就跑掉了。夜里的狼据说是凶猛的,我们灭了手电,只衬着月光,循着狼吠,走到山头,狼群也早就溜走了。那些动物嗅到人类会跑,恐惧是天生的吗?陈教授一言不发往山外走,出了山,我们回头望,雾气笼在半山腰,像一条条水泥盘山公路,山头也更像是一座人类建筑。他说生命不应该是畏惧,那些狼和熊在一定程度上是致命的,极具杀心的自然攻击性已经被无形中驯化了,这个你懂吗?这也是我们不去动物园拍摄的原因,铁笼里的老虎吃一块铁钩上的腐肉,凶猛的狮子钻过一个个打火机点燃的铁圈,那是马戏,蹩脚的马戏,跟自然规律无关,跟本质无关。深山里的野生动物,已经是藏的状态,早就被包围了,我们像射进山林里的子弹,弹孔已经遍布每一棵无辜的树干上了。
胡丽丽拽过木质沙发,背对窗台坐好,雨丝飘在头发上,令其服贴在额头,笔记本放在并拢的膝盖。她并没有在记,只是听我说。我把快燃尽的烟摁死在烟灰缸里,又捏起一支,继续说。
陈教授订了机票,我们乘坐卡塔尔航空,从广州出发,两天后落在满是沙尘的非洲草原上,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导游是国内提前找好的,非常熟悉自然保护区的边缘地带,价格不便宜,车子也是配好的老款悍马,只有横杆,没有车窗,车座底下藏了把双管猎枪。导游想得极为周全,我们将要踏足无人之境,他用英语告诉我们枪支的使用方法,我仔细听,保险、子弹、折舌机关、管筒闭合,陈教授从包里拿出相机,开始旋上镜头。面前是枯黄的矮草,小腿的裤脚被草茎刮擦着,远处零星的树,像站岗的人,云状的树冠,耸耷着,却好似用力托举着什么。再往前走,就出了保护区,Every bullet has its billet,这是导游说的,每颗子弹都自有归宿,生死有命。陈教授也听懂了,径直往前走去,我心里一哆嗦才想起来,脚下踩着的土地,特不真实,距离我熟悉的校园大约一万公里,也不知道这一切是否值得。我握紧双管猎枪,看越野车掉头往回开。两天后,它会在原地接我们,我背了足够的食物,胸前挂着指南针和GPS定位装置,就这样,我们出了保护区,陈教授早已举起了镜头。
那头小象是在当天下午被咬伤的,我们趴在矮草丛里一动不动,狮群距离我们一百米左右,一直盯着附近的象群。狮子是不会擅自攻击大象的,体格差得太多,但是也不免有些熊孩子掉队。有只小象没跟上队伍,不知道怎么跑到狮子那里,我和陈教授同时举起相机,他聚焦在那头小象身上,我则负责拍摄全景。他说,9点钟方向。我切出镜头视野,看到头狮将象群缓缓隔开,留下那只失了方向的小象,它开始莫名地向我们奔来,七十米、五十米、三十米。它突然停在原地,宽大的耳朵不协调地前后扇动,随即趴在地上,我撑起身子,视线越过象背,看到一头雄狮疯狂摇头,已经撕咬住了小象的后腿。快门咔嚓、咔嚓,在我身边响起。陈教授小声说,趴下。小象的哀鸣像一只鸡,我不知道为什么这么联想,我想起我妈把鸡吊起来放血的场景,又想起野狗咬住兔子的脖子,象鼻整个拍在地上,像一只手,尽力往前伸着,在够什么,二十米,也就只有二十米。我握紧双管猎枪站起来,大吼一声,狮子先是一愣,接着抬头看我,那东西,鬃毛围着脸一圈,嘴巴还有深深的血痕,它试图向前走来。陈教授拉住我,他说,你知道自己在做什么。我按导游说的,打开保险栓,往地上开了一枪,雄狮没有后退,我甩开陈教授,继续往前走,又朝地上开了一枪。我和雄狮对视,它的眼神没有一丝恐惧,浑圆、坚硬,舌头偶尔探出,舔舐着嘴唇。我不知道就这样互相盯了多久,额头沁出的汗已经滴进嘴巴里,湿咸,我像一棵树般坚定,一动不动,其实我的子弹已经打空了,但是我还是举着,努力举着那把猎枪。雄狮最后还是退回去了,大概是早就吃饱了,攻击小象的部位也不是喉咙,像是在玩而已。我检查了一下小象,也没有别的办法,它的后腿血色模糊,双耳翕动,鼻子撑地,试图站起来,却又总是失败。
下午导游提前来接我们了,我和陈教授坐在后排,我一直紧紧握着那把猎枪,手在颤抖,尽管我并没有射击狮子,但是子弹飞了出去,硬硬地击在地面上,那些荒草,荒草里的土,土里的石块,枪口巨大的火焰,枪膛发出的爆裂声。越野车飞驰而回,距离一处河滩时远远地停住。我们侧头往外看,小象瘫倒在河边,母象用长鼻子拱它的肚子,小象没有任何反应。母象用鼻子抽起河里的水,喷到小象的头上,接着仰天长鸣,跺着脚下的大地。我感觉到了震颤,草原的热气蒸腾,一切扭曲在视野里,陈教授举起相机,聚焦到小象身上,按下快门。他说,你救或是不救,死亡就在那里。我说,那是因为我没有提前开枪。
胡丽丽打断了我,她下了沙发,坐在床上,靠着我说,如果你提前开枪呢?会怎么样?我搂着她,说,会怎么样?陈教授说,除了我的枪声,还有偷猎者的枪声,这个世界我们管不过来的。他没有拍到那个平衡点,我们这一趟没有结果,他倒是不生我的气,我很内疚,你知道吧?在回去的路上,我翻看相机里的照片,小象环在母象的周围跳走,用鼻子缠绕母象的鼻子,生命还在,它们会一直在镜头里。
胡丽丽说,所以还要去。我说,是的,还要去。她说,签证我也有,这次带上我。我说,不带,我们不带女性。胡丽丽把我推倒在床上,跨步骑在我的身上说,我像不像一头狮子,雄狮。我说,你别闹了,陈教授不会带你去的。她抓住我的衣领,说,死亡的距离,这是我为你们写的实录,死亡的记录者,横杠,陈建德和他的小跟班王川。
2
我们从非洲回来,就被陈丽丽盯上了,她研究生毕业课题还没有着落,索性肥水不流外人田,把校内这两个摄影家拍成新闻。这是她亲口说的,和我谈恋爱也只能算是附加价值,有种打入敌人内部的感觉,多少也算师生恋。我告诉她,我就是个教授助理,顶多算个打杂的,要是喜欢师生恋,麻烦还是找陈建德。她一下就被我逗笑了,但还是蛮认真地打听我们拍摄过的作品,也看过一些,这次非要跟着去,我实在做不了主,也不知道该怎么跟陈教授开口。也算是有种拖家带口的感觉,但胡丽丽坚持说,不要提我们的关系,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我尊重她,准记者的新闻撰写,我们就当她的毕设。
陈建德将近六十岁,这次旅行也算是摄影课题生涯的结束了,如果不是上次我的干涉,也许去年就可以结题了,买张机票,去美国看儿子,拍拍小孙子之类的,享享福。狮口活物,一直是他想拍摄的死亡系列之一,几乎沉迷地让我帮他找到了各种视频资料,研究狮子的进食,牙齿的锋利程度,口腔的大小,舌苔倒刺,撕咬的力度,拍摄角度,他已经把这种猎杀时刻看作一种超脱生命本质的艺术,用摄影营造的非自然死亡的压迫感,踩在平衡之上的记录。越是理解他,越是觉得自己去年拿着猎枪冲上前去的行为无比愚蠢,我们企图改变什么呢?
陈建德约胡丽丽在家里见面,我也没去过,不太了解他的私生活,按他的说法,最好的记录就是关于生活的一切。胡丽丽多少有点紧张,没想到陈教授答应得这么快。我跟她说,就是约个见面而已,没答应要带你去。她倒是很自信地说,成功的记者就在于成功地迈出了第一步。
周六晚上,广州又下起了大雨,学院到处都泥泞着,山坡上冲下来的土覆了水泥路面,后勤处开出铲车清理着道路。道阻且艰,胡丽丽说。我懒得理她,有时候她极其贫嘴,不知道是不是记者的特色。家属院在学院后山,小径也已经布满草叶,胡丽丽脖子上挂着相机,小心翼翼地走,我搀着胡丽丽上到台阶尽头,一栋灰色二层小楼露在了眼前。她说,这合不合规?我说,你一会儿问他本人得了。她又说,你来过吗?我说,没进去过,经常送相片。
陈教授穿着白色T恤,套着一件摄影马甲,下身穿着棕色短裤,打着把黑伞,已经在院子门口等着我们了。我把手从胡丽丽后腰上抽回来,提前说好的,不提情侣的事儿,尽量让工作关系变得干净一些。换下满是污泥的鞋子,陈教授领我们进来,屋子没有外面看得大,里面显得有些局促,没有所谓的客厅,进门的房间里除了窗,围了一圈书架,中间立一张长方的书桌,上面放着两个相机,七八个镜头,长长短短,三脚架立在落地窗边,像极了工作室,跟家不着边。陈教授继续把我们往里领,在一间相对宽松的卧室站定,这间屋子看上去比所谓的客厅都大,地面上只有两张布质沙发,墙面上都是相片,整齐地按照时间顺序和主题进行分类。陈教授说,看吧,小王也没来过,对吧。我和胡丽丽先是看了看四周,我找到了我们在养鸡场的照片,他都有备份,算是个小型展览,在养鸡场破壳照片旁边,还有没展出的屠宰照片,鸡血流了遍地,成片的鸡脖子吊在火钩上。我转回头,陈教授已经坐好了,示意胡丽丽也坐下,她也转回身坐好,我则站在她的身后,安静地等着。
陈教授说,新闻系的?胡丽丽说,快毕业了,也对摄影感兴趣,想记录一下您的工作。陈教授笑着说,我这也没什么好记录的,就这间房子,就是全部了,我和小王俩人,两年拍摄的东西都在这儿了。胡丽丽拿出小本子,有模有样地记,说,都是有主题的吗?陈教授说,也不完全是,也看心情,前些年拍静物,建筑,就立在那儿,屋檐,石墩,几片玻璃反射的光,好看,有愉悦感,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但时间久了,就发现,那都是人为的,刻意的,你懂吗?我们这个世界过于刻意了,人总是想着改变什么,对吧,小王?陈教授说完看着我,我点点头,说,啊,是,有些东西改变不了的。陈教授点点头,继续说,去年开始,我开始拍死亡系列的相片,你是因为这个来的吧?胡丽丽停下笔,说,是的,我是听说老师您在拍死亡的距离,好像是这个名字。陈教授说,是的,死亡的距离,我们一直在尝试,除了距离以外,还跟心境有关,你必须放下畏惧,真的像一个死人一样,才能真的接近死亡,还只能是接近,我们永远无法切身体会。死亡的距离,是一种摄影的伪记录,把那一瞬间,从生到死的一瞬间,用画面保存下来,就足够了。人啊,总是执着点什么。
胡丽丽又问了几个问题,陈教授耐心地回答,我听得多了,开始四处走动,在屋里看着各种我没见过的相片。一侧的墙上已经为死亡的距离系列摄影留好了位置,林中的老虎是我们在华南勉强拍摄到的,嘴里叼着一只家养的鸡,即使公开了一阵,也没有人相信,人们不愿意相信一只野生老虎生活在几里地的村外,用各种技术手段极力证明我们是电脑合成的,也是从那次开始,我们开始寻找其他机会。这组照片,会在暑期后渐渐丰富起来,结题讲座会在大礼堂进行,大屏幕上打出一行字,死亡的距离,主讲陈建德,助理王川。也许我们会因此获奖,因拍下各种野生动物的獠牙,撕咬血肉,斩碎生命的本真而获奖。我看到墙上还有一幅特别的相片,跟摄影的主题都不靠边,是陈教授和一位男生的合影,我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说,老师,这是您儿子吧?陈教授转回头往上看,说,是的,陈少华,美国念书,也是读的摄影。胡丽丽说,子承父业。陈教授说,两年前去世了,活着的话应该和你差不多大。胡丽丽扭头看我。他继续说,那张照片是唯一的合影,摄影就是这么神奇,总觉得他还活着,就一直那么大,不会再高,也不会变胖,手掌搭在我肩上,现在肩膀上还感觉像是有个人在拍我呢。说完他自己笑了起来。我和胡丽丽都没再说话。
最后胡丽丽还是提了正事,她说下个月要跟我们一起去非洲,为了让记录更真实、更原始,需要切实跟随陈教授。陈建德先是一愣,然后看了看我,我说,记者可能都这样。胡丽丽说,普利策新闻奖,说不定我毕业就拿奖了。陈建德又被逗笑了,上前拿起胡丽丽的手,正反面看了看,说,你这手好像也不仅仅是按下快门那么简单。胡丽丽说,老师您说得还真对,我还会掌勺呢。陈建德大笑起来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
这就算同意了。
胡丽丽把相机放在沙发靠背上,设定了倒计时,接着又跑回来,相机发出滴滴声,我们三个并排站着,面对镜头,进入镜头,被咔嚓声锁住。
3
突然有些激动,胡丽丽说。我从迷糊中醒过来,看见她靠在宾馆床头上,敲击着笔记本电脑。我说,你还没睡。笔记本屏幕上闪烁着一行标题,摄杀时刻。我说,你起的名字?胡丽丽把电脑屏幕合上,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柜,重新滑进被窝里,说,你们,特像杀手。我说,什么?她说,摄影杀手,记录死亡时刻。我说,你别这么激动,其实挺危险的,上次跟你说了,陈教授倒是无所谓,也才知道他孩子死掉了,怪不得这么豁得出去。胡丽丽在被窝里搂紧我问,那你豁得出去吗?
我开始吻她,睡意已经褪去大半,她迎上来。我说,我争取保证你毕设顺利完成。她笑起来说,那我保护你,生命完整。我说,那咱不妨先造个小生命。说完我箍住她的身子,她挣扎不得,开始咬我的嘴唇,我疼得叫起来。她才停下,说,我觉得陈建德有点着迷了。我说,怎么讲?她说,你注意到没,那面墙上有些照片,太血腥了,我欣赏不来,如果我是你,天天跟着拍这些,我会受不了的,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我说,你的意思是?她说,我也不知道,说不上来,艺术令人走火入魔,还好你没有什么建树。我把被子扯过她的头顶,她哈哈大笑。
胡丽丽签证有些问题,延迟了半个月,还是陈建德搞定的,我们在七月中旬开始坐上飞机。陈建德话少了很多,上了飞机便戴上了眼罩,像有心事。我和胡丽丽坐他两边,一路没法交流。她已经开始写稿子了,看来是真打算以我们为蓝本,做点什么出来。我拉着她的手,很快就睡着了。
再醒过来,飞机已经落地了,转机后,座位分散开,我和陈建德坐一起,胡丽丽在前面。陈建德没再睡,一直看着窗外。飞机重新穿过云层,耳压升高,我闭上眼睛咽气。胡丽丽是你女朋友吧,陈建德说。我没有犹豫,随即说,是的,老师。他说,公费旅游。我说,没那个意思,她真想给您来个采录,稿子都在写了。陈建德说,这个世界怎么运作的我都知道,不能再无功而返了。我说,我明白。陈建德说,那就行。飞机颠簸起来,我抓紧座椅。陈建德说,陈少华被枪口抵在额头上,还没来得及说最后一句话。我说,枪?陈建德说,其他的什么都不知道,死亡比我们想得简单得多,我甚至没有去把遗体运回来。我说,还在那儿?陈建德说,不清楚,没有遗体,就没死,对吗?我说,是吧。陈建德说,得了,别骗自己了。你救不了那头小象,你能做的只是迅速按下快门,不停地按下快门。王川。我扭过头去,看着陈建德望着窗外,他说,什么都不要管,听见了吗?我没说话,飞机持续抖动,机舱传来报警音,机组人员用一串标准的英文安抚着大家。
导游接到我们时已经半夜了,我们就近住下,第二天开始前往马赛马拉自然保护区。导游看见胡丽丽,两眼放光,让她坐在副驾驶,和她不停地用英文交流。胡丽丽每句都应,又扭回头用中文跟我说,我去做压寨夫人怎么样?他们马赛人的长矛能杀狮子,比你的相机强多了。我白她一眼,陈建德说,他们还配有长刀,就别在腰里,另外,一夫多妻。胡丽丽看了眼导游的腰,一把皮套的长刀系在腰间,接着抱起胳膊,拉低了帽檐。
导游告诉我们,这里已经很久没下雨了,我问他是不是一直不下雨,他笑着回复,雨季来了天天下雨,但是最近很奇怪,动物也都焦躁,晒透了。敞篷越野车里都是土,扭曲的光穿不透上升的热量,地上像是铺了一层膜,下脚后的地面明显比去年烫得多。陈建德拿出相机,从背包挑选好镜头旋上,又拉上了防晒衣的帽子。胡丽丽穿的靴子能高三厘米,和我差不多了,她说,这笔记本电脑带着没用,数据都热化了。我让她留了相机和记录本,把电脑让导游带回营地。导游从车座底下照例掏出那把双管猎枪,递到我手里,这次没有多说,知道我去年开过扳机,只是笑了笑。胡丽丽说,Every bullet has its billet。导游大笑,用马赛语说了几句,谁也听不懂。胡丽丽说,他夸我。我拿枪屁股杵了杵她的胳膊,接着把枪背在身上。
越野车往回驶去,沙土如一面黄色的瀑布。胡丽丽说,那天晚上你讲的故事,我现在站在故事里了。我说,这故事也属于你了。陈建德已经走出去五十多米,站在一棵树下,调整着镜头。这儿不记得是不是去年那个地方,草原上的各处看上去都一个样,边缘地带更是,这里相对安全,没有保护区里动物那么密集,也没有非保护区偷猎者那么嚣张,相对而言,自然而又恰到好处。我和胡丽丽跟了上去,陈建德蹲下身子,在树下发现了一具动物的尸体,裸露的胸腔,一半坠着腐肉,一半仅剩骨头。陈建德说,这是一头小犀牛,牛角还在,肚子是被狮子吃的,这个撕咬力度,不可能是别的动物了。胡丽丽看了一眼,扭头把早上吃的吐了出来,我扯着魔术头巾遮住鼻子,举起相机,按下快门。胡丽丽说,咱的车走了吗,麻烦叫回来吧,我已经害怕了。我拉住她的手,说,小点声,从现在开始,提高警惕。陈建德说,附近有狮群,应该是越野车把他们惊跑了,我们再找找看。
我拉着胡丽丽跟在后头,陈建德独自迈着快步,异常兴奋。上午十点,云像大片棉絮般浮在靛蓝天空的底端,几只秃鹫在翱翔,热从体内拥挤着迸发出来。我背紧身上的猎枪,又看了看子弹袋里红头的霰弹。胡丽丽问我,这东西怎么用。我说,怎么了?她说,你告诉我,我感觉安全。我拿下猎枪,按导游去年说的,跟她说了一遍。她问,你有许可证吗?我说,我的大小姐,你现在在非洲,不法之地的摄影天堂。
下午,我们找到一处小湖泊,急剧骤缩的面积,可以看出干旱的程度。陈建德让我们趴在一棵树下的草丛里,开始放下设备,调整焦圈。胡丽丽问,在这里就行吗?我说,水,在这里是必争的,死亡也在这里发生。我指着湖边一处物体说,你看那个。胡丽丽顺着我的手指往那儿看,我也掏出相机,调整长距离,把相机屏幕递给她看,说,斑马,被啃食的斑马。陈建德说,胡丽丽,你可以给我们拍几张照片了,小心点,可以往后撤一撤。胡丽丽说,我不,我后悔了。她紧紧贴着我,和我的猎枪。我说,没事,我拍。我后撤几步,拍下了手握相机的陈建德,和视野远处的湖,湖边的尸体和飞鸟。我继续举着相机,透过镜头向更远处望,三头狮子正迈着步子向湖边走来,其中一头雄狮,两头雌狮,后面还有。我低下身子,匍匐过去,重新趴好,小声说,它们来了。陈建德举起相机等着,说,等另一群动物。胡丽丽说,要多久。我说,不知道。陈建德说,不能错过了。胡丽丽把头埋进草丛里,一动不敢动。我说,你不用那么怕,它们离我们还远,这起码二百多米,你身子瘦,不够它们塞牙缝的,没威胁。
没有别的动物。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像是一段一段的过去,也像是一团一团的过去,太阳从头顶挪了方寸,还是头顶,铺洒的热令人难捱。我和胡丽丽将近睡着,又觉得燥热,汗透了身子,草叶扎人,偶尔还有叫不出来的虫子爬上来。陈建德慢慢往前挪。我说,老师。他回头说,我靠近点,狮群不能再错过了。胡丽丽说,他去哪?我说,没事。一群犀牛从视野远处的右侧踱了过来,体格大,站在河边喝水,丝毫不惧怕狮群。它们两股生命互不干涉,只是看了几眼。胡丽丽说,和谐社会。我说,你不害怕了。她说,有点习惯了。转眼间,陈建德已经爬出去四五十米,我跟胡丽丽说,不行,我们一块往前来点。胡丽丽说,等狮子去咬犀牛吗?我说,对。她说,上次是小象。我说,跟我来。
我和胡丽丽顺着陈建德挪出的草辙往前爬,在他屁股后面停下后,他回头看了看,说,你们别动了,危险。我说,还有一百多米,不能再往前了,狮子看到你,就像看到那头小象。胡丽丽说,你不是说不够塞牙缝吗?我说,老师。陈建德没理我,握住手里的相机,按了几下快门。我不敢喘气,狮子暂时像只猫般横卧在水边,向我们看来。它们也许看不见我们,也许懒得理我们,我判断不了,也不敢判断。陈建德继续向前爬,又爬出去二十米时,一切有了动静。几头狮子可能觉得无聊,开始围着犀牛散步,犀牛群有点惊慌,喝饱了水,准备往外跑。这个间隙,三头狮子围住了一头体格较小的犀牛,最凶猛的雄狮开始靠近,嘶吼着扑了上去,犀牛后蹄蹬地转了一圈,狮子落了空。看上去气急败坏,开始追。犀牛乱了阵脚,大群开始往来的方向狂奔,较小的那只,往我们这个方向跑来,速度极快,这一幕似曾相识,我咽下口水。胡丽丽捂住了眼睛。陈建德继续往前爬。我说,老师。他扭回头,说,举起相机。我照做,按下快门,把前行的陈建德和追赶犀牛的狮群同时框进镜头里。
陈建德在距离我们二十米的位置停住,犀牛倒在他的面前,震起的黄土飞散,我看不清。胡丽丽说,犀牛压到了陈教授。我说,别说话。实在太近了,我一只手举着相机,一只手死死地握住双管猎枪。看不清陈建德,犀牛被雄狮扑倒,压在身下,另外两头狮子也开始上来,死死咬住它的腿。雄狮踩上它的侧背,一口下去紧咬它的脖颈,它们不是在玩耍,是在捕食。鲜血从伤口喷射,胡丽丽忍不住叫了一声,我捂住她的嘴巴。雄狮抬起头,往这儿看了一眼,眼神透饥饿和凶残,又低下头继续撕咬。犀牛发不出任何声音,死亡逼近,已经切进它的体内,从五脏六腑开始破碎。尘埃落定,我看到陈建德继续往前爬了一小步,胡丽丽想挣扎着起身,说,他疯了。我按住她的身子说,别动。陈建德的右胳膊微微抬起,相机几乎紧贴着犀牛落置的头颅,我听到咔嚓一声,又咔嚓一声,陈建德做到了。
雄狮被声音惊扰,停下动作,从犀牛身上跳下来,向四周嗅着。胡丽丽说,狮子。我依旧按住她,说,不要发出动静。她说,枪,再不开枪就晚了。我说,别动。
陈建德身子开始往后退,但还是被发现了,雄狮张大嘴吼叫一声,獠牙夹带的血块溅射,他爬起身来,对着雄狮的大嘴按下相机快门,咔嚓,咔嚓,咔嚓。第一声咔嚓时,陈建德站立着,微风还没有任何抽动,第二声咔嚓时,风被快速搅动,雄狮已经扑倒了陈建德,第三声咔嚓是在陈建德完全被按压在草丛后,仍旧单手举起相机完成的。痛苦的喊叫声随之而来,不知道狮子咬住了他的什么部位,陈建德的挣扎毫无用处,迎接他的没有别的,只有死亡。
胡丽丽大声喊了出来,我搂紧她说,别动,你管不了。胡丽丽浑身颤抖地站起身子,我拉她趴下,她抢走我身边猎枪,端起来跑上前去。我半蹲起来,看着她瘦弱的身子,直挺挺地站在狮群前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死亡对她来说还很陌生,还未被她熟知,反抗、干涉,胡丽丽在做着傻事。她大声叫喊,嘴里是一些平常听不得的脏字,语言已经不具有任何威慑力,狮群仍旧原地不动,雄狮从张建德身上迈下来,向着胡丽丽走来。
我站直身子,举起相机,将这一幕锁进镜头,在这瞳孔般的视野里,一切极为不真实,咔嚓,咔嚓,我不停地按下快门。画面里我仿佛看到自己端着双管猎枪,断腿的小象在狮口下不停地挣扎,是否是同一头狮子,我不清楚,死亡总是相似,牙齿也同样锋利,并无太大区别。胡丽丽哆嗦着将枪口举起,瞄准雄狮的眉心。双管猎枪即将鸣响,湖面上的鸟又会再一次惊起而飞,在头顶不停盘旋。热早已经占据了我们所有人的身体,陈建德没有再爬起来,他的胸口正渗着血,顺着镜头的光圈流往干枯的地面,胡丽丽没能扣动扳机,保险栓她并没有准确找到,我看着天上低矮的云,想起导游的话,他说,这草原很久没有下过雨了,就像从没下过雨。大地干裂,一切如旧又如新,我将镜头聚焦,瞄准那头雄狮,它撕咬过陈建德,正准备扑向胡丽丽,咔嚓,咔嚓,快门声让我明白,一切已经被我框住,没什么好担心的,我们终将存在。咔嚓,咔嚓,我企图摄杀那头雄狮,心里却很清楚,世界不会因此改变,狮群终会将我们吞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