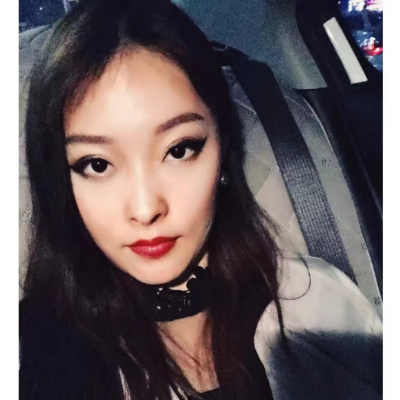她第一次拥抱了我,在那片花海,风流动的速度慢了,蝴蝶正好经过。
1986年,我正式成为一名流浪画家,那时的所有家当除了画板,就只有一把可作为我心里支柱的吉他。
卡斯木的格桑花开得漫山遍野时,是我第一次见到她——
她在花海中起舞,长发散开,像极了丛林女神,阳光也眷恋着她,连发丝都闪烁地发出了微光,如白昼中静谧的萤火虫。
我将她融进画板,迈入了那片花海,神经近乎麻醉般的迷蒙。
做为一个画者,我见过无数的女子,以及她们的无数形态,青涩的,赤裸的...在遇到她以前,我只是一个被冠名的“画家”,我许久不会心动,心脏似乎被长久麻痹一般,而那一天,我仿佛苏醒了,我孤寂的灵魂开始像少年般跳跃,引领我慢慢走向她.....
我试图和她交谈,但她只是看着我和那幅画,竖起大拇指并打着手势,我便知道,她是无法说话的人。
她赶着羊群带我来到家中,里屋人听到声音拨开纱帘走出房门。
听到我的需求,那位中年老人点了点头,开口说:“小伙子,你可以住下来,这间房的东头有一间单独的小房屋,你可以住那里。”
“那太感谢了,这段时间会麻烦您。”
那姑娘也走入房屋后拿出一条白色哈达,戴到了我的脖子上。
“她是我女孩,叫仁央,无法说话的人。”
说着他神色流露出哀伤,轻轻摇了摇头,又接着说:
“我叫才仁平措,你可以叫我阿克才仁。”(阿克为藏地对大叔的统一称谓)
“我叫李健辉,您可以叫我健辉。”
他点了点头,把我领到房东头的小房屋,四周的黄泥墙壁,雪松木柱子和围栏,带有藏风图腾的卡垫,和桌子前的火炉盆都使这间不大的房屋看起来简单古朴。
天色渐黑时,仁央和阿帕来帮我烘了火,室内暖黄色的灯光将仁央的脸照成如油画一般的人,她也换上夜晚御寒穿的深蓝色藏袍,我愣着看出了神。
隔着木窗,还能见到空中硕大的月亮,更让我感到欣喜。
才仁告诉我,仁央的母亲很早就已过世,他独自抚养她生活,而仁央从出生起就注定无法和常人一样开口讲话。
那年她21岁,我已29,虽只相隔8岁,但我当时的发型和故意蓄起的胡茬,使整个人略显沧桑。
他们的热情质朴,缓解了我那时一半的焦虑。
第二天早饭后,我背着吉他,和仁央一同赶着羊群到距离雪山脚下更近的草地,坐在帐篷外,我弹着吉他唱起邓丽君的《小城之恋》。
她开心地鼓掌,却不能讲出一句话,从那天开始,我下定决心教她学汉字,于是,我们上午学写字,下午一有空她会教我手语。仁央会写的第一个名字,不是她自己,而是“健辉李”,虽然看起来像老外念的“倒装句”,却足以让我兴奋许久。
我问她:“‘我爱你’手语怎么做?”
她用手指指向自己,然后双手轻轻握拳交叉在心脏上方,指向我。
我用手语照做了无数次,“我爱你”。
那个傍晚,她走在羊群中央,苯日神山峰顶缀落了金色的光,仿佛一道“神”的圣谕,连大地之色也忽然变得奇妙,云朵将要远去,草和花朵似乎也开始疲倦。
我放大声音唱:“我背着我的旧吉他,到处去流浪,经过了一个小村庄,那里有个姑娘,她站在高原的花海中,远方有成群的牛羊,我一眼就爱上了她,想把她带回家,我说亲爱的,我没有房子,你会爱我吗,我听见她说,拉桥拉嘎(藏语“我爱你”之意)我说亲爱的,我也没有钱,你还爱我吗?我听见她说,带我回家吧……”
我和她隔着羊群互相望着,她笑着笑着便红了脸……
在我去卡斯木半个多月后的一个清晨,曦光正垂散在屋顶,仁央早起煮好了藏茶和牛肉饼,我搓着手,早上的温度,只要一开口,就不断冒出热气,阿克才仁已盘起腿坐在卡垫上,仁央也坐在他身边,她还穿着那件藏蓝色袍子,串成圈的松石和蜜蜡点缀在她的额头及发上,阿克才仁细细地啜了一口藏茶,然后嚼起了牛肉饼,神色有些气愤。
“听说羌纳乡有人去偷耗牛了,天杀的贼,那可是牧民的血汗!”
“抓住没有,偷了多少?”
“十多头,不知道运到哪里去了,并不是在一处人家偷的,一定有伙伴。”
阿克才仁说着看了我一眼:“辉,你可要也来帮我注意,万一贼跑到我这个偏僻的小村来偷,还有我的羊群,哦,我一定要和他拼了老命。”
我安慰才仁:“我夜里睡得轻,有动静肯定能马上出去查看情况,您不用太担心,起码我们可是两个男人。”
“哎,那就好了。”
“有厉害的把式没有?枪肯定是不行,别的比如类似棒子的有吗?”
阿克才仁突然像想到什么,放下茶杯一骨碌翻起身走出门,一会儿便拿来一把鞘头刻有云纹的长锋藏刀,还有一条马鞭。
“辉,这是吓唬人用的,鞭子可以抽他,刀可不能动真的...”
我站起来甩着那条鞭子,发出“嗽嗽”的闷响,险些抽到自己。
才仁从我手里扯过鞭子,干净利落几下就见响,我感叹他手法实在是高。
对这两个精美如同艺术品的物件我十分喜爱,吃过早饭,便把藏刀和马鞭收在我屋里的凳子旁。
第二天傍晚乌云密布,阿克才仁回来后一数发现耗牛少了一头。
我吹着平时才仁唤牛的口号,一路找到草原附近,又想到这种地势过于空旷无处躲藏,应该往林子处走走看,天空也忽然下起雨,隐约听见前方林子里传出声响。
隔着树看到,有个影子在前面晃动,我跟着影子向前走,疾来的雨水将我的衣服浸透,脚下也开始发滑,等我来到那影子的跟前,才发现那确是头耗牛!我找到它身上的绳子,可绳子不知何时被误缠到树干下,前走不能,后走不得。
我蹲下准备去解,低头的瞬间突然喉间一阵恶心,胃里似翻江倒海,头脑晕眩,紧接着双目一黑...
夜晚时分我醒来时已回到房间,浑身热得发烫,仁央在一旁正拧着毛巾。
“牛牵回来了吗?”
见我醒了,她赶紧将毛巾盖到我的额头,点了点头,眼里露出担忧,此时就站在我睡卧的卡垫旁双膝跪地俯身看着我。
她马上从我身上离开,站起身抚平藏袍上的褶皱,然后匆匆走出房门。
那晚,我做了不齿的梦,梦里,我和仁央极尽缠绵,交换着彼此的灵魂,我的吻疯狂地落在她的颈间,耳垂,每一寸皮肤,手指穿过她的长发,她的身体如太阳女神般富有美好的生命力,饱满的胸脯,我轻启她的嘴唇,任我们的舌头缠绕在一起,贪婪的索取那甘甜的吻,灵魂的碰撞,肉体的契合,仿佛顷刻之间又切换到须臾的宇宙,我发出低吼,见她眼角溢出一滴晶莹的泪,然后那泪忽然变成钻石,我的面前出现白皑皑的雪山,我心里开始生出愧疚感,不该沾染雪山一般纯洁的女神。
“辉,健辉,哦,莲花生大士保佑你,谢天谢地,瞧,睁开双眼了,我摸摸,啧啧,烧也退了。”
阿克才仁正摸着我的脑袋,我胡了一把脸,这才感觉到胡子已经长到了扎在手上发软的长度,我已多天没照镜子。
“昨天你大约是因为不能承受高原下雨天的低气压,再加上被雨打透了身体,所以晕倒了,这很正常,很多汉地人来到藏地都要得了肺水肿...”
“你竟然还知道帮我把耗牛先栓到树干上才晕,哈哈哈哈…”
才仁爽朗地笑。
他显然并不知道栓绳子的不是我。
“我女找到你时,你正趴在地上,离牛粪不大远的地方。”
我尴尬地挠头笑了笑。
“她把你背了回来,下着雨,很远的路,不好走,几次都差点摔倒,等你烧退了一点儿才离开房屋。”
我赶紧坐起身来,因用力过猛头脑又是一阵晕眩,刺痒着喉咙干咳了几声。
“她现在怎么样,人在哪里?”
“高原上的女娃没你们汉地那样娇气,总是淋雨,出力气,很习惯了。”
“她一早都烧好饭了,你快去吧!”
我梦境中的愧疚之情还没消散,当再次面对仁央时,昨夜的画面又开始显现,我的脸上开始有些烧灼。
“你还好吗?”
她认真注视着我,目光里没有一丝闪躲,用手语告诉我“我很好,”“没有关系,”“不用担心。”
“喝点酥油茶,能去去你的寒气,还有这个包子,可是耗牛肉的,炒奶渣不知道吃不吃得惯?”
“说实话,辉,你小子让我心动,哦不,心感动。”
“你冒着雨帮我找回了心爱的耗牛。”
阿克才仁将桌上的食物全推到我跟前。
我喝了一口酥油茶,身体瞬间变得暖而踏实,仿佛这个村子,这个家已成为我的灵魂归宿。
“我知道耗牛对于牧民的意义,有的牧民甚至将耗牛视作孩子,朝夕相处的伙伴,改善生活的依托。”
才仁点点头,说:
“牧民和牦牛互相尊重,妇女挤牛奶,牦牛是同意的,你站在远远的地方,牦牛会认得你。”
“幸好不是盗贼,不然怎能将我的伙伴找回?”
“对了,辉,你要回去了吗?我真希望你能多住些时间。”
“8月份和我一起去游牧,这是最好的时节,你会觉得新奇又欢快,虽然是冷的,但你可以奔跑在大草原,像天空中飞翔的鸟一样自由,夜晚还能在帐篷外点燃篝火拿着你的吉他,哦,如果你怕冷,我可以借给你羊毛毯,让你可以在夜晚躺在草地上去看整个夜空的星星。”
我一听来了精神,“那打算哪天去?”
“很快了,8月一到,几天之后就要赶去那里,林芝的鲁朗牧场,离南迦巴瓦雪山更很近了。”
我已决定再过些时日返程,确切说是在看到仁央之后发生了改变。
在8月1号那天一大早,我们便赶着羊群和四十多头耗牛去往鲁朗牧场,那时普遍牧民都还没车,所有必备物品只能绑在耗牛身上,等一切准备就绪,仁央递给我一件深褐色的高领毛衣,她用手语告诉我,“马上穿上”,“可以暖和”。
我接过,没等穿,暖意已从手心蔓延至全身。
“去穿上吧,这是我女亲手为你做的,赶了好几个夜晚才织好,看,酥油灯下熬起的眼睛,红肿了吧,手都要磨起泡,你这城里小子,一定没穿过这样的衣裳。”
仁央低头握住手指,看我正看向她又连忙背过身后。
“温暖的耗牛毛能够使你不感到寒冷,哦,我慈悲的伙伴,感谢它们奉献的一切。”
阿克才仁说着摸了摸面前耗牛的背,然后又贴了贴脸,耗牛温顺地眨眨眼。
我略低头,合掌至额头,表示感谢。
穿上黑色的藏袍和藏靴以后,加上我蓬松凌乱的头发,沧桑的胡子,更像是一个真正的藏人了。
我和仁央走在前面,她牵着獒,阿克才仁在我们身后骑马赶着羊群和牛群,由村子出发,经过卡斯木草原,牛群和羊群浩浩荡荡地卷起地面上的尘土,从远处看黑压压一片,颇有排山倒海之势,最后横穿318国道直至鲁朗。
到达鲁朗牧场时已经晚上七点多,夏季的藏区9点多才能完全天黑,日落之后仍留有余光,以致天空类似山区里冬天清晨的天色。
选好了离河流较近的位置,可让畜群方便饮水,再卸下所有装备,待我和阿克才仁把畜群拴好,仁央已在帐篷内置好了黑炉,用干牛粪生了火,水壶里的水很快沸腾,溢到炉壁上发出滋啦啦的声响。
铺好防潮地毯及卡垫,阿克才仁把羊毛毯卷打开,扔给我一条。
“我们三个要睡在一个帐篷里了,不过没关系,晚上帷帘会隔起,我们互相都不打扰。”
“如果你觉得寒,外袍子也可以盖到毯子上。”
“小伙子,总是不要那样娇气,藏地的男人都是十分健壮而有力的。”
“烈马可以降伏,凶猛的獒犬也会归顺,对待姑娘又是那么柔情,哈哈哈。”
“你要是成为我的女婿可要像藏地的汉子一样勇猛才行。”
阿克才仁说着端起仁央刚沏好的酥油茶,走出帐篷,坐在草地上吃着干牛肉。
我和仁央也在他身边坐下,端起茶杯。
“怎么也算是乔迁之喜啊,我们应该庆祝一下。”我提议。
“你们先喝下这杯茶暖暖胃,我去拿酒来。”
阿克才仁钻入帐篷,接着拿出一个陶罐,我和仁央相视一笑。
“来,让我们以这广阔的草原为家吧,让我们今晚喝醉吧!”
阿克才仁喊着高昂夹带藏音的语调端起酒杯,一饮而尽,酒水顺着他的下巴洒在藏袍。
我喝干这杯酒,胃肠里稍稍暖开了,空气却愈加寒冷,热气的形态在眼前逐渐清晰,我进屋把牛粪炉搬出来,放在离仁央最近的位置。
“来,辉,这一杯,我们敬南迦巴瓦雪山,神秘而慈祥的母亲!看,她正远远地看着我们。”
我抬头向雪山望去,高耸的雪山峰笼罩着大片云雾,仿佛用丝绸遮住面目的神女,我仰望着她将酒杯举过头顶,一饮入肠。
仁央将青稞酒又温热,我们连干数杯后,体内的血液开始变热,胃肠的暖适感逐渐蔓延至全身。
阿克才仁忽然脱下藏袍,只穿着内衫毛衣便围着炉火跳起舞来,仁央也加入其中,如夜幕之下的仙子。我用吉他做伴奏,写下在草原的第二首原创歌曲“神女峰下”。
“载歌载舞的人儿啊,远处安歇的耗牛,都沉睡了吗,在神女峰的怀抱里,微光闪烁的帐篷呦,我们心中的家乡,我敬爱你啊,与我共饮一壶酒……”
草原上的欢声笑语,在那个夜晚,随着琴音和歌声飘散至很远很远,在云端,也许又传到神女峰的“耳朵”里……
第二天早上还没睁开眼,就听见阿克才仁在帐篷外惊呼“辉,你这小子,真是走运得很,神女山‘南迦巴瓦雪山峰’为你掀开面目了!”
“快出来看阿,去年我夏季两个多月没见过它两回,啧啧,你来第一天竟然就看到了!”
我迅速穿好衣服,走到篷外,和阿克才仁并立向南迦巴瓦峰望去,只见它褪去了洁白的面纱,露出银白色的高峰顶,远看就像是镶嵌在天空与山脉之间的闪耀钻石。我举起合十的双手,在头顶,在额心,最后至胸口,深深地鞠了一躬。
“辉,你是幸运,可以受神灵眷顾的人……”
阿克才仁炯炯地看着我。
“藏族的传说有很多很多,比如,谁找到了八瓣的格桑梅朵(格桑花别名),就找到了幸福。”
“您找到过吗?”
“当然,八瓣格桑梅朵并不很难见,有时大片的出现,藏地的人民,不论男人女人,都见过它,我想可能是那遥远的神灵对每个藏人的祝愿吧!”
吃过早饭,我支起画板,在油画布上重新勾勒画面,以南迦巴瓦峰为背景,仁央在画面的正前方雪山脚下的格桑花海里起舞,天空中浮动的云朵,远处的山脉,挂着经幡的黑帐篷,近处草原上的耗牛和绵羊,流淌的河流,笼罩着朦胧的阳光。
我将这幅名为《神山下的少女》的油画,终稿时间定在半个月之后,那时将完成整部画作包括细节部分。
在来到鲁朗的第五天,我们把耗牛和羊群分散在草原上,獒犬欢快地随着牛群奔跑,洁白的羊群仿佛从天空中坠落到草原上的流动云朵。悬挂在草甸上的经幡随着风呼呼作响,女人的长发会拂到眼前,男人的短发会吹过耳后,无际的青草会低下头,有的弯腰,风有时又会将它们吹成一道道弯波的草浪,草甸山坡的巨大石头上,刻着彩色的祈福藏文。
不远处的几个牧民家的孩子正向仁央做着鬼脸,其中一个叫贡布的男孩向她扔了石子,我立马跑过去,仁央用手语重复说着“不要淘气……”,却又无可奈何。
“哑巴”,“她是个说不出话的哑巴!哈哈哈哈……”
这句话刺中我的心口,我愤怒捡起一旁的木条要动手,被仁央拉住。
“哪个小兔崽子再敢来说这两个字,我一定让他的屁股开花!”我怒吼。
几个孩子吓跑了,我扔下木条,双手拉住她的肩膀。
“不用担心,以后他们肯定不敢再来了。”
“别往心里去,都是小屁孩说的话。”
经过这件事,仁央和我好像更近了一步,她看我的眼神开始变得深长,我们无拘无束地一起牧牛。早起,在清晨守着燃烧着干牛粪的黑炉喝藏茶,在霞光遍照的傍晚弹琴、跳舞,向广阔的草原伸出怀抱,夜晚躺在草甸的半山腰上,抬头仰望星河。
终于有一天,我认真对阿克才仁说:“我想娶仁央做我的妻子。”
他没有同意,也没有反对,只是在将黑的帐篷里点亮了酥油灯。
“早就知道你这小子的心思,我女是个很好的姑娘,只不能说话,怪我,这是生来就带给她的……”
“我不敢把她许给任何人,年轻的孩子,你们如果最后嫌弃她,会给她带来很大的伤害!”
他脱下靴子,坐在卡垫上无奈地叹气,似乎在等我的回答。
“才仁,我是认真的,我对她的感情甚至已超越很多形式上的东西,升华到了对灵魂的渴望,我想做能守护她的人!”
说着,我感到自己鼻子酸涩,眼里有些发涨。
“不瞒你说,才仁,她让我感到踏实,你并不知道,我从未有过这种感觉,从小到大一个人生活,我不知道什么是家...”
“说真的,即便后来我在京开了画室,立足脚,我都不知道家的含义,没想到在这个四处游荡的帐篷里,在这个能接纳每一间帐篷的大草原上,我竟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意义...”
“才仁,我这些天都在想这个问题...”
阿克才仁开始惆怅的喝起酒“城里的孩子,变化很快,我听说过许多,哎,我想去信任你,或许我该试着相信……相信你和那些喜爱变化的孩子不一样……”
我只是定定望着才仁,说:“她在我心里,是可以视为神圣的南迦巴瓦雪山的人……”
他似乎终于等到了满意的答复一般,笑着点点头,不再说话……
我在花海中找到大片各种颜色的八瓣格桑梅朵,但并未摘下,我蒙住她的眼睛,她睁开眼时我大声喊,“仁央,我把鲁朗所有的八瓣格桑全部送给你!”
然后又贴在她耳边轻声说“把所有的幸福都送给你...”
她第一次拥抱了我,在那片花海,风流动的速度慢了,蝴蝶正好经过。
她摘下一朵粉色格桑,放入我的上襟,用手语对我说“我愿把我的幸福送给你……”
那天夜里,我听见有人揭开帐篷内的帷帘,走到我身旁,带着淡淡的藏香,她用手指轻轻划过我的脸颊,微凉的指尖停留片刻,又抚上我的下唇,我装作不动,忽然有发丝贴入脖颈,清凉的皮肤触碰到鼻尖,我浑身战栗,鼻息间变得紧促,嘴唇被覆上了两瓣柔软,她吻过我的下唇和嘴角,当她的唇瓣摩擦在我的唇间将要剥离的时候,我用力吻住她,用舌尖撬开她的皓齿,然后反手将她翻身向下,我们拥吻着,我把头埋入她的脖颈间亲吻,轻含住那如白扣的耳垂,她在我怀中微微抖动,胸口起伏.....
而我始终没有突破最后的防线,用双手撑住身体平息了燃烧的欲火,而当我想要控制的一刹那,仿佛在心中又看到了神圣的南迦巴瓦雪山。
那夜的最后,我们在帷帘的这一端紧紧拥抱,在稀薄的空气里,在鲁朗的沉默里.....
我在雾蒙蒙的晨间作画时,她会为我披上更厚的藏袍,再递给我一杯热茶,我们笑笑,没有语言,她静静地坐在我身边,有时会捡起草棍逗地面爬过的昆虫。
八月份下旬,距离立秋的时间正好过了近半个月,而《神山下的少女》也终于如期完成,按照参赛当天的时间来算,我选择人不返回通过邮寄将原画包装好,半个月左右邮寄至京,大概10月初就能知道最终结果。
顺便去林芝拜访一下老朋友多吉,阿克才仁听说我要去林芝看望朋友,特意为我带上酥油和陶罐青稞酒,通过阿克才仁联系了可以送我前去的骑行摩托车。
临走之前,仁央用手语对我说“祝你成功。”
我只打算最多3天就返回,不会耽误太久。
当天中午便抵达林芝,由于没有电话事先通知多吉,我凭记忆找到他家时,他惊讶地张开嘴巴“健辉?”
“你竟然找来了!”
“是要回去北京了吗?”
“我遇到了心爱的姑娘,多吉,我想为了她留下来...”
“哦,这是真的吗?难以置信,你竟有如此的缘分在这里,我能说什么好,上次这种事情还是发生在传说,那我可真要真诚地祝福你!”
他说着双手握起我的手并贴在他的额头。
“健辉,我为你高兴!”
多吉兴奋地说着。
第二日早上,下起了暴雨,我去邮局办理好邮寄回来时路面已经出现积水,按情形看计划只能改变,返回时间要延后。
直到第四天晚上大雨才停,西藏广播电视台用藏语播报着当地多处降雨情况,多吉在一旁替我翻译:“波密,及通麦大桥附近路段都发生程度不一的山体滑坡及泥石流,请民众注意安全,尽量避免出行,如必要出行需选择绕行或远离高危山体。”
第五天早晨,我只想快点回到鲁朗,但多吉告诉我,骑行车这类天气不会出行,起码要等到明至后天,于是我只能焦急地等待。
看不懂的藏文书被我翻了又翻,佛经和唐卡仿佛已成为我维持度日的生机。
终于在第七天,我辞别多吉,随骑行摩托离开了林芝,这次是个叫嘎玛的藏族小伙子,当我说目的地为鲁朗时,他说“经过色季拉山时有时会遇见飞石,要很小心。”
“鲁朗在前天发生了山体滑坡,好像有人死亡,这只是人们传的,广播并没播报这里,我们骑摩托人没人去鲁朗,不清真假。”
我胸口一紧,然后安慰自己说,不会的,如果真有问题广播为什么不说呢?
我不敢再多想,戴好头盔后一路前行,经过色季拉段,路面没有想象的巨石,只有零散坠落的碎石。在下午1点多,我们到达鲁朗。
越接近我内心的不安感似乎越凝重,我发疯似的朝草原跑去,拦住一个牧民。
“这几天发生山体滑坡了吗?有谁遇险了?有谁?求你快告诉我!快!”
我抓住他的肩膀,几近崩溃大喊。
“四号的事,就在前面的山坡,你认识吗?”
“一个叫诺布的孩子正站在坡下,从山顶要掉落石头的时候,那个哑姑娘为了救孩子被石头埋住了!”
我心里最后的救命稻草破灭了,一下子瘫倒在地,最后的侥幸也化为乌有,我不知道怎么走到阿克才仁的帐篷,仅仅一周时间……我不能接受!最后在帐篷外崩溃大哭。
这时阿克才仁忽然走来诧异地看着我“辉,你怎么才回来,哦,对了,我这糊涂人,是这几天下雨!”
“仁央正好煮好了茶,你这小子,快喝了暖和暖和。”
我看见仁央掀开帐篷走了出来,我冲过去抓住她的手臂,摸着她的脸,完好无损!
“遇险的不是你?”
仁央惊奇地望着我。
“你是怎么了?”阿克才仁问。
“我听说前面发生泥石流、仁央遇险了!”
“怎么可能呢?我们这里安全得很,是谁乱说的!”
我抱着仁央不撒手,她静静地看着我,然后摸了摸我的脸,我握住她的手,又开始哭起来,她揽过我的头,拥抱着我,亲吻了我的脸,然后她缓缓松开我,眼角流下了泪。
泪落到地下,并不是泪,变成了钻石……
“辉,你醒了……”
阿克才仁轻声唤着我的名字,那是我不曾听过的,略带沙哑的声音。
我正躺在帐篷内的羊毛毯上,酥油灯昏黄的光燃起来了,敞开的帐篷门透着外面深蓝的天色和蒙蒙的草原。
“仁央呢,才仁?”
他垂下头,手挡住了眼,让我隐约听到小声的低泣。
“我的女,她是伟大的,她去了神灵在的地方,与神灵为伴了……”
空气中寂静得使人心慌。
“昨天我已在天葬台为她举行了天藏……”
“我女无上的灵魂一定已回到了天际,或许莲花生大士将接走她。”
他又看向帐篷外远方的天空,似乎试图让自己释然。
我觉得天旋地转,胸口仿佛压了一块重石,巨大的悲伤在胸腔里翻涌,泪水不住地流。
“现在我也没有任何留下你的理由,辉,你明天就可以离开鲁朗...”
“对了,”阿克才仁突然递来一张纸条。
这是一张我画画的废稿的一角,已攥出了皱。
“我女衣服里找到的,你看是什么字,我看不懂汉字。”
我接过,打开。
只见纸条的反面写着歪歪扭扭的几个汉字:
“我爱你辉。”
第二天,我并没有离开鲁朗,我找到发生山体滑坡的地方,巨石已被清理,那个叫诺布的孩子和他的母亲在一旁的路面,放了许多美丽的花,而我只放了一朵粉色的八瓣格桑,那个曾嘲笑他的孩子也来到这里……
我走在每一处我们停留过的地方,在她牧牛的地方,在挂满经幡的草甸上,在大片的格桑花海,在我第二次又见到南迦巴瓦峰面目的地方...云雾更散了,它掀开了全部的面纱,不知道是否因为想抚慰我的伤心。
在以后的每个夜晚,我期待她入我的梦,但是,再也没有……
10月份初,我收到了关于比赛的结果通知,是一封信,“李健辉先生,您的作品《神山下的少女》已获得油画类一等奖!因奖金数额较大,请本人返回北京至原参赛评委审核处签字领取,执此信有效。”
:(X)望本人前来,盼与您协商合作事宜。
我收到信的当天,长达15天的汉城亚运会正式闭幕,中国获得94枚金牌。
不管是关于人的事,还是关于国家的,外表看起来好的总是一齐扎着堆地来,我又想起,如果在我最难熬的时候听到这两个消息的其中一个该有多好,只不过现如今,为我雪里送炭的人已不在,那个从山里背下我的人,笨拙写我名字的人,为我织寒衣的人不在了,那这些飘渺的东西对于我来说,又有什么意义呢?
我的灵魂好像又飘远了。
回北京的时候,我没有再经过多吉家。
我的胡子又长得老长,也没管顾它,我想反正爷已是“真正”的艺术家了,往后京圈里的人又要再高看我一眼了,从前那些不值钱的画再拿来也定能卖个好价钱。
接待我的人戴着副斯文的眼镜,见到我的第一眼便伸出戴着圈戒指的手要握我的手,我接过他的手,坐下,他客客气气地为我倒了水:“李建辉先生,久仰久仰,您的油画令艺术界所震撼!”
“它让我仿佛看到了维米尔的真迹,实在梦幻,实在美好!又那么地神秘而神圣!”
他将所有友好的词汇全形容出来了,谁能想到几个月前我还是那般地窘迫。
“李先生,希望您留在北京,如果您有什么需要我帮助的,尽管说出口,我想请您入驻我们的画廊,国内的画家,您是前几位。”
“哦,谢谢您的认可与抬爱,我还有些事情需要处理,您说的我会好好考虑,我们有机会再见。”
我用类似阿克才仁一样的语气答复了这最精明的人,然后走出了房门。
等我返回鲁朗,阿克才仁这时已不在草原,想来是回到卡斯木了,我将这些钱的大多数捐到了藏地的基金会用于资助贫困儿童。
然后在林芝租了间房屋,按照藏人的风格,有佛龛,有莲花生大士的唐卡,还有温暖的卡垫,与暖炉,我在这里做出了第二张关于仁央的画“废墟之下的神灵”,画面里,一个发光的女神被困在废墟之下,后面是崩塌的山石,路前面站着逃出险地还没消退惶恐的孩子……
最后这幅画在北京与我谈合作的那人的画廊里进行了拍卖,以97万美元被一名荷兰籍老人所购买,他便是那维米尔的忠实粉丝,当他得知这副画背后的真实故事后,竟然也放声哭泣。
对我说这仿佛是维米尔的真迹,这无私的“神灵”足以令他震撼感动,他愿意永远将此收藏。
这些钱同样一部分被我分配给了藏地的基金会及贫困儿童,一部分分给了远在卡斯木的阿克才仁,愿他以后能富足地生活,不用再恐惧那偷牛的盗贼。
后来我时常从林芝到卡斯木,再从卡斯木到鲁朗,南迦巴瓦雪山依然眷顾着我,时常拂起它的面纱,如今这个已年过半百的老人仍然每夜等待着那心爱的姑娘入梦,那条马鞭和长锋藏刀已成为伴我入梦的伙伴,耗牛毛衣穿得发旧了,却也温暖着我,隔在掌心里的温度屡次带我回到多年前的寒冷清晨,美丽的草原今天已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欢声笑语,而我的心里,却永远守护着那个鲁朗的沉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