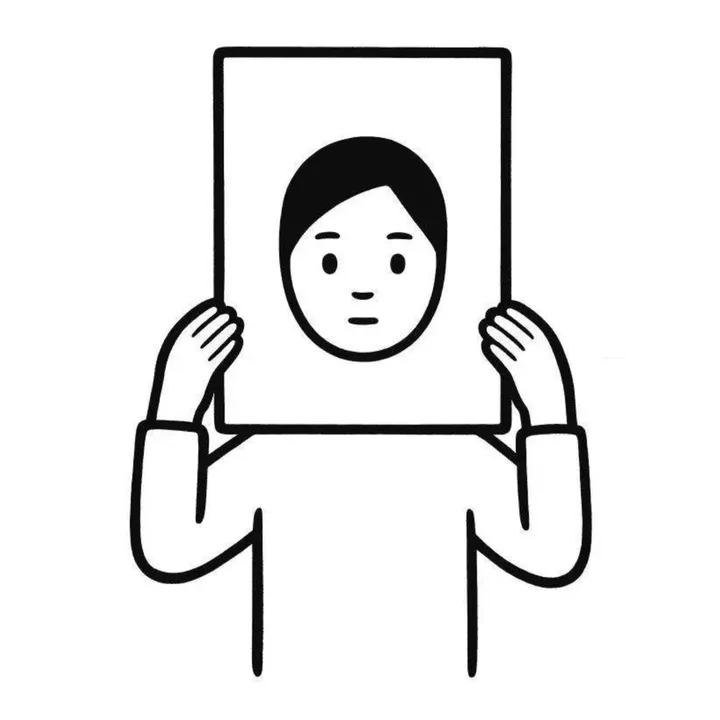我们都是船,不是人,大海是波浪状的,把我们碰在一起是缘分也是终结,碰就会碎,水会灌进来,然后慢慢下沉。
1
张慧把合影摆在电视柜上,和65寸电视比起来,它极小,背景是流动的瀑布,就在桃花峪的某个角落里,记得和摄影师走了很久才找到这处位置。天很热,头发即将融化,张慧头上的盘花耷拉着,我应该是帮她打着伞,摄影师走在前面,用脚踩平探出路面的杂草,头和相机一并埋进胸里。烈日当头,水声渐近时,才多少感到一些安慰。
照片里的天是修过的靛蓝,丝毫看不出一点慌张,张慧依偎在我的肩膀,我们站立在溪流的凸石上,看着摄影师汗涔涔的额头,等着快门的手落下,多次调整姿势后,又多次调整表情,喜悦被捏成固定的形状后,才得以匆匆离去。我直盯着镜头,动作木然,左臂搂着张慧,几根手指从她的腰间露出,原本太阳过大,眼睛眯成一条缝,照片中也被修过了,眼窝拉大,眼神空洞,像另一个人。张慧眼神含笑,嘴角被提拉起来,像照片上方有两条细线。
这是我们的结婚照,婚礼定于八月十八号,还有一个来月。在卧室床头上方的墙面,还有一幅大的,内景,空调很足,一大团花束下,表情显得自然一些。客厅沙发上方的墙面有从网上购买的儿童抽象画,蓝色的大象,眼距宽阔的两只白色眼睛,一根更深蓝的象鼻垂到画的下沿,好看,童趣、高雅,我极力保留,才得幸没有被结婚照替换。
木质茶几上就一个电视遥控器,张慧拿起来,换个位置又放下,一会儿又看看刚刚放好的小尺寸合影,从电视柜上拿起来,又换个角度放下。她最近总是在重复这么几件事,重新摆放物品的位置,怀疑新家具存在空间的合理性,擦拭一切可见的表面,期待灰尘能早点落下,又因灰尘落下而自生烦恼,按她的说法,变换物品位置是寻找结婚的某种新鲜感,擦拭是保持新鲜感。
我不想反驳她,我们一年前相亲认识,彼此有些好感,住在一起也就半年,时间也许不足以磨灭新鲜感,但也不乏疲倦,当真正生活开始的时候,犹疑总是存在,也许是我的问题,身子迈过去,就愣在那里,使不了劲,也抽不回来。参与结婚照的拍摄就令我浑身疲乏,张慧多次指责我,说我不配合,是不是还想结一次婚,我笑不出来,婚后我不清楚,结婚这个环节不太能融入,但为了不让她起更多疑心,我把笑挤得更认真了一些,拥她入怀的手也更用力了。
李佳仪联系我的时候,我和张慧正在红星美凯龙为一款是否合适装在洗漱池的进口水龙头而起了争吵,在精致和朴素之间摇摆,彼此都提高了分贝,互不相让。陌生号码的信息我一般都不看,当时为了某种不满和逃避,我站在一处展示花洒下,掏出手机,盯着这个号码发呆,内容很长,像个小作文,我捕捉到一些词汇,又糅合成一句话。我回来了,在中心医院的十四层病房里,窗外是中学的操场,我仿佛在前面走,你一直跟着,就要走进夕阳里。
从没想过她会再次联系我,觉得失真。我没有回复,张慧在和销售人员交涉,大概是在价钱上下功夫,比比谁的嘴皮子更快。这一点张慧不甘示弱,本身从事的银行工作就让她练就了跟客户打交道的基本法则。我依旧在花洒下站着,听着又进店里的另一波人的嘈杂,像一团密密麻麻的针,逐渐走来,我向内一躲,靠在展示墙上,花洒没有固定好,摔在地上。销售人员赶忙跑来,张慧疑惑地看着我,我对着销售人员说,你们这个不结实。张慧好像一下明白了,偷偷给我竖起大拇指,貌似我暗中做了什么很有价值的好事。水龙头最终便宜了一些买下来,尽管不便宜也会买,安装在洗漱池的上方,可以抽得很长,拿在手里,喷洗边边角角。
晚上睡前,张慧觉得床垫好像有点问题,躺上去总是觉得弹簧顶着脊背,我试了多次,没有太大的感受,她坚持把床垫正反调换,重新铺好被单,再躺上去,还是觉得硌,像是跟弹簧睡觉。我说,那就调换吧,反正床也是刚买的。她那时候已经有点烦躁的迹象了,开始左右不是,我安慰她,难得完美,生活如此。她消化好,躺下来开始琢磨结婚照的事,又咨询了同事朋友,打了几个电话。
我盯着墙面刚挂上的时钟,从九点到十点,再到十一点,张慧喋喋不休,不时给我看几张模版,店家,评价,挑选外景位置,山,水,薰衣草花海,瀑布和桥。我只顾点头,玩弄手机。李佳仪的信息又来的时候,我把陌生号码改成了她的名字。她说,自己可能住不了太久,事还蛮多,医院里到处都是将死之气,没有生机,风景也看久了,想看书,也想看看你。我没忍住笑出声,张慧侧头看我,我提了提身子,枕在床头说,笑话。她说,你觉得薰衣草还是瀑布。我说,薰衣草吧,香,有味。她想了想说,照片闻不出味道。我点点头。她好像累了,一下滑进被子里,说,水龙头挺划算,我看网上都贵300多。我说,好用,能拉出来洗澡。她不再理我,背过身去。
我重新点开李佳仪的信息,回复过去,下午在忙,不好意思,你想看什么书?李佳仪回复,霍乱时期的爱情,你看过吗,爱情。我知道霍乱是种病,打开网络搜索,才知道是马尔克斯的伟大作品,表达的是一种历经折磨的爱情的尊严。我侧头看看张慧的后脑勺,头发茂密,散落在枕头上,像一把没有打理的精致拖把。我没觉得什么折磨,到三十岁时,银行和国企,教师和公务员是名正言顺的门当户对,交叉在相亲公园里总能无限配对,我像拼图版上的一块拼图,被推来推去,此刻躺在这里,也许是时间所致,也许是命运,按我妈说的,三十了,你不结婚我还要抱孙子。
2
这本书很厚,塑封我没拆,从书店买了后就送到了医院,电梯升至十四层,肿瘤住院部,看着吓人,实际颇为热闹,人声鼎沸,小推车上是热气腾腾的午饭,还有几声吆喝,像是上了火车。走廊的护士忙忙活活,手里拎着打空的吊瓶火速赶回护士站,又猛地蹿出来,我一个也没拦住,在走廊里乱转,17床的名牌贴在门口标签处,李佳仪找到了。
推门进去,阳光直刺过来,偌大的窗户外面挂着太阳,窗帘卷成个结悬在空中晃悠,两个病床空了一个。李佳仪在靠窗的床沿坐着吃香蕉,香蕉剥成一朵花,花蕊断了一截,在她嘴里藏起来。她比印象里消瘦了些,扎着到肩的马尾,穿着蓝白条纹病号服,看到我时并不惊讶,也没站起来,只是说,你没变样。她声音陌生,喑哑,像是落进了沙。我走近了坐在磨得破损的看护椅上说,好久不见,书我给你拿了,还没去封呢。李佳仪把香蕉放下,拿过书,立马撕掉塑封皮,又转身从床头柜上摸来一支笔,打开第一页,写下了一行字,递还给我,说,这书我看了,现在你看。我接过来,打开书页,扉页是几个大字,李佳仪的船。她的字坚韧有力,笔画突出。我抬头打量她,她皮肤白皙,眼里有光,不像生病,嘴巴又重新嚼起香蕉,一点也不羞涩。她说,你好像老了一些。我说,你年轻了。她说,多久没见了。我说,两年吧。她说,咱俩谁删的谁。我说,是你吧,不了了之。她笑起来,说,想我吗?我说,不了了之。她拿香蕉皮砸我,我躲开,香蕉皮黏在背后的墙上,我扯下来,丢进垃圾桶里,说,你劲够大的。她说,看见你,就有劲。我说,你别说笑了,当初把我删得干净,唯恐避之不及,以为要当女明星了呢。她哈哈大笑,能从嘴巴里看见洁白的牙齿和粘在牙齿一侧的香蕉碎块。她从来不顾忌,直来直去,也没有不好意思,看着她有力地嬉闹,总觉得这个地方不适合她。窗外的阳光洒在她的脸上,面颊柔滑,没有一点时间的痕迹,我们也像是真的在火车上,房间各种仪器的底噪像是列车划过铁轨的哐当,正在奔赴某次未尽的旅行。
你什么时候出院?我问她。李佳仪收回笑声,把左手伸出来给我看,上面是刚打完的针眼,大概有四个,明显鼓着包。她说,今天怎么也打不进去了,鼓了两针。我说,疼不疼。她说,我老公还在非洲,就快变色了。我憋着笑,拿不准她的语气,说,所以回来住院,严重吗?她说,小手术,不想多说。我点点头,没有多问。我转移话题,说,这书讲的什么?其实我已经看了个梗概,马尔克斯写了一对忠贞不渝的爱情,在暮年重逢,飘荡于海上,过于乐观和美好。李佳仪说,我们都是船,不是人,大海是波浪状的,把我们碰在一起是缘分也是终结,碰就会碎,水会灌进来,然后慢慢下沉。我说,太高级了,能不能通俗点。她说,那你自己看吧,必须看,看完了,咱俩讨论。我说,还有下次?她准备过来扭我胳膊,她以前就喜欢扭胳膊,用拇指和食指捏起一个极小的缝隙,戳到你胳膊的肉里,逼你发出几声怪叫。
她过来时,我抱住了她。时间凝固了,光从她的头发缝隙里穿过,落在白色的床单上,那里有她身子压成的痩小痕迹,我不知道她在这张床上睡了几个夜晚,又即将面对什么样的手术治疗,窥探始终是种罪恶,我在犯罪,同时也在因犯罪而感觉惊讶。胳膊环绕胳膊,夹紧她的身子,这里面大概还有一种责备和抱怨,关于什么,已经不能说清了。
我感到她的手掌紧贴着我的背,头靠在我的肩膀上,就那么几秒,我们被拉回两年前的那个郊区。车外是恍惚洁白的雪,车窗渐渐升起一层白雾,从下缘爬升,遮挡了所有可见的玻璃块。我们被封闭,同时被逃离,被保护,被世俗隔绝,我扒掉她身上所有厚重和轻俏的衣物,我们藏身于后座,用自身的体温供给着整个世界的能量,她的每一声喘息都使我沉醉,每一处用力都令肌肤震颤,我是被上帝选中的种子,在她柔滑的体表寻找可以破土而出的凹陷。
护士进来时,她重回到床上坐好,护士让她躺下,她照做,把马尾重新散开,铺到枕头上,伸出右手,悬在空中。护士捏住她的手腕,来回拍打,说,你老公来了啊。她愣了一下说,是啊,来了,看着怎么样。护士觉得奇怪,但还是打量了一下我,我往后退几步,杵在窗台上。护士说,挺好,挺好,给你老婆弄点好吃的,看这瘦的。说完又拍了几下,李佳仪的手背红了起来,血管凸出,针从一处顶点戳进,红色的血液回流。护士走后,她闭目养神,我解开窗帘的结,拉住一半窗户,把阳光挡在床尾,坐在看护椅上翻书。
李佳仪的船。我又看了一遍她的字,才从故事开头看起,看了几行,翻到最后,字数二十多万,瞬间不想看了,我看不完,也没太大兴趣,随即合上。李佳仪眼睛都没睁开,说,你才看了几页。我说,三行,有个医生和尸体,我瞧着书太厚,有点费眼。她说,那你还我,船你别上了。我把书紧在胸口说,什么船。她睁开眼睛,半坐起来说,李佳仪的船,我给你写的,你看完这本书,我们讨论讨论爱情。我觉得好笑,她一脸认真,我说,爱情有什么好讨论的,前一秒死去活来,下一秒人不见了,都懒得找。她说,你在生气。我说,你想多了。她嗯了一声。
生气这个词言重了,记得当初是她老公去非洲的第一年,也许是因为寂寞,或者是什么别的,我没问过,我们不经常探讨这个问题,她来找我,我就陪她。她喜欢聊电影,最喜欢在电影播放时发表一些关于剧情走向的揣测,比较影响观感。电影院里除了屏幕不断变换着亮光,周围都是黑的,还有时不时从黑暗处传来的几句论断,每当此时,我就会握紧她的手,心想,她的手也这么被别的男人握着,想生气但也确实没有资格,像个局外人。有次也侧面问过,这样会不会有什么影响,她说,非洲的铁路很长,要绕海岸线一周,拐几个来回,他也许早就有了黑宝宝,不想提。我努力琢磨,黑宝宝诞生的基因组合,是取决于父亲还是母亲,始终无法下定结论。她说,你要是觉得不好,那就走吧,我放过你。她说放过的时候,没有看我,我忘记了她在看什么,电影荧幕还是马路,大海还是车水马龙,我都觉得荒凉,她开始往前走,每走一步,我就往暗处陷下一步,我追上她,再没想过离开。
下次你过来,带着书,我要考考你,她说。我重新翻开书本,她再次躺下,时光缓慢流逝着,吊瓶的点滴像落进心里,窗外一切正好,李佳仪睡着了,如果我去吻她,也许她也不会拒绝,我只是想了想,心里便咯噔一声。把霍乱时期的爱情夹进腋下,慌乱地走出了病房。
3
客厅的蓝色大象还是被换掉了。下午,张慧的父亲坐在沙发抽烟,电视机里是一场足球赛,蓝色对红色,张父押的红色,最后输了,看蓝色不顺眼,问张慧,背后这个大象是怎么回事。我抢着回答,说,是抽象画,网上淘来的。他说,你们的结婚照不是照了,怎么不挂上。我说,卧室里有,电视柜也有呢。张父猛嘬了口烟,张慧用手指把烟灰缸往茶几内侧推了推,他还是把烟灰弹在了桌面上,说,把这个换了。
电视里吵闹的欢呼声淹没了主持人的解说,我从书房拎出铁轨的内景照,踩着凳子,把大象拆下来,把我们放了上去。张父慈眉笑脸,说,这多顺眼,寓意也好,勇往直前嘛。当初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就说了,这个地方,必须得放个结婚照,喜庆。我拎着大象回书房,把窗户打开,烟味无孔不入,我现在闻了呛,已经戒烟一年多了。张慧和父亲聊着银行的一些事,又聊了聊接下来的婚礼,他们好像都定好了,好像张慧要和父亲结婚,这种感觉极为怪异,我把门掩上,坐在桌前翻开了书。
“女孩抬眼看了看是谁走过窗前。正是这偶然的一瞥,成为这场半世纪后仍未结束的惊天动地的爱情的源头。”
看得云里雾里,什么爱情可以惊天动地长达半个多世纪。张慧父亲早年离异,现在银行一把手,呼风唤雨,女人也轮着换。我不好评论,张慧也不过问。我父亲去世得早,母亲一直一个人,就盼着有个小的,好再年轻一回。爱情是什么,我透过门缝看张慧,她低头擦着茶几,把父亲抖落的烟灰擦净,抹布攥在手里,眼睛盯着电视机,等待着下一场即将到来的球赛。大象画立在墙根,乍看有些孤独,透着莫名的悲哀,两只眼睛里是打转的瞳仁,我把视线转回来继续看书。
晚上躺下,张慧反复辗转,在被窝里闹腾,说,这床就没毛病,弹簧不碍事。我说,这事提了多回了,加了500,还是管用。她说,也不是,就是质量问题,看着挺好,芯坏了。我听着浑身发凉,把被角往上提了提,倚在床头。一盏夹灯,黄光不耀眼,刚好可以看清字,书在我手上。张慧说,你最近怎么看起书来了。我说,放假没事,闲着也是闲着,补充营养。她从被子里靠过来,一只腿盘住我的身子,说,什么书?我把她搂过来,说,马尔克斯,你听过没?她说,没有,听过马斯克,婚车就买他的吧,电动汽车,加油多,起步稳,安静。我说,你是不是傻,电动汽车你加什么油。她把我的书抢过去,胡乱翻着。
灯光是扇形,只能打到她的侧脸,书上的东西都看不清,她没在扉页停留,我舒了口气。就算是看见了,又怎么样,老同学而已,解释吗,怎么解释,不解释吗,有什么好解释的。她翻够了,觉得书沉,猛地扔到床角,没丢准,书掉到地板上,砰的一声。我从被子里钻出来,挪步过去捡起,再回头时,张慧像条蛇,侧躺在被子上面,睡衣肩带刻意剥落,露出半胸,头发蓬松,眼睛藏于发丝后头,妖娆,妩媚。我把书放到床头柜,爬上床,把她拥进被窝,顺手关掉夹灯。她呼吸很厚重,身子壮实,很快反客为主,我丢了兴趣,但也努力配合。未婚妻在身上起伏,轮廓臃肿,背后的墙面煞白,我盯着时钟,瘦小的秒针匀速转动,我希望它转快点,大脑充血,肢体不受控制。张慧发现了有些异样,停了下来。我说,怎么了。她说,是因为我爸吗?我说,你爸怎么了?她说,我爸让你换画。我说,没有,继续吧。对话说完就软了,再进不去。她下来,躺好,说明天还有几个客户,就先睡了。我打开夹灯,把灯头转向外侧,半扯着身子看书。
“最终,在习惯的魔力面前,他屈服了。很快,他便为自己的屈服想出了一个简单的理由。这里就是他的世界,他对自己说,这个悲伤而压抑的世界是上帝安排给他的,他属于这里。”
把书翻到扉页,手指放到那几个字上,笔墨从指尖刺进去。李佳仪在汽车后座睡着时,裹着长款棉衣,她懒得穿内衣,说不想动,我把羽绒服也给她披上,起雾的玻璃沾满雪花,车内欲望褪去变得异常冰冷,座椅发凉。李佳仪闭着眼睛,枕在我的臂弯,安静得像一只熟睡的猫。我怕她真的睡着会着凉,便摇了摇她,她说,你别动我,让我死在你怀里吧。我说,你瞎说什么。她不回话,眼睛睁开,眯起来看着窗外,只能看到一片楼宇的阴影映在玻璃上。
这是一片烂尾楼的郊区,我把车开到这里,她说有种逃离感,很令人兴奋。我不明白什么逃离感,雪已经把挡风玻璃盖得严严实实了,谁也不会找到我们。她抖落披好的棉衣和羽绒服,再次骑到我的身上,吻我,用细柔的发丝触我,没有话语,没有理由,她像一粒掉落的珍珠,努力回到蚌里。
我合上书,把当年的情景继续想下去,李佳仪后来真的睡着了,她劳累,疲倦,还带着恨意,我把车从郊区继续往外开,送她去机场,她临时改变了主意,我沿着机场路往南开,一路往南开。
张慧打起了呼噜,声音像起伏的小山,鼓起来又塌下去,她脚一蹬,肩膀露了出来,空调冷气很足,我把被角给她拽上去。熄了灯后,总是睡不着,给自己的屈服一个简单的理由,我属于这里,眼底是一片宽阔的机场路,李佳仪蜷缩在后座上,身上裹着厚厚的衣物。
我摸出手机给她发了个信息,费尔明娜像一只蛹。
4
病房里人多了起来,隔壁床躺着年纪稍大的妇女,闭着眼睛,半盖着被子,男人坐在马扎上,握起妇女的手,把头埋进床沿。其他几个人,抱着胳膊,背着手,像是妇女的亲戚,在聊细胞的生与灭。
我往里走,李佳仪站在床边背对门口,披头散发,朝着窗外。我靠近她时,她吓了一跳,转过头看我,我发现她状态不好,眼袋很深,没有上次有精神,里外像蒙了层灰。我还是问了,今天还好吗?问完又觉得很蠢,这种句子像不过脑子。我在她旁边站好,同样看往窗外。
十四层的高度把中学校园缩成指甲盖大小,操场的假草坪貌似清洗过,在微弱的夕阳下反着光,远处天边的云过于平坦和规整,像一条烧红的马路。她说,多少年没回去了。我说,回哪去。她伸手指了指那个指甲盖,说,回那儿。我说,都多久了,那还是911飞机撞大楼的年代。她说,我记得啊,刚过了教师节,我送的花还在讲桌的粉笔盒里插着,飞机就把楼撞了,电视里都是烟,呛人。我说,跟我们又没有关系。她说,那时候起,我就觉得,跟每个人都有关系。我说,你太会联想了,一会儿船,一会儿飞机的。她说,我是说,意外随时发生。我说,是,我们躲在十四层的中心医院,随时可能有一架装满乘客的飞机向我们飞来。目光中的云不再笔直,扭曲了身形,像是有东西从中穿过。我接着说,一会准备趴下,飞机会撞到头。李佳仪抱起胳膊,紧在胸口,说,我不躲。
隔壁床的亲戚带着笑走出病房,男人出门送,妇女睁开眼睛与回头的我对视,我接着把头扭回来,感觉她的眼神有刺,浑身发麻。我说,书我读了将近一半,昨天给你发信息,你也没回,你看了吧。李佳仪说,你知道我得的什么病吧。我说,我知道。信息发完我就在查,中心医院十四层肿瘤住院部的女性病症,乳腺癌对我来说是一种极为陌生的病灶,我不太了解,但也多少从网络搜到一些,再往下查都是绝症,令自己恐慌,也开始担心身边熟睡的张慧,索性放弃了。李佳仪继续说,带我去那吧。她手臂缓慢抬起来,指着不再反光的操场。
李佳仪拉上围帘换衣服,我在门外等着,给张慧发了信息,有局,晚点回去。傍晚的走廊安静,平和,人们走路缓慢,抬不起腿,像灌了铅。她穿了一件白裙出来,纤细,轻盈,裹着病态的倦容,手腕的标签藏在身后。我试图扶她,但又不知道该把手架哪,犹豫时,她把手伸出来,握住了我的手。我们向外走,于电梯下降,失重的几秒里侧头看她,她极为平静,目光朝前,手心冰凉。
校园自然是不让进的,晚饭点还没有到,学生出不来,李佳仪说我们是老生,来看老师的。我暗自发笑,这个生够老的,老师的名字我都不记得了。她跟保安闲聊,报上了几个名字,徐建,张红兵,王思惠,保安连连点头,放我们进去。进门左转,我们去了操场,天色已经暗了,头上灰蒙蒙的,有些浑浊。我说,可能要下雨。她说,你别松手。我一直握紧,争取黏住。从操场侧门进去,草坪干净,整洁,绿色变暗,没有光打上去,四周的照灯没开,远处教学楼的灯挨个屋子亮起,有细细的光丝游过来。
我们开始走,沿着跑道内圈,她步伐轻盈,脚步小,我控制步子跟着,像踩在玻璃上。她舒了口气,说,那我要考考你了。我说,来吧。她仰头看天,还是一副中学学霸的模样,趾高气扬,说,你觉得费尔明娜为什么跟医生结婚。我说,费尔明娜她妈想抱外孙。她甩开我的手,我又续上。她说,你认真点。我说,我很认真,我妈想抱孙子,去年在相亲公园,就是南湖那里转了四天,给我找了个女人,我下个月结婚。她步伐变大,胳膊被拉得很长,我跟上,把夹角缩小。她说,你爱她吗?问题太尖锐,我把手攥紧,她嘶了一声,瞪眼看我。我默不作声,从她暗色的瞳仁里看膨胀的自己。
我说,她爸是银行行长,我们的房子位置很好,就在山边上,推开窗子,先进来的是鸟鸣,然后才是露水味的风。卧室有四个,其中一个改成了书房,我喜欢客厅里的一幅儿童大象画,不知道是谁画的,很孤独,看着总想起些什么,最近才明白,蓝色像大海,白色眼睛是船,船与船之间有会喷水的山脉阻隔。不过现在都被换掉了,所有房间的墙上都有结婚照,严重修过,我没那么帅,看久了觉得不是我家,跟我没啥关系。
李佳仪继续往前走,我跟上去接着说,两周后在蓝海御华大酒店,就长城路那边,西装是暗红色,不太喜欢,像枣壳。婚纱不合适,她有点壮,花了一个小时现改的,我坐在婚纱堆圆凳上看书,总觉得自己在婚姻坟墓的中心,有什么东西即将把我掩埋,我已经半年多不吸烟了,未婚妻说戒烟戒酒,婚后就要孩子,得提前半年。我找前台要了根烟,点着火吸了一口,谁也没看见,我觉得我还活着。
说完这些话感觉很累,即将瘫在地上,手被紧紧握住。李佳仪说,夫妻生活的症结在于学会控制反感。我笑了笑说,你真会总结。她说,不是,这是考题,你看得不仔细,这话是费尔明娜说的。我说,弱者永远无法进入爱情的王国,阿里萨的母亲说。她说,我们都是弱者。
光从头顶洒下来,操场四周的探照灯是多孔的,像密密麻麻的洞,不知不觉我们已经踩在了假草坪上,位于整个操场的中心。光圈在半空缩紧,李佳仪停下脚步,转回身,脚下像有舞台升起,我向前一步,她把我的手抬起放到她的胸前。手掌全部抚上去,能感受她裙内娇小的乳房,她没穿内衣,手感柔嫩,像托起一块豆腐。她说,喜欢吗?我不知道说什么。她说,这里,有一块肿瘤,癌变的可能性很大,也许明天,也许今晚。爱情从这里面发芽,根是很久以前就埋进去的,那会儿,我们也在操场上,你写信给我,读给我听。我说,我忘了。她说,你别说话。我只能安静地摸着她的胸。她说,你乐于表达,说你喜欢我,我故作高傲,觉得能掌控一切,从这里出去,到北京,到美国,到加拿大,澳大利亚,欧洲。我说,你是旅行家。她又瞪我一眼说,叫你别说话。然后沉下心绪继续说,乌尔比诺是河北省高考状元,家里世世代代是工程师,在北京有很大的企业,京台高铁的项目也有参与,不满足国内发展,去了非洲,立志要把非洲铁路偷偷刻上名字,佳仪铁路,纵贯南北,绕海岸线一周。我说,乌尔比诺是个医生,没参加过高考,抓鹦鹉时摔死在自家花园里。你偷换概念,又是考题吧。李佳仪说,你使点劲。我勉强用力抓住她的胸,那块柔软贴在手心。她说,两年前的你,劲没这么小。我说,你是病人。她说,你也是病人。
两年前,车没停过,从机场路上了高速后一直往南,开到后半夜没油了,找到一处服务区,李佳仪从后座醒过来,神情恍惚,看着我发呆。我把她抱出来,她站在地上,双腿发颤,哆嗦个不停。太冷了,我抱着她,给她取暖。她开始哭,说自己应该在飞机上,这是什么鬼地方。我有些自责,也不好辩解,匆匆把油加满,掉头往回开。李佳仪坐在副驾驶,头朝着窗外,用英语打着电话,接着又换成中文,亲切的老公称呼,收敛起眼泪的做作,嗓音撑开,说自己堵车了,没赶上飞机,明天应该能到,简单寒暄几句。挂了电话,我没有多问,那不是我的世界,我现在是个安静的司机。她把侧边头发捋到耳后,整理了一下面容,头探向我,似乎要吻我。我躲开,说,我在开车。她说,我有点恍惚。我说,我知道,你睡吧,两个小时后带你去机场买票。
5
婚礼如期举行,蓝海御华大酒店包了一半停车场,来了很多人,我和张慧站在门口挨个迎接,我几乎都不认识,眼皮抬不起来。昨晚没睡,一个人在卧室里躺着,看着满屋子的结婚照,觉得幸福好像敲错了门。
凌晨三点化妆师上门,四点开车去张父家接新娘,伴郎有我同事,大部分是她的朋友,一个六个,分两辆特斯拉,喧嚣从一早就会开始。我躺在床上,享受最后片刻的宁静。拧开灯,把霍乱时期的爱情看完,新忠诚号上的费尔明娜和阿里萨已经老得不成样子,两个人像泰坦尼克的恋人站在甲板上摆pose。阿萨里升起黄旗,谎称因霍乱检疫隔离,船无人打扰,从世俗之海出航,永不靠岸。
我把书翻到扉页,给李佳仪发了信息,书我读完了,幸亏乌尔比诺死得早。等了一会,她竟然回复了。她说,打给我,睡不着。我把电话拨过去,她说,方便吗?我说方便。她说,你把手伸出来。我把手伸到空中说,伸出来了。她说,告诉我你摸它的时候,是什么感觉。我说,摸什么?她说,我的乳房,它已经没了,我想想象一下。我愣了会说,很娇小,可爱,软绵绵的,像一块果冻,舍不得用力。她说,行了,好像在了。我说,疼吗?她说,能不说废话吗?我说,好,书我看完了。她说,那爱情是什么?我说,一生一世。她说,傻瓜,我告诉你,费尔明娜和阿里萨来到四十年前的老地方重温蜜月旅行,被载他们出游的船夫用桨活活打死了,船夫为了抢走他们身上的钱。
她一口气说完,有些喘,冷静了几秒后接着说,你明白了吗?我说,我不明白。她说,马尔克斯是个骗子。我说,什么?她说,你什么时候结婚。我想了一会说,就今天,一早。她说,有人会给你化妆吧,你是不是已经把楼下所有的井盖贴上红纸了,大门口的双喜用什么贴的,浆糊还是透明胶,婚车准备了几辆,钱都提前付给人家了吗?婚礼视频做好了吗?背景音乐是你们自己选的吗?完了还要吃饭,一共订了几桌,来人都随了多少钱,晚上趴在床上数钱,数完钱再做爱,就在现在这个床上是吗?我说,你怎么了?她说,你这个骗子,你早就结过婚了,土都快把你埋了,用力闻闻吧,大口喘气吧,窒息才是命运,谎言能撑多久。我说,你冷静一下。她说,你带我走吧,我的船破了,都是脓,刀子从侧面划进去的,取出的不只是瘤子,远不只是瘤子。我说,你冷静一下。她说,李佳仪的船破了,你管不管,我今天去找你,行不行。我说,你冷静一下。
张慧的父亲走到我的身边站了许久,用力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身子下沉,差点没站住。他说,激动吗?我说激动。他从口袋里摸烟,我带着火机,派上了用场,把火苗给他捧过去,点上。他吐口烟说,当老师挣不了几个钱。我说,挣不了。他说,就图个稳定,老实。我说,是,很老实。他说,放心了,一会叫爸大点声。我说,好的,叔。
张慧挪步过来,说,我爸又点化你了。我说,没有,老爷子很好。她的婚纱拖地,两手拽着裙摆,满脸堆笑,很大方。我说,你今天很漂亮。她说,结婚管用。我说,什么用。她说,你能看到真相。我大声笑起来,眼神放远,越过停车场,落在酒店大院门口,期待着什么。
如果李佳仪跑过来找我,我会做什么。枣壳色的西装暗沉,我略痩,白衬衫在后背用别针扎住,动作幅度过大就会刺进肉里,保持腰背挺直,睡眠不足,浑身疲乏。如果李佳仪跑过来,我会做什么。把西装扔进大厅,西裤衬衫都脱掉,从陆地上船,于酒店之海出港,握住桨,把她搂紧怀里,升起瘟疫之旗,无人可以靠近,无人有勇气靠近。
张慧说,婚礼完了,把大象挂回去吧。我看了看她,说,没事。她点点头。客人一波一波,我重新挤出笑脸,像个木偶。
舞台灯光闪烁,主持人像打了鸡血,逗得台下阵阵欢呼。我站在酒杯蛋糕台的侧旁,眯着眼看,眼眶里始终有块白斑,是刺眼的灯留下的余象,看东西像缺了一角,主持人缺了一块耳朵,摄像师缺了一根胳膊,远处被张父领着走来的未婚妻缺了一个乳房。
我手心出汗,感到烦躁。音乐升起时,舞台前方从地板腾空而起一条小路,两旁激光射灯耀眼,四处乱打。我被主持人推到舞台中央,像搁置于大海的扁舟,被音响震颤。张慧走来时眼里含着泪花,望着父亲,张父直盯着我,我咬起牙齿,咽下口水。
主持人为了活跃气氛,安排了几个幼稚的环节,我一一配合,眼神不停地瞄向大门。主持人发现了这一细节,竟然用话筒调侃说,看来新郎还在等人。我浑身一哆嗦,他接着又说,有缘人,心上人,枕边人,情人,爱人,珍惜你的眼前人。我不知道他在扯什么,台下掌声响起,话筒交到我的手上,我看着张慧,眼睛还是不舒服,白斑还在。某一秒抽离神经,听到有人在哭,因身体的不完整而抱怨,因情感的无处发泄而寡欢。
凌晨的机场空旷而荒凉,手续处理好后,李佳仪将坐一小时后的飞机返航,这是两年前的冬天,她说,你可以走了。我说,如果我不走呢。她说,我管不了。我走出机场的大门时,雪又重新飘起来,地上的雪花凝固又融化,变成一滩滩水,散发着某种臭味。我就在那里站了一个小时,抽了一盒烟,直到飞机从停机坪开出,又飞上了天,我才重新坐回车里,拿出手机把李佳仪删得干干净净。
大厅的门被推开,有人倚着门框站在那里,头发散落肩头,形影孤单,瘦削,抱着胳膊,捂着前胸。我仔细辨认,终不得结果,看不清是谁,她没动,只是安静地听。
于是,我说,我们就像船,大海宽阔无边,离了港就没有岸,我愿意卸下一切,升起黄色的旗,扬起破旧不堪的帆,你如果问我,时间有没有年限,生活是否困惑不堪,我可能无法回答,爱情是什么,满嘴谎言和忠贞不渝,都可以。
我想好了,能否上你的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