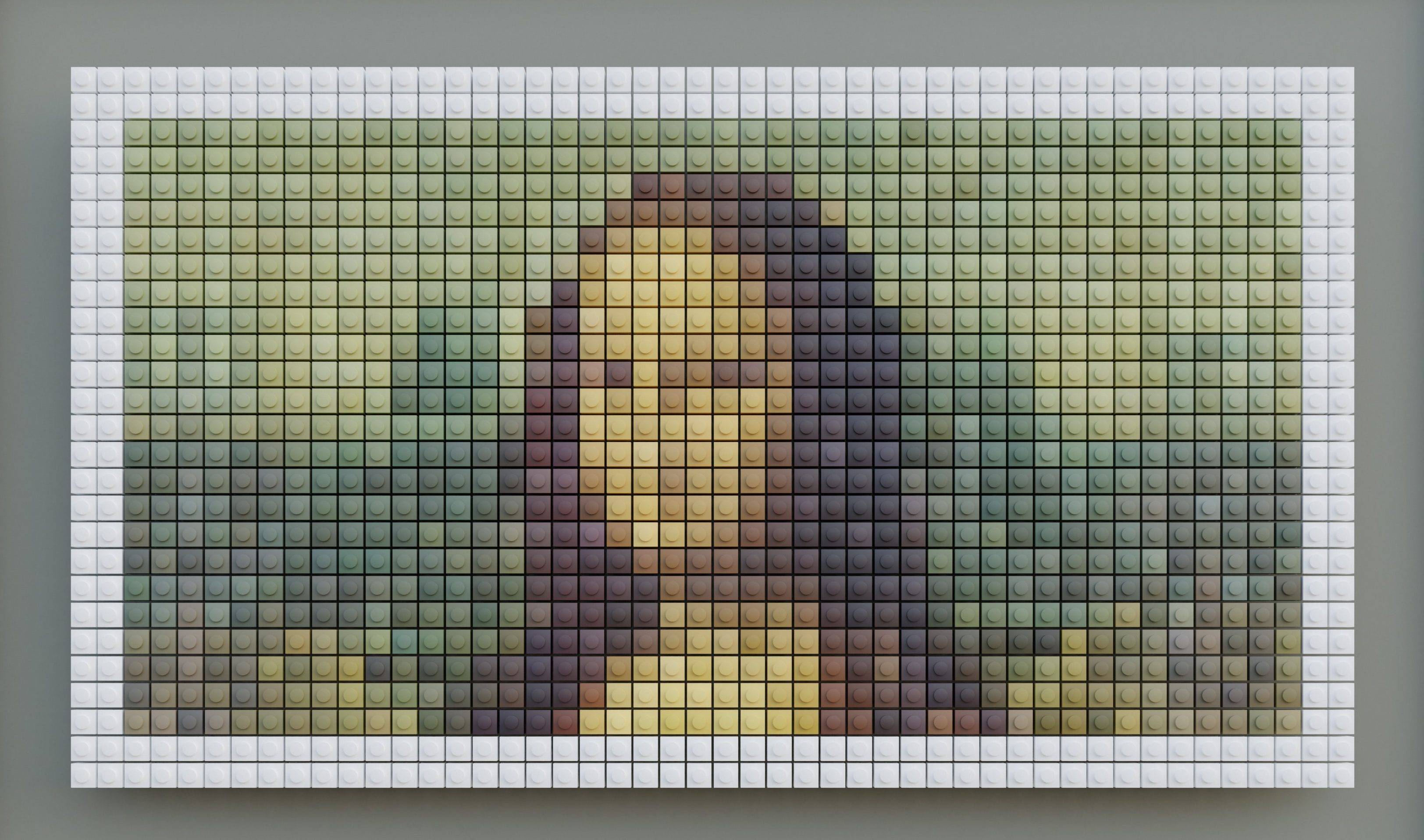
「后台谈话」是由「ONE一个」发起的作家访谈类专栏。我们相信,不管文学场如何人声鼎沸,「后台」始终是那些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艰难求索的作家,和他们的心灵内史。
谈话者:
李停,「故事大爆炸2022」首奖作品《在小山和小山之间》作者。女,1990年生,安徽人。本科于北京电影学院就读电影剧作专业,东京MARCH日本文学专业硕博连读。现定居东京,从事写作、翻译。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李停你好,先恭喜你获得了故事大爆炸的首奖,这几乎是一个万里挑一的奖,我觉得含金量很高。作品也完全值得。在获奖作品里,感觉你用显微镜分别为大家展现了女儿和母亲。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篇作品一定是来源于生活的,或者说提炼于生活——我这么武断或许是“中国式”的。我的第一个问题是,你妈妈真的叫任蓉蓉吗?你会不会担心妈妈看到了这篇获奖作品后,产生一些复杂的心情?
李停:小饭老师好,谢谢你的鼓励。看到你的第一个问题我笑了,因为我妈妈和任蓉蓉从人生经历到做事风格,几乎没有任何相似之处,也许在性格上她难免有“中国式妈妈”的地方,但我可以肯定她看了这篇文章只会觉得跟自己毫无关联。包括我的丈夫,他看了这篇文章,也觉得那个渡边跟自己毫不沾边。我认同你说的,作品一定是来源于,或者说提炼于生活,我只能归结于我的作品的主要情节来源于别人的生活。这和我喜欢与人打交道,喜欢观察人有关。至于情节里包含的情感,一部分是我从别的事情感受到的、我认为和故事情节吻合的个人体验,一部分是我观察别人后得出的思考。
小饭:那做你的朋友挺“危险”的。确实很多作家都会拿身边人开刀。关于故事,我想问当初为何会安排这样一个“悲怆”的结尾?当然,在这个故事里,或许没有更好的选择。如果说母女的和解是“明亮”的结尾也能说得过去,但我注意到有评论认为“结尾走进了闭环”,我有同感。写作的时候是怎么想的?
李停:结尾我只是顺势而写,当时的情感到了那里就成了那样子。我没有想过它是“悲怆的”还是“明亮的”,“闭环”这个词也是你提出来后我想了一下,确实如此。结尾比起母女的“和解”(我甚至不认为她们和解了,只不过母女两人的神经都放松了一些),我更在意母女对新生命到来的态度。“会有很多事情来分散你的注意力,干涉你,让你没有办法关注自己的孩子……你要时刻专注,要警惕,要坚强,只有这样才能保护你的孩子。”这句话里有几层意思,一是妈妈后悔没有保护好自己的小儿子导致他意外死亡,二是妈妈后悔因为小儿子的意外死亡,由于自己的精神崩溃而给女儿带来的不幸童年。第二层意思是我觉得最痛的,因为一个母亲势必会因为任何一个孩子的死亡而崩溃,她明明是最受伤的人。而她同时作为另外一个孩子的母亲,对自己的崩溃负有罪恶感,无法自处,在她看来,两个孩子她都没有保护好。第三层意思是我希望女儿听懂妈妈的话后,能想到自己纠缠在一段复杂的感情中只会被分散注意力,失去对自己的孩子的关注。
小饭:我很意外得知,你是在获悉得奖之后才“发现”自己怀孕的。小说中所描写的一切是你想象中会发生的吗?是因为某种轻微的恐惧,还是因为理性上的预判?
李停:准确地说我是在9月初知道入围后确定怀孕的。这也牵涉到上一个问题,8月我一直在等备孕结果,所以对其他事都不怎么关心。直到8月最后一天无意看到征稿,才把7月写完的《小山》匆匆发了过去。小说的原型是我在学校的“创意写作课”上的一个小作业,当然,是日语的。不过因为日语水平不好,进度很慢,但我的故事已经成熟了,等不及了,我只好先用中文把它敲出来。这个小作业源于我在豆瓣上看到一个“努力”嫁在日本的女孩说,比起自己的中国人妈妈只会家长里短,日本人婆婆更爱艺术、思想开明。当时我直觉她没有看到另外一面,妈妈的那一面。我想把妈妈的那一面写出来。事情有很多面,各面却互不知晓,这个定律在母女关系中最为让我痛心。我没有把这个和自己联系起来,在我心里它是一个纯虚构。
小饭:在你的作品里我能感受到你是一个特别能“换位思考”的人,包括你这篇获奖作品的写法,也是人物交替叙述。你是何时发现自己有这样的品质的?这种特质在写作上对你的帮助是怎样的?
李停:我喜欢和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也做过很多不同的工作,因此我了解同一件事、同一句话,在不同的眼睛里天差地别。我很讨厌片面的叙述,因为我觉得愚蠢、没劲——事情怎么可能只有那一面,而且是利于你自己的那一面?你一定隐瞒了其他面的存在。对我而言,第一个问题是:你有没有连自己都隐瞒,或者说,你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在隐瞒,有没有一个瞬间你面对自己时会觉得悲哀,为一切。第二个问题是:事情一定有很多面,各面之间很可能互不知晓。用上个回答里我说到的“嫁在日本、觉得日本婆婆比较好的女孩”举例,我会发散性地想很多方面。比如她本人生活得开心吗?用一纸“日本人配偶者”签证留在日本会不会被丈夫看轻?她口中的爱艺术的日本婆婆是什么样的人?别人如何看她,她又如何给自己定位?她妈妈知道这些吗?我知道她一定很难,那妈妈呢?我还会戏谑地想:日本婆婆爱艺术,中国妈妈可以包包子,这是不同的时代背景,如何比较?为了看清楚整件事,我不得不站在不同的角度来看问题,再把我认为值得写的角度强化。我希望把事情摊开了看,摊开了谈,至少在一些关键时刻。事情有很多方面,我敬佩那些能看到一件事的很多方面但不轻易下评价的人,这让我感觉有一种包容、余裕,是我向往的品质之一。何时发现这种品质?应该是因为我被女生朋友说是“男性思维”。语境是女生朋友跟我抱怨她男友的不好之处,话里全是她多可怜多无私而男友多么混账不是人。我总是能立即指出她的逻辑漏洞,揭穿她其实也说了一些伤人的话、有一些小心思,而她现在绝口不提这些是没有好处的,对她自己看清关系没有好处。一开始她会反驳,后来她也意识到看全面些对自己改善关系更有利。这种特质对我在写作上的帮助,可能就是比较少事实漏洞吧。
小饭:那你会建议自己的丈夫阅读自己的作品吗?会和最亲密的伙伴交流自己的写作吗?无论是在作品完成之后还是在构思一部作品之前?你认为这样的交流是有效的吗?
李停:我丈夫知道我所有的构思,一旦我有任何新想法就会迫不及待告诉他,不管他有没有兴趣。他一直给我很多建议,补充了我看不到的某些方面,还会提出他自己的观点。我还有一个从电影学院时代开始就最亲近的闺蜜,十几年了,我们会聊每一本看过的书、电影,各自写的所有东西。我几乎每天都会和丈夫或者闺蜜聊天,我敢说他们对我的了解已经到了多余的地步(笑)。交流对作品有没有效我不知道,但交流肯定构成了我这个人。在大学的“创意写作课”上我也认识了很多的写作者,大家会讨论各自的作品,我比较毒舌,经常把文质彬彬的日本人问得一愣一愣。
小饭:我很想知道你在日本大学的“创意写作课”具体学到了一些什么?之前很长一段时间我们认为写作没办法教,作家没办法在高校被“培养”,但后来人们的观念变了,国内很多大学也都开设了类似“创意写作课”的班。我能感觉到你是受益其中的。
李停:我也认为写作是不能被“培养”的,但可以被“讨论”。我在的“创意写作课”就是以讨论为主,老师也没说想要培养谁,愿意多写他就会看,不愿意写也没人管。这个课开在大学院(研究生院),只有研究生和博士参加,几乎所有成员都是有工作经历的,多数也还在工作,其中一些出版过作品。老师每周会给一个主题,比如“死亡”、“钱”、“仪式”等等,大家围绕同一个主题写自己的东西,下周带来,在全部人面前读一章,然后展开讨论。期末有自由主题创作,想写什么写什么,也是一个个拿出来念,然后讨论。不定期有老师的作家朋友来课上交流,大家还有据点,是个上海菜馆,我们经常在那里喝酒吃饭聊天。有个韩国人,是资深文学编辑,她想写自传,说了一通伟大构思和奇妙设定后,我举手问:“故事明白了,我只有一个问题,你是谁?我为什么会想知道你的一生呢?”她后来成了我在日本最好的朋友之一,全家一起去旅游的那种。我们不仅在课上,在私下吃饭时也会激烈争论,但从没有真的生过气,因为都是在讨论创作观。她最终承认自己做编辑更顺手,也一直欣赏我的文章,说我应该写作。最近她负责了凑佳苗的《告白》在韩国的出版,送了我一本日语版,一定要我看后讨论,我实在是看不下去,逃了好多次。还有一个日本同学,写的是古代嫦娥的故事,夹杂日语古文,我老实告诉她我完全读不懂,她也不生气,还热心帮我改日语文法,现在我们成了能聊爱情的朋友。如果说我受益,应该是结识了一些喜欢文学的老师和朋友吧,大家彼此有个牵绊。
小饭:那你写到计划生育那一段的时候,有没有去查阅资料?这一段写得也很“紧张”,密度很大,有画面感,哪怕一些配角(比如芬如)都有人物光环。作为“没有生活经验”的年轻作者,你是怎么做到这些的?
李停:没有查资料。但我打电话和妈妈说,我要写一个有关计划生育的小说,问了她两个问题,“如果怀上了怎么办。”“如果月份大了打不掉怎么办。”关于第一个问题。我妈妈告诉我,我的一个亲戚就是怀上了去农村躲起来,直到生完再回城。她说那个年代这么干的人很多。我回忆起那个亲戚的事,意识到我确实在一段时间内没见到她人在哪里,而她回来时确实多了一个宝宝。但以我当时的年龄,肯定不可能意识到她身上发生了什么,我又代入如果她是我的妈妈,而我跟她一起去了农村经历待产的过程,我长大后又会记得多少?即便她经历了她人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但对我来说可能只是一次长时间的留宿而已。第二个问题。“引产”这个词是妈妈告诉我的,她是医生。至于需不需要引产、几个月需要引产,都是当时当地的政策而定,有松的地方,有紧的地方,有松的时候,有紧的时候,这些事随机性太强。这也是我的一个痛点:站在一个妈妈的角度,自己的孩子的命运要被这些随机性而决定,这是多么大的悲哀。另外我在日本生孩子也认识了一些孕妇,大家交流很多关于孩子的想法。从怀孕到生出一个健康的宝宝,妈妈要担心的事实在是太多了。任何一点孕中的反常,妈妈都生怕是出了什么问题,谨慎对待,我只是把这个事实放在了一个极端的语境里。
小饭:写这些的时候会有所顾忌吗?会觉得这些题材是敏感的吗?或者问得更具体一些,你会为自己的写作做一些自我审查吗?比如,什么样的内容和作品,你不允许出现在自己的笔下?
李停:没有。写剧本明显需要更多的审查,小说我没有这种意识。非要说的话,我不愿意写不体面的描写,包括会让我生理性不适和心理性不适的,我认为绝大多时候都没必要用这种刺激,是滥用。
小饭:你平时会看日本小说吗?事实上我认为你的写作风格有日本小说的影响,尤其是早些年很流行的日本私小说,青山七惠为代表的那一批年轻作家你怎么评判?我还有一个问题,小说中提到你在翻译一本日本小说,很想知道这件事是否也有现实原型?是怎样的一本小说呢?
李停:几乎不看。最早刚来日本的时候看过一些,是为了学日语,年轻作家用的日语生活化,适合学日语(笑)。青山七惠的书我也只看过一个开头,看不下去,总会分神。可能因为我在日本生活久了,对那种流行日式文学有点不耐受。我确实翻译了一本日本小说,而且主要是在我怀第一胎的时候,和我肚子里的宝宝一起完成的。小说是我的博士导师写的,译本于今年3月完稿,预计明年能出版。
小饭:问一个笨一点的问题:你认为一篇好小说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故事,人物,还是结构,或者说语言?你最推崇哪一类作品?你的阅读结构和知识结构是怎样的?
李停:这个问题很有趣,因为随着年纪变化我的答案很可能是截然不同的。我就谈谈目前我的感受。我现在认为一篇好小说得好读易读、让人愿意反复读。好读易读应该是指讲故事的方式很舒服,语言平实。让人愿意反复读是情感充沛,人物真实。有些书我真的只能读一个开头,就忍不住去做别的事,这种就是不好读。而大部分的推理小说都让我有一种“凶手知道了就没必要看下去”的感觉,更不可能读第二遍。我最喜欢的作家是石黑一雄、约翰斯坦贝克、毛姆,中文写作里最喜欢白先勇。他们的所有书我都反复读过太多次,而且每次都感觉被感染、被注入活力,像是营养补充剂,也像是希望之塔——同为人类,他竟然能写成这样。知识结构指什么我不太清楚,我学得很杂。高中我是理科生,很喜欢数学。本科在电影学院文学系,后来在东京念文学博士的其中一年,受导师引荐,我从文学系跳到了经济系,一年时间都在经济系教授门下学习。导师原话是:“文学是最通俗的经济学。文学聚焦复杂扭曲的人性,理解文学,才能理解经济学。”也就是说,想学好文学,理解经济学是很重要的。此外我还在全球知名的化妆品公司工作了四年,兼职教过中文,和朋友合开了公司,学了很多税务知识。如果不做这些看似和写作无关的事,我可能根本没有想写的东西。
小饭:我也很喜欢约翰斯坦贝克那本《斯坦贝克携犬横越美国》。那种游历中的见闻,是否会接近你现在的生活状态?你觉得身在国外,用中文写作,假如写到中国或者中国人,是否会存在一种距离感,这种距离感会让你写作更自由吗?
李停:我好像不是在游历,而是真的生活在这里。我希望我认识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要类型化、标签化,而是一个个丰富多彩的人,我用心去理解的人。当我用日语写作,只要没有在小说里特别提到国籍的话,读者会默认我在写的是一个日本人。长期使用日语,切回中文写作状态时确实有一种迷之自信,觉得自己能说清楚自己的全部想法而不被误解,这当然不可能,只是相较于用日语而言中文表达会自信很多。如果说距离感的话,我想正这是我对自己的一个要求——不要贴着,拉开距离。写中国人,我既不想完全以中国人的身份去写,也不想以日本人看中国人的视角去写,我想把整件事情的各面先想一遍,再决定从哪个角度写。我特别害怕“贴着”,特别警醒“我我我”的写作,如果写了“我我我”,我会难免像问那个韩国朋友一样问我自己:“看到你你你了,但你哪位啊。”
小饭:是什么机缘让你注意到“故事大爆炸”,以及来投稿的?在这之前了解国内一些文学平台吗?
李停:这个说起来有点玄乎,我是8月30号无意中看到的,真的是无意,无意到我已经忘记是从哪个页面了。我还记得当时是下午四点钟,我必须在半小时内出门办事,就先把投稿链接复制到了自己邮箱。9月1号截稿,我是在8月30号晚上投稿的。文学平台完全不了解。
小饭:嗯,接下来会有怎样的写作计划?在哪些地方能看到你更新的作品?
李停:我在写一个“岛上”的故事,希望明年能完成。我不是一个多产的作者,因为我总是同时在做很多事,写作像是我的后台运行程序。如果不是不得不写、不写我就会满溢的故事,我不会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