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哪一刻,会觉得“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
在哪一刻,会觉得“已经不是原来的自己”?

前几日和朋友聊天,他说他三十多岁,因为丢了一棵白菜,而被他爸训了一顿。我顿时想起我妈,在长久以来的大部分记忆里,她应该是一个经常懊恼,极端,情绪化极其严重,易燃易爆,定时炸弹,家庭的“敌人”,用各种方式尝试自尽过多次,并同时也是一个无比坚强的正面人物,开过五次刀,包揽家里大小琐事,修太阳能也会跟着四五米高的梯子爬上楼顶监工,和亲戚朋友的关系也很微妙,毫无边界感,闹翻几年,也还可以再和好,爱往往窒息,亲近的人是唯一瞄得准的靶子。
我跟朋友也讲述了我的经历,他表示所遭受的情感压抑如出一辙,总感觉自己长不大,尽管已经不小了,但还是被摆布,被当作孩子一般处理。于是我开始回忆我的蜕变时刻,小时候在家里是听话的一方,我姐的性格泼辣,总是与母亲发生冲突,在儿时的住宅空间里总是飞荡着凳子,椅子,碗筷和菜刀,此起彼伏的声波对抗,对生命威胁的吆喝,摔门,狂怒,暴躁,每一位家庭成员都像瞬间上了战场,扮演着各自的角色,我像不负责任的战地医生,怀着巨大的反感和恐惧不停地为双方抚平身心的裂口。对于擅自逃离的敌人,我还会满大街寻找,用乞求的语言将其劝回。我无法不管不顾,同时又羡慕与母亲对抗的姐姐,那种潇洒与自由,并不介意爱的伤害和并不需要所谓的温暖的枷锁。
后来长大了,慢慢了解母亲的性格缺陷也非她所能控制的,心理学上有个专业术语叫边缘型人格障碍,于是开始冷静地看待她的行为,并计划脱离“集体”,开始断脐。我开始不再敷衍地面对每一场冲突,不管因为谁,因为什么,我总是冲到前线,去理论,去爆破,去扛旗,去完成阵地的坚守,去宣誓自我的主权,暴风骤雨的击打甚至头破血流,母亲一次次的锋芒同时伴随着一次次的软弱,我试图解开心结,去对抗她内心的那一团麻,每一个她哭泣的深夜里总有我强硬的劝慰,我把爱揉成了一个石头疙瘩。二〇一二年,母亲最后一次自杀,喝了一杯用来刷厕所的硝酸,每个人所有的事务均停滞了,母亲转到省城医院,强酸已经开始腐蚀口腔,食道,肠胃,一摊摊黑水从母亲口中喷涌,她像一头被放血的野兽发出来自地狱的哀号。四肢被绑缚,推镇静剂,挂水,医生连夜会诊,多次下发病危通知书,我知道我失败了,语言的反击像是刽子手的刀,我也知道我成功了,母亲逐渐消瘪的身躯完全告别了原先的自我,她变得虚弱,任人摆布,开始懊悔,奢求生命能够再次垂涎她,放过她不计后果的行为,放过她的无理取闹。住院将近一年,从病毒科到肛肠科,扩张食道,切断胃口,上拉肠道缝合,她活下来了。而我,完成了一次心理上的弑母,在床榻边用棉棒蘸水擦拭母亲烧掉的嘴皮,扶她勉强撑起身体,处理她的每一次大小便,在每一次手术室外等待,为她兜住无法承受的剧痛所带来的眼泪,她变得异常平静,听话,像个婴儿。
那个时段,我慢慢脱离了与母亲的共生关系,开始接受她当下的和将来的所有命运,接受她的恢复,也接受她毫无预兆地死掉。我也许痛苦,也许难过,但不再有自我同时将要毁灭的无助感,我与母亲的纠缠即刻斩断,我才得以站起来,看到不属于我的我,也广泛接纳除了母亲以外的爱,明白个体的自由与精神的毫无束缚是生的脉搏,同时也更爱我的母亲,她的一路艰辛与抗争都是爱的变形,也许来自儿时的疏离,可怕的控制,无限的渴望,无从追究,但永远是我的母亲。
这种感受也许无法复制,但心理的羁绊大同小异,也许成长的代价也是如此,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是与他人的对话,与自己的对话。也有朋友交流,说自己三十多岁第一次谈恋爱了,原来的自己是那么自欺欺人,原来的生活是那么孤陋寡闻。新鲜,丰富,或者痛苦,仇怨,都在生活的夹缝里一点点挤占你,能量槽积满就选择去“杀”,“杀”掉迫害自己的他人,或者拖累自己的自己,突然感觉的蜕变,又是另一场远征的开始,去战,勇敢去战。
责任编辑:梅不谈 onewenti@wufazhuce.com
征稿信息见微博@ONE一个工作室 小红书@ONE一个编辑部 置顶内容。
回答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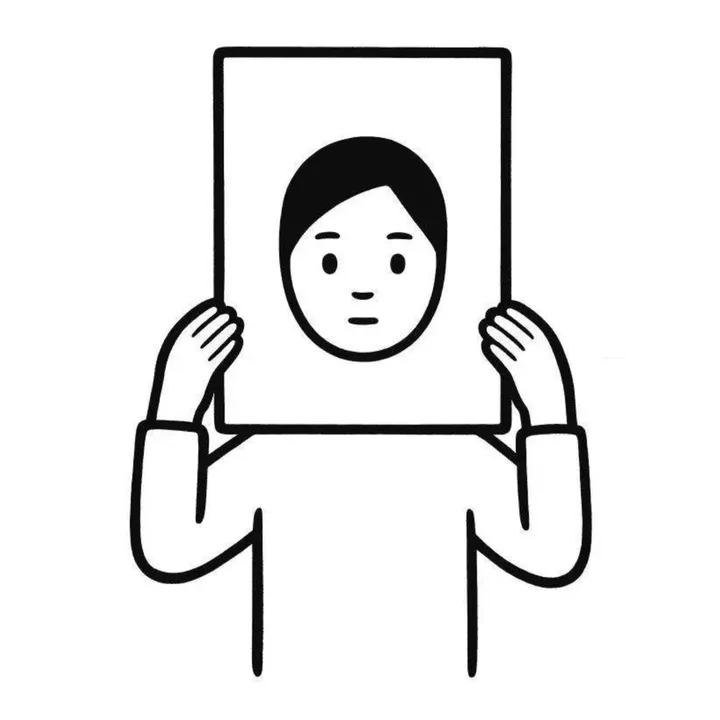
|
西小麦 @西小麦打字中
一个写字的。
|
相关推荐
| 问答 |
为什么人很难走出自己的舒适区?
|
| 问答 |
社会公德心&人际边界感,该如何权衡?
|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