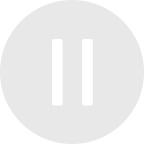陈鸿宇,创过业、打过工,刚认识他的时候,他的微博粉丝只有小几千人,从2015下半年到2016年初,他的微博粉丝就迅速涨到了3.9万,每一条微博下面都有女粉丝喊着“陈叔”“老公”。
作为独立音乐人,他红的速度比自己想象中要快很多。2016年2月,陈鸿宇的社群品牌“众乐纪”获得了十三月唱片200万元的天使投资。
突然就小红了。
尽管陈鸿宇离走上主流还有很长距离,不到4万的微博粉丝也不算什么。但其实他在各音乐播放平台和一些圈子内已经形成了一定的影响力。豆瓣上《早春的树》播放次数已突破10万,带许多人进坑的《理想三旬》在2015年12月底QQ音乐的播放次数也突破200万,网易云音乐上陈鸿宇首张专辑《浓烟下的诗歌电台》8首歌曲评论数全部实现了999+,这种整张专辑都受乐迷欢迎的情况还比较少见。
对于音乐内容,十三月创始人卢中强说:“我特喜欢陈鸿宇的唱,不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唱歌传递出的感觉,我觉得他比较像民谣那种偏行吟的方式,从行吟的角度来说他挺极致的。而且他对唱歌的认知特别好,他和乐手鹏鹏,演出的过程都是设计过的,虽然这个设计跟职业者相比还差一点,但是他们在前奏、间奏、整个编曲的主动机上的设计,是难能可贵的。”
“媒体会给你一些标签,比如民谣诗人,下一个朴树,你自己如何看待外界对你的形容呢?时间久了之后会反感这些比较刻板化的定义吗?”
“每一个人都会被冠有一个标签,我指的概念是到了一个更多人知道的层面上,市场会给比较难分类或者还没有分类的东西一个名字、符号或者概念,所以我倒无所谓反不反感,可能大家对我的理解就是这样,自己具体做成什么样不受标签影响就可以了。至于说第二个什么,或者诗人什么,你自己非往这上面靠,觉得符合大家的预期,我觉得才是违背内心的,才会让自己的路跑偏。”
“如果让你自己来决定用一个词形容自己的话,你更愿意使用什么呢?”
“独立音乐人。独立音乐人的感觉在我看来,就是一种独立精神的存在,这种独立精神有你自己的思考和判断,在这个基础上还有独立的审美,再去做什么事,可能会爆发出你自己独特的美学体验或者是独特的价值观。如果说对自我认可的一个语言化的表达,我觉得就是这个,没有真正的独立,独立其实是相对的,是你尽可能地不去随波逐流、不去跟着大众的言论、不随网络的风向改变自己。”
陈鸿宇生于1989年,高中就组乐队玩音乐,写了不少歌曲,但都没有发表。他的职业经历丰富:餐饮、打工送外卖、电台做策划,从内蒙古大学新闻专业毕业后来北京的他和其他北漂一样,对未来充满希望又时常感到迷茫。
于是在2015年1月,陈鸿宇凭兴趣创建了众乐纪。
陈鸿宇从来不忌讳谈商业,他认为音乐人只要在创作音乐的时候不商业,当作品完成后,去推广、传播是再正常不过的一件事。陈鸿宇认为,只要做得足够好,稍微有点商业头脑总不会缺钱花。
但作为管理者,刚上任的陈鸿宇也有烦恼。
虽然陈鸿宇的首张个人专辑众筹以1000%的成绩超额完成,但在乐童众筹的页面下,我们看到有2页的评论反馈了自己的不满。
“说好的手写信呢?就两张空白纸?”“延期那么久就发出来几张彩印纸,几个月的时间连几千个自己名字都写不完?”“CD里面没有文件?”“专辑到了,压坏了好伤心……”
造成上面结果的原因可能有许多,快递公司、团队、时间都是可能造成问题的因素。但对于这些早期的支持者来说,虽然是客观原因,如果一些细节没能做好,会影响到支持者的心情,进而影响对陈鸿宇以及众乐纪的信心。在如何管理团队方面,陈鸿宇要从原本的“单枪匹马”变成团队的领导者,他仍需要学习和摸索如何提升覆盖到乐迷的每一个细节的体验。
“谈谈第三张个人专辑《与荒野》吧,这张专辑的灵感最初来自《荒野生存》,还记得当初看这部电影时的感受吗?”
“仿佛我就是他,在那些荒郊野外、在麦田里去跟那些农民、路上的男孩女孩去聊天,然后走到阿拉斯加的荒野里,就自己一个人,大概就是这种感觉,特别地感同身受。我觉得每个人都是心里有什么才会被感动,所以就去阅读、旅游、交朋友,所有的这些事打开了自己更多的体验,如果你不打开自己的话,你可能永远都不知道世界上还有这么一部电影还有这么一个人,他会和你内心深处已经有的一些信息和神经产生联络,让你爆发出很兴奋、很向往的那种情感。”
“当时是在什么情境下看的这部电影?”
“还在内蒙古上大学时看的,朋友给我推荐的。那个时候可能是因为年纪小,还没有足够的能力走到各处,充满了对新鲜事物的向往,看的东西和接收到信息,会印象深刻,甚至转化成自己的一个特别认可的奋斗目标或者说向往的理由。所以看完那部电影之后,灵感就开始发酵,我什么时候也要感受荒野,感受这种自己在大的场景中一种孤独又不孤独的存在。其实我从小是在荒野中长大的,小时候在家里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上,就很多次转着圈地看星星,或者跑到草地里等等,这些是扎根在心里的。”
“第二张专辑比较怀旧,这一张专辑呢?”
“《与荒野》纯哲学探讨的感觉强一些,里面很多歌的某些字句单拎出来适合一些场景,但放在歌里的话,没有前后文的关系,也许显得没有那么易懂。”
“在传唱度上,和前两张相比有一些差别,你会感觉有一点失望吗?”
“不会,我没想把传唱度当作标准,所以不会失望。我对做音乐这件事,不太会感到失望,因为我知道我做的东西是我自己想做的,我现在能比较好地控制我自己做音乐的方向和态度,如果我控制不了这个我可能会比较失望。”
“你对年龄的变化不敏感?”
“不太敏感。我觉得对年龄变化敏感可能是因为没事干才会敏感,有事干的人往往都不太会。我理解的可能是随着阅历或者是年龄的变化会不会在精神上有一些新的东西。很多人岁数大了,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可能就是他做的那些事能带给他活力,能让他保持一种对世界的充满好奇的态度,这种情况下这个人就不会对年龄敏感。”
“对自己成名这件事会有压力吗?”
“没有啊,成名会有什么压力?用玩笑话来说,当成名变成一种压力的时候,那得是多大的名啊。对于成名这事我的态度比较自然。说实话你也就是在网上唱唱歌,你知道你粉丝涨了点,有很多人喜欢自己的歌,那还能有什么呢?”
“可能很多人关注你,对你个人的经历好奇,或者更关注你了。”
“现在这种关注还没达到咱们说的那种,有人直接进入到你的物理世界里,你的私人生活里,那倒还没有,而且自己日常的生活也还能保证,没有说到哪儿会很麻烦出行不方便。现在正好处在比较中间的状态,还好。”
“是否可以理解为你对自己的路是有一个预期和目标的,所以在这个过程里,并没有感受到那种因为备受关注而突如其来的压力?”
“对,我自己认识得还算是清晰吧,心态比较正常,没有对这些抱有过大的期望。我以前在微博里发了一句话:你下海游泳之前,你进入一个环境之前,最好分得清哪儿是哪儿,环境是环境,你是你。环境就像一个浪潮,在进入浪潮之前没有理想或进入之后没有反思便会被卷走,再也记不起曾经因为爱、因为年轻而诞生的种种想象,成名不必趁早,分得清哪里是浪哪里是我的时候就刚刚好。”
“2015年你做了众乐纪,一直到今天,有没有一个外部事物(或一段时间)给你的影响,超过了你的承受能力?就感觉是一下子被拉着走那种。”
“没有,我没有过多的那种期望,所以并不会出现这种事情。我为什么会被拖着走呢?就像我刚才说的,没有完全真正地独立一样,人是在社会环境下、父母教育下、国家民族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不被环境影响和改变只是相对的,我只能保证自己相对不会出现这种情况,还是保有自我思辨性和独立性。
我做音乐之前开快餐店,骑着电动车送餐什么的,现在再让我回到那个生活我也能回得去,只是一个阶段有一个阶段的境遇。但往往到一个境遇和情况里,有钱了有名了,生活舒服了回不去以前了,这种可能应该算是你说的那种被改变。我还算能认真地保持着对生活和对人的不卑不亢。‘不卑不亢’四个字,要做到很难啊。”
节选自《春歌丛台上:对话33位音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