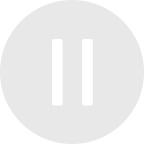“许仁,你明天跟一下音乐节的采访。有一个独立歌手快出专辑了,我们跟她约了专访。”主编安排了我这周的选题。“叫什么来着?陆恩恩?好像几年前在北京唱过一阵子。”
“10年在北京,14年去了香港,后来在台湾发展。”我敲着键盘答道。
“看你平时挺不走心的,对独立音乐人这块还挺了解的。”精准的回答让主编有些吃惊。
“陆恩恩,她是我学姐。”敲打着键盘的手停了一下,一些往事在文字间流淌。
和别的学姐不一样,陆恩恩只当了我一年的学姐,我入学时,她大三,我念中文系,她念艺术系。陆恩恩的专业课念得如何我不知道,但她歌唱得很好是全校都知道的事情。
她那时在成都玩音乐的年轻人里刚刚露出头角,会有酒吧请她驻唱,也跟一些学生组过乐队,她唱着别人的歌。
我第一次见陆恩恩是在学校的迎新晚会上,她的节目在后面,临近出场时礼堂忽然涌进很多人,他们不是新生,挤满后排的通道,好似演唱会上狂热的歌迷。
我回头望向后排那些学长,原来大学是这样子的,可以明目张胆地向喜欢的女生示好,即使校长和主任还坐在第一排。也只是那回望时的分神,便错过了陆恩恩的登场,当被欢呼声惊的再回过头时,那个穿着白T恤牛仔裤的姑娘已经站在了台上。
她闭着眼睛,双手握着立麦,“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她唱出了第一句偌大的礼堂便瞬间安静了下来,也或许是这初识的浅浅嗓音,让我见她时都不太敢眨眼,呼吸也变得很轻,生怕自己会发出任何声响打扰了那台上低唱的女子。
台上的她并不耀眼,也并不像什么明星,只是声音柔和又抓人,仿佛一层毛茸茸的光吸附在她身上。但在那四分钟里却让我生平第一次怨恨自己的平庸。
“她是谁?”后排疯狂的安可声中,我对旁边的同学耳语。
“恩恩!陆恩恩!”她大声地回我。
我按着同学的口型又复述了一遍,“陆恩恩?”好像念那两个字时需要点两下头。
“对!平时在学校很难见到她的,她唱得真好是吧?”
“嗯,嗯。”我又点了两下头。
我从小并不追星,真心喜欢的作家倒是有几个。见到陆恩恩那晚,我有点异样,打开流量,用手机网页搜索着手嶌葵,搜索《the rose》,访问了学校的贴吧和人人网。但陆恩恩不是明星,我找不到更多关于她的信息,我想我不是要追星,只是对那个闭着眼安静唱歌的姑娘着了迷。
寝室很快熄了灯,我打着台灯趴在床上看季羡林先生的书,“而今我已垂垂老矣。世界上还能想到她的人恐怕不会太多。等到我不能想到她的时候,世界上能想到她的人,恐怕就没有了。”
躺下后我有点自私地想,如果她不被那么多人喜欢该多好,那样我会觉得自己离她近一点。
和她们说的一样,陆恩恩很少出现在学校,我也不知道她平日都去哪里练歌驻唱。我在那所大学里默默念着书,也默默念着她。
社团招新时,中文系的同学大部分去了戏剧社,诗歌社,辩论赛,只有我和传媒系挤着去了广播站。报名的人很多,他们念起稿子来都字正腔圆悦耳动听,我偷偷看了学长手里的报名表,文娱栏目的框框里挤满了人名,只有体育新闻那一栏空空的。我报了名,成了广播站体育新闻栏目唯一招到的女生,只要能进来就好,和音乐有点关系的地方,说不定是能遇到陆恩恩的。
大二时,陆恩恩要毕业了,在广播站的我也终于竞选上了导播,拥有的最高特权是每周值班时,可以在节目的间隙放自己喜欢的歌。那时我iPod里存的歌大多跟那个即将毕业的学姐有关。
渐渐地全站的人都知道,许仁在值班时一定会放《the rose》,当然,如果还有同学真的在听广播也会发现这件事吧,以及那些无法诉说的情愫。好多个清晨,我独自在广播站放歌时,都会觉得自己是《肖申克的救赎》中放着莫扎特《西风颂》的安迪,沉醉在那种偷来的自在中。
后来的一件事证明我来广播站是对的,因为文娱部的责编邀请到了陆恩恩来做一期节目,我还未刻意讨好,当天值班的导播就主动跟我换了班,或许他们都知道“许仁是为陆恩恩而来的”。
隔着播音室的玻璃,我低头摆弄着播控台上的按键,假装不经意地抬头对玻璃对面的她微笑,互相给了OK的手势后,那期节目开始了。原来她说话时的声音也这么好听,精致的短发让人觉得清爽又潇洒。按照节目安排好的流程,她讲了她是如何喜欢上音乐,讲了她追梦的故事,讲了这个她并不熟悉的学校,还讲了一些鼓励后生的话。
节目结束后,她笑着跟大家道别,出来时,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说:“辛苦了。”
那是陆恩恩跟我讲过的第一句话,我抬着头对她笑,傻傻地望着大家把她送出播音室,心里突然冒出一句,“许仁!你在傻笑什么,去追呀。”
我忽地站起身,随着人群追了出去,她并未走远,我跑了几步追上她:“学姐!”
她转身依旧是那样好看地笑着。
“能约你聊天么?哦,不……聊聊音乐什么的……”我语无伦次的搭讪。
“嗯。”她点点头。
“可是,可是我还要导后面的节目,你能等我下么……”让她等,我觉得自己是奢求了。
“几点结束?”她问
“还要一个小时。”我低头看着手腕上的表。
“我也要去系里办些事,那七点半在操场见吧。”她没有拒绝,她没有拒绝。
“好!七点半!操场!”我开心得有些不知所措,重复着她的话,转身又急匆匆地奔回导播室。
三月末的成都还有些许凉意,可七点半的晚风又柔柔的让人心醉。我站在那望着她走来,原来心心念念的一个人向你走来是这样的,在心里为她亮着一盏夜灯,眸子里便会透出点点光。
“刚下节目,是不是该约你去吃饭?”她好细心。
“还好,不饿,喜欢在操场走走。”我又傻笑了,还说了傻话:“我是许仁,学姐好。”
她点点头,我们便围着操场一圈一圈的走着:“是在迎新晚会上见到学姐的,唱得真好。”
一定很多人夸她唱得好,她并没有说谢谢这类的话,只是说:“如果我不唱,很难拿到学分毕业。”
是呀,她总不在学校,原来陆恩恩这么优秀也是要修学分的。
“学姐,你总让我想起小红莓乐队里的多洛丝。”
“因为短发么?我一点也不酷的。”她笑着问。
“感觉很像,在一个都是男生乐队中,有一个自带光环的女主唱。”我是在刻意恭维她么,可我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小红莓呀,听多了有种无病呻吟的感觉。”她轻声哼了几句《dying in the sun》,“你觉得么?”她问我。
“你这样哼唱都比多洛丝好听很多。”我默默答着,没敢说出口。只说了,“那学姐喜欢谁的歌呢?”
“我自己的。”她不假思索地答出,又摊开手着看我,“虽然还没有。”
“可以参加选秀呀。”成都出过那么多的选秀歌手,可是没有陆恩恩。
她摇了摇头:“我还是喜欢慢慢的。一个人唱歌和给一群人唱歌是不一样的。”
“那学姐以后一定会红的,你的名字一听就是会红的那种。”我点了两下头。
“第一次有人这样说,你真这么想么?”她觉得有趣。
“嗯,嗯!”我又点了两下头。“你看,像许仁这样很普通的名字,是不太容易被人知道的。”就好像许仁一入学就知道陆恩恩,但陆恩恩今晚才知道这学校里有个许仁。
“那也说不定。”她低语着。
“学姐,毕业你要去哪里唱?可以去听你的LIVE吗?”我也低下头,陆恩恩快要毕业了。
“去北京。”
“北京?”这让我猝不及防,那遥远的城市。
“去给一些歌手当和音,那边做音乐的人会更多一些。”她答道。
“和音……”我想到演唱会时,在光打不到的角落里,有一群人在哼唱着。“甘愿么?你唱得这么好。”我一直觉得她会是一个乐队的主唱。
“甘愿,做自己喜欢的事,就甘愿。”她答得坚定。
“那想看你的LIVE有些难了。”
“不着急。还好自己是女孩子,进可攻退可守,趁着年轻先去尝试一下吧。”她好似在安慰。
“对呀,我们都是女孩子……”我小声嘟囔着。
“以后如果去北京玩可以找我。”她说道。
“嗯,嗯”,我点了两下头,“有点远唉,学姐留电话给我好么?我毕业了就去看你。”
她没有拒绝,留了电话给我,那是一次不太长的谈话,我们只围着操场走了四圈,她便匆匆离开了,那天我手机的通讯录里多了一个重要的人,叫陆恩恩。
她们那届学生毕业后,还记得陆恩恩的人便不再多,一个迟迟没有作品的驻唱歌手很快便被人忘记。
她去了北京,也变更了电话,但她没有留我的联系方式,我便收不到号码更新的短信。那串留在手机里的数字我始终不敢删除,偶尔打过去会听到一句,“你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学姐,你在北京还好么?我这边听不到你的歌了。
采访陆恩恩,对于我来说已经不用再准备什么资料了,网上所有能查到的关于她的信息,都早已在我脑海中游荡多年。她是哪里人,毕业于哪里,什么星座,给谁唱过和音,出过几首单曲,去过哪些地方,这些我都知道,即使我们只有一面之缘又七年未曾相见。
陆恩恩在采访间再见到我时,愣了一下,或许是还有些许印象吧,我和她握了手,开始了采访。
“恩恩,你终于回北京了。”我先开了口,第一次觉得娱记的身份真好,对话时可以亲切的叫她的名字,面对着她我依旧不太敢眨眼,呼吸也变得很轻。
这个开场白让她意外,但很快又礼貌性地笑了起来,“一开始是很排斥回来的,但开始的地方,总要回来看看。”
“像是给自己交出一份答卷么?”我小心翼翼地询问。
“算是吧,效果好像还不错,对么?”她有些不好意思,音乐节上已经有她的歌迷从各地跑来北京捧场。
她在北京那会是不太顺利的,无人知晓也无人问津,除了和音工作外,她在酒吧唱爵士,在乐团当场记买烟买咖啡,也在租来的屋子里日日夜夜地写歌,练习吉他,把那些不太成熟的demo上传到一个独立歌手平台上,并在上面开了博客,记录着她在北京的点点滴滴。
陆恩恩的这些点点滴滴我都知道,那时我电脑浏览器的主页便是她的博客,她离开北京后那里便荒芜了,我再了解她就只能翻墙去Facebook。
采访过程中,我说出了她在北京时的几个细节,比如她在哪里买到了第一把吉他,又比如她喜欢跟朋友在夜里轮滑刷二环。这些都让她很吃惊,陆恩恩并不是什么大明星,她现在连经纪人和助理都没有,这些往事可能连她自己都不太记得了,她的歌迷也多是纯粹喜欢她最新几首作品。
采访很快就结束了,需要问的问题我自己都能替她答出,一切只不过是走个过程。
我把本子塞进双肩包,再一次向她提了那个请求,“能约你聊天么?”
“嗯?”她也收拾好东西刚准备离开,“不刚刚聊过?”她笑着问。
“这次不聊音乐。”我起身背起包回道。
“那你送我回酒店吧,穿过这条街区。就在那。”她伸手指了指窗外CBD的方向。
我们下了楼,两人并肩走在来往的人群中。“以前的国贸没有这么繁华,我刚来时这只有一家星巴克,北京的变化太快了。”她讲给我听。
“学姐,你在台湾还好么?”我没再叫她的名字。
她又愣了一下,笑着碰了下我的胳膊,“我刚在那见到你时就觉得有些眼熟。”她眯着眼假装用力地在思考,短发精致又好看,或许总爱笑眼角有一些浅浅的纹,“许……仁!对么?”
“恩恩,”我点头,“我就说我的名字太普通,不太能被记住。”
“那会还答应你来北京时听我LIVE。”她想起了一些。“你多会来的这边?”
“后来在成都又读了研,去年一毕业就来了。”我回道,“可惜我来时,学姐已经去了台湾。”
“这样呀,怪不得你那么了解我。”她喝了口手中的咖啡。
陆恩恩我了解你,因为我不是你的歌迷。
其实她在北京时,我是来过的,只是北京太大了,我去了很多她博客里提到的地方,但都没有遇到她。考研成绩出来后的那天下午我就定了来北京的机票,心里想着如果在那座城市能遇见陆恩恩,就用尽全力告诉她,“可不可以在我读完研来北京之前,先不要离开。”不管我多么不喜欢北京,可是北京有你,没有你的成都再风情万种,也比不过有你的北京。
但那时并没有遇见陆恩恩。我读完研来到这里时,她已经南下,我去了一家杂志社的娱乐口做编辑,同学总笑我是为了见明星,因为她们都去当了老师,公务员或者去了大型出版集团。
其实做什么都没关系,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就甘愿,她说过的。“总觉得学姐还会回到北京。”我对她说。
“不太喜欢这里,但市场需要,时不时还是要回这边唱一唱。独立音乐人很穷的,台湾那边氛围相对好一些。”她又喝了口咖啡。
我看过她在台湾的一些小型LIVE SHOW的视频和照片,轻松又自信,或许是吹到了太平洋的暖风,在那里的陆恩恩自在如风。但刚刚接受采访时,我们面对面坐着,我看到了她因为紧张而微微发抖的手。陆恩恩是单纯地喜欢唱歌,她享受做那样的自己。
“我也不太喜欢北京这里,太大,人又多。如果没有豪车,没有紫色的头发,没有寒风里的春装,没有奇怪的口音,没有出众的外貌,没有过万的装备,没有钱,在这个城市里很难刷出存在感。”我拉了拉自己的双肩包。
“可你还是来了,这里机会还是要多一些。”她看向我。
我笑了笑,是因为学姐呀,但我不敢告诉她,小城市给不了太多物质,可总能让别人的目光在你身上停留片刻。就像陆恩恩还记得许仁。
去酒店的那条街很短,不一会便走到了。“你要上去坐坐么?我明天就飞台北了。”看我没有回答,她开玩笑道,“当然,再聊的内容不能写在稿件里,可以么?”
我笑着点点头:“嗯,学姐。”
进了房间她慵懒地靠在床上,我把背包放在地上,重新扎了扎马尾,坐在了椅子上。
“你不要叫我学姐了,还是叫我恩恩吧。”她看上去有些疲惫,那杯咖啡没有抵消掉她这几日奔波的倦意。
“嗯,嗯。”我轻轻点了两下头。
“其实觉得自己也不算是娱乐圈里的人,只是因为和声时认识了大哥,很感谢他带我出来。我这样的歌手是不是很难写出精彩的专访。”她问道。
“嗯,你又没有什么绯闻可以让娱记爆料,说白了都是互惠互利的事情。”这个行业每天发生的事情其实都不新鲜。
“我独身一人,除了唱歌实在没什么好写的,难为你了。”
“为什么要独身呢?在台北不会孤独么?”我问道。
“男人会需要伴侣和婚姻,女人并不总需要。”她答道。
“对呀,女人可攻可守。”我学着她当年说话的样子。
她闭上眼笑起来:“你还记得……可为什么向前走是被祝福的,结婚也是被祝福的,我那时活成了自己却不被祝福。”
我看着眼前这个只比自己大两岁的女人,这些年,学校保护了我不被现实压迫,但陆恩恩这几年的北上南下并不轻松。“恩恩,无论怎样的你,我都祝福。”恩恩,我那时想过要来北京陪你的,只是你先放弃了这里。
“你呢?在这里过得还好么?”
“还好,一人吃饱全家不饿,只是……”我笑了笑没说。
她也没再说话,等着我继续说下去。
“很羡慕台湾呀,这里的法律还不允许我结婚,我没办法退一步,去找个异性结婚生子。”
她好似明白了一些,过去的几个月平权在那里闹得沸沸扬扬,“只要是爱着的,终究会得到祝福的。其实你也可以去台湾的。”
我不是陆恩恩,我便做不到为了理想仗剑走天涯,“我已经为了一个人来了北京,这里还有些东西需要我守着。”
她自然是没有听出我为谁而来,要去守护什么,“也是,每个人都是不同的。”
“恩恩,你以后还会来北京吗?”我问道。
她点了点头:“专辑出了以后可能会常来跑宣传。”
“以后可以听你唱着自己的歌了,好希望你红,又不希望你红……但你还能回来便好。”有时希望陆恩恩就这样该多好,我不用跟那么多粉丝来分享她,这让我觉得离她很近很近。
我看了看窗外,天开始阴得厉害,像是要来一场北方的雨,我又看了看她,疲倦让她像是要睡去了。“恩恩,你累了就休息吧,我能在这里把稿子写完吗?看样子要下雨了。”
“好……”她说完没多久,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我轻轻地敲着键盘,生怕会吵醒她,心里为她哼唱着,“some say love it is a river……”
“她说,你必须在声音里放入你自己的勇气,你的力度和你的自身特质。”屏幕上落下这样一行字,作为那篇专访稿的开头。
雨下了半个小时便停了,我合上本子,起身看了看她,好喜欢陆恩恩,第一次见她时也是闭着眼在唱歌,我把自己的外套脱下给她盖上,恩恩,这好像是我唯一能为你做的事情了。
“你回来好不好,让我有一个可以一直留在北京的理由。”我轻声对着那熟睡的人低语着。慢一点,久一点都没关系,我并不介意时间,只是不要在来遇我的半途突然走掉。
我关上房门离开了,那是我最后一次见陆恩恩,依旧没有她的联系方式,只留了工作邮箱。朋友总说我:“许仁你来北京像是在寻找着什么,四处兜兜转转的,就像很久以前来过一样。”
没有人知道,我来这里是为了寻找另一个人在北京留下的痕迹,并替她小心翼翼地保管好。这里人来人往,北京是记不住那么多人的,但我记得你。
三个月后,杂志社收到一个台北寄来的包裹,里面是一件叠好的外套,外套里放着陆恩恩的首张专辑。CD做得很精致,歌词单好似一个日记本,里面记录了她这些年做音乐的点点滴滴,其中一页上印了一张台北飞往北京的登机牌,下面又印了一行手写的小字。
“给自己一个留下的理由。”
文/即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