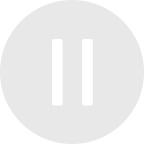《郭源潮》录音室版发布已经快一个月了,音乐播放器的数据显示我最近像中了毒一样地loop这首歌。和四年前那张《安和桥北》一样,我还是喜欢正式版多过小样。录音室版本当然比demo更显一个音乐人的素质。是的,宋冬野如今,已然配得上独立音乐人的称号。
说回四年前的《安和桥北》的成功,制作人韦伟(旅行团键盘手,同期发行的阿肆的《预谋邂逅》也是他制作的)功不可没。在专辑发行前,大多歌的demo(有的就是粗糙的演出录音)已经听过了,可在听到录音室版专辑的时候,我还是吓了一大跳。这些歌被打磨得精细、丰富,和之前听到的版本简直云泥之别。当然还是会有很多人会说,“我们还是喜欢以前的版本/还是demo好听/还我简单的宋冬野”诸如此类的话,我想说,你们开心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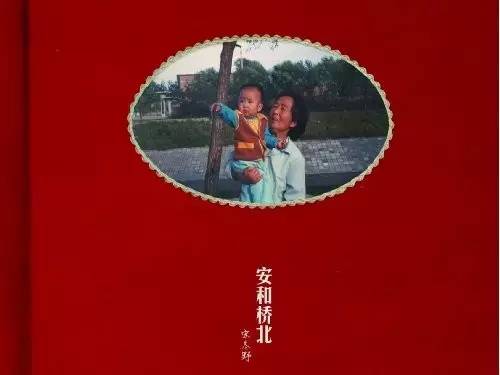
《安和桥北》发行的那阵时,我几乎每天都在听。那时正经历很痛苦的事情,只有这张专辑似乎能慰藉我。所以到了大一,百城巡演的时候,我去了南京站。那时门票才80一张,青果咖啡馆早早被宋冬野的歌迷占据包围,入场前大排长龙,排在我前面的小伙子给我看手机里他和艾未未的合影。
因为去得早,站在了第一排,青果的工作人员为前几排的观众准备了小马扎,坐在我旁边的是南京的两位记者,入场前,他们问到宋冬野这一拨人属于什么音乐风格,有人答流行民谣、校园民谣,有个小姑娘说是新民谣。
整场演出下来,胖老师出了很多汗,没说什么废话,唱《董小姐》前还故意弹成了好像是孙燕姿还是阿肆的某首歌,他似乎不好意思面对这首自己写成的歌,尽管这首金曲某种程度上改变了他的人生。演出结束后,几乎所有人都在排队等着签名合影。对了,那天李志也来了,和黄燎原一起。

等到百城巡演到武汉站的时候,我似乎对这个胖子和他的音乐已经兴趣不大了。时隔一年,宋冬野走进剧场,票价水涨船高,他更红了,红到了三线城市的商场和发廊,我也和那些自命清高的人一样,与之划清界限。身边开始听他歌的人越来越多,我只会时不时偶尔偷偷听一下当时感动许多人的那张《安和桥北》。
即使听了很多八卦传闻,在我心中,宋冬野的为人处事依然算那股浪潮里红起来的人当中比较靠谱的。很喜欢他的谦卑。不同于某某、某某某、某某某乐队的是,宋冬野,无论是进去前,还是出来后,他都带有一种“自省”,不急于占据市场,粗制滥造出一堆垃圾,当然这也导致了演出时的“炒冷饭”,但这也没办法,人总得生活。

相比之下,你是更愿意听一些速食速朽的垃圾还是听宋冬野的“摇滚版”董小姐呢。他是有作品的歌手,而且好作品不止一首,《安和桥北》如果不是错过金曲奖报名时间,在小巨蛋得年度专辑我都会相信,翻当年台湾音乐杂志,你就知道这绝不是在信口胡驺。
而鲍勃迪伦得诺奖和宋冬野吸食大麻这两件事根本八杆子打不着。拜托,鲍勃迪伦得奖和他是不是民谣歌手本身关系就不大,他早就摆脱了民谣的标签,拿起电吉他的那一刻就被当年的歌迷骂为犹大,事实上他早就摆脱掉了一切标签,也不需要任何文学奖项来褒奖。
也没什么可大惊小怪,好多年前他就是风传的热门人选,我大二时英语考试的ppt里就说他可能会得诺奖,当时英语老师那一脸“what the fuck”的表情我记得清清楚楚。总之,一切都是板上钉钉,胖子付出了相应的代价,甚至这代价,在我看来,过于沉重。

不知从何时起,这个世界变得越来越保守主义。人人自危,不敢说错话站错队,不敢表明立场,要顾及政治正确,要顾忌舆论压力,要三观正,明星艺人得做道德模范,一旦被抓住把柄,永世不得翻身,哪怕你认错改过,人民也不给你自新的机会。
记得几年前《小时代2》电影里面有句台词:每个人都应该要有一次被原谅的权利,如今看来,这个权利早就没有了。每个人都有犯错的时候,会得到相应的惩罚和代价,但在当代生活中,有些代价看起来太不合理。
不能演出,宋冬野也没闲着,他自己买机票去草莓看朋友们演出,去杭州拜访他的偶像万晓利,最近在他的instagram上,万总和酒球会的王老板出镜率非常高。偶像万晓利几年前离开北方,隐居在杭州,戒了烟酒,宋冬野的到来让他近年来首次破例,大家一直喝到凌晨三点。

“一朝悲歌成金曲”,董小姐的走红给宋冬野带来了全新的生活,而他当初走上音乐这条路的启蒙则是万晓利2006年发行的那张《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他说第一首陀螺就把他听哭了。
在《郭源潮》中,宋冬野还用“事发之木和东窗之麻”来致敬万晓利的“在东窗事发的麻木里转”,事实上他早就这么干过,早在《梦遗少年》中,他就用“世上唯一懂鸟语的人 死在了2006”来调侃偶像。很多人说他音乐格局小,可《梦遗少年》的歌词,真的是一个小格局的人写得出来的吗?

说回郭源潮,这次真的是细节丰富,气象万千,万晓利评价说“木头到电”。宋冬野所费的心力,其实是很容易觉察到的。苦学编曲,在录音棚打地铺的他也终于敢自称音乐人了。不再借助于故事来写歌词的他,在脑海里虚构了一位老者和青年的对话,得益于早年图书出版发行的经历,宋冬野的文字功力向来了得。
“悲歌三首买一切”“石灰街车站的海鸥”“太平湖底陈年水墨”“哥本哈根的童年传说”,还是那么擅长用典,让人会心一笑,“层楼终究误少年,自由早晚乱余生,你我山前没相见,山后别相逢”还是金句频生;再加上气势磅礴的编曲,这样的宋冬野,如何让人不喜欢。

得知宋冬野被拘留的那天,我在看鲁豫采访李安的视频,李安说他父亲对他说到:“入山不必太深,下笔不必太浓。”胖老师也无须向偶像万晓利看齐,隐居不是他的性格,他知道如何在红尘中打滚又如何保持出离的状态,这次大麻事件之后,他会更加明白这个道理,他才不是自己口中的傻逼,他聪明着呢。
据说他现在的状态很好,云游访友,和父亲的关系也很好,认真地在做音乐,学习如何做一名合格音乐人。对一个向来有自省精神的人,人生的磨难也是磨练。指不定哪天他就会写出让自己真正满意的作品,这一切没有想象的那么糟,不是吗。
文/王囡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