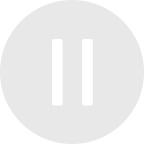我喜欢南京。
十里秦淮,沿着通济门到水西门,穿城而过。在过去,这里商贾云集,一片繁华。
当然,这都是历史课本里的故事,对于我来说,接触一座城的最初,还得是吃。
刚来南京的时候,倒没什么好印象。那时候刚开学,天气又热又闷,拖着行李箱从火车站一直到胜太路,汗就没断过,大气喘不上来,心跳快,非常狼狈。学校伙食也不好,菜又辣又咸,米饭又硬又干,简直崩溃。
不过待上一段时间,味蕾就慢慢适应了这里的味道。甚至,我现在开始喜欢南京的米饭了,虽然硬,但很适合炒饭,米粒全是散的,色香味均匀。在北方,炒个饭,米都粘成一坨,一点食欲都没有。
南京的饮食就像个娇羞的姑娘,久一点,你才能发现它的喜人之处。表面上,南京确实没啥好吃的,各家各户楼底下,不是黄焖鸡,就是皮肚面。要想找出南京的美食,你可得花点心思。不用去看电视里的美食节目,也不用去大众点评看排行榜,那都是给外地人看的,没用。你得住在这里,听朋友说,或自己去找。芳婆的糕团、金陵的大肉包、毛家的水饺、丁家桥的锅贴……船帮菜、会馆菜、小吃,一应俱全,惊喜有的是。
吃了可口的饭菜,才有心情在街上闲逛,就连风景也因嘴里的余香顺眼了许多。
不过梧桐树的好可和这美食的余香无关,那是我第一眼就爱上了的。在南京,大大小小的路两旁都种着硕大的法国梧桐,萧萧瑟瑟,漂亮得紧。这些树,小的也要几十岁,大的多达上百岁,庞大的树冠将道路遮盖,热天可以遮凉,雨天可以遮雨。而八百多万人就在这温柔的阴凉与遮蔽下在城市中穿梭,惬意地生活。
但饮食也好,环境也好,一个城市能留住心的,还得是人。
2012年,我从北京回到南京,做野外合作社。鼓手谢斯彦,贝斯手王云龙,都是原班人马,然后从豆瓣上找到了吉他手刘遥。我们在中央路上均价最贵的小区租了间地下室,700一个月,开始排练,这一待就是两年,第一张专辑《野外合作社》就是在这里做出来的。
结果专辑做好了,却赶上南京音乐环境最差的时候。熟悉的组织和场地一一倒闭,只有古堡在傅厚岗挣扎着开了个二店。那个舞台非常小,小到我这么一个胖子站都站不下,以至于有一次演出,是吉他手站在中间,我站在边上唱完的。后来我们又开始在老斑马给名气大一些的乐队暖场,熬到2014年,我们才在老斑马办了野合的第一次专场。
那次专场来了很多人,B哥也来了,和公爵坐在黑暗的小角落里,一声不响。要知道,以前都是在台上见到活着的李志,这次在台下见到了。我紧张得要命,虽然整场下来非常亢奋,但还是提心吊胆的。这感觉就像,草原上总有一双猎食的眼睛在注视着你,你就找不到在哪儿。
去年欧拉开业,那便成了我们新的驻地。季老师、秋秋、公爵、董事长、巫婆,一年下来,得到他们不少的帮衬。我们在董事长的排练房排练,免费,如果有本事,还可以顺到董事长的龙井泡茶喝。偶尔,董事长也会莅临现场,亲自指导排练。当然,如果他真的来指导了,你也会崩溃的——因为整场排练,他会比你还投入。
去年底,公爵提议我们把这首《南京之声》在欧拉录个同期,也是免费的,从头到尾将近6小时,费时费力的一件工作,我也只请季老师他们吃了一份20几块钱的藤椒鸡煲。
这一路走过来,你会发现,在南京这个摇滚圈子里,有太多的人都在帮你,只要你喜爱摇滚乐,愿意做乐队,纯粹地帮助,纯粹地热爱音乐。不信,你也在南京做做乐队试试,即使你不去找他们,有一天他们也会找上门来。
久而久之,你会习惯一种常态。你周围的人,食物,地标等等。你有一个非常安全可控的范围,你知道遇到什么事情会想到谁,你的郁结,你的喜悦,都可以得到释放。你也总会有所期待,期待明天偶遇什么人,约什么局,聊什么脑洞,得到什么消息,收获什么成果,这种安全可控又充满未知的诱惑。
如今的南京城,到处都在挖,到处都在建。一个新南京正在悄然而至,如今的老门东俨然一座历史悠久的南京迪士尼。南京鸟巢、南京水煮蛋应该也会接踵而来,一切bigger than bigger。更不用提熙南里、五福里、鸣羊街、通济门、水西门……不知道以后还会不会看到十里秦淮穿城而过。专家声称,不会让老门西再变成另一个老门东。是的,专,家,说。
无论在哪个角落,无论早晚,你都会听到施工声。这么循环反复的噪音,都可以忍受,足以见得大家还是喜欢摇滚的。
当然,尽管如此,我还是喜欢现在的声音。大的格局已摧枯拉朽,无法改变,但在南京小的角落里,小的声音,还在有惊喜发生。
八九十年代的声音是洪流,大家顺流而下,湍急的河水汇成一股江海,集中往一起走。而现在,每一个乐队,每一种声音,都在拓展,不再背负使命,各走各路。每个声音都是巨人,都代表着自我。
文/王海洋
南京之声
南京之声
王海洋
每个声音都是巨人,在时代中表达自我
责任编辑:十三妹 shisanmei@wufazhuce.com
作者

|
王海洋 @野外合作社王海洋
野外合作社乐队主唱
|
|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