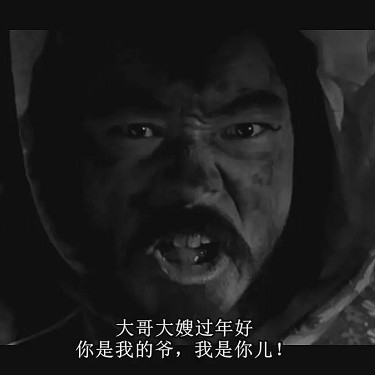朱塞佩·托纳托雷的拍片数量不多,大多以浓郁的浪漫主义风格为主,几乎每部都是精心锤炼的作品。如《海上钢琴师》,与他的另外两部作品《天堂电影院》、《西西里岛的美丽传说》合称为“时空三部曲”。
这部电影的口碑两级分化很明显,喜欢它的人将其视若神明,不喜欢它的人把它比作糟粕。所以《海上钢琴师》便有了一个奇怪称号——世界影史上最好看的“烂片”。

但这并不妨碍《海上钢琴师》的伟大。在豆瓣电影TOP250中位列第15位,95万人的评价下依旧保持着9.2分的高分,许多人认为它是一生必看的电影。
高级的天才钢琴师1900,遗憾的豪华邮轮弗吉尼亚号,落魄的小号手麦克斯,经典的斗琴片段,以及对自由女神趋之若鹜的人群……

这些不同的视角都让《海上钢琴师》的解读不止一种,但这样的好电影值得多说。
01
小时候的我们和1900一样
1900从未上过陆地,因为那里有太多欲望,而1900是个纯粹的人。如同小时候的我们一样,很单纯,也对世界充满好奇,对规则不屑一顾,可以尽情的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与个性。
未被世界浸染,都曾特立独行。
但最后皆被现实打磨成平凡人,因为我们都明白年少轻狂的好日子,一懂事就结束。不像1900那样,没有束缚,没有世俗的约定。

在船上,他能够做他想做的一切,也可以保持他想保持的样子,如他可以不理会指挥,随心所欲的弹奏自己喜欢的曲子。
但我们不一样。在成长的过程中会被要求做个好孩子,于无形中剪掉可以天高任飞的“翅膀”,在妥协、沉默中长大,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失去了个性、扔掉了脾气。提高了所谓的情商,说着违心的话,做着违心的事,学着违心的假笑,但这一切会被美名其曰为“长大”。
其实1900也想过长大,想过与世俗接轨,所以他才会选择到了纽约下船,可走到一半却扔掉了帽子,返身回到船上。

因为他看到了无尽,看到了不可控的事物,看到了想要慢慢把他变庸俗的所谓懂事。他不想失去内心的热烈、激情与叛逆,才选择了继续做小时候对规则嗤之以鼻的自己。就像那时候为了不让警察带他去孤儿院,在船舱躲了22天,最后出现在钢琴前一样。
可我们与1900不一样。长大后的我们都变得包容了,对待万事万物懂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有些人把它叫做成熟,但准确的说法应该是算了我们都长大了,我们也逃无可逃,因为我们没有1900那样找到可以躲避的船舱。
02
拒绝步入世界
1900有他的自由,他的自由是:当弗吉尼亚号遇到大浪时,其他人或在呕吐、或待在房间、或穿上救生服,而他选择在舞厅随着船体的摇晃,坐在滑行的钢琴上弹奏美妙的音乐。

因为他可以拒绝随波逐流,因为他生下来就没有步入这个世界,所以他可以选择不步入这个世界。这不是勇敢,这是一种本能。
而我们生下来就被抛进了世界,所以我们步入这个世界并不是多么勇敢,只不过由不得我们选择而已。
我们也曾被这种本能感动,去追求远方的诗和田野,去羡慕以梦为马,浪迹天涯的生活。我们开始说走就走的旅行,放下手中的PPT,去阿拉斯加看鲟鱼跃出水面;不理会客户的催促,去玉龙雪山看铺满的皑皑白雪;忘却拥挤的地铁公交,到青藏高原转遍所有经筒,漫步在拉萨街头,做世间最美的情郎;踢开办公室的无聊,到茶卡盐湖欣赏荡起的阵阵涟漪,走在佛光闪闪的高原上,三步两步便能看见天堂。
可我们终究成不了1900,不会像他那样坚持不下船。

03
偏见与优越感
我们先来看看偏见和优越感是怎么产生的。
任何文化都是具有包容性的,可总会有所谓的大多数把文化中糟粕的部分拿出来并加以放大作为论证别人无知落后的证据。也许本意不坏,但是当一群人都跟随的时候,玩笑也就演变成了事件,事件随之成为长久难以消除的世俗认知,偏见、优越感产生。
1900又是怎么做的?
他对待任何人都是一致的,在他的认知中无分三六九等,也不管肤色是黑是白,因为在船上他学到的就是包容一切。如他小时候被一群和丹尼一样的黑人锅炉工养大,养父意外身亡后,他加入了船上的演奏团,又和一群白人打得火热。

所以他可以在头等舱为上流人士弹奏爵士乐,也可以在三等舱为穷人们演奏布鲁斯和民间小调。
再来看看优越感,1900身上仍旧没有这种歧视。在头等舱参加舞会的都是白人,即便爵士乐的发明者杰利已经功成名就,但他到来时依然会引起一阵惊呼“他是个黑人”。

但1900并未这样惊讶,刚开始是把他当成能够读懂自己内心的音乐知己,只是在杰利爆粗口之后,他才动怒。
可其他人不同,他们的潜意识里就会将黑人定为下等民族,而他们是高贵、优雅的,这是他们肤色和阶级的优越感。
而区分优越感最普遍的辨别方式,是嗅觉、视觉、听觉、味觉、语言……嗅觉即气味,这种气味是三等舱架子床上的穷人味、廉价的面包味、低劣衣服上的发霉味、长期不洗澡的汗臭味……
电影中,对这种气味的优越感,也有展示。白人富人为了听到1900弹奏自己喜爱的音乐,与三等舱的穷人挤在一起时,他会用手帕捂住鼻子。

既然如此,问题来了。为什么在现实中根本见不到1900式的人?
答案很简单,因为以现实的标准来看,1900或许根本不存在,他没有可以证明自己身份的任何证件。在电影中,导演也告诉了我们,1900不会活在这个世界上,所以他选择让爆炸声响起,让1900随着弗吉尼亚号一同消失。

04
我们都是孤独患者
陆地世界没有1900活着的痕迹,只有无尽的孤独和世俗,也许他恐惧未知,害怕迷茫,但他的内心始终有着近乎偏执的孤独。
他能够看懂舞会上每一个人的想法、性格和情绪,如偷着上来想要搭讪的底层人,装清白的贵妇,虚假的有钱人……,可他依然孤独。
他在三等舱为穷人弹奏音乐时,眉飞色舞,快乐的就像第一次和丹尼一起读报纸那样简单。
可当人群一拥而散后,只留下1900坐在钢琴前,眼神中尽是失落,他还是要面对自己的小小世界。

正如现实世界中的我们,一个人的孤单,是狂欢;一群人的孤单,也是狂欢。
表面上的1900合群、快乐,有着庞大的社交圈,当一个人独处时,清楚的正视自己的内心时,才明白其实他和我们一样,是一个孤独的人。
05
你想要怎样的生活
1900的唯一挚友麦克斯,有三次畅想他下船后的生活。
第一次是希望他结婚生子、田园牧歌;第二次是肯定他名满天下、家财万贯;第三次是渴求他改变自己,重新开始。
但1900并不想下地,因为他一旦落入凡尘,结局应该和程蝶衣一样,卷入时代的洪流,再多的坚守也敌不过薄情寡义、沧海桑田。
这不是他想要的无限生活,他不想像陆上的人那样,浪费很多时间琢磨为什么。
“冬天到了,就急切地盼望夏天;夏天来了,又担心冬天将至;所以你们永远不厌其烦的旅行,总在追寻遥远的四季如夏的地方,我觉得这种地方根本找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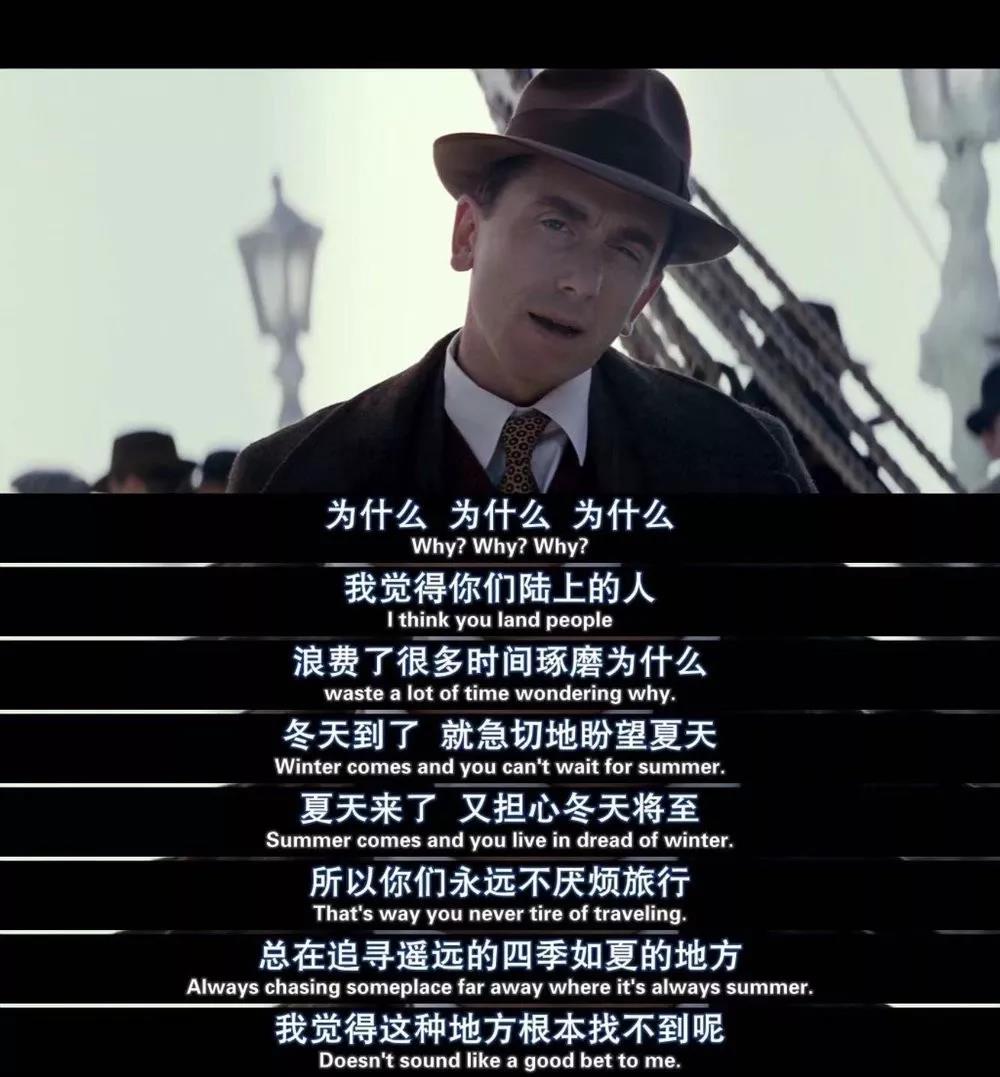
这种找不到的地方不是1900的生活,找得到的安逸才是他心底最美的艺术生活,所以他一辈子也没有下船,所以他掰断了已经录制好,可以令他光芒万丈的唱片。
但麦克斯与他不同,他更像是沉默的大多数,一直在寻找不知道终点的夏天,渴望着耀眼的瞬间和划过天际的刹那火焰。
船上的芸芸大众也是如此,抛弃已经逐步没落的欧洲,在冉冉升起的美国开始新的生活,追求属于自己的美国梦。
这些都是他们的生活,无关理想、无关高低。
正如张国荣在《我》中唱到:“我永远都爱这样的我。不用闪躲,为我喜欢的生活而活;不用粉墨,就站在光明的角落。我就是我,是颜色不一样的烟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