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作周期长达十个月的纪录片《他乡的童年》跨越中、日、芬兰、印度、英国、以色列,是总导演周轶君在咖啡店餐巾纸上花了10分钟定下的一趟关于“童年教育”的解惑之旅。
这段旅程的初衷,不为美食,不为美景,只是她作为困惑的母亲,想去寻求关于教育孩子的智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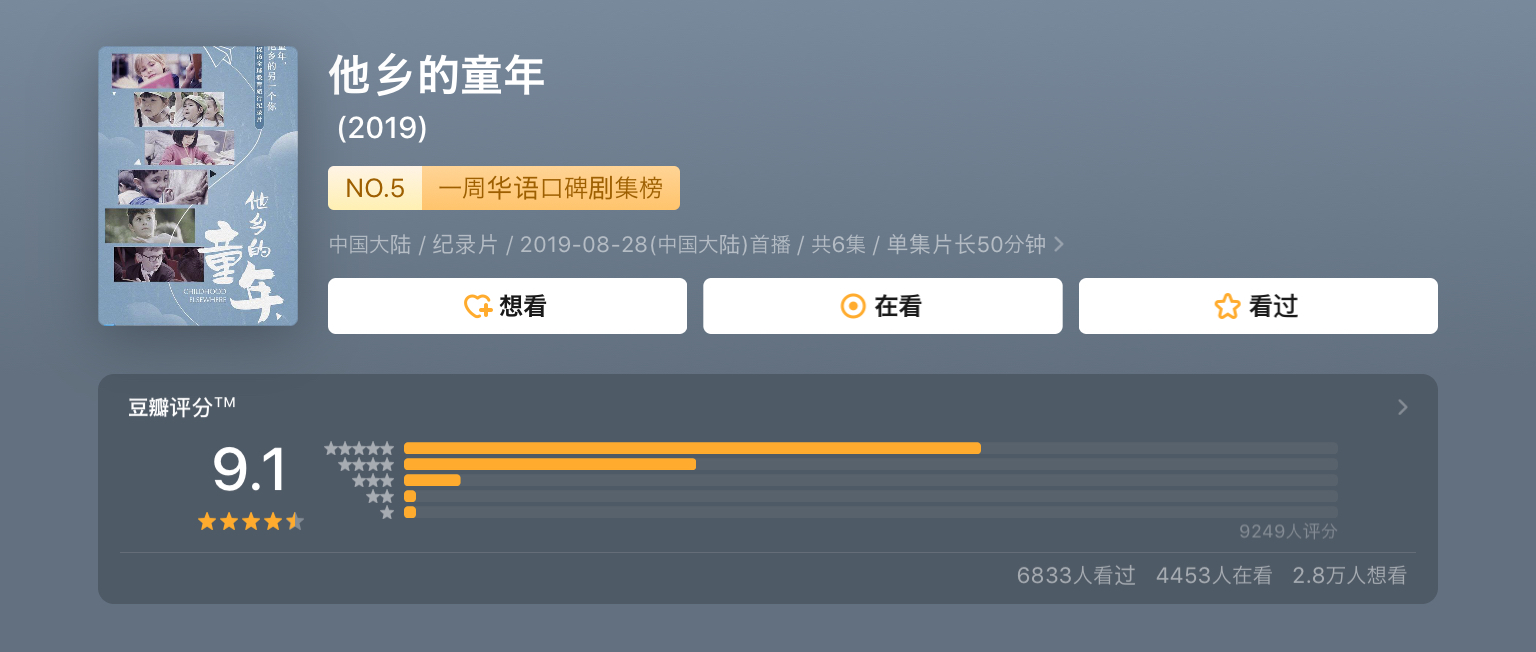
作为两个孩子母亲的周轶君,曾是2002年至2004年全球唯一常驻以色列加沙走廊的国际记者,她带着新闻人求真好学的“职觉”,担任该纪录片的总导演,片子为每个国家的教育特色设立了一个主题,六集六个国家,带我们看看“童年教育”在他人他乡会有怎样的不同。
前 方 到 站 ——
01
中国
围绕“传统文化”展开的中国,在播出时作为最后一集以收官战登场,我却推荐大家作为开篇站,先睹为快。
周轶君在中国台湾采访作家张大春。张大春喜好书法,正推出一册关于造字的书目,书中提及,若从传统古文解读“赢”字,则是“多余”的意思;解读“乖”字,则是“背离,违背”。可回想一下这两个汉字在童年时期曾高频出现的句式,哪儿还有汉字原本的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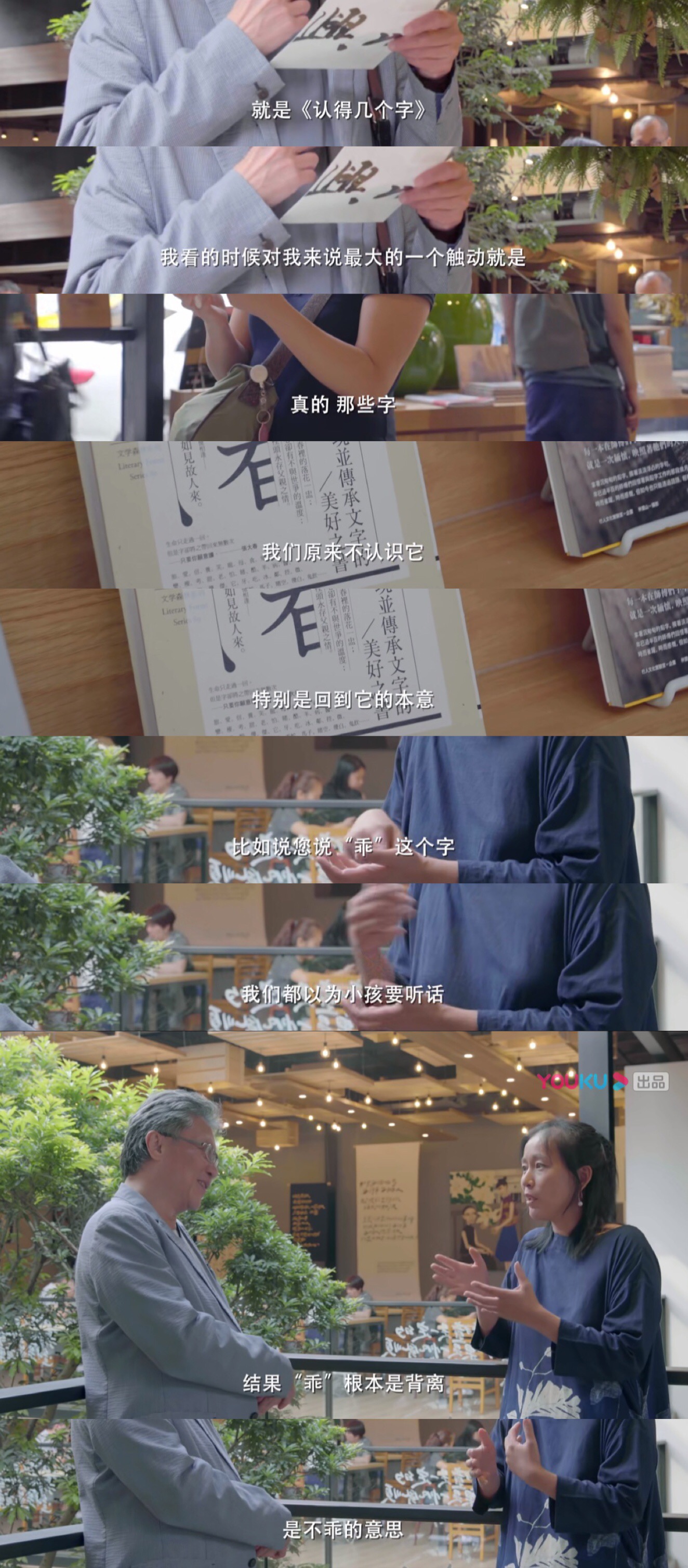
难道传统文化消解在现代教育之中了吗?不。
安徽小团山香草农庄中英书院,模仿古代私塾提供通识教育,一群孩子正兴致勃勃与传统文化“触电”。他们在这里参与天象观星、立体风筝、田园诗书等课程,老师们在主打学科中融入了自然接触、手工制作、农林闲趣的体验。

中国家长并不排斥传统文化,可惜迫于社会晋升体系,只得将作为“陶冶性情”的传统文化深埋心底,只待孩子成年后有缘再会。中国家庭就此进入抗击升学焦虑的战斗。
02
日本
打小的集体规训,为日本形成秩序社会功不可没。纪录片选择“集体式教育”的主题展开探索,试图了解大和民族如何看待“个体与集体”的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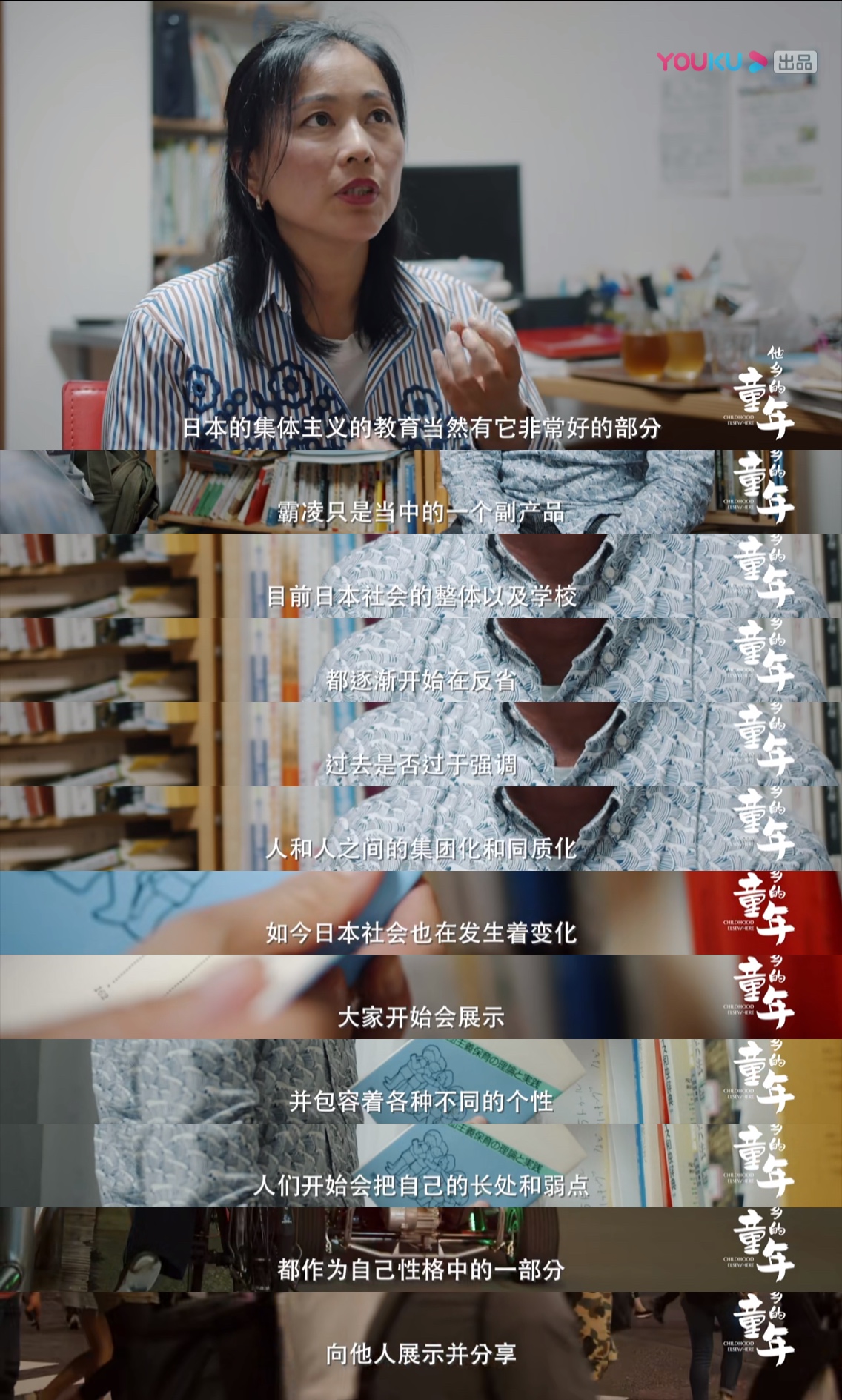
大阪莲花幼儿园历史悠久,在过去60年中让孩子不分四季的赤身锻炼身体,直到2019年4月才迫于舆论压力,终止了这一传统。剑道课上,孩子们跟随老师练习坐姿,要洪亮地喊出“请多指教”,并在每次挥剑时通过丹田发出气合(就是大喝一声)。
园长秋田光彦评价说:“日本是一个讲究纪律的民族,所谓纪律,是为了使社会生活、社会集团以及各种各样的组织,以一种良好的势态运营下去的规则。理想的状态就是孩子们自发地去遵守。”

日本有项职业叫作“感泪师”,通过组织学生或家长集体观看感人短片,达到流泪释放的目的,这项职业的诞生源自日本“压抑不哭”的文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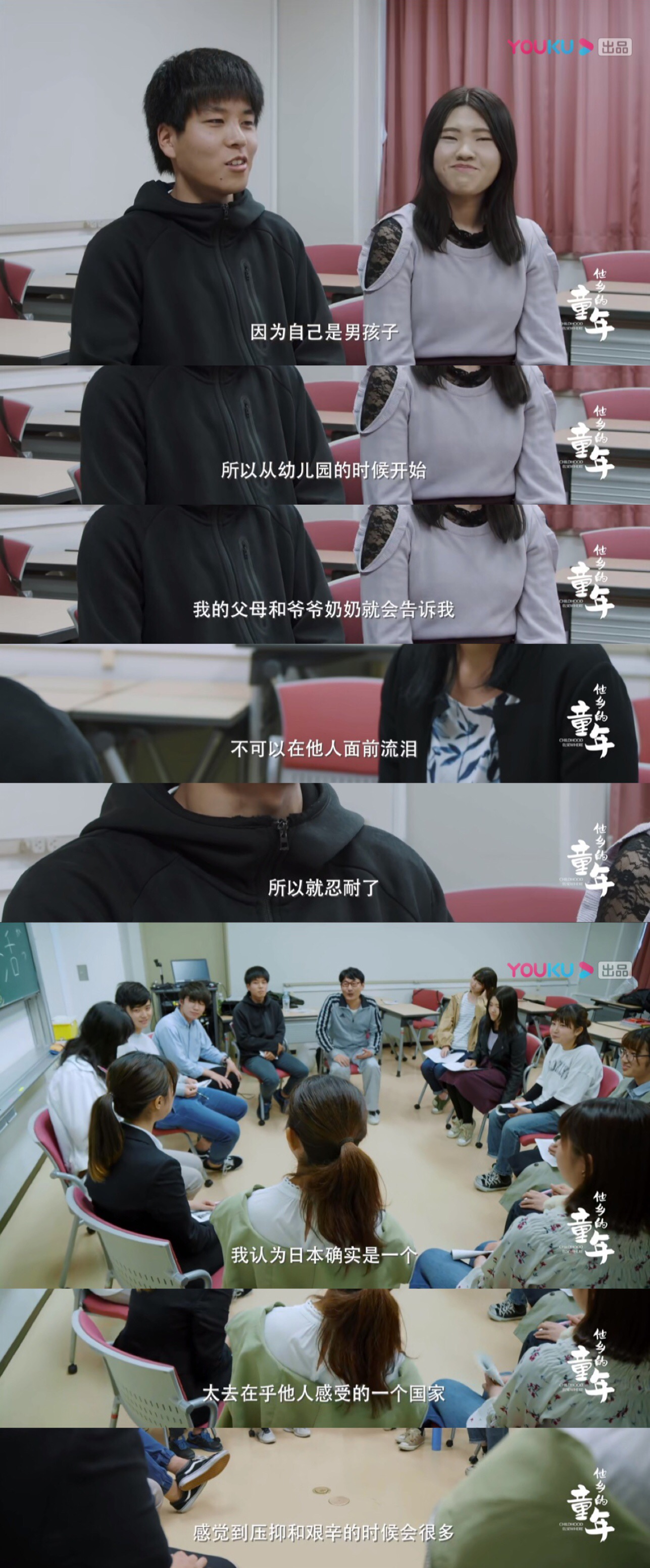
压抑眼泪,塑造“坚强”表象,是一种典型的东方意象,也是挫折教育的一种。当个体演绎外表的完好,去适应集体语境时,内心却在承受震荡,剥落,甚至飞灰湮灭。
03
芬兰
淡化竞争,尊重个性,平等教学,是芬兰传统的教育信条。周轶君在本站的探访体验中意外落泪,被镜头记录下来:
首都赫尔辛基一家康复服务中心,拉妮老师带学生来和长者们进行一次面对面的相处,开展一节主题为“时间、年龄和我”的现象课堂。课堂上,学生和年长者组成混合小组,年龄差超过五十岁。年长者们以孩子为模特进行绘画,其中一位尤其享受,完成了一副独特视角的头像,周轶君问其是否接受过绘画训练,随后被告之:
画画不是为了竞争,而是为了表达,于是她终生保持着这个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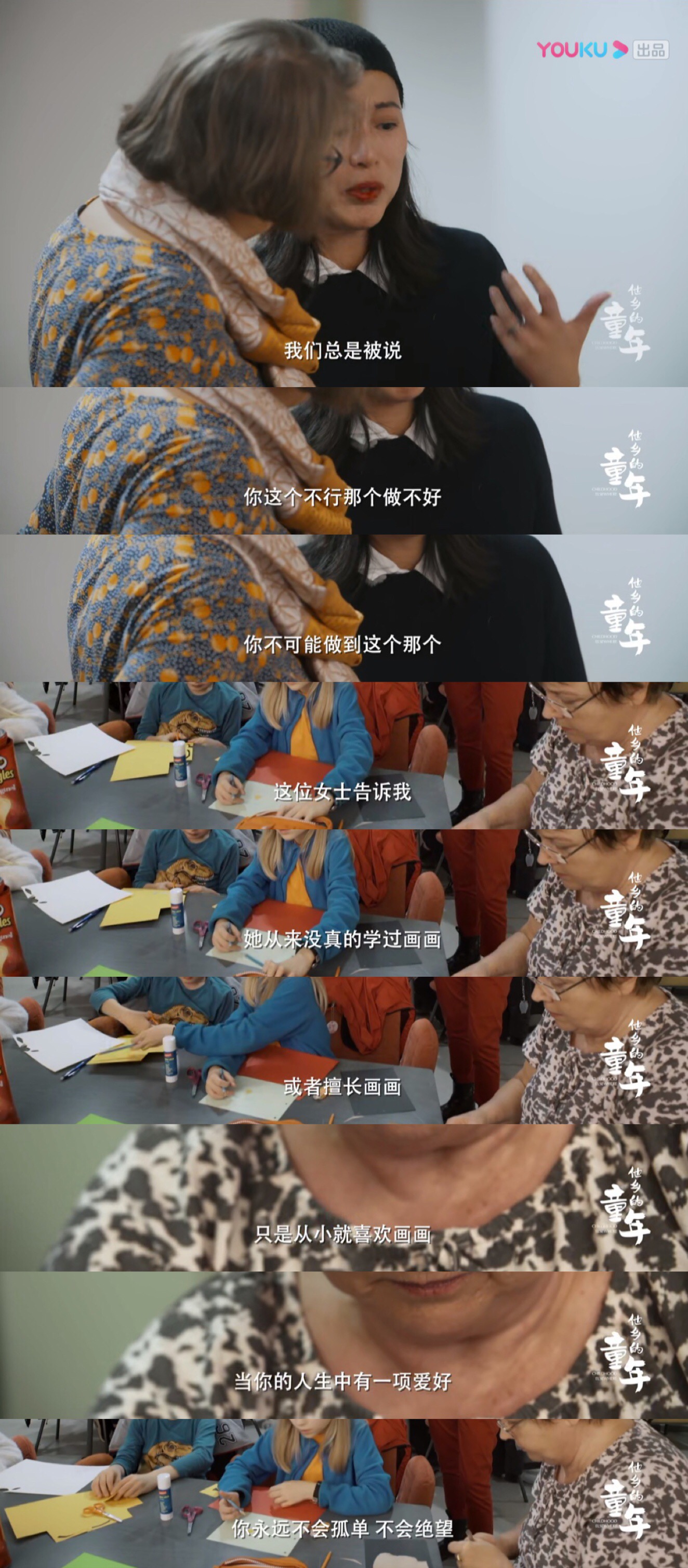
芬兰卡苏卡拉小学,学生正在森林完成劳拉老师交付的“任务”,譬如找到“可爱的东西”“恶心的东西”。周轶君问:“学生们需要叫出每种树的名字吗?”老师回应“需要的,但是凭他们的想象力给出名字就行,并不需要正确答案。
这堂课的目的在于培养孩子和自然的关系,让他们学会爱惜,保护自然。”
教学模式没有标准答案,需因地制宜,在森林的孩子向森林学习,在城市的孩子应该学习城市,重点在于:让孩子与他们生活的环境产生联系。毕竟学习是为了回到生活,回到所处的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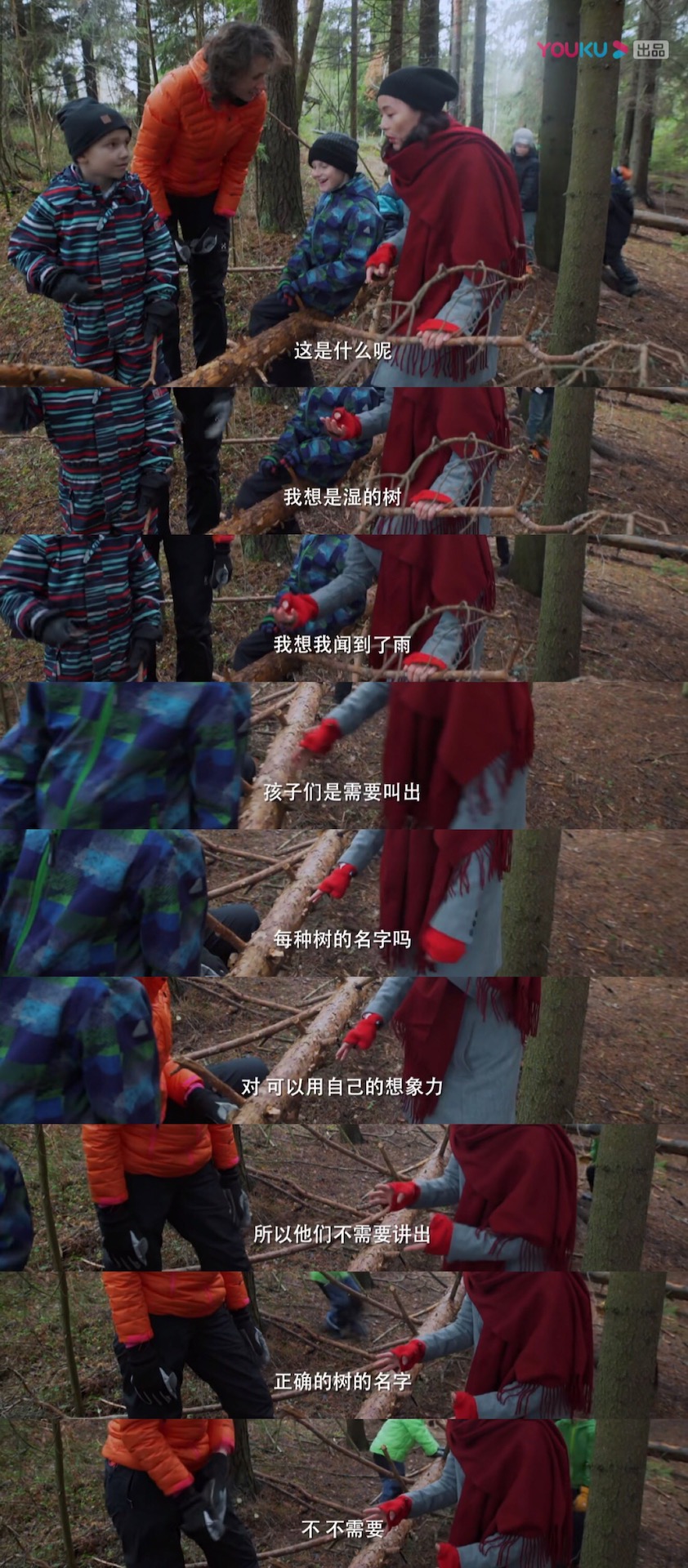
作为全球教育最强国,芬兰相信,要把钱投在人身上,再由人去创造财富,于是即便社会存在贫富差距,可孩子受到教育的机会,使用的资源都是平等的,这里没有只给富人的学校。如果问芬兰最好的学校是哪一所,答案会是——最近那所。
9岁男孩尤斯特斯描述自己未来想当程序员,被问及什么叫成功时,他淡然地回答道:

愤怒的小鸟创始人彼得·韦斯特巴卡坦言,在芬兰孩子不会没出路,即便没上大学,家长也不会认为是世界末日。因为没有竞争,芬兰评估学生的不再是“学到多少”,而是“如何学习”。由此,“积极教育”成为芬兰教学新趋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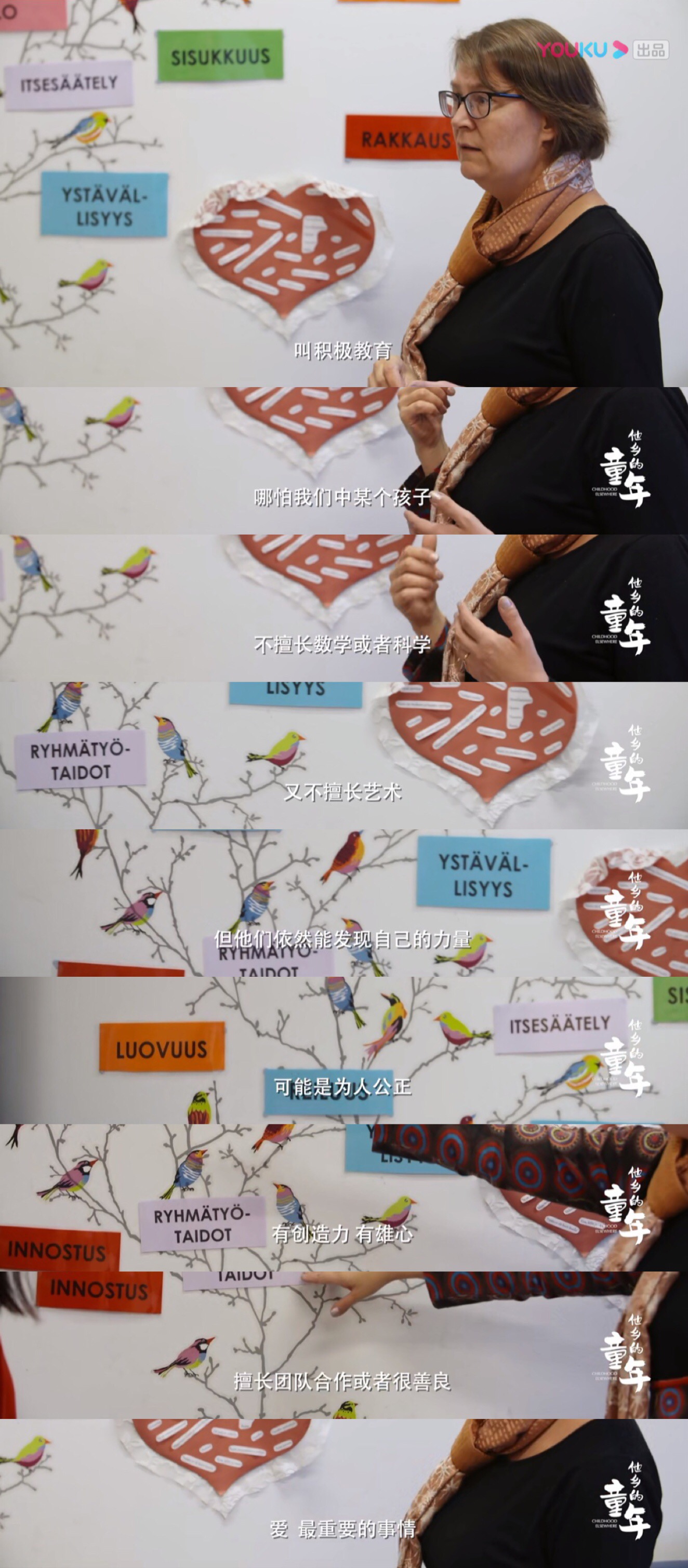
爱,是最重要的事情。
04
英国
“精英教育”是英国站讨论的主题。说起精英教育,人们都会首先联想到礼仪、绅士品德等等,很少有人会联想到“体育”。
毕业于英国著名的私立学校伊顿公学的马术运动员华天,打开了我们了解“精英教育”的体育之窗。马术常被认为是奢侈运动,代表富裕阶层,许多家长送孩子学骑马都选择私教,华天认为这恰恰错失了学习骑马的乐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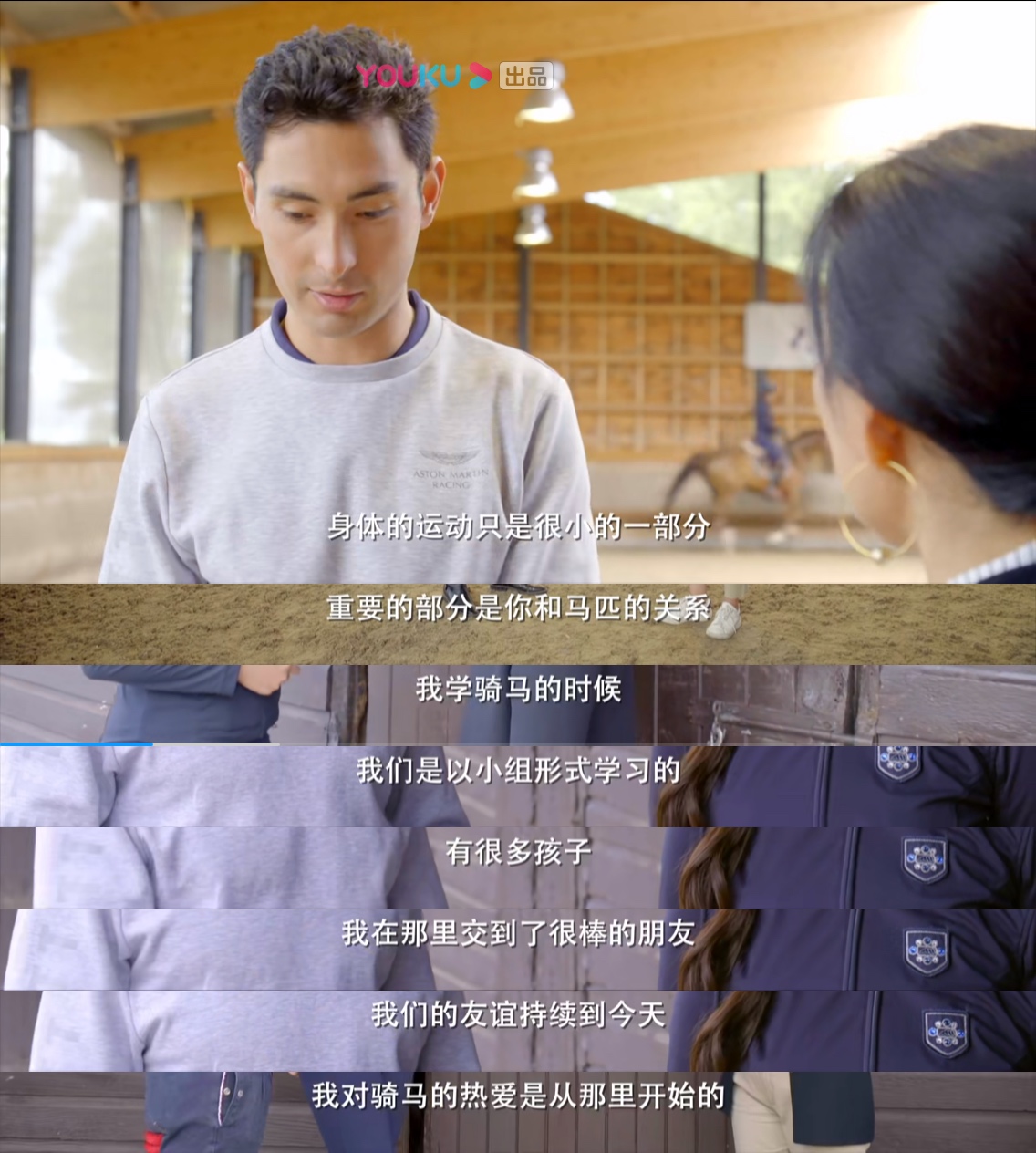
若要探究“精英教育”的精神内核,帕特里克校长认为是推崇年轻人参与社会,让年轻人成为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

05
印度
当纪录片来到拥有14亿人口,贫富极速分化的印度,周轶君认识到了印度社会最重要的特点——“多样性”,摄制组中7个印度人,均来自不同种姓、不同民族,且分工合作的方式低效得出奇,周轶君感叹——整个旅程仿佛一个中国人在当地进行就业再培训。
正是经历了困难与混乱,纪录片才得以抓取到印度教育之特色——拒绝标准答案,在每个困境中寻求新的解法与秩序,“云中学校”项目,便是印度教育特色的缩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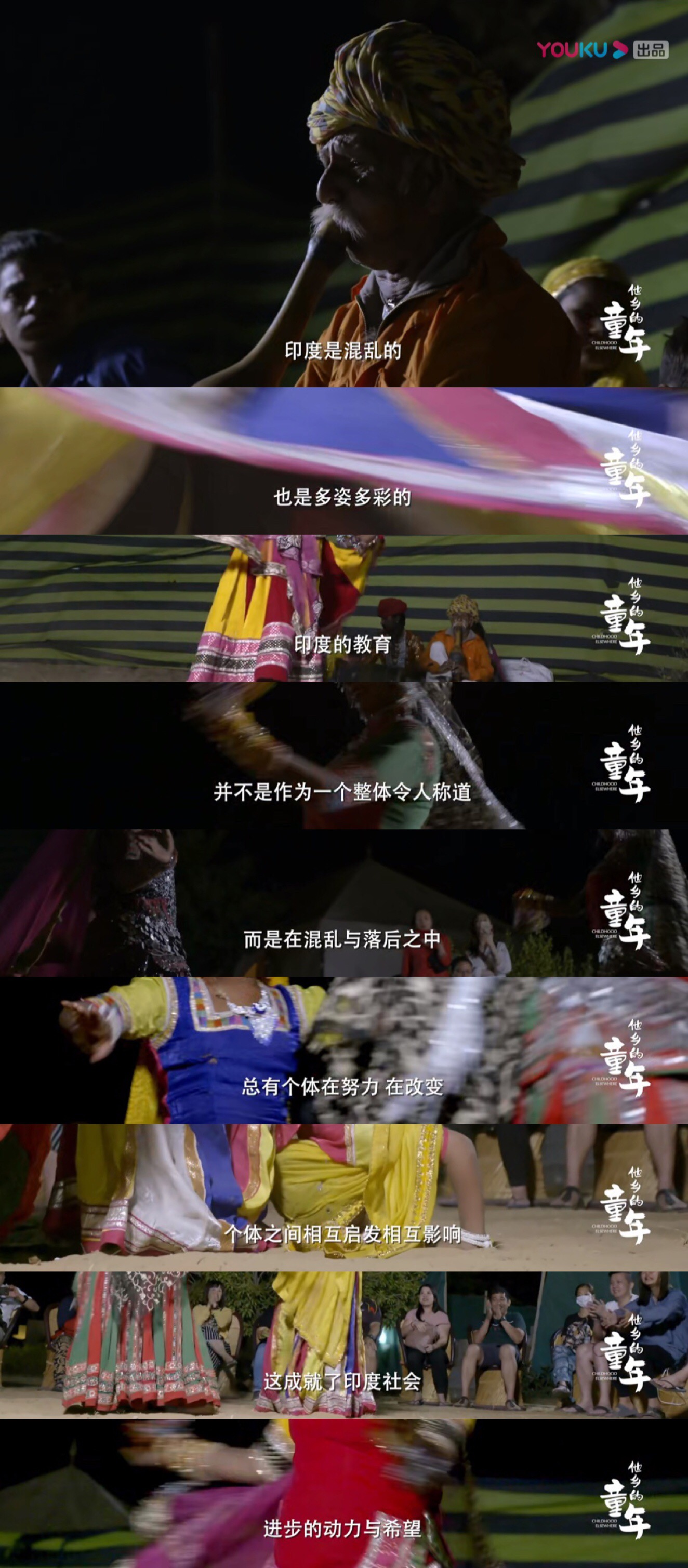
“云中学校”的创始人苏卡塔教授从上世纪90年代起,在印度的偏僻村落安装电脑,试图利用互联网填补村民与外界的鸿沟。他相中了地理偏僻,交通落后的卡拉卡提村。
卡拉卡提生病的人很少能活下来,因为来不及送去医院,村民中用茅草遮盖屋顶的不在少数,甚至还会出现衣服不够穿的情况。家庭条件稍微好一点的农民,仍旧使用着不能上网的手机。互联网在这里只是一个学习工具。

“主动学习”成了云中学校项目的的一项拳头优势。
06
以色列
面对成败输赢,没有沾染太多东方压抑文化的以色列,自有一番坦然。若用特拉维夫大学管理学院主任的话说,那便是——以色列人的思考方式是生存模式,我们生活在以色列,对明天从来没有把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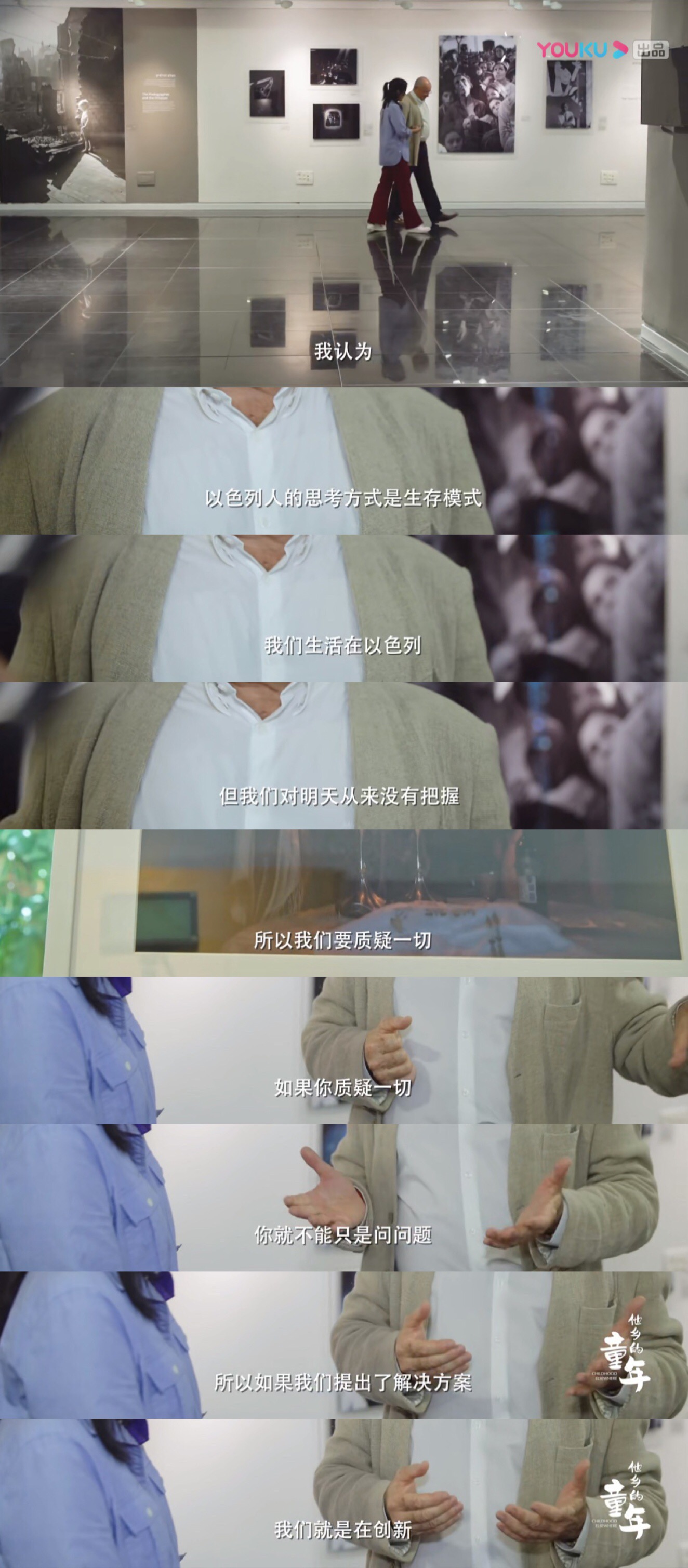
今时今日的以色列,一方面仍旧是个全民皆兵的国度,一方面也是纳斯达克上仅次于美国的创业大国,“Start-up Nation”成为他新的关键词。当我们的影视剧正热烈探讨童年创伤时,以色列已经开始谈论“童年创业”了。
阿克发·阿亚洛克高中Green Start学院的一个机器人小组,正热情地展示着自己的“科研成果”。16岁半的组员奥里,是研究这类机器人的创业公司CEO,和他同期活跃在学院中的还有另外13家青少年创业公司。这个不下96%的创业失败率的国家,失败从来不是结束。

出于职业习惯,选择到大世界里解惑的周轶君完成了纪录片制作。解惑的初衷没有达成,可她说“这个片子不会提供解决问题的办法,而是开阔眼界的东西。”
仅仅六个国度,儿童成长的可能性已经如此之多,解惑之旅已延伸为自我发现之旅。
回想我们的童年时光,早已“一饮而尽,无法续杯”,可那些按下暂停键太久的爱好,也许是时候再续前缘。在有限的余生里发现更多的自己,继续成长,做个不会孤单,不会绝望的快活人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