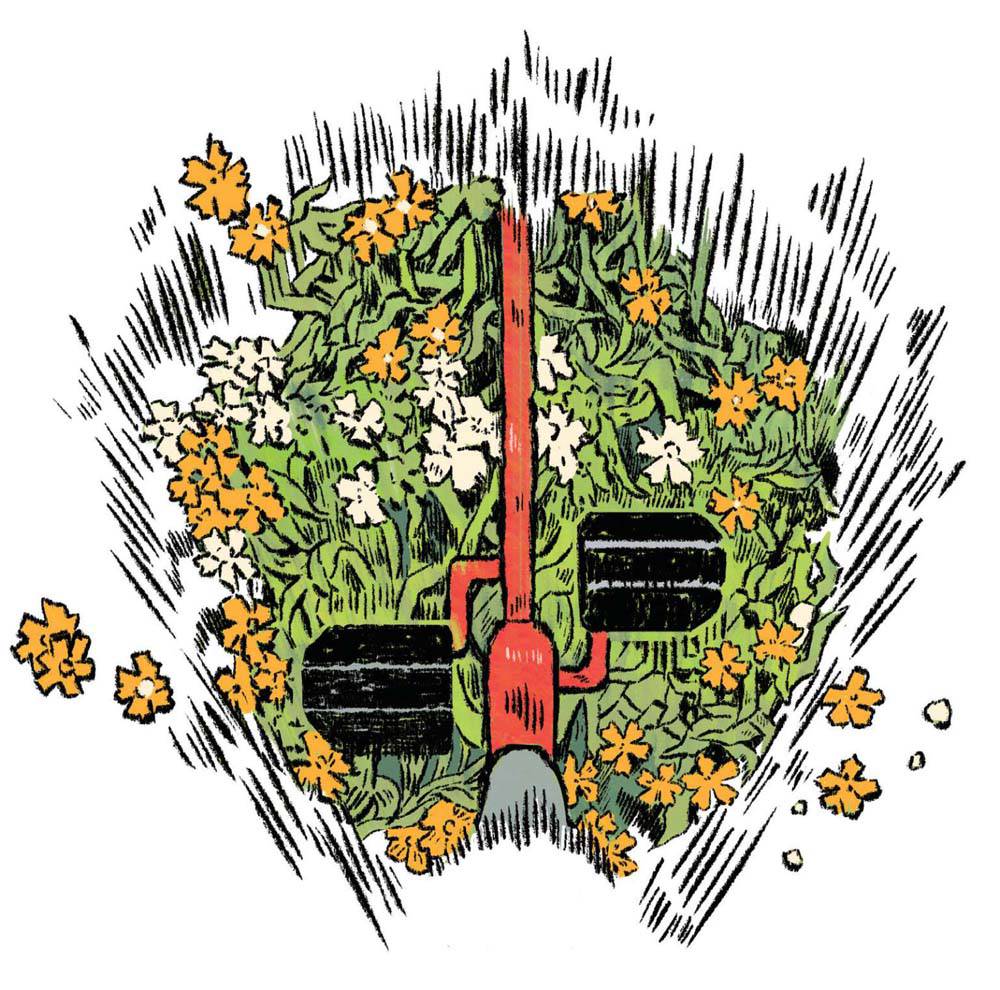在这个世界里,人需要进行资格认定,由你的猫打分,决定你能否成为正式的铲屎官。
一
我没有猫,前一天还是这样,今天早上我睁开眼睛,看到了自己的猫,迎来它的第一句话:“嗨,小子,以后你是我的人了。”
我无视其中的怪异感,勉强坐起身靠在墙壁上,按着自己的腹部。我有个老毛病,睡前心里憋着事,一是会失眠,二是醒来腹部疼,不是一般的自内往外地疼,是自外往里,肌肉绷得很硬,又硬又疼,前女友说这是躯体化,让我到医院看一看,分手后我也没去看。
猫有一张丑脸,像被车轮碾过,毛色很怪,自头到尾黄色花纹越来越淡,跟喷色喷一半没墨一样。它跳上了椅子,在舔爪子,腹部是纯白色,肚子肉肉的,这是一只奇怪的加菲猫。
为什么说它奇怪,除了它会说话外,我还能读懂它的表情,比如现在,它臭着一张丑脸,一对红铜色的眸子透着不耐。它见我盯着它,跳到我的腹部上。
腹部肌肉回馈痉挛的痛感,我身子一抽搐,把它吓掉下床。
加菲猫爬回了椅子,一脸惊讶:“你是要死了吗?”
“没,只是小小的老毛病,抱歉吓到你了。”我感到很抱歉。
“真的没事?”
“真的。”我已经独自居住将近半年了,头一次感受到他人即使是一只猫的关心。
“我饿了,快去给我买猫粮吧。”
我又不感动了。
我靠着墙缓了十多分钟,腹部疼痛渐消,也不僵硬了,下床穿好衣服,对猫说,我去买猫粮了,你好好在家待着。
这是一家老小区,我住在顶层十二楼,十二,这个数字很好,两个六的和,但我没感到自己顺起来。住在这里半年,身体倒比以前好了,与老小区没有电梯有关。
我从顶楼下到一楼,高层住户很少,楼道昏暗,满墙贴着一张张破碎的小广告,里面有妇科的,开锁的,考研的,男科的,一张贴着一张,一张压过一张,层层叠叠,相互竞争又配合有度,共同填满墙壁的每一个空白。小区太老了,老到没有人知道它的物业,太久没有清洁工光临这里。在这样尘埃的间隙,小广告越贴越多,越积越多,直到某一天,有人发现这里只有说话流口水的老人,针大小的字落在他们眼里是一团墨渍,自那后就没人来贴了,小广告也积满了厚厚的尘土。
三楼有一辆废弃自行车搁置在楼道,身上爬着蜘蛛网,车链子积有厚厚的油。它曾几何时跟随主人走过很长的路,但现在已经老了,靠着墙壁的一边,奄奄一息。穿过它,迎面是堆积的纸盒子与塑料瓶,它们有股很大的味道,到这里我会捂着鼻子,奔着门缝露出的光跑去。
每一次下楼,我都有一种奔向救赎的错觉,在昏暗的气氛中,冲向一抹温暖的光,这是很多电影里的场景。我打开门,室外的光填满我,然后就没有然后。待业在家,日日没有变化。
最近的超市在几条街开外,步行二十多分钟。夏天的太阳很大,几个老头在树荫中下棋,几只老猫在脚边穿梭。
老小区没有物业,没有不让养猫狗的规定,猫狗三三两两结伴游荡,偶尔在某个瞬间从视野盲处蹿出。
九月初秋的午间,饭后散步的好时候,慵懒的阳光烘得我心暖暖的。一个胖老人,没有牙齿,头发稀疏,一只无毛猫跟在他后面,同样的老态,同样的步伐缓慢。小巧的老太太抱着带蝴蝶结的吉娃娃,她们瞪大眼睛,滴溜溜圆。拄拐杖的老人有一条瘸狗,同样走三步歇一步。世上有千样的人,就有千样的宠物。
我来到了超市,门口排了长长的队,我排到队尾,问前面大妈人怎么这么多。
大妈烫了个卷发,一丛丛的,像顶团毛球,怀里抱只穿粉裙子的白猫,也顶了个毛球。
大妈告诉我,今天是周一,管理局在超市统一发放宠物粮,都来领取。
“发放?”
“是啊,发放,不用买呀。”
“不不,是免费发放,但也是买。”
我很疑惑,大妈说这是传统,自古以来就是这样。
我没管“自古以来”下面藏有多么大的历史疑问,而是认真排起队。“免费”是一件多么美妙的事,对于一个没有工资的人来说,“免费”是如同耶稣显圣、佛祖割肉喂鹰般的神赐。
她问我的猫呢,我说它在家,长得丑,脸像被车轮碾过,不好意思出门。大妈伸手指逗逗怀里的小猫:“还是我家小美女最可爱,你家的猫是加菲吧,加菲猫就是有张惨不忍睹的瘪脸。”
我点了点头,很认同她的话。
“你一个月工资多少呢?”
我有点不好意思,说自己没工作呢。
大妈很诧异:“你不是有一只猫吗?你是刚毕业才领到自己的猫吗?”
我更诧异,没说话,瞪着俩眼睛看着大妈。“原来还是个新手呀,没事,等你过了实习期就有工资了。”
之后我就不说话了,大妈见我不吭声,回头逗起了小猫。等队伍排到我,已是下午,太阳透出一股低垂劲,亮得发虚。队伍尽头有两张小桌子,摆在超市门口,一张桌子上竖着根“旺旺管理局”的旗子,另一张桌子的旗子是“喵喵管理局”,我的队伍排在“喵喵管理局”的桌子前。一个穿着绿色工作服的人让我把头伸过来,瞪大眼睛,他拿一个像体温枪的东西,枪口幽幽发着绿光,在我眼睛那一扫,叮咚一声,背面的显示屏出现了信息,那人看了几眼。
他说,还是个刚毕业的大学生,刚分配的猫咪吧,起名了吗?
我摇了摇头。他让我今天四点前去趟喵喵管理局光明街办事处,把手续给办了。
我领回了猫粮,一箱子,侧面印有一只猫咪图案,像是三花猫。
等我把猫粮搬回家,短袖的前后背被汗水浸透了,我脸上汗淋淋的,靠在门口不停喘粗气,汗水还不停地往下滴。我缓口气,敲了敲门,说我回来了。
门缓慢地打开个缝隙,露出半张猫脸与一只红铜色的猫眼睛,它见是我,跑到一边没了身影。
我侧身靠开门,把猫粮放在玄关下,猫等得不耐烦了,骂骂咧咧的,脏话很丰富,不重样,有的比喻很有新意。一只猫竟能骂出贯口。
我好奇,问猫,你是从哪里学的。
猫告诉我,是看电影学的,它在公司看的。
我问它是什么公司。
它说:“就是公司呗,喵喵公司,跟喵喵管理局有合作,领分摊任务,这片的猫都是从那出来的。”
“你是在那工作吗。”
“不不,公司是放假去的地方,叫上班,家是工作的地方,叫休息。”我被它绕得有点懵。
它摇摇脑袋,一副“孺子不可教也”的样子,跑开了。我说那我还要给你准备床吗?猫没理我。
一会后,它叼了个猫碗回来:“我快饿死了,今天不让你做鲜鱼了,你快把猫罐头给打开。”
我用小刀拉开箱子,里面真有活鱼,在玻璃瓶里甩着尾巴呢。箱子里一半是活鱼,用玻璃瓶装着,贴着“喵喵有限公司”的商标,另一半是鱼罐头,写着“臭鱼烂虾连锁超市”的字样。
玻璃瓶没有550ML的矿泉水瓶高,但壮,很宽,里面游着一条小鱼,很无知的样子。我跟猫说:“要不你直接吃活的,多鲜。”
猫摇头,说:“不能,那不绅士,不卫生,文明猫怎么能生吃鱼。”
我撇撇嘴,猫怪讲究的。
我打开鱼罐头,倒进猫碗里。猫碗是塑料的,绿色,碗边绘着小鱼图画,像小孩子的涂鸦作品。鱼罐头太腥了,倒干净后我立马后退,把罐头扔进垃圾桶里。腥味很重,气味针扎鼻子般难受。
猫吃完,让我去洗碗,我听话去做了,边洗边跟猫唠起嗑,猫大爷边舔着脚边应付我。
我说:“你多大了呢?”
“几个月来着,记不大清了。”
“我二十二岁了。”
“你们人类的年龄没用,反正会死掉,我们猫咪可不会。”
“你说在家工作是什么意思呢。”
“我在家,你伺候我,这就是我的工作,你可小心伺候着本大爷,我不高兴就让你实习期不合格。”
“实习期不合格会怎么样呢。”
猫走回主卧,声音渐小:“会完蛋哦。”
二
猫午睡醒后,我带它去办手续,我扫了一辆单车,它坐进篮子里。
我们蹬着车到办事处,里面人很少,午后的阳光透过窗户投在大理石的地板上,弥漫着慵懒的气息。
办事处有三个窗口,紧靠窗户是两排椅子,只有一个大爷搂着一只猫咪躺在上面睡觉。猫说他的脚好臭。大爷没穿鞋,脚搭在椅子把手上,大脚趾盖骄傲地刺破袜子,露着汗淋淋的头。
我面对的办事员是个小姑娘,一头齐耳短发,西装领带,我表明来意,小姑娘拿那个发绿光的枪扫了扫我的眼睛,猫跟我说了,这是在扫描虹膜。在这里,每一个人的虹膜信息都有备案,无论是消费还是办事情,扫下眼睛就行。
办事员打印了两张表格给我,第一张题头是“铲屎官工作签约表”,上面写着我的个人信息,年龄、性别、出生年月、上学经历,乃至这半年在家待业上面也写得一清二楚。第二张猫主子信息登记表,是空白的。
她递过来一根碳素笔,让我给它起个名字,其他信息会有专门工作人员进行采样填写。
我先在第一张表的确定一栏签上自己的名字,又在第二张姓名一栏写了一个字——“猫”。
工作人员带走猫进行了一系列的健康检查。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猫回来了,表也填写好,办事员递给我一张“铲屎官实习证”,告诉我下个月再来一趟办事处,进行资格认定,由你的猫进行打分,决定你能否成为正式的铲屎官。
我离开办事处,面对着太阳,我知道从今天开始我有工作了,虽然是实习生,但好歹不是无业游民,我很开心,打电话给大学时的一个舍友,想和他聚一聚。
舍友很爽快地答应,我们约好晚上七点去母校附近的东北大饭馆。七点我和猫准时到,坐在一楼5号桌,我看了眼手机,七点十分,他还没有来。
饭馆一楼的收银台上方挂了一个复古时钟,时针很懒,好半会才挪个位置,分针看人脸色行事,我盯着它看,脸色不虞,它才勉强走两步,秒针是个孩子,管它走得慢,不管它走得飞快,一会不看它,它就跑了好几圈。七点十五分,舍友推开饭店的双开玻璃门。
他带来一只狗与一个女孩,我认出女孩是街道办事处的办事员,舍友介绍这是他的女朋友叫梅,那是他的狗叫开心。
我说:“这是我的猫,叫猫。”
我和梅握下手,猫跟开心握下手,我们是认识了。
开心打了个领带,坐在椅子上。它说:“你就是铲屎官的大学舍友呀,自我介绍下,我是他的狗主子,叫开心。”
我跟开心握下手,双方表情郑重,像签约协议,交接舍友所属权。开心是条藏獒,很壮,坐在椅子上能够到饭桌,猫不能,它太小,所以坐在我怀里,看着开心一脸敌视。
我抚摸猫的毛,让它放松,看向小梅:“咱俩是见过吧。”
小梅笑了笑:“是的,在办事处。”
我问她,你的主子呢?
她说我没有主子,我为人类服务,这世上有两种人,一种是你们作为铲屎官为主子服务,一种是我们作为猫狗管理局工作人员为人类服务。
舍友已经点好了菜,把菜单递给我,我点了条清蒸鱼,猫应该爱吃。
我问舍友怎么迟到了,他告诉我是因为接梅,梅加班了。
我好奇:“梅的工作很忙吗?”
梅说:“平常不忙,只有毕业季最忙,你是我接待过最晚上班的大学生了。”
我有点不好意思:“我也不知道,毕业后就稀里糊涂在外自己住了小半年,也不知道还分配工作呀。”
梅继续说:“今天加班是遇见特殊情况了,有一只狗把铲屎官的手咬了个大口子,他来到办事处时捂着手滴了一路的血线。”
“铲屎官为主子负责,我们为铲屎官负责,我是先通知的医疗科,把他拉到医疗科室,再让保卫科去抓那只狗,按法来讲应该被关进监狱。”
我看向怀中的猫,幻想一个关满猫咪的监狱是什么样子。
梅说:“还有一种可能,如果铲屎官没有起诉,罪犯又改过自新,有概率被送去狗咖强制服务几年。”
我好奇那是什么地方,梅告诉我,狗咖和猫咖,是培训铲屎官的地方,实习期不合格,就要到猫咖学习。
猫在我怀中伸了个懒腰,吐出粉嫩如软糖的舌头,它的肚子晃了晃,像一块大蛋糕。
猫是一只加菲猫,我小时候喜欢看一部动画片,里面的主角也是加菲猫,很能吃,还会恶作剧,喜欢披萨与欺负小狗欧弟。猫胃口小,上来盘鱼,吃了一小半就饱了,剩下一半是我和梅吃掉的。舍友与开心不喜欢吃鱼,他们吃菜最多。
藏獒开心,头上的黑毛是炸的,下巴也有很长的毛,它吃饭很小心,一只爪子先把住下巴的毛,另一只爪子拿勺往嘴送,嘴巴张合发出吧唧的声音。它再小心,食物也会粘到下巴的毛上,舍友会用纸巾帮它擦拭,温柔如对待一个孩子。我喜欢开心的眼睛,琥珀色,形状大小像一枚杏子,看向人透出温柔,与它的体格相反差。
吃完饭后,天黑透了,我骑单车拉着猫往家赶。天黑压压的,没有星星,像一口烧糊的大锅,初秋的风渐大,凉风作弄绿无多日的树叶,一路沙沙作响。猫很乖,在篮筐里蜷缩着身子,半橘半白的绒毛乱了形状,有的张扬,有的低伏,猫闭着眼睛把头深深埋进腹部。
三
实习期结束后,猫把我送进猫咖学习。因为我喜欢流口水,它对我的口水深恶痛绝。在我刚要登上猫咖校车前,猫对我说:“希望你改变流口水的坏习惯,每天在你怀里醒来,我都想洗一遍澡。”
我舍不得猫,趴在车窗上挥手告别,猫也挥手回应我,目送我渐渐驶离小区。
在我上车之前,校车里已经坐了两个人,一个秃头大叔,他养了一只斯芬克斯猫,因为喝醉踩到猫主子的尾巴,被猫告上法庭,判处在猫咖学习一年,另外是一个女孩,跟我一样,是因为实习期不合格而被送去猫咖学习。
猫咖位于城东校区,校车开了很久也没到。我坐在车里很无聊,大叔没有谈兴,女孩也郁郁寡欢,都是一副前途未卜的样子。我心里没有感触,觉得这是一趟新奇的体验。窗前的景色飞快穿梭,从高楼大厦的街景到树木繁茂的乡野景色,趋向于荒凉。
上车前工作人员没收了我的手机,那是一个戴着钢壳的大汉,用手里的叉子卡住我的脖子,从我裤子的右兜摸出一部手机与三颗花生米。他把手机放在收纳袋,花生米则是扔进嘴里。我很心痛,那是我在前天剥好的,猫临时叫我去铲屎,把它揣进裤兜忘记吃了。我的脖子火辣辣地疼,叉子在上面留下红彤彤的伤痕,从猫咖毕业后也没有消掉。
猫早知道我会被收走手机,提前准备了手表,这是一部老款机械表,表盘有很深的磨痕,猫在它更小的时候把表当滑板,在瓷砖上做飞快的滑行,很快,很疯狂,撞到一次墙后就不再滑了,可表盘已经被磨坏了,针的走向几近看不清,只能靠猜。猫让我将就用,能有时间看,哪怕是猜,也比没有强。
我能依稀看到模糊的表盘中有一块是黑的,但看不清具体指向哪里,我猜是十二点整。
校车在十二点整驶入猫咖。我们先是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下,戴钢壳的大汉走下车到铁门前的屏幕输入一串数字,大门自动打开,像得癫痫一样,边颤抖边向两边收缩。
校车穿过铁门,驶入一条黑亮的柏油路,我能闻到很重的沥青味,这是一条新路,至少没猫的年龄大。
它把我们拉到最大的一栋楼前,带钢盔的大汉押着我们下车,一个男人看着像恭候多时了,他站在门口迎接我们,脸上带着笑,笑肌把眼镜抬得高高。
他是这样自我介绍的,“同学们好,我是你们最最最最……帅的班主任,欢迎迎迎迎……新同学加入我们。”他有点磕巴,长着一张发生故障的嘴。
猫咖有三个班别,短期班、中期班、长期班,短期班是十五天,中期班多上五个多月,长期班最长,是一年以上。我与女孩被分入短期6班,大叔是长期3班。磕巴男是我的班主任,一个微商头型的妇女带走大叔,临走他眼睛含泪,迎着风稀疏的毛发冲冠而起,颇有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意味。
磕巴男自称姓陈,但我还是要叫他磕巴男,他说话太有趣,像卡碟。儿时在家看电影还是放碟子,有时候碟盘不干净,会一卡一顿,屏幕里的人跟着一卡一顿,图像抽搐,声音断断续续,来回重复。
磕巴男先带我们领了教材,有五本,很厚。女孩捧五本书有点吃力,我帮她拿了两本。磕巴男送我们到班级后就离开了,我看班级里只在角落有两个空位,我们两个人坐过去。
这是一间跟高中一样的教室,大约坐了不到四十人,我们来时正在上课,是一个戴眼镜的女老师,很像英语老师,但不教英语,她没管我们,自顾自讲着。黑板上画着口腔解剖图,她在讲人为什么会打呼噜,要用什么办法才能有效地改善打呼噜。
我扫了眼前桌的书,翻出一本教材,封面上写着《论改善危害猫咪的十大恶习》,现在讲到第三章改善打呼噜,流口水在第四章,下节课就能讲到了,我发誓要认真听。
讲了有三十分钟才下课,老师离开教室,我朝前桌要了张课程表,把它抄在课本空白页上。课程上五休二,课很满,但松弛有度,我很满意。今天上午还有一节课没上,叫《猫猫按摩》。
上课的是一个老头子,头发花白稀疏,顶着冬天的地中海。他带来了教学用具,十多条猫,每两个人共用一条。女孩和我用一条黑猫,很黑,像被墨泡过。
黑猫趴在桌子上,对我说,新学生?
我说:“是的,您好猫老师。”
黑猫老师不搭理我,闭上眼睛,摊开四肢,生无可恋。
它们就是梅所说的犯错的猫咪,每一只猫咪都戴着两种颜色的项圈,分别是绿色与黄色。我举手问老师项圈颜色的含义。秃头老师看向我,知道我是新学生,耐心解答说绿色项圈代表轻罪,黄色项圈代表重罪但态度良好,还有一种颜色是红色,是犯重罪还态度恶劣的猫咪会戴的,一般是无期徒刑。
我面前的猫老师是绿色项圈,它很乖,眼睛一直没有睁开。讲桌上也有一只猫咪,戴黄色项圈,老师双手打开,缓慢贴合猫毛绒绒的身体,他边摸边讲解,猫咪哪里最敏感,哪里禁止摸,哪里摸了会让它舒服。
我学到了猫咪的尾巴不能摸,怪不得在家我摸猫的尾巴,它会咬我。
课程结束后,磕巴男找到我们,带我们去了食堂。食堂人很多,猫也很多,我看到了上堂课的黑猫老师在拿叉子怼鱼干吃。吃完饭,他要带我们去寝室,女寝在东边,男寝在西边,他先送女孩,让我在食堂门口等他。
很多人吃完饭了,陆续离开食堂,其中青年男女居多,大概都像我一样因为实习不及格被送进来。
从我这个位置,能看到操场,它被铁栅栏分出一块一块,每一个区域都不同,有打篮球的,有踢足球的,还有充气城堡,旋转木马。
天色擦黑,风凉凉的,食堂的人流渐消,三三两两的学生与猫散步在街边,我心里突然涌现一种奇异的感觉,想看一看这里。毕业小半年,我从未走出房间,美其名曰是待业,其实连一份简历也未投过。我错过了国考、省考,各市的教招考试,我只是一味地躺着,别人问我你还在待业吗,我只会用一点羞愧告诉他,我已经在努力了。
我沿着水泥路,走进一片小树林,有两只猫咪在长椅上亲昵,鸟在叫。我看不到鸟在哪里叫,我猜那是杜鹃,它发出一连串的“布谷”声,从近渐往远消散。
林子里不止一对情侣,有人有猫,坐在长椅上,靠在银杏树干上。他们真亲昵,银杏树叶渐黄,我踮脚摘掉一片最低的叶子,穿过林子,汇入主干柏油路。
黑完全蔓延了,柏油路两旁的路灯亮着,吐着柔软的针,我想起王小波的《绿毛水怪》,里面写晚上的路灯,像大团的蒲公英浮在河道上。写得可真美呀,我忘不掉在高中夜晚的被窝里打手电看书的时光。那时我没有毕业,没有被关在房间里半年只吃泡面。
四
班主任找到我,责怪我怎么不等他。我跟着他穿过柏油路,到了对街,那有一栋黑色的建筑,是男生宿舍楼。进楼,门口有一道闸机,班主任在荧光屏幕上输入几串数字,让我站过来,录脸。
我们坐电梯上六楼,走到606,这是我的宿舍。打开门有一只狗在舔腿上的毛,班主任对它说,开心,你照顾下他,新人。开心瞪着一对杏形眼睛看着我,是你呀。
我也说,是你呀。
班主任见我们认识,于是关门离开。
开心说你是没及格吗?
我摊开手,这显而易见,“可你怎么来这,这是猫咖。”
开心说,“我是教官,带长期班军训,你们短期班没有。”
“你是一只狗,在猫咖上班?”
“不不,这是兼职,我在公司上班,你舍友在我那上班。”
这是一间五人寝,四张上床下桌靠着墙,一张单人床放在窗台边,很突兀。只有单人床空着,我自顾自地坐在空床上,开心递给我一瓶酸奶。
单人床只有一张床板,是四张大木板拼成的,坐在上面一晃一晃,发出病入膏肓的咳嗽声。我没有行李,磕巴男没问,我也没说,我打算就这样睡上一晚。
喝完酸奶后,我感到困意,躺在床板上渐渐睡去。在后半夜,我被歌声吵醒,“苍茫的天涯是我的爱……”
这是凤凰传奇的歌,儿时妈妈的手机铃声就是它,每当响起熟悉的歌声,久久无人搭理,我就喊,“妈,接电话了!”妈妈会从厨房里走出来,边走边在围裙上擦手。
我看一眼手表,光线太暗,猜不到时针停在哪里。寝室里只有我一个人,开心不在,我推开门,跟着歌声走。歌声把我带到卫生间,掀开帘子,开心与一群猫围坐在一盆火前,旁边放着一个小音响。
开心见我醒来很惊讶,“你怎么醒了,我在酸奶里加了安眠药。”
我更惊讶,“你干嘛这样做呀。”
开心不理我,与一只三花猫对视,再转过头看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张龙赵虎给我绑了他!”
一只布偶猫与一只狮子猫拦住我的去路,它们拿着刀,呲着牙,很凶。我举起双手,态度诚恳,“老师不打学生,我投降。”任它们用麻绳绑住我的手与脚。
它们把我放在马桶上,万幸没关上门。
曲子换了,变成《荷塘月色》,它们像是在办凤凰传奇同好会。
开心穿着西装,领带是红色,很英武,“你应该在睡觉。”
“可我没有。”
“是呀,命运造弄人。”
“你们要做什么。”
“我们要逃跑。”
“你不是教官吗?”
“我不是要逃出学校,是逃出这个世界。”
“这个世界,我不明白。”
“是的,逃出这个世界,你不明白吗,狗怎么会穿西装呢。”
“我还是不明白。”
“一会你就会明白。”
开心不理我,坐回火盆旁。从我这个角度,能看到开心的背影,与一点点窜动的火蛇。开心拿着一根棍子,最靠前围着火堆的猫都拿着一根棍子,他们把一个黑乎乎的圆东西插在棍子上。
我仔细看了很久,认真辨别黑乎乎的物体。
我昏昏欲睡,在几近睡着时,一声爆炸声,使我立马惊醒,开心在我的眼前变成了一堆爆开的绿色果冻,狮子猫是红色果冻,还有几个飞溅的巧克力,我馋了,这味道会很好。
随之而来的冲击波砸晕了我,醒来后我就坐在医院的床上,接受工作人员的审问。“好了,我已经把自己知道的说完了。”我摊开手,很无奈,他们在这里有三个小时了。“这就是你的经历?与一群宠物炸掉卫生间。”他拿着小蓝本,写着什么,看样子不相信我的话。
我感到口渴,不想再解释,在床上翻了个身,用被子蒙住脑袋。
在住院一周后,猫来接我了,捧着一束花,是耐热的蓝星花,有着淡蓝色的花蕊,花瓣的蓝色比花蕊更深,它的香气近似红烧牛肉面,我有点饿了。猫很不客气地坐在我的腹部上。
猫说,你实习期合格了,等出院去办工作证。 我感到开心,腹部不再痉挛疼痛了,猫开始翻床头柜的抽屉,里面有几块烂掉的宠物形状的果冻和巧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