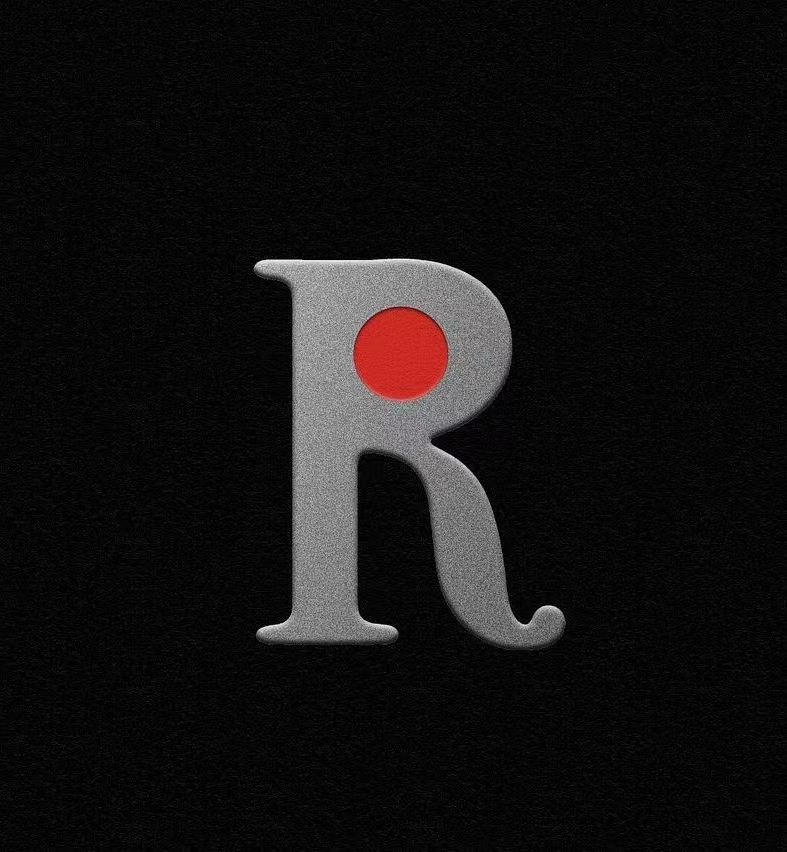失去音讯数十年的父亲,突然来到了这个家里。船只、海浪、阵雨,这样一幅景别里,父亲、儿子、孙女,缓缓贴近了一些。
父亲站在院子里,嘴里叼着一根烟,眯起眼睛,拍打身上的泥土。他的光头上长出稀稀落落的发茬,经过一下午的风吹日晒,全都打了蔫儿。太阳在溃退,墙壁的阴影从下到上侵占着父亲的身体,现在在腰间,不久之后将全面占领父亲。
几年前,他第一次见到父亲,也是这样的光头,发茬更坚挺一些,比现在胖,皮肤白皙,不像长期从事户外工作。这跟母亲说的有出入,不过他早已过了拿母亲的话当真理的年纪。当初自己居然对母亲的话深信不疑,想想也蛮可笑。
父亲将那双布满泥垢的胶鞋扔到向阳的墙根下,一只委在地上,一只倒伏下来,父亲没管它们,赤着脚,窝起脚心,身子左右摇摆,样子像在冰上行走的企鹅。走到屋里,将鱼篓交给母亲,从中抓出一只什么,看了一眼正在里屋写作业的彤彤,回到院子中央的阴凉里,坐在马扎上,抬头看了看天——一只燕子从院子上空划过,又把目光投向他,有些腼腆地笑了笑。他躲开父亲的目光,转身进了屋。
很多年前,母亲告诉他,父亲乘着一艘渔船出海,同行的还有十几个同伴。那艘船有他学校那么大,甲板上摆着很多鱼缸,他们捕到鱼后,放进鱼缸里,为了避免不同鱼类互相残杀,每种鱼都有专属鱼缸。盛鲸鱼的鱼缸最大,大概有学校教学楼那么大,鲨鱼鱼缸次之,面积也相当于一个篮球场,等到所有鱼缸都被装满,他们就会返航。他等了很多年,父亲一直没回来,他开始怀疑母亲。
母亲说得有鼻子有眼,不容他质疑。那时她二十啷当岁,还不认识父亲,有一天心血来潮,跑去海边捡贝壳,离海岸尚远,就看到海面上缥缥缈缈,浮着一层薄雾,像一口热气腾腾的蒸锅。走到近前,发现雾里面隐藏着一个巨大的灰色的影子,隐隐似有轰鸣之声从那个方向传来。母亲年轻时胆子大,她脱掉鞋子,挽起裤腿,向海里走去。她之前来过这片沙滩,退潮时可以蹚水一百米,水只没过小腿肚,这次她只走出五十米,水已经超过膝盖,而距离那个灰色的影子看起来还有很远。
她决定游过去。那是个夏天的午后,天有些阴,海水冰凉刺骨,她奋力游着,没一会儿就感觉身子僵硬,四肢不听使唤,此时海水深度早已超过她的身高,而她与那个灰色影子的距离似乎并没有拉近,她开始后悔自己的冒失。每划一下都要使尽全身的力气,终于,她再也划不动了,意识也开始模糊,这时候,她听到雾中传来二胡声,她想这可能是人之将死时产生的幻觉。在她失去意识之前,她看到一条小船冲破浓雾,像一只燕子,向她飞驰而来。他的父亲就在那条小船上,他救了她,把她带进雾中阴影,那是一艘巨大的船,当时还没有完工。她留在了船上,直到他出生。
在他一周岁时,船造好了。父亲与十几名同伴出了海。这个故事伴随了他几乎整个童年,升入初中后,像很多青春期的孩子一样,他开始怀疑一切,当然包括父亲的真实性。面对质疑,母亲不得不一次次填补关于父亲的细节,以佐证自己所言非虚。比如那艘船的样子,大概有一座山那么大,是用精铁铸成的,甲板刷成绿色,而船舷则是红色,样子也有些怪异,不像普通的渔船,整体方方正正,如同一个巨大的盒子。船舱有六台两层楼高的发动机,船尾共安了十个篮球场大小的螺旋桨,以保证船舶的动力。比如父亲天生的烟熏嗓,唱起歌来很好听,最拿手的是郑智化的《水手》,唱得比郑智化更具沧桑感。另外,父亲擅拉二胡,尤精《赛马》,琴弓一抖,真有如一匹银白色的骏马跃出海面,踩着浪头,朝听者奔腾而来。
那张黑白照片成为母亲关于父亲的叙述唯一的证据,他坐在椅子上,跷起二郎腿,二胡支在膝盖上,一手扶琴弦,一手拉琴弓。他的眼睛盯着天空,嘴角微翘,看样子十分陶醉。他当时没在船上,他的身后挂着一条横幅,上面写着,石家疃村文艺汇演。据说石家疃是父亲的老家,那里离海很远。
他第一次见到父亲时,彤彤已经出生,会跑会跳会叫爸爸了。母亲给他打来电话,要他回趟老家,当时正是秋收时节,他以为母亲一个人忙不过来,当即请了假,驱车返回。他进了屋,发现桌上倒扣着几只汤盆,母亲和一个男人相对坐在桌旁。那个男人垂着头,灰白发茬对准他,像随时准备发射的箭矢,母亲的模样拘谨,向他介绍那个男人时,她的声音干涩,发出机器缺少润滑的格格声。她说,这是你爸。那个男人抬头望向他,很机械地点了点头。气氛有些尴尬。
他早过了对父亲充满幻想的年纪。父亲跟照片上不大一样,仔细辨认,依稀又有些相像,随即觉得眼熟,似乎在哪里见过——像是每天在上班路上都会碰到的环卫工,又像棉纺厂门口修车的大爷,还像坐公交遇到的一名老者,他还给其让过座儿,对方向他表达了感谢。再看,又都不是。他确信,三十年来,从未见过这个人。
他把头扭向母亲,母亲脸色红润,说话磕磕巴巴,不是跟你讲过吗,你爸出海了嘛,现今回来了。一边说着,一边取走汤盆,露出下面的菜肴。他听到父亲小声说,对,出海。他一个字都不信。他看着那个男人,男人的目光躲闪。这个自认是他父亲的人,之前或许一直在蹲大牢,他的谦卑,还有他的发型,似乎都可以证实他的猜测。
他没能说服嘴巴喊出爸爸,他觉得应该给它点时间。三十年来,这个词第一次与某个具体的人联系起来。几年过去了,他习惯了叫父亲“诶”,更难改口。他逮到那么两三次机会,试探地询问父亲,那艘船是什么样子,每次父亲都回答得磕磕巴巴,好像背诵没有记熟的课文,他就更加确信自己的猜测。
父亲再次走进屋,四下瞅瞅,换上拖鞋,在彤彤面前摆弄起手里的东西——是一只海螺,等到彤彤抬起头,父亲又走到院子里,站在水龙头下冲脚,水流砸在他的脚上,碎成珍珠样。他冲脚的时候头扭向一边,打量着院子正中那棵石榴树。树一人多高,身材纤细,应该刚刚栽上不久,叶子有些泛黄,似营养不良。彤彤跟了出来,父亲脸上闪过一丝愉悦的光芒。隔着窗玻璃,他看到祖孙俩蹲在地上,一起盯着那只海螺,父亲用手碰了碰它,海螺生出一个头和几只脚,仓皇爬动。彤彤先是惊叫,随后大声笑起来。他想,不就是一只寄居蟹吗。
这之后,彤彤总是跟在父亲身后,一口一个爷爷地叫着。父亲起初还有些腼腆,不多久就跟彤彤有说有笑起来。晚饭后,彤彤拉住父亲的手,央求明天带她一起赶海,他在一旁阻止,你去了只会添乱。父亲却一口答应下来,令他暗生埋怨。
第二天,彤彤一大早就嚷嚷着,赶海喽,赶海去喽。父亲说,要等下午退潮。他知道再难阻拦,到了下午,只好跟随祖孙俩来到海滩。
潮水退得很快,不过半小时,就在沙滩上留下一道黑褐色的阴影。他抓紧彤彤的手,站在岸边,父亲赤膊,穿着连体胶鞋,把自己挽成一座拱桥,一边艰难地迈着步子,一边在泥沙里翻找。偶尔找到一只螃蟹,抓在手里,在脚下的水坑里涮涮,扔进背后的鱼篓。
他想起自己十来岁的时候,还钟爱大海,经常罔顾母亲的禁令,一有机会就溜到海边。涨潮时,坐在岸边,看着浪头接连不断从远处滚到脚下,直到淹没双脚。他的目光锁定大海深处,很多船在视线里来来往往,却没有他期待中的那一艘。退潮时,他脱掉裤子,只穿着裤头,走进沙滩,一路跟随着潮水,希望它们一直退下去,直到看到那艘船。海面上不时有海鸥掠过,偶尔发出的鸣叫,总让他觉得是在向他发送关于那条船的讯息,他懊恼自己无法听懂鸟语。有白鹭站在不远处,双脚栽进水中,双目凝视着水面,简直像一尊雕像,突然将头插入水中,叼出一条小鱼,快速吞咽下去。他摸起一块石头,投向白鹭,在心里向它发出指令,但白鹭不为所动,等他稍微靠近,猛地扇动翅膀,飞走了。
如今这片沙滩已很少再见海鸥和白鹭了。
彤彤拎着一只白色网兜,里面装着粉红色的胶鞋,赶海用的铲子和小桶。购于岸边商店,说是商店,不过一间简易房,门口支着一把巨大的遮阳伞。没有顾客,店主戴着墨镜,瘫在太阳伞下的躺椅里,不知睡着了还是醒着。彤彤选好,父亲争着付款,态度坚决,一共95,父亲嘟囔了句,贵死了,还是扫了付款码。
天阴起来,大片大片鳞状的乌云阻塞在空中,像是堵车的路口,太阳被彻底遮住,难以寻觅。海和天都灰蒙蒙的,海上漂浮着塑料袋包装盒之类的生活垃圾,不断被冲击到岸边,又被下一个波浪带回海里。附近在建码头,岸上矗立着一排橘色吊机,头部几乎抵达云端,看样子相当威武。他想到恐龙。海面上停着几艘船,想来是配合码头建设的。他没看到人。
父亲灰色的身影很快同沙滩融为一体,像一块亘古存在于此的石头。每抓到一只螃蟹或者牡蛎,父亲就会直起腰,拧着身子,向他和彤彤挥手。彤彤换上胶鞋,试探了几次,又缩回脚。他拉着彤彤的手,一直没松开。
他再次看向吊机的位置,那里水深一些,鱼也多,之前父亲在那儿下过一张抬网,十平米见方,吊在一根竹竿上,涨潮时下好,退潮时压住竹竿尾端,将网抬起,一次能捕不少鱼。父亲做这营生几年,直到码头开建。如今无法下网,又迷恋上赶海,几乎每天必至。
父亲翻起一块石头,发现了什么,拿在手里挥舞,说,彤彤,过来看看,爷爷找到啥。离得远,他模糊看到一个灰色的影子在父亲手里晃动。彤彤挣脱他,跑进沙滩,身姿雀跃,如鱼入水。他还是站在岸边,手中没了持握,心跟着空了一下。耳边又传来王淼的威吓,彤彤要是再有个好歹儿,我跟你没完。他知道,彤彤判给他,王淼心有不甘。
父亲摊开掌心,向彤彤炫耀,你看,海胆,可以生吃的,鲜得很。双手将那个黑不溜秋的毛球撕开,露出白色的嫩肉,示意彤彤张嘴。彤彤还在迟疑,他在岸边喊起来,别吃,有细菌。彤彤和父亲同时看向他,他重申,别吃,听到了吗,别吃。父亲把海胆塞进自己嘴里,用力吸吮,海胆皮贴在他的嘴巴上,像一蓬胡须,冲他挑挑眉毛,似在示威。他坐下来,眼睛贴在彤彤身上,将她紧紧箍在视线里。
彤彤几个月大时,坐在婴儿车里,被带去超市,他和王淼为奶粉的品牌争论不休,再回头,不见了彤彤。找了一圈,没寻见,王淼哭起来,不停捶他后背,他也急得冒火,汗珠从额头唰唰掉,眉毛就成了下雨的屋檐。惊动了超市,发广播,调监控,发动全体员工一起寻找,最终在二楼到三楼的步行梯拐角处发现了彤彤,婴儿车倒地,彤彤伏在瓷砖上,攥着一只苍蝇,正往嘴里填送。所幸没受伤。王淼将彤彤抱在怀里,再不撒手,他靠上去,想摸摸彤彤的脸蛋,王淼却背过身去。监控里显示,他们争吵时,一名红外套中年妇女从他们背后推走了婴儿车,听到广播寻人,将孩子塞入步行梯,自行逃了。从此,见到红外套,他都要多看两眼。
前年,彤彤上小班儿,一天放学,他去接,返回路上,见一药店,想起近来喉咙不适,拐到药店门口,停下电动车,嘱咐后座上的彤彤,等他一下,去去就回。原想不过一两分钟的事,付款却要排队,眼睛一直盯着门外,不敢让彤彤脱离视线。一辆灰色面包车靠过来,停在电动车前,他扔下药,箭步冲出去,面包车一颤,又发动起来,掉头走了。极有可能是人贩子。
如今,彤彤已上小学,走路稳健,擅跑能跳,每次外出,他都会想起当初把她独留在电动车后座上的情景,彤彤嘟着小嘴,怨怼地看着他。他一度怀疑它的真实性,但它固执地镂刻在他的脑海里,挥之不去。
彤彤跟在父亲身后,不时蹲下身子,又迅速站起来,样子像小鸡啄米,一会儿就超过了父亲,逐渐走近大海。海水推搡着白色的泡沫,不停冲刷沙滩,一个浪头扑上来,没过彤彤的胶鞋,彤彤兴奋地尖叫。他蓦地担心,喊,后退,后退,离水远点儿。彤彤却像没听见,用力踩起海水,沿着岸边来回跑动。父亲朝他摆摆手,示意有我呢,走向彤彤。爷孙俩并排站定,都面朝大海,父亲伸出手臂,向远处指指点点,彤彤也抬起胳膊,向父亲确认着什么。他从两人的指尖虚拟出两条线,一直延伸,在海面某个点交汇,那里颜色稍深一些,方方正正的,像一个盒子。他陡然一惊,眨眨眼,盒子成了椭圆形,大概是一座岛。
小时候,他长久站在海边,盯着远处某一个点,眼睛逐渐酸胀,朦朦胧胧的,海上出现一个红绿相间的方形物体,等他努力将目光聚焦,那物却消失不见了。数次之后,等它再次出现,他让眼睛保持之前的状态,移动双脚,向它靠近。可是他和它距离怎么也无法缩短,他继续走,直到海水灌入鼻腔,他赫然惊醒,忙倒退回来。后来,他学会了游泳。
天愈加阴沉,乌云压下来,几乎覆盖了海面,风在海和云的缝隙中扯动,将大海深处的腥味输送到岸边,类似衣服在潮湿的房间里储放多年的味道,他忍不住作呕。可能要下雨了。父亲和彤彤的兴致没被天气影响,仍在不懈地翻找着螃蟹和牡蛎。他叫出彤彤的大名,三个字刚出口,又被风塞回嘴里。
雨下起来了,大颗雨滴掼上沙滩,在他脚下砸出一个个坑洞。父亲拉住彤彤,往岸边跑,彤彤被拽了个趔趄,却大声笑起来。他双手遮在额头前,搭起凉棚,好让视线不被雨打断,仿佛目光能够在彤彤身上形成一层保护罩,以阻挡雨水的侵袭。彤彤跟在父亲身后,胳膊被扯得笔直,她不得不加快步伐,她喊着,爷爷慢点。父亲却没有放缓脚步,在雨的催促下,反而跑得更快。意外就是这时候发生的。彤彤被石头绊了一下,身子向前俯冲,笔直摔进泥沙里。他听到一声闷响,搞不清楚声音来自外部碰撞还是彤彤体内。他叫了出来,想冲过去看个究竟,双脚却像钉死在岸上。父亲惊恐地看了他一眼,慌忙将彤彤扶起。彤彤前胸和半边脸上沾满淤泥,她愣愣看着他,静默了一会儿,哇一声哭出来,泪水随之涌出,在脸上冲出两道沟壑。
他的心再次揪起来,向前迈动步子,脚踩进沙里。雨点打在身上,如战鼓擂动;海水涌动,辛辣刺眼;终又退缩下来,收回了脚。父亲抱起彤彤,彤彤不再哭,头伏在父亲肩上,后背偶尔抽搐一下。到了岸上,他去抱彤彤,彤彤却搂住父亲的脖子,怎么也不撒手。父亲说,别站着了,找个地方避避雨。
他们跑到海边商店,全身已经湿透。彤彤像是一棵小小的枯树,身上的泥巴树叶一样片片脱落,仍有两块顽固地贴在脸上,他伸出手,试图帮她擦掉,被她一把挡开。他的心一颤,生出一股怨怼之气,瞧向父亲,父亲咧着嘴,无谓地笑着。他们站在巨大的遮阳伞下,雨水暴躁地拍打着伞面,从伞的边缘倾泻而下。父亲透过雨的帷幕望向大海,目光被雨水稀释,轻飘飘地蔓延。他跺着脚,裤管贴在大腿上,像绑着两道枷锁;彤彤瑟缩抱紧双肩,样子更加狼狈。他看向店主,店主坐在门口的藤椅上,双指间夹着一根烟,不时往嘴里填送。他说,老板,有衣服卖吗?童装。店主喷出一口烟,笑起来,我这又不是服装店,哪里来的衣服呦,泳装要不要?
店主的玩笑令他不快,他想回击两句什么,店主却已站起身,走进店里。一会儿,踅出来,怀抱两件衣服,烟叼在嘴里,只剩烟头,说,找了一套校服,我儿子的,给孩子换上。下巴扬起来,凌空向他和父亲戳了戳,又说,你俩大老爷们儿,身体素质好,忍忍吧。父亲连声道谢,接过衣服,递给他,朝门内指指,说,进去换。
房子有两间,外面是店铺,里面是起居室,他把彤彤领进起居室,蹲下身子,要帮她脱衣服,彤彤猛烈摇头,说,我自己换,不用你管。把他推出来,从里面关上了门。他愣愣站在门外,想她不过一个七岁的孩子,却已经有了性别意识。如果王淼在就好了,她会更乐于接受王淼的照顾。如果当初王淼提出离婚时,他稍微表现出一点挽留之意,可能他们仍做着夫妻,共同抚养着这个孩子。现在,说什么都晚了,王淼已经再嫁,马上要生下第二个孩子了。
衣服肥大,罩在彤彤身上,像是舞台上伶人的戏袍。父女俩走出来,父亲已坐在马扎上,鱼篓顿在双腿间,跟店主聊得热闹。另有两只马扎摆在父亲旁边,他和彤彤坐了上去。雨势稍有减缓,能看到海面缭绕的灰色的雾气,雾中似有一个巨大的影子,在轻轻抖动。他一凛,揉揉眼睛,影子不见了,雨水仍在敲着伞面,噼啪响。他听到父亲说,男孩子都淘气,很正常。你看我儿子,现在文文弱弱的,小时候别提多调皮了,他妈揣兜里十块钱,准备第二天买花生油,结果第二天,十块变九块,问他,死活不承认。他妈拖他去商店,一问,一早他才用十块钱买了一根冰棍,找回他九块。自然少不了一顿揍,却就是咬死不松口。
他讪讪低下头,彤彤碰了碰他的腿,说,爸爸,你偷钱,不是好孩子。他哑然,这事儿确是他做下的,是他少年时期的一个污点,挨打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的嘴巴丧失了对美食的欲望。他想母亲会跟他保持默契,严守这个秘密,却还是告诉了父亲。父亲说,不是偷嘛,调皮嘛,馋嘴嘛,你爸品行很好的。父亲努力为他找补,他不想承情,说,就是偷,犯了错误就应该受到惩罚。
店主说,只是偷拿十块钱,算什么大事,我那缺德儿子,假期让他看个店嘛,老大不乐意,撺掇着来了,也不正经干,不是睡觉就是玩手机。说他两句,转头就跑了,晚上不见回来,一打电话,响两声,挂了,没一会发来信息,在去秦皇岛的车上。我想他哪来的盘缠,一翻抽屉,果然,钱都被顺走了,只给我留俩儿钢镚儿。说完,就笑起来,父亲也跟着笑,说,小子嘛,就是费力,正常。店主说,对呢,还是女娃省心。俨然和父亲成了知己,父亲说,就是,我这孙女儿,不是一般的听话。彤彤得了夸奖,脸上挂了笑,又不愿声张,努力把笑隐在嘴角眉梢里。
一会儿,彤彤把鱼篓拉到身前,伸手进去,在里面拨弄,突然惊叫一声,手迅速抽出来,在半空挥舞,手指上挂着一只螃蟹。他的屁股刚离开马扎,父亲已经抓住彤彤的手,两根手指一扭,螃蟹脱落。父亲抓着螃蟹,用力掼在地上,又踩了一脚,螃蟹在父亲的鞋底下变成黏连的碎屑,父亲说,敢惹我孙女,见阎王去吧。
彤彤眼眶蓄了泪,忍着没流下来。他拉过彤彤的手,手指肚上有道红印子,没肿,他往上面吹了口气,问,疼不疼?彤彤摇了摇头,没回答他,却对父亲说,爷爷,我没哭,乖吧?父亲把手搭在彤彤头顶,摸了摸她的头发,她的头发还湿着,打起绺来,在父亲手背上游走,像一条条小蛇。父亲说,乖得很。彤彤说,是不是比爸爸小时候乖。父亲表情有点怪异,偷眼看向他,目光被他捕捉到,连忙别过头,说,你爸还是有很多优点的,学习好,工作上进,待人真诚……他打断父亲,诶,别说了,我什么样您当真知道吗?父亲说,我怎么不知道?他从双唇间嗞出一声冷笑,诶,咱俩相处的时间有多久?五天,一个星期?两个手数得过来吧?为什么要骗孩子呢?父亲就沉默了,无声地望着大海。他不依不饶,说,您真的出过海吗?父亲的表情严肃起来,但在他看来,这不过是虚张声势,父亲说,怎么没出过?我还捕到过鲸鱼呢。彤彤拍起手,鲸鱼呀,它那么大个儿,您怎么抓到的?父亲把彤彤连同她屁股下的马扎端到自己面前,双手按在她的肩上,说,我就跳到海里,钻到鲸鱼的肚皮下面,你知道吧,鲸鱼最怕痒了,我用手轻轻搔它的肚皮,它就咯咯笑起来。这一笑不要紧,水顺着它的喉咙流到了肚子里,我不停搔痒,它不停笑不停灌水,结果身子就鼓得像个气球,漂在海面上,再也游不动了。这时我就用绳子拴住它的嘴巴,不让它把水吐出来,一直把它牵上岸。原本摊在躺椅里打瞌睡的店主突然睁开眼,嘟囔了句,吹牛不上税,又把头歪向另一边,继续打起瞌睡。
雨点裹了彤彤的笑声,落在遮阳伞上都变得悦耳起来。等笑声停下来,彤彤把头扭向他,问,爸爸,爷爷真厉害,你怎么就不会游泳呢?冷不防地,他的心被扯了一下,打个绊子,跌落下来,砸进腹腔,溅起一片回响。三年前,一家三口去游泳,王淼带着彤彤下了泳池,他只坐在岸边,双脚沾沾水,又缩到屁股下。彤彤套着泳圈,扑腾了一会,身子突然滑出泳圈,整个人沉下水去,王淼抓了一把,没抓住,急得大叫,呛到水,剧烈咳嗽起来。他在岸上,想立刻跳下去,双腿却不听使唤,僵在原地。彤彤被救生员救上来,发了两天烧,又活蹦乱跳。他以为这件事没在彤彤脑海里形成记忆,没想到,三年后,在这暴雨侵袭的海边,彤彤会脱口而出他不会游泳。事实比这更严重,他怕水,怕得要死。
父亲看了他一眼,拉住彤彤的手,说,不会游泳又不是缺点,很多人不会游泳,但可以当科学家,当飞行员。彤彤说,可爸爸不是科学家,也不是飞行员,他就是个卖房子的,我妈说他是个二道贩子。他愤怒地站起身,走进雨里,雨水从他头顶浇灌下来,他打了个冷战,缩回伞下,颓然坐在马扎上,说,妈的,这雨什么时候停?彤彤说,爸爸,不许说脏话。她看向彤彤,彤彤沉着脸,故意装作生气的样子,他的鼻子酸胀,说,如果我有一天出海了,十几年没回来,你会去找我吗?彤彤笃定地点点头,说,会的。他笑了。
十四岁,他溜上一艘橡皮艇,偷偷划出海,只驶出几百米,就被浪头打翻,掉进海里。他双腿踩着水,手臂搭在橡皮艇上,想把小艇翻过来,试了几次,都没有成功。后来,他的力气几乎耗尽,只好放弃。在他准备游回岸边时,他看到远处出现一条船,在海天交接处,露出红色的一角,方方正正的,正如母亲描述的模样。他激动不已,瞬间恢复了体能,奋力向大船游去。而那艘大船,似乎也在朝他的方向驶来。很快,他看到大船的全貌,红色的船舷,绿色的甲板,像一只巨大的鞋盒,随着海水起伏而上下颠簸。
小腿在抽筋,但他不想放弃,忍着痛,用双臂划水。大船已近在咫尺。他看到甲板上摆着很多鱼缸,鱼缸里游动着红色的鲸鱼,紫色的鲨鱼,还有一些色彩奇异却叫不上名字的鱼,他将嘴巴扬出水面,对着那些鱼呼喊,你们见到我爸爸吗?那些鱼被他的声音吸引,纷纷调转过身子,好奇地看着他。这时候,从鱼缸中间的通道里走出一名男子,虽看不清面貌,但他认定是父亲,他大喊,爸爸。那人似没听到,走到船边,坐下来,从背后取下二胡,悠悠拉起来。他再次喊,爸爸。那人拉得更加忘情,仰起脸,头颅打拍子般摇摆,他身后的鱼们也都随着二胡声翩翩起舞,甲板上霎时间霓虹闪烁。他第三次开口,却没发出声音,海水进入他的嘴巴,冲入鼻腔——在那一瞬间,他感觉海水并不是咸的,而是辣的,辣得他眼睛充血,鼻涕眼泪四溢,随后涌入胸腹,用力坠着他,他徒劳地打了几个扑腾,身子慢慢沉下去。
模糊中,他听到母亲的哭喊,他聚起全身的力气启动嘴巴,说,我爸呢?母亲哭得更加大声了,哭声中穿插进啪啪声响,母亲在打自己的脸。那以后,他再不敢下水,母亲也很少再提起父亲。他收回思绪,捏了捏彤彤的脸蛋,说,那我给你造一艘船。彤彤拍着手,说,好呀,好呀。将双臂撑开一个虚拟的无限大的空间,又说,我要一艘这么大的船。他说,好,想多大就有多大。父亲讨好似的说,我能加入不?他顿了一下,故意问道,您会什么?他期待父亲能够说出我在船上待了三十年,熟悉船舶的构造,或者类似的话,但是没有,父亲说,我会木工,还会电气焊,一定能帮上忙。他冷冷看着父亲,而彤彤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他,他略一迟疑,缓慢点了点头,说,要来也可以,工具得自己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