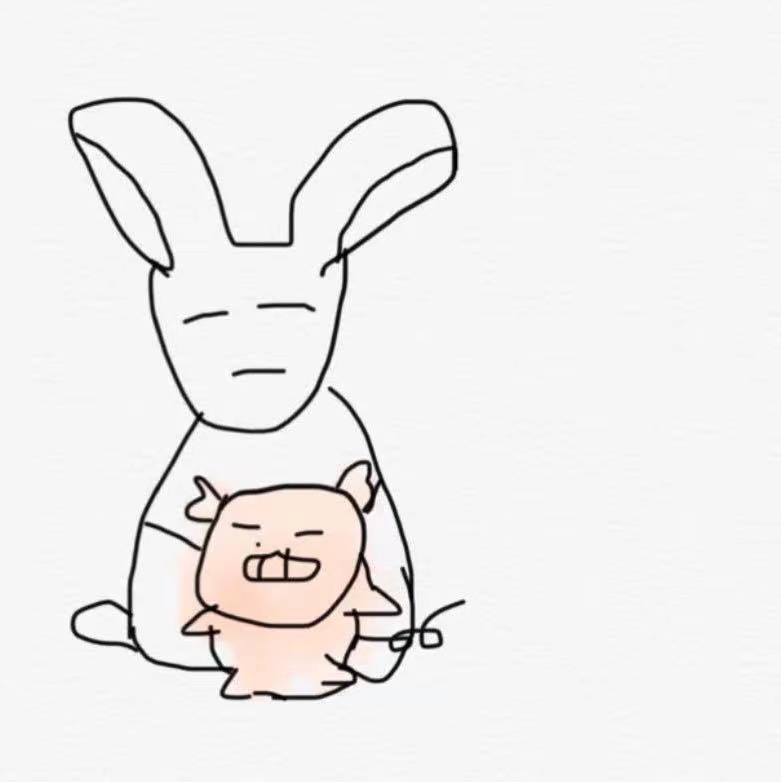生活的剖面往往都有最细密的纹理。
她们往山上开。同母异父的哥哥攥着方向盘,马叔坐在副驾驶,因晕车而沉默,母亲看向窗外,墨镜在反光,让人分辨不出目光的方向。路一直往后退,前面顶着一排重型卡车车队,哥哥放慢车速。有一个秘密藏在母亲胸腔里,肺癌,小细胞,正在像墨水一样扩散。只有患者被瞒着。
母亲问还有多久,哥哥低头,看了眼手机,说还得一个半小时。他们在半山腰休息,一个景区入口,马叔搀着母亲去卫生间,哥哥点燃烟,雨刚停,屋檐还在滴雨,几滴水珠飞溅到她脸上。她们的鼻子很像,大鼻头,鼻翼宽阔,话语急促时会不停伸展收缩。
他们又聊起那件事,有不止一人为其作证,但传闻在显露真面目前总会不停兜转。哥哥说少年宫有个练笛子的小男孩,一直高度近视,从仙游寺回来,两个眼睛变得炯炯有神,能一眼看到十几米高的苦楝树上趴着的蝉,哥哥又说他有个同学的老婆在医院X光照出来七颗胆结石,害怕开刀,就上了山,一下来,再去医院照X光,什么都没照到,胆囊光滑透亮,那七颗石头就那么无声无息地消散掉了。母亲和马叔从游客中心里出来,走向她们这边,哥哥放慢了语速,说,还有病友群里的李姐,她父亲从仙游寺回来,癌细胞就不再继续生长和扩散,如今已经十一年了。
母亲说去景区里面转转吧,坐了这么久车。哥哥为难,怕仙游寺的僧众晚点就休息了。两人争了几句。马叔站出来劝母亲,说再忍一会儿就到寺里了,先把正事办了,哥哥皱眉头,说去景区里转转也挺好,要不了多久。
马叔搀着母亲走在前面,她们放慢脚步跟着。山路不陡,沿途有锁链连成的扶手,尽头有一座瀑布,据说很壮观。这老头,哥哥小声骂一句。她没接话,马叔穿了双劳保鞋,鞋底因为长期外八被磨得内高外低,哥哥讨厌这个人,她还好,可能是因为接触时间短。两个月前,她从深圳回来,马叔从高铁站接她去医院,一路挂着笑脸,不停说话,一个谄媚的人,她判断。他和母亲跳广场舞认识,鳏夫,子女都不在本地,相处没多久就搬进母亲家里,车工退休,工资不会太高。哥哥觉得他是有备而来,一直想拆散,闹了几次,母亲落了泪,哥哥也心软下来。后来医院出了检查结果,马叔在身边好歹多个人分担一下情绪,哥哥也就不再逼他走了。
她和母亲其实不熟,双方都很难直视对方眼睛说出那些难为情的话。她是母亲三次婚姻的一部分,从来没成为过主体。高中毕业后,她往南边去,最初几个月双方还有联系,后来渐渐淡了。有一年,她谈成一笔大单子,拿到提成和调休假,不知道该去哪,就回了家,在楼底下看见阳台延伸出的晾衣杆上晾着一床洗得发白的蓝色被单,盯着看半天,终于想起那是她小时候盖过的。她有恨意,延绵不绝的模糊着的线,看不清楚头,不知道该恨谁,眼泪落得很轻。继父从阳台探出身子来收被子,她转过身,离开了,之后再也没回过家,直到这次。她接到哥哥的电话,辞掉工作,坐火车回江城,沿途经过不少长隧道,手机信号被隔开,只能看着倒映在车厢玻璃上的脸发呆,她有皱纹,挤在五官的间隙里。她想起曾经的男友,她没能在那个男孩的欲望开始衰败之前嫁给他,所以她们都被时间汰换掉一部分肉体,直到现在,她终于有机会为自己许愿。
她想要母亲的房子。
那是母亲第三次婚姻时买下的房子,有她和哥哥的房间,三室两厅,贷款已经结清,现在值不少钱。她的房间保留着原样,书桌上的书和文具被收进箱子里,床上覆着一层薄薄的罩布,她掀开一角,坐下,感到悲伤。她在深圳租的单间是不规则的形状,所以所有家具都被斜放着,没有规律,像是暴风雨后的甲板。她的室友们一直在变,只有一个女生被她记住。她决定离开深圳的时候,去挨个敲室友的门问有没有闲置的大号纸箱能让她装点零碎寄回去。女生打开门扉,转身回房间深处去搬纸箱,房间地上都是粗颗粒状的沙子,女生走过时,袜子的条纹让它们扬起、落下。箱子很大,足够罩住她蜷缩着的身体,黑暗里,她能摸到沙子坠落撞出的磅礴震动感,感到安心,后来,在医院陪床的某一天,她突然意识到,女生房间内铺满的是猫砂,但在那间房子里租住的两年时光里,她从未听到过猫的声音。
母亲走不动了,他们在一座靠近溪流的亭子里休息。
游客很多,大部分是中老年人,哥哥去商店买拐杖,马叔和母亲靠在亭子边,佝偻着腰,看山上的茂密森林,水声清晰,偶有鸟叫,她问母亲怎么样,母亲抬眼看了眼她,没回答。马叔赶快接一句,你妈就是累了,没大事。她说累了我们就回去吧,这地方太潮,肺炎会加重,母亲说胡说,潮才能治病,不然为什么天天做雾化。哥哥回来了,拿来两根金属登山杖,递给母亲和马叔。马叔说不用,哥哥说买都买了,别瞎逞能,回头腰间盘突出再犯了,哪有人管你。马叔讪讪一笑,接过登山杖,挂在手上。
路过溪流,她们继续往深处走,中间路过两只野鸡,张开翅膀尾羽从山头滑翔过去,橘红色冠子像烧着了,石阶很滑,母亲精神却越来越好,一个人在最前面带路,马叔跟得很吃力。母亲说快点,看完瀑布还得赶快下山,趁天黑前去仙游寺,哥哥说已经冬天了,现在枯水期,不会太好看,母亲说好不好看这辈子也就看这么一回了,哥哥说等你好了再来看也不迟,母亲不说话,马叔接了句说等好了是得好好出去逛逛,到时候去贵州,去看黄果树瀑布。她脑子里突然冒出来一个问题,黄果树瀑布会有枯水期吗?仔细一想,又觉得是个傻问题,肯定会有的,黄果树瀑布也只是瀑布。雨又下起来了,她们在上山路中有山洞遮蔽的一截躲着,母亲坐在石头上,她盯着看。发根都是白色的,脸色发黄,脖子上的血管向外凸着,像纵横交错的道路。母亲剩下的时间还很长,她突然意识到,可能还有十几个月,肺癌会一点一点腐蚀掉她剩余的肉体和精力。山洞内聚集的游客越来越多,气氛变得温热,雨水在洞壁两侧往山下流,水声把说话声冲得混乱。哥哥和马叔站在山洞边缘抽烟,母亲和她藏在山洞中间,躲避水汽,目光都往洞外飘,过了几分钟,母亲先开口,问她深圳怎么样?她说挺热的,母亲问海边怎么样?她说风大,阴晴不定,母亲问准备什么时候回去。她想了一会儿,最后才回答,等你病好了就回去。
等病好了,母亲说,我去深圳看你。
山洞黑着,游客手机屏幕的荧光来回撞,哥哥和马叔在远处背对着她们,烟蒂的火光被烟雾向上拽着。妈,她叫一声,但还是没勇气说出来,母亲看向她,她咽下原本想说的话,问,和马叔怎么认识的。母亲嘴角有了弧度,像小女孩会泄露出的表情。母亲讲的和她从哥哥那里听到的大差不差,只是多了细节,很多繁复的细节,母亲讲到兴起的时候会低下头,像是在因把自己的情感公之于众而感到难为情。她想到自己的继父,在感情尚未破裂的那段时光里,母亲也是用这样的笑把他们夫妻俩和自己与哥哥分割开,可是哥哥是男性,能仗着不会被责罚硬闯进每一段母亲的亲密关系里,但她不行,母亲会嫉妒,所以她只能躲得远一点,再远一点,直到离开家。雨变小了。妈,她打断母亲,你得的是肺癌。
母亲直勾勾地盯着她,像是对她为何在此感到疑惑,没表情,她开始后悔,雨砸向石头的声音比呼吸声更轻,需要聚精会神才能体会到,人群开始向洞外移动,哥哥正转过头来寻找她们,母亲用手把一缕掉下来的碎发抚到耳后,一字一句地,坚定地说,不是的,我得的是肺炎。她终于得知,母亲早就知道了,只是靠着一根无比强韧的弦拴着希望,不会被任何事物剪断。她说妈,我说的就是肺炎。
他们继续往山上走,她已经几乎能听见瀑布的声音了,但有可能是错觉。雨后的森林味道很独特,淋湿的叶片把气味堆砌到一起,让人感觉渺小,木梯湿滑,哥哥不时回头看向走在队伍最后的她,她没被触动。有一年,哥哥来深圳谈客户,夏天,她们一起吃饭,哥哥穿着件长袖衬衫,腋下部分有汗渍,吃完饭,哥哥主动提出去她租的地方坐坐,反正离高铁站不远。房间里,她坐在地上,让哥哥坐在床上,这间不带卫生间的小单间只有十个平方,彼此都很局促。空调打开,温度很快降下来,哥哥双手平放着,紧贴大腿外侧。这边确实热,哥哥说,多买点藿香正气水放家里,感觉不对就喝。她点点头,知道。哥哥又说,空调不要老吹,人会吹伤。她突然笑出来几声,但没说话,哥哥目光往窗外飘,天空被城中村的电线切分得七七八八。一个人在外面,一定要照顾好自己,哥哥说,有什么事,就跟我打电话。哥哥离开后,她盯着床上的那处凹陷发了很久的呆。半个月后,她突然收到快递,打开,是一个塑料空调挡板,夹在空调出风口位置就可以防止冷风向下直吹。她觉得没有必要,就一直扔在角落,直到搬家时才重新翻出来,拆开包装,一张红色纸片从里面掉下,她捡起来,看见上面印着好评返现3元。她把纸条塞回盒子,把挡板和其他杂物一起留在了那间房子里。
她想要试探哥哥对房子的态度,只是苦于编排语言。
她能隐约感觉到哥哥的错觉——自己只是一个不解风情的妹妹,因为敏感而时常陷入无法言喻的悲伤氛围里。他的战场都在正面,所以难以走向那些卑猥又复杂的想法,他不会意识到,血缘关系只是从脐带延伸出的脆弱枷锁,只要血液停止流动,就会立刻枯萎脱落。哥哥在台阶上站着,说让她走前面,她说走不快了,哥哥说那就走慢点。她知道他是好意,台阶很滑,如果她向后摔,他会接住她。她们擦身而过,哥哥的眼睫毛沾了水雾,狭长眼睛正往山下看,有媚态。我们小时候经常爬山,哥哥在身后说,这是谎话,她记得,只爬过两座。第一座是继父带她们去的,第二座是高中毕业的暑假,她整夜失眠,哥哥骑电动车带她在城里乱转,不知怎么就绕到一座山上,为了留足够的电回家,他们在半山腰就停下,透过一堆杂草看了会儿江城的夜景,灯光都聚在河的两岸,眯起眼睛看,像是不停闪烁的篝火。她曾在某几个瞬间对哥哥有过真情,但时间往后,悸动总会被恨意冲刷掉,日子再久点,就连恨意也不剩下了。哥,她想了想,问,你讨厌马叔什么?哥哥想了很久,她的袖子已经被锁链完全打湿,哥哥终于回答,说觉得跟爸比差太远了。她知道他说的是继父,她说,可爸和妈已经没有感情了,哥哥摇头,说那么多年,怎么会说没有就没有,她说,不会很突然吧,他们的感情是一点点消失掉的。哥哥不说话了。她鼓起勇气,说,哥,我准备留在这边了。她没转头去看哥哥的脸,哥哥的声音从后面传来,那是好事,离家近点,能互相照顾到。她接着说,我想搬回家里,哥哥回答,到时候找人收拾收拾。把水电重新修整一下。可她没有计划过真的住进去,只是想迅速卖掉,拿着钱去房价便宜的小城生活。哥哥顿了一下,补充,这事不要跟妈说,老太太年纪大,小心思多。她知道原因,但还是问,什么意思?
她听到哥哥的手拽住锁链,水珠被弹向四面八方,金属碰撞之后会有轻微的一声脆响,像是有什么东西被归零,她不知道是否别人也能听见。哥哥说小午,不管妈怎么想,我们都是一家人。她不由感到悲哀,母亲有爱过她吗?就算有,也没法影响现在的关系了,尘埃已经落定,她想说点残忍的话,来把哥哥的幻想戳破,但话到嘴边,还是说,我知道,你是我的家人。
他们终于能看见瀑布了,一面高耸山壁,水流贴着往下滑,薄暮般挂着,雾气蒸腾,仔细看能看见瀑布下光滑的石壁。瀑布落下,形成很大一个水潭,不少游客聚集在那边,他们在观瀑平台看了一会儿,决定去水潭那边转转。枯水期的瀑布很美。她突然这么想到,就这么不吵闹地飘下来,轻轻地撞到岩石上,碎裂掉。如果真能拥有一个自己的家,要怎么布置呢?可以打通几面墙,所有东西都光明正大地摆上台面,也许她可以找到一些爱好,买一架电子琴什么的,她很早就想学,只是过去从未有机会和空间展露自己的欲望,年轻快速流逝,她一直努力赚钱,可心里对于安全感的价标也始终再变,直到现在,她终于如此接近未来。她可以带男人回家,会告诉他们如何进入这所房子以及如何离开。她会拥有一个自己的卫生间,能坐在马桶上发很久的呆,不会有人打扰。她应该还可以剩下些钱,可以再买辆车,一定要是油车,只要加满油就能随时旅行,去那些总能在短视频上刷到的地方,没钱了就打打零工,任何时候感到劳累就能回到只属于自己的房子里。她颤抖起来。
去往水潭的路上会经过一座吊桥,吊桥很窄,标牌上写明一次只能两人通过,她拦住走在前面的母亲和马叔,说吊桥比较晃,哥哥扶着母亲,她和马叔一组,马叔答应,母亲抬着眼皮看她。她们先出发,马叔扶着吊桥边的绳索扶手,走得慢,她在斜后方跟着。她看见他的夹克袖口被磨出白色,polo衫从裤腰里掉出来,下摆摇晃着,藏青色秋衣往外漫出阴影。马叔,她问,你今年多大了。快六十啦,马叔回答,之前干过几年有害工种,所以提前退了。她也扶上绳索,攥紧,有水珠被碾碎。
马叔,她说,我们不希望你和妈结婚。
她把哥哥也算进来,但哥哥其实会同意母亲再婚的。不断重组的家庭总会诞生出像哥哥这样的子女,抓住一点善意就能塞进心里。马叔愣了一下,然后很快又换回笑脸,说没想那么多,这把年纪了,能在一起就很知足。她说,妈年纪大了,很脆弱,我们不能让妈受伤害。马叔笑着问,不会的,没人会伤害你妈妈。你,她放缓脚步,说,尤其是不能受到你的伤害。
马叔不再笑了,他转过身,和她对视。他的眼睛很浑浊,黑色瞳仁周围晕染着一圈褐色,马叔说,小午,你妈提过结婚的事,但我没同意。她停下脚步,吊桥摇晃着,水潭反射着夕阳。马叔说,我儿子在威海一个船厂上班,等陪完你妈之后,我就搬过去。在江城待了大半辈子了,好多地方都还没去过呢。她说谢谢你,马叔。他们走过吊桥,然后等待母亲和哥哥过来。
他们一起走到水潭,黄昏将近,光晖被不断打碎,荡漾着,让人眯起眼睛。她很高兴,一切障碍都被扫除,接下来,只是等待时间像推土机一样慢慢碾过就好,她不想去幻想母亲死亡之后的时光,但在此刻,却忍不住。母亲马叔和哥哥站在水潭边,一家人的模样,她走近他们,母亲坐下,盯着瀑布,问,那个传闻是什么样的?仙游寺的那个?哥哥望着水潭出神,不知在想什么。一个僧众,她回答,年纪很小的一个小孩子,他只要摘下叶子,再在河里浸泡一下,贴到病人眼睛上,就能治好病人。母亲笑起来,说这种你们也相信。水潭的另一边有一株桑树,正随风摇晃着,哥哥脱下鞋袜,淌着水走过去,摘下几片桑叶,又走回来。不去仙游寺了,哥哥说,我们自己来吧。哥哥把桑叶递给她,她接过,有些疑惑。哥哥解释,你是咱们家里最有灵性的人。她不禁笑出来。
她拎着两片桑叶,浸入水里,从水面上看,手也跟随光晕一起摇晃,溪水很凉,秋天的桑叶已经老了,筋脉并不随波逐流,小僧众为什么要把桑叶贴到病人眼睛上呢?她想,是想挡住什么吗?她把桑叶从水中提出来,母亲坐在石头上,往后躺倒,已经闭上了眼睛。她轻轻抖掉桑叶上的水分,然后贴在母亲眼睛上。太阳已经看不到了,水潭和瀑布都呈出一种青色,快要把石头和树木和人也都融成一团。母亲沉默着,哥哥和马叔也不再说话,只是望向瀑布,她走上前,轻轻把手放在母亲的双眼上。有一股温热的力量,正从桑叶里透出来,扎进她的手心。
我康复了。母亲说。她用手盖住桑叶,但没取下来。
母亲的手搭上她的手,缓缓坐起身,取下桑叶,然后从石头边站起来,说,轮到你了。她听话地坐下,石头下半部分很湿,粘稠的感觉开始缠绕她的小腿,她侧过身子,看见母亲正蹲在水潭边,用桑叶搅动池水,她回到仰躺的姿势,以免继续看着母亲枯槁的手臂。半空里,细小的虫群正在盘旋聚集,母亲从水边走过来了,有什么正在滴落,母亲来到她旁边,她闭上眼睛,母亲把两片桑叶贴在她眼皮上。桑叶很涩,沾了水后很有重量,像是两簇沙子堆上她的眼睛。那个从深圳寄来的纸箱在运送途中被撞烂了,被留在了快递站。她买过一包猫砂,偷偷在母亲的房子里倒出来过,猫砂落在地面上,不再弹起,没有造成任何震动。哥哥和马叔的声音都消失掉了,她只能听到母亲的呼吸声,嘶哑着的,有轻微的金属音,正往四周撞。等我病好了之后,母亲问,你想去哪里?
桑叶的粗糙向下渗透,她的眼睛正触摸着母亲刚才留下的泪痕,她闭上眼睛,等待着,但雨已经停了很久了。
离开这里,她说,永远也不会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