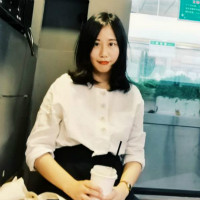并蒂而生的姐妹,在独生子朋友间生长。都说双胞胎是彼此的镜子,能照见所爱的,也会照见所厌恶的,她们的亲情由此衍生一丝裂痕。当被迫分开,她们因为相似而出现的裂痕因为差异而弥合,小说在两颗跳动的心之间,讲述一种悠长的治愈。
1
九十年代中期,我和父母生活在一条名为访冬巷的小巷里,那一带全是筒子楼,住的多是工厂子弟,邻居们彼此之间极为熟悉。
在出远门谈不上便捷的年代,这条巷子几乎就是我全部的世界,我最初对外界的认知都是在那里形成的。比方说,在那个年代,每家每户都只有一个孩子,报纸上叫我们这群人“特保儿”,我不知道什么是兄弟姐妹,也从未想过自己会有哥哥或妹妹。
正因为如此,茉莉姐妹的出现仿佛是刺进访冬巷的一道光,让我意识到世界上还有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茉莉姐妹搬过来的那日,我正坐在巷口,和奶奶一起卖花。我们主要卖三种花,分别是栀子、玉兰和茉莉。栀子属白,大朵,看起来素净,玉兰则带点淡黄,只要别在衬衣的领口处,一天都能散发幽香。而我呢,倒是最爱茉莉,因为茉莉听起来和“魔力”同音,在年纪尚小的时候,我总是幻想戴着茉莉花穿成的手串,变身为动画片中的魔法少女。
虽然看电视剧的时候,就知道世上有双胞胎的存在,但第一次看到长得那么像的两个女孩,我还是惊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她们穿着一模一样的白色裙子,梳着一模一样的麻花辫,穿着一模一样的黑色小皮鞋。即使是凑近了瞧,你也很难讲出她们有什么区别。像是拿着一张纸,送入复印机,然后机器吐出另一张一模一样的纸。
“我叫付茉。”
“我叫付莉。”
两个女孩同时向我伸出了手,我愣在那,有些尴尬,一时不知如何回应。我在想,会否我先握住付茉的手,付莉就会生气呢?
和我这种在家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占尽全部好处的独生“小公主”不同,在茉莉姐妹的家里,所有的东西都要一分为二——蛋糕得两个人吃,汽水得一人一半,就连父母的爱都得公平地剖为两半。但一碗水总是很难端平的,付莉常偷偷和我们这些人讲,其实她一点儿也不喜欢她的姐姐,她有时候恨不得家里只有她一个人,这样她就能拥有全部的东西和全部的爱。
事实上,作为家里唯一的孩子,我时常感到一种难言的寂寞。在很小的时候,我就学会了各种自己和自己玩的技能。在过家家游戏中,我能独自分饰三角,在无人的角落,我可以自言自语数个小时,我想,这绝不是因为我是双子座,而仅仅是因为在那样一个环境之中,你只能独自成长。
有时,我也会想,如果有一个哥哥就好了,这样我在学校里受欺负时,就会有人保护我。小伙伴问我,那如果是个弟弟呢?我说这可就麻烦了,他大概会在沙发下面塞满他的臭球鞋和臭袜子。
其实最好是姐姐,又或者是妹妹,这样我们两个人就能依偎在被窝里,看着窗外的月光,说些贴心的悄悄话。又或者,哪天被父母骂得狗血淋头时,我能第一时间找到一个倾诉对象。
人总是这样,喜欢幻想一种自己未曾拥有的生活,而当自己身处其中时,便觉得百般不好。
虽然和茉莉姐妹是同时认识的,但不知怎的,我和付莉的关系要亲近些,兴许是因为付茉看起来过于优秀了,她不仅会吹长笛,学习成绩也很好。她像是那种高不可攀的女孩,总是一个人拿着书,走在树林里,背诵着什么,而付莉呢,倒是更贪玩些,每天都和我手挽着手,聊有什么好看的动画片。
“其实我总是在想,家里就我一个就好了,这样我爸妈就不会总是拿我跟姐姐比来比去。你不知道那种感觉,太难受了,就像是一个参照物,只要你不如她,总会显得特别没有尊严。”
付莉站在一棵大树下,吃着彩色冰棍,向我抱怨着,我忽而想起,母亲讲过,在我之后,她还怀过一个孩子,但是当时政策不允许,她就把孩子流掉了。她总是反复地说,如果生下来,大概是个男孩,你就有个弟弟了。
尽管做独生女如此地寂寞,但一想起会有个不知道哪儿来的家伙分走家人对我的爱,我便觉得,寂寞就寂寞吧,寂寞总好过被人拿着疯狂比较。
升入初中后,我突然开始对自己的外貌在意,这表现在我不喜欢母亲给我挑的那些衣服,而希望自己独自寻觅自己觉得时尚、好看的衣物。除此之外,我还开始留意各种各样的镜面体——走在路上,遇到穿衣镜,我会停下来,打量一下自己。坐在车上,透过玻璃的反光,我也总会想着,自己的脸上会不会长出难看的青春痘。没事的时候,我也会随身携带一面可以塞入荷包的小镜子,一有空就拿出来,东照照,西照照。
付莉对我的行为很是不解,或者,换句话说,和我们这种镜子爱好者恰好相反,她厌恶所有的镜面。无论是在卫生间的洗手台,又或是商场的各类试衣镜前,她总是低着脑袋,尽量不把自己的脸展示于镜中。每当我问她为什么时,她总是摇摇头,冷着一张脸,避开我的问题。
“你讨厌镜子吗?”
“不是,我只是不想看到那张脸。”
起先,我以为是付莉对自己的容貌不满意,隔了很久我才发现,她是对自己的姐姐心怀芥蒂。在漫长的青春期,她总是花很多小心思将自己和姐姐隔绝开来,但旁人不在意,还是时常将她们姐妹二人认错。
2
有一年暑假即将接近尾声时,付茉失踪了,这引发了所有人的恐慌。大人们讲,最近出现了一个连环杀手,专挑穿红衣独行的女孩下手。付茉喜欢红色,常穿红色连衣裙,尽管我们告诫她注意安全,最好穿得素净些,可她不听。
一整个下午,我们在巷子附近不停寻找,也将此事汇报给了警察,然而付茉仿佛真空消失了般,不见踪影。
付莉咬着唇,在巷口徘徊,她穿了白色的衬衣和白色的裤子。我问,你不担心你姐姐吗?她摇了摇头,又迅速点了点头,很犹豫的样子。我又问,你姐姐的失踪不会跟你有关吧?她连忙退后几步说,怎么会呢?我没有你想的那么坏。
据付莉说,当天早晨,她和姐姐是一同出门的,去了市中心的新华书店看书,看着看着,她觉得十分无聊,于是嚷着回家,她姐姐和她一起回来后,说自己有点事,然后就离开了,结果到了深夜都没归家。
事情闹得沸沸扬扬,付家的大人心情也不好。大人心情不好,自然要拿小孩子出气,付莉就成了他们宣泄怒气的工具。一整个夜晚,我听到付莉在家中嚎啕大哭,她不停辩解着,但父母就是不理会她的求饶。隔了一阵,她从家中跑了出来,躲到了我家里,母亲虽然不想管其他人的闲事,但仍旧收留了这个可怜的女孩。
翌日清晨,警察上门,说他们在公园里发现了付茉,原来,付茉那时开始偷偷谈恋爱,和一个小男生约会,地址就选在公园,只是那天对方有事,没有去成。她独自在那等了很久,等到天黑,等到闭园,最后在公园角落的长椅上睡着了,这才没有回家。
虽然所有人都知道冤枉了付莉,但没有任何人对她道歉。
事后,我和付莉坐在梧桐树下,大声咒骂着世间的种种不公,我从书包里掏出一本从地摊上买来的杂志,翻到其中一页说:“这里头有个双胞胎的故事,很有趣,你想看看吗?”付莉一边吃甜筒冰激凌,一边说,她很累,懒得看字,让我把故事复述一遍。于是我开始讲,说是有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姐妹,他们同时喜欢上了一个男人,最终男人娶了姐姐。后来呢,有一天,妹妹妒火中烧,把姐姐推下了郊区的悬崖,然后自己回到了城市之中,假装是姐姐,和姐夫生活到了一起。就这么过了几十年,这个男的压根不知道自己的老婆换了人。
“或许这个男人根本什么都知道,只是他不说。”付莉咬着甜筒酥脆的外皮说:“等我长大了,就去另一个城市生活,离我姐远远的,离我爸爸、妈妈也远远的,这样就不会发生你说的那种恐怖故事了。”
事情的变化总是比人们想象中更快。付莉还没来得及将脑中所想付诸行动,现实就率先起了变化。在梧桐叶铺满访冬巷狭窄小路的季节,茉莉姐妹的父母准备离婚。
众所周知,若是家里只有一个孩子,父母要离婚,到了法庭上,法官肯定会问孩子是想跟着爸爸,还是跟着妈妈?而付家则没有这个烦恼,他们想好了,一个人带走一个。一切如此的公平,如此的自然,他们好像也没打算和这对双胞胎姐妹商量什么。
得知这个消息时,我正晃晃悠悠骑着自行车闯入小巷中,我看到付莉低着头,哭哭啼啼的朝巷子外走,我拦住她,问她想不想去文具店转转,她点了点头说“好”,又说,她要跟着她妈妈去另外一个城市生活,行李都已经打包好了。
“这不是刚好合了你的意?还把你的计划提前了?这样你不就可以跟你姐姐分开了吗?”
“不知道,这种感觉很奇怪,一开始我也很高兴,但想着要跟姐姐分开了,又觉得有些难受。姐姐对我不坏。”
付莉告诉我,在很小的时候,她对姐姐充满了恨意,恨到想杀死对方。有一次,我们在访冬巷里玩躲猫猫的游戏,她和她姐姐一组,两个人躲到了一栋废弃的老楼之中,她当时看到了一个柜子,还有锁和钥匙,她想着把姐姐骗进柜子,然后锁起来,这样姐姐就会从这个世界“消失”了。她这么想了,也这么做了,她指着柜子,把她姐姐骗了进去,然而,等了一秒钟后,她的姐姐忽然在里面朝她招手,说,让她躲进去,因为里面安全,不会被人发现。起初,付莉以为是姐姐拆穿了她的诡计,要对她进行报复,结果隔了一会儿,付茉一边咳嗽一边说:“算了,这里太脏了,你还有哮喘的毛病,我们还是躲到别的地方去吧。”那一瞬,付莉突然意识到姐姐对她是有爱的,她忽然觉得很羞愧。
3
付莉和她的母亲搬去了遥远的北方生活,而我留在了湿润的南方。我们没有失去联系,仍以书信方式联络着,交换着学校的趣闻又或最近喜爱的明星、电视剧等。付莉告诉我,虽然她离开了姐姐,但又多出了一个没有血缘关系的“哥哥”,那是她母亲的继子,脾气坏得很,经常拿她出气,打和骂都有过。每到这个时候,她就十分想念她的姐姐付茉。
在付莉离开的那段日子里,付茉还继续住在我家附近,渐渐地,我也和她熟悉了起来,每次和她聊天的时候,我总感觉,付莉还在这儿,只是换了一种性格。
初三的那个暑假,我因为看电视剧,幻想做个功夫少女,于是跑去学了跆拳道,在道馆,我碰见了付茉,她告诉我,她从初一开始练习,已经有一阵了,虽未在外面进行过实战,但在各项赛事中,倒也拿了一些奖。
离开道馆,我们结伴归家,走着走着,付茉突然问:“你坐过火车吗?”我摇了摇头。那个年代,父母忙于工作,我仅有的几次出游都是跟着学校去植物园或者烈士陵园,我没有去过外地,没有见识过外面的风景,更不敢一个人踏上旅途。
“我想坐火车去找我妹妹,然后把那个欺负她的男的揍一顿。”
付茉告诉我,事实上,她也和付莉通过信。有一次,她们两个人因为一起去看病危的奶奶,终于再度见上了面,在那个充斥消毒药水味道的医院走廊里,付莉趴在她的肩膀上哭了起来,说那个念高中的“哥哥”经常趁大人不在时,潜入她的房间,欲行不轨,虽然她对大人们讲过此事,但奇怪的是,所有人都不在意,说可能只是闹着玩的。
“你看过《两个小洛特》吗?”我从书包里抽出从新华书店买来的新书,递给了付茉。
付茉摇了摇头说,她没看过这本书。我指着书背面的介绍说:“这个故事挺有意思的,说是两个长得一模一样的小姑娘,从两个不同的地方凑到了一起,她们发现自己的生日和出生地也是一样的。聊着聊着,两人意识到她们是一对双胞胎,只是由于父母离婚而被拆散,于是她们想出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姐姐代替妹妹,妹妹代替姐姐,回到离异的父母身边,尝试让一家人破镜重圆。”
付茉捏着书,沉思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能把我书借我看几天吗?”我点了点头。
隔了三天,付茉讲,她已经偷偷买好了火车票,准备独自去看妹妹,无论如何,她要把妹妹从那种窒息的环境之中拯救出来。
付茉离开的那日,我从奶奶那要了一串茉莉花,认真地编成手环,给付茉戴上,边戴我边说:“茉莉花,有魔力的,希望你一路顺风。”
然而,我未曾想到的是,在我们这些小屁孩酝酿着干件大事,改变生活的走向时,大人们却早已在不远处将一切收于眼底。付茉还没有上火车呢,他爸就带着“大批人马”杀到,我也愣在那,感觉无地自容。付爸爸不仅带来了火车站的工作人员,还带来了我的父母。我妈提着我的耳朵就把我拽到了一边。大人们围着付茉,站成了一个圈,我在外头远远看着,感觉那像是一个人造的囚笼。
那日之后,母亲给我关了“禁闭”,不允许我再与外界来往,我成堆的漫画书被没收,也失去了业余玩乐的自由,道馆自然是不用去了,小伙伴们也见不上面,唯一的安慰来自付莉的信,那一阵,我们互为救生板,靠着写信来度过漫长而痛苦的时光。付莉告诉我,为了躲避那个所谓的“哥哥”,她转了学校,去了一个可以住宿的全女子学校,虽然因为住校少了一些自由,但终于不用在深夜偷偷哭泣了。
4
小说和电视剧总有皆大欢喜的结局,而现实世界却多是破碎。和《两个小洛特》的happy ending不同,茉莉姐妹的父母并未再走在一起,他们分别成立了新的家庭,开始了与之前截然不同的生活。
念了大学后,我和付家姐妹的联络渐少,仅有的信息交流只能透过冰冷的网络呈现。不过,令我大概意外的是,这对早年看来水火不容的双胞胎,竟然在成年之后住到了一起。付莉告诉我,她在上海的一家外企工作,而付茉则在做律师,两个人租下了一间老破小,共同生活。
“你们的爸妈没说什么吗?”我问。
“我们长大了,他们管不着。”
上海迪士尼开业后,我总酝酿着去玩,在上海这座都市里,我认识的人不多,最熟的也只有付茉和付莉这对姐妹花,于是,在抵沪的前一天,我们约好,三个人要见上一面。
之前看杂志,上面说,人在小时候的容貌是父母给的,而人在成年后的外貌则会因为各自不同的经历而改变。再度看到茉莉姐妹,我忽然意识到,其实她们在某个角度来说是完全独立的两个个体,尽管她们的五官还是一模一样,但气质已经完全不同,我很容易认出谁是姐姐,谁是妹妹。
付茉戴着一副银丝边的眼镜,留着短发,看起来干练得体,像是TVB剧里走出来的职场女性,而付莉则染了一头深棕色的长卷发,穿着碎花连衣裙,很温柔的样子。
再度见面,我们三人都很感慨,付莉讲,在和继父一家生活在一起后,她差点患上抑郁症,尽管总是被那个“哥哥”骚扰,但她的妈妈从来没有站在她这边。好多次,她站在高楼的天台上,总有一股跳下去的冲动。自毁的事情也有过,比如用小刀割自己的手,割出一道一道的血印子。
付莉说完,付茉接过了腔,她跟我说,在那段时间,一向身体健康的她也总是觉得莫名的心脏乱跳,浑身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也没查出毛病,后来她在一本书里看到,说是双胞胎之间存在着神奇的心灵感应,即使两个人相隔万里,也常会产生同频的感受。
聊着聊着,我们不免又说到了婚恋的话题,我再度提及小时候看到的狗血故事,付莉说,她和姐姐商量过了,也许未来两个人都不结婚,这样,自己努力工作、赚钱,两个人买上一套小房子,永远居住在一起,也未尝不可。
聊得差不多了,付莉从包里取出一个透明塑料袋装的茉莉手环送给我。她说:“还记得吗?那天,我们刚走到巷子口,我问你,这是什么花,你说,这是茉莉花,一种有魔力的花。”
“那个时候太小了,都是开玩笑的,花怎么会有魔法?是我骗你的。”我摆摆手说。
“只要你相信它有魔力,它可能就真的能改变一些事。”
那天夜晚,我们三个人在迪士尼看了一场灿烂的烟花秀。散场后,我们沿着长街向外走,付莉告诉我,在她和其母亲搬到另一座城市生活的那些年里,她是靠着茉莉花和书信的安慰熬过去的。那座北方城市没有卖花的姑娘和阿婆,她只能用能洗掉色彩的笔在手腕上自己画出一圈一圈的花。
“现在你相信茉莉花有魔力了吗?”付莉问。
“信,你说得都对。”我们三个人手挽着手,放声大笑。暗夜之中,我似乎能嗅到手腕处隐隐约约传来的花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