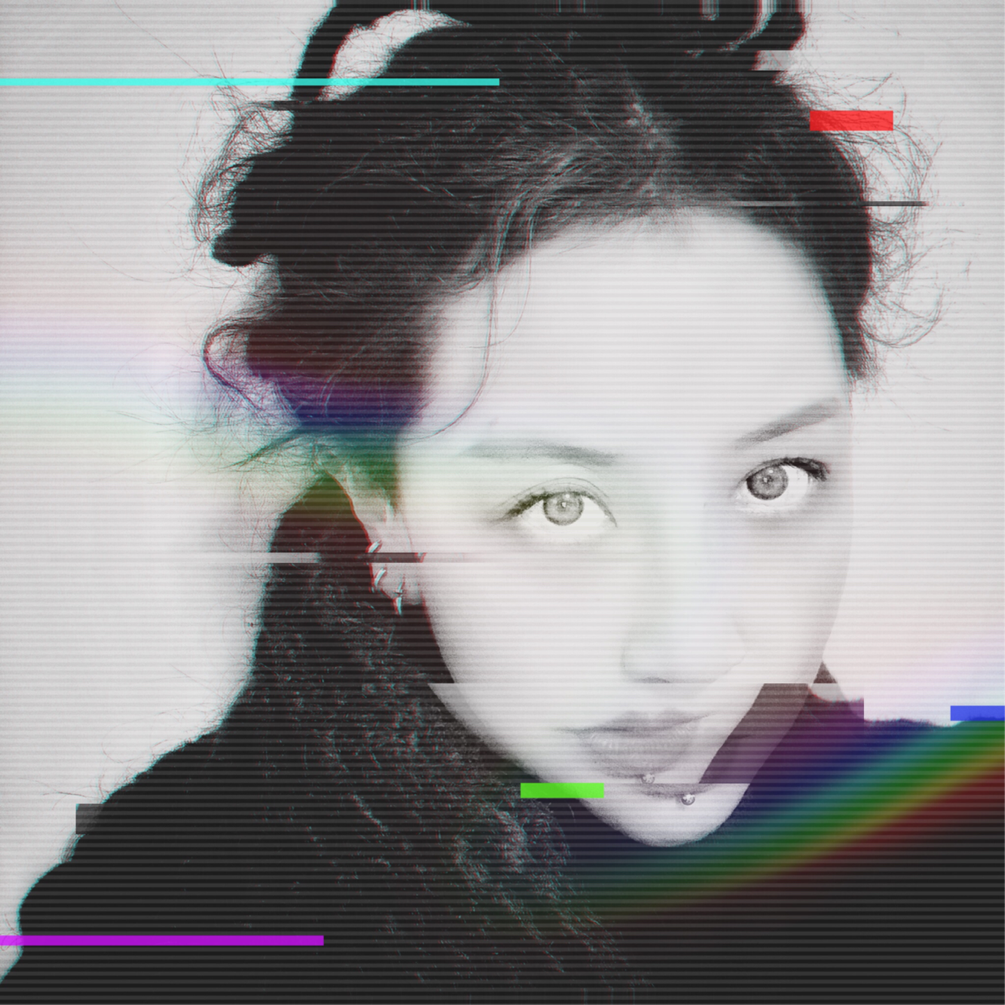…… ……
And we’ll light ourselves on fire
我们将引火自焚
Just to see who really wants to believe
只为了看谁真的想要相信
That it’s just me, tender, humor in hair
那就是我,和善,头发渗出幽默
Half me with something to spare
这一半的我有用来出借的什么
Rhythm, folds now go untold
节奏折叠,此刻无言地前进
Gently, my mistake
温和地,我的错误
Old burn let it take you days
往日烧伤 让它带去你的时间
And for days, now I’ll wait around
而这阵以来,现在我会等待
And we’ll light our lives on fire
我们都将在火上点燃自己的生命
If anyone will come rescue
是否有人会拯救
What’s left of me
我剩余的部分
Please Won’t Please – Helado Negro
1
早在胖胖给我打第一通电话之前,我已经知道他很久了。北京艺术圈说大不大,经常混迹各种展览和活动的无非也就那么些人。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每个艺术区都迎来了短暂繁荣,798、草场地、黑桥、环铁、百子湾……平均每周至少有5到10个展览开幕,相关从业者总是有很多机会在各种画廊、美术馆和艺术家工作室碰面,一来二去,陌生的面孔渐渐都变成了熟张儿。有时候在什么场合碰见,无论认不认识,大家都会打个招呼聊上几句,或一起到外面抽根烟。我跟大部分北京的朋友都是这么认识的,所以胖胖的交际圈跟我有不少重叠,正是从其中一个朋友那儿,他问到了我的手机号码。
那天他打来电话是夜里11点多,我正坐在电脑前,要么写稿,要么边喝酒边看下载的恐怖片。“喂,你是米奇吗?”听到我的回答后,他毫不见外地说:“我是胖胖,那谁给了我你的手机号,这周五798有个展览开幕,你去吗?”我说我去,那天同时还有其他几个展览开幕,我要给其中一部分做展讯,还得采访一位首次做个展的艺术家。他高兴地说:“这次开幕是我帮他做媒体联络,你能来太好了!咱们到时候见!”我还能想起他的语气,无论当时或现在都不使人感到生分,反而透着一股自来熟的亲切感:“以后咱们就一块儿玩呗,我还有很多朋友要介绍你认识。”我也很高兴,有人愿意主动跟自己交朋友,这首先是一种认可,能够满足我的虚荣心。再加上作为性格比较被动的人,我经常需要外力帮助才能暂时离开自己沉浸的世界。
因为这通电话,我们成了朋友。我并不知道胖胖具体在哪个机构做什么工作,后来也从没当面问过,只是断续从别人口中得知,他在艺术媒体、画廊、艺术公关公司都待过,后来好像自己弄了个工作室,接一些外包的展览策划和艺术家宣传之类的活儿。“胖胖”是他的绰号,按照北方普遍的身材,他其实算不上胖,因为个儿不太高,整个人看起来有点儿圆圆的,爱穿颜色鲜艳的潮牌服装,老背着双肩包,经常戴各种棒球帽。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一个朝气蓬勃、喜气洋洋、能言善道的人,社交能力特别强,我一直喜欢跟这样的人打交道。
大家对胖胖还有一个普遍印象是把他当作艺术圈的联络人,他有几乎所有相关从业者的联系方式。当时我在时尚杂志做编辑,出于个人爱好做了非常多当代艺术的内容,有时候我们想采访某些新锐或不知名的艺术家,但凡通过其他途径找不到联系方式,问胖胖准靠谱。他似乎乐于扮演推手似的角色,一个八面玲珑的多面手。这一方面能彰显他的交际能力,另一方面也证明他手里资源多。平时他经常带人们走访艺术家和策展人工作室——媒体从业者、画廊主、藏家、明星名人、有些背景的艺术爱好者……一来二去,形成的人际关系网相当可观,再加上他素来为人大方,大家都愿意跟他交朋友,时不时也能谈成一些事。
认识之后那几年,胖胖跟我长期维持着堪称频繁的联系。他每周至少给我打三四个电话,约着看展览、吃饭、唱K、逛古着商店、去书店买书、凑各种艺术圈饭局、去他家打游戏,或只是单纯地一块儿到处晃膀子。我并不总是参与他组织的这些活动——尽管并不社恐,但我不算特别爱交际的人,而且性格多少有些古怪,除了工作需要,我几乎不想主动结交什么人,对于经常要参加的工作应酬也感到厌烦。况且那时候每个月有不少工作任务,我得花大量时间采访、写稿,除了本职工作,我还在其他杂志和网站开了不同的专栏,按照每周和每月的频率更新,各类约稿加起来,每个月至少得写出二三十篇。除此以外,我还得花大量时间喝酒。
30岁前,我还没把自己喝废。那时候的酒量虽然已经比不上巅峰时期,但喝一斤乃至一斤半二锅头不成问题。啤酒更是不在话下,燕京“大绿棒”(北京本地最常见的燕京10度啤酒,一箱24瓶,每瓶容量600ml)像水一样流进我的身体,又像一条被污染的河流那样缓慢而滞重地离开我的生活,2块5一瓶的价格确保了可以无限量畅饮,每个空瓶还能退5毛钱。我经常随意乱喝蒙古口杯(一种小杯包装的30度白酒,容量130ml)或在便民超市能买到的任何一种酒,外出跟朋友聚会也总是喝大。
从18、19岁开始,很长时间里喝酒支撑着我的生活,那时候身边的人好像也都这样,酗酒蔚然成风,年轻人普遍以喝大为乐,从不顾及后果。也许聚众喝酒只是为了寻求一些精神安慰,尽管谁也说不出究竟为什么时常感到沮丧——彼时北京房价尚未起飞,我们的职业也还算体面,尽管收入不高,至少是在自主选择的范围内做自己想做的事。要么跟当时的流行风气有关?喜欢摇滚乐的年轻人,没有一个不爱喝酒,说是发泄情绪也好、寻找精神寄托也罢,只有当我们跟有着同样爱好的人一起玩时,才能产生足够的愉悦和那种近似于“High”的感觉。我们编辑部里也有不少酒精爱好者,熬夜加班改彩样时大家经常在办公室喝酒,或者下班后一块儿到附近的小饭馆尽情畅饮。
胖胖很少出现在我们的喝大酒聚会里,尽管在某些酒局上他也会跟别人一起喝,但我早就发现他并不喜好杯中物。他喝酒只是意思意思,为了显得合群,或作为某种交际手段,一杯调酒能品尝一晚上。所以严格地说,我们不能算特别亲密的朋友——他从没在我面前失态过,我向来也很少跟他聊任何触及内心的话题,我们只是经常一起玩罢了,就像放学后约着打乒乓球的那种朋友。这也导致后来当我开始回忆他时,很长时间里找不准自己的位置——我总害怕自己的怀念显得多余、矫情、加戏太多,也无意为这份友谊添油加醋以便证明些什么。当一件事已成定局,其实说什么都嫌多余。
从前我们都住在望京及泛崔各庄地区(包括798、草场地、黑桥、马泉营),要攒局非常容易,随时随地一个电话就能凑到人。在我发现胖胖不爱喝酒的同时,他大概也发现了我不爱交际,所以后来他约我的局经常不超过三个人,更多时候只有我跟他。我曾经清晨七点多接到他约我去朝阳公园划船的电话——“咱们可以在某某地方的永和见,先喝个豆浆吃点儿早饭,然后去公园晒一晒”;也经常凌晨三四点被他叫出去唱K——“你没睡呢吧?咱们去望京唱会儿K?我跟谁谁打车呢,一会儿到你们村口接你。”我们会花整个下午在鼓楼或东四的胡同小店里瞎转悠,跟他在交道口“等待戈多”买的皮带我一直用到现在,牛皮、日本货、纯手工,皮带扣是个歪嘴笑的骷髅头。
长此以往,我对这个人有了更多感受——尽管已经把几乎全部时间花在人际交往上,也为别人奉献了很大一部分生活空间,胖胖恐怕依然十分孤独。这一发现使我有些伤感,因为大家的处境很可能相差无几,但我们从没聊过类似话题。不知道为什么,他特别害怕独处,好像任何时刻身边都需要有人,至于跟别人一块儿干什么他反倒并不在意。在这一点上,我跟他完全相反。我需要长时间独处,每天绝大部分时间我都渴望单独待着,随便干点儿什么或什么也不干。可孤独没有从任何人的生活中缺席,我们也从来没找到什么更好的办法与之相处。
当胖胖后来搬到黑桥,我们两家离得更近了,他又在我住的村里结交了一个玩得挺好的艺术家,有一阵儿更是老往马泉营跑。有时候吃完晚饭他还不想散,磨蹭半天说咱们附近走走吧。等到天完全黑了,又提议:“去我家玩会儿游戏呗?”我爱打拳皇、街霸,但他不喜欢玩格斗类或者太复杂、太花时间的游戏,因此我们总是任天堂网球双打,一打好几个小时。在我的印象中,他住那套二居室的房子非常空旷,就像身处一片荒野里。当时黑桥的回迁小区刚建好,住户还很少,周围都是荒地,夜里从阳台望出去外面总是漆黑一片,天上也没有星星。
我对胖胖的性取向有过怀疑,莫不如说这是我们那个小圈子里一个公开的话题,有时大家会聊起,他自己也常参与,甚至当面开开这类玩笑他也不在乎。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完全不在意,当然至今我也不知道他到底喜欢异性或同性,或二者皆有。在他口中经常能听到各种各样的艺术圈八卦,关于他自己的事却总是隐藏在迷雾背后。诚实地说,我从未了解过这个人。当然这种不了解并不妨碍我们一起玩,我向来觉得人和人之间不必了解那么多。
2014年,我接到一个上海的工作邀约,从杂志办妥离职是4月底,计划5月中旬去新单位入职。离开北京之前那一个月,我不停地跟朋友们聚会,吃饭喝酒唱K,听大家开玩笑、打赌、信誓旦旦地说以我的性格在上海待不了半年就得回北京。其中一次饭局人比较多,地点选在美术馆后街小云南,这是我比较钟爱的一家馆子。在场的都是当时玩得好的朋友,印象中那天晚上我跟胖胖好像没说上什么话,他吃东西很节制,当我们痛饮啤酒时不知道他在干嘛。在合影中,他的座位背对着镜头。
从此我们很长时间没再联系。
2
再次见到胖胖是我离开北京一年后的冬天,我已经彻底告别了媒体行业,不再写任何东西,进了一家挺大的艺术机构,成了老老实实的上班族。那段时间某个奢侈品牌在我们单位做了一场盛大的展览,为期三个月。作为工作内容之一,每个周末我都得组织一些不同主题的派对,目的是扩大展览影响力,同时请各路时尚人士来玩。这种活动很容易找到酒类赞助,场地是现成的,没有其他预算,于是由我准备了音乐,并在一些关系户来的时候负责营造氛围、担任DJ。人们兴高采烈地无限畅饮,看展览、拍照并上传到社交媒体,来的人绝大部分我都不认识,并且非常确信以后也不会跟他们有交集。
有一天胖胖给我发微信,说他在上海,陪同单位领导来开美术馆之间的馆长年度会议。那天晚上我这边正好有个Party,于是盛情邀请他和他的同事来玩。他们在派对结束后才到场,保洁阿姨已经开始打扫卫生,我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长廊抽烟。他带来了一男一女两位同事,看起来像是初涉职场的样子,还保持着青年艺术从业者身上那股子矜持。之前我已经喝了一些工作酒,也无意开展什么假装热络的交际,场面一度有些尴尬。后来我接连开了几瓶红酒极力劝饮,不断斟满他们的酒杯并频频邀约干杯,据说俩人回到酒店都吐了。
胖胖还是不怎么喝酒,只在我们碰杯时端起杯子走个形式。尽管后来已经没有太多联系,但见面一点儿都不生分——他瘦了一些,这丝毫没有影响我对他的感觉,还是那么亲切、温和、适度的礼貌与足够的客气。我想跟他好好聊聊,又不知道该说些什么,于是大家像商务会面那样谈起了工作。这时我才知道他也去了一家艺术机构上班,台资背景,职位好像是公关媒介总监一类。那地方就在我从前住的村子附近,曾经去参加过几次活动,环境挺好,建筑以诸多的红砖块为特色,不知道后来做过什么展览。现在那儿成了北京郊区网红拍照景点之一,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送他们离开时,我跟胖胖在单位门口拍了一张合影。帮忙拍照的是那位男同事,他很明显已经喝多。照片没有拍好,门头的射灯从上面直射我俩的脸,我看起来龇牙咧嘴,表情十分不自然。为了进行粉饰,我用一个App里的动物头像把我的头挡住,并且没有保留原图片文件。这种行为挺愚蠢的,那阵子我特别沉迷伪装,说白了还是因为虚荣心,以及对自己没有足够的认识。刚来上海那几年,各方面我确实挺能装,总想着要彻底转型,丝毫没觉得自己做不到。改照片的事后来让我万分懊悔,因为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胖胖。可谁又能提前知道这些呢?关于生活我们始终了解得太少,对于命运更是一无所知。
2017年1月发生的一切至今仍缺乏实感。元旦后两三天,当我首先在朋友圈看到某位青年艺术家发布胖胖的死讯时,我认为这肯定是他们商量好的一次行为艺术。比如做个展览,假设自己的死亡,活人被活人瞻仰……从前我们聊过很多类似不着边际的设想。但很快有越来越多的人发布消息,我被拉进各种悼念微信群,此后几天这件事在朋友圈和各种艺术论坛反复刷屏。我只能说我感到不可置信,甚至来不及悲痛,因为胖胖才30岁。当我想找点儿照片表示怀念时,只找到了那张最后的合影——漆黑的夜色中,我的头被一个虎头挡住。一切荒诞至极。
那阵子我刚好在北京——2016年即将结束时,我因为处理一些事情回到北京跨年。得知胖胖死讯的那个下午,我正在朋友T家里玩。就在几天前,我还跟胖胖联系过,我们约了12月31号在朋友的酒吧见面。那天晚上他没有露面,我给他发了微信,说跨年大家都挺忙的,我还要待几天才走,如果他之后有时间我们再约个饭云云。最后我祝他新年快乐,希望他新的一年一切顺利。没收到回复,我也没放在心上,他有那么多朋友,顾不上赴约也是正常的——过后有空再约呗。
根据后来获知的消息,他去世的时间是12月31日凌晨,当时他独自在家。也就是说,当天夜里我给他发信息的时候,他其实已经不在人世了——认识那么久,他从来没有失约过,为什么我竟然觉得他不回消息是正常的呢?
关于胖胖死亡的细节我并不了解,据说法医鉴定结果是心脏骤停,也就是俗称的猝死,近些年多发于工作过劳、长期熬夜的中青年人群。我不知道他是否很长时间缺乏休息,也不知道后来这几年他过得如何。他的死亡是否给我带来什么启示?——不能说我没有感到害怕,也想着要少喝酒,改掉熬夜的毛病。可是自那以后,我只是长时间发蒙。跟两个好朋友聊起他生前的事时,我流了会儿眼泪。在悼念他的各种微信群里我从未发过言。追悼会我没有参加。朋友们组织买花圈时我随了份子,后来收到一张花圈的照片,挽联上写着我的名字。
一个画面骤然浮现在脑海——我们在望京常去一家通宵营业的小饭店,位置在阜通东大街,靠近花家地南里。有一天喝了四十几瓶玛克利,当时还是绿色的塑料瓶子,喝之前得摇一摇。“这种东西怎么可能喝醉呢?”我们大笑着说,“老板,再来四瓶!”后来我再也没有喝过玛克利,再也没有去谁家玩过网球双打游戏,再也没有谁会半夜打电话来跟我聊天、约我出去玩……随着时间过去,我成了表情冷酷的中年人,不高兴再交什么朋友,只想跟大部分人保持距离。我问过胖胖:“你怎么老也不睡觉?”他满不在乎地回答:“你不也是吗。”我突然明白了,他之所以那么爱半夜找我,可能是因为那个点儿经常只有我没睡觉。
一个曾经鲜活的人彻底从人间消失,任何失去都比不上这种消失。我从来不喜欢描述死亡,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关于这件事,我与其说是恐惧,不如说是无知。我试着面对恐惧,也早就承认了我的无知。可是在回忆中,我觉得那些人都还在——所有曾经相聚又离开我们的人——无论他们是否已经死了,或尽管活着却杳无音讯。
3
某年六月,我们在一个周末突然决定自驾去北戴河。同样是胖胖先打来电话:“你明天没事儿吧?咱们一块儿去北戴河?”事情很快就定了下来,共有三人参加,除了我和胖胖,还有一位住在马泉营的艺术家。这个组合无论怎么看都很奇怪,我跟那艺术家并不熟悉,更谈不上是朋友,只一起吃过几次饭,还都是胖胖组织的。我只知道艺术家跟他的老婆孩子在北京生活,住在我们村子另一头的小型艺术区。我没记住他的名字,也没看过作品,仅从外表和谈吐想象不出他创作的是什么内容。
那次短途旅行为期三天,我们周五出发,在北戴河住了两晚,周日下午返回北京。关于这次邀约,我是这么理解的:他们俩要去北戴河,反正车上还有位置,就顺便再捎上一个人,随便谁都行。毕竟多个人气氛热络些,吃饭也能多点两个菜。旅游过程没留下太深印象,也就是说既谈不上好玩,也谈不上不好玩。大家和和气气,吃了海鲜,逛了几条街,在海边待了很长时间。
反倒是我们住的地方非常有趣,那是一所老干部疗养中心,一切建筑和房间设施均呈现八十年代风情。几栋四四方方的苏联式建筑呈口字型拼接,当中有个大院子,内含凉亭、烧烤房,天一黑广场就亮起彩灯,还没完没了地播放交谊舞音乐。住客寥寥,那几天除了我们好像没有别人。广场上的灯整夜亮着,透过薄薄的窗帘照进房间里,影响了我的睡眠。
时间过去太久,当时的感受已经忘得差不多了。那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去北戴河,惊奇地发现海水很脏,跟以往对大海的印象完全不同。那是一种灰黄色,许许多多白色泡沫浮在浪花上,气味难闻。每天下午我们都在海边度过,沙滩也很脏,有一些粗大的水管,污水就这么直接对着大海排放。在此时的回忆中,那些画面非常沉默,我一直喝啤酒,胖胖间或用蓝牙音箱放歌,“下面请欣赏老鲍勃表演的牙买加歌曲,这是一个非常欢乐的民族……”艺术家不知道在哪儿。沙滩空无一人。没有人需要说话。
胖胖给我拍了点儿照片,其中一张是我面向大海的背影。他说:“你丫像一个不知道打哪儿来的海边旅客。”我认为他在那个时刻精准地洞悉了我身上的某些特质——“旅客”,多么具有过去时代特征的形容词。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我的了解要比我以为的多。自那时候开始,我找到了自己的人生定位并概括为一句标语:愿能永远做个海边的旅客。没人知道旅客都从哪儿来,人们也并不在意,旅客永远只待一阵子,最后总是要离开。这一角色天然不具备任何目的性和远大志向——旅客来到海边,就只是为了打发一会儿时间——旅客总是想在海边逗留,对这件事永不厌倦。那个黄昏因而在人生中具备了重要意义,说是促进了我个人的完整也不为过,很难说我的人物性格和此后的发展轨迹是否因为旅客身份的明晰而逐渐开始发生变化,但我想冥冥之中万物自有联系。
这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们在小饭馆吃了几顿不好吃的海鲜,从马迭尔冰棍店门口路过时胖胖坚持给我们一人买了根雪糕,在车上他给我们普及北戴河的房价……最后一晚,我们打包了烧烤回去吃。在院子里的凉亭坐了很长时间,却早已忘了聊天的内容。我想描述得更生动一些,可的确已经想不起更多细节。也许随着死者的离去,人们与之曾经共有的记忆也会逐渐消失,又或者这种遗忘从更早之前就已经开始。我们不得不承认,就算人们还活着的时候,也经常搞不清楚生命的轨迹要走向何处。
另一个跟旅客有关的画面是我们走在草场地艺术区附近一条暴土狼烟的乡村公路上,可能要去某个画廊,也可能刚从画廊出来。那天我们情绪都不高,暂时没什么地方要去,也没有什么事等着要做。那种状态是那个时期的生活常态,总结起来就是闷闷不乐,百无聊赖。很多满载沙石的大卡车从身边飞驰而过,那种不顾一切的劲儿就像路边正在行走的是两头牲口,而卡车可以毫不犹豫从我们身上碾过。
胖胖抽着烟,问我:“你想过走吗?”
“去哪儿?”我问。
“随便哪儿,哪儿都他妈比这儿强。”说完这句不知道说过多少次的话,他仿佛出了口恶气,把烟头扔进旁边的河里,拿出手机打电话给认识的黑车司机,问问能不能来接我们一趟。
当时崔各庄还没通地铁,那地方公交车根本不经过,除了黑车没有其他交通工具能带我们离开,而四周特别荒僻,就连黑车的影子都见不着。那些年,每次去远郊的艺术区总得走很远的路,一次我去七棵树园区某个影棚拍片,回程时点儿特别背,路上一辆黑车也没碰着,走了7公里多才看见人烟,甚至路过了一个墓园。后来当我回想起北京的广阔,心里无数次感叹——如果从前有共享单车,我们的郊区生活会幸福很多。当然,崔各庄乡的群众从来不认为自己生活在农村,他们会说朝阳区的边儿上也是朝阳区,首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祖国的心脏。
4
过去,人们常常嘲笑时尚杂志从业者,说这帮人“拿着几千块工资,却在教富有的人怎么花钱”。不可否认这是一种确实存在的现象——众所周知媒体行业收入不算高,但结合社会现实,大部分中国人开始有钱也不过是近十年的事。我入行那会儿算个分水岭,2008年北京奥运会之后,国内各行各业迎来了一波快速发展,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审美需求还远远没有培养起来——当时网络并不像如今这么发达,大众获取资讯的途径主要依靠报纸、杂志和少数几家门户网站,更谈不上有什么成体系的时尚产业。所以除了奢侈品广告、时装摄影图片和潮流资讯以外,杂志能提供的还有包括旅游、美食、生活方式、美妆指导、情感故事、文化艺术等等多方面的内容,其主要功能通常被认为是一种“城市生活指南”。
作为一家本土时尚杂志的文化编辑,我做的事跟促进消费没什么关系。大量当代艺术展评、书评、乐评,活跃在一线的设计师、艺术家、作家、建筑师深度人物报道、明星封面故事……我写的主要是这些东西。对我而言这很有意义,因为除了北上广这类一线城市,国内其他地方很少或几乎不可能接触到这些内容——假如有一些年轻人对文化、艺术和时尚感兴趣,他们可以在时尚杂志上获得很多资讯。所以每当我们老板说杂志前半部分文化内容是“赔钱货”的时候,我要求自己尽量毫不在意。但我们真的把资讯传达到了需要的人手里吗?其实也不见得。高昂的定价筛除了大部分读者,即便到现在,北上广以外的城市又有多少人会每个月花50块买一本杂志呢。
胖胖曾经开玩笑说:“时尚杂志都是假招子(北京俚语,意即:虚假的、不实在的,用以形容故意做出某种像真事的姿态)。”我判断他不含恶意,也刻薄地回嘴道:“艺术民工也好不到哪儿去。”大家一起哈哈大笑,为了不上不下的生活状态和尴尬的处境。假如其他没什么交情的人自以为聪明当面说这种话,我会非常生气,当场就要让人下不了台。是因为自卑感作祟吗?或当时的生活的确存在某种无法调和的内部矛盾?——每天出入光鲜的工作场所,接触的尽是明星名人,自己却住在东五环外的村子里,去趟南锣鼓巷路上需要2小时,晚上喝完酒打车回家随随便便就得花一百多块车费。
我知道我心理并不平衡,我一直知道,也不能说完全不在乎,否则我就不会离开。在北京那么多年,我始终住在马泉营,搬了几次家也没离开那个村子。朋友们经常把喝大的我送到楼下,但谁也没去过我家,包括胖胖。我不会否认一开始决定住马泉营只是因为别无选择——要么就得住地下室。尽管去北京之前充满了斗志,觉得再艰苦的条件也能扛,遗憾的是所有对北漂生活的浪漫幻想在亲眼见到地下室的瞬间就烟消云散。以为自己“能为了理想吃苦”和真的吃苦是完全不一样的事情,除了一门心思搞乐队的人以外,不可能有太多人愿意长期忍受那样恶劣的生存环境,所以我心里始终对真正的理想主义者抱有一份敬意。
马泉营位于五环外,是隶属于朝阳区崔各庄乡的一个村子,耕地早已全部被征用,原有的旧村落后来改建为新型农村别墅区。村民很富裕,每户都仿照旁边观塘别墅的格局建了几百平米的联排别墅。最早住这儿的大部分是在望京工作的韩国人,还有大量尚未成名的贫穷艺术家。随着租房的人越来越多,村民在原本的别墅外围加盖了一圈房子,装修成带厨房和厕所的开间公寓用于出租。当时我们杂志的摄影师住在那儿,得知我要找房,他说:“来我们村吧!988路公交直达,包你满意。”
村里的别墅分为三个区,除了房屋外墙涂料颜色不同,每户格局都一模一样。一区和二区并排位于东面,跟西面的三区之间隔着灯光篮球场、农贸市场和许多小饭馆,还有一个四季都是枯枝败叶的大荷塘。暖气是村里自己烧的,水暖,很热,每月只需交100块钱。严格地说,村里居住条件并不差,同等价位在其他地方只能合租一个小隔间,别说厨房了,连窗户都不一定有,还得跟不知道什么来路的人共用厕所。朋友们都知道我对这儿感情深,前几年有人偶然去马泉营办事,还特别拍了照片发给我看,那个村子已经繁华得认不出来。对于一穷二白的北漂来说,马泉营称得上是苦海方舟,真正的救命之所——特别是2011年底逐步开通地铁15号线以后,去望京只需要10分钟,列车全是崭新的紫罗兰色,干净、人少、采用最新设计,冬天座椅下面会出暖风。
我在村里搬过四回家,先是住在一区132号一楼,房东赵阿姨人很好,房租一月一付,甚至不需要押金,我在她家住了很长时间。当二楼带天台的一室一厅空出来后,我搬到楼上,独自占据整块天台,一边听吹万的首张专辑一边喝啤酒,很是过了些快活日子。直到一天早晨外出采访,回家时发现整个天台被全部拆掉。
当时这样的事每天都会发生,要么突然把路面凿开,在底下换什么污水管道;要么又因为听说了拆迁的小道消息,家家户户急忙在楼顶加盖一层……宁静、和平的生活环境时刻被弄得一团糟。怎么就他妈那么爱瞎折腾呢?我想不明白这个问题。为了安居乐业,我最后搬到了三区,那户房东全家不住在这儿,他没那么多工夫在村里搞改建,我终于过上了几天消停日子。
后来发生了什么?我有过很多机会搬走,也托朋友帮忙找过不少房,但就是没动窝。一开始嫌搬家麻烦——那几年我们单位老换办公室,先是从798搬到了雍和宫附近的歌华大厦,后来又搬到了小庄中国第一商城,我无论住哪儿,去趟单位都得长途跋涉往返路上四小时。谁知道最后单位竟然搬到了马泉营附近的一个有机农庄,这可以说是我一辈子遇到的最绝的事:一边的玻璃阳光房是编辑部办公室,另一边的园子里养着一群大鹅,前院是有机菜地,后院有鱼塘和秋千,中午大伙儿在食堂吃饭,抽烟就站在菜地边。那个冬季经常在户外晒太阳,我走路10分钟就能去上班,这种事在北京基本上属于不可想象。
最后我对那个村子产生了感情。这是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吗?我觉得很有可能——某种人会爱上那些折磨过自己、同时又带来极大影响的东西。人总是这样,需要找一些借口、自己制造一些幻觉,以便维系某种想象,否则生活就难以继续。如果没有离开北京,现在我应该还住在村里,离开那一切是非常困难的事情——直到今天我可能尚未真正离开。
后来无论身处哪个城市,深夜坐在出租车里时,我经常回想起马泉营隔壁奥特莱斯的停车场。白天车总是停得满满当当,而夜里则每天都空空荡荡,无数间隔车位的细小地灯有序排列,远远望去就像天上的星星落到了地上。这大概就是我必须写下这些往事的原因,其实不是为了告别,非要形容的话,可能更类似一种提醒——你走过的路、做过的事、度过的日子……同时也是清算。
后记
当被问到对金钱的看法时,我最常听到人们说“够花就行”,以表态自己并不贪心。至于多少才算“够”,每个人又有不同标准——在三环内买套三居室、外加一辆宝马,这样够吗?80%的家庭得为此偿还30年贷款,这还是凑齐了首付的前提下,并且——你不一定能摇到车牌。中国的当代生活就是这样,无论你在哪儿,想过所谓的“好日子”,普遍需求都差不多。我没有这些方面的需求,穷点儿也没什么,这使欲望带来的痛苦无形中少了很多。
不可否认在这方面我还保持着一个朋克的本色——穷得理直气壮、死不悔改。这未尝不是一种天真,大概也说明没真正受过什么苦。我想要的永远是“另一种生活”,每天晚上有派对可以玩,日常生活就是看展览、看演出、看话剧、听音乐会、喝酒,跟老实巴交过日子——再遵守国家要求生俩孩子——完全不沾边那种。所以后来有了去上海的工作机会,我没怎么考虑就把北京的生活连根拔起,打了几个包,头也不回地奔着十里洋场而去。
胖胖跟我说他小时候一直想当明星,觉得总有一天会出人头地,但碍于外形,估计不可能在娱乐行业有什么发展,只能退而求其次搞艺术。我能理解这种心情,从前北京遍地都是这样的年轻人。大家野心勃勃,甘愿吃苦,否则谁会放着好好的日子不过,离乡背井大老远去北京。但他说的话我没往心里去,听过就算,因为不知道深聊下去该说什么。直到一块儿唱了K,我才明白他对自己的期待不是空穴来风——他唱歌非常好听,尤其是陈奕迅的歌,可以毫不费劲顺着歌单挨个儿唱下去,包括以高难度著称的《浮夸》,状态好的时候几乎原音重现。他的粤语发音也很不错,除了唱歌还会讲很多日常对白,说是长期看老港片自学的。
此时想起这些往事,浮现在我脸上的是微笑而非泪水。无论什么样的时代,总有人心怀梦想,并愿意尽力去追寻。我有幸见过许多这样的人,胖胖就是其中之一。他们的存在使我觉得一切尚可忍受。说白了,人活一辈子,阶级和出身已经决定了大部分事情。除了绝少一部分人能受惠家庭免于奋斗,其余的日子都差不了太多。无非是房子稍微大一些,车稍微贵一些,孩子就读的学校好一些,家里存款多一些……当生活落实到每一天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钱财的多寡会造成物质享受上的差异,但钱永远不会成为衡量生命价值的标准——你又带不走。对于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东西,我从不执着。
随着年龄渐长,想要坚持些什么好像越来越难了。人的生命是一个倒退的过程,曾经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天会消失殆尽。早在24岁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人可以变得越来越成熟,这不是坏事,但我们既不会更聪明,也不会更漂亮,甚至不会更年轻。我们用时间换取了一些社会经验、一些维持生活的金钱,可这种经验我并不觉得宝贵。这只不过是随便什么人只要愿意牺牲自我、花费时间,到头来总归能学会的东西。我们身上那些与生俱来的部分才是绝无仅有的,然而活着就意味着要眼看它们消失。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不觉得死亡是一件绝对的坏事——胖胖的生命永远停止在盛年,当人们回想起他,脑海里浮现出的是他年轻的模样。当然我们可以这样认为:继续活下去,他的生命或许会有更多精彩。但同时也将伴随着无处不在的、很可能无法避免的损伤。假使两方面能够基本持平,人们就会认为一个人度过了美满的一生,所以教义鼓励人吃苦,并创造了各种自我安慰的说法,以便在受苦时进行自我欺骗。对我个人而言,这永远是一种可悲的社会现实。
现在你或许已经发现,对于真正想表达的部分,我选择尽量少提——但不可否认,我的观点或许打从一开始就有失偏颇或过于极端。我希望每个人都长命百岁,只要他们甘之如饴。我懒得再表达不同看法,说真的,这么多年了,我已经累了。
这个故事的标题原本叫“尸体”,开头我打算这么写:“三年前,有个朋友死了,非常突然。”目的是营造一种“局外人”的冷峻,我长期致力于培养简洁的笔触,更节制,更冷静,也更客观。可是回忆朋友时,我用不着冷静客观,我只需表达我的情感和怀念。尽管我算不上是胖胖最好的朋友,但我们曾经共度的时光非常重要——他曾经给我打来的电话对我非常重要,他愿意跟我交朋友对我非常重要,每次他约我去玩都使我暂时逃离了孤独……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那一切,我都要对他致以感谢。
当我终于把这些往事写完,三年过去了。等到修改完毕决定发出来,又过去三年。对胖胖的回忆将永远停止在六年前,以后不会再有更新。随着他的消失,那些时光成为了永恒。任凭世事如何变迁、任凭人们的关系怎么变化,那一切都不会改变——这未尝不是“永恒”的一种实现。关于我们的友谊,我没有遗憾。在过往共度的时刻,我始终诚实地以真心与他交往。
最终打败人的只是时间,总有一天你会老得什么也干不了,时代如何并不重要。旅客的宿命就是永远在路上。旅客会走完这条长路。不论时代变迁中海潮如何湮没往事,也不论我们的内心有多少个部分被彻底毁掉……很奇怪,此刻我突然有一种超脱之感,犹如故人音容宛在,隔着一片海,远远地对我大喊:“不要输给时代!要永远做一个海边的旅客啊!”
海涛声声入耳,波浪翻卷着时光。潮水总有涨落,而曾经的爱恨永存。
又一个春天来临,我在寂静的深夜,听人读了首诗:
昨天 今天 以及明天
是小而珍贵的刹那聚在一起组成整个人生的瞬间
盛开绽放的青春的刹那
和无可奈何改变了的刹那的瞬间
还有说着忘记
想要回避的那些瞬间
全部聚在一起
组成了整个人生
直到今天才更加深刻地体会到这一点
坚信我们人生中每时每刻的珍贵
绝对不会改变
而我们会像无法凋谢的花朵一样
依旧是那个样子
那般美丽
刹那的瞬间
各位的浪漫
今天也还好吗?
我小心翼翼地问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