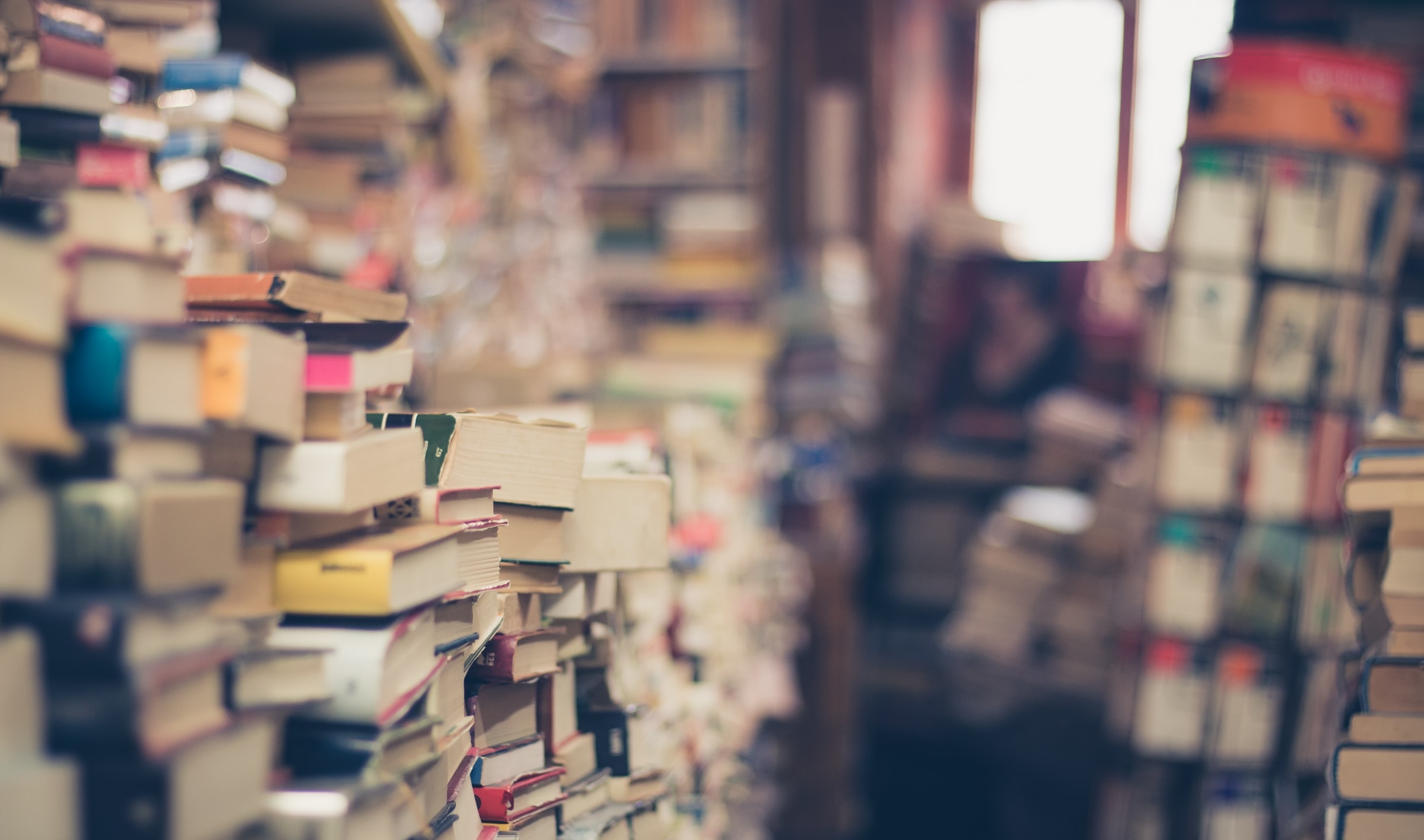
「后台谈话」是由「ONE一个」发起的作家访谈类专栏。我们相信,不管文学场如何人声鼎沸,「后台」始终是那些在写作这条道路上艰难求索的作家,和他们的心灵内史。
谈话者
哥舒意,本名孙辉,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上海作协签约作家。代表作品:《泪国》《恶魔奏鸣曲》《沉睡的女儿》 。
小饭,自由职业者。
小饭:哥舒意老师好。认识您也不短时间了,一直没有机会问,这个笔名的缘由?是不是你在其他地方也说起过?最近看到你好像也用本名在发表作品了,这又是为什么?
哥舒意:小饭老师好,我们认识挺久了,不过确实没有正儿八经地聊过。这个笔名是写第一部小说时顺手取的,出版时编辑跟我确认是不是用这个名字,后来就沿用下来。今年在《人民文学》2月刊发了中篇《与巨石沟通》,编辑是刘汀老师,当年我们一起参加了一个文学奖,也认识了十年了。他因为一直称呼我真名孙辉,在发稿时就问我用这个是否可以,我觉得新年有个新的开始挺好的,真身出道。我也觉得作家最好是用真名。
小饭:你作品很多,风格也很多变。你自己说过,“跨界作者”听起来好像很厉害,但是在出版方看来,这是没有准确定位市场的同义词——那你自己最喜欢写什么样的作品?比如题材。写什么题材会让你感觉到自己是在真正进行自己界定的写作行为?
哥舒意:从写作角度上,我认为一个作家应该勇于尝试不同的领域,不同的题材。但是从出版的角度,作家也是品牌,是商品,需要标签化。所以你最好是悬疑作家,是科幻作家,是现实主义文学大师,是历史学家,并且,在垂直分类里最好能做到前几名。就像科幻想到刘慈欣,历史想到马伯庸,悬疑想到东野阿婆,中国的有我们的朋友蔡骏那多。这些都有助于分门别类,让读者按阅读需要找到你。其实题材什么可能不是限制,有的人一辈子都只写推理,只写科幻,因为兴趣点就在这里。有的人却不喜欢自我拘束,麦克尤恩也写科幻,小白也写科幻,罗琳化名去写推理。对于我来说,题材只是外壳,是内容借以呈现的表现形式。所以到现在为止,我所写的题材都符合我自己界定的写作行为,尤其是长篇小说,可能每个创作阶段侧重不同。三十岁时我写过《秀哉的夏天》《沉睡的女儿》《中国孩子》三部曲,直到去鲁院遇到施战军老师,他点评后我才意识到这三本书其实都是成长小说。这也是那个阶段我的创作。
小饭:如果要向读者,或者一个新朋友介绍你,你会把自己的哪一部作品列入自己的代表作?《泪国》?《造物小说家》?《秀哉的夏天》?《沉睡的女儿》?《恶魔奏鸣曲》?
哥舒意:继续前面说的,作家的创作其实是分阶段的,每个阶段的作品都不一样,目前我仍然是在继续写。最早一定是《恶魔奏鸣曲》,第一部作品,在《收获》上发表,让我走入文学道路。然后第二阶段是《秀哉的夏天》(再版时名《如果世界只有我和你》),这个对我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很多朋友是通过这个作品认识的。比较近的是在《人民文学》上发表的《与巨石沟通》。
还有个多卷本的系列作品还没有出版,我把它叫《泪国编年史》,这个是奇幻科幻,以后人们想阅读了解我某个层面的创作,基本可以从这套书里知道大部分的信息。
小饭:有人称你的写作为“古典主义”,你认同这个说法吗?在所谓的古典主义作家和作品之中,你得到过什么样的启发?
哥舒意:我没有和出版编辑聊过这个问题,我想当时编辑写这个文案的时候,大概因为我写了古典童话系列故事,这个古典的意思是回溯,返璞的意思,就是说我们故事的起源,返回人类叙事开始的时候。这里有一些叛逆,但我也确实认为,小说是要说故事,写作要有意义,写作必须有审美和自己的内在,你也通过写作寻找意义,就像是最早的叙事者,是在篝火旁接受神启,把故事告诉给大家。我看外国现当代作品比较少,尤其是近些年来引进的。在文学启蒙阶段,影响我的是法国那些作家,巴尔扎克,雨果,左拉。他们都具有自己的社会倾向,可能是在他们那里,我受到最初的教育,作家必须有自觉性,写作必须要有意义。
小饭:这漫长的写作过程中,你曾经有过为市场妥协的写作吗?得到过什么样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自己有过怎样的收获?
哥舒意:我倒是从来没有过为市场妥协,因为我真的不知道市场需要什么。在写作上我比较任性,只考虑自己想写什么。曾经在《萌芽》上写过非常轻松有趣的短文,被很多年轻读者喜欢,到现在还有人在转,挺适合做绘本。我一个出版人朋友很认真地说,这些已经不适合作为现在的你的作品来出版了。你的作品是跟着你往前走的,有些事可以先放下。在传统的写作出版上,我不认为真的能通过妥协来获得市场,自发性的写作永远只能忠诚于自己。能够妥协的写作者会是很好的编剧,会是很好的网文作家,因为他们要么是真正服务于甲方,要么是服务于读者,甲方和读者不爽的话,会拒绝买单并且骂人。有一个我尝试达到的效果是,希望文字不要给阅读造成门槛,所以有的作品是连孩子都能读,我的作品给过我的朋友们,你也知道我们朋友基本都是评论家和作家。某长兄和我说,他的妻子一口气读完了,鲁院读书时的老师说,她的妈妈在读这本书,还有两个作家同学和我说,他的孩子很喜欢。但是这样也会有一个问题,文字处理得过于顺滑,有时会被文学杂志拒绝。
小饭:被文学杂志拒绝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很多前辈作家也会遇到这样的情况,比如余华,他会说,“那我再投一家”。如果被编辑要求改稿,余华说,改,只要你发我就改。你会跟余华老师那样吗?
哥舒意:这个话题,每个作家都可以写一箩筐,“你这里要不要啊,不要我去下一家”。其实具体问题具体对待,我第一个长篇发在《收获》,编辑就要求改稿,怎么改呢,原文二十五万,必须删到十万才行,因为只有十万字的版面了,这就没什么选择了,你想上就只能改,把所有的枝节全部删掉,精简到只保留故事主干。这个就是余华说的,只要你发我就改。后来我还遇到过编辑让我先改,拦腰减一半,但是改了也不一定能发的情况,这个我就有点难办,我觉得这可能属于婉拒吧。记得有一次和黄孝阳聊过(他是我鲁院同学,很难过他已经走了),他的《人间世》因为太长,杂志也想要他删,他大概意思说,我已经过了一定要在杂志上发表的阶段了,如果刚开始写作,应该会改的,现在就没有必要,所以他就选择拿回没有发表。编辑和编辑之间也会不一样,他们秉持的理念不同,有的编辑会尽量尊重作者的创作初衷,认为保持原态是最好的,因为成熟的作者在创作理念上有自己的想法,最重要的是展现作者想展现的。有的编辑是尽量为作品考虑,他会以自己的看稿经验尽量帮助作品更完美一些,所以会对作者提出要求。我觉得这两种编辑都难能可贵。我认为被文学杂志拒绝是非常正常的事。每个杂志有自己的审美和用稿要求,编辑也有自己的标准,所以你遇到一个能够契合的编辑是很幸运的事,这个编辑会和你成为很好的朋友。并不存在这篇稿子在这里被退了,在另外的杂志上发表了,我因此觉得扬眉吐气扳回一阵,真的不会有这样的心理。最多在心里想,可能我和这个杂志八字不怎么合。金宇澄老师有一次说,你们不要随便写质量一般的小说,然后到处等待上稿,要写就写杂志不能拒绝的头条作品。我觉得金老师说得对,不过实际上确实很难做到像金老师那样几十年磨一剑,一下子繁花天下开。所以有足够的发表渠道也很重要,这家拒绝,那我再投一家。余华老师真是坦诚得可爱。
小饭:你觉得什么东西最难写?比如人物,人物的复杂性,人的内心,或者现实世界的一些可疑?
哥舒意:写作上有句话是,万事开头难,中间难,结尾难。饭老师列举的这些,想写好都很不容易,其中任何一个侧面,如果能做得很好,基本上作品就能立得住了。可能再现现实尤其显得不易,比方说,现实中,公检法体系是怎么运行的,里面的工作人员的心态和职业习惯,农民工在城市里的生活你是否能描摹出来,你以为他们想的和事实上他们想的是否有差距。这又跟写作进入的角度有关系,所以我不太相信第三人称的主观视角,你的主角是张三,张三是个农民工,你在小说里写,张三想,张三觉得,张三以为。但是这些都不成立,因为你不是张三,你是个写张三的写作者,你对事实上的张三真正的心理一无所知。这方面我很保守,我认为人物获得的信息是有限的,你能写的是有限的信息里呈现的东西。有时写作很像演员扮演一个角色,好的作家往往要经历很多观察很多,才能找到你扮演角色的内心,这通常并不容易。有的人写了几十本小说,你会觉得里面人物都面目模糊,问题可能就在这里。
小饭:哥老师提到的这些我很感兴趣,你认为一个作家的作品,必须从经验出发吗?有没有一种能扭曲和仿造经验的技能让作家获得创作的自由?我举个例子,假如哥舒意老师要写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你必须变成一个女人,还是说只要让你想象自己成为了一个女人?
哥舒意:我觉得作家写作和那个chatgpt原理上很像,首先我们必须建立足够的数据库。数据的来源可以是现实观察,亲身体验,文学阅读,影视观看。所以在年轻的时候,数据不够时,在写作上会显得狭隘,这种狭隘有种可贵的真诚。作家的作品,完全是自身经验的产物,即便是再虚构的奇幻小说,其创作底层都是来自作者的现实映射。就像饭老师提到的,一种能扭曲和仿造经验的技能让作家获得创作的自由,我觉得我们可能是在不知不觉间多少都获得了这种技能,但它可能不是能够无限扭曲和仿造的,它有自己的边界,它的边界就是作者的局限,好的作家,边际会比较宽,在这个边际里,他都能进行再造。如果我要写一个三十岁的女人,可能是要让自己在心里变成一个女人,不是全部,是用你内在的一部分去完成这个女人。我们老是说,好的作家都是雌雄同体。但是十八岁的年轻人,是很难真正想象出一个三十岁的女人,三十岁的女人需要很多生活来填充,并不是进入一个外壳里就能做到,想象自己是就能做到。不过如果在有限的出场时间,表现出有限的内容,这个问题还不是太大。能够写出经典女性角色的那些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托尔斯塔的安娜卡列尼娜,我认为他们都是获得了足够的经验,我们不管这经验从哪来的,这个经验的来源一定非常可靠。我刚发表的《与巨石沟通》,是写夫妻情感的,写妻子。这个小说,我想写了很久,然而只有在我自己获得了婚姻体验后,它的写作才能比较自然。
小饭:最喜欢和文友交流什么?还是会和不同类型的文友讨论不同的东西?
哥舒意:我的写作可能和别人不太一样,我在写作之初没有过同行者,没有参加过类似新概念这样的比赛,那时也没有互联网,是在一个相对闭塞的环境里写作,闭门造车。所以直到很久以后,我才慢慢学会和人交流。但是在创作时,绝对不会拿未完成的作品和朋友商量情节的构思,结婚以后,这个情况好了一些。但是还是不太习惯完稿前的交流。我们那个每个月的小范围聚会,点评朋友的作品,很有启发性,但是问题在于,不同类型之间,对于文本的要求是完全不同的,例如写本格推理的作家只在乎推理逻辑细节和诡计。他们自己之间会有很好的交流。你和这些不同领域作家的对话,也会很有启发,会发现原来写作真的是隔类如隔山。除了编辑,第一次有同行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还是在鲁院时,后来渐渐在杂志上也有了一些。其实这些评论者,他们自己也是写作者,我第一次听到时,其实内心很感动,因为我觉得有人在试图理解你,而且他们确实看到了你自己没有意识到的东西,简直像是做了文本的心理分析。年龄越大越会觉得,能够得到理解是多么地不易,你是通过作品,和这个世界建立起了联系。
小饭:你觉得一个写作者最重要的品质是什么?坚韧?专注?富有怜悯心和包容心?你觉得在你身上你自己最喜欢的品质是什么?
哥舒意:坚韧,专注,怜悯和宽容,这确实是一个写作者身上最重要的几个品质。前两者决定了你可以写下去,写很久。怜悯和宽容决定了你作品的深度和宽阔。我其实是一个很容易分心,专注度和集中力都不太够的人,唯一可以认可的是,我在做事上却很专一,不会半途而废,我想好了一生写小说,我就会一直地写,不管阻力来自何方,不管是否受到质疑。我们都写了应该有十几二十年了吧,大概会一直写下去,不会觉得无趣和枯燥。
小饭:这种信念感不光有用,其实也让人幸福。你说的质疑,很多是关于评论。有什么样的批评你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一个朋友批评了你的小说,言辞激烈了一些,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因此伤害和影响彼此的感情吗?
哥舒意:被批评当然会不开心,这是人的自然反应。不过我也不认为这会妨碍彼此间什么,对一个作品的看法,很多是和审美,和自我的文学观价值观有关。当一个人不认同你的作品,是在这些层面上和你起了冲突,不兼容。这个没有必要强求,你也不用硬要说服对方,你是作家,不是辩论家,不是为某个别人在写作,你始终是在为自己在写,你不可能改变自己来顺应别人。别人也不会改变自己的审美来顺应你。作家始终是通过作品得到理解的,这也是个天然的筛选机制。
小饭:那你在不同的阶段,会不会产生一些与自己之前所坚持的文学理念巨大分歧的想法?这个时候你会做什么样的行动?
哥舒意: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只有偏执狂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如果要证明自己的文学理念是正确的,就必须继续往下写,一直写到最后,没有其他任何可以取巧的方式。把你坚持的文学理念贯彻到自己的作品里。坚持自己的道心很重要,不过万一道心动摇了,就需要更加有毅力地,重塑自己的道心。反正我们不是物理学家,不用对这个世界的运行规律负责。只不过这里说,只有偏执狂才能成功,其实并不是让大家都偏执,更多的偏执狂都倒在了路上,走到最后的人,确实有幸运,也足够坚持。无论从事什么,改变自己的思想其实是最痛苦的事。没有人愿意承认是自己错了。能够改变自己的理念,这往往也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小饭:你觉得一个年轻作者如何保护自己的写作才华?你自己是怎么做的?
哥舒意:我遇到的年轻作者都挺会保护自己的写作才华。其实我不是很理解这个问题,你觉得现实不让你写作了,还是现实逼你写别的了。路都是自己选的,不管对错,都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而且我认为写作和生活,生活最重要。只是有些人的生活,就是写作。
小饭:是这样的。我记得哥老师是养猫的。猫是很多作家的伴侣,人和猫之间,你最在意什么样的交流?如果可以用文字表达,你觉得你的猫对你说得最频繁的是什么?你是怎么想起需要养一只猫的?它的名字叫什么?
哥舒意:如果以后条件允许,我也想养狗,我喜欢这种生命之间的亲密感。养狗比养猫麻烦得多,所以从这点而言,不是作家选择猫,而是作家大多数都怕麻烦。我每天铲屎喂猫撸毛,可能是因为,被需要是一种深沉的幸福,我知道我是被猫需要着,它每天对我喵是想玩想吃想睡。吃饭了一定是它想对我说的。我认真养的第一只猫是和妻子一起收养的一只立耳公橘猫,叫蛋蛋。因为它有一对很完美的猫铃铛,当然已经去掉了。在《与巨石沟通》里,我也写到了它。小说里它是重要角色,勇敢地去宇宙寻找自己失去的蛋蛋。
小饭:在过去的人生经历中,你认为有哪一段是你特别看重的?并被你不断写入作品的?为什么?
哥舒意:人生是个不断抛弃的过程,以前无论你受到过怎样的遭遇,总有一天你会觉得那是可以放下的。人生是个荒凉的旅程。可能在某个阶段,是会有执念,不断地强化这段经历,但是总体来说,是渐渐淡去的。我不觉得自己有什么是不断写入作品。但我也理解有的作家不断重复同一个主题,对他来说,可能每一次的再现,就是每一次的谅解,就是每一次的救赎。
小饭:现实生活给你带来的灵感更多,还是精神生活给你的更多?你怎么看待灵感这回事?
哥舒意:在比较年轻的时候,可能是精神上带来的灵感比较多,因为那时确实没有和这个时代,这个社会产生过多的关联,你所有的知识,美好体验,强烈感情都来自文学,影视,音乐。但是随着年龄越长,你开始入世,和周围世界产生强关联。以前我对我父母辈,祖父母辈的故事都一无所知,也不想知道太多,但是这些年,我越来越想知道他们的过去,他们经历过什么,你也会对同时代的境遇本能地产生反应,并且想用故事再现它们。我认为灵感是头脑训练的结果,是在生理层面可以解释的现象,大脑神经元的突起产生了关联,有的人天生突起比较多,这就是天赋。但是大脑是可以训练的,经常使用是会强化这一点。日常的写作读书都是在进行训练。
小饭:说起天赋,你害不害怕AI,chatgpt抢了自己的饭碗?你觉得自己(或者这一代作家)在这玩意儿面前的竞争力是什么?
哥舒意:我其实有点沮丧,我沮丧的是,我的写作跨领域,每个阶段写得也不一样,看来并不能让它深度学习来替代。如果它能根据我的数据模仿我的写作,我觉得我的产出会提高吧,相当于有了分身。可能诗歌,网文,套路化的写作,有更高的替代优先级。它可以模仿我们的作品,但它无法模仿我们的人生。而我们的人生我们的经历,塑造了我们,再由我们创作出了自己的作品。但我认为,AI和编辑,AI和作家的合作,有可能会产生火花。
小饭:现在如果让你去一个国企上班,你愿意吗?朝九晚五,享受人间烟火?但是可能会让你失去很多写作的时间。
哥舒意:不愿意。我中间有很多年去工作了,没有持续化地写作,我做过编辑,也做过公司的合伙人,有期权。但我还是想继续写小说。比较一下工作和写作,我的感觉是,如果是工作,其实很多人都能取代你,并不是缺你不可。但是写作,你的作品只有你能写出。写出一部作品的满足感是其他无法取代,哪怕是很多钱。物质消费给我带来的满足感其实是有限的,我到现在都没有买车,在现有生活的条件下,没有必要为了更多的钱去消耗自己有限的人生。我认为我是通过写作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我并不是说工作不好,而是觉得,写作就是我的工作。
小饭:你相信命运吗?是一个宿命论者吗?有没有想过改变自己的人生——哪怕其中一段?
哥舒意:可能在某种程度上,或多或少相信一些。我好像不太好说自己是否是宿命论者。是所有经历的事,把我塑造成了现在的我。我有想过改变过特别有伤害,特别灰暗的时刻,比方说我小时候被电击伤,差点截肢,留下半边身体的伤疤,还有其他的。但是这些灰暗的时刻,也是塑造现在这个我的成因,我的性格层面,心理层面,多少都会有这些黯淡时刻带来的影响,但是我挣脱了它们,也可能是共存了。毛姆有一部小说,《人生的枷锁》,人确实要摆脱很多桎梏自己的东西,但是也要学会接受,因为它们已经成为你的一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