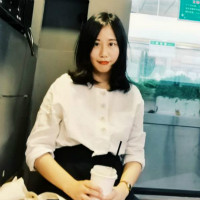一年就这样结束了,而风暴终会平息,我仍可以选择下一次的出航。
1. 这一年,与飞禽走兽相依
作者:杜梨|现代文学和创意写作硕士,已出版《致我们所钟意的黄油小饼干》《孤山骑士》。
院中的灰瓦檐上,银杏树正是盛黄期,大风将它刮疏一些,逐渐地呈扇形滑落,慢慢地落空。这美凋零得很缓,被咖啡丈量过的时间,窸窣通过北京这盏琉璃沙漏。北京很少有这么漫长的秋天,秋天通常很快就过去,漂亮的衣裙也很短暂。
今年的核酸很漫长。因工作原因,我大概做了两百次核酸。从未因十混一被扣下,也幸运地躲过一切封闭。到了年底,终于和大家一起,应声倒下,感觉过往的时间都被浪费了。
这三年,离京次数一手掌握,和八十多岁的奶奶只见了两面,哪怕奶奶就在燕郊。婚假去厦门呆了几天,不幸被批在最热的季节。扛着大炮在闽南38度的高温中寻找南方的鸟儿,闪耀的栗喉蜂虎衔着蜻蜓,强脚树莺躲在灌木丛里偷偷唱歌,随便一听就能捉到妖娆的画眉鸟。闽南的溽热和繁茂的榕树,还是给了我超出肉体承受的美。这是我今年唯一一次出京,我很珍惜。
如果不能出门,我就在家采访,写小说,读好书,刷动漫,逛手办,买各种类型的手工和原材料。或者蹲在地上挖土种菜,陪我的动物们一起玩耍,不同的动物都要游戏至少几小时。春夏的育雏季,楼下的灰喜鹊家族经常在清晨4点50左右大声惨叫,我会准时惊醒,迅速冲下楼,往往能看见上树攀援的流浪猫咪,坚定又狡猾地慢慢向灰喜鹊的雏鸟逼近。我跺着脚嚷两句,猫咪就跑了,灰喜鹊也能恢复平静。有一个月我为此精疲力尽。
一天,我下班回家,十多只灰喜鹊压着粗哑的警报声,一齐扇着淡蓝的翅膀,纷乱地从一棵柳树冲到另一棵柳树上,而在树下,一只橘猫衔着幼鸟,迅速穿过道路,躲进了一边的绿化丛。我跑过去,“天啊!咪,你吃了一只小灰喜鹊!”
橘猫放下猎物跑了,它还会回来的。我前去查看,并不是小灰喜鹊,而是一只斑鸠的雏鸟,早已没了生机。灰喜鹊家族的愤怒驱逐,竟是出于鸦科智慧所发出的邻里警报吗?我有些感动。吃过饭我再去看,斑鸠的尸体已经被猫儿叼走。而那对斑鸠夫妇下了地,在土地上四处走动,不停地大声咕-咕-,那咕声与往日不同,似乎是在寻找消失的孩子。
育雏季节出意外的雏鸟算作自然损耗,但随着气候变化加剧和人类活动等影响,育雏的艰难是肉眼可见的。流浪猫咪也不能算城市的野生动物,而是应算人类遗弃家猫所带来的次生灾害。猫咪捕猎是天性,领养代替购买,也是助力城市生态的好办法。
今年,我在东宫门收养了一只全身皮包骨,奄奄一息的小流浪御猫。如今,小帕尼尼已经是6个月的8斤巨猫,油光水滑,炯炯有神。园内的流浪猫扎堆生活,靠着百家饭命如薄纸。只有一位相熟的同事姐姐不停地帮园内的流浪猫幼猫找领养,捕捉成猫和亚成猫做绝育,都是靠自己微薄的薪水。酷热的夏日,她骑着电驴到我家,给帕尼尼打针,帮它度过了最艰难的一个月。每每想起这些,总觉得还是好人多。
我买了很多盆营养土和蚯蚓肥,播种了农科院的高级种子,刚刚萌芽我梦想中的白菜,就被松鼠刨得一干二净,只有我的四川辣椒们顽强地躲过了它的攻击。松鼠进了秋冬,着急地囤粮,一出来玩儿,就把所有的坚果都挨个埋进她信任的花盆中,携着各种小种子,冲进房子的各个角落,四处寻觅她安心的地方。本来不喜欢南瓜籽的她,把我妈晾晒的所有南瓜子全部薅下,把那些滑滑的南瓜籽都挨个种进了盆里。
不多时,阳台上长出了一茬又一茬的南瓜芽,南瓜芽生长极快,直直的腰杆儿,两片小叶子对开,叶片和茎秆都毛绒绒地扎手。有一株南瓜秧,甚至迅速蹿了一米多,开出巨大柔软的黄花,带着锯齿边缘的叶片晃悠着,看着让我很感动。松鼠知道这是她种出来的吗?她可能根本不知道她种下的南瓜种子都开花了,但那些可爱的南瓜秧子在被我们拔掉之前,一定对这只硕鼠心怀感激。松鼠知道她藏东西的每一个地点。这更加让我确信,世界上的大部分松树都是松鼠种的。
单位要求两点一线,健身房停了又关,打破了常年健身的规律。2020年初,我买了杠铃,壶铃和哑铃,我妈给买了高级防震垫,在客厅铺了一片天地,能回父母家我就举铁。不回时,我穿好速干衣和压缩裤,捆紧护膝,去空旷的地方跑4-7公里,回来再吃氨糖软骨素和钙片。买了新的泳衣和泳镜,等疫情过去,要去学新的泳姿,还想去潜水和度假。
每周的休息日都是单休,我就抓紧那一天和家属去徒步或爬山。下半年,我买了相机和镜头,再约各种自然之友去四处拍鸟,认识了不少有趣可爱的朋友。有几个月,一轮到休息,我立刻早起,吃完早餐,载着朋友们,带些士力架或两个面包,拎1.5升矿泉水,带着8斤的设备进山、野地或是郊野公园,去寻找各种各样的鸟,回到家中已是傍晚。我逐渐适应了索尼200-600的镜头重量,甚至两边手臂也变得紧致,肌肉造型不费吹灰之力。
有次去爬居庸关,台阶上咻然长出两只黄口小鸟儿,我以为自己是在动画片里。旁边的垛口中,工人师傅们在装修商店。那是两只从烽火台垛口的窝里,被大风吹落的雏鸟儿,有只掉进了工人师傅的水桶里,被师傅捞出来,浑身湿漉漉的。我看到了它们的父亲——北红尾鸲,雪花小平头,歪头衔着蜻蜓,橙棕色的小衬衫,四处找机会落地。我和小书将它们移到旁边的草地,避免游人踩踏,那小小的父亲立刻追过来喂食。只要雏鸟还在,哪怕已经送不回高处,亲鸟都不会放弃喂食。
秋季猛禽迁徙季,我背着相机和食物,夹着小板凳爬到百望山的猛禽观测点,在山上站一天,和大家一起观看各类猛禽迁徙。常年在百望山附近生活有红隼,白尾鹞和雀鹰,而迁徙的猛禽经过,只是遥远晴空中的一个小黑点,需要很多双眼睛一齐观测。最常见的是普通鵟,也就是我们常说的老鹰,而雕、大鵟和某些鹰则数量较少,需要运气。还看见了草原雕、短趾雕、凤头鹰、白尾鹞、苍鹰追着打普通鵟等一系列珍贵的鸟类。接着,便是过冬的雁鸭,各种娇艳的朱雀,燕隼夫妇育雏,长耳鸮一家过冬。
去年我结了婚,今年我拍了结婚照,明年我再举办婚礼。今年,我接待了无数游客,生了无数的气,完成了第一部非虚构集,写了满意的采访和稿子,新的小说也让我快乐。给猫盟的月捐刚好两周年,蚂蚁森林、庄园、海洋和种果子每天都在坚持,我和栗鹿助养了一窝生活在阿勒泰地区的蒙新河狸。忙碌是快乐的,运动是快乐的,但最爱的还是睡眠。
如今,我的身体变得更结实,抗阻能力变强,体重因爱吃零食上升,BMI也升至21,肌肉含量达到了76.4斤,内脏脂肪4斤,蛋白质也达到了18.4的优质标准,成为标准肌肉型。
这是个月球离我们越来越远的宇宙,我将带着这强韧的体魄进入2023,回首无路,只能用力向前跑,夺回逝去的日子。
2. 佛光佑人
作者:虫安|写作者,故事发烧友。
今年我专职写稿已有6年,2019年,疫情还没发生,我也开始转运,到处发稿,到处卖稿,口袋鼓鼓的,每天睡到自然醒,睁开眼就想着去哪儿花点钱。
这高速上坡的一年,我在one也发了一篇2万字的悬疑小说,叫《囚门恋》,影视版权卖给了一位拿过金马奖的导演。
疫情开始后,我的运势还在上升,一本没指望过审的书出版了,首印了3万册;获奖的短篇也开机了,张国立导演,韩三平监制,刘震云文学指导,范伟周冬雨主演;一篇一万字的短篇还拿了阿里薪火故事大赛的首奖,去阿那亚领完奖,版权也卖给了一位我很喜欢的女导演。
疫情3年,大环境很糟糕,但写作者能碰见的好事,就像消消乐,被我一路撞上了N多的同色方块。
2022年,我的运势开始下坡,签下来几份文学策划和编剧的合同,全都半路撂挑子,收不到尾款;仓促写成的一堆稿子也没能“过编”,没混来稿费;人际关系也四处恶化,好心办了太多坏事,被朋友谩骂也被家人指责;国庆节去游玩的途中,还出了一次车祸,车子撞上了高速的护栏,幸好护栏牢靠,不然车子就冲下了山崖,小命难保。
我是89年生人,生肖蛇。算命的说,今年我犯太岁,万事都得当心。我便迷信起来,买了本命佛的牌子,又去九华山烧香。回来后,过日子就像登冰山,担心滑脚,担心坠崖。
兴许是前两年过得太好,膨胀的心态一下子收紧,人就很难受。
今年写作方面没什么进展,空闲时间就多,我便总去打球。一天,我在球场碰见个“强手”,球风硬朗,个头虽小,却很会用身体。只是他的指甲盖蓄得老长,把我的手臂划伤了,我便骂了一句脏话,氛围立刻被挑热了,大伙儿腾出空间,让我两“斗牛”。
我憋着一年的火气,当然应战,结果没讨来一点便宜,反倒被他剃了光头(一球未进)。他那边的队友欢呼庆祝,嘴里喊着“卧槽,牛逼呀!”,我感到自己被羞辱了,捏紧了拳头,要去打人。一个朋友眼看拽不住我,喊了一声:“你不晓得你今年犯太岁呀!”
我那只就快伸到对方脸上的拳头,有了一丝松动,悬停在半空中一秒多,总算缩了回来。
事后,我了解到那位强手才20岁,曾经入选过CUBA阳光组。我打不过人家很正常,跟他较劲,实际上就是一种傲慢和装逼,是眼里没谁,“让你晓得老子有多牛逼”的膨胀心态。结果,自然拎不清自己的实力,输球又输品。
回家后,我有一丝后怕,要是那一拳没收住,就得二进宫了,轻则吃15天牢饭,重则回炉再造两三年,续写下一本《监狱风云》。
我庆幸请过神烧过香。
有天,我发现佛牌没在脖子上,到处翻找。我以为打球弄丢了,后来发现掉在了球袋的夹层里,是那天打球时摘下来放进去的。
2022年底,我干脆孵在家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奥密克戎却是挡不住的灾星,朋友圈里的人却都在渡劫。我想我也躲不过去,但脖子里挂着佛牌,心里便也安稳了不少。
倏忽一下,2022年就要结束了。朋友们,如果你还身处低谷,运势不对,该烧香烧香,该迷信就迷信吧。
迷信便是相信,一切会好。
3. 写在阿根廷夺冠后
作者:郑然|青年写作者,编剧,现居上海。
动笔的时候,才发现总结自己是最难的。脑子里都是碎片式的记忆,但也许这才是记忆真实的样子。那些记不起来的影子或是忘记的事情,也就无法成为自己的记忆。就像法国作家安妮·埃尔诺在回忆父母亲时,曾说,我也不知道该从哪开始说起,但她想把能记住的都写下来。大意如此。
首先是忧心的部分,作为一个人对自己身体的了解程度,这一年明显觉得身体比之前差了很多,生了两回病,病程都比我自己预料的要慢。大部分时间总是觉得累,想睡觉。也总是忘东西,回忆事情有些费劲,令我很焦虑,觉得自己进入了某个生命特定的阶段。但又觉得自己没做好准备迎接它,一直在用过往的经验来应付它,这种焦虑延续了一整年,但又无法真正开始解决这个问题,一来是时间不够(当然,也许是借口),二来总是对锻炼的事情一拖再拖,好在拖到年底,终于进入一些状态,开始锻炼起来,这是个好消息,我希望能一直延续下去。
今年印象最深最高兴的事,是在福建平潭看到的非常美丽的夕阳。因为工作关系,七月初去了一趟平潭岛,到达的第二天傍晚,在回酒店的盘山公路上看到了晚霞,那是我第一次了解“霞”的含义,彩色的云,但这不是字面意思,而是你必须亲眼见到它的样子。昏沉沉的晚霞落在海岸线的风车上,巨大的白色风力发电风车那时逐渐变成一个高大的影子,我坐在车上想将它的样子拍下来,可按下快门的时候,却发现无意间拍到了公路边一对手拿烟花拍摄婚纱照的新婚夫妇,因为车速,他们的样子看上去有些模糊,但笑容清晰,成为我这一年印在脑海中久久不散的画面。
年底,卡塔尔世界杯开始的同时,国内的防疫政策也逐步放开。奥密克戎传染的速度超出大家想象,不到两周,身边的朋友和家人都纷纷阳了,一方面担忧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抵御这种病毒,一方面又希望朋友和家人都能安全顺利度过这波传播高峰期,像三年前那样,大家可以重新自由安排自己的生活和旅行。
12月19日凌晨,看完世界杯最后一场阿根廷vs法国的伟大决赛,当阿根廷军团一代又一代伟大的球员陨落在那座大力神杯面前,最终在2022年的冬季,夺得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冠军,登临足球世界的王座。之后我反复重看了蒙铁尔最后那个制胜点球,心情久久难以平复,但更多的是喜悦之情,这是一场献给所有人的成人童话,也给这一年画上了完美的句号。许多平时不太关注足球的朋友也坚持看完了这场将近三个小时的比赛,三年疫情的困顿和憋闷,总需要一些振奋人心的消息和传奇。我在其中一位朋友的朋友圈看到一条动态:“愿这世上所有的奇迹终将实现。高兴!”
毕竟,阿根廷为足球梦想奋战近四十年最终圆梦的故事,还不够让你我相信生活,热爱人生吗?
4. 跌宕之年
作者:兔草|退役文案,杂耍写手。出版有《研究怪兽的人》《去屠宰场谈恋爱好吗》。
三十岁后,我的土象星座特质越发明显,这主要体现在我极其热衷于列计划,按清单执行,不接受任何偏离既定轨道的事情发生。然而,2022年所经历的一切仿若一则寓言——我驾着一艘目的地清晰的小船出航,却在中途遇到暴风雨,待一切平息后,我总算捡回来一条命,但去往理想之地的航道已经毁坏了。
在短信搜索栏键入“延期”二字,跳出来数十条密密麻麻的信息,原定于春天在上海观看的音乐会、话剧统统延期,而在盛夏,我离开生活了五年之久的魔都,回到家乡,那些没有看成的演出终究成了无法弥补的遗憾。
许多事情都与预期相违背,比方我以为之前工作的那家外企永不裁员,可以一直做到退休,结果在七月的早晨,我拿着一杯拿铁坐进狭窄的小会议室,领导满脸歉意地通知——“你被裁员了。”是一种极复杂的心情,有不需要上班的解脱加上拿到不错赔偿金的喜悦,但同时也对一切产生了怀疑,这意味着要比原计划更早地离开上海了。还有许多事没有做,还有很多人没有见,还有很多列在笔记本里的玩乐地没有去,但“分手信”却已经递到了我的手中。
四十度的高温,城市仿若发烧,我在车站等车,同事过来跟我搭话,问我后续的安排与计划。人近中年,失业后几乎再难找到工作,人生开出新的词条,我“被迫”成为了自由职业者。原以为这件事还会延后几年,但它轰轰烈烈地降临了,我成了那些文章里的“中年失业者”。只是这一次,没有那么颓丧了,好像已经预习过一遍,立刻就捡起了之前预备好的方案,开始低消费加搜索远程工作。
翻开2022年初列的计划安排,唯一没有完成的一项是——“带妈妈出门旅游”,原以为这是最轻松容易完成的一项,却没想到在今年成为最难的事情。我们真的哪儿也没能去成,无论是距离武汉极近的恩施,还是一直想去却一直没能去成的泉州。
2021年,我和母亲一起去了扬州、临海、石塘。在临海的一家咖啡馆,我见到了老朋友路丁。在那个颇有复古风情的咖啡馆里,路丁点了一杯名为“白夜”的咖啡。我们整整聊了四个多小时的天,谈写作,也谈生活。可能是都混得不尽人意,所以有一种失败者会谈的感觉。夜晚,要分别了,我想,这是难得的一期一会,要是每年能见上一次面就好了。而现在,生活的地理范围已经离开了江浙沪,感觉似乎更难见上面了。
下半年,宝铂理想国文学奖揭晓决选名单,朋友小周入围。我忽然想起,也就是前年,还是去年,我和小周在上海见面,我们一起经过一大片嘈杂的工地,小周谈及出版的困难及发表的愁苦,声音逐渐低了下去,好几次,我都听不清他到底说了什么。我一再安慰他,你还年轻,年轻就代表有很多的机会,但他表情还是很痛苦,好像对未来缺乏期待。不过今年的一切证明,有才华的人始终会被更多的人看到。如果今年的他穿越回去,遇到当时的他,或许也会拍拍对方的肩膀说,没什么的。
人无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饶是我这样的算命爱好者,也不真的清楚未来有什么在等着我,常会想起儿时家里附近的一座彩虹色滑滑梯,感觉高有数十米,人从上面滑下来,会产生眩晕之感。我生性胆小,缺乏冒险精神,从来都不敢坐那种滑滑梯,而生命之中,那滑梯却始终存在,成为我绕不过去的心理障碍。
以前在书中看过一个曲线,所有的事情都是起起伏伏的,但从大方向看是上扬,这个规律好像被叫做“螺旋式上升”。我总开玩笑说,三十岁后,人生全是下坡路,坐滑滑梯啊,一路坐到底,屁股被砸得生疼。但现在看,这个下滑的过程也不全然是痛苦与恐惧,我甚至能抬起头来看看中途的风景。
虽然没有带母亲离开武汉去外省市旅游,但在这座城市里,我们结伴度过了一个秋天。二十多岁离家,在北京与上海漂泊十余年,其实很少和母亲相伴一个季节,现在,我们在秋天观赏到了城市里最美丽的风景,一起吹了江风,一起看了银杏,似乎也是另一种形式的“出门旅游”。我在龟山公园的坡道上说,这地方看起来像济州岛,或者,就假装真的已经置身于济州岛了。
每隔一阵,我都会更换自己的“手边书”,就是那种一放好几个月,甚至大半年的那种。在春天,我的手边是一本马雁的杂文合集《读书与跌宕自喜》。我一直搞不清楚“跌宕自喜”这四个字是何含义,这几日闲来无事,突然查了查——“跌宕自喜”一词出自《诗辩坻》卷三中毛先舒评李白七言歌行曰:“太白天纵逸才,落笔惊挺。其歌行跌宕自喜,不闲整栗,唐初规制,扫地欲尽矣,乐智生活。”翻译成大白话就是:“不管处于什么样的处境都悠然自得,不丧失志气,自我调整到一种喜悦、安乐、轻松的状态。”
在这本深蓝色的大部头书籍上,还有一行小小的字,刚好印刷在奔涌的浪花之上——“以书写与念诵拯救事物于黑暗”。阖上书,有光涌了进来,一年就这样结束了,而风暴终会平息,我仍可以选择下一次的出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