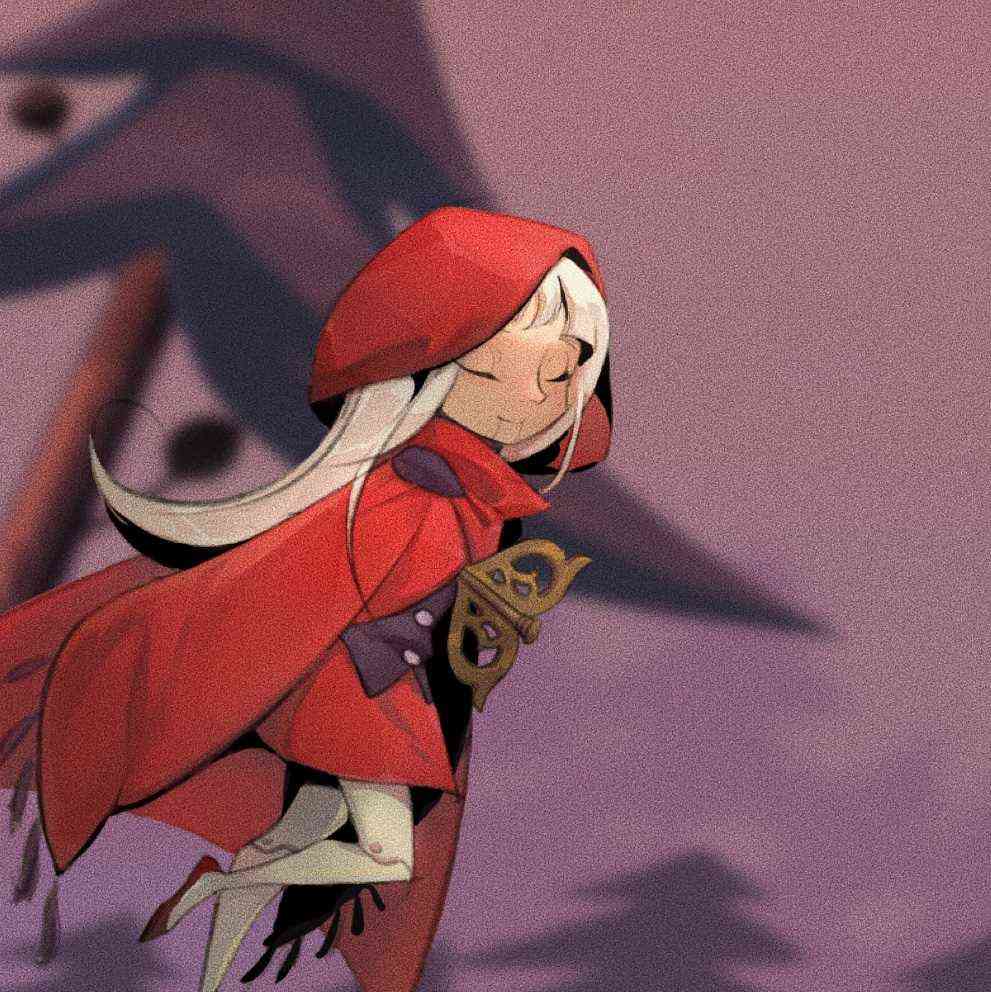一
姥姥的名字叫作马秀琴。
金戈铁马的马,钟灵毓秀的秀,琴心剑胆的琴。
但我却从未曾听过有人这样唤她的名字。能够这样喊她的人已经不在这个世界,留下的只会叫她妈妈,姥姥;或者,那老太太。
记忆里最后一次见到她,是在大三的暑假。姥姥家的老破小拆迁,搬到我家里来住,就住在我过去的小房间。
那些日子,她总是一个人坐在床上,望着窗外。窗外只有一条几乎没什么人会经过的马路,一次暴雨把窗前的高树劈掉了一半,她却能一直看到天黑。不说什么话,也不开灯。
二
我是被姥姥带大的孩子,但却已很难想起过去我们曾共处的那许多个年头的细节。
有时我甚至觉得每个大人从孩童时期以来的那些已经被忘记的,不管怎么努力也没办法记起的连续时间也许都是从未存在过的。我们就像科幻小说里的那个终于发现自己名为“过往”的记忆都是被捏造的主人公一样,时常陷入自己在过去究竟是谁的虚无。
脑海里与姥姥相连的记忆碎片是她身上的味道,那是一种很旧很闷却又很温暖窝心的味道,一种似乎只属于老人和她从过去的生活里带来的,有些年头的气味。像血液融进骨髓里一样藏在她的围巾、衣柜和被褥里,藏在她短短的头发、下巴软乎乎的褶子和数钱、翻书时候的唾沫里。直到现在,它又出现在我过去那间小小的卧室里。
姥姥家的老破小从传闻拆迁至今已经过去了十多年。
最早拆掉的是离姥姥家那一栋不远的一片棚户楼,几乎是一夜之间,家门外变成了一片由瓦片、土墙和木板组成的泛着潮湿的霉味的海。
那些被粉碎了的不合时宜的旧房子,就像一下子被抽去了筋骨的巨人,从能够遮住云彩的地方轰然塌陷。房子的器官在看不见的夜里散落一地,不知从哪涌出的积水,就像房子最后的血液,在破裂的墙壁缝隙里,供养着不知从哪里游来的野鱼、蝌蚪甚至癞蛤蟆。
砸得大小不一的墙块,是一个个摇摇欲坠的小岛。一群尚没有读书的小孩,成群结队,在这片时日无多的废墟之海上,为能抓到一条鱼,荒废一整个下午的时日。
这片废墟并没有被很快地拾掇起来。它以极快的速度出现,却又在那之后像是被遗忘了似的被长久地停放在此。
那时候,每天下午我总是带着装满水的矿泉水瓶跟着两三个比我都要大些的男孩儿向着废墟的更深处“探险”。我们找到了一处将将能够五个人一起坐上去都不会感到挤的大平台,幻想着能在阴沟里抓到迷路的大鱼。
废墟里的鱼知道自己正赤裸地在一片陆地上横冲直撞吗?知道自己吮吸着从过去生命中携带而来的水,终会走向干涸吗?来自过去的水总会有再也不足以聚合成供养他们的海洋的一天。
废墟里的鱼就是这样荒诞地挣扎在自己无法决定的命运里。但这荒诞的图景却让童年的我们感到快乐。
三
姥姥说她过去的家也是这样一栋不合时宜的自建房。低矮,年迈,尘土飞扬。她在那间房子里永远地失去了自己的丈夫和小儿子。
我的妈妈和两个姐姐在成年后决定带着母亲离开家乡,去到另一个更加先进的、年轻的城市生活。她们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地告别了老房子,就像告别贫穷,告别读不起书的愤懑,告别三个孩子分食一颗鸡蛋的窘迫。
那一年,姥姥的人生已经过完了一大半。
四
四个女人的身份仿佛就在一夜间发生了置换。空间切割出的,不仅仅是城市的边界,更是年过半百之人对于之后生命与生活的想象力。
或许连她自己都很难说清,是从哪一刻开始,她似乎再也无法决定自己命运的走向。
是从那列从北向南驶去的绿皮火车开始吗?还是从那间陌生的六十平米的清水房开始?一步一步,就像是被女儿们抬起脚,却被蒙起眼,不知道下脚时会落在哪里。
我和哥哥就在那一间未经修饰的清水房里被抚养长大。老人因循着旧日将四个女儿拉扯成人的智慧,将全部的柔情与迂腐都灌注在了完全属于这座城市的我们身上。那样的她鲜活而矛盾,既带有年长之人阅尽生活的坚定,也带着对崭新世代和城市环境的胆怯。
儿时的我并不能够理解这些。我只知道姥姥是特别的,她带给我的一切都是素未谋面的新奇感。
她会把我和哥哥穿小的衣服剪开,用木尺子比着裁成四四方方的方块,用大锅熬成的米糊糊做成的胶水把它们粘成一块块的手工花拼抹布。一块据说可以卖几分钱。她做这些的时候我就搬个小凳子拄着腮在一边看着,觉得把旧衣服变成可以卖钱的抹布的姥姥实在好厉害。
每天早上她要赶早市去买菜,一天三顿,没有什么花样。比起姥姥的菜,五角钱一包的辣条和一块钱三根的棒棒糖对我来说才是八珍玉食。妈妈每周给姥姥固定的买菜钱,钱不多,但她还是怕丢了,或是在人挤人的菜场被扒手顺走。为此,她在秋衣的内衬里缝上了一个布钱袋,将零钱码齐、折好,塞进衣服里,等到小贩大声嚷嚷着结账时再慢慢从钱袋里把所有钱拿出来,一张张数好确认没错,再极小心地把对应数目的零钱递出去。我以为这个世界的人都是这样装钱的,也都是如此认真地对待每一角钱。
姥姥还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每个周日都要跟着几个奶奶一起去社区的教堂做礼拜。从教会那她得到了一本黑色封皮烫金字的《圣经》,央求我帮她在扉页写上自己的名字,那年我刚刚上学,字写得歪歪斜斜,姥姥却高兴地说:“啊,姥姥的名儿是这么写的?俺们媛媛真厉害,啥都会哈!”那之后她每晚睡前都会坐在床上眯缝着眼睛念念有词,中间的一大段琐碎我早已没了印象,在当时的年纪恐怕也听不懂,只记得每次祷告完毕后她总要重重地说上一句“阿门!”每次祷告的内容也都不一样,有时是祈求上帝保佑我的感冒快点好起来,有时希望他保佑我三门功课都能考满分,再后面保佑我考上一个好高中,考上一个好大学……
古文明的训诫和十字架的隐喻都太沉重了,在一个老人坚定而单纯的爱里,连上帝都需要入乡随俗。许多年后,当我读到丹麦哲学家索伦·克尔恺郭尔的一句:“信仰上帝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决定,而是在完全无法知晓未来时的纵身一跃”时,我想到了姥姥。我突然理解了为什么她那样热衷于给自己“找点事做”,因为好像必须要存在一桩可以称之为“信仰”的事业,用来帮助她打败衰老、软弱和一无所知的恐惧。
也许只有这样,才不至于在一日一日的重复中,无比清醒地看见时间正从自己的身上碾过,而未来,没有什么可期待。一切旧事都已变成废墟,一切新事都是封堵希望的围墙。
五
后来渐渐地,妈妈开始跟姥姥频繁地吵架。大到管教孩子的方式,小到“这盘菜还没有炒到断生为什么就端上来,吃了不会生病吗”“为什么总要在出门遛弯的时候捡些破烂儿回来堆着,你就不嫌脏吗”。任何一个由头都可以成为她们的声音逐渐拔高的理由。亲密无间的相处让鸡零狗碎的日常变得令人烦躁,让她们变得一刻也无法忍受那些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的细节。如此经年,直到姥姥不再应声,开始沉默地接受着女儿输出和给予的一切。
她好像在某一天里突然就变成了一只撒了气的气球,不再依靠频频的歇斯底里去争论攸关生活种种的对错,不再总是以“我难道没有好好把你们一个个养大,我饿死你们了吗,没良心的东西”为武器捍卫自己依然能够坚信的正确。她不再关心女儿们的生活,她们的家庭,更下一代的未来。吃饭,睡觉,不思考,也不争吵,活着对姥姥而言变成了一件非常平铺直叙而异常简单的事。
她主动自发地遗失掉了过往为了将日子填满而养成的勤劳习惯。在过去支撑着她度日的那一套坚实的叙事逻辑,似乎在很短的时间内迅速瓦解掉,连同着堆放在水池边成山的碗盘,落满灰的阳台、桌面,被油垢封印的吸油烟机和灶台,整日整日开着的电视和滚烫的机顶盒,我所熟悉的姥姥被沉默、迷惘和孤独一并吞噬了。而那时的我就像一个忠诚的卫兵,不假思索地与年轻的母亲站在同一战线上,回之以冷漠。
六
二零零九年的除夕,是姥姥第一次离家出走。不过这只是站在我的视角下的陈述,对于姥姥而言,她只是迫切地想要赶回她原本该存在的地方。
我们至今仍不知道不会用智能机的她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买到的客车票,又是用什么样的方式去到了客运站。因为没有行李箱,甚至也没有可以长途旅行用的背包,她只好将那一点点能称之为“家当”的行李包成一个布包袱,像极了江湖剧里那些趁着月黑风高在腰间系块儿布兜就行色匆匆隐没于黑暗中的无名女侠。
白天的时候大家还没有意识到不对劲,因为白天姥姥一向在家里是坐不住的,必须要出去四处转转,有时候走远了,午饭就来不及回来吃了,为这事他们已经闹翻过多次,所以也没人在意。但到了下午,妈妈开始觉得不对劲,一般快到了晚饭点,姥姥就会回来,更不必说那天还是除夕,每年的除夕夜,我们总会比往常更早开饭。急忙翻出电话本联系了一圈,把能问的人都打听了一遍,我妈终于慌了神,拽着我爸去报了警。我被一个人留在家里,对着一桌子做好的菜也不敢动筷,心里觉得既害怕又委屈,不明白期待已久的年夜饭为什么会变成这样,担心姥姥遭遇危险,却同时也对她生出无限的怨怼。她无法知道除夕和新年对于一个孩子的意义,就像我也无法知道日常生活到底是有怎样的重压,让一个老人窒息到必须逃离的地步。
三天后的早上,姥姥自己回来了,轻描淡写地告诉我们她独自回了趟老家,随之而来的自然是一场不可避免的激烈争吵。交手多年,对于这样的场景她们已经太熟悉了,用什么样的语气说什么样的话可以正中靶心,什么样的神情能让对方更清晰地看见自己的愤怒,一句一句,她们的声音纠缠在一起,化身成一只目眦欲裂的野兽,在房子的上空不停歇地咆哮着。那样的妈妈不像妈妈,姥姥不像姥姥,而夹在中间的我,却因此染上了要用一生的讨好去消解对于冲突和崩坏的恐慌。
争吵以姥姥几乎喊破喉咙的一声“杂碎”收场,她们都哭了,那实在是一个让人难忘的年。
此后老人除了吃饭的时间很少在家里露面,不是在天还蒙蒙亮的时候就穿戴整齐出门了,就是一整天窝在房间里也不说话,有时候路过姥姥的房间能隐隐约约听到老人自己在碎碎念,说的到底是什么也听不清楚,像极了过去她所热衷的同上帝的对话。妈妈总是觉得姥姥一定是背着她在咒骂着她和两个姐姐,然后继续沉默着做饭、洗衣,养活下一代。她们似乎都没有欲望,也不怀抱任何希望能够修复这段不知从何时起崩裂的关系。
一次放学,冬天,天黑得早,远远地我看见姥姥一个人坐在小区里的长凳上,头戴着自己几年前手织的大红色毛线帽,两只手因为冷蜷缩在棉衣袖子里。我原本以为,每天在外面要待上好几个小时的姥姥,是因为认识了些要好的朋友,能够彼此作伴,说说话。
我心里的某处突然觉得很难过。我看着姥姥,就像在海上凝望着黑夜中一个就要被风浪淹没的寒冷的,破碎的岛屿,她与这个世界间存在着一层我们看不见也永远无法理解的障壁。那些可怖狰狞的看似没来由的暴躁,那些掺杂着咒骂的饱含怨气的哭喊,都是她想要冲破这堵墙,随着时间继续走下去的呼救。她的反常绝不是因为她的老年病,因为年迈取代了理智,憎恶取代了爱意,而正是因为她对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一切震荡的感受太过强烈,而能够作出的回应却几乎没有。
我走上前,轻轻拉住姥姥,问她:“姥姥,一个人坐这干吗呀?”
老人抬起头,看我,笑着:“媛媛回来了,走,走着,回家!”
七
陪妈妈回老房子收拾东西的时候,我在姥姥过去的房间发现了她没有带走的《圣经》,上面积了很多灰,翻开扉页是我写下的歪歪扭扭的“马秀琴”。
我们在很多年里又搬了两次家,房子越买越大,身后留下的废墟也越来越多。
年少时的棚户废墟早已经被陌生的完整所取代,那些我们如何努力也终究没有落网的大鱼,成为了永远埋葬在这一幢幢新房子下的秘密。
这将是我们最后一次回到这里,三天前已经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买家签好了合同,我们决定把这间房子卖掉让我能继续读书。
我坐在姥姥的房间里,用力嗅着空气里尘封着的只属于我姥姥的味道。我突然意识到,姥姥,妈妈,在废墟中渴死的鱼,老房子,新房子,其实都是我自己。
与她们相比,明天的我最大的财富叫做未知,那个我始终未放弃,向外寻找与我的内在可以合一的,能够叫作海洋的事物。
姥姥一定寻找了很多年,所以她的死亡不是一瞬间,而是在很久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