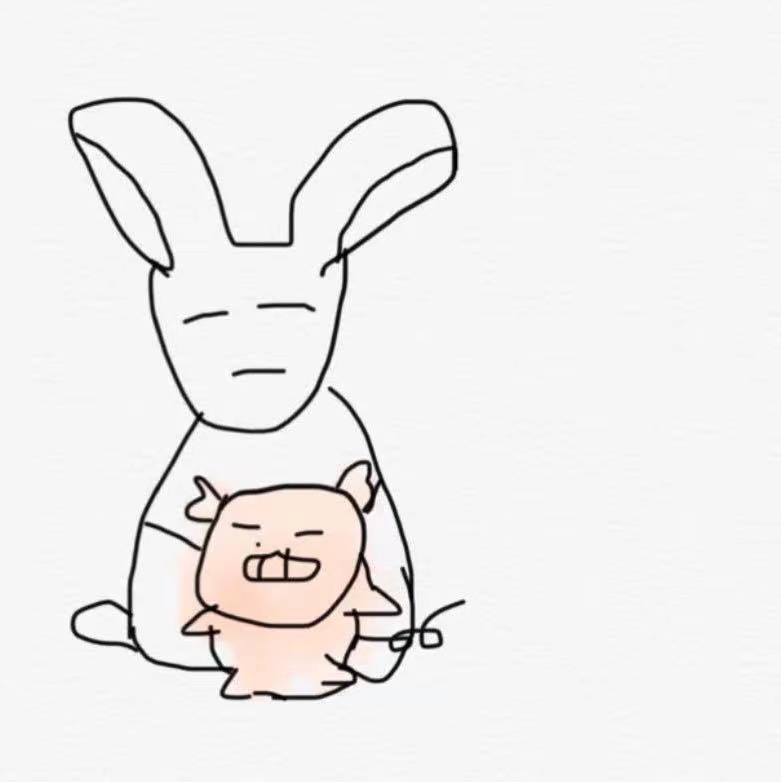春天,山顶镇地震的时候,赖雨踢倒保温瓶,开水从破碎的壶胆中绽放,吊灯摇晃,赖雨摔倒,时间流速在这一刻如同下坠的纱巾一样慢下来,给予她直至老年时才再次感受到的平静与空旷,她看见墙上的电子表轻轻被墙面弹起,放在电视机顶的遥控器向外探身,转瞬坠落,紧接着,几百粒滚烫的雨滴淋上她的小腿,蒸汽氤氲。初二时赖雨在生物课上学到昆虫的变态发育,总想起开水从翠绿色保暖瓶中破茧而出的画面。
这场地震和山顶镇曾发生过的和将要发生的几百场地震一样迅速被镇民遗忘。赖雨在中心医院烧伤科住了两个月时间,期间,林琳常去看她,周末一起过夜。病房在一楼,外侧是山,内侧靠着长满橘色花朵的花园,白天会有一个坐着轮椅的男孩霸占中心位置,男孩肤色淡,戴针织帽,偶然一次赖雨见到他帽子下面的光头,阳光照射,四面八方散着金光,赖雨拉上窗帘,仍能看到灰色窗帘中间有一个透光点,那是男孩在的位置。
赖雨的腿留下疤痕,褶皱盘旋而上,后来随着她身高的增长变长变淡,高中时彻底消失。刚入院时,医生给她吊一种黄色的液体,滴很慢,刺痛随着血管爬遍全身,她变得嗜睡,尤其是在有阳光的白天,夜晚停药,她偷偷起身,赤脚在医院里散步。机器的鸣叫是背景乐,有些冗长、带着气流吸吐的声音,有些短促到没有实感;护士的脚步声是需要警惕的声音;窗外昆虫鸣叫是触不可及的热闹夏夜。
她在走廊尽头的房间里找到一张衣柜,躲进去,关闭木门,声音就全部消失,甚至连自己心跳的声音也听不见。她透过衣柜缝隙看外面,最开始只是狭窄的一条竖线,能看见被月光照亮的写字台的一角,光芒很柔,不会使她困倦。两天后,这条线逐渐扩大,她得以一窥写字台的全貌,棕色木头,厚重,边角发白,上面盖着一块完整玻璃,玻璃下压着一些纸片,玻璃上放着四本书和杂志,一个竹子样式的笔筒,都带着层气膜光晕。一周后,她能通过两扇门扉的缝隙看见整个房间以及房间窗户外的花园,有朵在月色照耀下才会开放的向月葵,有短暂的暴雨和淡黄色的彩虹,有鸟,很小,在玻璃外绕着两个圆圈在飞,倒着的8。
看见明媚夜晚的第二天,这个房间被上了锁,赖雨后来又在医院里找到很多其他衣柜,但再没遇见这种宁静又绮丽的缝隙。
虫鸣最强烈的夜晚过去,林玲在第二天午饭后到来,那时赖雨正沉睡,晚饭时她醒来,看见林玲坐在靠近窗户的床侧,穿波点连衣裙,头上戴顶山顶镇少见的棕色编织草帽,捧着本书在看。赖雨问哪来的帽子,林玲说她叔叔从上海回来,还有带威化巧克力,但是刚才被她吃光啦。
“咱们放暑假啦。”她说。
赖雨正穿衣服,暴雨突然下起来,从山顶袭向医院,病房靠山一侧的窗外能看见湿润的梧桐树叶随着雨滴快速下落,另一边,花园里眯着眼睛晒太阳的病人因为雨声睁开眼睛,光头男孩也在其中。雨到达花园,惊叫一片,护士快速穿梭于花园与病房,把被淋湿的病人们一个一个推回来,光头男孩在第一滴雨滴落上脸颊时表现出不可思议的活力,他挺起肩膀,用力抡起双臂转动轮子,轮椅在雨中横冲直撞,漂移横挪,三番五次从护士的包围中突破出来,如踩着雨点节奏起舞的芭蕾演员。男孩的笑声穿透玻璃直达病房,他的帽子掉在一丛冬青上,两个轮子带起两束细长的水花,四名护士从东南西北四个方向扑过去,轮椅侧翻,他摔在石阶旁。被护士抱进屋子的时候,男孩仍没停止山雀般的笑声。
赖雨带着林玲在嘈杂的走廊里穿梭,用医院饭卡款待林玲两个刚出屉的豆沙馅包子,她们在拥挤食堂里并排挤在一个凳子上吃包子,水滴声、布料甩动声、说话声、餐具碰撞声-、咀嚼声,林玲说,下午看书的时候,看到医院后墙上有一个裂缝,赖雨说后墙上有不少裂缝,林玲摇头,她用力伸展双臂,说:
“那个裂缝很大,能过一辆摩托车!”
太阳下山后雨势渐微,过十点,乌云也飘散,赖雨和林玲从刚查过房的住院部溜出来,跑进花园,一抬头就看见漫天繁星,月亮很圆,被放在最中心的地方。她们沿着淡黄色砖墙走向后院,拎着凉鞋,赤脚踩进映着夜空倒影的一个个水潭,林玲哼着一首叫《开心就拍手》的歌,是放暑假前音乐课教的。她们不断踩碎星月,星月不断复原,歌唱到一半,她们就走到后墙上那条裂缝旁。裂缝有两米宽,两边断口光滑,像一个后门的雏形。
赖雨说:“这是山的嘴巴。”
她们走入山的嘴巴里,林玲紧紧抓着赖雨的右臂。借着月光,赖雨看见面前的草地上有零星的白色花朵,一直连到山坡转角。她们沿着从稀薄变繁茂、未曾断裂的白色花路一直往上走,经过两次转弯,历时二十分钟,最终走进一座藏在山顶内侧的山谷,发现一间已经废弃的小型游乐场,月明星繁,流明在游乐场里的建筑上滑动,金属光泽。林玲被群山顶峰中突然显现的游乐场震撼到,愣在原地,落下泪来,她说感觉自己走进动画片里,赖雨用袖子帮她擦掉眼泪,两人牵着手走进游乐场大门。
游乐场约有两个足球场大,地上草深,器械被埋在草海之间,像群岛。乐园中心是一座三层旋转木马,木马外各自散落其他大型器械:海盗船、跳楼机、最边上一座比医院楼还要高的摩天轮。一些比较矮小的器械已经被草淹没大半:旋转茶杯、碰碰车、几个破了洞的蹦床、被腐朽栏杆围住的一个真坦克模型和一个真大炮模型,此外,赖雨和林玲游弋于各个岛屿之间查看时还频繁碰到深草之下躲藏着的各种健身器材、玩具、石桌、长椅。
三只蛐蛐从草里蹦出来,攀附类植物绕上高大器械,摩天轮的左半部分和底部被植物爬满,林玲说是植物里长成的一架摩天轮。她们走向儿童玩具区,滑梯突然剧烈地颤抖起来,紧接着,几百只灰色白色兔子从滑梯口涌出来,持续穿过她们,钻进身后草海。这场灰白色浪潮持续将近4分钟,最后一只兔子消失时,林玲仍坐在地上,赖雨挡在她身前,保护着腿软的她。兔群的声音渐行渐远,赖雨扶起林玲,两个人都笑起来,赖雨说给我们的王国起个名字,林玲想了片刻,说:
“叫兔子洞吧。”
兔子洞王国在此夜被两名三年级少女发现并命名。
最初一周她们忙于修缮。赖雨在后院找到一块木板,清洗干净,晒干,用马克笔写上兔子洞,这块木板就被透明胶带长久地贴在旋转木马三层。林玲从山下花店借来两把除草用的大剪刀,用整整三晚,清理出七八条连接各个岛屿的道路,分割草海。旋转木马定为兔子洞首都,她们用绷带和纱布贴住锈迹斑斑的栏杆和破损的墙面,从家里拿旧毯子铺满地板,三层天花板塌了一半,月光直射其中一匹粉色的马,赖雨在马头、马身、马屁股各摆上一个雪晶球,射下来的月光扩散,整个三层都弥漫雾状光亮。
她们在王国里画画,用蜡笔在每个空白处涂写颜色;带去电子琴,弹奏回荡整个山谷的曲子,总有鸟群被惊醒然后从她们头顶飞过;在草海之间玩捉迷藏,规则是藏好之后就不能再动,有次林玲就仰躺在草海之间的石桌上,望着星星,草叶被晚风吹动发出的声音总让她想到海边、海浪,她伸展双臂呈一个大字,感觉自己正飘在半空中,俯瞰整个兔子洞王国,没有任何恐惧。她们往王国各个角落藏了很多东西,有坏掉的遥控车、棒球棍、旧照片、旧包包。
昼伏夜出。住家里的时候,林玲十点就洗漱上床,躲在被窝里写日记,等家里的座钟敲响十二下,她就背着背包从窗户翻到院子里,步行离开。午夜的山顶镇很不一样,天全黑,街道上一个人都没有,林玲的皮鞋踏在沥青路上,脚步声从镇头慢悠悠荡到镇尾,这种独处给予她一种从未有过的兴奋,她踢路边的易拉罐,用手指在路灯下玩影子游戏,弯腰查看路边放置的纸盒,最后,她翻过医院,穿过裂缝,终于从宁静的小镇走向藏在月色中的王国。
一周后,第三位国民到来。那天刚下过暴雨,赖雨和林玲坐在三层的马车上下跳棋,水滴从屋檐不断下落,撞入水潭。棋下一半时赖雨听到一个有规律的声音,很远、很轻、很干脆,像是啄木鸟敲响树干,她们从窗户里探出脑袋,望向唯一一条通往王国的路,声音来的方向。声音继续变化,拉长动态,像燃烧木柴发出的细微爆裂声,但响度未加,再过十分钟,响起炉子上水壶沸腾声,赖雨说这是蚌躺在海底沙滩上呼吸的声音。蚌呼吸声持续七八分钟,山谷小路转角出现一个男孩,瘦高,光头,是曾经在花园里散射阳光、在雨中追逐的少年,现在他带着多样的脚步声来到王国,脑袋依然在散射月光。
赖雨和林玲下楼迎接他,为他详细介绍王国的每个设施。男孩叫吴海,友善,笑着跟随在叽叽喳喳的她们身后,偶尔发出一句赞叹,说得最多的是这里真凉快。他从碰碰车旁找到一把被爬墙虎缠绕包裹的塑料椅子,枝条富有弹性,拖着这把椅子上旋转木马三楼,摆在角落,藤蔓没有一根断裂,这张椅子的移动为旋转木马和碰碰车创造出一条青翠的、有活力的连接。
吴海留下,次日,山顶镇地震,震感不强,王国没受影响,唯一痕迹是一张石桌从中间开裂,裂缝中发现几十粒橙黄色种子,吴海把它们种在摩天轮下方的空地上。地震之后,兔子开始出现。第一晚是一只白兔,蹦跳着来到王国门口,驻足,注视着旋转木马三层的三人,一小时后离开。第二晚是一只白兔一只灰兔,它们和坐在咖啡杯里看漫画的吴海四目相对,吴海站起来,兔子随即逃跑,钻进树海。第三晚,林玲从家里带了三根胡萝卜,他们三个围在离大门口最近的双杠旁,等待三只兔子到来。不到一点,兔群来了,几百只灰色白色的兔子排成三排靠近大门,然后在正门外停步,吴海走过去,把胡萝卜递给最前面的三只兔子,打头兔子坐在地上,前爪抱过胡萝卜,传向身后,后者亦如此,胡萝卜很快被传到看不见的兔群尾部,与此同时,也有东西从兔群尾部传过来,小,但兔子传得吃力,两分钟后,这样东西传到最前方的三只兔子怀里。吴海弯腰,接过兔群给予的礼物,是三颗沉甸甸的淡青色鹅卵石,鸡蛋大小,举起来对着光能看到剔透的内里。双方互换完礼物,兔群再次钻回树海,吴海把礼物分给赖雨跟林玲,她们各自藏起来。之后两天,兔子们陆续回归乐园,几百只兔子住进王国各个角落,不惧怕他们,不主动靠近。
之后一周,王国迎来雨季。
每晚,连绵不绝,细碎的雨轻洒下来,柔和、缓慢、静默。吴海竖起一把巨大的透明雨伞填补旋转木马散落的缺口,他们三人坐在塑料穹顶下,赖雨说想做漫画。这项计划次晚开始,林玲画场景,赖雨画人物和道具,吴海写台词,她们用中性笔在薄透硫酸纸上作画,画完之后由吴海将纸叠在一起,构建完整故事,5天时间,第一幕完成。
夏天小镇,操场,石砌乒乓球台,握住一张旧球拍的初中男生大笑,和他同台的对手一个一个接连下场,垂头丧气,少年身后的树坑里堆满赢来的零食。
雨停,巡视王国,他们发现摩天轮下的空地上长出十几个黄色蘑菇,一指高度,伞盖仍有泥土,转完一圈回来,赖雨发现蘑菇已经长到她小腿高了。吴海说没见过这种蘑菇,林玲说看看它能长多大,他们坐在摩天轮外侧栏杆上盯住蘑菇。在他们的目光注视下,蘑菇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向上延伸,一小时后,一只蘑菇长到和栏杆平齐的高度,突然停止竖向攀升,转而延伸伞盖,很快,其他蘑菇也都在同一高度停止向上,横向延伸,分毫不差。几分钟后,蘑菇们的伞盖撞在一起,迅速融成一个水平平面,吴雨站在栏杆上俯瞰,看见一个边角分明的长方形台子,他走上前,用双臂测量蘑菇台的长、宽、高,他惊喜地叫出来:
“乒乓!”
他用食指敲蘑菇乒乓球台的台面、背面、支柱、侧边,声音干脆,富有质感,他不由地赞叹出声:
“真是一张好台子。”
他托家人买来挡网、三个球拍、几十枚乒乓球。他开始教赖雨和林玲打乒乓球,从握拍到挥击,一周时间,他们可以在蘑菇台上对打,林玲对乒乓很感兴趣,她练芭蕾舞,四年,乒乓的节奏在她眼里是另种舞蹈,更富激情。他们对打时,摩天轮周遭的草地上开始长出许多翠绿色的枝条,表面光滑、顶端两侧有叶,这些植物通常在一场对局刚开始时生长,到达赛点时超过他们三人,根茎舞动,一场对局结束就迅速衰败,钻回地底,不留下任何痕迹。王国消失后的第三年夏天,赖雨终于在图书馆根据样貌找到这种植物,大莱尼蕨(R.majorK.etL.),下泥盆纪时最为繁茂,在二迭纪灭绝。
他们在乒乓的间隙,完成了漫画的第二幕。
赛场,大比分落后于刚进球队的新球员,男孩流汗,握拍手颤抖。输,比赛结束,男孩坐在场外草地上,球拍在身侧。新球员拿了奖牌出来,大笑,和男孩握手。
暑假快要结束的时候,林玲带来了第四位国民。青年女人,戴眼镜,头发束脑后 ,不知道年龄,他们看不出成年人的年纪。林玲在来王国的深夜路上看见她一个人坐在路边台阶,林玲询问她是不是没地方去,女人点头,林玲说镇上半夜会有三只很坏的野狗,会抢女孩的包,女人抬头,林玲牵起女人的手,拉着她走向王国。
“我们到没有狗的地方去。”
女人到来,他们领着她参观王国,询问她的名字,她没回答,只说让他们叫她姐姐。兔子洞王国的遗世美感让姐姐在参观尚未完成时便落下泪来,她说自己曾经也有这样一个王国,初中,下午16.00放学,她和三个男生一起去镇上已经倒闭荒废的皮鞋厂里玩捉人,经常玩到太阳下山,那时候她总躲在已成废墟的破败澡堂子里,阳光透过侧窗的教堂玻璃彩色花窗照进来,手臂上颜色闪烁。
林玲说我们不玩抓人,但是可以一起玩捉迷藏。
姐姐加入王国,但始终没告诉他们真名,她说自己错过了说名字的时机,现在再说是一种傲慢。她每晚22.00来,1.00离开,她带来零食,通常是坚果和沙琪玛,她带来最新款的玩具,她带来一个电脑和投影仪,为大家放一些没看过的电影,通常是英语片,字幕赖雨不能全部看懂。她的乒乓球打得很好,总是以压倒性优势赢赖雨和林玲,但从未赢过吴海。
“你可以试试去打职业。”姐姐劝吴海。
漫画第三幕完成。
训练,每一秒。所有节假日、深夜、清晨、午休时间,男孩在省队训练室里挥拍,和队里其他队员车轮战,放弃休息。和新队员对练,再次大比分输掉,新队员大笑,说男孩不够享受。
剃掉头发,要让脑袋保持冷静。继续加量训练,压缩吃饭时间、压缩睡觉时间,不要社交,眼睛盯住乒乓球。
姐姐买来四张躺椅、一个太阳能供能的小夜灯,光亮很足,旋转木马区域如同白昼,她带来一盒蚊香和两瓶驱虫喷雾,薄荷味,弥漫整个王国,她带来一顶巨大的帐篷,撑开能遮挡整个健身区域。一个晚上,赖雨和林玲在王国里玩寻宝游戏,互相发掘对方藏在王国里的东西,路过坦克模型的时候,赖雨发现一个兔子雕塑,真兔子大小,藏在草里,惟妙惟肖,在之前从未见过。她叫来林玲和吴海,他们也表示从未见过,林玲在石头兔子耳朵系上一截红色丝带。
之后的几个晚上,兔子雕塑一个接一个冒出来,大部分是在草丛中,最后,吴海在道路上发现一尊,他们终于明白,兔子雕塑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他们寻找兔群,兔群的数量已经无比稀薄。他们在海盗船旁边发现一只行将石化的兔子,它的下半身已经变成石头,上半身皮毛洁白,林玲伸手抚摸,兔子用脸颊轻轻蹭林玲手掌,耳朵晃动。历时一个小时,兔子最终变成一尊雕塑,泛青绿色。林玲的眼泪打湿雕塑周围的泥土。
他们把最开始兔群赠送的三枚鹅卵石找出来,轻轻敲响兔子雕塑、在兔子雕塑身下画圈、让月光透过它们照亮兔子雕塑,但毫无作用,姐姐查遍各种资料,仍一筹莫展,兔群的数量越来越少。他们见到的最后一只兔子是在摩天轮旁,它抬起头注视着已经被植物完全包裹的摩天轮,一点一点被石化,变成一尊兔子雕塑。他们握着鹅卵石站在一旁,没有任何动作。之后他们找了一整个晚上,王国只剩下漫山遍野的兔子雕塑,林玲说她现在有点害怕了。
次晚,林玲没来王国。第三天白天,林玲来找赖雨,说自己昨天睡过了。赖雨请她吃苹果,她们在医院里四处散步,赖雨说自己的腿伤已经好了,林玲说刚好下周开学,太阳下山后林玲离开医院,赖雨送到医院门口,两人都没再提王国的事。
赖雨在王国的倒数第二个晚上,吴海整夜都在画画,他额外承担林玲的背景工作。凌晨,吴海把已经叠好粘贴的漫画递给赖雨,然后向她和姐姐告别,一个人走出王国,走下山路,没有多变的脚步声响起。姐姐一直在哭,她说:
“我偷走了你们的王国。”
赖雨想,不是这样,王国不是我们的。并非我们创造了王国,而是王国接纳了我们。这不是姐姐的错,我们每个人归根结底拥有的也并非同一个王国,只是在内心明确的成年人姐姐到来之前,我们三人在这场山谷的旖旎氛围里已经混淆了自身意愿与动机,我们现在是小孩子,但终会长大,王国会驱逐我们。
“姐姐。”赖雨说,“王国还在这里。”
赖雨的出院手续在第二天办结,她的小腿留下一截伤疤,从脚跟攀至膝盖,像大莱尼蕨。她坐巴士离开医院,上坡的路在窗外倒退,日光辉煌地从屋顶漆瓦上反射过来,深色的山脉包裹着屋群。赖雨想,这些景色,有哪些是林玲每晚独自看到的?她在摇摇晃晃的座椅上摊开吴海最后画好的第四幕。
全国赛,第二场,男孩碰上另一名从未见过的选手,个子矮小,戴眼镜,反应极速。他无视右腿膝盖疼痛,拼尽全力,0:3输掉比赛,被搀扶着离开赛场时,他看见新队员举起球拍,笑着晋级。
医院里,医生诊断韧带撕裂,住院一个月,观察六个月。办好住院,男孩坐轮椅来到花园中心,太阳强烈,照得他睁不开眼。他突然释怀。
“原来乒乓球是天才们的运动。”
他自言自语。
开学日,赖雨没见到林玲。她找到班主任,班主任说林玲父亲调到镇外工作,一家人都搬走了。林玲给赖雨留了封信,赖雨坐在走廊里看完,里面写了些不舍的话,大扫除的同学擦墙,水珠甩到信纸上,林玲的字迹变得模糊。
高三毕业后,赖雨考上镇外大学,临行前,她偷偷溜进山顶镇医院,想再去一次王国,但后围墙没找到任何一条裂缝。她向门卫打听,住院部的围墙这几年是否翻修过,门卫否认。她突然想起最开始躲在医院某个办公室衣柜看见的缝隙,想起自己小腿上曾经有过一条长得像大莱尼蕨的缝隙,她想,山顶镇有过几百次地震,有的缝隙被打开,有的缝隙被合上,这很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