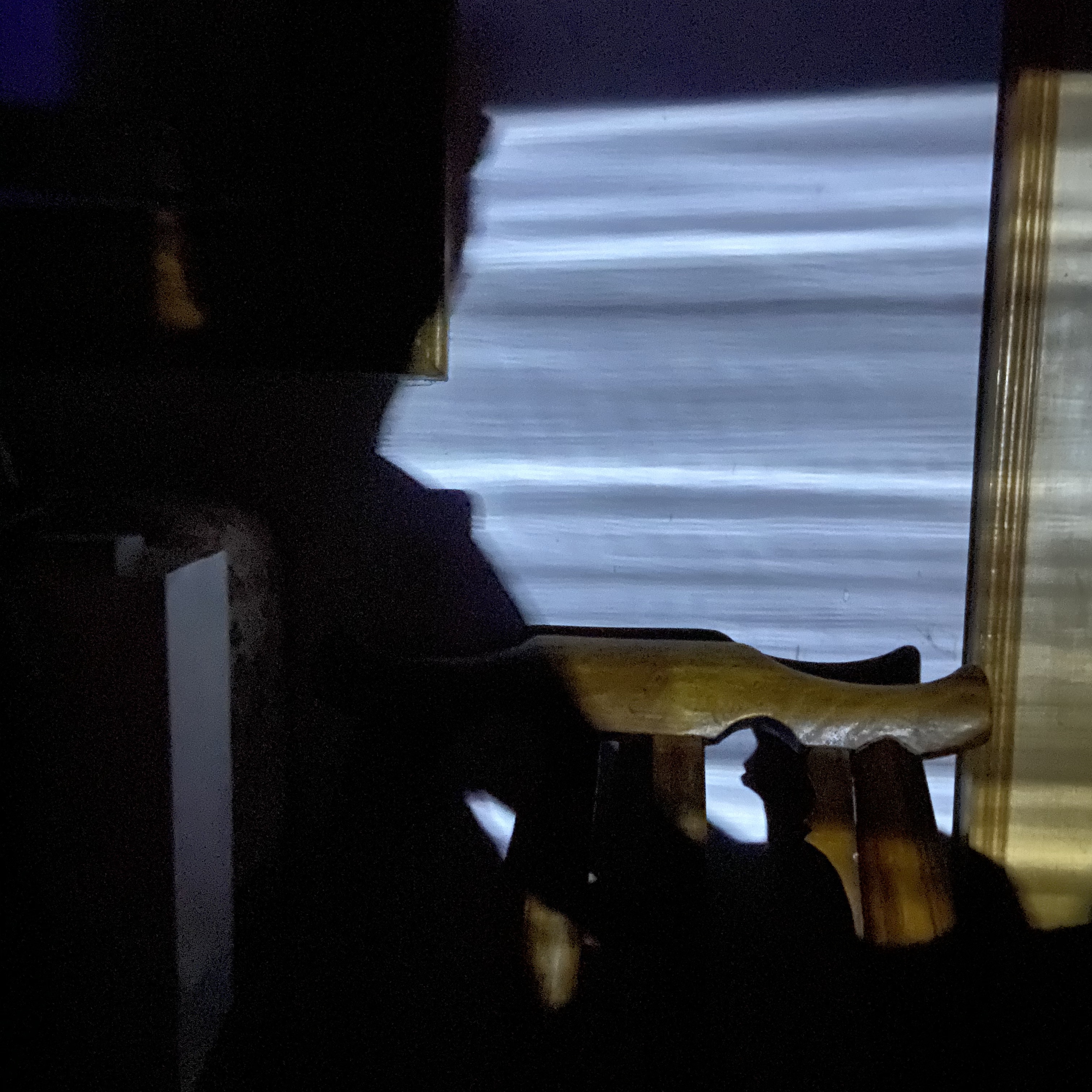一
乔栋死了。
百二河的修缮工程仍由那帮广东人负责,据说他们雇了一个声势浩大的保安队,有四十多号人,沿岸巡逻,日夜不辍。下一个中元节,大家不知道该到哪里烧纸。警察找过我,希望我回忆起乔栋的一些旧事,可我真的没法提供什么有价值的内容。我说,我没什么可回忆的,乔栋就是书读太多,脑子乱了。跟乔栋在一块的时候,我从来插不上话,大部分时候我都不知道他在念叨什么,只是随声附和,说你说得对。也许就在他念叨的这些东西里,隐藏着他的真实,可惜我没有仔细听。高中我俩在一个学校,我大他一届,在校门口奶茶店认识。他很大方,偶尔请我喝杯奶茶,联络并不算多。高三那年,我妈单位组织团建,去爬山。他也在,我才知道他妈也是电视台的。之后我们熟了一些,他想学书法,我妈派我去教他,于是就经常见面。
那次他回来,正巧我去台里找我妈要钱,在广电门口遇见他,他正跟他妈吵架,脖子上挂着一台单反相机。他妈气哼哼地走了,他站在原地不动,直勾勾地盯着广电的自动门,像要把门给盯碎。我跟他打招呼,他飞快地冲我笑笑。怎么跟你妈吵架了,我问。我想借无人机,台里那架,她不给,他说。那是公家财产,你妈说了也不算,我说。她可以借,他说。你要无人机干嘛呢,我说。拍视频,他说。什么视频,我问。百二河开闸放水,拓宽河道,沿河的建筑都在拆,我想记录下来,他说。也不一定要拍视频,拍照也一样,我说。对,我先从拍照开始,他说。
他邀请我参与,当一个见证人,他好像也没别的朋友。当时我正打算恢复正常的生物钟,改变白天睡觉晚上喝酒的恶习,就答应了他。他的首个目标是一座桥,桥就在他家旁边,穿过楼下的菜市场,再走过一条满是发廊足浴的街就到了。桥龄三十三年,马上要拆,然后重盖。从前我就通过这座桥去乔栋家教书法,他爸时常穿过这桥去买豆皮和热干面,买回来主要都给乔栋吃了。桥那头的熟食市场里有一家豆皮绝顶好吃,不是三鲜的,不放笋和肉,只放小小的豆腐块,每天人声鼎沸。拆桥工作开始后,两边就封了,乔栋爸嫌绕路绕得远,也不再去买豆皮了。
二
第一天。乔栋穿了件黄色短袖,外搭黑色马甲,像记者似的端着单反。拆除还没开始,工人们都在忙别的。日头正晒,人们都摘了头盔,摞成一座小塔。
百二河不是河,而是一条臭气熏天的水沟。前些年味儿重得厉害,水面始终泛着恶心的绿。河道整治之后好了点,但水还是浅,不配河的名字。河道原本干什么的都有,跑步,骑车,跳广场舞,主要还是跳舞,每到晚上就非常热闹,围绕着长长的河道,像盛大的游行。据说百二河生态修复工程的第一项举措就是开闸放水,用大水将河道淹没,把百二河变成一条真正的河。水可能来自上游的艳湖公园,那里有个水库,水库抽干了就抽汉江的,直到水流充盈河道。河岸部分要运土运树,把两岸弄成生态湿地。
似乎到处都在拆迁,一切都在翻新,甚至是才刚刚成为新的不久的事物,也被毫不犹豫地替代。河上的桥都是十几年前造的,年代久远但质量很好,再过一百年也不会塌。之所以要拆桥,仅仅因为与新修河道相比,这些旧桥显得过于破烂,似乎隐喻了生活糟糕的人们。
这种意象的存在是不被允许的。
乔栋说,好多人因此没了落脚的地方,新河只是第一步,城市要重新孕育自己。
乔栋又说,我奶奶,前些年死了,是自杀。
我站在一边没搭话,等他继续往下说,他却不说了,又举起相机对准河道。工人在架设水管,很粗,白色的,下面有铁架子撑着,已经搭了很长一段距离,我们脚下是它暂时的尽头。乔栋对着水管猛拍,镜头一直绵延到远处河的拐角。他看了看自己的作品,感觉不太满意,一张张删掉。天快黑了,我们沿着街走,他抓住最后一点光继续拍照。在我的认识里,他的确像个艺术家,拍照时显得恍惚且神经质。为了选角度,他不停来回,时而蹲下,时而站起。突然他扭过头对我说,我奶奶是自杀,她本可以不那样的,大概十年前,人们说,应该修建一座宏伟的大坝,很多地势低的村子都得被淹,村里的人劝我奶奶去住安置房,给三套,小洋楼,她不去,要留在村子里,死也要死在江水里。可是人家不干,要按规矩办事,所以他们就强行把我奶奶拉走,最后真的走了,走半道上她翻桥跳了江。
依稀记得那时候,许多写字的人都被请来了,他们要为这场迁徙谱写史诗,把乡民的骨头变成铅字,血水凝成印泥。乔栋给我看了一张照片,照片里一个老人蜷缩在土堆上,身后背一个箩筐,筐里是一树梅花,其他没有任何行装。乔栋说,那是他家门口的一棵树。
第二天。我们长驱直入,下到工地里边。昨晚跟朋友说起这个事,他说自己在技校的朋友在现场,能带我们进去。那人挺热情,直接把我们领到河道底下。这一河段的包工头姓沈,来自离市区最远的县,那里盛产工头,人精心黑。老沈看上去很和善,时髦地烫了个头。跟着老沈的有几个技校的实习生,都被他单方面收为弟子。乔栋给人家鞠了好几个躬,然后举起相机到处照。老沈笑呵呵地看着。我给他递烟,他夹在耳朵上,他右边耳朵也有一支,比我的贵。老板送的,他得意地说。
我猜他们老板是广东人,乔栋在寻找最佳角度的空当时对我说。
为啥,我问。
他仍是不说话,按下快门,呵哧呵哧地拍。
乔栋虽然时常把我晾着,我却并不想打他,要换了别人我指定不耐烦地给他两脚,我的耐心似乎只对他。乔栋像在作画,镜头为笔,天地为幕,酣畅淋漓。我们走了很多路,沿着河流而上,经过许多座桥,他把它们一一记录下来。傍晚,我们离开河道,沿路标语随处可见,天花乱坠。乔栋指着简易隔板的标语,给我看上面的小字:
广东水利水电三局宣。
第三天。乔栋换了件短袖,白色的,短裤还是那条。老沈不让我们进,说昨天老板来了,知道这件事之后不太高兴,不给拍了。今天是个相对重要的日子,有着修长吊臂的卡车开来了,上头挂着钻机。
今天是桥斩首的日子。我本以为他们会把桥炸掉,这样似乎来得痛快。但老沈说桥的规格不够炸的,容易误伤,只能人工剔凿或机械破碎。小孩们被大人架在脖子上,大一点的爬上歪脖子树俯瞰,像极了菜市口的盛况。乔栋和我站在街边小卖部的二楼阳台,看得很清楚,桥的样子破败不堪,裸露在外的钢筋混凝土像极了人的骨骼。它即将被撕碎。与河道平行的就是人民路,主干道上车辆川流,熙熙攘攘的人从斑马线上穿过,渣土处的大马甲尘土满面,行色匆匆,卖豆皮的一家子正装行李上车,准备搬到北京路的新址。每个人的脚都踏上过那座桥,可这个下午,它被人们彻彻底底忽视了。
桥要死了,乔栋喃喃道。作为一座缆索桥,这桥造得很成功,索塔坚固,桥面坚实。它年岁大了,但老当益壮,由东风公司承建,那时他们还把这里当成家呢。桥顶焊了一个铁球,再上面是颗铜制的五角星,危险而曼妙。这工艺品和桥之间用一根铁柱撑着,钻机直取要害,奔铁柱而去。铁球和人的脑袋可真像,慢悠悠地垂下去,失落得很,然后人头落地。球落在地上碎开了,原来里面是空心的。人群哦的一声,缓缓散开。
我转头看乔栋,这历史性的一瞬他居然没拍下来,而是转过身抓拍人群,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我鬼使神差地掏出手机,替他和桥拍了张合影,这是唯一的一张。
三
居委会的女性们酝酿发动一场战争。这个消息通过她们隐秘而深远的情报网迅速扩散,很快传遍沿河的每一处街道。电力处的张平林被委任为此次行动的宣传干事,他在单位搞得是新媒体运营,擅长煽风点火。他杜撰了好些故事,把拆河道说得跟外敌入侵似的悲壮,网民群情激愤,战得不可开交。乔栋写了篇小说,叫《死桥之殇》,我妈看完给他妈打电话,哭着说她自己也要去保卫河道,还没说完对面就挂了。
乔栋的拍摄持续了三天,之后桥的拆除工作被搁置,据说有人往市里头反应,说工人倒卖建筑材料。居委会诸君果然都不是等闲之辈。不过在乔栋眼里,这桥已经是一座死桥了,被取了首级的人当然不是人。乔栋闲下来,趁我有空的时候又练起书法。他写字从不临帖,总想自己琢磨出一套体系,所以他一直写不好。
桥的照片他只是潦草地补拍了几张照片,就再也没去拍过照,好像对记录失去了兴趣。他将这场浩浩荡荡的拆迁称为人们对自尊心的仓促证明,就像过年时都要买新衣服一样,只不过是没有必要的炫耀。这是我第一次对他的看法产生质疑,因为事情好像没有那么简单,人们会因为自卑而修一座桥吗?我不知道。
他回来的时候正巧赶上中元节,九月二号,他本打算三号返回学校的。往年河道都是祭祀之地,人们在桥头买黄裱纸,从天地银行提款,拎下河道。卖纸的顺便会给根白粉笔,让你在地上画圈。一圈是父辈祖先,一圈是母辈祖先,还有一圈给孤魂野鬼。男人掏出根烟点上,再拿一张百元钞票,在黄裱纸上拍打,形式上就把纸变成了钱。黄纸用稻草浆做成,毛毛的,摸起来很舒服,烧起来快。中元节的河道暖烘烘,每一家子面前的火光都透亮分明,联起一条长长的火龙,人们站在火堆前念念有词。待到火快烧尽了,纸都变成了灰,像是从火中炼出一座坟来。大人放张裱纸在地上,小孩就跪下磕头。大家似乎是同步的,火整整齐齐地熄灭。这时候,人们不约而同地拿木棍捅一捅已经灰黑的纸堆,里面还在烧,那火焰既炙烫,又阴冷,在纸灰中幽幽地燃着。只需用棍子把上面没烧干净的纸钱戳下去,纸堆里的火便迫不及待窜出来,河道又齐刷刷地亮了。
又过了几天,乔栋请我吃豆皮,我俩绕了老远的路。装家当的车就停在店门外,捆得结结实实,把限乘四人的小货车盛得满满的。他说,这家店最后一天开业了,人太少,撑不下去,看来人都是懒呀,断了座桥就懒得跑了。他说着,把一块豆皮囫囵吞枣咽下去,又喝了口米酒顺气。我看见他胳膊上有道伤,挺深,我问他咋搞的,他说是造船划的。
晚上,我们溜进工地,看船。
一排PVC管被绑在一起,用塑料绳捆着,形成一个简单的筏子,踹一脚估计能散架。他把船藏在一个大洞里,可能是维修用的通道,足够容纳两个人,但散发着杂糅各种气味的恶臭。你这也叫船?我问。不叫,所以需要你帮忙,他说。我倒是认识几个哥们儿会弄,但我劝你别费功夫,你这破筏子扛不住水,我说。乔栋似乎没听见,只是直勾勾地盯着他的船。晚风猎猎,管子活了一样,扭动着身体,要从塑料绳的束缚里挣脱。百二河最后指不定汇入哪个污水处理厂呢,你想去污水坑里泡澡?我说。乔栋再次沉默,我也不说话了,我们静静地从一个破洞里望着外面。河道上人开始聚集,手电筒的灯光汇在一起。
河只会流入比它更宽的河,乔栋开口说。
人越聚越多,桥下一堆建材里人头攒动,是跳舞的阿姨们,足有几十人,都穿着舞蹈服。她们围成一个大圈,各自的孙子孙女站在桥边放风。我带着乔栋偷偷混进人群。一个老太太站在人群中间讲话,口若悬河。她手里端着黑色保温杯,穿暗红色印着福字的棉衣,头发卷曲且蓬松。我认识她,我们学校的团委书记,平时的爱好就是发表演讲。她老公是武汉一所大学的团委书记。
她说:咱们的前期工作很有效,感谢各位干事做出的贡献,但这还远远不够,我们最终是要把我们跳舞的地方拿回来的,这是为所有姐妹的权益做的斗争,也是为沿河居民做的斗争。之前下发的宣传册里已经将咱们的纲领“三要”和“三斗”说得很清楚了,我就不再赘述,我主要讲点实实在在的。最重要的是,桥不能塌,这座桥塌了,百二河上所有的桥都要跟着塌,河道也就没了。我们要守住桥。其次,大家也知道,犬子在市政府当科长,估计今年年底还能往上走走,这不是重点,他明确表态,上面也在犹豫。市政要规划,但老百姓的权益也要讲,我们相信,咱们的声音是不会被忽视的。
那老太太说了句什么,其他老太太们哗地散了,怀里抱着一堆纸,满河道张贴。我走近看,是海报,张平林设计的,色彩鲜艳,主题明确,八个大字:人在桥在,保卫河道。我都能想象明早工人们上工时的惊讶眼神,他们将被淹没在传单的汪洋大海中,从此向人民的唾沫星子屈服。
乔栋拍下了这一盛景,为这场很快夭折的失败示威作了留念。
第二天,意气风发的人们提着饭盒、马扎或是小广播,到河道边欣赏自己的杰作,然而人们失望了,河道的墙上干干净净,看不到一片纸屑,工人们若无其事地干活,不时拿眼睛偷瞟街上的人群。老太太因此急火攻心进了医院,她老伴从武汉赶回来,自作主张撤了她的职,居委会们群龙无首,联盟土崩瓦解。我打听过,后半夜,所有工头都因为一通电话从床上爬起来,率领工人们倾巢而出,收缴墙上还没呆热乎的海报,他们说这叫清理城市牛皮癣。另外,乔栋的破船也不见了。
广东人不愧是广东人,乔栋如是说。
四
我市与广东积怨已久。去年搞过一个魅力城市的竞选,本市与广东一座相同级别的城市进行了一场选票大战。那段日子,群众每天起床第一件事就是打开手机,先投上十票,然后走出卧室,问问自己的母亲老婆儿子有没有投票。机关、学校还有工厂都把投票作为头等大事来干,双方拼得你死我活,对方稍微比我们多那么几千票,就要有不少办公室的电话开始打鸣。最后我们还是败了,作为一座大山里的城市,败给了改革开放,败给了三大国家级经济区的交汇处,败给了优雅迂回的海岸线。据说,对方那里诞生过不少名人,譬如冼夫人,譬如高力士。
再次见他是中元节前夕,在咖啡馆见面,他用一根硕大的吸管喝咖啡,实在有些违和,桌上放着他的相机。得赶紧把照片拍出来,等我春节回来估计来不及了,他说。有点难,不好办,就站外边拍几张算了,我说。不行,还是得进去,不然没有参与感,他说。
河道重新开始施工,工地外装了闸机,工人们打卡上下班。乔栋在门口堵过老沈几次,没有用,新的河流脉络正在逐渐成型。喝完咖啡,我们在城市里瞎逛,很多地方都开始拆了,简易隔板像是城市的裹尸布。乔栋巡视着,神色黯然。乔栋妈说自己儿子总跟个佛爷似的,看谁都觉得可怜。这会儿我觉得她说得不错。我还记得乔栋在《死桥之殇》里的一句话:他悲悯地看着这一切,桥似乎与他一体,在这个雨夜,死桥融入每个经过它的灵魂。
我们站在一座与死桥平行的桥上,乔栋在路边的摊子上买臭豆腐。这桥能走车,是主干道,幸免于难。死桥跟它比应该很自卑。死桥最早是一座竹桥,那时就有很多人从它的身上走过,而后它成了水泥桥,一度是百二河上最漂亮的水泥桥,那金属制的圆球和五角星曾有很多人观摩,称赞这充满力量的制造工艺。脚下这桥仅五六年,跟死桥比还是个孩子,可从它身上过的人应该要比死桥多得多。广东人来自大海,对山里的众民来说,他们是新人,他们摧毁我们的桥似乎成为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我突然间有些害怕,仿佛我自己、桥,还有这座城都要变旧,成为时代的弃儿。乔栋在我眼里原本是个新人,可他却变成最先被抛弃的那个,他步了死桥的后尘。
乔栋端着臭豆腐,胳膊架在栏杆上,望着死桥。河道还在作业,伤痕累累,白色管道里,将来会流淌天然气。你看看我家门口这路,窄不窄?没法进救护车,我妈生我的时候,我爸抱着她,就从死桥上过,身后我大姨大姨夫小舅小舅妈追着跑,桥对面上了百步梯就是人民医院,别看了,医院早拆了,现在是台湾老板的地皮,他说。嗯,我说。我在这儿忙活什么劲呢,我也不知道,他说。嗯,我说。原址上要建一座新桥,是拱桥,桥面用玻璃做,可以直接看到下面的河水,通体白色,桥柱是波浪状的,像苏联人迷恋的现代主义建筑,别的我不清楚,但以后老人们肯定不会再走这座桥,过桥跟爬山似的,年纪大了受不了,他说。嗯,我说。很久之后,新桥也会塌,有人会像现在这样守护那座新桥。他说。嗯,我说。
我心不在焉,因为有一双眼睛正注视着我们,我感到不自在。远远地,乔栋满面愁容的母亲在人群中看着他,她和自己的儿子间也隔着一条河,这条河上没有桥,也没有船。
五
我很久没跟爸妈一起下河道烧纸,回忆显得有些模糊。小时候,火光亮起,天是深蓝色的,深邃的红与沉静的蓝如此相配,人的表情在火焰映衬下变得扑朔,半明半暗,仿佛体内正沟通两个不同的空间。我们都牢牢盯住火焰,仿佛进入酣畅的睡眠,直到火焰彻底熄灭才醒来。长大后,烧纸时的天越来越亮,可能是我的心理作用,再也没有那样让我陷入昏沉的时刻。那天乔栋去得很早,他抱着相机,站在工地门口,广东水利水电三局的招牌前。工头们在简易板房前集合,若无其事地抽烟,时不时看手机,广东人没来。还有一小撮工人围着楼梯,手里都抄着家伙,挖掘机停在一边,司机坐在驾驶室里发呆。钢制的楼梯踩起来叮叮哐哐地响,由人行道下通到河岸,紧挨着死桥。概率正在酝酿,各式的事件穿行林间,每个人都神经紧绷。
傍晚,遛狗的人先来了,其中不乏大狗,主人们闲扯,狗子汪汪乱叫。有的狗跳进仅没过狗腿的河水里,主人就从人堆里冲出来,大声叫骂。阿姨们来的会晚一些,她们需要做饭,饭后收拾完男人和孩子的狼藉,便换上练功服,拎着音箱,跑到河道来。女人间的团结也仅限这几天,先前她们为争夺地盘掐过不少架。随后,河道的灯亮起来,散步的来了,跑步的来了,孩子来了,男人来了,各种稀奇古怪的玩具来了,自行车来了,滑板来了。人声鼎沸。我脑子里回忆起新年,有做爆米花的把机器支在河边,做好了,轰的一声,跟开炮似的,再拿面口袋一接。不仅爆米花,还有炒米,一边还有烤红薯的炉子。没见过这阵势的,都趴在河岸的栏杆边围观。买完爆米花的也不走,混进看热闹的人里边嚼边看。往后,这诸多情形不会再见。
天渐黑,卖黄裱纸和纸钱的人扛着扁担坐在桥头,对着临街小区的门洞,今天的炊烟见得很早,这会儿晚饭应该都已经结束。那人并不着急,默默坐着。乔栋向他买了裱纸,抽出一张垫屁股,坐在面店门口。我坐在店里,面汤已喝完,微微冒气。陆续有居民走出家门,男的女的都有,四五十往上的年纪,围拢到卖纸人身旁,别的小贩也凑过去,递黄裱纸,递粉笔,递打火机。几个稍微年轻些的,一齐推开隔板,板子倒在地上,震天响。人们顺势涌入,楼梯在众人脚下吱吱呀呀地叫,人和梯子都颤颤巍巍。河道的路崎岖不平,被挖得四处是坑,坑里积水,建材七扭八歪地摆着,分明不让人好走。工人们没动,都背着手,看着街上的人纷纷下来,从他们中间穿过。工头还在等电话,有几个把手机举过头顶找信号。
他们应该把楼梯拆了,这样别人就下不去了,我说。乔栋没说话,举起相机拍照。周遭安静得可怕,河道上走的人似乎化为幽灵,无声游荡着。一朵火焰窜起来,又一朵火焰窜起来,夜完全黑了,火龙蜿蜒盘踞于百二河。一架无人机从人们面前飞过,越升越高,从天空中与河道相望。之后我看了电视台的报道,视频拍得很美,这架无人机所幸没有丢脸。鸟瞰百二河,火在不同的段落被点燃,像一部小说,起承转合,荡气回肠。
火光有种魔力,街上的人不自觉地走下河道,在一团团火焰间徘徊。每家都给孤魂野鬼画了一个圈,丢几张燃烧的裱纸进去。风很大,一不留神纸就吹跑了,也不去捡,任由它们或升上天空,或落进河里,或飘进别家的火堆。死桥被斩下的首级还在原地,一颗破碎的铁球和一颗五角星,工地上堆了数不清的PVC管,里面有几根曾是乔栋的方舟。回忆到这里似乎不再规整,零零散散的,像碎玻璃。我记得人们随后聚集在桥上,以河为界,一边是百二河的居民,一边是拆迁队。桥体坚固如初。桥下的火燃尽了,纸灰堆成一个个坟包,仿佛硝烟四起的战场。这时我才发觉天真正黑了,月光孱弱,毫无威严。老沈为首,站在桥东。团委书记为首,站在桥西。老沈身后是几个精瘦的工头,工人们挤在后面。团委书记身后什么人都有,像要唱戏的架势。警笛声在响,可似乎遥远不可临近。乔栋在书记身后,影子一般,相机举在胸前。
我们老板说了,让你们烧完香已经是仁至义尽,明天桥必须塌,这工程是有政府批文的,老板们不怕你们闹事,人家占理,而且是市里找的人家,不是人家屁颠屁颠来的,老板说这个很重要,你们该搞搞清楚,差不多就算了,百二河整治还不是为了大家好吗?老沈说。他顿了顿,回忆广东人还说了些什么。哦对了,老板还说,将来河道建好,会有大面积的绿地公园和广场,有专门的地方给大家跳舞,请大家不要操心这个问题,老沈说。
人们骚动了一阵,书记略作沉吟,说,那也行。
不行,你把电话给我,我要和你们老板理论,乔栋说。老沈把手机背在身后,乔栋去抢,两人抱在一起。乔栋爸从人堆里冲出来,想把乔栋拉开,他妈跟在后面。人们混作一团,不分敌我,没有打架,只是相互推搡,谁都想挤出去。女人们在人群外议论着,争吵着,形成另一个世界。乔栋就在这混乱中离开了,从桥上翻下去,不知道是谁推的他,到今天也没有定论,四周摄像头都拆了,黑灯瞎火什么也看不见。可能是老沈,也可能是乔栋的父母,或是别的什么人。桥高七八米,本来摔不死的。那颗五角星的一角洞穿乔栋的身体,他惊慌地大叫,四肢张开。试图撑起自己。乔栋妈的尖叫声更大,桥都在震,乔栋血流得更多了。桥上人流拥挤,乔栋的父母被夹在漩涡中央无法动弹。我冲下去,第一个到乔栋跟前。
我感觉我好像要死了,他说。救护车叫了,马上就来,我说。要是人民医院没搬迁,这点距离我应该还有救,我真不想死,他说。不会的,死不了,我说。替我拍张照吧,留个纪念,他说。行,我说。还是算了,现在不太方便,他说。他爸妈跑下来,也帮不上什么忙。乔栋没再说话,可能是吓坏了。他眼睛瞪着头顶的桥,渐渐无神,倒映出死桥残破的身影。无人机再次从头顶飞过,我捡起一块石头扔向它,它居然灵巧地躲开,我不断扔,它却戏谑地来回躲避,最后它玩腻了,飞到桥的另一边。
史载,清朝时人们为了方便灌溉,在百二河与犟河上拦河筑坝,共十处,我的家乡因此而得名。
死桥在乔栋去世半个月后才塌,像多米诺骨牌似的,桥一座座消失。之后我每次经过,心里都憋闷得很。也许,我也需要一根木棍捅一捅,在纸堆深处,火焰还能继续翻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