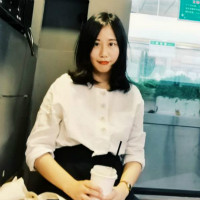1.
半年前,我和雯开始商议去喜马拉雅山一事。我们即将三十,没成为谁的妻子,也不是谁的母亲,更非公司中流砥柱。年少时渴盼的巅峰从未出现,下坡倒是清晰可见。有人说,三十岁后,新陈代谢减慢,身体机能会逐步衰退。为此,我和雯打算去挑战一次极限,但就在我们准备出发时,她忽然住院了。
医院里弥漫浓重消毒药水味,我一度怀疑那是为了掩盖死亡味道。电梯内,病人和家属挤在一起,表情肃穆,仿佛电梯一开,所有人都要奔赴一场葬礼。抵达三楼后,我直奔尽头,在走廊处拐个弯,就是雯的病室。
她住双人病房,病友不在。我去时,房间内安安静静,看起来空无一人。在雯的床位上,被单高高耸起,如雪白山包。太明显了,她总爱玩这种捉迷藏游戏,学生时代,她就喜欢躲在各处吓我,有时是墙后,有时是大树下,而现在,她从白色被单内渐渐露出一个脑袋,大声喊道:“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今天是我俩三十岁生日。三十年前,我们出生在这座城市,出生时间相距不过五个小时。她小学的时候在铁厂的子弟小学念书,初二转入我们学校,因为生于同年同月同日,我们自然成为了无话不谈的密友,命运似乎在某个刹那将我们缝在一起,而今,这线纠缠得越来越紧。我们是朋友里少数未婚未育者,也正是因此,我们从密友变成了战友。
雯掀开被单,扑向我,如小兽般在我身上嗅来嗅去。我命她坐好,然后从包里抽出了一个礼盒,之前开玩笑说要互送礼物,我说送你一个自慰棒吧,她撇撇嘴说让我滚。用一个流行语说,雯是母胎单身,即从娘胎里出来到现在三十岁,她没谈过一次恋爱,没和男人牵过手(小学春游时除外),没和男人接过吻,更谈不上进一步的亲密接触。我说再这么下去,你就距当代女性越来越远了,雯听到这些,总是摇摇头说,忙着赚钱呢,哪有工夫谈恋爱?
我送雯的礼物是一个金属银质按摩棒,说明书上写:铂金闪耀璀璨光芒,三百六十度深雕面部曲线,手感舒适的小巧滚轮,专为女性面部而设计,犹如专业美容师纤细手指抚摸,紧致呵护肌肤,令你重返童颜。我把那按摩棒拿在手里掂量掂量,怎么看都像男性阳具,趁我不备,雯夺过按摩棒,在自己脸上滚了起来,滚了几分钟后,撇着嘴说:“什么破玩意,一点效果也没。”
雯把按摩棒甩到一边,忽然捉过我的手,按在她胸上。我浑身颤抖,想起儿时在电视节目里看过的可怖游戏——嘉宾们围在一起,盖有黑布的玻璃匣子依次排开,里面放着蜥蜴、蛇、老鼠、虫类等,观众可以清晰看见里面的生物,而嘉宾却只能听到众人的尖叫声。他们不知道自己把手伸进黑匣内,会触摸到什么。
雯的伤口处缠着纱布,纱布上还渗有药水痕迹,我轻轻碰了一下,迅速弹开,尽管她强装镇定,但我知道,在手术的这几天里,她经历过一场精神海啸,她必然意识到,自己永久失去了什么。尽管我们安慰着她,告诉她没有关系,只要没有扩散就好,但谁也不知道厄运如果降临在自己身上,我们会如何应对。
胸部。高耸的胸部。那曾是雯引以为傲的身体部位。她长得像她父亲,眼睛小,嘴唇厚,鼻梁塌陷,尽管常年健身,但小腿肚上的肉却永远减不下去,唯有胸部,她没有灌溉,没有保养,却比别人要挺拔紧致饱满。
还没有男人碰过她的胸。
雯的身体如尚未被发现的山林秘境,多年来,无人涉足,没人能领略到这种美。而现在,这座山体忽然塌陷,被移为平地,可能发生的一切瞬间灰飞烟灭。
“没关系的,现在到处都是做义乳的,我去做个假胸。”雯拍拍我说:“做得跟真的一模一样,而且尺寸还能定制,你说多棒。”
我点头称是。想起几日前遇到一位在整容医院工作的友人,对方曾聊起整容趋势,讲三十岁之前的女性喜欢做隆鼻,割双眼皮及开眼角等,而三十岁后,她们更热衷于身体保养,隆胸或私密整形,还有面部肌肤老化的修复……
既然早晚都是要重新做手术的,晚做不如早做。雯拍拍我的肩膀安慰道:“没事,我没事。”而我却几乎要哭出来了。雯从初中起就颇照顾我,在她转学来之前,我因性格懦弱,常受人欺负,甚至被同班男生黑钱,而雯成为我的同桌后,迅速将这些人教训了一遍。我到现在还能忆起那个日光正盛的下午,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雯拽着那些人到我面前说:“不准再欺负她。”果然自那日后,再也没有不良少年来欺侮我,日子好过多了。
好人为什么没有好报呢?
雯的母亲死于乳腺癌,这是一种家族女性难以逃离的遗传病,尽管每年都在体检筛查,但雯还是没能逃脱这种噩运,但幸运的是,发现得较早,癌细胞还未肆意扩散,如果得到有效治疗和控制,存活几率极大。
“这么说来我运气还算好?”雯拍着手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说对吧?”
就在我俩讲话之际,虚掩的门被推开了。来者是汪小娟,我俩初中同学,传说中的班花。岁月待她不薄,不仅未在她脸上刻下伤痕,反而给她增添了一些成熟女性独有的风韵。
雯并不想告诉任何同学她因病住院一事,但护士走漏了风声。护士是汪小娟朋友,两人在偶然聊天之际提到了雯的名字,汪小娟这下把事情宣扬得满城风雨,所有同学都知道了。初中毕业后,同学们各自打拼,几乎已全部结婚生子,生活稳定,有三四个甚至已有二胎,如我和雯这般单身女性,少之又少。我们拒绝参加同学会,那等于变相展现自己的失败,在他人或炫耀或谈论日常生活时,我们像两个小丑,只能躲在暗处窃窃私语。
以汪小娟的姿色,不嫁给有钱人也难。大学毕业不久,汪就在其母亲安排下嫁给了一个富二代,二十五有的第一胎,二十八有的第二胎,一个儿子,一个女儿,凑成“好”字。难得的是她还没放弃自我追求,每日必去健身房跑步或举铁,几乎每天都要晒自己健身或旅游的照片。
人生赢家。这是我们对此类人群的定义和划分。
汪小娟放下那束妖娆花朵,凑近我们两个之间,浓重香水味令我相形见绌,昨夜刚加完班,衣服都来不及换,就奔赴医院,别提在自己身上洒香水了,好几次,我在深夜的办公室累得筋疲力尽,对着镜子里容貌平庸的自己,都会问出一句话:“如果我长得美一些,生活是不是不用这么辛苦了?”
没有如果。命运枝芽已分叉,我们和汪小娟走了截然不同的道路。
雯把我拉过去,偷偷凑在我耳边说:“有没有什么办法,赶紧让她走?”
汪小娟的姿态像慰问灾民一样,仿佛我和雯正处在矿难现场。雯对汪的厌恶还不止于此,早在初中时候,汪就抢了雯暗恋的男孩。那个男孩高而瘦白,篮球打得极好。每天放学,雯都要扯着我去球场看那个男孩打球。然而这样的痴心暗恋没有任何意义,不及美人捧着课本悄悄从男孩面前经过……男孩最终和汪小娟谈了一场从初中到大学的校园恋情,就在我们以为他们会白头偕老成为同学群中的佳话时,汪小娟甩甩手,将那个男孩扔在一边,转头和母亲介绍的富二代走到了一起。如此现实,如此不近人情,如此让雯捶胸顿足。
“时间不早了,让雯子好好休息吧,我们出去喝喝咖啡,坐坐?”我边说边把汪小娟拽离了病室。离开时,我偷偷在门缝处朝雯使了个眼色,用唇语说:“等我回来。”
2.
显而易见,和汪小娟的聊天并不愉快,在近半小时谈话内,她一直在谈论刚结束的旅行,在巴黎,在伦敦,在某座风情万种的海岛。说完之后,又盯着我说:“你最近有什么旅游计划吗?”有,当然有。近一年来,我一直在研究爬喜马拉雅山一事,依网上攻略所说,登八千米以上山峰和乘坐宇宙飞船离地飞行死亡率一样高——都是百分之十几。尽管珠峰自九十年代后商业登山逐步成熟,死亡率较低,但若是遇到意外,常会全军覆没,生还几率近乎为零。
我最终决定去爬安娜普尔纳大本营线,即传说中ABC环线,安娜普尔纳位于尼泊尔北部喜马拉雅终端,环线沿途散布诸多客栈可供游客休息和用餐,经多年商业开发,已成为一条成熟徒步路线,难度中等。从尼泊尔博卡拉出发前往安娜普尔纳大本营,沿途可近观尼泊尔人的神山鱼尾峰及其他诸雪峰日出。
“有什么意义吗?这么危险?”汪小娟捧着咖啡,困惑地盯着我说:“你们两个女孩子,路上遇到事故怎么办?”
我和雯没想那么多。在我们看来,三十岁后的人生必是另一段坎坷之路,走与不走,石头和玻璃渣都已铺满整条路。在此之前,我们想找到一种方式证明自己。这样即使老了,即使满鬓霜白,即使掉光了牙齿,回想起雪峰日出那一刹的美丽,心中还能缓缓淌起一片溪流。
汪小娟不懂,正如我也无法完全理解她的生活。
见过汪小娟后,我开始神情恍惚。这一年来,我关闭了朋友圈,不再看同学们的动态,仅有几次登录,也是为了转发公司新闻。我不想知道他们过得如何,更不希望他们知道我过得怎样。现代生活虚伪如美图游戏,均可以拉伸、变形、美白、瘦身。人人都竭尽全力展示自己完美的一面,而那些覆盖在冰山下的黑暗,无从知晓。
“明明有轻松的地方你们不去,偏偏要选那个难的,自讨苦吃。”汪小娟的话一直在我脑中盘旋,我不知道,生活是否还有得选,如果选了另一条路,未来又会怎样,就在苦思不得时,我接到了邹宇的电话。
邹宇是我的未婚夫,曾经是。
一年半前,我还在每天期待着自己的婚礼,婚礼由我一手操办,从户外选址到婚庆公司乃至摄影公司,都由我精心挑选,我安排做一场草坪婚礼,以精致花束搭建成森林游乐场,来宾手持一张游乐场进场券,券上印有我和邹宇的卡通头像。而就在我筹备正酣时,忽然发现,邹宇出轨了。出轨对象是一个做酒水推销的年轻女孩,身材丰满,腿长肤白,除了着装较为暴露庸俗,其余外貌的确胜我一筹。在此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和邹宇有相似教育背景及相近三观和爱好,然而还是不及年轻女孩对她的轻轻撩拨。在掌握好证据及知晓他们常开房地点后,我带着雯杀了过去。
不,准确来说,是雯带着我杀了过去。
我曾想哭哭啼啼分手就此了事,但雯说不能便宜了邹宇这个大骗子。捉奸夜晚,我和雯穿着黑衣黑裙,戴着墨镜,像两个杀手,冲进酒店。破门而入时,邹宇和那个女孩衣衫不整,我窥见女孩裸露的乳房,像一块椰子蛋糕。忽然就想起邹宇在不同场合嫌弃过我身材不够丰满,屁股和胸像男人,那一刹,我没忍住,哭了出来,哭或许不是因为背叛,而是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因为这种事情而惨败于人。
那天夜晚,我在酒吧里一边喝酒一边哭,想着和邹宇的往事,雯一直陪在我身边安慰着我。那天夜里喝了多少瓶酒最终也忘记了,只记得醒来时,雯已经把热开水递到了我的手边。
邹宇在电话里说:“出来聊聊,地点你定。”
若是之前,我一定会大骂一声贱人,挂断电话,但现在,我的声音先于意识柔和下来,我对着电话说:“好,我周六会在攀岩馆训练,差不多四点左右,你有空就过来吧。”
和邹宇分手后,我又相亲过几次,但那些男人各项条件均不及邹宇。母亲劝我,男人嘛,偷偷腥,总会回来的,浪子回头金不换。我看着母亲,看着她沧桑妥协的面容,想起父亲的出轨,想起母亲认识的那些阿姨们丈夫的出轨,想起他们聚在一起说,没事,在外偷吃归偷吃,能回来就行。
母亲常暗示我,邹宇已是我在这个年纪能找到的最佳婚姻对象,他父母在铁路局工作,工作稳定,退休薪资较高,而邹宇本人也在一家跨国外资公司担任部门经理。母亲说,没有更好的了,你看看,你再这么下去,还有什么挑选余地,这就是一场兔子拔萝卜比赛,好的萝卜早就被人收割殆尽,留下来的,不是烂的,就是坏的。
每周末,我都要来攀岩馆一次,最初,是希望自己在徒步安娜普尔纳能保持充足体能。后来则逐渐演化成一种减压习惯。每次抬头看见那些假的峭壁与山石,总能激起心中逐渐熄灭的斗志。
一开始,我只能爬个三五米,我的手部力量无法支撑身体,每次遇到这种挫败时,我都会瘫倒在练习垫上,想象自己的人生,还没开始奋力攀登,就已经坠落地上。兴许是为了跟自己较劲,我每次去攀岩馆,都要朝上再爬几米。教练会传授一些秘诀与技巧,但能否做到,全看个人,想要登顶,除了多爬多练,别无他法。
邹宇到时,我正在训练。
或许是心里有事,一直状态不佳,手上似灌了铅,莫名沉重,想往下爬,却总觉得有千钧的力在往下扯,爬到一半时,我觉得自己要掉下去了,像悬空在半山中间的人,知道下面是万丈深渊,却一步也不能向前,就在我觉得今天的训练注定要以失败告终时,一股力量将我朝上托举了起来。
是邹宇,他常年保持着健身习惯,手臂坚实而有力,在他的协助下,我终于开始爬到了顶端。
“最近怎么样?”邹宇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感觉你脸色不太好。”
邹宇此次来找我,是为了复合。和我分手后,他迅速和那个洋酒推销女郎分开了,浑浑噩噩时,出去和人约过,也谈过那种三个月两个月的恋爱,他说离开之后才发现,那些女人都是虚的,空心皮囊,只有我,才能真正理解他,对他好。
这番话的确有些打动我,但那夜捉奸的事还停留在我旧伤口上,隐约渗出血迹。为了转移话题,邹宇又问我,最近雯过得如何,他听说雯生病了。在同学圈和朋友圈内,雯的事像一枚炸弹,投下去后,激起巨大余波,人们热络讨论着,表达自己对雯的同情,而大部分人背地里只是在暗中庆幸,庆幸噩运没有降临在自己身上。
“太可怜了。”邹宇说:“真是没想到。”
人们越是可怜她,雯就越是生气。她不喜欢接受怜悯的眼光。她常说,老天不欠我的,我也不欠老天的,该来的总会来,没有什么好躲的。
邹宇感叹了一番后,又悄声道:“听说你们两个想去爬喜马拉雅山,胃口倒不小,但是没个男人,是不是还是不太行?行李都没人提,自己背多重。”
“那总比和男友结伴登山,却被吃了要好。”
在搜集有关喜马拉雅山登山资讯时,我曾看到一条新闻,说是一对情侣二月底赴尼泊尔攀爬喜马拉雅山,最后被登山客发现时是三月九日,此后便失联。两人失踪当日,山区多处降下大雪,造成雪崩,两人一度试图退回海拔较低的河谷地带。在山上呆了近一个月,男方在纳查特河谷被救援人员寻获,而女方则在被发现前三天不幸去世。受困到弹尽粮绝时,女方曾主动对男方说,两人谁先死去,还没死的那个人,就要靠吃对方的肉活下去。最终,男方没有吃下女友的尸体,但我不知道,如果救援人员再发现得晚一些,男人该如何独自在雪山生存,会不会最终耐不住饿,生啖人肉。
“你好好考虑一下吧。”邹宇说:“两个人总比一个人轻松些。”
3.
接雯出院前一天,我再一次梦到了喜马拉雅山,梦到了田野、森林、峡谷、湖泊、溪流、戈壁、灌木丛、冰川、雪山,春夏秋冬不再按照时间而变化,而是存在于同一个时空之中,所有的一切,动态分布在这座最高海拔八千多米的山上。
在我面前,冰雪耸立,山川如巨人卧在眼前,正当我想走过去,仔细欣赏冰川风景时,山忽然坐了起来,那是一个人,一个白色的女人,裸着乳房,头上沾染有片片雪花,我看不清她的脸,因为风雪太大,等我握着登山杖努力走过去后,我看清了她的脸,是雯。
醒来后,我满脸泪痕,说不清为何会在梦中流泪。邹宇发信息说他已经订好了酒店,希望我和他的父母吃一次饭,重修旧好,这或许是一次机会,一次不用费力就能享受到某种更轻松生活的机会。但雯还在医院里,穿着病号服,等我接她,等着和我共进晚餐。
坐车去医院的路上,司机打开广播,调到新闻频道,我本无意听无聊新闻,但忽听主播说到:“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震中位于博卡拉,重烈度区从震中向东延伸……”
我握着手机的手开始颤抖。也就是说,假设,雯没有动手术,那么现在这个时间,我们可能正在博卡拉的某处酒店内。大地崩裂,山川震动,我们还没有抵达所谓的巅峰,就被突如其来的意外劈砍成残破尸体……
我已无意去喜马拉雅。
还不如去海岛,即使不潜水,不做任何危险行动,就那样穿着比基尼,坐在豪华酒店内,捧着一杯冰茶,不好吗?又或者骑在粉色火烈鸟上,戴硕大墨镜,拍一张风靡国外的网红照片发到朋友圈昭告天下自己活得很好,不好吗?
“你就是为了证明自己,所以喜欢逞强。”邹宇的话像刺一样深深扎进我的心里。这么多年来,我没能功成名就到足以鄙视普通人的生活,又没有通过完成普通人的生活而融入集体。而爬喜马拉雅是一种仪式,一种自我求证的仪式,现在,祭坛坍塌,风景消失,一地残渣。
雯拍拍我的肩膀说,出院后,她希望再次启动安娜普尔纳计划,她说这一年来,每次想起雪山日出,都会觉得还有生存下去的勇气与动力。
我摇摇头说,不太想去了,那边都地震了,八级大地震,搞不好以后还有余震,我不想去。
就在这时,邹宇的电话又打了过来,雯清晰地看到了来电人的名字,之前我还写的是渣男,现在已经换回了邹宇的本名。
“他来找你复合了吗?”雯神色黯淡,似乎猜出了什么。我说对,邹宇回来找我了,他让我考虑一下。
“那你怎么想呢?”雯盯着我说:“所以,你在山和邹宇这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
我没有回话,空气一时安静。雯拿过我整理好的包说:“我明白了,你去见邹宇吧,剩下的,我自己来。”
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是个彻头彻尾的观光客,只不过隔岸观火看了一场灾难片,而雯是被夺去了一部分肢体的幸存者,她已独自承受了一场肉眼不可见的大地震,这地震自地壳深处而来,已将她残留的雪峰、山林尽数瓦解。我们现在拥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身份,已不可能平静对谈。
我没有挽留雯,也意识到我们可能会就此走上两条截然不同的路。雯没有说话,推开门,独自离开了病房,我嗅到消毒水的味道越来越浓,弥散在房间每个角落。
4.
我最终还是赴了邹宇的约,但席间交谈并不开心,邹宇父母像买猪肉一样把我打量了一番,又提及邹宇表姐最近刚生了孩子一事。看得出来,他们不是想要一个儿媳妇,而是急于找到听话的生育皿。
彻底和邹宇断掉后,我打算和雯好好谈谈,但她音讯全无,似乎故意躲着我。她离开了过去的公司,原因残忍,老板认为她身体抱恙,无法专心工作,流言像癌细胞一样在同事之间扩散,有几个刚入职的年轻小姑娘甚至说,看吧,到了一定年纪不结婚,就容易得这种病。
我也去过雯子的家,但那片老房子正在拆迁。我想起初中时经常上她家玩,那房子只有三十来平米,小且局促,转不开身,雯没有单独卧室,夏天总是弄张凉席睡在客厅里。工作七年后,她贷款买了一套小户型,希望和父亲分开住。还贷款时她脸上没有那种普通年轻人的哭丧嘴脸,总是开心地说:“姐也有自己的房子了。”
她到底有没有提到过要去喜马拉雅山的事呢?
我忽然想起,在半年之前,我们热络坐在某烧烤摊内,雯一边吃着羊肉串一边说,她对怎么过生日没有任何主意,全看我的意思。
“你是搞策划的。你说了算。”
也就是在那时,我忽发雄心壮志,想去征服喜马拉雅。实际上,也并不是想真正地登上山巅,而是希望在抵达的那一刻,能拍下照片,发一张朋友圈昭告世人我竟可以征服这座高山。
雯到底去了哪里?
有人说,雯或许是隐居某深山治病去了,也有人说,她是去了博卡拉。我不知道哪条消息是准确的,只是希望她还能再次完好无损出现在我面前。
抱着最后一丝希望,我给她写了一封邮件,邮件里写了一句话——“montains may depart.”这句话出自以塞亚书,全文的意思是“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爱必不离开你”。
我在邮件里写下了见面地点与时间,希望她能在那一刻出现。
约定日到来时,我去得极早,一直在咖啡馆里坐着,心怀忐忑。等了一小时后,门口终于出现一个白色影子——是雯,她黑了,也瘦了,像去了一次热带地区,整个人如脱水过一次,精神,干练。
“你去了哪儿?”
雯说她哪儿也没去,只是搬到新的住处,一边找工作,一边刷纪录片,看了上百来部,全是有关幸存者的,有些是大屠杀中活下来的犹太人,有些是二战中失去双腿的老兵,有些是飞机空难后生还的乘客……
然后呢?
雯捧着桌子上那杯雪顶咖啡,双手环绕杯壁,那一小撮冰淇淋做的雪山便在我们眼前耸立起来。我再度想起了田野、森林、峡谷、湖泊、溪流、戈壁、灌木丛、冰川,还有那场可怖的雪崩。
雯舔了一口“雪山”说:“活着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