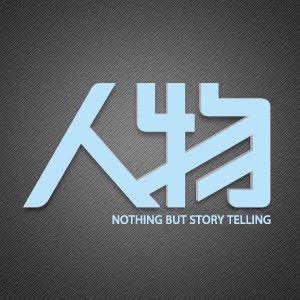1.
经过一夜的飞行,我在早春的清晨抵达伊斯坦布尔。在机场外抽了根醒神烟,然后便跳上开往塔克西姆的大巴车,开始了我在土耳其的短暂生活。
土耳其只是这段旅程的中间站,夹在伊朗和埃及之间,留给它的时间并不多。临出发前收集资料的过程中,我无意间读到一本名叫《纯真博物馆》的小说,作者是写了《我的名字叫红》的帕慕克。
令人意外的是,正是这本偶遇的小说,和由作者本人建立的真实的同名博物馆,让伊斯坦布尔变成了一个难以言喻的城市。
帕慕克在书中讲述了一个有些伤感的故事:男主角富家少爷凯尔默虽有婚约在身,却依然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18岁的芙颂,并和她偷偷约会。这段恋情持续了一个半月差两天,直到芙颂在凯尔默订婚前决定离开。凯尔默悔婚,耗尽一生追寻芙颂,却没能再度将爱人拥抱在怀。他陪在芙颂身边的八年间,搜集了一切芙颂用过、摸过的东西,将它们据为己有。在芙颂死后,凯尔默建造了这座纯真博物馆。
小说中始终以第一人称(凯尔默)视角来描述故事,并且在最后一章加入了凯尔默委托作者写这本书的情节。同时,书中每一章节提到的重要物品——小到照片、铅笔、收据,大到绘画、家具,全部都按顺序陈列在博物馆中。帕慕克走遍世界找来如此多的“物品证据“,让人难免会相信了这场虚构的真实。
可以说,这座纯真博物馆将整个故事,以及那段时期的社会风貌,甚至弥漫在过去岁月中的空气都真实的封存了下来。
这种有些变态的执着,让人充满好奇。

2.
从塔克西姆巴士站走到青旅还有一段距离。迎着清晨的海风和打扮入时的中学生擦肩而过,街边的破房子看起来像是旧伦敦,但肩上的行李以及飞行的疲劳让人无心欣赏,我后来才意识到这就是帕慕克在书中提到的老伊斯坦布尔贫民区。在密密麻麻的小巷子里穿来穿去,走了不知道多久,濒临崩溃时,却一头撞见了这座纯真博物馆。

博物馆所在的那座红色小楼是书中重要的场景载体,它既是芙颂矗立在贫民区的狭小的家,也是凯尔默在试图追回芙颂的八年间无数次拜访过的地方,更是芙颂死后凯尔默的栖身之所。
比起其他来探访博物馆的忠实读者们,我实在幸运很多。不少人特地赶来拜访,却在楚库尔主麻的小巷中陷入怪圈,兜兜转转才能在楼与楼的缝隙中找到它——尽管外墙翻漆了砖红色,但它狭长的形状实在不易被发现,就像一本书,只有书脊的部分展示在街上,除了楼侧悬挂的红色旗帜上写有纯真博物馆的字样,再没有更多的标示。

《纯真博物馆》这本书中有一个有趣的细节,男主人公凯尔默在讲这个故事时告诉作者,他希望这本书的读者能够有一个免费参观的机会,并且书中也确实印着一张一次有效的门票标识。
我带着一本中文版忐忑地走向售票处,心想着要如何向工作人员解释他们看不懂的中文译本。然而担心实在多余,售票处的女士似乎已经对被翻译成各种语言的小说习以为常。她带着“谢谢你的前来“这样温柔的微笑,在书上的门票位置盖上一个芙颂蝴蝶耳环形状的印章,放我这个紧张的读者进去了。

3.
“究竟什么才是爱?“凯尔默在书中问道,”与芙颂相恋的那一个半月差两天,我们共做爱44次。从芙颂消失那天算起,339天后,我终于再次见到了她。这之后的整整七年十个月,我为了看芙颂、吃晚饭去了楚库尔主麻。其间一共是2864天,409个星期,去了他们家1593次。在我去芙颂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我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我爱芙颂,也爱她爱过的,甚至是触碰过的一切。我悉数收集起那些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发卡、烟灰缸、耳坠、纸牌、钥匙、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等等,将它们放入了自己的博物馆。“
我不相信纯爱,在阅读的过程中,凯尔默对芙颂的感情在我眼中更像是由人性中难以规避的缺憾造成的自私、狭隘、毫无廉耻的求之不得。
走进博物馆大门,右手边是一整面钉着芙颂抽过的烟头的墙——那4213个烟头。几乎每个烟头旁,都有小小的手写文字,纪录着它源自芙颂生命中的哪个瞬间——她在饭后的短暂消遣,或她在小酒馆小酌后倾吐的烦恼,每一个快乐的或不快乐的平凡日常。
站在这面墙前,回想起凯尔默总结的关于芙颂的一切数据,想像他在这里拿起墨水笔小心翼翼地,不用搜肠刮肚就能轻易想起每个烟头的来历,气定神闲又饱含爱意地写下短语。这些脑海中无法控制的画面,和凯尔默那份近乎变态的偏执就这样裹卷在一起,迎面击中了我。

这面墙的左手边,是另一面钉着九个显示器的墙,循环播放着女孩抽烟时手部动作的影像。场景中没有声音,也没有人,每一段只有十几秒。在这些动态影像中,染着深色指甲油的纤长手指夹着烟,好像在随着主人的谈话情绪做出下意识的小动作。烟灰缸的形状也在不断变化着。
她的手有时看上去很俏皮,有时似乎懒懒的想要摆脱谈话,有时又好像在表达无奈的状态,当然,还有开心时挥动香烟,让烟尾在空气中颤抖地打转。我暗自揣测着芙颂点燃和掐灭每根香烟时的内心戏,没有人说影像中的人就是芙颂,但在这座博物馆中,一切美好的源头都应该是芙颂,没人能够反驳。

静态的烟头墙和动态的“制造烟头的过程”影像交织在一起,通过视觉编织了一张细密的网,让人忍不住相信故事的存在,所有对于小说的真实性的怀疑在这样步步紧逼的证据面前开始动摇,整个虚构的故事因为这座博物馆而过于真实。冷颤从后脑勺一路蹿到尾骨,我被这种缜密的、美好的固执钉在原地,动弹不得。
4.
除去作为纪念品店的地下室,博物馆共有四层展区,逃过那面烟头墙的追捕后我走向二楼,才正式开始了当天的“找物品游览“。
书中共分了83章节,每一章节提到的物品被放在一个标有该章节数字的木格子中。馆中少有大型照明,在昏暗的环境中,观众被小型聚光灯带来的暖光吸引,走近一个个格子,走进帕慕克为读者介绍的老伊斯坦布尔的生活。

馆中的空气像是来自旧时光,从1975年缓慢流动至今。没有人说话,我甚至连大声喘气也不敢,生怕搅乱了作者努力建造的、能将观众短暂拖回小说中所描绘的上世纪伊斯坦布尔美好生活的时光机。走在其中,像进入另一个世界,外面的一切已经无关紧要。
出发前我读了两遍书,将所有书中提到的物品都标记出来——芙颂穿过的黄色高跟鞋、使凯尔默和芙颂邂逅的仿造名牌皮包、芙颂遗失在他们幽会的秘密小楼中的蝴蝶耳坠、凯尔默当着芙颂夫妇的面偷走的汽水瓶……在这狭长的展示空间中,我目睹着所有引起过我好奇心的物品,和那些原本我并不注意的物品一起被好好保存着。那些文章中无意间提到的请柬、驾照、小猪摆件、破旧的玩偶胳膊、动物尸体模型、徽章、邮票……所有能够将小说从二维的想象拉入三维世界的证据,都被帕慕克以凯尔默的名义收集、展示出来。

参观的过程是艰辛的,我翻着书,逐条逐件地分辨眼前的物品在书中出现的位置,再仔细欣赏它们的外观,甚至将在意的物品样子以自己的描述批注在书上。身边陆续有观众在移动,也有和我一样携带实体书前来的读者。完成对章节物品区的参观时,回头看看其他淡定的观众,我才感到自己的行为偏执得令人发笑,和凯尔默同样,病得不轻。
整座博物馆的参观已经过了大半。沿楼梯爬至阁楼,能够拜访的只剩下凯尔默度过后半生的小屋。一张床,几条旧毛毯,一把木质椅子,台灯、床头柜,属于凯尔默童年的儿童三轮车,几样简单的物品就能堆满这十平方不到的小小阁楼。书中说,失去了芙颂的凯尔默再也没离开过芙颂生长的小楼,并在这里将自己的一生以及关于芙颂的回忆讲给了作者。

5.
站在阁楼,我忍不住去想,凯尔默和芙颂之间的感情是爱吗?在他们初次邂逅的一个半月差两天中,他们拥有的44次夏日午后的做爱是真实的爱,没有关上的窗户,风吹动窗帘,远处孩子们的玩闹声音飘进耳中,这甜蜜和遥远的体验是美好的爱。
但爱不过只是爱而已,爱与爱也并没有区别。当凯尔默意识到他再也无法和芙颂在一起时,那八年时间中,我能够认为他仍然像最初一样只是沉浸在爱中吗?
曾经在怀里挂着的、张开双手也掉不下去的东西有一天带着高傲的心从此远离,并像看蠕虫一样轻蔑地望着你,对待傻瓜一样的利用你时,人类心中那种难以忍受的征服欲会沿着爱进化的荷尔蒙冲进脑腺体,造成无可避免的痴汉行为。
凯尔默是痴汉没错,在无可救药地思念芙颂时,他会伸长了舌头去舔嘬芙颂用过的尺子,撅着大嘴亲吻芙颂抽完的烟蒂,收集关于她的一切。但是因为凯尔默本身富家子弟的身份,使这种变态的情感又带着绅士的优雅。整个博物馆里弥漫着用天鹅绒遮盖面部一般的窒息感,昏暗的灯光,小格子承载的物品,都领着观者在不知不觉间走进一段感情最深处所昭示的人性弱点。

从始至终我都认定早在芙颂第一次失踪时,她对凯尔默就不再有爱情了。凯尔默的母亲说芙颂是“非常贪婪,非常骄傲,非常自负的女孩“,虽然严厉,但不无道理。
芙颂应该是“有点贪婪,有点骄傲,有点自负的女孩“,她短暂的生命和存在于70年代伊斯坦布尔贫民区的灵魂是超前的,她会踩着黄色的高跟鞋雀跃地与情郎幽会,在青春最饱满的时候享受肉体的快乐,做着不切实际的明星梦,并且勇敢地追求梦想,不惜利用身边所有可利用的资源。
她是我们身边那些有点小聪明的笨美人,她们知道自己的美丽,并会利用自己的美丽,当意识到无法得到凯尔默关于婚姻的承诺时,及时地抽身而去,快速打扫自己的心情,重回战场时,昔日爱人已成为她眼中的人生踏板。剩下凯尔默一个人困在人性最可笑的贪恋中,像傻子一样无法自拔,毫无保留地将无法得到的感情供奉神坛多年,通过收集爱人碰触的物品聊以慰藉自己膨胀、饥渴的欲望。

至于我,只是这样和凯尔默一起消费着芙颂的“好“,渴望着视人如草芥的高傲的灵魂,像变态一样爱世上所有变态的人、事、物。
离开前我再次站在那面烟头墙前,一度试图数清是否真的不多不少刚好4213个,数乱三次后,我逗笑了自己,也终于从那种蔓延了几小时的窒息感中抽脱出来。
有人说作者帕慕克经常假装成普通游客,潜伏进参观者中,观察来访人对这座博物馆的反应。
我试图假装帕慕克站在我身边,凯尔默和帕慕克的身影、视线重叠在一起,我终于让自己彻底分清了虚构和现实,我意识到这座博物馆中珍藏的一切都是真的——小说中的情节是假的,但感情是真的。故事是虚构的,但那些物品都在证明,1975年伊斯坦布尔这座城市就是像书里写的一样在流转着,上流社会和贫民生活悬殊的差距;人们的生活充满着电视机,汽水,明星画报,香烟;凯尔默们和芙颂们经历着爱情、分手、婚姻和失败。
纯真博物馆的名字没有起错,它也许代表了凯尔默对芙颂拼尽全力的渴求是纯真的;也许是想证明70年代的伊斯坦布尔是纯真的;又或者是作者本人借由凯尔默的叙述对自己生长的旧土耳其表达出纯真的爱。而此时此刻的我,只是乖乖地抱着写满标注的小说,带着神秘的痴汉微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这座红色砖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