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密斯船钟
文/金宇澄
我师傅姓秦,钟表厂八级钳工,额角戴一只钟表放大镜,讲宁波口音上海话。一九八〇年代初,上海尚有无数钟表工厂,我随秦师傅踏进车间,眼前一排一排上海女工,日光灯下做零件。秦师傅说:“我师傅的师傅,以前叫‘外国铜匠’,等于我‘外国师爷’,这个赤佬爷爷讲过,中国人,最最了不起,发明一双筷子,象牙筷,毛竹筷。外国,有一座阿爱比思山,四十年前大雪封路,有个外国农民怕冷不出门,手工锉了一件‘擒纵轮’,厉害吧。外国乡下人厉害,每家每户,备有什锦锉刀、小台钳,家家农民做金工、刻工,开春阶段,收集邻里手工零件,眼睛一眨,老母鸡变鸭,装出一只三明一暗玻璃门八钻自鸣钟,想想看,天底下有这种怪事体吧。”
这段言论让我记得,我最熟悉的地方,不是上海,是东北。我到东北农场混过7年饭,经常大雪封路,大兴安岭,雪灾一场接一场,我当时做泥水匠,落了大雪,也要走家串户,修烟囱,修火炕,但即便我当初再卖力,也不可能想到,可以手工锉一只生铜“擒纵轮”。中国人不会有这种怪习惯,每家每户,炕桌上面摆一只笸箩,放一叠卷烟纸,十几张黄烟老叶,看不到一把锉刀、一只台钳……雪实在太大了,这种天气,东北人是“猫冬”了——烤火,卷根黄烟,吃开水,吃瓜子,嚼舌头。
直到我回了上海,调到厂里,踏进钟表世界,不管生张熟魏,人人懂得校快慢、擦油、理游丝、调换钟表面子、点夜光粉。工余时间,我翻开一本破书,怕别人讲钟、讲表,怕听滴滴答答声音。周围师傅师妹与我相反。印象比较深的是,秦师傅搬来一件东德GUB精密天文航海船钟,引得外车间不少人围观,议论纷纷,这座小钟,外套精致木盒,钟身、钟盖均是铜制,密闭防水厚玻璃,夜光读数,附带万向支架,即使船身历经超级风浪颠簸,摆轮一直保持水平运作,相当稳定,包括机芯、秒轮,结构极特殊。至于航海钟带进厂内的前因后果, 包括之后车间陆续出现其他船钟,“报房钟”、“船舷钟”等等,具体记不得了,我只学到两个中国字:“船钟”。
一九八〇年代初,香港开始渗透新式电子钟、电子表,本地钟表业走低,国企大量生产电风扇、洗衣机,无限制需求机械“定时器”,秦师傅因此调入“定时器研发组”。有一天,秦师傅对我讲:“大地在颤抖,空气在燃烧,暴风雨就要来了。”语气重点是“暴风雨要来了”。这句有名电影台词,外国地下党名言——南斯拉夫某某老钟表匠面对镜头,讲了这一串接头暗号,意味深长,背后满墙挂钟,发出滴滴答答声响……
造机械“定时器”,零件不算多,也千头万绪,厂内早年进口的瑞士钟表机床,匹配专业零件,难以转为他用,钟表业极其陌生的“注塑”模具,按常规金工来做,无法达到精度,面临情势是,厂产钟表,销售下滑,自做“定时器”,达不到行业要求,不少专业大厂,开始进口“定时器”……一切变化,就是秦师傅宁波普通话预测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以后,再以后,这些厂,这些师傅们,全部消失了。我做了编辑。
二〇〇〇年,我推门走进长乐路一家古董店,壁上三只船钟,让我头晕眼花,店主敬我一支烟,搭讪道:“海上强国,英国牌子史密斯 SMITHS;高精度有美国货,当年做两万三千只汉密尔顿HAMILTON天文船钟,全部装备海军;苏联货色 CCCP,铝壳,白壳子,卖相难看一点,其实是战后吞并东德技术,抄东德 GUB 牌子,也不错的。”
我脑子里,忽然听得秦师傅宁波普通话,“暴风雨就要来了”……像我重回车间,秦师傅讲:宝塔轮,十二钻,不锈钢棘爪,鸡嘴弹弓,厚夹板,五十六小时……混进了店主的声音。
我念经一样答复:“夜光读数,抗冲击,抗摇摆……”店主说:“前天卖脱了一只赞货,钢蓝秒针,时分针嵌金。”奇妙莫名。这一天,我最终买了SMITHS船钟。记得秦师傅讲过,SMITHS 有调整精度“快慢夹”小窗,眼前这一个,即使调到最慢,全天也快了一小时,可惜我这个曾经的徒弟,至今不懂“擦油”。店主讲,目前擦一次钟油,市价四百。唉唉,我不算秦师傅徒弟了……
去年路过乌鲁木齐路某旧货店,一位潦倒老先生,夹了一件哥特式老黑座钟进门,店主开价三百二十,老先生还价五百,店主不允。我走来走去,期待老先生带钟出门,我想跟到店外开口说,我可以出五百……但我同时自问,买了钟,我以后呢,我不是南斯拉夫老地下党,罢了。走出店来,我想到了秦师傅。
旧钟的记号、钢印、标识、油漆特征、底盘式样、钥匙,提手,样样沧桑。我曾经的熟人,台词、机器、画面、回忆,全部隐退了。上海是一块海绵,吸收干净,像所有回忆并未发生过一样。
故乡的酒
文/贾樟柯
我是山西汾阳人,当地有个说法,所谓“黑白两道”。黑是指煤,白指白酒。有时大家相互开个玩笑,就说,我们山西人就是要黑白两道。白酒是汾阳的支柱产业,也是人际关系里相互沟通的重要方式。我跟酒的交道打得很早,据妈妈说,应该是五岁之前,来家里做客的朋友,用筷子蘸了酒给我喝,结果呼噜了一下午。差不多开始偷偷跟朋友喝酒应该是高中开始的,在那样一个封闭的县城里,最快乐的事,就是大家坐在一块喝酒。最夸张的一次是全班所有的男生,周末带了菜,在教室里喝酒聊天。县城成长起来的孩子,对酒很感兴趣,对赌 也感兴趣,所以我们有句话说,酒越喝越厚,钱越赌越薄。我很怀念中学时代那些喝醉的时光,它代表我们对未知和未来的惶恐,那时我们一无所有,能够感动彼此的只有友情,它让我们对这个世界不那么惧怕。
我偏爱这些翻涌着情绪的时刻,爱下一刻的茫然未知。我所拍摄的电影,很多根本不是计划的结果。对我来说,一部作品的产生必须开始于剧本的写作。想要表达的愿望会在某刻变得强烈。摊开稿纸,打开电脑,但仿佛迷失了。我能感觉到我正在召唤我自己,另一个我在告诉我,要倾听自己。我并不是个痛苦的人,生活中倒是总很容易释然。然而那种焦灼,是一种在庸常生活中突然遭遇诗意的渴望。坐下来,用影像去遭遇那种诗意。那种感受一时很难用言语表达。所以我觉得,阅读和写作是人应该保持的生活习惯。它们不应该被认为是职业性的活动。它是人类普遍应该拥有的生活方式,当我们不阅读时我们有很多局限。事实上我们突破不了自己的局限性。那么,阅读不同的书籍,实际是跟不同的头脑交流。生活时常将我们隔离在一个理解情感自我的过程之外,阅读和写作是理解自己内心情感的途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了解、感受自我的需要。所幸我自己一直在保持阅读和写作的习惯。
我的电影有一个特质,是在关注变化。我觉得这种特质不是我所独有的,而是一种人类的普遍。人类一直在变化,所有那些有生命力的艺术家,不管是什么年代,都在质询着这个世界的变化。从历史的维度上去理解创作,敏感的创作一定面对时代的变革。比如小津的电影里充满了那时的变革,包括物质,包括新科技给人带来的影响,铁路,发电厂,还有战后日本社会的迷茫。这种对于世界的敏感,在我最初的生命体验中,来自于大自然,我觉得人应该少惦记人的东西,多看动物,看万物生长,看春去秋来,关注过这些东西,感受过这些东西,就比较容易爱自由,再跟人相处,就比较容易平等。我的家乡不是什么典型意义上的山清水秀,但从小还是保持了跟自然的紧密连接,县城很小,没太多娱乐,在旷野里躺着看云飘一下午,就是特别大的娱乐了。
大概两个月前,《中央车站》的导演沃尔特·塞勒斯来拍摄关于我的纪录片,他跟我一块回到我的老家。有天晚上,我请好久不见的老朋友吃饭,他也跟着一块去了。我们喝酒,喝很多酒:汾酒、竹叶青和红酒掺着喝,最后大家都醉了。这场聚会最后演变成一场热泪盈眶的打架。巴西导演紧张坏了,问我说,你为什么不制止呢。我回答他,因为大家打得都很愉快,这就是我们沟通感情的方式。
指挥棒
文/谭盾
这根指挥棒是我二十多年前在波士顿买的,它的棒体用芦苇秆制成,手柄部分用的软木,拿在手上很轻,但挥起时却能让观众感受到它的分量。我第一次用它指挥是与马友友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合作,这一拿就是二十多年,用到现在。
这根指挥棒凝聚了我从小学到读完博士,二十七年学习的心路历程。我在中央音乐学院学习的是双专业,指挥和作曲,跟随李华德教授学习指挥、赵行道教授学习作曲,去美国留学时,又受教于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后来成为职业作曲家后,发现自己最为崇拜的还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那些指挥作曲家,比如马勒和伯恩斯坦,前者的《大地之歌》,后者的《西城故事》,他们所有的作品基本都是当代最有影响力的作品。还有法国作曲家拉威尔、俄国作曲家斯特拉文斯基,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指挥家,同时也是作曲家。我自然也希望自己的 作品能由自己来指挥。
在指挥方面,我无疑是幸运的。因为我在作曲方面先成功了,所以当我可以自如地以作曲家的身份和世界上顶级的乐团合作时,他们也会邀请我去做指挥。我第一次用指挥棒是从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开始的,第二次是费城交响乐团。一般而言,指挥家的道路是从下而上的,先从中学的合唱队开始,再到城市,继而到国家,最后成为世界级的大师。而因为作曲,我幸运地从开始就指挥了世界顶级乐团。
我记得第一次指挥波士顿交响乐团的时候,乐团总经理跟我说,你可以闭着眼睛想象这个乐团是一条河流,你不要去改变河流的走向,但是你要让自己在这条河流中间流得更自如,而使得这条河流更漂亮。这句话实在精彩!我常常是拿起指挥棒时要去感受手中无棒,在手中 无棒的时候要感受心中有棒,这种“有”与“无”的辩证是一种强烈的道家意识和禅宗意味,就像老子说的“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我的指挥和老庄、禅宗有关,这让我对于指挥棒的使用非常敏感,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也是我个人非常珍视的音乐的信仰。
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的生活每天都和这根指挥棒息息相关。它对于我来说就像李小龙的三截棍,或者武僧手中的少林棍,是内部心灵与外在舞台的桥梁,也是自我和大众之间的桥梁,更是我的音乐从灵魂走向大自然的桥梁。从音乐的角度来说,无论是变化多端的风格、层次复杂的哲理、东西文化的融合,其实都跟使用这根指挥棒的风格、技巧有关。比如说用这根指挥棒指挥法国印象派的音乐时,它就会变得飘逸而阳光;当它用来指挥贝多芬的音乐时,会让人觉得刚柔相济、命运多舛;用来指挥我自己的音乐时,就会有瞬间的时空转换感,从黄土高原到楚国蛮疆,从江南丝竹跳到北方的紫禁城。
嵇康说,声音没有哀乐之分。声音之所以成为音乐,是因为内心有感触,这根指挥棒在普通人挥舞的时候自然是没有音乐的,但是在我手中却不一样,它传递的是内心深处的能量。
本文选自《珍物:中国当代文艺百人物语》
珍物
责任编辑:卫天成 weitiancheng@wufazhuce.com
作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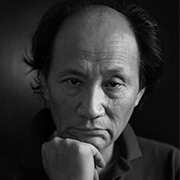
|
金宇澄
著名作家,代表作《繁花》。
|
|

|
贾樟柯
中国著名导演。
|
|

|
谭盾
中国著名音乐人、作曲、指挥。
|
|
点击可下载ONE一个app |




